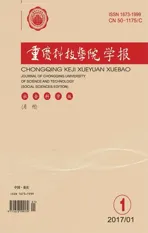“11·27”大屠杀前的营救行动初探
2017-03-22王浩
王浩
“11·27”大屠杀前的营救行动初探
王浩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台湾前对关押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的革命志士进行了集体大屠杀,共有200多人殉难。在大屠杀前,狱内外一直在进行各种营救行动。狱外的川东地下党对关押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革命志士并不是坐视不管,而是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从1949年7月起就通过采取“花钱买人”“走关系”,甚至试图武装劫狱等方式积极实施营救;狱内的革命志士也不是坐以待毙,而是通过运用策反看守、狱医、警卫连连长等方法积极进行自救。
重庆军统集中营;集体大屠杀;狱内外营救行动
1949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台湾前夕,对关押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处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实施了系列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血案,杨虎城、江竹筠、许晓轩等人在屠杀中殉难。系列大屠杀起于9月6日,止于11月30日。在这一系列大屠杀中,尤以1949年11月27日至28日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最为惨烈,死难人数也最多,共有200余人殉难。实际上,在大屠杀前,监狱内外的各种营救行动就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目前,由于资料匮乏等原因,学术界还没有对大屠杀前监狱内外的营救行动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研究。面对这一研究空白,笔者在查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大量B类档案、烈士档案以及采访知情人士的基础上,从狱外和狱内两条线对大屠杀前进行的各种营救行动进行详细、系统的考证,并试图通过考证还原历史真相,以便更准确地向人们宣传“红岩”历史。
一、狱外:川东地下党组织的营救行动
1949年7月,川东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在重庆市市中区(现渝中区)临江路45号天瑞公司召开会议,会议由刘兆丰主持,卢光特、李陪根、李治平、熊扬和蒋仁风等人参加。会议总结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即将崩溃,在溃逃前有极大可能对关押在军统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等处的革命志士进行屠杀。因此,决定“在不放弃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用贿赂和金条购买等方式营救个别被关押战友的同时,还应积极做好准备,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进行劫狱。”[1]771949年9月,江伯言受钱瑛的派遣回到重庆,向川东地下党传达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着重传达了钱瑛同志对川东特委的要求:“千方百计把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营救出来,需要用钱买的就花钱买。”[2]423接到上级的指示后,川东地下党正式决定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营救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的革命志士,营救任务“具体由特委委员林向北负责”[1]77。
(一)营救前的讨论
接到任务后,林向北马上向自己联系的地下党员进行了传达,并组织大家商量营救方法。商量对策时,有同志建议派人回到起义的地方去动员一些人来,找准时机武装劫狱;也有同志建议策反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行动组长漆玉麟,甚至有人提出“做做徐远举的工作,把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3]253。与会同志救人的心情非常强烈和迫切,讨论也很激烈,但这次讨论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营救方法。
(二)第一次打入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无功而返
党组织交给林向北如此重大的任务,使他倍感压力,但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使他时刻在思考如何营救。正当林向北绞尽脑汁想办法时,有一天,参加过川东武装起义撤退到重庆的徐荣恒突然找到林向北,告诉他自己在磁器口碰到中学老师贾佐。贾佐现在已“弃文从武”,在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当中队长。这次偶然相遇,徐荣恒还得到一个重要消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正在招新兵。贾佐得知徐荣恒处于“待业”状态,建议徐荣恒去报名。为此,徐荣恒找到林向北,向他请示能否前去报名。
经过一番交流,林向北还得知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又称志农部队,是一个武装特务组织,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的警戒任务。中队长贾佐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中央特科搞过情报工作,还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中断了与组织的联系。
林向北觉得这是一个营救的大好机会,他当即要求徐荣恒利用与贾佐的师生关系,打入志农部队,摸清贾佐的个人情况,同时深入打探部队信息,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更多的同志进入该部队。通过交流,林向北了解到贾佐急切希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非常愿意配合将地下党的同志安排到部队的重要岗位。随后,林向北安排文伟、曹志固等4名同志在徐荣恒的带领下打入交通警备第一旅,在贾佐的帮助下被“安排在关键的位置上”[4]335。林向北计划利用这支部队作为营救革命志士的武装力量。
正当营救行动有序进行时,一场意外使这次营救行动被迫中止。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中队长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很多人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有的人甚至对贾佐在任中队长之前的经历产生了严重怀疑,并秘密进行调查。有着丰富特工经验的贾佐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随后悄悄离开了部队。贾佐的突然出走,使徐荣恒等打入交通警备第一旅的同志只能撤出,这次营救行动被迫中止。
(三)第二次打入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有所收获
徐荣恒等人从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撤出后不久,川东地下党又找到一个机会打入该旅。9月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地下党员张平河在磁器口看到一张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招收新兵的布告。张平河立即将这一信息报告给林向北,并告知自己可以找到关系打进这支部队。经过研究后,林向北同意了张平河的计划,同时要求张平河多带几个同志进去。
随后,张平河通过“小学同学陈立群的亲友蔡遐欧的关系”[5]30,和陈立洪、杜文举先后打入了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干训班,当不拿军饷只管饭吃的勤务兵和传令兵。据陈立洪、杜文举后来回忆: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干训班是专门训练潜伏特务的,有300多人,住在渣滓洞斜对面的五灵观立人山小学内,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经常到这里讲课。
鉴于张平河等人是勤务兵和传令兵,行动相对比较自由,因此,林向北要求他们摸清军统集中营内的情况,“绘制一张详细的地图”[3]257,以便于研究营救行动和制定营救方案。
得到上级的指示后,张平河、杜文举和陈立洪立即讨论如何完成绘制地图的任务。为了安全起见,3人决定共同绘制地图,把兵力部署、岗哨设置等关键问题记在脑子里,找地方把地图绘制好后交给杜文举,再由杜文举交给党组织。明确任务后,3人利用给长官打水、买东西等机会,绕道去白公馆、渣滓洞、阅兵场等地了解情况。有时,他们还故意走错路,到处转悠。经过近2个月的摸查,3人绘制好一张一尺见方的地图,上面标明了军统集中营内部的兵力布置、岗亭哨所、营房住地等信息。1949年11月中旬,陈立洪将绘制好的地图交给了林向北。
正当杜文举等人绘制好地图准备下一步行动时,他发现干训班的课程表上有一名教员叫邬竟成。杜文举曾经和邬竟成见过一面,他怕自己被邬竟成认出来,身份被揭穿,就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干训班。陈立洪和张平河坚守在干训班,但由于两人力量有限,直到大屠杀前也没有找到可行的营救方法。
(四)试图掌握二十四兵工厂警卫队
二十四兵工厂离渣滓洞监狱很近,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渣滓洞的某些角落,如果能控制该厂的警卫队,就能增加营救的可能性。恰巧,地下党员张平河的哥哥张平江在二十四兵工厂当工人,又是一名进步群众。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很多同志撤退下来就到张平江家里掩护。林向北希望张平江在厂里广交朋友,搞好与身边工友的关系,特别是要和警卫队搞好关系。之后,张平江通过工友结识了二十四兵工厂警卫队副队长,成功使两名同志打入了警卫队,其中一名同志还当上了机枪手。
林向北等人计划在完全掌握二十四兵工厂警卫队后,利用有利的地形封锁渣滓洞哨所里面的守敌,再派另一支队伍进去营救。正当他们按照计划推进时,二十四兵工厂警卫队被抽调去对付人民解放军。事发突然,打入二十四兵工厂警卫队的两名同志被迫撤了出来。
(五)策反国民党“反共保民”军第一师师长廖开孝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贵州,直逼重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把主力部队都调到南岸设防,城里只剩下“反共保民”军第一师负责维护社会秩序。这支部队由重庆市里的工商业从业人员组成,根本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和解放军形成直接对抗。林向北等人觉得这是一个策反师长廖开孝的绝佳机会。因此,林向北和蒋仁风等人商量,决定委派蒋仁风去做廖开孝的策反工作。
蒋仁风和廖开孝见面后,明确提出3点要求:一是解救军统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二是国民党败退时,尽可能地维持社会治安;三是配合解放军解放重庆。廖开孝知道国民党失败的结局在所难免,答应了蒋仁风提出的后两点要求,但以军统集中营里地势险要以及“反共保民”军第一师没有战斗力为由,拒绝了营救。
(六)收买国民党“中国新闻社”社长袁建之
林向北的妻子廖宁君及岳母陈联诗都参与了营救行动。陈联诗有一个亲戚叫段成操,后来嫁给了“中国新闻社”社长袁建之,袁建之的人脉宽泛。林向北和妻子、岳母商量,看能不能利用袁建之疏通一下关系,说不定还能救一些人出来。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廖宁君通过段成操找到袁建之,告诉他自己有亲戚关押在渣滓洞,请他想想办法把人救出来。考虑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袁建之答应了廖宁君的要求,但是需要廖宁君提供一些钱去走关系。廖宁君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林向北、蒋仁风。商量时,大家觉得用钱买人的方案虽说不是十拿九稳,但也是一个操作性比较强的方法。
不久,袁建之向廖宁君回话说,自己联系的人要10两黄金换1个人。最后经过讨价还价,改为5两黄金换1个人。5两黄金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为了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川东地下党也全力以赴。陈联诗向她妹妹借了20个银元和1个金戒指,又在其他亲戚处借了50个银元。川东地下党的谢彬和吕迪在盐务和粮食单位工作,他们凑了60个银元,而且把金项链也捐了出来。廖宁君把川东地下党的同志东拼西凑的180个银元和几件金首饰交给袁建之,希望他尽快去营救。袁建之立即买了1副麻将和1支火腿送到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张姓法官那里,但这位张姓法官并没有立即收下礼物,而是告诉袁建之等事成之后再说。张姓法官随后前去办理这件事,不久他回来告诉袁建之,说现在救人已经不行了,早几天还可以,他托的人已经逃到成都去了。
为了营救关押在军统集中营里面的革命志士,川东地下党的林向北等人可谓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试图购买武器,进行武装营救;他们策反廖开孝,甚至想到用钱买人。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异常复杂,狱外组织的营救行动始终没有成功。
二、狱内:革命志士积极进行自救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关押在军统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并不知道狱外的川东地下党在组织力量营救他们。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从1949年9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了分批屠杀。鉴于严峻的形势,狱中的革命志士迫不得已行动起来进行自救。自救的方式主要是策反狱医、看守等人员,试图说服、感化他们,以便创造条件逃出监狱。
(一)策反渣滓洞狱医刘石仁
刘石仁是天津人,1948年初被分配到渣滓洞担任狱医。因为长期受国民党错误舆论引导,刘石仁认为关押在渣滓洞的人都是“违纪分子”,不值得同情。因此,刚到渣滓洞时,他对狱中的“犯人”另眼相看,每周只到渣滓洞巡诊两三次。之后,随着与“犯人”的不断接触,刘石仁发现他们并不是国民党宣传所说的“杀人不眨眼的吃人恶魔”,相反,他们“有高尚情怀、坚强意志”[6]698,刘石仁开始同情他们。
狱中的革命志士观察到刘石仁的思想变化,大家觉得可以对他进行策反,说不定能为逃出监狱创造条件。因此,难友们不断地接近他、感化他。何雪松等人主动找到他,希望他多为狱中的难友做好事;“江竹筠等人还帮助刘石仁洗衣服。”[4]342
刘石仁到渣滓洞两个月后,发现女牢的“政治犯”周泉香呕吐不止,询问得知周泉香是新婚不久就被捕,有严重的妊娠反应。刘石仁向所长李磊报告,希望改善孕妇的生活条件,否则可能会导致胎儿死亡。李磊直接拒绝了刘石仁的要求,并希望他不要插手监狱的事。李磊的话激怒了刘石仁,两人当场就吵了起来。最后,刘石仁提出“自己掏钱给孕妇买营养品”[7]244。李磊不愿和“政治犯”的关系过度紧张,就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
刘石仁的表现让革命志士们刮目相看,因此,曾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具有丰富统战工作经验的胡其芬决定把他列为重点策反对象。1948年5月的一天,刘石仁匆忙赶到女牢,为突发“重病”的难友看病。在号脉之际,刘石仁感觉到手心突然有东西塞进来,顿时慌了神,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号脉完后马上顺势把手里的东西放进裤兜。回到办公室,刘石仁拿出裤兜里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个纸团,上面写着:“医官,听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的帮助”[6]700。在革命志士的策反下,刘石仁开始为难友们向狱外传递信息,“至少有20人托刘石仁给家人送信”[7]246。
1949年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渣滓洞,狱中的难友们深受鼓舞。为了让外界知道军统集中营里的情况,狱中的革命者们拟定了一份300多人的被关押者名单,交给刘石仁带到狱外转给地下党组织,希望设法寄到香港,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然而,由于国民党的邮检非常严格,这封信被查出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马上要求李磊追查是谁泄露了名单。刘石仁被叫去询问,但他始终不承认。因为找不到证据,此事不了了之。解放后,刘石仁被安排到西南农学院任校医。
(二)策反渣滓洞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四川荣县人,世代贫农,初中毕业后到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当文书。1947年8月,因川康绥靖公署被撤销,黄茂才到重庆行辕二处管理档案,后又被派往二处的邮检组。因为不懂官场的规则,不善于拍马屁,黄茂才被邮检组组长列为裁员名单,后来经人疏通关系才保住了饭碗。1948年5月,20岁出头的黄茂才被调到渣滓洞当看守。
黄茂才和初到军统集中营的其他看守一样,他被行辕二处总务课长安国华、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等人灌输了“进监狱的不是好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坏人”等思想,李磊还要求黄茂才严格遵照监狱的规章制度管理犯人。刚到渣滓洞,黄茂才对关押在里面的革命者心存芥蒂,始终保持“距离”:路过牢房时,他不敢正眼看牢里的情况;放风时,他总是离革命者远远的。虽然不与革命者接触,但他不像其他看守那样对革命者凶神恶煞,狱中细心的革命者觉察到黄茂才和其他看守“不一样”。有一次,他巡查经过女牢时,江竹筠轻声地问他:“小兄弟,你年纪尚轻,为什么到这里来当看守呢?”黄茂才一愣,马上答道:“不是上面安排,我才不愿意到这里来。”说完,马上转身离开了女牢。又有一次,黄茂才经过女牢时,曾紫霞对他说:“小兄弟,我们帮你做了一双鞋垫,你收着吧。”黄茂才见周围没有其他看守就收下了。之后,男牢的何雪松、陈作仪等人经常找机会与黄茂才接触,主动关心他的家庭情况。长时间的接触后,黄茂才发现狱中的“犯人”并不像上级所讲的那么可怕,相反,他们中有的是教师、记者、学生,他们说话都很文明,待人也很有礼貌,很有人情味。黄茂才也不再故意躲避革命者,偶尔还和他们说说话。有一次,黄茂才还开诚布公地给“犯人”们讲自己并不想来这里当差,并不想害人,“到渣滓洞当看守,就是为了混口饭吃”[7]249。听了黄茂才的肺腑之言,江竹筠开导他,希望他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人民会原谅他的一时糊涂。
通过狱中革命志士的循循善诱,黄茂才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仅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者送信:尽可能地延长放风时间;难友们传递信息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狱中的革命活动;他还化名为张立修、黄克诚,为难友们送信。有一次,黄茂才和渣滓洞看守长徐贵林搜查各牢房,在楼上6室陈作仪的枕头下发现一张摘录新闻报纸的纸条。千钧一发之际,黄茂才借徐贵林转头询问之机,“把纸条放进裤兜撕掉”[6]696,这才避免了险情。
渣滓洞大屠杀的前几天,黄茂才突然接到上级的遣散通知。要走之前,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女牢的难友。狱中难友胡其芬化名为吉祥,写了一份《最后的报告》交给黄茂才,请他将此信交给重大医学院的大学生况淑华。黄茂才按照曾紫霞的要求,及时将信交给了况淑华。后来,此信转到中共川康特委沙磁区工作小组负责人刘康手里。胡其芬写给党组织的报告里面详细讲述了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分批屠杀,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希望狱外的党组织尽快营救狱中的同志。
刘康接到信后,决定马上组织武装力量进行营救。然而,由于时间仓促,计划还未实施,狱中的难友就被国民党特务屠杀了。没能营救出狱中的难友,成了刘康心中永远的痛。
解放后,鉴于黄茂才曾帮助过狱中的难友,人民政府给他安排了合适的工作。
(三)策反渣滓洞警卫连连长邬志声
邬志声是重庆云阳人,1949年3月被调往渣滓洞监狱任警卫连连长,负责渣滓洞外围的警戒与守卫任务。虽然警卫连和看守没有工作上的交集,但工作的区域很近。随着接触的增多,黄茂才和邬志声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邬志声经常到黄茂才的寝室串门,在聊天的过程中经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腐败的不满以及对个人前途的担忧”[8]352。黄茂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狱中的难友韩子重、江竹筠等人。韩子重眼前一亮,希望黄茂才做邬志声的工作,策反邬志声起义,让他率领警卫连消灭军统集中营范围内的特务,掩护难友突围。同时,希望黄茂才找一个机会,让自己和邬志声见个面。
一天,黄茂才乘李磊、徐贵林等人不在,把邬志声叫到渣滓洞内院的办公室。在这里,韩子重等人给邬志声讲了当前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也讲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宽大政策,希望他认清当前的形势,带领警卫队起义。邬志声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些心动,但考虑到起义的行为有可能危及家人,表示愿意考虑考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9年11月初,国民党突然把邬志声及其连队全部调离渣滓洞,前往重庆石桥铺休整待令。突然的变故,使得这次营救行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四)策反白公馆看守杨钦典
杨钦典是河南郾城人,只读过小学,抗战时期在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当兵,1943年到重庆交通警备队,1948年6月被调到白公馆当看守。杨钦典刚到白公馆时,关押在里面的黄显声、许晓轩等革命志士经常给他讲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鼓励他戴罪立功。经过大家的教育和帮助,杨钦典思想变化很大。他在能力范围内,给狱中的难友以极大的方便。
1949年11月27日,在军统集中营大屠杀时,因为渣滓洞关押的革命志士人数太多,那里的特务处理不过来,上级就把白公馆的特务全部调往渣滓洞协助屠杀,白公馆只留下看守李育生和杨钦典。杨钦典知道解放军已兵临重庆城下,此时的他守着还未被处决的革命志士,心里非常矛盾:把他们杀了,解放军肯定不会饶了自己;把他们放了,国民党也要追究责任。正当他犹豫不决时,罗广斌在牢门口对杨钦典说:“国民党已经逃走了,解放军马上就要攻下重庆,你还是把我们放了,戴罪立功,我们都给你证明。”听了罗广斌的话,杨钦典虽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打开了牢门,罗广斌、郭德贤等19人成功脱险。解放后,杨钦典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回到河南老家务农。
三、结语
在重庆军统集中营大屠杀前,狱外的川东地下党试图通过策反、花钱买人、武装劫狱等方法进行营救,但当时军统集中营由于是国民党重点布防的地方,有重兵把守,加上川东地下党对集中营里的情况不熟悉、营救时间紧等其他偶然因素,营救行动都失败了。狱中的革命志士虽然都在想办法自救,但策反的对象都是底层的看守、狱医,不能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除了策反白公馆看守杨钦典还算成功外,其他的策反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1]钟修文,李畅培,厉华.铁窗风云(下)[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2]厉华,刘和平,王庆华,等.魔窟:来自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3]林向北.往事难忘:一个参与营救“渣滓洞”战友的老人的回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4]厉华.红岩档案解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5]林向北.黎明前的营救[J].红岩春秋,2003(6).
[6]杨顺仁.撩开神秘的纱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7]孙曙,陈建新,刘和平,等.红岩魂:来自B类档案的报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8]丁少颖.江姐真实家族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编辑:文汝)
K265.9
A
1673-1999(2017)01-0088-04
王浩(1984—),男,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为红岩英烈事迹。
2016-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