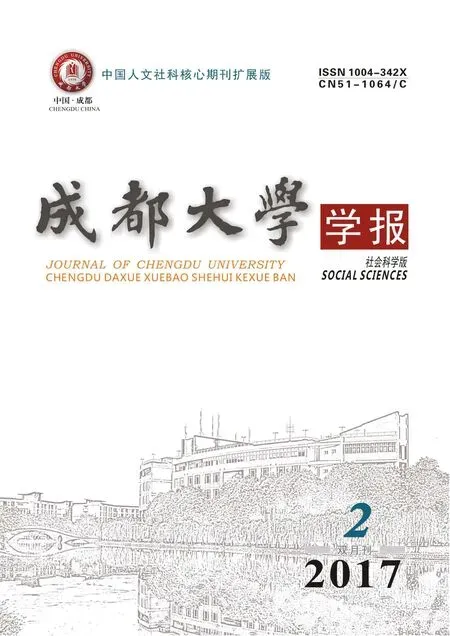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四川卷续)之许金门篇*
2017-03-22李轼华冯乃光
李轼华 冯乃光 万 平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2.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73)
·口述史·
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四川卷续)之许金门篇*
李轼华1冯乃光2万 平1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2.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73)
许金门,绵阳市川剧团艺委会主任,著名演员、编导。十岁学戏,师从生角名家周孝平,专攻川剧红生。在多部三国戏中扮演的关羽形象深入人心。其演出唱腔洪亮,形神兼备。1955年开始从事编导工作,编导了《黄继光》《焦裕禄》等一系列现代戏。从绵阳市川剧团退休后,继续从事编导、演出工作,积极组织成立梨园会馆,进行川剧演出。
许金门;川剧;艺术人生
许金门,男,1933年出生,四川成都人,绵阳市川剧团艺委会主任,著名演员、编导。十岁学戏,师从生角名家周孝平,专攻川剧红生。在《白门楼》《三战吕布》《挑袍》《古城会》等多部三国戏中扮演的关羽形象深入人心。其演出唱腔洪亮,形神兼备。1955年开始从事编导工作,编导了《黄继光》《焦裕禄》等一系列现代戏。1987年从绵阳市川剧团退休后,继续从事编导、演出工作,积极组织成立梨园会馆,进行川剧演出。1993年在绵阳召开的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其编排的目连戏大受好评。2000年编导的川剧《火烧濮阳》对传统戏的抢救工作意义重大。
采写时间:2014年3月22日上午
采写地点:绵阳市川剧院
采 写:李轼华 胡 艳
摄 录:张 俊 胡利蓉
李轼华(以下简称李):许老师您好,您是一位投身于川剧事业七十多年的老艺术家,我们今天想采访一下,您的一些人生经历(从艺的经历),以便留下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下面呢就请您谈一谈您一些基本的经历,好吗?
许金门(以下简称许):好。我今年81岁,出生于1933年,我是成都人。曾经在眉山,就是乐山专区的眉山,那当时是一个军队的剧团,学名维新舞台。
两个剧团,一个新又新,一个维新。新又新是师长(组)队,一个(维新)是旅长(组)队。就是军队的一个川剧团。我从十岁的时候就到剧团去拜师。因为我喜欢川戏,从小就喜欢川戏。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唱那个,都能唱,还能唱《恨杨广斩忠良》《南阳关》那些剧目。学艺过后我就拜周孝平老师为师。那时候是拜师要写纸,要以拜师为贵。学习三年,帮三年。学艺(后)很快进入了剧团。我学的生角,就是生旦净末丑的生角。后来就专攻红生,演关公,(演)关公唱了很多戏,原来唱过《白门楼》的关公,《三战吕布》的关公,《挑袍》的关公,《出关》《古城会》的关公等这些戏。
因为我个子高,我扮起的关公形象比较像那个人,并且我也喜欢那种角色,就喜欢上关公戏。解放前,我在唱戏,解放后我也在唱戏。喜欢跑乡滩里打板子。川剧里的形式还是很多样化,我就说一下川剧的历史形态。川剧很古老,据了解它来源于傩戏,过去叫作端公戏。据我们老师传下来给我们的川剧来源是端公戏。四川关公戏,现在是叫傩剧,它的来源进化成川剧。过去四川很多地区都有这种剧团,叫的是乡班子。除了大的剧团以外,还有很多乡班子,叫作草台班子。乡班子一直在各乡站演出,场会演出。那时候演出的活动面比较宽,全天都有。一个县起码有五六个剧团,比较多,遍布四川。唱戏的人走到哪里就可以搭班子,广谊剧目、桂华科社,这些都是有名的科班,如广谊剧目就是有名的班子。传统的叫跑滩,跑滩就是搭班子,这个剧团待一段时间,那个剧团待一段时间。从艺人本身来讲,他有一个锻炼的阶段、过程。
出师过后,我就跑到北边一边(川西坝)到剧团。到剧团有个好处就是学东西,学很多戏,各班各戏。或许有个说法,川剧剧本很多,除三皇五帝、夏侯商周、唱不完的三列国,还有唐三千宋八百等剧本很多。一天要唱四台戏,早台、中台、店台还有夜戏。过去很多演员接很多剧本,唱很多戏,哪怕是一个下角色(配角)都要接很多戏。搭班就是一个学戏的阶段,各个班到处去学戏,它通乡,拜老师……也不叫拜老师,就直接搭班学戏,也是一种偷经学艺的办法。很多演员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锻炼实践机会也多。解放前一天四台戏是草台班子的一种状况。观众很多,爱川剧的人也很多,叫唱民戏。请剧团唱戏俗称请班子。由场镇上的人组织,有财神会、土地会、观音会等各个乡镇上的会。会所来包戏,所以请一个剧团来唱十天,由它点戏,不是你想演什么就演什么。迎神戏,祝贺戏各种戏都有,大戏小戏都要。在当时的情况唱戏,由于观众来源比较多,唱戏的地方比较广阔,甚至大户人家堂屋里面也在唱戏,傩剧的基地,就滚打了那么多时间。
解放过后,我就到了这个剧团,现在叫前奏剧社。解放过后,就在这个剧团。当时我是排武戏(武打戏)为主,那时候我就在当助理导演,当时叫说戏,就是帮着说武戏。每天唱打斗戏(排练),开始进入排练过程。解放过后,排了很多戏,接着到了绵阳。成立国营地区川剧团,还有一个川西川剧团,就进入到了国营剧团。当时有一百多人,有很多名演员,有肖凤鸣、周孝平等很多演员,还有陈书舫的爱人谢文新也在这个剧团。成立过后,这个剧团就进入到正轨,一直很兴旺。当时成立国营剧团过后,一直是自己挣钱,自己发工资,自己买房子,很多都有节余,就是现在绵州那个地盘,自己挣钱买来的。后来解放过后,就演了很多戏。
从1955年我就进入了排戏工作,搞编导。我从开始编导就演了一个现代戏,《爱国英雄黄继光》,那时候出于对黄继光的感动,英雄爱国主义的那种,马上写了一部小戏(武戏)。接任编导之后1960年代我写了一部现代戏《焦裕禄》,当时看了报纸出了焦裕禄,很感动。就动笔写,很快就写出了一个剧本出来,马上就排了这个戏。演出过后,四川广播电台宣传在广播里。后来去体验生活,又重新写了一个,这个剧本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也是比较成功的。从我自己来解释,是很满意的一个剧目。还写了一些剧本,写了一个王玺平武报恩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得到演出,但是出版了的。其他传统戏太多了,我主要谈传统戏,传统戏剧本太多了,每天要演很多场。“文化大革命”以前,演的是两三场,每个星期要排一个新节目出来,我们改剧本改得比较困难。“文化大革命”之前剧团的成绩比较好。“文化大革命”过后,样板戏出来,又学样板戏和现代戏,所以退休生活延迟二三十年,我1987年退休,退休过后我还在排戏,排目连戏(国际目连戏)。一直到2000年退休过后,我就成立了一个梨园会馆,为一些爱好川剧的人做这个会馆。梨园会馆做什么呢?就是川剧组场合和川剧演出。这个就是聚合一些爱好川剧的人在一起活动。每周固定二四六七四场,不坐场就串场,一直在做这个。后来在2000年和杨昌林合伙在新都川剧团,结合了一些名演员排了一个《烧濮阳》,由我改编、排导。这个戏也是我自己做了碟子,是一个传统川戏。后来又改了一个《三进忠》,它没有上演,但有个剧团将它演出了,我们没有正式排练,只是写了一个剧本,《三进忠》是个古本。跟杨昌林商量做了一个修改,准备在省川剧院投排,结果没有排成。
作为我个人的艺术道路,我又唱戏,又搞编导。我的人生道路大概就是这样子。
李:那许老师,您能不能具体地跟我们讲讲您当年在学戏或者是在演戏过程中有哪些酸甜苦辣的事情?
许:这个说老实话,学戏是比较吃苦的。我小时候十岁到剧团,说实话我比较聪明,我进班半个月就上戏台唱戏。当时我老师周孝平专门教一个戏给我唱,我就学会了,唱的就是《南阳关》。但又小,大靠(子)又穿不来,就用大靠(子)的腿脚绑在大靠(子)身上做袍子就开始唱戏。不过那个过程是比较艰苦的。腿啊、腰啊、体形锻炼是比较吃苦的。痛,真的痛。当时的生活也不是很好,剧团只供饭,生活条件很差。后来老生,唱不出来。出师三年过后,原来我嗓子很好,唱了很多戏,也搭了很多班子(大班子小班子都搭),在成都大剧院,新又新唱戏。因为嗓子好,受人喜欢。一旦老生过后,老班不要了,就要跑滩,就只有朝乡班子跑,经常饿饭。对我来讲,我是学武的,我开始学武戏。所以我后来学武戏,就学翻跟斗(嗓子就用来这个,原来是唱文的,后来学武的),学靶子功这些东西。但我个子高,我十四岁的时候在蹿个子,学一些靠架戏,唱一些下驷角的戏(嗓子哑了)。后来嗓子(恢复)又慢慢开始唱戏,这个是件很艰辛的事情。解放过后就好多了,稳定了。
李:您三年就出师了。十岁的时候开始学戏,三年出师,解放后就到了绵阳市川剧团?
许:三年出师过后还有很多年,一直到1949年的时候就跑滩,这一段都是很艰辛的。解放过后很好的事情是生活好起来了,有安定的生活,安定的地点。过去是经常饿饭,说老实话,这是很苦的事。艺人更苦,别人看不起。最大的人生(屈辱是)别人看不起,喊的“戏娃子”。说的是你唱戏进不了家门,别人看成下九流(当时是别人这样看的)。就我自己来讲,我不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喜欢这个东西。我曾经有个笑话:我逃学看戏,把书包挂在树枝上看戏,书包都掉了。我十岁的时候读书,我把书包挂到三苏祠里面去,跑到这边来看戏,转过去找书包没有了。就是这个笑话,挨了几顿打。老的管得严,后来说我爱看戏,干脆叫我去学戏。这段从戏时间很艰苦,但有苦有甜。作为一个人来讲,从小受了一些苦,后来也有些甜的地方。唱得来戏过后,受人喜欢,人又小。那个时候,有很多大人喜欢我。老年人看这个娃娃人那么乖又唱得好,就经常给我送钱来,送吃的。我又爱好这个(唱戏)。嗓子哑了过后就比较苦了,就跑滩。解放过后,人也十六七岁,长大了,这个生活也安定了。但那些年没文化,只认得到几个字。后来解放过后,自己自学文化,写剧本,也就这样子自研书来的。我的艺术道路大概就是这样子。我的爱好就是关公戏,我现在还能唱。关公的那些角色,特别喜欢《挑袍》。就是关羽辞曹过后,在霸陵桥饯别那场戏。这个戏是我们老师的口传。我们老师唱这个戏唱得好,我也是他口传的一个徒弟。我也喜欢这个,就是《挑袍》。其他还有很多唱腔戏,最爱就是这个戏,我现在没办法,唱不出来了。为什么呢,没有鼓师,没有帮腔了,自己还可以哼,前年还在唱,昨前年还能唱。
李:您能给我们来两句吗?
许:凉时节秋生八月……(注:许老师现场演唱)擅长的戏还有关羽其他的戏,比如说《古城会》,还有很独到的地方。所以关羽我一直很喜欢,他的高矮(和我合适),我一直很喜欢关羽这个人,他一身正气……
我的艺术道路大概是这样过来的,特别是对川剧这个东西很惋惜。因为川剧这个东西是个古老的剧种,是过去到现在承续,不断地改进,不断地革新,这是新的变革。所以川剧的改革和振兴,我是不服气的。振兴川剧怎么整,这么多年来,它本身就是自身进化。原来的化妆很难看(后来改进了)。川剧有很多独到之处。比如川剧的一个耳帐子,看起来就像两块门帘子的耳帐子,既是床,一会儿是城门,一会儿是城墙,一会儿又是山。它变化很多,变化很大。川剧舞台是虚拟的,一根马鞭,它是虚拟的,不可能是骑马。川剧独到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那个戏曲,很多精炼的东西,小生的扇子,生角的口调,这个是老先祖们遗传下来的。过去的川剧好多都是口传心授……教的特别是唱腔动作都是潜移默化教出来的。老先人一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因为特别的动作、形象,老先人传下来的就是这个路线,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是很多老师创造的一个路线。川剧有流派,京剧有流派,其他剧有流派。所以川剧还是有流派,只是没归纳而已。各人的学生都有跟老师同道的地方,因为川剧班多,还分上河下河,分川北川东川南,它有各班的戏。而且表演的程式大同小异,基本对人物的塑造都是共同的。这个川剧的来源不简单,是真的不简单……现在看来可惜了。为什么可惜?失传。“文化大革命”过后,就存在个什么问题呢,戏断代,看戏的人断代,唱戏的人断代,我们这代人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八几年,“文化大革命”过后还兴旺了一段时间。
“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每天要唱好多戏,到解放过后都是这样的。白天要唱,星期天三场,晚上要唱,每天都要唱。这些资料累积了很多东西在川剧里面。所以觉得可惜。剧本流失,省上买起跑的人多得很,像我们私人保留的东西,剧团都没有了……观众少了,经济效益就差了,所以就改革,绵阳的改革就很成问题。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是(不该)把剧场分割了。本身剧团有剧场的,现在把它分成两个单位。一个剧团要跟剧场分开,分开过后,你要演戏就要去租剧场,看到卖都卖不得,还要租剧场去演戏就更恼火。所以(搞)演出的作家就更少了。反过来,有些当官的说你不演出,说你好耍,没有舞台怎么办,过去每个乡坝子都有个万年台,整个四川,绵阳,舞台是拆完了的,原来每个乡政府都有个大的台子唱戏,那些地方是拆完了,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搞这个事情第一步就是场子给你收了,这个怎么演戏呢?反过来说剧团不演戏,就好耍。找不到地方演。过去还可以下乡,拉起板板车、架架子下乡演出,过去,箱箱子要自己拉车子,用架架车拉起,演员都拉车子。后来这些地方我们没得了,没有剧场,到处找不到地方演,要演不接待。我们还是想演出。这就是一个败笔。把剧场给拆了,还要修房子,占地盘,搞经济修复。这个时候我反对这样搞。
所以川剧市场来讲,搞不起来。原来有很多火把(剧团),民营的火把(剧团),都是农村里的爱好者搞起来的。现在火把(剧团)都找不到地方演出了。就上庙子找,就看到庙子还能演出。因为市场不在,我们原来有个剧团,那个剧团就是火把组合的剧团。
李:那它现在有机会演出吗?
许:它在演,它还是很受到支持……本来我们场子是现成的,演不起来。最后我成立一个艺术剧团还是这样。就把我们的人“砍了”全部退休,有38岁就退休的。奇怪,真是奇怪。等于我们演员退休,稍微老年就这样退休了。我们想传下来的都传不下去,一生的东西拿不出去。教一批学生,唱不出来了,学生也没人唱。一个乐队,打击乐给你取了,全部退工退休,全乐队给你取消了,全部退休。这种搞法是一错误的决定,导致这些剧团彻底撤销掉了。所以绵阳撤得很彻底,当官的把川剧撤得很彻底。我们耍着的那么多演员,我倒还组织一批爱唱川戏的人唱。但现在我们也没地方唱了。没有地点,乐队敲鼓师这么多年没有培养,老鼓师死了就没人了。特别是传统戏用脑袋记,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绵阳成立剧团过后被人忘了,很寒心。
李:作为一个老艺术家看到川剧的这种现状,确实是很痛心,那么您觉得川剧现在没有可能振兴或者传承了吗?
许:就全省来看,就看省川剧团、市川剧团还在。现在没演了。为什么呢,各个县都拆完了,原来乡上都有剧团,普通人普及到这个程度。现在的火把(剧团)都是由乡上剧团组织起来的,现在拆完了的。过去每个县都有一个剧团,地区的拆了,没有演员就没演。所以断代,就是戏断代、人断代、观众断代,你要承认这一点。
李:如果川剧要振兴可能需要一个政策,一个经济,各个方面的。
许:这个戏曲全靠依傍于权势,依傍于经济,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权势的人坐台坐不起来,没有经济的人坐台坐不起来。过去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才坐得起,他是为了玩乐,为了高兴,为了热闹地方,还有就是为了宣传。当时宣传忠孝节义、忠贞爱国这些东西,他就搞这些东西。我们的戏曲现在没人看了,纳入新经济。纳入经济效益是很简单的,你要扶持它,给它走地的地方,给它演出地方。名副其实地修绵阳大戏院,八千块钱一场,谁敢去唱,那个艺术家本身就不敢去唱。人家就把剧场拿出去出租。农民没有地不好生活,剧团没有剧场叫别人怎么生活。修了个剧场,成都四川剧院还给了个锦江剧场,绵阳就没有这个场子。有个场子八千块一场场租费,你请哪个剧团都不敢去。修起过后就交给开发商去经营了,它本身不经营。所以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失误,我们团培养了两个地方的演员,从我们手上培养出来的(全盘培养出来的两个演员)一个演员蒋淑梅,一个演员去当文化局副局长去了,带头“砍”剧团,把剧团“砍”得溜光。38岁在这退休,他是搞艺术剧院的,选了那么多川剧演员,都被“砍”了。现在彻底“砍”完,就没有川剧了。
这个要想振兴川剧,还要下大功夫。作为四川来讲,这个问题大。这个是历史造成的,豫剧怎么来搞,黄梅戏怎么来搞,越剧怎么来搞(值得研究),京剧国剧更不说了,人家有学校,有专门的研究数据。你川剧有什么,谁来学,到现在都不愿意来学,因为没有前途。我们现在在那里摆着,没有用武之地,也没有时间场所。要想唱戏,又没有打击乐,又没有鼓师,又没有琴师。怎么办,这门学问很可惜。(学生)他们也没有学到好多戏,功夫倒学得多,武功都学遍了,戏找不到,最多有两个戏就过去了,现在更加没有戏唱。我们过去要唱百个戏,我现在都能唱这些。“文化大革命”那么多年,没有时间与经济,也没有实践。没有实践就记不住东西,要有生产,要去接触,还要学。从我个人来讲,我们在唱戏的过程当中,看得多,要去看别人怎么唱,要去体会,要去学习,要去优培一个,都是这样子出来的戏。每个演员要唱戏都要去学,老师在唱戏,我们端个茶壶在旁边看,都是这样子出来的戏。因为实践场所,没有实践怎么学会,你看别人教学生是怎么教出来的。所以绵阳这个地方更加难整。现在省专业是不是在招生我是不知道的,没有人了,老师没有了,人少了,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川剧就败在这里。
“文化大革命”过后,没有狠抓,戏断代、人断代、演员断代、观众断代,给(川剧)造成了很多危机。我认为要想把川剧搞起来,还离不得领导的重视,当官的不重视,估计着就没戏。过去川剧说个笑话,过去中央的很多是四川人,朱德、罗瑞卿、张爱萍,这些中央首长喜欢看川戏,每年川剧都要进京,有了地点,名气也出来了,特别红火。所以这些东西离不得权势的扶持。
李:那是川剧演员最幸福的时候。
许:对,是最幸福、最心欢、最兴旺的时候,那个时候川剧要买到票会很难。到现在,没有人买,那时候是买不到,这时候是卖不掉。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权势的问题,重不重视的问题。我觉得传统的戏曲在我们这一代消失了,真的寒心。从我们这一代就没有了,我们这一代对下面还有几代依然还有期待,作为学生,他们怎么没继承,所以对学生感到惋惜。我真的觉得川剧就这么消亡了,成为历史模块了,就完了。
李:那您现在的学生还活跃在舞台上吗?
许:他们现在演了小品,不演川戏了。近年在川剧院跳舞,现在正在(搞)演出公司。原来的戏剧院拆了,搞了个演出公司,拿到经济市场,川剧市场挣不了钱,就不演川剧了。怎么办,就这样完了。
李:您后来除了演出以外,还在从事编导工作,您刚才也说了,你最满意的代表剧目就是《焦裕禄》《烧濮阳》。您能不能详细地谈一谈这两部戏的排练情况?
许:这两部戏,60年代排的《焦裕禄》,60年代的时候作为宣传典型。我个人来讲,当时看到报纸很激动,凭着那股热情连着三天写出来。当然写这个剧本过程中请了很多人,请老师来进行座谈。三天之内写出来的剧本,一个星期排出来了《焦裕禄》。排出来过后,演出比较成功。那个李泽荣就演焦裕禄,演出过后他就很热爱。排那个戏时,没有生活(体验),当时是凭着材料写的,合作着写,写来就很有感情,那些唱腔、那些唱师、那些情节安排(都很好)。那些领导看了过后,特别是四川台跑过来看了过后,马上就播出去。这个时候还是很艰苦,领导也很重视,宣传教育感到了政治气候也需要这样的剧目。我的体会就是随着政治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那些剧本就是一个很有出路的东西。当然这个也不是编导的事,焦裕禄是真人真事。当时要宣传他,这种人物该宣传,到现在还是全国教育,就凭这个来权衡它,根据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编写剧本。
后来搞了个《烧濮阳》就是个传统戏。这个《烧濮阳》原来是和杨昌林一起商量的事情,剧本由我来改编,改编这个原来只有很短一节,只唱得到40多分钟。改编过后大概演两个多小时,就增加了很多内容,就把这个情节整得更具体性了。办这个的时候,那时川剧就开始不景气了。2000年不景气了。文华川剧团都不怎么演出了,就看新都川剧团在成都找新演员,是由杨昌林亲自参加,演的陈宫,那个罗健演的吕布。我亲自改编,就是编导,现在还有碟子,那个《烧濮阳》的碟子。这些戏有这样一个体会,作为传统戏作为川剧的剧目,“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从“文化大革命”过后,这个三列国就没得了,舞台上就不出现这些戏了。有意识地把三国戏弄出来,下了很大的功夫整这个文化剧,当时想筹点钱,搞三国戏。当时有这个想法,把三国戏翻出来,整理改编,一本一本地改成来唱。搞了这一本戏过后,然后就离散了,没有精力,也没有经费,搞不来。当时拿了三万块钱来排这么大个戏。排这么大个戏,演员都是义务劳动,吃伙食都没有工资的。包括道具都是东拼西凑拿进来的,省川剧院拿些道具,市川剧院拿些道具,我们这里拿些道具去搞的这个戏。我们那么大个剧团,道具都失传了,没有了。大概就这么多嘛。
我大概就想到这些戏。川剧要想重新搞起来,还要下很大的力气,特别是绵阳,就再说一句,特别是绵阳,很难。
李:好,谢谢许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责任编辑:刘晓红 张 蕾)
2016-08-30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2YJA760062)阶段性成果之一。
李轼华(1970-),女,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冯乃光(1962-),女,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教授;万 平(1954-),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K825.78;I236.71
A
1004-342(2017)02-1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