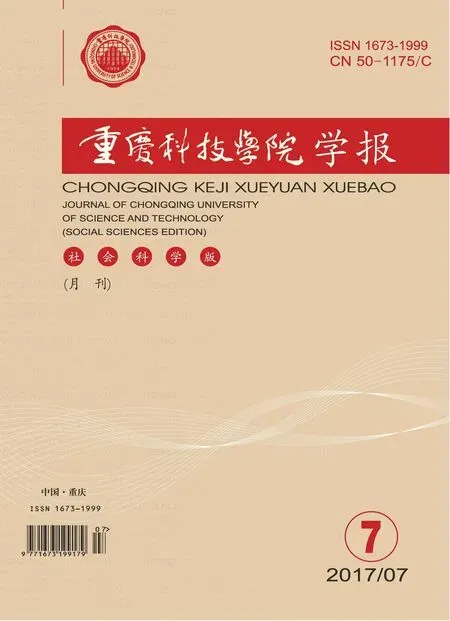小说《极花》的饥饿书写探析
2017-03-22陶倩影
陶倩影
小说《极花》的饥饿书写探析
陶倩影
贾平凹的新作《极花》以被拐女孩胡蝶为焦点,展示了在城市现代文明挤压下的农村社会,以及圪梁村人的现实生活图景。作为农村的守望者,贾平凹在《极花》中着力书写了物质饥饿、性欲饥饿以及更深层次的精神饥饿,建构了人格理想,寻求了饥饿救赎。
《极花》;物质饥饿;性欲饥饿;精神饥饿;饥饿救赎
小说《极花》以一个被拐女孩的视角讲述其被拐卖、被生子、被解救、被返回的故事。作者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中说:这是一个陕西老乡女儿的真实故事,而他并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的故事。“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1]207贾平凹执着地书写现代文明挤压下的农村社会,以及圪梁村人的现实生活图景。笔者立足于现实层面,深入揭示《极花》中人物的饥饿困境,探究现实背后的人性本真。
一、“饥饿”主题
饥饿,生物学上是指机体未获得自身所需的食物或营养的状态。这种饥饿状态的持续会使生物个体形成寻求食物的冲动与焦虑,而性欲的冲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食欲的冲动。约绪·德·卡斯特罗认为:“饥饿现象,不论是食欲的饥饿,或是性欲的饥饿,都是一种原始的本能。”[2]饥饿是一种基本的生理现象,更是文学的表现对象。文学意义上的饥饿书写不仅在于物质、性欲方面,更是精神意义上的饥饿,是苦难悲剧的根源。
新时期以来,饥饿成为了作家们书写的重要主题。一方面,作家童年的饥饿记忆影响着自身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作家则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呈现饥饿困境,直面现实苦难,呼唤人性复归。例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写革命前后老百姓的生存饥饿;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透过群众的生存饥饿来指向干部的精神饥饿;阿城的《棋王》对王一生“吃”的生存本相书写。而莫言则是当代饥饿书写的代表,他曾说:“我是被饿怕了的人”,“饥饿和孤独是创作的两大源泉”。例如,《粮食》中的梅生娘为了躲避保管员的检查,将豆子吞进肚子里,回到家再吐出来给婆婆和儿子吃;《透明的红萝卜》中因为饥饿导致身体比例严重不协调的黑孩;《丰乳肥臀》中的底层群众忍受着饥饿,权力阶层却用食物谋取利益。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写道:“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3],其原因是社会底层群众丧失了对食物的控制能力。
在中国饥饿叙事的建构过程中,贾平凹“着力展示乡土、都市等不同文化场域内个体与群体的人性饥饿的本真状态,力求在‘肉身—情感—行而上’的饥饿的文化图式中凸现3个层面观照视角的贯通,以此来解释人性的本能欲望。”[4]例如,《废都》中庄之蝶回旋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等众多女性之间,于性欲废墟之上是精神的虚无;《高老庄》中人的精神饥饿导致本能欲望的丧失;《怀念狼》同样书写人的精神饥饿困境,叩问人类的存在意义等等。贾平凹在新作《极花》中力图从更广阔的人性维度上,书写物质饥饿、性欲饥饿以及更深层次的精神饥饿,思考饥饿困境的救赎之路。
二、饥饿表现
(一)物质饥饿
《极花》的物质饥饿书写主要表现在“吃”上。小说以被拐女孩胡蝶的视角来窥视圪梁村人的生存状态。黑亮家的早饭永远是稀得能见人影的豆钱粥,即便喝两碗三碗也抵不住饥饿。为了留住胡蝶,黑亮去镇上买麦面蒸的白馍,认为她只要吃好了便不会离开这里。“有一次竟还是买了个猪肘子,我以为这是要做一顿红烧肉或包饺子呀,黑亮爹却是把肉煮了切碎,做了臊子,装进一个瓷罐里,让黑亮把瓷罐放到我的窑里,叮咛吃荞面饸饹或是吃炖土豆粉条了,挖一勺放在碗里。”食物的匮乏凸显了圪梁村人贫困的物质生活状态。老老爷过生日,村里人带着粮食去拜寿,嚷着给老老爷补粮,明明不多的粮食却成了村长口里的3万石粮,“苦焦的地方可能就是以生日的名义让大家周济吧”。粮食无疑是圪梁村最大的物质财富。土豆是这里的主食,村里人认为它成熟了就得及时挖,不然就像埋下的金子一样会跑掉,土豆俨然成了圪梁村的金子。挖土豆是一年里最忙碌的日子,在外打工的,出去挖极花的,甚至赌徒小偷们都得回来挖土豆,“村子如瘪了很久的气球忽地气又吹圆了”。艰苦的生存环境,贫乏的食物储备使得胡蝶不断地想逃离这里,回到城市中去。
而这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吞食农村的结果。贾平凹借黑亮之口说:“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都吸走了!”在城乡叙事中,贾平凹一方面冷静、刻薄地叙写着乡村社会的颓败与困顿;另一方面又批判着现代城市文明对农村社会的侵蚀,从而反映出其矛盾的叙事心理。
(二)性欲饥饿
性欲是一种原始的本能欲望,当这种欲望被持续压抑后便会造成性心理的焦虑。“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1]206圪梁村的女孩或是去到城市或是不愿意内嫁,所以光棍们只能通过买卖来获得媳妇。“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1]207性欲的饥饿围困着圪梁村,82岁的张老撑弄大了妇女的肚子,黑亮窑洞里有从脖子到脚被刀砍过的美女图,立春和腊八共享着同一个女人,光棍们的门口放置的石头女人……
男人被性欲的饥饿压抑着,女人则成了男人满足欲望的工具。《极花》所建构的男性世界是带着霸权意识的,女性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胡蝶被拐卖后拼命地想逃离,逃回她的城市。而当她被黑亮强暴怀孕以后,便过上了圪梁村人的生活。不论是因为黑亮的束缚还是孩子的牵绊,此时的她衍生出了心理认同感。她主动向黑亮求爱,“我看着我的身子,在窗纸的朦胧里是那样的洁白,像是在发光,这光也映得黑亮有了光亮,我看见了窑壁上的架板,架板上的罐在发光,方桌在发光,麻袋和翁都在发光,而窑后角的凳子上爬着了一只老鼠,老鼠也在发光。”与《废都》中颓废的性不同,胡蝶在性欲中完成了“受活”。同样被买来的女人訾言,成为了立春与腊八分家的一样物品,面对胡蝶是人还是财物的质问,訾言说:“我只是个人样子!”在这种饥饿中,性与爱表现出了原始的背离。
(三)精神饥饿
贾平凹在物质和性欲的饥饿困境之上着力建构人物的精神饥饿困境。胡蝶,一个随母亲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她穿城市人的衣服,说普通话,穿高跟鞋,想挣大钱,而这种欲望致使她陷入了人贩子的圈套。她被拐卖后关在圪梁村黑亮家的窑洞里,拼了命想逃回城市,仿佛城市才是她的归宿。她企盼老老爷能帮助她,等来的却是一纸星图。胡蝶在黑亮家人的监视下过着日子,坚持认为“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厌恶农村和逃回城市的念头从未停止。而这种心理在她怀孕后发生了裂变,她主动拿掉了阻隔黑亮的棍子,与黑亮热烈交媾。她开始习惯了圪梁村的生活,学会做圪梁村的媳妇,孕育着黑亮的孩子。但她仍然挂念着母亲,幻想着回到城市,在梦境与现实的混沌中,她被解救了。城市依旧不是她的城市,弟弟的羞辱,记者的采访,冷漠的流言,逼迫她又回到了圪梁村。
胡蝶的心理图式是在“看星”的过程中完成的,当老老爷第一次让她看自己的星星时,她说:“是不是我的星在城市里才能看到?”此后,看星成了胡蝶不自觉的行为。直到她怀了黑亮的孩子,她看到了一大一小2颗星,心里却慌乱起来,“这么说,我是这个村子的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这村子的人呢?命里属于这村子的人,以后永远也属于这村子的人?”这一发现冲击着她的心理防守,而冲击背后生出了一种心理认同感。最后,胡蝶回到了村子,阴天里老老爷在看星,胡蝶说没有星,“但好像又有了,再看,到底是没有。”胡蝶向往着城市,而城市的冷漠迫使她重返农村,在绝望中走向了精神饥饿的困境。
圪梁村神巫文化的代表麻婶子同样遭受着命运的拨弄,前后跟过3个男人,生出的孩子是1个头2个身子。在不幸中认识了一个老婆婆,学会了剪纸。剪了便给各家送去,即使受到丈夫的打骂也并未停止。剪纸成了麻婶子生命的外化形式,而麻婶子则成了圪梁村的神。黑亮爹为了留住胡蝶,请她来招魂。走山后昏迷了几个月,却在棺材里突然醒转过来。此后,村里人觉得麻婶子不是人了,成什么妖什么精了,传说她的纸花花有灵魂。剪纸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而麻婶子剪的纸花花却有了神性,成了圪梁村人的精神信仰。
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掠夺着农村的资源,农村的生产力,农村的精神文明,而苦于基本生存资料匮乏的农村又如何找到出路?贾平凹以深沉凝重的笔墨批判着城市的罪恶,同时反思着圪梁村人的精神救赎。
三、饥饿救赎
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中谈道,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对积累性、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极花》是写一个被拐卖妇女的故事,拐卖妇女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贾平凹要建构的是法律背后的人性饥饿困境。他的法律意识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并不想把它写成单纯的违法犯罪事件,《极花》是为了思考人的存在意义而创作的。黑亮间接参与了拐卖胡蝶,并且野蛮地占有了她,成为胡蝶不幸命运的帮凶!然而,贾平凹却用他的朴实、勤劳稀释了罪恶,力图发掘城市和农村夹缝中的人性之善。胡蝶的悲剧是人类的“平庸之恶”造成的,汉娜·阿伦特认为这种恶是不思考,是个人完全服从于体制之下,放弃思考判断权利的恶。恶的“平庸性”在于它可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拐卖胡蝶的人贩子、黑亮、圪梁村人、城市的看客都存在着恶,胡蝶的恶在于她最后的心理认同。贾平凹游离在城市与农村的失落之中,企图寻找人性的救赎之路。
《极花》中老老爷的存在象征着中国农村最后的坚守,他是村里辈分最高、知识最多的人,村里每年的立春日都是他开第一犁,极花是他首先发现并起的名。他教胡蝶看自己的星,他为村里人起名,毛虫对他爹不孝三朵要他去给老老爷认罪,他还捉蝎子给村里人泡酒,编彩花绳儿给村里人许愿人畜兴旺……老老爷是圪梁村的精神支柱,无论村里的大小事都要请他做主,国家的法律在这个闭塞的乡村没有一点作用。即便如此,圪梁村的生活秩序井然而和谐,是圪梁村人不懂法律,还是国家的法律辐射不够?笔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对现代文明侵蚀下凋敝农村的最后希冀,贾平凹曾发出“我是农民”的宣言,农村是他的根。他直面现代文明中农村的罪恶与绝望,是其乡土意识的本能凸显。小说结尾安排胡蝶于梦境中返回了农村,叙事意图表现出了其复杂的矛盾心理。
贾平凹以15万多字结束了《极花》,他在后记中提到试图跳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小说以农村的落后来批判现代文明的侵蚀,城乡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指出饥饿困境的根源是人性的“平庸之恶”,唯有思考才能反抗。《极花》展现了贾平凹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但他却没有指出饥饿救赎的真正出路,这或许就是贾平凹式的留白。
[1]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约绪·德·卡斯特罗.饥饿地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3.
[3]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
[4]王刚.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审美视角与话语建构[J].小说评论,2007(6).
(编辑:文汝)
I207.42
A
1673-1999(2017)07-0077-03
陶倩影(1995—),女,安徽大学文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7-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