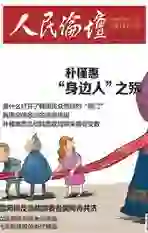“闺蜜门”事件如何一步步被放大
2017-03-20匡文波
匡文波

[摘要]韩国总统朴槿惠的“闺蜜门”自被曝光以来就吸引了无数民众的关注,韩国媒体在事件的发酵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结合媒体在事件蛰伏、发酵以及爆发过程中的影响方式来看,媒体分别从对群体的赋权、对事实的披露以及舆论的纠偏三方面来对政治事件的进程进行了导引。
[关键词]“闺蜜门” 群际情绪 政治风波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轰动韩国乃至世界的“闺蜜门”事件不断发展,“闺蜜门”的层层坐实与民众负面情绪的爆发几乎断送了朴槿惠的政治生涯。政治事件的性质决定了它关乎国民利益,民众的参与度无疑是极高的,相对自由的媒介平台很可能会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的产生,而过于保守权威的媒介报道又会致使公共话语空间的缺失。
群际情绪是指个体认同某一社会群体,群体成为自我心理的一部分时,个体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情绪体验。从政治事件本身来看,一旦受众通过媒介的影响进入了与“闺蜜门”对立的群体,自然就会产生相应的群际情绪,而其反应的程度也决定了事件的影响力大小与预期的发展情况。美国心理学家史密斯提出,群际情绪是认知一情绪一行为的三者融合。笔者以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线,结合群际情绪中的认知评价、情绪与行为倾向的演变进程,分析媒体在这场事件中的影响。
蛰伏期:媒介赋权下的认知塑形,朴槿惠丑闻被揭露
在群际情绪理论中,认知评价过程是群际情绪形成的第一步。在事件的蛰伏期,媒介往往通过引导来决定公众印象的初步形成与认知的塑形。在“闺蜜门”事件中,梨花大学的学生维权运动与调查是蛰伏期的标志。学生群体由于教育资源与成绩评估的不平等对校长发起弹劾运动,就抗议的规模上来看,行为的实际参与人数有限,所达到的影响也不会如此巨大,但新媒体社交平台为学生这一“弱势”群体的赋權改变了事件发展的进程。在社交平台导致的传播赋权过程中,社会民众能通过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实践陸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获得权力和能力,从而获得改变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媒介的赋权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将维权的信息通过新媒体渠道进行发布与扩散,扩大了运动的民众参与度与影响力;二是在网络媒体上对崔顺实女儿郑维罗的信息进行检索与挖掘,并对结果进行公开发布,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为“闺蜜门”事件的发酵奠定了基础。
在事件发生的蛰伏期,媒介倾向于依照社会规范与主流价值观对信息进行一定的加工,在网络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信息就完成了发布者、受众与媒介的三重选择,使公众产生了相应的印象与初步认知,即崔氏借用朴槿惠的势力达成了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行为。虽然在此过程中,媒介并未将言论联系至实际,选择[生图文信息的呈现也极可能是失真的,但社交媒体中所体现出的现象与韩国社会基层民众对资本政治上层人群的恶意揣测不谋而合。这意味着民众尤其是可能受到相似迫害的学生群体,极易接受这种形式的认知塑形,而这也促进了朴槿惠丑闻被揭露的进程,以及出现日后在以学生群体为主的推动朴槿惠下台的游行活动。同时,事件蛰伏期的铺垫也将此事件先行引到了社会领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群众认知基础。
发酵期:力量博弈下的情绪激发,民众负面情绪迅速发酵
早在2014年,以保守派著称的报纸《朝鲜日报》就已经开始关注朴槿惠执政背后的一些疑点与端倪。在总统秘书室行政警官对朴槿惠前任助手郑润会(即崔顺实前夫)的秘密调查中,就有爆料称朴槿惠在韩国的权力排在夫妇二人之后,而当时的韩国舆论对此并未给于反应,除了民众缺少对事件的基本认知,当时的政治局势显然也会压制此类报道。同样是在2015年,《朝鲜日报》在对青瓦台人事调整以及“文化荣盛项目”的调查中,掌握到了崔顺实的一些线索,却又以时机不成熟为由放弃报道。2016年,韩国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失败后,《朝鲜日报》终于开始对青瓦台进行深入调查,并从7月起在反对派的支持下对崔氏相关的两家基金会进行丑闻披露。8月,青瓦台对《朝鲜日报》进行打击,促使其收敛报道内容,而在韩国一些媒体对崔顺实身份进行公开后,《朝鲜日报》将其之前收集到的所有材料公之于众,开始对青瓦台势力进行反击。由于其新闻的发布时间主要在梨花大学对郑维罗的身份调查之后,在内容上对与青瓦台相关的经济陸丑闻进行了切实地披露,使青瓦台势力受到了打压。因此,笔者将其对事件线索跟进而进行的阶段陸报道归结于此事件的发酵期。
在政治丑闻中,群体所感受到的大多是强烈的负面情绪体验。在事件蛰伏期负面认知的引导下,这家保守派媒体通过对事件线索的阶段陸报道持续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此时政府对报道的遏制反而会激发民众的反抗情绪,新闻内容中对丑闻事实的逐步揭露也使民众的负面情绪应运而生。在事件的发酵期,媒体偏向于模式化的报道方式,尤其以保守派媒体为例,虽然存在着对基金会集资事实的揭露,但政府的管制仍是制约其行为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基层民众对媒体的信息披露心理期待值很高,一旦媒体出现报道立场上的反复,民众对于政府的抵制情绪就会快速发酵。基于此,媒体的报道方式成为这一发酵过程中的重要催化剂。同时,这种群际情绪所引发的负面舆论极易导致谣言的蔓延。在这期间,关于邪教献祭、意识控制等传闻在网络媒体中散播开来,甚至有人将其与之前的沉船事件进行联系,这些难以制止的网络谣言在韩网的飞速流传对民众的负面隋绪进行了进一步的激发,将事件推向了质变。
爆发期:舆论引导中的行为纠偏,明晰与梳理复杂的舆论场
毫无疑问,这场政治事件的爆发期源于JTBC电视台对废弃平板电脑内容的揭露,2016年10月25日起,韩国众多民众与高校学生多次举行大规模集会,并以各种形式对朴槿惠进行嘲讽与批判,要求其下台。在此过程中,处于这场风暴核心的媒体JTBC也从一家成立不到五年的有线台摇身一变成为目前关注度最高的新闻频道。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这家电视台身后的财阀势力对持续跟进报道与政党势力的博弈。作为最关键证物披露方的媒体,相比于事件爆发之后才进行跟进追踪的SBS等老牌媒体,它显然已经掌握了“闺蜜门”事件中的公信力。在对关键证物的披露过程中,它将自身拿到的所有材料都直接呈现给观众,并且JTBC的报道不限于电视直播中的可视化呈现,还将信息分发至多种社交渠道,利用YouTube展开实时直播,使更多民众尤其是韩国的年轻人能够通过更多渠道获得事情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电视台也通过对信息的全方位展示,从源头上杜绝了一部分虚假消息的传播。通过对目前情况的官方解读,为事件爆发之前复杂的舆论场进行了明晰与梳理,引导公众对这场政治事件的认知趋于理性化。
在政治事件中,媒体无疑是公众对事件观察的一面镜子,当然,公众也不是机械化的个体,媒体必须通过对报道的客观化以及对公众诉求与价值取向的适当迎合,才能够真正引导具有主观性的群体。在“闺蜜门”事件中,媒体的职能缺失也并不在少数。由于目前青瓦台势力的削弱,一些媒体为了争取最广泛民众的支持以及摆脱权力对自身的干预,它们陷入了不同程度的非理陸与激进中。这种情况尤其以网络媒体最盛,在当今的韩国舆论中,崔顺实的参政程度目前是并无定论的,而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鼓吹崔顺实对韩国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这些行为都会为媒体的舆论引导中的行为纠偏带来阻碍。
政治事件中媒体的作为,对群际情绪与舆论影响的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结合媒体在事件蛰伏、发酵以及爆发过程中的影响方式来看,媒体分别从对群体的赋权、对事实的披露以及舆论的纠偏三方面来对政治事件的进程进行了导引。当然,这场政治事件自身所携带的特質,如女性为中心、傀儡政治这些吊诡的现象自然也是引发其迅速传播扩散并引起剧烈反响的原因。韩国作为一个典型以人情为特色的东方国家,民众对于政治环境中的权钱交易与门阀政治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其接受限度大概也仅局限于权力中心对周边的辐射式影响,而这次的“闺蜜门”事件使公众震惊的是国家的总统竟然会被一个特殊的小圈子操控,这将使韩国人对政治架构的不信任感大大加重。
政治事件中媒体的作为对群际情绪与舆论影响的程度之深,我们可见一斑。因此,将其投射至宏观的角度来看,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媒体还是公众最主要也是最可信的信息来源,为了保证对民众认知、情绪与行为的恰当引导,媒体需要适时转变角色,针对事件进展的不同时期对群体进行及时的平台构建与信息补充。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求报道基本内容的客观与准确,而是政治陸内容披露所带来的与权力的博弈也是亟需社会责任感与自身担当的。对真相的追求、公众的支持以及自身利益的平衡将是媒体一直以来的追求所在。
在韩国的政治生态中,政治人物总有其幕僚,幕僚多年来忠心耿耿地伴其左右,为其出谋划策。一旦政治人物位居高位,跟随他多年的幕僚就成了青瓦台总统秘书的首选。发源于幕僚的总统秘书,不需经过国会听证,由总统钦点,制度对韩国总统秘书几乎没有约束力。韩国多次有人要求改变对总统秘书特别机制的提议,但最终都未真正实现。
在韩国,检察官地位高、权力大、国民支持度高。如果“闺蜜门”事件能够促使韩国改变其总统秘书的特别机制,将净化其政治生态。毕竟,“闺蜜门”事件给了韩国人一个反思政治痼疾的契机。但是,“闺蜜门”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几大财阀,而这些财阀又离不开国家的扶植,尤其是政府控制了金融业,那些财阀自身没有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提供的贷款,乃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韩国社会金钱政治、政商勾结根深蒂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根除亲信子政、亲信腐败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全国新闻自考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李芮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在‘茉莉花革命中的作用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1BXW03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峰、佐斌:《群际情绪理论及其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6期。
②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③李春雷、舒瑾涵:《群体性事件中舆论场域的媒体构建路径分析》,《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8期。
④朴东勋:《韩国“闺蜜门”的走向及政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第11期。
责编/高骊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