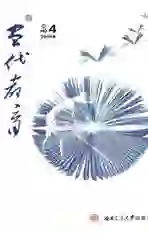他的微笑留在我心里
2017-03-18刘福林
蔚桦兄走了,带着微笑走到“那边”去了。不,那微笑没有带走,还留在“这边”,留在我心里。
我与他是在《贵阳晚报》见面相识的。《贵阳晚报》大约是1978年创刊的。我与他都被列入第一批调入人员名单,他调进了,我因厂领导坚决不放而未如愿。那时计划经济恶习还十分浓厚,人才流动阻力极大,我只得身不由己被卡在那鬼地方苦熬。但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晚报社走走,于是我们便谋面相识了(其实早就在心里互相认识了)。第一次见面握手,他就送给我满面微笑,留下十分谦和的形象、十分婉约而又专业的谈吐。这个良好的“老哥子”式的第一印象,使人产生愿意长久交往的感觉。
当时我正处于诗歌创作的高潮期,不断有作品发表,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就是关系亲密的表现。他为人很正派,对文艺界的一些“歪”事很厌恶。那段时间,他经常见到我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诗作,而且我的名字排在后头。他对那位与我合作者的底细很清楚,因而感得很奇怪:难道刘福林不如他吗?一次在中华中路的新华书店门口,蔚桦兄碰到了我,便问起我们合作发表诗作的事,很想知道点内情,证实点什么。而我是个很能委屈求全,很能吃亏,也很能顾及他人面子的人,因而没有把祥细内情如实告诉蔚桦兄,过后想来觉得有点内疚。估计蔚桦兄也能猜测得出我们的内情,也能体谅我的难言之隐,所以他没有责怪我。以后每次见面,他还总是满面微笑,一幅老哥子不计小弟过的姿态。1981年第3期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发表了我的一个组诗,他很快就看到了,见到我时,满脸微笑地向我表示祝贺:“能在这份很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诗,还是组诗,不简单,为你高兴。”后来有多次我俩在青年文学活动中相遇,他总是微笑着,有时还拍拍我的肩膀向不认识我的青年朋友们推荐说:“他叫刘福林,很有成就的诗人。《十月》发表过他的诗,还是组诗,不容易呵!我省作者在《十月》发表作品的不多。”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我的诗水平不高,力度不够,曾经努力向上发起过冲锋,但总是冲不上去。蔚桦兄这样热情地推举我,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蔚桦兄才是真正有成就的老资格的诗人。青年时代他在云南当兵时,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成为部队和云南较有名气的军旅诗人。退伍回贵州后,他仍然写诗,但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扼杀了他的诗才,使他的诗没有出路,无法见“天日”,只得“孤芳自赏”。粉碎“四人帮”后,文艺从严酷的寒冬走向了温暖的春天,当初几乎是暴发式地繁荣。曾经郁郁寡欢了十来年的蔚桦兄前程豁然开朗,不断用诗畅抒胸怀,脸上时时都绽放出抒心的微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从极左路线的深重灾难中走过来的蔚桦兄,深切感受到在粉碎“四人帮”中力挽狂澜、斩妖除恶,接着又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位伟人邓小平,救国、救党、救民的伟大功勋。他倾尽全部的诗才,大手笔地创作出一部我省诗歌史上的宏篇巨著《邓小平之歌》。这部长诗也可以说是在全国首开先河。它不仅仅是爆发了他个人的思想感情、艺术功力,更是情真意切地抒发了所有從极左路线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渴望自由、民主、平等、科学、进步、美满、幸福的人们对这位伟人的赞颂、崇敬、爱戴、感恩之情。
思想解放后大展才华的蔚桦兄,感恩这个来之不易的新时代。在他所经历的人生中,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愉悦、快乐、奔放,因此脸上时时都挂着情不自禁的微笑。曾经有道“愤怒出诗人”,蔚桦兄却反其道而“微笑出诗人”!现在他微笑着走了,但在我的心里还久久地留着他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