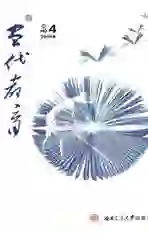猫?归
2017-03-18张出尘
张出尘
天蒙蒙亮,院子里外婆栽的花儿,红的红、黄的黄、白的白、紫的紫,抖擞着叶子,在夏日的阳光中开放了。远近的鸡鸣打破了小院的宁静,“嗑!嗑!”烟杆敲打着石板台阶,隔日的烟灰碎碎屑屑,连带着清新的空气都被染上了浓浓的烟草味。
“起来咯!出晨去!”外公嘶哑的嗓音穿透堂屋里外。我和弟弟来不及系上鞋带,衣扣错了位也不管,急急忙忙地赶上已经迈出门槛的背影,高高兴兴地仿佛认为天底下的大事也不过就是随着外公出晨去。
一天中离家的时间可以这么早,候着东方朝阳的升起;一天中回家的时间也不用那么晚,等到西方的夕阳浸红了天。
外公、我、弟弟清早从家出发,慢慢走上一公里的路,来到镇外的祠堂,找一块磨光的大石头坐下歇口气儿。我和弟弟交换路旁采摘来的野花和果实,拿一根细长的草茎逗耍着抓来的蚂蚱,外公斜举起长长的通体漆黑的烟杆,“哗啦”一声擦燃火柴,凑近烟杆头,啪嗒啪嗒地吸着气,黄褐色的烟草冒出点点火星,火柴棒也快烧到了尾,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吁——,日子好长。
外公话不多,和我说话的情景哪怕死劲回想想破了脑袋也记不起一个。记得清的只有外公常年穿的深蓝色、质地坚硬的中山装,一根或枣红或漆黑的长烟杆随身携带,一顶藏青色的毡帽总落着几点烟灰,涩人的烟草味涌进旁人的鼻腔冲荡了整个身心,并遗下一阵阵涩烈的余响。我和弟弟对外公一直怀着敬畏的矛盾心情,远远地我们玩我们的,嘀嘀咕咕地小声讨论回家后怎样丢几样鲜花、果实偷偷地喂外公养的麻雀,但偶尔又故意发出巨大的笑声,像是要把自个抽烟叶、望着远处眯睱着眼的外公吵醒。记忆中并没有外公被搅醒后恼怒的模样,而是我和弟弟一边不停地傻笑,一边追打对方越跳越远地逃跑了。
我离开小院已有十年,外公去世也过了五年。敲打石板的嗑托声恍若隔世,出晨时看见过的鲜花、听见过的鸟鸣、抚摸过的风儿渐渐褪色,甚至浓浓燃烧的烟草味儿也需闻到与之相差无几的烟味,在遭遇空白、模糊、停顿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地说:“噢,这个气味我从前闻过。”
每年的清明节祭奠,于我而言只是一场活人责任性地除草任务。真的思念无需刻意的时间、地点的提醒,正如一颗流星迅速地划过天边是个大大的偶然,想念一个人时他生前种种虽一瞬即逝,却也感受得到余光带来的颤动。上香、跪拜、烧纸完毕,亲戚朋友在坟冢上滞留了一定的时间。收拾收拾,扒开挡路的灌木,留意脚下滚动的碎石,到了山脚回首瞧一眼淹没于荒草丛中的墓碑,最后朝向来路转身归家。
我和弟弟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彼此无话可说。间或搭了几句话,也只能以随声附和匆匆结束。弟弟的个子比我高出不少,臂膀不似小时候我作姐姐时可以任意捏拿的了。每次被我欺负得厉害时,就抽抽嗒嗒地跑去找闭着眼假寐的外公,他哽咽着喉咙乘我不在搬弄是非,两个小人吵得急了又有打一架的势头,外公好整以暇在关键时刻掏出几角零钱平息了我和弟弟的怒火。第二天又接着带我和弟弟欢欢喜喜地出晨去了……
“咦?有只死猫!”弟弟突然惊叫出声,将我从好不容易回忆起关于外公为数不多的记忆中抽离出来。我顺着他指示的方向一看,原来在几堆杂草的遮蔽下,躲藏了一具黑猫的尸体。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只流浪的猫静静地在草垛中睡着了呢。枕在前腿上的头微微前倾,眼皮并未紧紧闭合而露出一条缝,毛茸茸的尾巴盘曲着包裹住整个猫身,就是一只在家里温暖的火堆旁睡熟的猫咪罢。
曾听人说起,家猫临到死之前是知道自己要死的。它们会在那天从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离家,拖着老残的沉重躯体,走得离家越远越好寻个最好无人发现的角落,然后等待死亡的最终降临。丢了猫的人家会逐渐忘掉猫是白色还是黑色的、喜欢躺在沙发上还是喜欢躲在柜子里,是不是喜欢把老鼠的尸体放在冰箱下……都会随着时间忘了,就像人的离世一般。
彼时外公的身体每况愈下,隔三差五地来回跑医院,糟糕的是最后连路都走不动只能躺在病房里了。不能相信,这哪是孩提时期带我和弟弟连续走上一公里中间不喘气的人呢?外公本就瘦,但他是瘦得精神矍铄。我上高中后学业繁重,外公住院有一段时间了我才抽空去看望他,并且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刺鼻的消毒水味洗刷掉我一身的烦躁,来来往往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及护士提醒了我这里不是有小院的外公家,或许有一天外公会真正的死去并不会回来了。
推开病房门,外公就仰躺在内。仅剩的一层皮紧绷在他的脸颊,枯瘦的双手青筋爆出,双目失了平日的精神,浑浊的眼球直愣愣地只是往上看。我木呆呆地站在原地,害怕多看外公一眼,嘀嗒嘀嗒地数着药水滴进血管里的次数。爸爸俯下身轻声示意外公我来了,外公機械般转动脖颈用浑浊的眼球看向了我。凄凄凉凉的,我习惯性地脱口叫了声“外公”。他听见了,口齿不清地用单音节的词应我。我遵照一般看望病人要做的事,询问了大体的身体状况,潜意识里自动忽略了问外公多久回家。
尴尬难耐的我,坐在椅子上那一刻是无比希望尽快离开的。外公大抵是看出了艰难地轻微晃动着枯枝般的手臂,含糊不清地说:“走,走,回去学习去。”
出了医院,被冷冽的冬风一吹,我哭了。
两个星期后,我再次回到坐落在小镇的小院参加外公的葬礼,只是那一天我挤不出眼泪。
眼前是绿油油漫无边际的嫩草,金色的油菜花零星散缀,胭脂花的果实还未变黑,一掐就能掐出汁水。弟弟因发现了猫尸,开始话多起来。聒噪的样子,仿佛让我回到了小时候。
还是夕阳西下,火烧云像断了的棉絮般,絮絮攘攘地铺满了整个头顶的天。我和弟弟背靠背坐在发烫的石头上,发配今日捕获的战利品。外公站在远处,佝偻着背,擎着烟杆向我们这边喊,嘶哑的声音好像在说:“回来了!归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