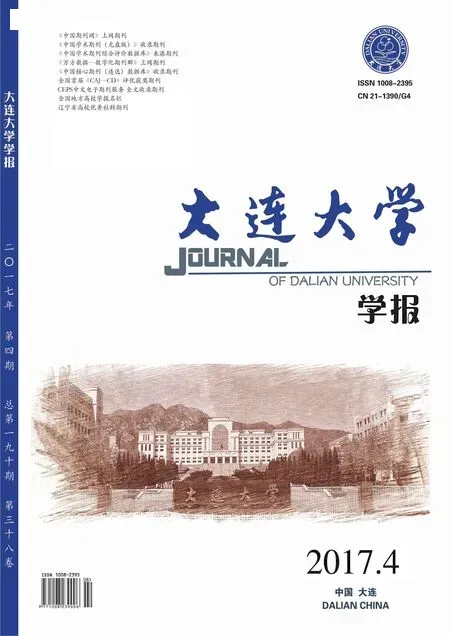迷失与追寻
——托尼・莫里森《爵士乐》黑人身份主题解读
2017-03-14刘惠媛
刘惠媛,周 旭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迷失与追寻
——托尼・莫里森《爵士乐》黑人身份主题解读
刘惠媛,周 旭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在群星璀璨的美国黑人文坛,最闪亮的莫过于托尼・莫里森。作为世界闻名的非裔黑人小说家,也是世界上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她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都显示出黑人文化传统的深刻烙印。本文以托尼・莫里森《爵士乐》中的美国黑人身份解读为切入点,通过对《爵士乐》中主人公身份“迷失”及“追寻”等主题的梳理,系统分析黑人历史及黑人文化对其身份建构的内涵,解读托尼・莫里森作品的独特魅力。
黑人身份;迷失;追寻;文化内涵
一、引 言
当前,在非裔小说家中,托尼·莫里森是一位在生活和创作中都十分关注自身认同的作家。她于1992年出版的小说《爵士乐》便是其代表之一,小说历经十年,在美国七十年代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虚构而成。与众不同的是小说并非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文本随意性是该书的最大特点,人称和角色的心理变换即兴跳跃,好似一出精彩绝伦的爵士乐,有前奏、高潮和结尾。这些安排旨在反映20世纪初黑人的生活情况和社会现实。
小说主要围绕在黑人夫妇乔、维奥莱特和黑人少女多卡斯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其间叙述了从南方乡村迁居到北方城市的乔与维奥莱特在此过程中的情感变化以及性格演变。主要情节是:中年黑人男子乔·特雷斯爱上十八岁少女多卡斯;多卡斯移情别恋,乔愤怒之下将其射杀,而多卡斯拒绝就医导致死亡,妻子维奥莱特知晓后打闹葬礼;在与多卡斯姑妈的交谈中了解了她的过去,放下心结后,转变态度,选择原谅,与丈夫和解。
本文拟通过对作品中隐含的迷失主题进行深度剖析,揭示黑人在社会、家庭和自我三个层面的迷失,分析其背后原因,并探寻莫里森对此主题所表达的意义。
二、黑人迷失的缘起
伯纳德·W·贝尔在《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中提到当代黑人小说:“大多数的非裔美国黑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像他们19世纪的先辈一样,并不倾向于他们的叙述作品中忽视道德和社会问题。”[1]
莫里森人生经历丰富,家中排行老二,祖辈当过奴隶,双亲原为美国南方佃农,为摆脱贫困与种族歧视迁徙至俄亥俄州。讲故事、听民间故事、歌唱构成了她主要的重要生活,也是日后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她的作品中贯穿了对黑人民族的关注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反思。《爵士乐》这部作品就是设定在20世纪初南方黑人迁居到北方工业城镇的这一时代浪潮下,黑人生活的迷茫与挣扎。不得不说,《爵士乐》中也暗含着她父辈的影子。小说以一场婚外恋为引子,男主角黑人男子乔·特雷斯年约五十,由于个人与社会原因与黑人妻子维奥莱特关系冷淡,出现婚姻危机,其后恋上黑人女中学生多卡斯,因其移情别恋被乔开枪打死,其间涉及到黑人众生相。
莫里森的作品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她力图用作品来反映黑人现状以及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以达到反思及求变的作用。在小说《爵士乐》中,莫里森从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破裂、自身的孤独感等方面再现了20世纪哈莱姆地区生活的黑人的迷失。
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上,《爵士乐》小说展示了美国黑人在白人社会中异化的不同反应。尽管黑人占美国人口的一份子,但他们仍然被白人排斥,处于社会边缘。
书中多卡斯的姑妈便是其中代表,象征着一生遭受着苦难的传统黑人妇女。黑人暴动带来的政府镇压使得黑人处境艰难,以为人洗衣维持生计的爱丽丝目睹了妹夫被汽车压死,妹妹之后被火烧死之后,她成为了恪守规矩的人,减少与白人接触。第五大道是她最怕去的地方,“在那里,白人从小汽车里探出头来,手里隐约露出叠好的钞票,在那里推销员摸她,就好像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们来屈尊出售似的;商店的经理要是够大方,让你试件衬衫(帽子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纸巾。在那里,她这样一个经济独立的五十岁女人没有姓氏。”
由于亲人的惨死,让这样一个淳朴的黑人妇女更想要保护好侄女多卡斯,潜意识地认为黑人为求自保,必须得低人一等,不能太过耀眼。为此,她教导侄女在白人女孩面前装聋作哑,走在路上靠着大楼墙根,躲避白人,禁止多卡斯化妆打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丽丝也不例外,也喜爱靓丽的女性,但她却只能把这种艳羡之情藏于心中。然而她所做的一切似乎起到了反作用,多卡斯往着反方向发展。
书里描绘的黑人角色大多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勤恳工作,遵纪守法,期待在白人社会获得一席之地,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不为社会接纳,被边缘化而迷失,从而导致自我分裂和自我身份的迷茫。
残缺的家庭关系也是小说中人物陷入迷失状态的表现。书中描写的角色家庭几乎没有幸福美满的。黑人少女多卡斯的父母在暴动中惨死,黑人中年主妇维奥莱特的父亲忙于黑人运动,无心照顾家庭,对家人不管不问,家里一贫如洗,时常有人要债,母亲不堪重负投井自杀。其夫乔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三次寻母无功而返。
主流社会的排斥、残缺家庭使得非裔美国人一直边缘化,没有归属感,一股孤独之感弥漫在整部小说之中。
由上可见,小说致力于叙述哈莱姆黑人群体在精神上,价值观上面临的困境,以及普遍的迷失现象。这也不由使人深挖隐藏于内的根源。
三、黑人迷失的具象
莫里森在《外国语文》2016年8月份刊登的《文学的情调——托尼·莫里森访谈录》中说道:“时间流逝,世界在变,人的思想意识也在成长,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时空、心境、视角都会带来不同的认识。”《爵士乐》中的主要人物正如她所说,随着情节发展,思想意识、性格也经历着一场演变[2]。
(一)家庭的忽视
本文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家庭的缺失。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一切都处于暴动之中,到处都是游行示威,充斥着暴力和疯狂。多卡斯本来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女孩。父亲在圣路易斯东区拥有一家台球厅,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活还算富足。可是在那个暴乱的年代,尽管父亲并未做任何出格的行为,也没有武器,却硬生生的被人从电车上脱下来给活活踩死,母亲去现场后忍住悲痛回家,可是房子被点燃,于是活活地被大火烧死。多卡斯当时在好友家睡觉,躲过一劫。可是悲剧发生后,她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对此事不再提起。自此之后,她由姑妈抚养,变成了玩世不恭的女学生。
在主人公黑人主妇维奥莱特的记忆中,父亲因为参加黑人运动常年在外不归,母亲独自一人维持家计,为此常常入不敷出,家里常常会有讨债的人,家里有时候需要靠邻里接济方能度日。一贫如洗的家庭状况让母亲不堪重负,尽管后来外婆特鲁贝尔听闻消息后帮忙管理家庭,可是母亲似乎并未因此好转,不堪精神压力而选择投井自杀。父亲回家后对于母亲的死讯的反应也是十分冷淡,只是说“见鬼。噢,见鬼。”然后呆了几天又一走了之。父亲对于子女似乎也不太在乎。母亲的悲惨遭遇让她对孩子产生顾虑。“维奥莱特从中得出的重大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孩子。不管发生什么,绝不要有一双小黑脚叠在一起,一张饥饿的小嘴叫着:妈妈?”[6]106外祖母每天都会讲述她在白人家帮佣的日子以及女主人的儿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被迫早早出来工作,于是在工作之余认识了乔。家庭缺少关爱让她义无反顾的离开家乡追随乔。童年的阴影使他不敢要孩子,而年纪渐长,对孩子的渴望越来越强,最后差点做出抱走白人家小孩的事情。
乔则是个孤儿,被黑人夫妇收养后一直被养母像亲儿子一样对待,为此询问养母父母下落,并且把养母的话误解成父母一定会再次找回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乔生性敏感,就像一个小男孩一般,心理的隔阂使得他无法和养父母的家庭融为一体,早早的出去打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久的毫无音讯等待使得他想自己出去寻找母亲。他寻找了三次,每次都离身为“野人”的生母距离很近,可是母亲一直不肯现身,有意躲避着他。多次寻而不得,让这件事情成为乔的心结,他渴望被爱,但是也缺乏与爱人沟通的能力。他把孩子看成麻烦,让维奥莱特两度流产,侧面体现了他对亲情的淡漠。乔的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也为后来夫妻不和,他转而投向多卡斯做了铺垫。
(二)社会的缺位
故事的大背景是美国的大迁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工业城市的飞速发展使美国社会十分繁荣,同时,美国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人民。当时,在黑人眼中,大都会的生活深深地吸迎着他们[3]。
书中也对黑人的美好憧憬进行了描述:“干清闲工作就能赚钱——在大门前面站一站,用托盘内送送食物,哪怕给陌生人擦擦鞋子——你一天里挣的钱比他们在真正一个收获季节挣的还多。白人们简直是在把钱扔给你——就因为你热心帮忙:给出租车开开门,拎拎行李。”[4]111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书中也多处暗示当时黑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乘务员正好路过,觉得好笑却没有笑,他没有必要在这节坐满黑人的车厢里面露笑容。”[4]31
黑人少女多卡斯好友费丽斯对于学校和母亲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在学校里朋友不是很多。在我念书的学校里,不是男孩子凭着皮肤颜色结伙抱团,女孩子才是这样。”[4]213
“我知道那枚戒指是母亲偷的,她说是她的女老板送给她的,可我记得那天在提分尼商店见过它。一枚银戒指,镶着一块叫做蛋白石的光滑的黑宝石。我妈妈来取一个包裹,那个女售货员就去拿了。她给那个姑娘看了她的女老板写的条子,这样他们就会把包裹交给她(甚至在店门口也要出示条子,这样他们才会让她进来)。”[4]214
在多卡斯被枪击后,费丽斯拨打救援电话,可是事实却是残酷的。因为听到需要救治的人是一名女性,于是救援队第二天早上才到,延误了救治时间。
这些例子都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对于黑人问题的冷漠,种族问题的严峻性。当时动荡的社会,许多白人将其归咎于黑人。乔、维奥莱特以及其祖母是逆来顺受的代表,而年轻一代多卡斯、费丽斯则寻求改变,用自己的方式对歧视提出反对。
(三)自我的沉沦
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传统价值观也在逐步瓦解,“迷惘的一代”应运而生,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成为其人生信条与行事准则。
多卡斯是小说中独树一帜的反叛者,在大城市的喧嚣中长大的她深受城市文化和白人文化的影响。不同于姨妈的默默忍受,为了让自己更出众,她选择了这种玩世不恭的反叛社会的生活方式。多卡斯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她没有想过未来,想方设法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努力让自己成为舞会中的焦点。在她看来,“只有裤腰带以下的生活才是生活的全部所在。”[5]60因此,大都会的诱惑让多卡斯自甘堕落,为了满足所谓的虚荣,她肆无忌惮地周旋于各式各样的男性。这也为后文的被枪击埋下伏笔。作者借多卡斯的悲惨结局说明,“黑人女性只有两种,一种是拿着武器的,另一种是手无寸铁的,她们都没有好下场。”[5]77-78
辗转来到心仪已久的大都市,乔和维奥莱特物质上得到了极大丰富。可是在都市这个大染缸里,两人都发生了变化。两人的感情似乎发生了中断。维奥莱特似乎有了精神崩溃的症状,与人交谈老是文不对题。在大城市中,她似乎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她不像乔原先认识的那个干净利落、有主见的女人。渐渐地开始沉默寡言。在家里也不和丈夫说一句话,一直围着家里的鹦鹉转,鹦鹉会一直回答我爱你。
在这种情况下,乔也忍不住向朋友玛尔芳抱怨:“维奥莱特对她的鹦鹉比对我照顾得更好。余下的时间,他就坐我不能吃的猪肉,要不就烫头发,我受不了那味儿。也许结婚像我们这么久的人就是这样。可是那份安静啊。我真受不了那安静。”[4]50
在夫妻感情中迷失的乔在推销化妆品的过程中认识了多卡斯。相似的经历使他们惺惺相惜。多卡斯成了乔的精神寄托。与其说乔对于多卡斯的感情是爱情,倒不如说亲情的成分更多。
四、黑人身份的追寻
《爵士乐》中,追寻的情节层出不穷。小说中的黑人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仍然继承着非洲祖辈特征,他们渴望在美国找到心灵的栖息之所,为此对自身的认同与追寻是黑人一直以来的追求。
黑人中年男子乔作为一个孤儿,一直在追寻母亲的足迹,更换了七个名字。名字的更换和寻找母亲都表明了他对自身身份的疑惑,也说明他对于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寻母也是寻找心灵皈依之旅。
维奥莱特对于自身的反思和最终确定自我也贯穿着全文。发现夫有婚外情之后,维奥莱特一直很愤怒,所以有了小说开头的葬礼毁坏多卡斯尸体的举动。她将一切的责任都怪罪在多卡斯身上。随后,在与多卡斯的姑妈爱丽丝多次交谈的过程中,维奥莱特了解了多卡斯的身世和经历,使她潜藏内心深处的母性给激发了出来。“她到底是哪个抢走她男人的女人,还是那个逃出她的子宫的女儿?”“再有一次,再有一次,我也会爱她的。”[4]114她在如何面对多卡斯这个女孩的态度上摇摆不定。这时候,已经成为她好友的爱丽丝的话点醒了她“用你所剩的一切去爱,一切,去爱。”[4]118
穿插其中的格雷寻母也照应了追寻这一主题,上层阶级白人女孩薇拉•路易斯因为与黑人青年的私生子与父母闹翻,于是便将维奥莱特祖母特鲁•贝尔一起带走独自生活。这个私生子就是戈登•格雷。母亲从未提起过父亲,但一直都有着对父爱的渴望,在得知生父真实身份后,他如是说道,“只有现在,他想,当我知道我有一个父亲的时候,我才感到缺少了他:他应该在这个地方,其实却不在。”
通过仆人特鲁•贝尔所给的线索,一路跋涉,他找到了父亲。寻父之旅是他的思想蜕变之旅,从得知自己有黑人血统的抵触的态度到完全接受。父亲的一番话让他不再纠结自己的肤色和血统问题,重新认识自我,确立身份。
寻父寻母本质都是对自我身份定位的追寻,追寻的过程也代表着黑人对自我的肯定与接受,这也是莫里森借小说想要传达给读者的讯息。
五、结 语
爱一直都是莫里森小说的主题,《爵士乐》通过莫里森独特的组合方式,以乐曲的方式排列组合,时空交错,让主要人物自己说出自己的故事,由此传达出了黑人的文化底蕴。它暗示了小说时代背景:故事场景设置在1926年美国纽约的哈莱姆黑人聚集区,当时这里的大部分黑人是从家乡迁徙到此自立谋生。与此同时,爵士乐更象征着文化碰撞与融合。在这个大背景下,小说中乔、维奥莱特、多卡斯等人成为了那个时期黑人的代表,他们的故事也让读者了解了当时黑人到大城市生存的心路历程,以及黑人内部磨合最终融合的过程。作者试图用两性的融合解决文化的冲突,结尾夫妇的重归于好也暗示着文化的融合,强调了爱和交流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1]伯纳德·W·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496.
[2]焦小婷.文学的情调——托尼·莫里森访谈录[J].外国语文,2016,32(4):1-4.
[3]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5.
[4]托尼莫里森.爵士乐[M].海口:南海出版社, 2006.
[5]Toni Morrison.Jazz[M].New York:The Penguin Group,1993.
Abstract:Toni Morrison, 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world-famous stars and writer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fro-American female Nobel Prize winner in Literature, is deeply rooted in black culture writing.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lack history of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a focus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theme of Jazz as in “loss and pursuit”.The cultivation of Jazz will explore the uniqueness in Toni Morrison’s works.
Key words:Black identity; lost; pursuit; cultural connotation
Loss and Pursuit——An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Blacks’ Identity in Jazz
LIU Hui-yuan, ZHOU Xu
(College of English,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I712献标识码:A
1008-2395(2017)04-0040-05
2017-02-10
刘惠媛(1968-),女,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周旭(1992-),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