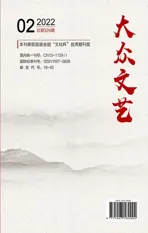论《边城》中暗藏的残酷性
2017-03-13廖鹏飞玉溪师范学院653100
赵 敏 廖鹏飞 (玉溪师范学院 653100)
论《边城》中暗藏的残酷性
赵 敏 廖鹏飞 (玉溪师范学院 653100)
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情美”“人性美”的背后却暗藏着不可抹杀的残酷性。妓女的麻木,刀客的横行,船总顺顺与老船夫形成的强弱关系,在《边城》里隐约可见。
悲情;残酷性;强弱关系
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处于动荡、混乱之时,这样的时代需要有鲁迅的《呐喊》来唤醒民众的愚昧,需要有郭沫若的凤凰在烈火中再生。痛苦的时代需要愤怒的作家。而沈从文一再强调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关注乡下淳朴的生活方式,而蔽去城市扭曲的人性不表,有意用湘西边城的田园河溪的风情来表现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于是,有的人认为“《边城》不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缺少深广的社会内容与深刻的社会主题。”2有的人说“《边诚》不是现实主义作品,”直指“不真实,不典型”。3
多数人都认为《边城》主要体现的是湘西“人性美”“人情美”。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强调:“用坚硬的石头堆砌而成的希腊小庙上,供奉着‘人性’。”很显然,他是对有些论者单从阶级性、典型性去理解《边城》的反拨。强调反映的是“人性美”,健康的“人生形式”。应该说,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理解是最有说服力的。正像《阿Q正传》的多重意义,《哈姆雷特》的多样解读,都已超乎作者当时写作时的思想意蕴。或许他作品中所反映的深广意蕴连他自己都还尚未发现。《边城》自问世之日起,因其形式与内容的别样性,人们对它理解是多样的,甚至连沈从文也不甘寂寞,要对自己作品强调说明。本文试着探讨《边城》中所呈现的现实意义和边城社会染上的与整个中国俱有的残酷性。
沈从文出身于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半殖半封的时代,列强的入侵,政府的腐败,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痛不已。沈从文从小体悟到了生命瞬间灭亡的恐惧。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对死亡、黑暗、腐朽的深恶痛绝,他骨子深处既存有湘西纯朴的“人性”,也有对肮脏社会的诅咒。而他更愿意把人性中的“真、善、美”表现出来,以呈现给世人达到净化世人灵魂的效果,与鲁迅改造国民性同流。只不过沈从文隐藏丑恶于深处,在他的文章中很难直观显现现实,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4这“背后隐伏的悲痛”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是怎样的“悲痛”以致于让作者来提醒读者?可以见得,这份“悲痛”在其作品中的分量。
小说第一节中写到翠翠父母的往事,军人和老船夫女儿的爱情应该是幸福美满的,如果他们真是两心相悦,还有必要“背着那忠厚的爸爸发生暧昧关系吗”?这其中,深隐着一种封建世俗观念,在未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男女关系便属于不正常,要成为“合法”的恋人,必须通过家长和长辈的允许。显然,军人和船夫的女儿不在“规矩”之列。在未得到世人的承认以及为了维护“作军人的名誉”,军人“首先服了毒”。船夫的女儿在生了小孩(翠翠)之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这一对本该拥有幸福未来的情侣,还为尝试爱情之果的滋味,便命丧阳世,可悲可叹。沈从文似乎没有告诉读者这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恶果。应该说他没有直接告诉读者其中原因。如果深究,便能感受到这是封建世俗封建婚姻的恶果,家长制下的封建包办婚姻怎能允许自由恋爱的抬头?“殉情”便是他们的解脱之路。在为翠翠父母的不幸感到心痛与惋惜之时,作为家长的老船夫又何尝不值得同情与可怜?女儿的死亡无疑给这位忠厚的老人带来了沉重的伤痛。不但要忍受孤独之苦,还得为女儿之死负上愧疚之责。在之后的时日里,老人时常从翠翠身上看出女儿的影子,也隐约感受到翠翠的性格与女儿的相似之处。于是,在老人心里埋下了不详的隐忧。再看这对殉情男女给他们的女儿翠翠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离去让翠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之爱,那么翠翠是一个获爱不健全的孩子,从小由爷爷带大,他们相依为命。等到翠翠长大“有心事”后。便和爷爷有了代沟。需要倾诉“心事”的翠翠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这样,翠翠“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她的那颗需要交流的青春之心被压抑着,忍受着孤独寂寞之苦。从翠翠父母的殉情到老船夫和翠翠的孤苦,我们能找出是封建婚姻和世俗的残酷性所致。这种残酷性不仅体现在当事人(翠翠父母)身上,还延伸着它的危害。
《边城》可以沈从文构造湘西世界的力作,在这个世界里,仍然隐藏着与整个中国俱有的社会残酷性。在《边城》第二节写到湘西妓女时,妓女已经成了正当行业,人们也有了正当理由去消费,“到了晚间,则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了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这真是对现世的绝妙嘲讽。如果作者不是反讽,很难相信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美”!这一群“从附近乡下弄来的”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成为“某种寄食者”,满足“商人的需要”和“水手的需要”。残酷的社会让她们牺牲了一切,更让人悲痛的是她们自己也因无力反抗,麻木到了认为这是一种“义务”,周围的人们也只是以惯常的眼光打量着一切,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国民“人性”的丢失,国民“弱质”“腐朽”的隐现,在作者文字背后是异常清晰可见的。再看湘西边城的刀客,“遇到不得已必需动手,便霍的把刀抽出,站到空阔处去,等候对面的一个,接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帮里的风气,即为‘对付仇敌用刀,联结朋友也必需用刀’,故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它失去那点机会。”在边城中,“刀”已然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工具,快意恩仇之中呈现着一幅血淋淋的场面。在边城人民眼中,只有朋友和仇敌两类。也就是说边城里还不存有第三类中间人,那么这两类通常都是要与“刀”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看来,边城里岂不到处是刀光剑影。再者,沈从文一定对“懦弱”的国民性深感忧患,于是借助人性中残存的兽性力量以“刀”的形式来激发人们的斗志。在这里,“刀”象征着原始未开化的兽性力量,与当时边城外的中国所遭受洋枪洋炮的武器比较起来,边城人民似乎真的是化外之民。“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了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中国其他地方正存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边城人民淳朴的背后还透露着无知和愚昧,构筑着作者乌托邦的情结。
注释:
1.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国闻周报,1936年1月第13卷1期.
2.张德林.怎样评价《边城》,书林,1984年第1期.
3.徐葆煜.《边城》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书林,1984年第1期.
赵敏,玉溪师范学院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廖鹏飞,玉溪师范学院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