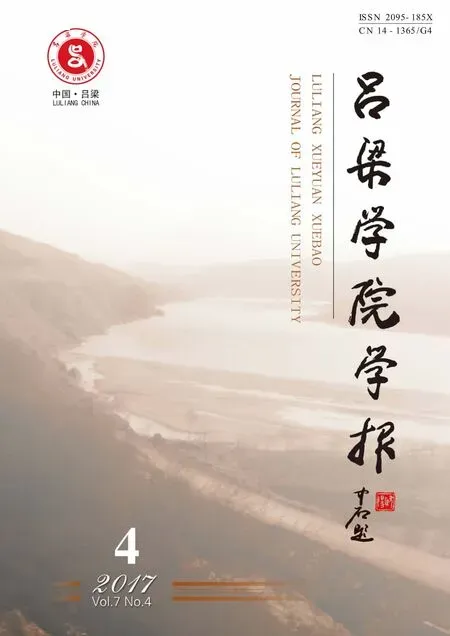语言效忠
——小说《坚硬如水》的革命叙事伦理
2017-03-12张海城
张海城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1)
一、互文与革命叙事空间的建构
《坚硬如水》讲述了退伍军人高爱军和夏红梅的革命发家史及爱情史。小说以文革为背景,着力叙述了共生共长的两个事件:革命和爱情。高爱军、夏红梅这对革命伴侣,因革命收获爱情,又因爱情持续革命。他们爱得炽热,爱得痴迷,爱得疯狂,却出乎意料地在革命事业即将宏图大展的时候成为“反革命通奸杀人犯”,终而被执行枪决。
故事,就此完结。叙事,却并未结束。其“尾声”是这样的:
许多许多日子之后,我和红梅允许从《温柔之乡》返回一次耙耧山脉。我们发现那里的人们都在阅读一本名叫《坚硬如水》的小说,而那些不识字的人们,又都在演说着我和红梅的故事。当我们到枪决我们的程岗以西的十三里河滩时,发现那审判的台子早已不在,可在我们流血倒下的地方,青草绿茵,异常旺茂。就在那块草地上,正有一堆男娃、女娃在割草放牛,他们彼此游戏着相互探看对方的秘地。看完了,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儿,在日光下脱得赤赤裸裸,一对一对做着一些男女游戏时,便有一位佝偻驼背、白发稀枯的老婆婆在村头唤他们中的谁回去吃饭。他们只好都从草地慌慌张张起来,穿好衣服,扛着草篓,赶着牛羊回家去了。
我和红梅也只好又回了温柔之乡。
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再见,革命!
别了,司徒雷登[1]326-327!
“革命”为何?缘何讲“还未成功”?“司徒雷登”所指为何?那些“男娃”、“女娃”是否有所隐喻?为理清上述叙事,我把它同小说开始的部分并置,发现二者有种互文关系。
小说开头写到:
等我死过之后,安静下来,我会重新思考我的一生,言论、行为和我行走的姿势及对那鸡屎狗粪的爱情的破解。那儿是一片温柔之乡,是思考的上好去处[1]1。
显然,这里提到的“温柔之乡”同文末的“温柔之乡”当属同一处所。上述叙事话语的焦点应为“死过之后”、“安静下来”和“重新思考”这几个短语。
显然此刻他尚未死去,且仍处于激情状态。如前所述,高、夏二人爱得疯狂,爱得痴迷,此处却用“鸡屎狗粪”限定爱情,究竟包含着高爱军怎样的爱情判断。他认为温柔乡是最适合思考的地方,但小说并没有让叙事跟进,而是开始了痛说革命史的叙事。直到小说末尾,我们再次看到了“温柔乡”。此时高、夏已是黄泉之人。许是他们又经历了几番斗争,才得以被“允许从温柔之乡返回一次耙耧山脉”。此次返乡,小说主要叙述了以下几个片段:识字的人在读一本叫《坚硬如水》的小说、不识字的人在言说他俩的故事、男男女女的孩子在他俩的赴刑之地,窥探着对方的秘密。他俩故地重游,相信定有一番滋味涌起,从“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再见,革命!别了,司徒雷登!”中我们可以探知一二。那么,涌起的究竟是什么?没错,是革命。革命的兴味再次涌起,革命的故事还在继续。
如前所述,小说开头与尾声构成互文之关系,叙事彼此牵连,互相指涉。要言之,死后的高爱军思考的无非革命、爱情,还有抛弃他的故乡。那一声“别了”,更多的是揶揄。在此,互文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并未指向意义终点,而是揭橥了如下问题:
“反革命通奸杀人犯”高爱军和夏红梅经历了一场怎样的革命?是什么事件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他们赋予了革命怎样的意义,尤其是死后?
厘清上述问题,需要回到小说叙事之维,在对叙事话语的探究中找到答案。
二、革命话语的叙事效用
通读小说可以发现,小说的叙事无疑是一场狂欢,既有革命话语的狂欢,也有爱情话语的狂欢。显然“狂欢理论”可以很好地阐明个中深意,然而我无意于此。如果说狂欢是一种修辞,那么当它遭遇革命(政治)后,革命话语的狂欢在革命者的效用为何?革命者操有如此言语方式,其意何在?从狂欢者角度切入狂欢行为,行为主体便成为焦点,个体与历史于此交汇。
先读一段小说原文:
8点整,我正式让吃着、抽着、说笑着的年轻人们安静下来了。我说大家静一静,同学们、朋友们、战友们,大家静一静!他们对我这样对他们的称谓先是新奇地笑一笑,跟着就奇特地安静下来了。
接下来,我就把世界和国家的形势给大家分析了。我说: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今天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崭新的历史时代。在毛泽东思 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亿万革命大军,正在向帝修反,向整个旧世界,展开猛烈的进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环顾全球,毛泽东思想的战旗迎风招展;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
“在一片空前大好的形势下,也有几个苍蝇在嗡嗡碰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加紧勾结,拼凑反华、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新神圣同盟,对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反扑,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华逆流。”[1]47
以上引文省略了小说原文中剩余约3千余字之“我说”部分的内容。它们彼此连贯,一泻而下。在我看来,它不但是话语的狂欢,更为重要的是它揭橥了退伍闹革命的高爱军初回程岗遭遇“石牌坊”之战后潜存着的洪荒之力,其叙事效用在于实现了革命信息的转移与共享。
在革命过程中,基层革命者大多无法接触上层(最高)领导者(尤其是领袖),他们对革命信息的掌握只能以其直接领导为中介来完成的。这一过程便是革命信息转移与共享。
高爱军汪洋恣肆的长篇“我说”,便是转移与共享革命信息的行为。它以一种狂欢的方式完成,极易煽起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信念和文化的分享会增进合作,因为有共同目标,还有应付类似难题的协调”[2]400。加之高爱军口若悬河、激情四射,猛烈地冲击了群众的革命无知,极易形塑个人崇拜,夏红梅便是其死忠。
如此叙事话语,小说中俯拾皆是。有论者称其为毛话语的再现,也有论者指摘小说叙事的毛病。但,这正是阎连科写作这篇小说最早的动因:
最初写《坚硬如水》这样一部小说的时候,不是任何一个故事,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使我想写它,而是那种“文革”的语言,当我回头去想的时候也有种非常着魔的感觉。
我就尝试寻找一个合适的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故事把这种语言记录下来[3]208。
当历史尘雾散去,当历史规限退出,阎连科被“文革”话语的魔力所吸引,将其重现并加以追问。他所做的一定不仅仅是“记录”。在我看来,“毛话语”的叙事功能在于,它彰显了革命者高爱军对革命的“语言效忠”[4]139。
三、革命叙事的伦理面向
革命者效忠于革命,是一种信念,甚或信仰,是革命者必备的品质之一种。效忠方式有很多,舍身成仁自是一种,效忠领袖亦属其间。革命者的阶层差异,使得效忠方式呈现差异性。上层的革命者多直接宣誓效忠的方式,远离领袖者虽无法如此直接,但他们仍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完成,譬如悬挂领袖的画像并每日拜谒或日诵领袖之言。“毛主席语录”作为林彪的发明,其意也无非宣示其对主席的敬仰与效忠。“红宝书”在文革期间的兴起,不能不说是群众效忠主席的一种方式。
在《坚硬如水》中,我们看不到“红宝书”,准确讲是不需要“红宝书”。高爱军已将“革命话语”牢记于心,他恰似一个革命话语的语料库,掌握多样革命话语资源: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革命样板戏戏文等等。高爱军对革命的效忠,是通过再现这些话语的方式完成的。小说中他不断援引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革命样板戏戏文等话语的行为,将他的“语言效忠”展现得声色俱佳。可谓言必有据。
高爱军回乡闹革命是在1967年,正是红卫兵气势如虹的时候。像所有红卫兵一样,没有任何授权仪式,高爱军以革命家的意念,以一个秘密会议,开始了他在程岗的革命事业。然而高爱军并没有在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检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毛主席的效忠。通过“语言效忠”,高爱军就如同与革命签订了一份协议,也因此获得一种“权威”。
文革期间,毛泽东与红卫兵之间好似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毛泽东把革命的重任交予作为代理人的红卫兵,毛泽东就是他们权力的由来,革命事业就是他们权力的保证。毛泽东和红卫兵之存在弗朗西斯·福山所谓“权威转授”的关系。
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称,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但他同时指出并非没有对皇帝权力的限制。他认为对皇帝权力的真正限制力量有三:其一,缺乏诱因来设置庞大的行政机关以执行命令,尤其是征收较高的税赋;其二,缺乏行政能力所限制的只是供应方面,而不同的皇帝也有自己不同的税收需求;其三便是权威的转授 (delegation)。因为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作出国内所有的重要决定[2]279。
福山认为“权威转授”,是通过选择代理人——可以是专家、官员等,并赋予他们以权威。如此联动,构成了其所谓的“非人格化官僚体制”。可见,“权威转授”是必然的。文革期间,在毛泽东与红卫兵之间,同样存在“权威转授”现象。二者之间权威的转授,是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检阅红卫兵等方式完成的。通过上述行为,红卫兵的行为被赋以“权威”,这便是他们革命力量、革命豪情的来源。
福山强调,权威转授的背后是权力的转授,也就是权力的部分下放。然而,本质上,红卫兵并未真正获得权力,所以当其造反运动危及到党,毛泽东毅然选择重选代理人。这一桥段与高爱军的经历何其相似!
宣誓效忠,便需对敌作战。高爱军的核心作战策略是掌握对手的反动事件、话语并将其加以组织,呈送给相关权利部门,藉此打击敌人,抬高自己。在我看来,这一“行动元”凸显了异质性言说方式与毛话语的冲突。异质性言说方式的出现,便是对“威权”的挑战,是对革命的背叛,是反革命。当此,革命者唯有高举革命之剑与之斗争。
话语的伦理,在它被当事者说出时即显现出来,并因言说者的强势而展示出霸权力量,侵占所到之处,不论其是否愿意。革命斗争有很多面向:权力、利益、族群、文化等等,而语言也是各派争夺的高地。通过对话语权力的占有限制对手,使其丧失言说空间,继而丧失生存空间。当对手服膺于自己,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就意味着斗争的胜利。况且,斗争总得有因由,而语言恰恰是一个很好的由头。相较于思想、行为等因素,语言的反动更易捕获,且更易赋予意义。语言本身能指、所指之特质,先天地给对手提供了“罪证”。
四、革命爱情:语言效忠的延展
由叙事建构起的语言效忠,在小说的另一处语言的狂欢场——爱情中展现得亦可谓汪洋恣肆。高、夏二人深情而露骨的话语,效忠的是爱情。爱情叙事的加入,绝非仅仅表征革命的原欲性,更重要的是阎连科借此实现了对革命的重构,是其革命叙事的重要构成。
与革命叙事的“公开”不同,高爱军和夏红梅的爱情发生在墓穴、河滩、地洞这类地下空间,因此被人诟病、质疑。殊不知,高爱军革命的成功曾也取决于在地下空间完成的事件,譬如高夏二人冒充夫妻去王家峪搜集王镇长的罪证。地上、地下哪有那么地泾渭分明。公开者或为阴暗,地下者也有可能是光明。恰如北岛之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之复杂,岂能作简单的二元之分。在阎连科“露骨”的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者令人动容的情爱。它萌动于原欲,所以显得粗糙,狂野,无所忌惮,它服务于革命,是高爱军革命的推手之一。有关高、夏二人的爱情叙事,其意义表征较为明显,且已被研究者谈及。在高夏二人“狂情暴爱”之外,小说还有一种饶有兴味的“爱情”被以往研究者忽略,我称其为“照片门”事件。由该事件所承载的叙事伦理是对高、夏爱情叙事所表征的叙事伦理的超越。
“照片门”事件是这样的:终于搞垮王镇长的高、夏二人,拟被提拔为县级干部。地委关书记派车邀请其到县委大院自己的寓所。等待关书记的过程里,高爱军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参考消息》,从中掉出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戴着眼镜和无沿帽”,照片下方写着“我亲爱的夫人”[1]240。他觉得这个女人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究竟是谁。没等他搞清楚,关书记便出现了,照片便从叙事中退出(但没有真正退出,其后的叙事皆因此而起)。关书记的赞誉让他渐渐忘记了对照片的疑虑。会面完毕,二人被安排在招待所等待下午和关书记的谈话。然而等来的却是刘处长。他说关书记被二人气得脸都青了,气得把电话机都摔到地上了。就这样二人被关进特别拘留室,其后是监狱。逃狱回来的二人,在监狱里最终被告之关书记真正需要让他们交代的是那张照片被他们放哪里了?茫然的二人并没有让关书记得到想要的答案(但确实没有对照片做任何处理),最终被推向革命断头台。
即将执掌一县的高爱军的革命征程因“照片门”事件戛然而止,并最终丧命。革命者死于同志之手,是以,阎连科革命叙事的伦理得以延展,但这并不是全部,其超越性凸显在写于照片上的“我亲爱的夫人”所表征的伦理面向。
照片之上“我亲爱的夫人”,是老革命家地委关书记亲笔书写。小说中没有任何能够解答他为什么写的信息,我们只能“大胆妄为”地想象。这位关书记“亲爱的夫人”是江青——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女人,她借着红卫兵不断提高自己的权势,威胁中央干部。我们不能肯定地讲关书记和她之间发生过什么(虽然刘处长说过关书记和中央的领导也有来往)。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爱情,那么关书记珍藏这张照片并写下“我亲爱的夫人”的行为,满足了他革命的“意淫”。或许他也像夏红梅编造出毛主席接见她的故事一样,编造出江青这一人物,支撑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直到现在。
高夏二人的狂情暴爱虽在地下,却也汪洋恣肆,关书记则遮遮掩掩。关书记的照片尚未找到,他是步高爱军之辙,抑或继续青云而上?那张照片到底在哪里?籍着爱情叙事,阎连科完成了对革命叙事的重构。
《坚硬如水》的革命叙事同爱情叙事并行,从而杀死了革命之纯然正义,直面历史个性,挖出历史的淤泥,完成了对革命(叙事)的重构。
[1]阎连科.坚硬如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阎连科.阎连科文论:小说与世界的关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4]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