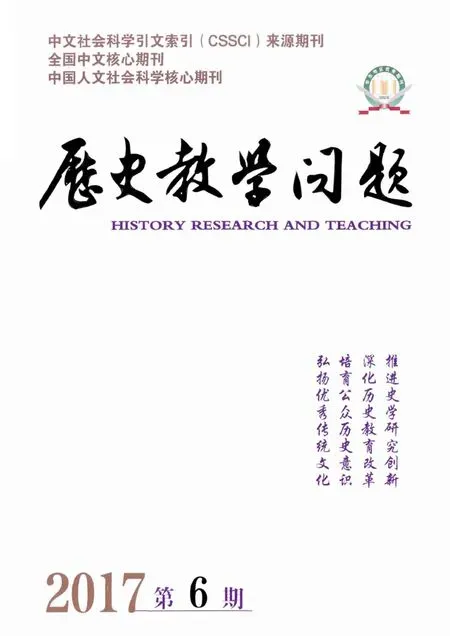身体政治视域下的土改运动研究
——以川西北地区为例
2017-03-12崔一楠
崔一楠 徐 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重塑乡村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西南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式治理实践不仅改变了西南乡村的面貌,还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随着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以及新理论、新观点、新视角的不断涌现,学者们逐渐摆脱了宏大叙事和注解式研究的束缚,试图在充分挖掘、利用地方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话语转型、范式创新、视野下移的方式来探究土改运动的多重面相。就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而言,从身体政治角度出发来考察土改运动的成果尚不多见,兼具身体史、新革命史双重学术志趣的研究亟待丰富。①参见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检视身体、革命两者的交织互动,可以拓展现有的研究视域,让乡村社会变革中的国家与个人、现代与传统、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得到更为生动、新颖的诠释。有鉴于此,本文遂以川西北地区为例,在对土改运动的探讨中,经由身体去认识革命,又通过革命来解析身体,希冀此种尝试可以发挥抛砖引玉、见微知著之功效,为方兴未艾的新革命史和身体政治史研究贡献一己之见。
一、诉苦动员:身体之伤的回忆与解读
20世纪50年代初,西南新解放区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重塑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中共基层干部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如何将民主革命的思想传递给农民,使其理解和认同,进而转化为行动,最终建立起新的乡村治理体系。就川西北地区而言,这样的努力并非一蹴而就。虽然在红军长征时期,当地一些村落经历过苏维埃运动的洗礼,但无论是革命理念的影响范围,还是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组织化程度,均无法与革命老区相提并论。解放前,宗法制主导下的川西北乡村呈现出差序格局、伦理本位的特征,地主与农民之间既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又掺杂着血缘、道德、宗教等多种复杂因素。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农民从未意识到乡村中的阶级分别,在他们看来,自己与地主之间只有穷与富的经济差异。尽管生活十分艰辛,但在传统道德观、宿命论的影响下,大多数农民没有强烈的反体制意愿,不会轻易萌生革命的念头。
动员农民参加土改运动不能仅靠按部就班的政策宣讲,土改动员的关键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诉苦来点燃民主革命的燎原之火,促使劳苦大众真正觉醒。诉苦要顺利进行是有前提的,即农民对苦难已有所体悟,否则就会出现“不懂为何苦,不知怎么诉”的尴尬局面,为此,“干部务必让农民回想起自己和别人被地主打骂、残害时的情景,避免空谈剥削”。①川西区绵阳土改工作团:《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9。由此可见,身体上的苦感是农民理解政治话语的基础,“苦难”需要经过生理体验才能升华为“觉悟”。有学者认为,诉苦成功与否取决于生活苦难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了身体的真实体验之中,“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②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借助身体这一纽带,抽象的阶级苦被具体化、生活化,成为农民易于感知的血肉之痛,一系列围绕身体之伤的回忆与言说,一方面能让农民在情感宣泄中加深对地主的仇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直观而真切地体察到今昔地位的强烈反差,强化翻身之感。
诉苦开展伊始,基层干部通常选择一些“老长年”、③“老长年”指长年在地主家帮工的农民,与普通农民比,他们在经济上更为拮据,生活上更加窘迫,大多没有能力成家。妇女、老年人等身体苦难较重的人作为重点动员对象。干部与这些农民一起生活、劳动,在饮食、穿着、举止行为上都与“庄稼汉”没有差别,身体力行、平易近人的姿态无疑会迅速拉近干部与农民的距离,在“摆龙门阵”(闲聊天)时,“访苦”和“引苦”工作便开始了。干部往往从冷、饿、累、痛等生理感知出发,引导农民将身体苦难与地主的行为相联系,通过回忆、对比,身体之苦在被提炼、归纳后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地主成为造成农民血肉之痛的罪魁祸首。“访苦”与“引苦”绝非照本宣科般的抽象说教,而是感同身受基础上的沟通与启发,当听到农民诉说往日的种种苦楚时,干部与农民抱头痛哭,其他人见状无不为之动容,最终农民会在极具感染性的场域中“越诉越伤、越伤越痛、越痛越恨、越恨诉得越起劲”。④绵阳土改工作团:《关于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绵阳市档案馆,69-12-10。
基于身体受难的诉苦还需经历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小范围的诉苦后,全村、全乡乃至全县的诉苦大会随之召开。在诉苦大会上,身体政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农民纷纷讲述自己目睹或遭受的身体之伤,例如农民无意间撞见地主的女人与他人通奸,地主不但杀人灭口,还将农民的老婆、女儿卖到妓院。⑤绵阳土改工作团:《绵阳县石马乡为死难农民报仇雪恨追悼大会简介》,绵阳市档案馆,69-12-9。为了逼迫庄稼汉交租,地主唆使恶奴骑在农民身上毒打,用剪刀戳,直到血肉模糊才停手。⑥中共绵阳地委:《土改问题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1。农民的身体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地主“野兽”般的嘴脸,尽管围观群众未必人人都经历过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但是有关身体之伤的反复叙述会把人们带入到一种情景之中,讲述者的身体感受给农民提供了理解政治话语的“具身性认知”场域。⑦所谓具身性认知,即通过身体的感知体验来构建我们赖以思考的概念和范畴,换言之,概念和范畴是基于身体的,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身体本质性的介入认知过程,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记忆。参见叶浩生:《“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心理学报》2014年第7期。对于农民来说,“压迫”“剥削”等名词是抽象、隐喻的“靶域概念”,需要借助易于感知的“源域意义”(如伤痛、流血、打骂等)来理解、消化,持续的“具身”体验会深刻影响农民的思维方式。随着控诉的进行,地主对农民的肉体摧残迅速激起了人们的愤恨之情,受难者“嚎啕大哭,悲伤过度,几次昏倒”的场景更让农民体会到切肤之痛。⑧安县土改工作分团部:《安县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四川省档案馆,建西-1-81。人们看到的情绪会唤起“感觉—运动系统”,从而在自己与受难者之间形成“情感共鸣”和“心境相通”,达到“所见即所感”的效果,这种共享的身体状态能够实现情绪互通,使“客体性他人”变成“另一个自我”。⑨刘亚、王振宏、孔风:《情绪具身观:情绪研究的新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期。当触目惊心的身体叙事营造出一种善与恶截然对立的氛围时,遭受蹂躏的个体立刻得到了集体意志的有力支持,仇恨之火在会场里蔓延,一时间农民群情激奋,一边舞动着拳头,一边高声咒骂,要求让地主血债血偿。①绵阳土改工作团:《关于土改中发动群众问题的检查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10。
农民遭受的身体之伤为土改运动提供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身体感受及其意义构建成为农民接受革命性政治伦理的基础。在血肉之痛的表达中,曾给农民带来苦难的“压迫矩阵”被简化,②柯林斯将其定义为,那些产生、发展并包含交叉性压迫的所有因素,包括战争、灾害、疾病等。参见P.H.Collins,“The New Politics of Commun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5,Issue 1,Feb.,2010,p.12.地主成了“现代”与“传统”双重语境下的敌人,他们既跟阶级政治势不两立,又与民间伦理水火不容。地主对农民身体的摧残严重背离了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展现出反人性、反社会的特征,作为破坏民间伦理秩序的元凶,地主在明确政治身份之前就已经具备了“道德原罪”。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互动关系在身体政治中有了如此的呈现:政治上的“罪”以民间伦理的“恶”为前提,维护民间伦理的“善”便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③崔一楠、赵洋:《叠加的镜像:土改多质性的微观审视》,《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土改运动在经济、政治之外,具有了明显的道德意义,它将农民从血腥的身体暴力中拯救出来,此举正是对行侠仗义、扶危救困等古老传统的伸张与维护,更有学者将其视为“宋明理学追求天理世界的现代表现”,是“新的圣王专政”。④金观涛:《中国人,可以告别革命吗?》,《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5年第13期。在“身体之伤—革命救赎”的逻辑中,政治被道德化,道德也被政治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借助“身体之桥”完成了与民间伦理的对接,传统的乡村资源被纳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二、斗争地主:身体规训中的权力展示
土改运动改写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在颠覆与构建中,身体逐渐从“个人私密物”的属性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公共视域之下,成为承载着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等多重意义的象征体。作为乡村社会的“异类”,地主的身体被视为罪恶的符号,代表着旧势力对农民的无尽压迫。在川西北各地召开的斗争会或公审会上,罪行累累、民愤较大的地主被押解到会场,接受农民的声讨、斥责以及国家的规训、惩罚。地主昔日的权威荡然无存,他们目光呆滞,低头认罪,有时还会通过作揖、鞠躬、打自己耳光的方式来体现忏悔、赎罪的态度。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地主的表情、语言以及肢体行为必须与斗争场景和阶级身份相一致,被权力形塑的身体流露出强烈的自我否定意味。借助稳定性规训技术(实现行为与特定政治身份的同质化)和连续性规训技术(控制人的位置、语言、行动)的应用,⑤王海洲:《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基于政治仪式中身体规训技术的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土改运动不仅完成了象征资本从地主阶层到农民阶层的转移,还让广大民众体察到旧势力崩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权威。
土改运动并非基层干部和农民领袖操演下的“政治独白”,而是广大乡村民众普遍参与的“身体实践”。为此,国家需要将一部分规训地主的权力配置给农民,使他们彻底与旧势力决裂,在“翻身”的同时实现“翻心”。斗争地主让农民以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体会到了政治地位的变化,迅速找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平日里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庄稼汉终于“抬起了头,挺直了腰”。很多人感叹:“活了这么大,终于见了晴天。”⑥彰明县土改分团:《彰明县摧毁反动组织的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20。随着斗争仪式营造出的剧场效应不断发酵,农民个体中蕴藏的革命性力量被调动而出,最终转化为底层群体的集体性情感表达——向昔日村庄优势权力与文化秩序挑战。⑦吴毅、陈欣:《“说话”的可能——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以前交租交晚了,地主就拿我爹当牛骑,爬慢了还用鞭子抽,老子今天不要钱,就想骑到他龟儿脖子上,给我爹出口恶气”。⑧绵阳土改分团:《复兴乡两个村子发动群众的检查》,绵阳市档案馆,69-12-10。“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做法不仅涉及情感的宣泄和阶级优越感的确立,还连接着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情结和思维定式。一直以来,“杀人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等儒家观念深入人心,若有父母、亲人遭遇身体伤害,那复仇就成为天经地义之举。对地主的身体规训包含了“家族恨”与“阶级仇”的双重意蕴,革命性从传统伦理中孕育而生,当农民认识到土改运动并非单纯的生理性身体复仇,而是亘古未有的制度性变革时,他们才真正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嬗变之旅。
集体性情感宣泄有时会带来“左”的偏差,火热的革命氛围会让一部分农民失去理智。在土改运动高潮阶段,川西北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体罚地主的行为,如“跪瓦片”“熏烟火”“喂蚊子”等,收缴不义之财时,有些地区存在捆绑、吊打地主的现象,民兵也习惯了“用枪托子顶几下地主,让他们规规矩矩说话”。①什邡县土改工作分团:《土改乡复查工作总结》,绵阳市档案馆,69-12-11。对基层干部而言,妥善处理土改运动中的身体暴力问题,准确拿捏斗争的尺度并不容易,有时会让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左”倾问题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必须加以制止;另一方面,如果完全禁止对地主的身体惩罚,严格限制斗争方式,就会让农民顾虑重重,达不到撕破脸的效果,无法实现乡村社会的重构。为此,“放手—过火—纠偏—再放手—再过火—再纠偏”成为川西北一些乡村的常态,既要动员民众积极投身土改运动,又要能掌控土改运动的激烈程度,这对于基层干部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工作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非所有人都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此外,适当时机的纠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此举既释放了民众在“偏向”中积聚起来的怨气,同时又提高了国家对民众的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解放者形象。②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三联书店,2001年,第387页。
除了斗争会和公审会,一些地主还面临着“关”和“管”两方面的身体规训。在土改运动初期,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认为,地主的身体不再是承载生命的个体,而是罪大恶极的政治化象征体,土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剥夺地主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清除旧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主张:“对待地主,不问罪恶大小,一律关起来就对了,以防他们造谣生事,搞破坏。”③川西区绵阳土改工作团:《第三期土改工作总结》,绵阳市档案馆,69-12-19。针对这种情况,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共川西区委多次下达指示,不断细化对地主的处理、安置办法,明确指示干部要区别对待地主中的“身负血债之徒”和“不好不坏之人”,如有鳏寡、年老的中、小地主,政府还要予以一定照顾。一些地主虽无血债,但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按照要求,他们必须在关押、管制中接受劳动改造,各县、乡会组织被“关”“管”人员从事烧砖、纺织、修路、开荒等劳动。体力劳动是改造地主的重要手段,地主只有亲身参与生产活动,真正体察到农民的辛劳与不易,才能从思想上产生触动。体力劳动是为思想改造而服务的,如果地主能够积极工作,没有怨言,他们可能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更多自由,甚至重新回到人民群众的序列,反之则成为死不改悔、冥顽不化的典型,接受更为严厉的身体规训。
除了国家和农民的规训外,地主还要面对来自家庭的批判。在川西北各地召开的“地主家属会”上,身体政治得到了一种另类的操演,生理性的血缘伦理让位于政治性的阶级认知,“我爹是地主,又是大爷(袍哥首领——作者注),不晓得害死了多少老实人,早就应该抓起来斗争,我拥护政府的主张”,“我儿子是恶霸地主,应该关起来好好改造,我还要揭发他的那些狐朋狗党,永远站在农民兄弟一边”,④罗江县土改分团:《关于召开地主家属会的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9。这类表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能够让我们明显感受到家人对于地主身体的厌恶。虽然难以分辨这些说辞是否出自真心,但地主家属必须明白,要想不受牵连,就必须成为仪式中的“理性人”,面对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他们不可能置身事外,只能融入其中,在身体和情感上与地主划清界限。随着政治氛围在乡村中日益浓厚,阶级伦理开始取代血缘宗法成为主导人们生活的原则和规范,任何有悖于意识形态要求的身体都会受到权力的规训,等待他们的不仅有政治的区隔,还有家庭的遗弃。
三、构建认同:政治感恩的身体化表达
土改使生活在社会底层、既无财富又无地位的穷人一跃成为乡村的主人,这种变化不仅带来了农民梦寐以求的政治、经济利益,还影响了他们对于身体意义的理解。近代以来,身体的变迁大体呈现出四种面向,即国家化身体的构建、法权化身体的开启、时间化身体的诞生、空间化身体的拓展。⑤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在这些身体之变中,农民往往只扮演着被动性裹挟的角色,然而土改运动开始后,昔日被奴役的血肉之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宣告解放,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农民欢欣鼓舞,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体感受与社会变革相联系,以一种主动性聚合的姿态表达对人民政权的认同和感激。例如有人说,解放前自己长年被地主压榨,没地方评理,躲在家里生闷气,最后得了咳喘病。清算了地主的罪恶后,他的气顺了,咳得也轻了,就跟村里人讲是共产党治好了自己的病。①中共彰明县委:《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10。类似的一幕也出现在罗江县,农民不约而同地讲述着“前所未有的身体体验”,旧社会体弱多病的农民在分到土地之后像换了个人,原来的头疼病痊愈了,弓着的背不驼了,他说毛主席的政策比吃汤药还管用。②罗江县土改分团部:《关于罗江土改工作中发动群众的检查向区党委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8。土改运动发挥了“身体治疗术”的作用,生理的伤病通过政治手段加以清除。农民的感激之情也在身体救赎中凝聚为一种情感能量,这种能量极具感召力,它是乡村民众接受革命意识形态,主动进行身体实践的精神动力。
农民的身体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就连美与丑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贫雇农时常讥讽地主说:“敢不敢把你的手伸出来,比比咱们谁的老茧厚。”“老子种田、割稻子时留下的伤疤有十几个,不信让你狗日的看一看。”③安县土改工作分团:《关于培养积极分子工作简介报告》,绵阳市档案馆,69-12-11。因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带来的印记给了农民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逻辑让疤痕、茧子、粗糙的手脚等都成为美的象征,是劳动人民的本色。而地主拥有的白皙皮肤、富态体型、光鲜衣着则都被视为丑陋、可耻的象征,是罪恶的证明。身体政治解构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生理的美丑由阶级的善恶所决定,审美被政治化,政治也被审美化。
借助身体意义的重构来表明政治态度,这样的方式不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还需扩展到群体当中,成为农民普遍认可的共识。在川西北各地组织召开的土改模范表彰会上,身体政治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基层干部给每位授奖代表带上大红花,一一握手表示祝贺,伴随着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叫好声,代表们向民众鞠躬致谢。妇女代表刘秀荣激动地说:“毛主席对我们一家有恩,我回去就要跟娃儿讲,让他参军,去消灭反动派、美国鬼子,以后他就是共产党的人。”雇农曾顺海跟在场的村民讲,他给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得田”,认为如果不是毛主席搞土改,他哪能娶上媳妇有了儿子,这个孩子不是老天爷给的,是共产党给的。④梓潼县土改分团:《梓潼县土改工作分团的检查通报》,绵阳市档案馆,69-12-9。农民的感恩之语具有明显的“身体国家化”味道,身体有了生理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既受之于父母也为政党和国家所有。土改一方面实现了身体的个体化,让农民获得了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不必再唯地主和宗族之命是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身体意义的升华,农民利用“以身相许”的方式既表达了真情实感,又建立起与政党之间的“类血缘”关系。中国共产党把农民的身体从封建桎梏中解救出来,置之于国家权力的保护之下,此种变革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在身体政治的视域下,广大妇女的身体认知状态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囿于“男尊女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乡村妇女普遍保守、封闭,她们被反复灌输着女性在生物学上劣于男性的意识,在父权、夫权文化中,妇女有着极强的身体依附性,“安分守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打破此种局面,促进妇女的政治化和社会化,川西北地区积极动员妇女参加土改,投入生产,一时间,“男人能做的活路女人也能做”成为乡村的主旋律,妇女的身体意义书写日益男性化。例如在绵阳县召开的妇女会上,获得土地的妇女纷纷表示,“过去娘家有九十九间楼,姑娘分不到一根椽子头”的时代结束了,共产党让妇女扬眉吐气,姐妹们应该报恩,大家要同男人一样垦荒、耕地、挑水、砍柴,哪方面也不能落后。村里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坚持要跟着家人一起种地,她说毛主席让她过上了好日子,自己要多生产粮食送给解放军。⑤绵阳土改工作团:《关于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绵阳市档案馆,69-12-10。昔日的“柔弱之身”被塑造为斗志昂扬的“劳动者之体”,一系列“女模范”“女代表”“女干部”成了乡村社会的“标准人”,她们是所有人的榜样,妇女们要根据“标准人”来进行自我意义的标定,诚如克里斯·希林所言:“标定、体验和管理我们身体的方式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偏离的,这会影响到我们是将自身及他人的身体实践承认为‘正确的’、得体的,还是需要控制和矫正的。”⑥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身体政治具有提取性功能,它给农民展示了可以效仿的模板,促使更多人接受这样的思想,即党所说的就是我想的,党所倡导的就是我该做到的。
为了让地主重新融入新社会,川西北各地组织“积极改造人员”召开反省会,一些洗心革面的地主讲述自己如何通过体力劳动达到思想净化、觉悟提高的过程,他们的身体曾是肮脏、罪恶的标志,经过劳动的磨砺和思想的蜕变后,生理的身体得到了政治上的重生。地主的诉说往往会带动台下家属的情感,地主家属泣不成声,他们一面表达着自己要与原有的阶级决裂,另一面不忘感谢干部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人民政府看我家房子坏了,借钱给我修房子,得了病干部还送药,毛主席的恩情我一辈子都要记得”,“我生娃难产,多亏了妇女干部帮着接生,要不然母子两个都没命,共产党就是活菩萨,没因为我男人是地主就丢下我不管”。①彰明县土改分团:《第二批土地改革工作基本总结》,绵阳市档案馆,69-12-19。身体如同感恩与认同的生成器,在情感叙事的渲染下,基层干部被塑造为乡村道德伦理的修复者,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有了温情脉脉的一面。
“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理解象征如何在社会中实际运作,以及了解如何在行动中使用象征的艺术。象征为人们理解政治提供了方式,因为政治过程往往依靠象征展现在人们面前”。②Novak,Michael.Choosing Our King,Powerful Symbols in Presidential Politics,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74,p.23.在土改运动中,身体是十分重要的象征物,它被当作一种符号和工具,成为表达政治认同、抒发感恩之情的肯綮。借助身体意义的生动表达和演绎,农民不仅近距离“观看”到了权力的戏剧性展示,还亲身参与其中,成为推动土改运动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土改运动寓“破”于“立”,不仅摧毁了旧制度与旧权威,还教育了广大农民,实现了人的革命化。
结 语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历程,身体从未因中国社会遭遇“千古未有之变局”而黯然退场,即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身体依然是政治视域中的核心问题。费正清在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指出,毛泽东是通过“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③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派伊也认为毛泽东的“目光超越了如何管理一个崭新社会的细节问题,着眼于如何塑造一种新人”。④路西恩·派伊:《〈毛泽东:领袖人物〉问题》,《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任何“人之再造”的努力不能脱离身体而存在,身体是思想变革的依托和载体,作用于思想的政治措施需要借助身体来审视和评估,没有身体的外化之行,思想的革故鼎新之意便无法落实。
就土改运动而言,从诉苦动员、斗争地主到构建政治认同,从意识形态的传递、政治仪式的操演到认知模式的更迭,身体政治始终贯穿其中。身体是农民接受革命理念的桥梁,昔日的苦难记忆必须经由血肉之痛的感知才能刻骨铭心,一系列关于身体受难的解读实现了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对接,今昔身体感受上的巨大反差不仅使农民产生了强烈的革命热情,还释放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者形象。作为新社会的“他者”,地主的身体不再只是生理层面的血肉形躯,而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体,斗争、规训地主既展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又让农民宣泄了情感,表达了主张,掌握了乡村的话语权。在土改运动形成的革命场域中,传统的血缘认同让位于阶级认知和政治情感,对地主身体的鄙视与区隔不仅是社会共识也成为家庭共识,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身体斗争并非单纯是对历史行为的惩罚,更有指向未来的作用,它为亲历其中者创造新的行为规范,以便使人明白,如何在社会主义政治下把握身体。⑤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的身体,在感恩与认同的表达中,人们的身体感知日益政治化,沉疴宿疾的祛除、生理机能的恢复、精神面貌的好转、审美观念的重塑都因乡村社会变革的发生而发生。随着阶级理论和革命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见于行,农民的身体归属呈现出国家化的倾向,妇女的身体形象也日益男性化,这些变化都预示着革命的身体将会成为中国身体的常态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