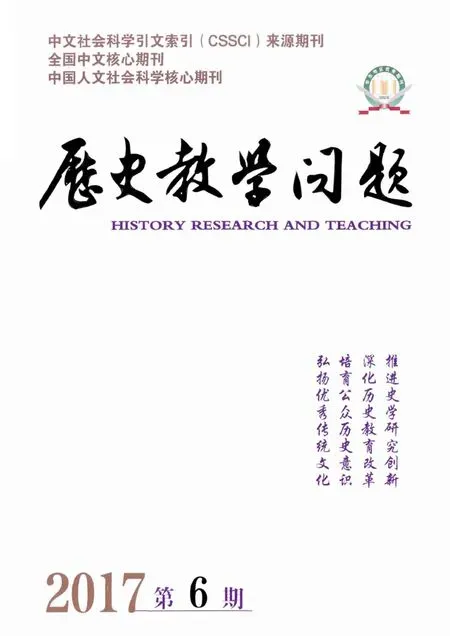普罗柯比的“史才四长”
2017-03-12王冰莹
马 锋 王冰莹
武则天长安三年(703),礼部尚书郑惟忠向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问:“我国自古文士众多,为何出名的史才鲜少?”后者在回答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①《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史德”的要素,并在其《文史通义》中还专列《史德》一篇进行探讨。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史德》,中华书局,1983年,第219-229页。而到了民国,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此作了总结式的发言,归纳作为史家的四种资格,并重新进行排序,将“史德”置于最前,“忠实”成了史家的第一件道德。③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17页。实际上,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中国史家,也同样适用于研究外国史家。观之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无论是蒐集材料的能力、记叙历史的能力、判断是非的能力抑或是“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品德,他都可称得上是位具备“四长”之才的史家。
“由普罗柯比所著的《战史》④国内学者关于普罗柯比的这部著作的书名有不同译法,有译作《战史》,也有译作《战记》或《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笔者在本文中采用《战史》的译法。《秘史》和《建筑》⑤普罗柯比著作的英译版包括了他的三部著作。见Procopius of Caesarea,History of the Wars,trans.H.B.Dew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trans.H.B.Dew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Procopius,Buildings General Index,trans.H.B.Dew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0.其中译本有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吕丽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普罗柯比:《战史》,崔艳红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后二者包括《战史》和《秘史》。尚无有关《建筑》的中译本。本文有关引文是在参考中译本基础上根据英译本进行了适当改动的翻译。不仅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主要史料来源,而且通常还是唯一的来源”。⑥Averil Cameron,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85,p.15.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史家还有著有《哥特史》和《罗马史》的约尔达内斯(Jordanes)、著有《历史》的阿嘎塞阿斯(Agathias)、著有《教会史》的埃瓦格留斯(Evagrius Scholastikos)以及著有《编年记事》的马赛林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但约尔达内斯的第一部作品用以记述哥特人历史为主,第二部作品只是罗马历史的纲要;阿嘎塞阿斯的作品则是对普罗柯比所写历史的补充;埃瓦格留斯将更多笔力倾注在安条克城(Antioch)之上;马赛林努斯·戈麦斯的重点则放在了拜占庭帝国的东方事务上。①关于这些史家的简要介绍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5-68页。也可见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Vol.Ⅰ,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pp.180-186.在此背景下,普罗柯比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仅是研究查士丁尼时代的重要史料,②J.A.S.Evans,“Justinian and the Historian Procopius”,Greece&Rome,Vol.17,No.2(October 1970),pp.218-223.也有助于研究拜占庭帝国史学史的发展特点。
事实上,国外的历史学家对他已有不少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生平事迹、写作年代与风格上。③相关论述如:Anthony Kaldellis,Procopius of Caesarea:Tyranny,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Antiquit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4;J.A.S.Evans,Procopius,New York,1972;Averil Cameron,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1985;Judith Herrin, “The Byzantine Secrets of Procopius”,History Today,Vol.38,No.8(August 1988),p.39.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这位拜占庭史家及其著作的关注度也有许多提升,除了对他本人和作品进行考察以外,④如崔艳红:《普罗柯比〈战记〉研究》,南开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她的《普罗柯比历史观述论——以〈战记〉为分析对象》,《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黄毅轩:《论普罗柯比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实践》,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马锋:《关于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重点在于利用普罗柯比提供的史料对6世纪拜占庭帝国政治与军事进行研究。⑤如赵瑞杰:《论狄奥多拉对查士丁尼时代政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许寅:《贝利撒留与哥特战争》,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马锋:《查士丁尼时代军事战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本文旨在以普罗柯比的著作为基础,运用中国史学发展中著名的“史才四长”理论来分析普罗柯比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历史学家的共通特点,以及他在拜占庭帝国史学史中承前启后的地位。
一、普罗柯比的“史学”
“史学”之于史家,若地基之于高楼,根基之于大树,是一切史学创作和研究的基础。古代历史学家所具备的“史学”之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史学教育与自我搜集的史料储备,二是来源于广泛游历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知识和新体验。而这些反映在他们作品中并流传至今的“史学”也为今日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
首先从普罗柯比的成长经历来看,《战史》开篇便提到了他出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凯撒利亚城。这里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中心。普罗柯比就出生于当地的一个上层贵族家庭,他在受到浓郁文化氛围熏陶的同时,还有充足的财力支撑他接受社会精英层的优质教育。⑥虽然当时拜占庭社会各个阶层大都能在孩童时代到20岁期间接受教育,但多数普通大众在接受初等教育后就不再接受高等教育。很明显,普罗柯比的家庭为他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关于拜占庭帝国的教育情况,参见N.H.拜尼斯:《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陈志强、郑玮、孙鹏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学界普遍认为,他首先在加沙接受了初等教育。当时“加沙是除君士坦丁堡以外唯一的文学中心,⑦在拜占庭帝国,文学与史学并无明确的区分,大文学的范畴包括史学。而且加沙的学校非常重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古典学者作品的教育”。⑧J.A.S.Evans,Procopius,p.32.在那里,他习得了不少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史学家荷马、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的史学作品,其中《荷马史诗》等还会被要求背诵。⑨拜占庭10或12岁的男童在从最初的“基础教育”转向第二阶段的“语法学习”的教育过程中,会全面学习古典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特别是对《荷马史诗》的背诵和理解。参见,N.H.拜尼斯:《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第185页。
然而史料的蒐集如果仅通过这一短暂的学习过程还远远不够。在初等教育阶段结束后,普罗柯比前往君士坦丁堡大学学习法律。在这所得到皇帝资助的学校,他不仅得到进一步系统学习古典史家著作的机会,而且便利的书籍资料查找条件也为他搜集、整理写作素材提供了方便。他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史学教育,以及他所获取的储备史料在其作品当中也有所体现。
在《战史》中,波斯战争卷的开篇就对拜占庭与波斯两国间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与概括,一直向前追溯到了408年拜占庭皇帝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383—408)时期两国的友好关系。①这位皇帝为保其幼子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408—450)的继位,指定由波斯国王耶兹德戈德(IsdigerdesⅠ,399—420)为保护人。而且事实证明他的这一举措非常英明,不仅狄奥多西二世最终成功掌握大权,两国之间还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参见普罗柯比:《战史》(上),第3页。在叙述汪达尔战争时,他在卷首便点明自己要“首先介绍一下汪达尔人的族属来源”,②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24页,第127-141页,第156页。后面还提到汪达尔人与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素有的冲突矛盾的发展。③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24页,第127-141页,第156页。这些信息的获取与作者对过往史书的学习有关,是他长期进行史料积累的结果。普罗柯比有关日耳曼人历史的记载被后人充分肯定。他在《战史》中记载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支日耳曼民族赫卢利人(Heruli)的情况,这成为相关研究最主要的原始文献。④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503-504.
其次,就如同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和中国的司马迁一样,普罗柯比也在用自己的双脚亲自丈量土地,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当时的人物与事件。广泛的游历也是古代历史学家提高自身“史学”之才的重要途径。而除了普通的游历之外,在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看来,最好的史家应该出身于政治家或是将军行列。因为这两者都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没有实际‘经验’,是历史研究中最容易导致错误的原因之一”。⑤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页。普罗柯比在527年被任命为拜占庭帝国东部军队统帅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法律顾问并随军出征。这一军事生涯给他带来的是传统政治军事史写作的最佳素材,他亲身经历了各式拜占庭战争及内部政治纷争。而且他同时还历练出了不俗的军事参谋力与行动力,这一点在他的作品里也有所反映。
在拜占庭与汪达尔的战争中,普罗柯比在将军贝利撒留的派遣下前往叙拉古收集敌方情报。现在说来,这一任务其实就是密探或者说军事间谍。他在顺利抵达叙拉古之后,与一位从事航运生意的儿时伙伴不期而遇。巧的是,这位伙伴的仆人3天前刚从迦太基回来,所以普罗柯比成功地探听到不少有利情报。比如“汪达尔人中所有的年轻人在不久前都远征戈达斯(Godas)去了……盖里莫尔(Gelimer,530—534)头脑中完全没有敌人来袭的概念,⑥盖里莫尔通过政变在530年取得汪达尔的最高统治权。参见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45-146页。根本不关心迦太基和所有其他的海滨城市的防务”。⑦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24页,第127-141页,第156页。这就意味着拜占庭海军完全可以自由航行,随意靠岸。当普罗柯比顺利抵达与贝利撒留约定的考卡纳(Caucana)后,拜占庭将士都被这一消息所鼓舞。普罗柯比也受到了贝利撒留的赞扬,这是对他军事才能的一种肯定。而他作为战争亲历者所搜罗到的史实素材不仅为其写作提供了参考,而且对于后世直至今日进行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史,尤其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对外战争史研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史料来源。
此外,据学者考证,晚年的普罗柯比最终还是成为了元老院的“杰出者”,他在560年获得了这一贵族称号。⑧转引自崔艳红:《普罗柯比〈战记〉研究》,第14页。而在562年,拜占庭首都出现了一位叫做普罗柯比的市长。虽然现在学界对这二者是否就是同一个人仍有争论,但无论如何,普罗柯比确实获得了一些政治经验,这对他的写作也有所裨益。同时,作为查士丁尼时代统治阶层的活跃一员,他亲身经历的事件也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史、外交史、疾病史、民族史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⑨David Braund,“Procopius on the Economy of Lazica”,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41,No.1(1991),pp.221-225.
二、普罗柯比的“史才”
“史才”之于史学,就如同裁缝手中的针线一般,它能够将众多已有材料进行适当的裁剪,重新编排一新。单纯坐拥大量史料却无“史才”的人,会变为“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盈,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⑩《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第3173页。具体而言,“史才”要求史家既需有文采,还应有组织能力。
在文采方面,普罗柯比在求学时非常注意古典修辞学的学习,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古典史学修养。就像拜占庭文明本身带有对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一样,普罗柯比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在模仿那些古典作家的写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著名人士的发言与演说。如果说贝利撒留众多的战前演讲能够被完整记下是因为普罗柯比也随军出征的缘故,那么当拜占庭与波斯两国交战之时,波斯国王的讲话理应无法再现。但是为了丰满书中人物的形象,普罗柯比模仿了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写作方法,对于作者本人未能在场的相关讲话,“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①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28页,第61页。在当时以政治史与军事史作为主要记载内容的历史传统下,对这些演说的记录使得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被凸显出来,普罗柯比之后的拜占庭正史也都坚持这一“人本主义”的原则。
普罗柯比对文采的运用建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之上,他的著作中处处体现出求真的史学本质。他在记叙爆发于542年的大瘟疫时,选择将目之所及的景象如实记录。虽然他不是医科毕业,但是描述得相当精准,可以推测他应该也接受过普及性质的医学教育。②在拜占庭帝国,医学教育比较普及。参见N.H.拜尼斯:《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第187页。他对于疾病症状的细致描述,比如“先是突然发烧……有一些人会在头一两天内出现腹股沟淋巴结膨胀的现象,这种情况仅发生在身体的‘腹股沟’部位,即在腹部以下,也可出现在腋窝处、耳朵侧面和大腿的各处。一个人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就说明他已经被感染了。此后病人的症状就有明显的不同了……一些人随之而来的是沉沉昏睡,另一些人则是强烈的精神错乱,这两种情况都是瘟疫进一步发展的典型症状”。③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01-102页,第1页。后来的学者根据这些详尽的记载,推断出这次瘟疫的性质应为鼠疫,还有些具体到了腺鼠疫。④国内学者关于这场大瘟疫的研究,主要可以参见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7期;陈志强:《现代拜占庭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同时,普罗柯比尤为关注文章的行文组织问题,在字里行间巧妙地渗透自己对于历史人物的针砭感情。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对于波斯王科斯劳(Coslow,531—579)的描写之中。在他的笔下,科斯劳是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并驾齐驱的东方专制君主。⑤Anthony Kaldellis,Procopius of Caesarea:tyranny,history,and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antiquity,p.14.但在《战史》中,他将科斯劳的登基与532年发生在拜占庭的尼卡暴动安排在一起叙述。在他看来,这两个事件可以作为两国各自“人祸”的代表。对于尼卡暴动中危害到政府统治的两派暴民的斗争,他没有任何的好感,就如同他对待新登基的波斯王科斯劳所抱有的厌恶感一样。
《战史》和《秘史》采取了以时间为主线索,辅以铺陈具体事件过程的叙述方法,这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史学中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结合。它综合了这两种体例的优点,能够使作者在纵向的历史叙述中,适时展开对部分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叙而又不显突兀。原本零散的素材经过他的再加工,所共同反映的历史就具备更好的继承与延续性了,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这也体现出他从波里比阿处继承的整体史观的影子。“历史学家再也不能用‘个别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了”。⑥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28页,第61页。以这一史观为原则写成的作品也在向读者传递这样的信息: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审视历史。
三、普罗柯比的“史德”
相较于“史学”与“史才”二长,刘知几认为“史识”才是史家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品质。在他看来,史家在作史的过程中应当“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⑦《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第3173页。章学诚提出要有“著书者之心术也”,⑧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史德》,第219页。原本包含于“史识”中的对历史真实反映现实的要求被细划在“史德”之下。梁启超也赞同这一划分,提出要做一个忠实的史家,就应避免夸大、附会和武断的毛病,也可以说是自身要对历史的是非曲直有鉴别与判断的能力,才能更好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在这一点上,普罗柯比就继承了以波里比阿为代表的一批古罗马史家力求真实与真知的史学传统。在他看来,相比于需要睿智思维的修辞学以及需要创新的诗歌写作来说,历史最需要的便是真实。并且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他准确地记载了历史人物的每一件善行或恶迹,从不文过饰非,即便那是他最亲近的人”。⑨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01-102页,第1页。
但事实上,普罗柯比的《战史》与《建筑》在涉及到查士丁尼、贝利撒留以及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等人时,几乎都是正面形象,大有颂扬之意。特别是将他的另一部作品《秘史》拿来对照时,这种差异更加明显。后者似乎是在为前两部作品中无法表明的个人感情找一个宣泄口,在后一本书的开头他写道:“我将要首先记述即贝利撒留的卑劣行径,然后再叙述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夫妇的恶行。”①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7;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31页。正因这种巨大反差,学界就对这两部作品是否是同一人所作产生过怀疑。“同样一个人如何写就《战史》这样一部著作以及《秘史》这样一部粗鄙之册的呢?19世纪有不少严谨的研究都否定了这一可能。直到赫尔利(J.Hanry)所编辑的重要而优秀的版本才确定了《战史》《秘史》与《建筑》三者风格的一致性”。②Averil Cameron,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p.8.
在他描写自己曾崇拜过、追随过的将军贝利撒留时,并未因为彼此之间曾经深厚的友情而刻意隐瞒对方的缺点。通过《战史》与《秘史》的对照,作者展现给读者的除了一个宏伟高大的将军形象外,还有一个犹疑不决、将个人感情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考虑的贝利撒留。在《战史》中,他英勇出击,积极谋取胜利,还经常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可是当他出击波斯军队并成功占领了西绍拉农(Sisauranon)要塞后,虽然在军队中也有士兵返回罗马的呼声,但“有人向他报告说他的妻子安东尼娜(Antonina)正前往这里……这时他认为所有其他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便下令班师回去”。③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p.25-27;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39页。这在普罗柯比看来这些对国家都是危险的,“他把个人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始终受他的妻子牵绊,因此他不愿意到远离帝国的地方去”。④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27;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39页。这与普罗柯比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大相径庭,令他在记述中表达出自己深深的鄙夷之情。
在描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查士丁尼皇帝时,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人物跃然纸上。这位皇帝会为了宣扬自己的智慧与正义而主动派军协助撒丁尼亚脱离汪达尔王国的统治,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愚蠢而邪恶贪婪的人,甚至他的长相也被形容为与罗马暴君图密善(Domitian,51—96)十分相似。⑤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95;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67页。普罗柯比给这位皇帝添加了不少负面标签。在他笔下,查士丁尼的缺点众多:不诚实、狡诈、伪善、两面三刀、朝三暮四、善于伪装、言而无信,经常出卖朋友。⑥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p.95-99;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67-968页。普罗柯比甚至认为,“大自然似乎把所有其他人的恶劣之处都转移和集中到这个人的灵魂之中”。⑦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101;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69页。而且他还对全体罗马人的穷困负有直接责任,仿佛是帝国最大的吸血鬼一般。⑧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写到“他自己既没有金钱也不容许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有钱。他看起来并不是贪得无厌,而只是痛恨有钱人。他随意地抛撒罗马世界的财富,给所有人造成了贫困。”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p.101-103;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70页。
在真实性之外,普罗柯比还注意到史学本身具有的“辨善恶、明是非、寓褒贬”的劝诫作用。同修昔底德一样,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垂训后世:“记载这些事情会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它既能帮助同时代的人也能为后世子孙提供借鉴,说不定后人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⑨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页。就连记载查士丁尼等人的丑行也是为了达到“也许人们会更加厌恶犯下这样的罪行”的目的,⑩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rt History,p.7;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下卷,第931页。警醒后世的皇帝要注意言行。
四、普罗柯比的“史识”
刘知几将史家应该具备的判断力和观察力统一归在了“史识”当中,而章学诚则将判断力划在了“史德”的范畴中,剩下的“史识”只包含有对历史独到的观察力。梁启超也同意这一具体划分,而且还提出史家在培养自己的“史识”时,应当注意既不要被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蒙蔽,也不要被自己已有的成见所蔽。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7-28页。是否具有独到的观察力决定了史家能否从新的角度审视历史,发现问题。
普罗柯比在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注意对非主流的历史问题的记述。这些在当时属于非主流的历史常常为史家所忽视,但却是后来史学研究中的珍贵史料。他在《战史》的写作中,除战争外,还描写了包括哥特人、匈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居民在内的诸多地区与民族的相关风俗与文化。①Irfan Kawar, “Procopius on the Ghassanid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77,No.2(April-June 1957),pp.79-87.他的这些描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希罗多德注重社会文化方面历史描写的继承,但他的描写却又是一个新的创举,即便是现代的“斯拉夫历史学者和斯拉夫古典学者在普罗柯比的著作中还找到了有关斯拉夫人生活和信仰的重要资料。同时,德国学者也从此书的许多事件中搜集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资料”。②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Vol.Ⅰ,p.180.而且,有学者发现他在描写哥特人时,并没有因为这些人一贯属于蛮族而过多地歧视他们,反而对其中一些哥特人的聪明与才智大加赞扬,③A.R.Burn,“Procopius and the Island of Ghosts”,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70,No.275(April 1955),pp.258-261.在他心中,部分学习了罗马文化的野蛮人也有了高贵的地位。④纪德明:《高贵的野蛮人——浅析普罗柯比对哥特人的态度》,《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第2期。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赋予蛮族人非文明的蔑视色彩,罗马人接受后更加强化。但是到了3世纪危机时期,这种罗马社会对蛮族的态度有所改观。这在已经传世的文献中可以发现。普罗柯比对待蛮族的客观态度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变化的代表。
普罗柯比在记叙历史的时候还努力地将自己置身事外,冷静思考,给出自己的客观看法。在描述大瘟疫时,他就在客观记载实情的基础上流露出一丝悲天悯人的感情,并且与深陷于死亡恐惧的其他人不同,他还注意到大瘟疫带来的积极影响。当时“过去分属于不同党派的人们都尽弃前嫌,共同埋葬死者。那些过去以卑鄙手段追求享乐的人,逐渐摆脱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堕落奢靡,勤奋地担负起救济的职务”。⑤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04页,第104页,第76页,第76页。而在他看来,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当人们面临即将来临的死亡,不可抑制的陷入恐惧之中,很自然地就做起了善事,学会了尊敬爱戴他人”。⑥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04页,第104页,第76页,第76页。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对历史的思考。瘟疫除了带来死亡与混乱,似乎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它能够使那些向恶的人再一次回归善良本性。
即使身处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中,普罗柯比也依然保有理性的态度。⑦马锋:《关于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他看来,人类连人世间的事情都无法正确地理解,更不用提对上帝的相关探讨了。但他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也多少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他著作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上帝与宿命的记载。“在安条克人陷入灭顶之灾以前,上帝就已经预示了这一即将发生的悲剧”。⑧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04页,第104页,第76页,第76页。上帝成了最应该负责的人。对于那些宿命,普罗柯比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很困惑,我不理解为什么上帝先要一个地方或一个人幸运,然后又毫无理由地抛弃他们,毁掉他们……无论如何,这座城市的美丽和伟大都不该被完全毁灭。”⑨普罗柯比:《战史》(上),第104页,第104页,第76页,第76页。显然,在他看来,一向敬重的上帝也有不当的安排。
但总体来看,他不愿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他对于当时流行的宗教狂热还抱有怀疑的成分。正是这一怀疑精神,他才能做到比中世纪的“神本主义”史家更为客观地描述和品评历史事件。而自3世纪的信仰危机后,在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中,世俗主义的理性史观与宗教的神学史观的分离趋势越发明显。普罗柯比坚持了传统史学的写作方法与态度,他与当时大行其道的拜占庭教会史家相比,为世俗性更胜一筹的拜占庭正史的发展埋下了深厚的基石,也为后世传统政治军事史史家起到了表率作用。
史才四长理论是判断优秀史家的一般性标准。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虽然彼此隔绝或者交往较少,但是人类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史才四长理论是中国史学中经过检验的评判史家的一般性标准。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适用于分析中国古代史家,也适用于分析现代史家和西方古典史家。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规范多借鉴西方,同时又强调中西贯通。但是在实际中,中国学界缺乏一定的学术自信,不能把已经被证明了的中国学术的优良经验推广出去。以史才四长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史学成就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可以为世界史学的发展服务。
以史才四长理论来观察普罗柯比,我们可以发现,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普罗柯比本身怀有一种对历史的自觉责任感。他既是古典史学的直接继承者,也是拜占庭正史写作的开拓者,后世史家多加仿效。他还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史观,与同时代的教会史学家不同,始终坚持“人本”的史学思想,为拜占庭传统史学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他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历史的可靠信史来源。普罗柯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具备有“史才四长”的优秀史家。普罗柯比是拜占庭史学史中最耀眼的明珠,是当今史学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后人对拜占庭史家的研究多集中于普罗柯比一人之身。而有关他同时代的史家或者之后的拜占庭史家,后人研究较少。因此这些群体是否继承了普罗柯比身上所体现的这些史家品质则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