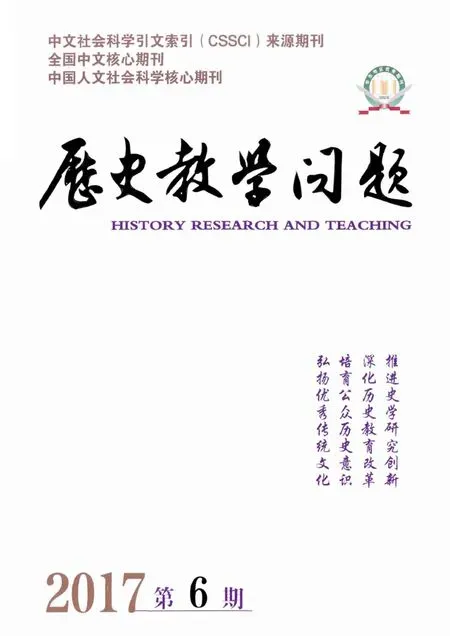北魏“离散诸部”“领民酋长”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7-03-12牟发松
牟发松
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是首次对领民酋长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创之作。①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初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周氏指出,经北魏道武帝“离散诸部”,其部落酋帅皆同编户,不过仍有“散处魏境”的鲜卑及其附从部落“未同编户”,“领民酋长者实为此类部落之酋帅也”。及至魏末,“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但大多是“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甚者徒有酋长虚号,而无部民”。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前承周氏研究,通过充分占有、深入分析相关资料,对北魏末大乱之前领民酋长所属种族、分布地域、地位变化,以及酋长与部民、北魏国家之间关系等,专章进行探讨,为北魏领民酋长制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②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卷下《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14章,卷末《约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
周、严二氏都明确指出北魏领民酋长制以部落组织的存在为前提。那么,这里就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如何看待道武帝时代“离散诸部”政策的施行,特别是“离散诸部”政策与领民酋长制的关系?其二,道武帝“离散诸部”之前的部落酋长(或称酋帅、渠长、统酋、酋大、部落大人乃至汗、莫何弗等等),以及离散之后仍然存在的部落及其首领,与领民酋长有何异同?其三,北魏末年六镇起事前后领民酋长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二者间的本质区别何在?由于这些问题事关北魏前期国家的体制特征,因而近年来颇受关注。③相关研究史综述,见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第1章、第2章,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二》第4章第4节,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太田稔:《关于拓跋珪的“部族解散”政策》,《集刊东洋学》2003年第89号。太田稔论文末列有一表,按论著刊布年代先后,列举了20位作者关于“离散诸部”研究的31种论著,并就各论著的观点分别作了简明的标示,此表实为一全面扼要的研究史。下文拟对已有研究及其问题意识试作梳理,并间述作者浅见。
关于道武帝“离散诸部”,研究者的理解存在诸多歧见,主要原因在于相关资料奇缺。其直接史料只有三条,见载于《魏书》的《官氏志》《外戚·贺讷传》《高车传》。④依次见《魏书》卷一一三,卷八三上,卷一〇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014、1812、2309页。《魏书》的《贺讷传》《高车传》均已亡佚,后人据《北史》卷八〇《外戚·贺讷传》、卷九八《高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671、3272页)补,溢出文字当是以《高氏小史》等他书附益之。详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卷八三、卷一〇三的“校勘记”。三条史料一称“离散诸部”,一称“分散诸部”,一称“散诸部落”,提法各异,今日研究者则多称“解散部落”。解散的具体时间,《高车传》泛称“道武时”,《官氏志》谓在道武帝登国(386-396)初,《贺讷传》谓在“道武(皇始元年,396)平中原”后,先后不一。解散的对象是部落联盟,还是大部族,或是二者之下的部落?亦语焉不详。《贺讷传》称“离散诸部”后“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官氏志》称“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则部民的编户化似乎涵括全体部众。然而部民的编户化是否与解散部落同步?编户化后的部民是否等同于一般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已有的研究并无明确一致的答案。而以上问题实关系到如何理解部落解散的内涵、目标、效果及意义。
在“离散”时间上,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认可《官氏志》所说的“登国初”。拓跋珪于登国元年正月即位代王之时,周边诸部(东边后燕,南边西燕,西边铁弗部,西南独孤部,西北贺兰部)均实力强大。同年八月独孤部刘显遣军与西燕新兴太守窟咄(拓跋珪叔父)“来逼(代国)南境”,以致“诸部骚动,人心顾望”,拓跋珪被迫“北逾阴山”,再一次逃奔舅氏贺兰部。①《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1页。有鉴于此,河地重造认为《官氏志》所载登国初年“部族制解体”有误,当如《贺讷传》所载在皇始初年。②河地重造:《关于北魏王朝的成立及其性质——从徙民政策的展开到田制》,《东洋史研究》1953年第12卷第5号。宫崎市定对河地氏的推断表示赞同,认为“离散诸部”应该在贺兰部大叛乱被平定的皇始二年(397)之后。③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4页。初版于1956年。山崎宏从部族解散与南北二部废止的关系着眼,认为道武帝的部族解散政策虽然是在登国元年发布的,但政策的遂行,则要等到天兴元年(398)新的魏国作为中原帝国的体制得到整备,亦即作为部族统治机关的南北二部制为带有“中国风”的八部制所取代之时。④山崎宏:《关于北魏的大人官》(上、下),《东洋史研究》1947年第9卷第5-6号、第10卷第1号。谷川道雄前承宫崎氏之说,认为在登国元年代国“草创时期采取如此大胆的措置(部落解散)令人难以置信”,应该是在强敌后燕被驱逐出中原并创建帝国的皇始元年至天兴元年之际。⑤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增补版),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5页。初版于1971年。古贺昭岑则断言在登国初的特定形势下,“无论如何部族解散不会在此时”,而应当在“北魏开始整顿国家体制的皇始之后”,具体时段与山崎、谷川二氏的主张相仿佛,即皇始、天兴间。⑥古贺昭岑:《关于北魏的部族解散》,《东方学》1980年第59辑,刘世哲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5期。
最早讨论“离散诸部”问题的内田吟风,认可《官氏志》所记解散时间,即登国初年。⑦内田吟风:《北朝政局中鲜卑及北族系贵族的地位》,《东洋史研究》1936年第1卷第3号,后改订收氏著《北亚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其后宫川尚志、田村实造、胜畑冬实诸氏亦持此说。⑧田村实造:《代国时代的拓跋政权》,《东方学》1955年第10辑,后收入氏著《中国史上的民族移动期——五胡、北魏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东京创文社,1985年。宫川尚志:《北朝贵族制度》,《东洋史研究》1943-1944年第8卷第45、46号,后收于《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京都平乐寺书店,1964年。胜畑冬实:《北魏的部族支配和领民酋长制》,《史滴》1993年第14号;同氏:《拓跋珪的“部族解散”与初期北魏政权的性格》,《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文哲史学别册1994年第20集。但他们也绝不认为“离散诸部”在登国初年便毕其功于一役。如内田吟风即指出平定中原之后“解散”政策才得以强制性的彻底推行,在道武帝时代大体完成,但也不是没有例外,如边境地带的部落制度大多保存下来,《高车传》所载“高车以类粗犷”其部落未被离散,即为其例,因而道武帝以后诸帝仍在继续推行部落解散政策。田村实造则认为在登国初年道武帝权力相当脆弱的情况下,难以设想能一举断行游牧民族部落的改编,因而当时道武帝只对直属的极少数部落尝试实行过。胜畑冬实对上引三条有关部族解散的史料作了深度解析。认为《官氏志》所谓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并不是针对“四方诸部”的措置,而是废止拓跋部内的部落大人制,道武帝给这些大人授予新的官称参加政权,并将其部落再编于自己麾下,借以强化其统治权力。他还认为三条史料所载部族解散各有特定时期、对象和措置,并非整齐划一之策。
内田吟风高度评价道武帝的部落解散,称之为“英明重大的决断”。此举“使部民编民化,一律强行郡县制”,“旧部落大人等同于编户,失去了对旧部民的统治权”,“分土定居,无迁徙自由”,从而果断排除了五胡诸国普遍实行的胡汉二重统治体制。他推算被解散的部落达数十万、部落民达数百万之众。一方面是北族部落民“中国编民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族“部酋子孙中国贵族化”,遂为此后北魏的汉化政策和胡汉融合奠定了基础。①上揭内田氏:《北亚史研究——匈奴篇》,第346-347、337-339页。这些论断为后来的研究者普遍接受,蔚为共识。如宫崎市定前承内田氏、河地重造之说,称“北魏直到太祖道武帝时代,依然维持着北方民族共通的氏族制度。……(道武帝颁布离散部族命令)剥夺了部族首领以部落酋长身份役使部民的权力,将他们还原成单纯的个人。……直属于天子(成为编民)”。②上揭宫崎氏:《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34-235页。谷川道雄称:“北魏帝国与五胡国家有一点截然不同,那就是在建国当初断然解散了游牧民诸部落。……部落民受国家的直接统治,原来的君长大人被剥夺了部落统率权。”③上揭谷川氏:《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95页。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学者就解散部落提出了新的看法,对以往的共识形成有力挑战。松永雅生通过研究北魏的审判制度,指出孝文帝改革前一直存续的三都审判制,是继承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部落审判,这就意味着当时北族的社会组织仍维持着部族制。进而认为此前关于道武帝解散部落为编户的认识,有必要重新加以检讨。他还指出拓跋珪“离散诸部”之后仍可见到表示部族存在的“部落”、“酋帅”等,认为“离散诸部”不过是将部族联合体切割成部族小联合体或者部落而已。④松永雅生:《北魏的三都》,《东洋史研究》1970-1971年第29卷第2-4号;同氏:《关于北魏太祖的“离散诸部》,《福冈女子短大纪要》1974年第8号。古贺昭岑则通过考察鲜卑拓跋族即“国人”的语言、服饰、家族关系、代都周围畜牧业、部族组织等方面,得出在京畿及邻近京畿的八国,虽经道武帝解散部族,酋帅率领的部落仍大量存在的结论,认为解散部落实为对各部族进行改编、重组,以便在京师周围集中配置部落兵。⑤上揭古贺昭岑:《关于北魏的部族解散》。川本芳昭相继发表一系列专文,论证指出北魏官制中的内朝制度,是基于游牧传统的,通北魏一代,不限于边境,包括被解散部落民聚居的畿内,仍大量存在统领部落的领民酋长或酋帅,北族的语言、习俗,体现部落成员间固有结合关系的聚居、同姓婚、血缘姓氏等,依然保存下来。总之,道武帝的“部落解散”,不过是将此前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单位如氏族、部落,部落组织、部落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依然存在,部族体制的本质仍得以保存,而非以往所理解的仅仅是例外和残余。直到孝文帝改革,部族制度全面解体的“部族解散”始告完成。川本氏所谓“部落解散”和“部族解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⑥川本芳昭:《北魏的内朝》,《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1977年第6号;《北魏太祖的部落解散和高祖的部族解散——围绕着对所谓“部族解散”的理解》,《佐贺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1982年第14卷;《关于北朝社会的部族制传统》,《佐贺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1998年第21卷。以上论文俱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
对解散部落的新认识,特别强调北魏前期的部族制传统,这一点已得到更多研究者的认同。胜畑冬实指出被解散的部落仍继续从事游牧,部落组织可以说是一种游牧业协作体制。太田稔则指出,将版图划分为若干区域并设置监督者,让分割出来的部落分散定居于各区域以事游牧,并视情况课以税役,这种“部落解散”不始于道武帝,不过是沿袭五胡诸国所施行过的政策而已。⑦上揭胜畑冬实:《北魏的部族支配和领民酋长制》;太田稔:《关于拓跋珪的“部族解散”政策》。韩国学者崔珍烈通过重新解析上举道武帝解散部落的三段史料,结合大量实例,得出道武帝时代及以后很多部族仍然保持部落组织的结论,道武帝所谓解散部落,不过是剥夺了部落联合体君长的政治、经济特权及军队指挥权。⑧崔珍烈:《北魏道武帝时期部落解散的再检讨》,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编:《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
对于《官氏志》所载道武帝之离散部落始于登国初年,中国学者大多不予否认,至于《官氏志》与《贺讷传》关于开始时间的不同记载,则予以折衷调和。李亚农称:“拓跋族在侵入中原之时,他们还在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太祖拓跋珪时,曾有取消部落组织的命令(下引《魏书·官氏志》略)……除了留居北方,与汉族远隔的拓跋族还保留游牧的部落组织而外,深入中原的拓跋族,在太祖珪的命令下,社会编制中的部落组织已被取消了,但在军事编制中的部落组织则仍存在。”⑨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37-138页。唐长孺认为:“离散诸部可能不是一时之事,但大规模的执行必在破燕之后,此时由于军事上空前的胜利,拓跋珪在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这样才能使部落大人、酋庶长驯顺地服从其命令。”①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马长寿也认为:“拓跋珪的分散部落始于登国初年即公元386年……但分散部落的事一直继续到平定燕国之后。……平燕以前,许多新附部落随同他们的部落大人或酋庶长在各处打仗,此时无暇分散而且也怕惹起部落酋长的反叛而不敢分散,所以大规模的分散乃在平燕以后。”马氏又详引《魏书·贺讷传》为例,认为该传“实在是一部拓跋的分散部落史”。②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69-272页。李凭针对古贺昭岑认为登国元年拓跋珪因受到西燕压迫率部逃往阴山之北从而无暇离散诸部,指出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即位代王,至八月投奔贺兰部,“新建的部落联盟曾有相当一段安定的时间”,“因此在这段时间内离散诸部并非没有可能”。③李凭:《北魏离散诸部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关于解散部落的原因、效果及意义,唐长孺指出:“由于从中国被迫迁入代京一带的人民非常多,促使各部落中杂居情况更为显著,部落组织完全不适合于新的局面,必须要加以改变。”这是解散部落的内在原因。“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不用说正在消灭的氏族彻底的消灭了。其次离散的部落都分土定居,不听移徙;纵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从事畜牧的人民在此时忽然一律都变成定居的农民,因而在较小范围内的移动应该准许;但是这只能是在指定的范围内移动,这样就把人们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面,同时也是地域划分代替部落、氏族的表现”。④上揭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唐氏强调被解散部落民的编户化、定居农耕化,进而肯定部落解散在拓跋封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从而确立了国内解散部落研究的基本方向。
马长寿在唐氏基础上续有推进。他也认为“分散部落的基本原因”是“部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原有的部落联盟变为地域性的国家组织”,而北魏境内的农牧业生产条件“使诸游牧部落有分土定居的可能”。他特别注意到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在定襄郡的盛乐附近“息众课农”;登国九年(394)“拓跋珪把在盛乐课农的经验推广到黄河套北从五原到稒阳塞外进行屯田”,官府将收获谷物按一定比例分给在这里屯田的魏之别部(“分农稼”);皇始年间(396-398)攻占河北后移徙山东六州吏民及杂夷“以充京师”,在繁畤“计口受田”,“更选屯卫”(八部帅及所率屯卫兵)监督生产;十余年后的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在郊甸大宁川也实行“计口受田”式的移民屯田。马氏强调说:“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与进行屯田的同时,北魏政府对于旧有的部落和新征服的部落强迫执行一种‘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马氏认为上述“息众课农”于盛乐、“屯田”于黄河套北塞外,“计口受田、更选屯卫”于繁畤、大宁川,与部落解散政策“是一件事情”,并将部落解散的源头追溯到376年苻坚灭代国后对拓跋部“散其部落”的处置,谓其为“日后拓跋珪”的“离散诸部”“奠定了一个有力的历史基础”,⑤上揭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69-274页。洵为洞见卓识。
关注经济、社会层面,是唐、马二氏研究北魏解散部落的重要特色,也影响到后来的研究者。李凭不同意古贺昭岑否定登国初离散诸部说,认为《魏书·太祖纪》所载登国元年二月拓跋珪“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与《官氏志》所载“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实为一事。李氏又以登国九年“河北屯田”(即马氏所谓“黄河套北屯田”)为第二次离散诸部,破燕之后在京畿推行全面范围的离散诸部(即马氏所称道武帝在繁畤“计口受田”,“更选屯卫”)则是第三次。并指出道武帝推行的离散诸部措施,“是前秦曾经对拓跋部实行过的所谓‘散其部落’措施的翻版”。可见李氏的意见与上述马长寿关于离散诸部的论述十分相似。不过李氏对三次离散诸部的考证更加细密,在离散时间、过程及对象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他还特别强调游牧部民的农耕化、编民化(“任使役”),认为北魏建国初“划分为畿内与畿外两个区域”,畿内主要安置内徙新民和“离散”后的部民,以务农为主,因此他认为离散诸部“无疑是道武帝时期最有意义的改革”。⑥上揭李凭:《北魏离散诸部问题考实》。张金龙更将“离散诸部”概括为“游牧向农耕的转变”,认为“毫无疑问,离散部落是决定拓跋鲜卑民族由游牧向农耕转型的关键性措施,有助于推动北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离散部落还意味着部落酋长原有的军事权力的削弱和剥夺。……这样,新兴的北魏王朝才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在北魏王朝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二》,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8-200页。不过李凭强调畿内安置的是经“离散”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民,与上述古贺昭岑、川本芳昭等认为畿内仍存在诸多游牧部落不无抵触,与上揭唐、马二氏的意见也有区别。
唐长孺并不否认被离散的部落民有的仍继续从事畜牧,认为畜牧业在畿内“占有颇大的比重”;他还指出北魏社会中有着浓厚的部族制传统:“代京的留住集团,征服与降服的各部落,以及束缚在军镇上的府户在魏末不管是鲜卑人与否都呈现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②唐先生曾将北魏“从事畜牧业的劳动者”分为三类,其中之一就是“解散部落以后的自由农民”。上揭氏著:《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同氏:《拓跋族的汉化过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马长寿认为:“所谓计口授田是对汉人、徒何鲜卑人以及其它有农耕经验的部落民而言,而分土定居和不听迁徙则对游牧部落而言,因为游牧部落转徙无常……所以特别强调‘不听迁徙’。”并不认为畿内、畿外的划分与农、牧分工有关。③上揭马氏:《乌桓与鲜卑》,第273页。李亚农认为离散诸部后北魏的游牧部落组织在社会编制中被解散而在军事编制中被保存,已如前述,但他又认为,“一个部落单位,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单位。一个部落的酋长,就是这个部族的军事统帅。部族的成员,平时都是从事于畜牧的生产者,战时又都是从事于战斗的士兵”。④上揭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第137-138页。按部落组织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军事政治组织合一,部落成员亦牧亦兵、全民皆兵,因而李氏所论离散后的部落组织与离散前的似乎并无根本差别。何兹全说:“在拓跋珪时期,拓跋氏氏族部落组织开始解体散为编户。……但一些较为原始的氏族部落,并没有和拓跋部同时离散部落组织,它们的部落组织仍被保留着。……登国年间散诸部落同为编户,只是拓跋氏族部落解体的开始,在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祖孙三代及随后的一个时期,拓跋氏的部落组织仍然存在着。北魏的兵,仍然是以拓跋氏族部落联盟为主的部落兵。”⑤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期,收入氏著《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陈寅恪早就指出,十六国北朝的兵民之分,即胡汉之分,胡人当兵,汉人务农、服役,军民分治即胡汉分治。唐长孺亦持此说。⑥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章“兵制”,中华书局,1963年。此章系据氏撰《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一文增订而成,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7本第3分。上揭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7、17、19诸篇。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载上揭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同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198页。问题是这些“带有部落军性质”的胡人兵士是否仍生活在真实而非虚拟的(如西魏北周府兵体制)部落组织中?何兹全认为至少在北魏前期是如此。
新近研究北魏离散部落最重要同时也是别开生面的成果,应推田余庆分别就贺兰部落和独孤部落的离散问题所作的个案研究。基于个案,田氏认为,道武帝离散部落,是一个激烈、复杂、不无曲折反复的暴力强制过程,而非简单的遵令而行。这种诉诸武力的“离散部落”,最直接、最急迫的原因是摆脱强大的外家部落贺兰部、独孤部对君权的牵制,以创建和巩固拓跋帝国,这是田氏的独见。田氏同样认定离散部落是“使被征服的部落分土定居,不许迁徙,同时剥夺其君长大人的部落特权”,君长大人、部众“同于编户齐民”;同样肯定“离散部落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拓帝业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正是他能结束五胡十六国纷纭局面重要的一着”。但田氏所论贺兰部的四次或者五次、独孤部的三次被“离散”,都是以战争为手段,以被征服的部族被“强制分割”徙置(甚至多次徙置)于他处定居、不得自由迁徙为主要内容,离散的部族首领或被击杀或被击走,但也有获授官职继续作为其“部民之统领者”,至于被离散部民的编户化、农耕化,似乎不作为核心内容。⑦田余庆:《贺兰部落离散问题》(1997年)、《独孤部落离散问题》(1997年)、《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与演变》(1998年),均收入氏著《拓跋史探(修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这些论述与其弟子李凭所论道武帝离散诸部特别注重社会经济层面颇异其趣,与上述日本学者后起的认为部落解散不过是对部落联合体进行分解,其部落组织依然存续的意见,异曲而同工。因此令人感到田氏所界定的离散诸部内涵与所述离散的过程、内容之间不无间隙。也有学者对田说提出质疑。①如张金龙:《读史札记》之一“关于贺兰部研究的质疑”,《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杨恩玉:《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文史哲》2006年第6期。
以上关于离散诸部的研究,如松下宪一所总结的,主要有对立的两说,一是部族制解体,部民编户化乃至农耕化,这是传统的“旧说”;一是部族制重组再编,即把部族联合体下的各个部族分割徙置,这是后起的“新说”。而原部落酋长与部民、国家的关系,与“前说”相对应的是部族酋长丧失对部民的统治权,部民作为编户直属国家;与“后说”相对应的则是部落酋长对部民仍有统治权,国家通过他们对部民进行间接统治。而关于部落解散与领民酋长制关系的理解也有两说:一是领民酋长制是针对解散对象之外的特殊部族的;一是作为部落解散对象的部族也曾实施此制,论者甚至认为“领民酋长制与部落解散的对象范围是相同的”。②上揭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第1章、第2章。川本芳昭将领民酋长视为“北魏时代率领部落的酋帅的名称”,被解散部落民聚居的畿内既有酋帅存在,也就有部落及领民酋长存在。③上揭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第124-142页。则领民酋长和终北魏一代始终大量存在着的部落酋帅似无原则区别。
魏末六镇起事后崛起的北秀容契胡首领尔朱荣,曾给许多投奔他的北镇流民豪强授予领民酋长称号,这些人多出自北族或为鲜卑化汉人,他们在见诸史载(主要见于唐代成书的《北齐书》《周书》)的北魏领民酋长中占有极大比例。胜畑冬实有鉴于此,认为领民酋长制与魏初的部族解散并非同时发生,因而领民酋长也不是从魏初以来就恒常设置的。④上揭胜畑冬实:《北魏的部族支配和领民酋长制》。直江直子则认为这些领民酋长不同于部族制下的酋帅,而是一种行政官员的称号,所率部落也是一种拟制的部族制。⑤直江直子:《“领民酋长”制和北魏的地域社会觉书》,《富山国际大学纪要》第8号,1998年;同氏:《北朝北族传——侯莫陈氏》,富山国际大学图书馆委员会编:《人文社会学部纪要》2001年第1卷。吉田爱的推断更进一步,认为史书中所见领民酋长,可能是尔朱荣为了将这些北族酋帅纳入自己麾下而创设的官爵。⑥吉田爱:《北魏雁臣考》,《史滴》2005年第27号。然而尔朱荣自其高祖尔朱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至荣本人袭任,凡五世为领民酋长,《魏书》卷74本传所载详确。《周书》、《北史》叱列伏龟本传亦载其上自高祖下至本人,五世继任领民酋长。自魏初以来世袭领民酋长的事例,亦屡见于石刻文献,如新出土的《赛思颠窟铭》,⑦孙钢:《河北唐县“赛思颠窟”》,《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宋燕鹏:《由一通摩崖造窟碑记看北朝厍狄氏的起源及其早期活动》,《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因而认为领民酋长为尔朱荣所创设,领民酋长并非魏初以来常置,实缺乏史料支撑。
最早研究领民酋长制的周一良就将此制的源流,上溯至十六国时代昭成帝什翼犍为“诸方杂人来附者”设立的“酋、庶长”,下推及北魏宣武、明帝之际的北镇“酋、庶(长)”,并称领民酋长在魏末“由部落酋长衍为不领部落之虚号”。⑧上揭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以北镇起事为界,领民酋长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后面貌迥异,唐长孺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领民酋长:“一种是老的世袭酋长”,在世代所领部落中固有的统治地位因朝廷的任命和分封而得到官方承认,“另一种是新选拔出来的酋长”,通过北魏政权的委任才在部落中取得统治地位,而当时所谓“部落”,“有时只剩下个名称,实际相当于一种军事行政基层组合”。⑨唐长孺:《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义》,《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北镇起事后新产生的领民酋长,其中大多数并非世领部落的酋帅,甚至原非北族,或为鲜卑化汉人,自无部落可领。总之,已成为一种朝廷委任的官职,不再具有部落酋帅自统部落、自治部民并世袭其职的内涵。及至北齐,领民酋长已法令化、制度化为一种流内比视官,并分化出繁复的等级、阶次,⑩张旭华:《北齐流内比视官分类考述(上)》,《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官制论集》,大象出版社,2011年。段锐超(指导教师为张旭华):《北朝民族认同研究》,郑州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3-72页。本来意义上的领民酋长也就趋于消亡了。
对北魏离散诸部、领民酋长制的理解,关系到对北魏社会政治体制及其历史走向的把握。上述强调北魏胡族体制特征的研究新动向,虽不足以否定北魏道武帝离散诸部在拓跋国家转型中的重大作用,却提示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特征对北魏政治体制的影响。对汉族农耕民和北族游牧民分别治理的所谓“胡汉分治”,对于统治民族即“极少数的胡人统治者”与胡人中“占绝大多数的”不同种族的“被统治者胡人”,亦采取不同政策即所谓“胡胡分治”,①所谓“胡胡分治”,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29-235页。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1页;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仍是十六国及北魏前期基本的统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