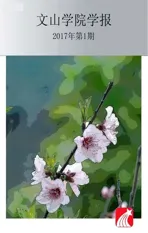颠覆与构建
——解读《尤利西斯》中摩莉的象征意义
2017-03-11王洪坤王小雨
王洪坤,王小雨
(1.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系,山东 烟台 264006;2.黑龙江大学 东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颠覆与构建
——解读《尤利西斯》中摩莉的象征意义
王洪坤1,王小雨2
(1.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系,山东 烟台 264006;2.黑龙江大学 东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摩莉是乔伊斯经典名作《尤利西斯》中最为精彩和最具争议的人物,人们对她的评价已不再停留在荡妇和色情狂之类的传统形象上。不绝于耳的恶毒攻击并不能遮掩摩莉成为反传统、追求个性独立的典范。文章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摩莉这一人物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乔伊斯塑造摩莉意在颠覆传统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和男权社会的专制统治,从而实现人性的理性回归,为爱尔兰宗教文化和民族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爱尔兰女性社会处境的同情和关注。
《尤利西斯》;乔伊斯;摩莉;颠覆;构建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年)是20世纪举世公认的文学巨匠,同时也是现代西方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1922年)被誉为20世纪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同时也是英国现代小说中最具实验性和争议性的作品。国内外“乔学”界对于《尤利西斯》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一些评论将《尤利西斯》视为登峰造极的旷世奇作;另一些评论却把它视为“下流不堪入目”[1]之作。该小说的女主人公摩莉·布卢姆是乔伊斯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她一经出现便在现代主义运动中掀起惊涛骇浪,其中有讴歌和赞誉,也有诅咒和诋毁。在第18章长达35页的内心独白中,她任自己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公诸于世,任人观览,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巅峰之作。乔伊斯最后一章不惜浓墨刻画摩莉这个人物,意在通过表面的性爱狂欢和怪异思绪传递作者对于关乎爱尔兰国家性别、男权、人性、宗教和民族未来发展等重大主题的独立思考,这也是该作品成为传世经典的主要原因。
一、颠覆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
社会性别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Gayle Rubin,1949年)于1976年提出的,它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权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社会性别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相对应,认为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该理论强调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主张人的性别角色是社会化的结果。在性别机制的规范之下,女性都不自觉地用社会预期角色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其后果不但使女性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而且也使她们成为隐蔽的受害者。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从家庭与性别关系不平衡的权利结构出发,对社会性别身份以及传统社会性别机制所定义的理想女性气质进行了嘲讽、批判乃至颠覆,消解了传统的男性主体身份、女性客体地位的二元对立,并提出“重建更民主自由,更符合人性的性别机制”[2]。
《尤利西斯》中的女主人公摩莉质疑传统僵化的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颠覆了她自身的社会性别形象。乔伊斯笔下的摩莉是一个招蜂引蝶、有欲无情、对性坦率主动的肉欲主义者,她的气质、行为举止和道德意识都远远摆脱了传统的性别机制的束缚,也因此被指责为“不合体统”,甚至是荡妇。在男性主导的文化里,由于自身的生理性别而遭受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女性成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女性除了传宗接代和满足男人的欲望外,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根本没有意识到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性意识和性欲望。忠贞不渝、被动顺从,向来是传统性别机制对女性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要求。摩莉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性方面的坦率和大胆。在经历了11年的无性婚姻之后,乔伊斯认可了摩莉的正常生理需求,并把它视为人的自然属性。乔伊斯把摩莉看成一个与男人对等,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彰显了摩莉形象对传统社会性别的颠覆。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之下,乔伊斯敢于对摩莉的反叛精神予以认同,表现了他超人的勇气和胆识,同时摩莉的形象对束缚女性的不合理性别规范也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刻意模糊和跨越性别界限,颠覆了人们对社会理想女性的成见,意在解除长期束缚女性的无形枷锁,使他们真正获得身心的自由。如果说性功能障碍使摩莉的丈夫布鲁姆天性柔弱、阳性不足,那么他明知妻子通奸却忍辱偷生,这便是典型的有女人气质的男人。相反,他的妻子摩莉在外面寻欢作乐、肆无忌惮,则表现为典型的男子汉气质。她甚至认为,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喝得烂醉如泥、好赌成性。如果由女人来统治世界,更不会看到生灵涂炭。摩莉对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不合理的角色十分不满,“究竟是谁替女人想到这么一档子事儿的呢 并且把它穿插到缝衣做饭养育孩子当中去”[3]815。摩莉敢于随心所欲地穿酷似男装的灯笼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不合理的男女双重标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相反,布鲁姆则被迫穿上了具有典型女性特征的紧身衣和裙衫。他们着装的变化一方面说明“社会性别的不定性和可变性”[2],另一方面表达了他们对男女性别二元论的不满与蔑视。可见,乔伊斯刻意淡化他们夫妻的生理性别之用意在于:在现代的物质文明下,社会异化和精神危机使传统的性别差异逐渐淡化甚至被颠覆,人们渴望建立起与自己的社会性别相适应的身份,以此来摒弃那些对男女性别的束缚与禁锢。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批判了有悖于人性的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谬论,呼吁社会解除强加给女人的性别道德规范,旨在消除性别不平等或性别歧视。男性的阴柔和女性的阳刚都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意味着乔伊斯将女性视为发展的主体,体现对男女性别自由选择的尊重。乔伊斯反对约定俗成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角色行为,提倡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性别,并努力构建自由民主,充满人性化的性别模式。只有承认性别的互补性,男女两性才能够获得自由和解放,才能达到两性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女性要学习男性具有的优秀品质,学会与男性建立彼此尊重、平等相处的关系,明白她们的斗争不是为了赢得更好的男人,这样她们的努力才不会被看成在既定的牢笼里的自由飞翔。
二、颠覆男权社会的专制统治
男权也称父权,是一种以男性意志为绝对中心的权力,即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过千百年来的固化,男性在社会中以统治者的姿态对女性提出角色期待,而女性对自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盲目服从,并主动迎合男性对她们的角色期待,造成女性长期尴尬地处于劣势与服从地位。随着女性反抗意识的觉醒,她们渴望摆脱男权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渴望在与男性的抗争中获得平等的机会和权力。摩莉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男权制度,使人们有机会聆听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女性的心声。
首先,乔伊斯在小说的叙述结构和语言表述上体现了摩莉在男权社会的边缘化和失语权。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他者”地位、“边缘化”形象、“隐形”行为和“失根”生存空间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在前十七章里,摩莉的形象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第四章布鲁姆给她送饭时的情景, 她睡意朦胧地在床上翻了翻身。第二次是在第十章里,她向一个残腿的水手施舍了一枚硬币。其他的时间摩莉只出现在人们的意识活动和谈话中,或者说“被限定在男人世界里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4]。乔伊斯采用这样怪异的手法来塑造他认为最为成功的人物,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摩莉“边缘化”的形象和“隐形”的行为实际上暗示她的“他者”地位和“失根”的生存空间。不过,读者真正解开摩莉的真面目还是在最后一章她那涌如泉水的独白中。乔伊斯通过语法的明显错误、词句的污秽庸俗、思维的跳跃与不连贯等表达方式,生动逼真地把摩莉这个混迹于中下层社会,对婚姻不忠但心地善良的妇女形象跃然纸面。作为女性,唯有她在小说中缄默不言,其内心独白折射出生活在男权社会下爱尔兰妇女那孤独、困惑和迷茫的精神现状。弗洛伊德曾把女性比作“黑暗的大陆”。只有把女性定义为他者边缘时,男人才能作为中心再现他自己。这个比喻清楚地说明了女性都处于边缘和从属位置,都被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
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曾说:“成为女人是不幸的,而最不幸是女人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幸。”[5]然而,摩莉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活现状并没有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她不甘愿成为男性的玩偶和批评的对象。她大胆泼辣地对男性的品行进行评论:“男人们都是那德行 男人们连女人的一半个性都没有。”[3]809她还幽默地嘲讽男人那物儿就好像是“世界七大奇迹中的一件似的”[3]803。对女性所受的社会禁锢和束缚,摩莉渴望“下辈子我们女人能过的自在一点儿 别再这么把自己捆绑起来”[3]817。她身上的女性意识觉醒初现端倪,“他们可休想把我拴起来 不 妈的 我才不怕呢”[3]821。此外,摩莉对男权社会所提倡的贞洁也进行了强有力的讽刺,“该死 该死 他们总是想看到床上的血印儿好知道你是个处女 他们个个对这一点老是放心不下他们都是些大傻瓜 哪怕你是个寡妇或者离过四十次婚 只要胡乱涂上点儿红墨水不就行啦”[3]815。可见,摩莉从潜意识里就有一股反抗男权压抑的叛逆精神。她不满足于被动享受、从属男性的客体地位,她用自己的出轨颠覆男权社会的专制统治,从而实现自我的解放。
男权神话趋于破灭,女性权利得到认可。摩莉在性行为中的主动性与进攻性击垮了男权的长期垄断地位,否定了男权文化所定义的男性性霸权。摩莉回忆20年前与初恋情人马尔维中尉在直布罗陀黑水边约会的情景,“我不许他摸我的衬裙里面 因为我那条裙子是侧面开衩儿的 我可把他折磨得没了魂儿 先挑动他 我就爱挑逗饭店里的那条狗”[3]808。虽然摩莉和情人博伊兰的性爱如鱼得水,但她对他的野蛮和无知却嗤之以鼻,认为他“不晓得拥有灵魂是怎么回事 里面只有脑灰质”[3]796,“他这个人简直无可救药 他天生就不懂礼貌 不文雅 啥都不会……是个连诗和白菜都分不清楚的蠢才”[3]821。摩莉对博伊兰的否定和拒绝,暗示着男权社会的性主宰的角色被否定,代表男权社会特征的性暴力和性霸权被瓦解。摩莉认为女性也可以由性行为的接受者变为施加者,她甚至幻想在性行为中具有进攻性,“我倒想当个男人 跨在一个漂亮女孩儿身上 哦 你做出的声音多大啊 就像是泽西百合”[3]816。乔伊斯对于男女所扮演的性角色进行了颠覆式的解构,同时女性也从他者的被动角色中解放出来。
男权是必然的主导,而女权依然存在。尽管女性的客体性是无法消除的,但摩莉挑战了男权价值体系中对女性主体性的贬低,更具革命性地颠覆了女性注定要作为客体而存在的谬论,从而引起人们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和思考。可见,乔伊斯借助摩莉的形象质疑男权社会所强加给她们的规范和约束,并敢于公开反抗男权社会的价值观,表达了他对男权社会的强烈不满。只有两性和谐相处,平等相待,人们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这体现了他尊重女性和张扬女性的意识。
三、实现人性的理性回归
1907年乔伊斯在里雅斯特演讲时说:“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3]7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乔伊斯笔下的摩莉在气质、行为举止和道德意识等方面都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因此被天主教徒视为异人,甚至是淫妇。那么,摩莉作为乔伊斯的代言人,寄托着乔伊斯一种怎样的人文情怀呢?那就是发自内心地对另一个生命深切的理解、关爱和敬重。通过展示摩莉的人性魅力,乔伊斯揭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及追求人性复归、人性完善的途径”[6],也表达了他对社会中的妇女精神荒芜的深切人文关怀。
乔伊斯曾说过,“我把那些最重要的话(那些具有人性的,十足人性的话)留在《潘奈洛佩》里讲”[7]。摩莉表面上是一个水性杨花,沉湎于肉欲的荡妇,但她思想独立、敢作敢为,是自己身体的主宰者。她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性,但却是一个具有完整而独立人格的女人。摩莉在独白中反复重温她与婚外男人的性爱经历,可谓是惊世骇俗,令人难以启齿。但实际上,摩莉也是一名家庭环境的隐形受害者。面对丈夫的性功能障碍,她只能望“性”兴叹,忍受着有爱无性的夫妻生活。经济上的拮据,生活的平淡,使她“无聊得像鬼一样 我几乎琢磨着要逃走啦 寂寞得发疯”[3]805。为了宣泄人的本性和寻求空虚灵魂的安慰,她只能终日沉溺于官能享乐之中。摩莉连绵不断的意识流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性意识,还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性欲望,因此《尤利西斯》被称为淫秽情色的巅峰之作。然而,摩莉把她人性中最隐秘而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世人,理应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摩莉向世界尽情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她试图摆脱传统社会观念束缚的强烈意识,表现了真实的自我,表现出一个能充分表达自己主观意识的独立主体。[8]可见,乔伊斯充分肯定了摩莉旺盛的生命力和她对性快乐的享受态度,表达了对摩莉长久压抑而强烈的原始欲望的理解,表现了他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认同。
摩莉的自信来自于她对自己女性魅力的认可,这种认可使她不愿放弃本真的自我。从字里行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摩莉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男孩子会喜欢我的 我会叫他神魄颠倒”[3]823,“我的两眼发光 还有我那胸脯 她们缺乏那股热乎劲儿”[3]810。她的初恋情人加德纳对她的赞誉言犹在耳:“随便哪个男人只要看见了我的嘴和牙齿 还有我那种笑容就非联想到那个不可。”[3]810摩莉的自信还来自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我十五岁的时候对男人和人生所懂得的比她们所有这些人五十岁时才知道的还要多”[3]810。这些都无疑沉淀成她内心强大的资本和自信的源泉。另一方面,摩莉的经济地位也使她在家里拥有话语权,并取得了和丈夫至少平等的家庭地位。丈夫因无法满足她的性欲而深怀歉意,他只能默认妻子背叛的事实,操持家务以减轻心灵的内疚,这都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摩莉自信的砝码。
乔伊斯曾明确反对压抑人的性欲望,他认为“性道德理应顺应人的本性的召唤, 而不是反之”[9]。人的本性是自然的、本能的、原始的,而人性能使人的本性完善、和谐和自然回归。摩莉在小说中被描写成一个肉欲主义者,她完全是按照自然法则赋予她的本能去感知生活,使我们看到一个精力充沛、热爱生活、放荡不羁的现代女性形象。频繁的性交片段正是她热情放荡、生育力强的象征。摩莉并不满足于丈夫对她的百依百顺,为追求男欢女爱的享乐生活,她不惜公开与其他男人偷情。摩莉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异性的性渴望,“我巴不得迟早有那么一天旁边有个男人搂住我亲嘴 什么也比不上个长长的热吻 麻酥酥的”[3]793。在《尤利西斯》中,性是窥探摩莉内心世界的窗口,“要想了解我 就来跟我睡觉吧”[3]796。“我喜欢他做爱的方式 他懂得怎样叫女人着迷”[3]798。摩莉与博伊兰的性爱更加疯狂、赤裸和原始,备受压抑的人性得到充分的宣泄与释放,博伊兰让她感受到女人的真谛所在。摩莉表面上看是一个放荡、纵欲的女人,但我们感受到她的激情和活力就像是“一朵山花”充满生机。显然,乔伊斯并非要把摩莉刻画成一个思想空洞的肉欲动物,而是采用异化的方式将压抑的人性毫不掩饰地放大。面对人性的割裂、扭曲和异化的悲惨现实,乔伊斯站立在一个更高的哲理层次上,塑造摩莉的形象来充分展示人性中灵肉的魅力,让女性的个性得到充分体现,独立的人格得以完整呈现,内心世界得以自由袒露。
乔伊斯对人性回归、人性完善的探索,既显得冷静、理智,又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6]。在摩莉扭曲的婚姻里,精神和肉体的出轨彼此呼应、交互出现,甚至还表现出精神忠贞、肉体出轨的现象,但乔伊斯的高超之处在于将人性和肉欲相互映衬,还原女性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和矛盾的意识活动,让人们倾听她们内心的呐喊和苦诉,看到她们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生存状态。小说最终以摩莉的大写Yes结束全文,摩莉的情人从她的纷繁思绪中淡化退出,可见,在摩莉的心中他们不过是 “布卢姆的替代品”[3]1187而已。夫妻关系有望和好如初,此刻人性的光辉达到和谐与共鸣,诠释了乔伊斯倡导的人性至上的哲学理念。只有让女性的性欲得到自然的释放,女性的人性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人类才能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找回失去的自由,从而实现人性的回归。
四、构建宗教文化和民族未来
爱尔兰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文明古国,曾经独一无二的天主教信仰起到了整合社会的作用。但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多民族、跨地区、跨文化的复杂社会体也随之形成,此时本族宗教和外来宗教的相互斗争自然成为社会动荡的焦点。在《尤利西斯》中,宗教作为政治制度的灵光圈,神化了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成为文化压迫的隐形工具和控制爱尔兰人民的帮凶。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来说,宗教则成为反对宗教迫害、反抗殖民统治的有力武器,他们反对宗教霸权,拒绝成为僵化的天主教和英国新教的牺牲品和替罪羊。摩莉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情色和人性层面的分析,一定还寄托了乔伊斯关乎人类宗教、民族等重大问题的深层思考。
乔伊斯选定摩莉夫妇作为主人公绝非偶然,他们的宗教身世暗示爱尔兰的天主教与外来宗教冲突的开始。在宗教民族斗争如火如荼的爱尔兰,犹太教的身份对布鲁姆是个不利的因素,周围人的漠视让他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并处处遭受压迫和歧视。为了能融入到爱尔兰宗教文化之中,他数次改变宗教信仰,以掩盖自己的犹太身份,但仍然受人欺凌。同样,在犹太族受歧视的爱尔兰,犹太血统对年轻貌美的摩莉也是个不利因素,这也是她委身下嫁给布鲁姆(一个没有固定职业,靠为报纸拉广告为生的人)的缘故。宗教所造成的尴尬身份使本不可能的婚姻在爱尔兰成为现实,实际上表达作者对爱尔兰天主教排斥和迫害异教的强烈不满。爱尔兰自古以来宗教派别往往互相排斥、明争暗斗,各自以神圣的名义去压制以至消灭对方。[10]这种宗教排他性容易引起国家的分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爱尔兰长期四分五裂,国家得不到独立统一。
充满肉欲的摩莉与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800BC-600BC)中奥德修斯忠贞守节的妻子珀涅罗珀形成鲜明的对比。乔伊斯毫不避讳地描述摩莉春意萌动的性意识,体现了她水性杨花的性格,这与天主教所倡导的女性典范形成极大的反差。在《奥德赛》中,珀涅罗珀是一个传统社会的理想女性,她对丈夫的忠贞不渝成为各个时代训诫妇女的经典教科书。在奥德修斯踏上去特洛伊征程的20年里,珀涅罗珀独自一方面操持国家的政务,一方面抚养倔强不驯的儿子,还要应对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显然,乔伊斯笔下摩莉是对“忠贞守节”的宗教文化的一种讽刺的模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乔伊斯安排摩莉的生日与圣母玛利亚的诞辰之日巧合,这种安排嘲讽了天主教社会中所定义的女性典范,表达了作者对摩莉敢于反抗、追求个性独立的叛逆精神的认可,表达了作者对传统爱尔兰社会宗教的蔑视和痛恨。
乔伊斯的现代性体现在他对传统宗教文化的挑战。乔伊斯虽然是在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长大的,但天主教会参与杀害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帕内尔以及教徒间的残酷屠杀,使他对宗教的虚伪性和残酷性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贯穿全文始终,我们可以感觉到摩莉是政治和宗教的局外人。她家隔壁的老太婆赖尔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在摩莉的眼中,“想必正因为没有一个男人会对她多看上一眼 她信教才信得那么虔诚 但愿我永远不会变得像她那样”[3]791,表达了摩莉对宗教的不屑和鄙视。摩莉拒绝忏悔是因为她看穿了教父神圣外衣下的虚伪和庸俗,“那阵子我常到科里根神父那儿去忏悔他摸了摸我”[3]793。摩莉对宗教也毫无畏惧和敬仰之意,她竟然在通往唱诗班席位的台阶上与情人激情接吻,甚至在教堂内男欢女爱无所顾忌。极具讽刺的是,正是这个不信教的摩莉竟变成了布鲁姆通向永恒护照所必不可少的密码,成为死者动物王国中的女神。[11]摩莉象征着布鲁姆心中的耶路撒冷,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的归属。
在摩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堕落和迷茫,但更感受到她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繁殖力。摩莉与不同特质男人的性爱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走向文化杂糅的爱尔兰的寓言”[12]。爱尔兰天主教与外来宗教的糅合,寓意着充满人性化的宗教应具备兼容性和包容性。她强烈的性欲则是女性非凡创造力的表现,象征着外来宗教势不可挡,呈现强大的生命力。爱尔兰宗教不应孤立地挺立在绝望的废墟上,而应坚持多元化原则,与外来的宗教融合,取长补短,才能使爱尔兰文化和文明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璀璨的光芒。
萧乾曾说,《尤利西斯》除了在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之外,还有民族主义思想(反抗英国统治)。尽管乔伊斯从1902年起流亡国外,但他时刻密切关注爱尔兰的局势,对爱尔兰人民的痛苦极为担忧。[13]摩莉的家庭是爱尔兰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乔伊斯之所以把摩莉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并非满足人们的好色猎奇心理,也许旨在引起人们对爱尔兰民族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思考,所以《尤利西斯》又被称为“爱尔兰民族寓言”[14]。摩莉家庭的破裂一方面是由布鲁姆本身的性功能障碍造成的,寓意着爱尔兰本族文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像博伊兰这样的奸夫所害,寓意着乔伊斯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即不受欢迎的“家里的陌生人”[3]7的严厉谴责和无情抨击。布鲁姆安于现状、苟且偷生的心态寓意着爱尔兰人麻木不仁、幻想合作,安于被英国人压迫、奴役的现状,使人感受到乔伊斯对祖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平庸却爱其弥深的爱国情结。显然,乔伊斯意在为爱尔兰摆脱精神瘫痪指明方向:在处理国家和民族问题时,应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以宽容与认同来代替诋毁与仇视,以和谐发展代替掠夺与奴役,爱尔兰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古老的爱尔兰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1] Barnhart, Clarenee L., ed. The New Century Handbook of English Literature[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7:67.
[2] 彭珍珠.《尤利西斯》 与社会性别[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1): 58-61.
[3] 詹姆斯·乔伊斯. 尤利西斯[M]. 萧乾,文洁若.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 French, Marilyn. The Book as World: James Joyce’s Ulyss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259.
[5]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814.
[6] 胡媛.《尤利西斯》中的性描写和人性探索[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121-124.
[7] Ellmann, Richard, ed. James Joyce: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278.
[8] 游巧荣. 论《尤利西斯》的复调性[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二十辑), 2014(春): 43-56.
[9] Joyce, Stanislaus. My Brother’s Keeper[M].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58:160.
[10]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93.
[11] Attridge, Derek,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239.
[12] 申富英. 论《尤利西斯》中作为爱尔兰形象寓言的女性[J].国外文学, 2010(4):112-119.
[13] 李维屏. 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21.
[14]Gilbert, Stuart, 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Ⅰ[M]. New York: Viking,1963:180.
(责任编辑 田景春)
Subversion and Constr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Molly in Ulysses
WANG Hongkun1, WANG Xiaoyu2
(1. Mechanic Engineering Department, Yantai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ollege, Yantai Shangdong 264006, China; 2.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150080, China)
Molly is a female character most brilliantly portrayed and most controversial in the novel Ulysses by James Joyce. Critics and scholars have so far identified Molly no longer as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a dissolute woman and nymphomaniac, because the conventional negative assessments of her could not conceal her as the paragon of being unconventional and pursuing independe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depth implication of Molly who is created by Joyce with the aim of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 of sex and autocracy of patriarchal society. By doing so, Joyce attempted to make human nature return to reason, and establish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rish people and their religious culture, meanwhile, it also reveals the author’s humanistic sympathy and concern over the social plight of the Irish women.
Ulysses; Joyce; Molly; subversion; construction
I562.074
A
1674 - 9200(2017)01 - 0089 - 06
2016 - 04 - 06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专项课题“人文素质教育视阙下的高职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创新研究”(CGW15023)阶段性成果。
王洪坤,男,山东栖霞人,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和英美文学研究;王小雨,女,山东栖霞人,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本科生,主要从事朝鲜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