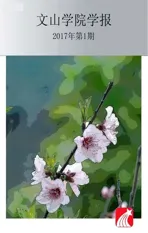明朝对贵州安顺府的经营
2017-03-11罗康智
罗康智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明朝对贵州安顺府的经营
罗康智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明代的安顺府,正式设置时间虽然迟至万历三十年(1602),但该府的行政规模却直接承袭于元朝。在明代的通滇驿路中,安顺地区的战略形势至关重要。明朝高度重视安顺地区的行政建置和军事控制。与明代其他府级行政单位相比,明朝对安顺府的经营表现出一系列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可以从安顺府设置的过程、设置后的职权结构,以及后续问题中看出。
安顺府;经营;基层建置
一、前言
明代的安顺府,正式设置时间虽然迟至万历三十年(1602),但该府的行政规模却直接承袭于元朝。明代的安顺军民府,辖境范围极广,东起猫跳河和格必河,西抵云南边境,北起乌江南部分水岭,南达广西边境。按当代实测地图估算,辖地范围将近2.3万平方公里。所辖民族众多,包括彝族、苗族、布依族、仡佬族,还有为数不少的早期汉族移民,但在明代,府、州、县所辖编户极为有限。
如明人著述所言,安顺地区在唐宋时一直为朝廷的羁縻之地。朝廷对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头领执行的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羁縻办法。对这一地区的山川形胜和风土民情,完全凭前来朝贡的各民族头领的自我介绍,以至于唐宋两朝正史中对这一地区的形胜记载都几近于空白。元朝统一全国后,这一地区的系统地名录才正式载入《元史·地理志》。但《元史·地理志》也仅是提供一个地名清单而已。由于《大元一统志》失传,元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同样只留下一串地名。明廷接管贵州后,几乎是白手起家,从头调查,首次编图。加上各种社会背景的牵制和技术上的困难,明代对于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在地名上留下的痕迹一直无法理顺。
大致而言,正当唐朝与南诏对垒之际,南诏三十七部中的一部,即“于矢部”在安顺地区势力坐大,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势力集团。大理取代南诏后,“于矢部”所辖地带被称为“特磨道”,“特磨道”的控制势力逐步深入到黔中地区。[1]但这一过程,唐宋两个王朝均所知甚少。仅是在一些私家著述中略有提及,如樊绰的《蛮书》、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等。在这些书中都提到了“特磨道”,并指明“特磨道”是大理将马匹贩运到广西的一个中继站。就实质而言,类似的记载仅是传闻而已,“特磨道”的行政结构、盛衰沿革、辖地范围,至今无从确考。以至于元朝接管这一地区时,“特磨道”如何被改称为“罗甸国”,元代留下来的文献同样无法确考。但“特磨道”“罗甸国”对安顺地区行政建置的影响,却可以在明代的典籍中找到旁证。明代接手的安顺地区掩隐在历史的迷雾中,人们可以对它的历史提出各种猜测,但就是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比如,元廷为何要将传闻中的罗甸国辖地,设为普安路和普定路两个行政单位?为何普定路的6个长官司长官家族大多出自彝族,而所辖的各族居民却被统称为“龙家”?又如,明廷如何将元代留下的两个不同的行政单位轻而易举的合编为一个府?再如,贵州省的其他地区总是土司林立,而在这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仅仅只有7个中小土司,而这些土司的级别都十分卑微,最高不过是安抚司而已,为何没有发展成大土司?这些问题至今还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较为可信的猜测只能是,早期的“于矢部”其核心地带仅止于北盘江以西的普安地区,其后,趁周边各族势力相峙不下的机遇,才将控制范围推进到日后的普定地区。由于腹心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差异,在元廷接管这一地区时依然存在,元廷才得以将传闻中的罗甸国辖境一分为二,分别设置为普安路和普定路,实现了分而治之的施政目标。也正因为普定地区的各族曾经被普安陇氏土司统辖过,因而这一地区的各族居民才被统称为“龙家”,而这一地区的土司家族也才因此而社会地位下降,大多数为“白彝阶层”,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小土司的领地才会如此辽阔,与他们的品级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样由于历史上曾经是一体,明廷也才得以反其道而行之,将二者合二为一,统编为安顺府。
在明代的通滇驿路中,安顺地区的战略形势至关重要。东起湖南,西至云南的驿路主干线,从东到西横贯全境。境内一旦有警,驿路必将受阻,因而维护驿路的安全,维持驿路的运行,成了该府施政的关键所在。为此,属于军事建置的卫所和属于民事建置的府、州机构,都沿着驿路按一条线排列,并在地名中打下了军屯和驿传的烙印。带有“营”“屯”“铺”“起”“旗”等字眼的地名充斥于整个古驿道沿线。
因而,历代学者对安顺地区的形胜表述虽然各异,但对安顺战略地位的险要却众口一词。《读史方舆纪要》云:“(安顺)府右临粤西,左控滇服,形势雄远,屹为襟要。”又《肇域志》称:“(安顺府)连贵州,抵普安,通金筑,据水西,西南要冲,夷深襟喉”。正因为战略形势险要,整个明代都高度重视安顺地区的行政建置和军事控制,这就给安顺地区的建置沿革,造成了一系列特点。若与明代其他府级行政单位相比,如下一些特点足以表明明代对安顺地区经营的特殊性,当然这些特殊性绝非凭空而来。
二、政治经营的特殊性
(一)行政机构设置早,配套完备迟
对安顺府的行政建置,《明史》载:“安顺军民府,元安顺州,属普定路。(洪武五年改置普定府)。洪武十五年三月(安顺州)属普定府。十八年(普定府废),(安顺州)直隶云南布政司。二十五年八月(安顺州)属四川普定卫。正统三年八月(安顺州)直隶贵州布政司。成化中,徙(安顺州)州治普定卫城。万历三十年九月(明廷将安顺州)升安顺军民府”。[2]1201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明初将元代的普定路改设为普定府,并将安顺州拨归新置的普定府统辖。明洪武十八年(1385)罢废普定府后,将安顺州拨归云南布政司统领。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朝廷将原属云南布政司的安顺州拨归四川都司所辖的普定卫统领。正统三年(1438)八月,朝廷将原属普定卫的安顺州拨归贵州布政司,作为直辖州。成化中期,朝廷将安顺州治所迁移到普定卫卫城,即今天的安顺市。从此时起到万历三十年(1602),普定卫与安顺州同城设治。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朝廷将安顺州升格建置为安顺军民府。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明代的安顺军民府,名称来源承袭自元代的安顺州,而辖地则来源于元代的普定路。安顺州在整个明代仅是地位略有升降,一直延续到安顺军民府正式设置时才被取代。安顺府下辖的镇宁州和永宁州,也是承袭元代旧制,并贯穿整个明代。
安顺府下辖的普安州与上述三州的建置稍有不同,《明史》有载:“普安州,本贡宁安抚司。建文中置,属普安军民府。永乐元年正月改普安安抚司,属四川布政司。十三年十二月改为州,直隶贵州布政司。万历十四年二月徙治普安卫城。三十年九月属府”。[2]1203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永乐十三年(1415)十二月,朝廷对普安安抚司实施改土归流后,就其领地设置为普安州,并将普安州拨归贵州布政司直辖统管,该州就此成为贵州设省后直接统辖的第一个州级单位。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明廷才将普安州拨归安顺军民府统辖,该州也和永宁、镇宁两州一样,一直延续到明末,其间并无重大变动。
综上所述,若就行政机构设置的稳定程度而言,明代的安顺军民府,可以称得上是“长期稳定,一贯到底了”,其他各府频繁发生的行政机构分合,辖地划拨,在明代安顺地区绝少看到。州级建置虽早,但州下的县级建置长期告缺,县以下的里甲建置到了明末尚无规范设置。以至于这四州在贵州设省后的200多年间,一直是空壳州,每个州仅代辖一到两个长官司而已。
(二)四州并行,三州遥领
万历三十年(1602)前,安顺地区一直并行着安顺、镇宁、永宁、普安四个州的建置,但这四个州的治所大多没有设置在它的辖境内,而是集中设置于其他地方,对自己的辖地和居民长期实行遥控,最突出的事例是镇宁和永宁两州。《明史》载:“镇宁州,元至正十一年四月以火烘夷地置,属普定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二十五年八月属普定卫,后侨治卫城。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嘉靖十一年六月徙州治安庄卫城。万历三十年九月属府”。[2]1203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到,镇宁州的治所在嘉靖十一年(1532)以前,一直设在普定卫城,即今贵州省安顺市内。值得一提的是,镇宁州统领的两个长官司的辖地并不毗邻,其中镇宁州统领的十二营长官司的领地位于今贵州省镇宁县的西北角,并有部分辖境深入到六枝地区,而镇宁州统领的康佐长官司的辖境却在今贵州省紫云县。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六月,朝廷才将镇宁州治所从普定卫城(今贵州省安顺市内)迁移到安庄卫城(今贵州省镇宁县县城)。还应当看到,即便明廷将镇宁州治迁到安庄卫城后,对其下属长官司仍然处于遥控状态。这是因为,镇宁州的州治仍然没有处于所辖两个长官司的领地内,直到明末,镇宁州的治所仍然游离在其统领的十二营和康佐长官司所处的领地之外。
永宁州也一样,该州统领顶营和慕役两个长官司,顶营长官司的辖境在今贵州省关岭县的北部,慕役长官司的领地则位于今关岭县的南部和镇宁县的南部。而永宁州的州治却和镇宁州一样,都设置在普定卫城内(今贵州省安顺市内),此情《明史》亦有载:“永宁州,元以打罕夷地置,属普定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二十五年八月属普定卫,后侨治卫城。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嘉靖十一年三月徙州治关索岭守御千户所城。万历三十年九月属府”。[2]1203结合当今地图,从上述记载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永宁州的治所与该州的领地之间,横隔着安顺、镇宁两州的辖境,从永宁州治到最近的辖地,至少也超过了80公里 。这种遥领状态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一直持续到嘉靖十一年(1532),总计长达140年。即使永宁州治迁到关索岭守御千户所治所(今贵州省关岭县城)后,永宁州治仍然处在军屯地上,依然没有落脚到自己的辖境内。
除了上述两州外,安顺州也存在类似现象。安顺州的州治,设置于元代普定路旧城,即今贵州省安顺市旧州乡,但其州治所在地却不处在其所领两个长官司(宁谷和西堡)的领地内。与镇宁和永宁相比,只不过治所与辖境稍近罢了。明成化中期,安顺州治所迁移到普定卫卫城(今贵州省安顺市内),这个新治所完全置于军屯地的包围圈内,同样不处于自己的辖境内,仅是遥领的距离缩短而已。从成化中期到嘉靖十一年(1532),其间经历半个多世纪,普定卫卫城真可以说得上是行政机构拥挤不堪了,小小的一个普定卫卫城内,同时并存着安顺、镇宁、永宁三州的治所,还有属于军事建置的普定军民指挥使司。此外,西堡、康佐等长官司的治所也挤在卫城内,这样的行政机构分布格局,在整个明代可以说得上是绝无仅有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将安顺州升格为安顺军民府,该府实领镇宁、永宁、普安三州,这是明代贵州行省中辖州最多的一个府。此外,该府还亲领西堡、宁谷两个长官司,也是贵州行省中“府亲辖地”较广的一个府,仅次于都匀府。
(三)长期军管,兵多民“少”
明代的安顺地区卫所林立,屯军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率。从的澄河渡口算起,沿着驿路主干线,自东向西排列着威清、平坝(又名平安)、普定、安庄、安南、普安六卫。按明代建置,一卫统兵5 600人,连同家属,一卫所辖的人口多达25 000余人,六卫共计统辖人口150 000余人。而当时的安顺地区虽有四州建置,却完全没有里甲建置,地方行政机构直辖的纳税户几近于空白,各州仅代辖长官司,长官司的赋税和劳役负担都由土司自愿“认纳”,而民户数额却长期空白,田亩数额也长期空白。整个明代的安顺地区,单就表象而言,几乎是随地皆兵,却不见民户。除了见兵不见民外,这些军事建置还具有军民两管的职能,行政机构虽有设置,但却长期依附于卫所,突出的事例有普定卫和普安卫。安顺军民府设置前的200余年间,安顺、镇宁、永宁三州一直由普定卫代管,普定卫也因此而升格为军民指挥使司。普安州则一直由普安军民指挥使司代管到明末。安顺军民府设置后,行政隶属关系来了一次颠倒,过去是军管民,此后是民管军。然而,这仅是停留在名份上,因为新的安顺军民府还有赖于普定卫及其他各卫作后盾,连安顺军民府的治所,都控制在普定卫的手中。因而可以说,明代的安顺地区几乎是军管到底。
(四)剿抚并用,刚柔相济
安顺地区的民族构成十分清晰,共计有彝族、苗族、布依族、仡佬族、汉族五个世居民族。但在明代典籍中,对民族的称谓却十分含混,除偶尔提到“罗倮”“革僚”和“苗”外,往往将这一地区的居民泛称为“龙家”。“龙家”到底是什么民族成分,整个明代典籍一直没有定说。直到近代,经过充分研究后,才知道它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是一个从前代传承下来的习惯性称谓。其中包含着苗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和汉族等众多民族。在明代,各民族居民均由土司代管,安顺地区的六个长官司和一个安抚司,分别管辖着不同的民族。大致而言,普安安抚司,即后继的普安州,主要统辖彝族居民,并兼管部分苗族、布依族和白族居民。慕役长官司的长官家族为彝族,辖境内的主体居民则是布依族。顶营长官司的长官家族也是彝族,统领的居民以彝族为主,苗族次之,也有少数布依族。十二营长官司的长官家族也是彝族,其属下居民,明清典籍都称为“龙家”,而实质上是以布依族为主,其次为苗族和仡佬族。康佐长官司家族为布依族,统领的主体居民是布依族,但却承担着招抚生界内苗族的重责,该长官负责招抚的苗族属于操苗语西部方言,麻山次方言的苗族,即麻山亚支系的苗族。明代典籍中有时称他们为“康佐苗”,有时又称他们为“克孟牯羊苗”。西堡长官司的长官家族出自彝族,统领的居民主要为苗族和仡佬族,这些居民在明代典籍中有时也称为“龙家”。宁谷长官司的长官家族也出身彝族,统领的主体居民是布依族,并负有招抚生界苗族之责,招抚的苗族对象包括两个支系,一个是操苗语西部方言贵阳次方言的苗族,明代典籍中也称为“龙家”,清代文献中改称为“青苗”。另一个是操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的苗族,明代典籍中也将他们称为“龙家”,清代典籍中改称为“花苗”或“白苗”。
在明代典籍中,除了将这些民族泛称作“龙家”外,仅偶尔正面提及“苗”或“革僚”字样,而且提及这样的字眼时,大多与战乱相关联。不过真正由民族间的摩擦而导致的战乱,在整个明代的安顺地区极为罕见。真正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挑战的民族间战乱,只有两次。其一是明初时,由于对明廷的屯田置卫措施有疑惧而诱发的战乱。这种战乱主要发生在普安州,具体表现为彝族地方势力与官军的对抗,总计仅有两次大的战乱。这两次大的战乱都发生在洪武年间,而且集中在洪武二十年(1387)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间。引发战乱的原因在于,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年(1387)征调湖广都司各卫所官军前往普安州的盘江河谷,实施大规模的屯田,在屯田用地的征拨上,由于情况不明误占了彝族的冬牧场,导致了相关彝族家支对明廷的不满,激变为阿资和密即为首的两次彝族地方势力反叛。[3]313-314事后由于明廷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不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致使由屯田而引发的事端迅速得到平息,并在其后的200余年间,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与普安州类似的情况,在安顺州的辖地内,特别是在西堡长官司的领地内,在明初时也频繁爆发,原因与前者相同,都是明军在征拨屯田用地时,无意中挤占了仡佬族和苗族赖以为生的土地资源,因而引发为苗族和仡佬族对明军的反抗。[3]317在这一地区,明军采用的是高压政策,凭借武力严厉镇压,迫使这些苗族和仡佬族居民逃散,从而巩固屯田用地。好在苗族和仡佬族当时的生计方式是游耕,对土地资源不追求稳定占有,因而这些冲突波及的范围不大,对明廷的威胁也不明显,但却留下了后遗症,到明代中期,西堡长官司属下的苗族和仡佬族抗税事件仍时有发生。
另一类民族间的摩擦则导因于各民族地方势力的内部冲突,包括土司职位的承袭、土司间领地的纠纷、土司内部各民族间的摩擦。但类似事件无论是在发生的频率上,还是规模上比之于同时代贵州其他各府都要少得多,也小得多。其中,真正对明廷构成挑战的只有一次,那就是发生于明弘治年间的“米鲁事件”。[4]8187“米鲁事件”牵动了明廷朝野,先后动用了4省兵力,前后历时7年,最后动用了南京兵部尚书亲自平叛,才结束了这场战乱。整个事件中,明朝高级官吏的贪污受贿,明军战斗力衰弱,明廷对土司的脱控全部暴露无遗,堪称明廷由盛入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这一事件的起因却十分蹊跷,居然是由土司家族内部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和父子兄弟不和而起。明廷对土司的控制、对土司承袭的管理一直十分成功,类似的争端若发生在其他各府,明廷都能做到游刃有余的迅速控制局面,而且大多能通过法制手段,依法裁决。真正发展为与明廷对抗的叛乱为数极少,而“米鲁事件”却令人意外,对这样一起家庭争端,明廷却无法依法惩处,最终演化为米鲁自称为“无敌天王”,将自己所住的村寨命名为“承天寨”,还为自己树立了只有皇帝才设置的“黄纛仪仗”,公然对明廷皇宫正门的承天门提出挑战,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这种胆大妄为的举措在整个明代的贵州地区,几乎是绝无仅有。甚至明末“奢安之乱”时,安邦彦和安位都不至于像米鲁那样胆大妄为。纵观整个事件本身,与其说是少数民族与明廷公然作对,倒不如说是明廷官场腐败而酿成的祸端。就实质而论,米鲁的反叛所争的不过是一个承袭权,但却发展成朝野震动的战祸,应当说是明廷咎由自取。
除了“米鲁事件”外,真正的土司纠纷仅有正德年间,安顺土知州与宁谷长官司的争地械斗事件。不过对这次事件,明廷处理得法,及时依法按照土俗裁决,双方进贡粮食赎罪,很快就平息了争端。就总体而言,上述几次事件,比起整个明代安顺地区的民族关系形势而言,都属于枝节问题。康佐、顶营、慕役、十二营四个长官司在整个明代,几乎未发生过一次民族争端,以至于在《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中对这四个长官司竟然只字未提,说明明代安顺地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
(五)重驿路安全,轻基层建置
安顺军民府设置前设置后,明代在整个安顺地区均无县级建置,更无编户里甲,府、州两级都是直辖一两个长官司。按照明代制度,土司虽有交纳税赋的职责,但交纳的数额则由土司“认纳”。各级土司根据自己的能力,能交多少算多少,政府既不清查户口,也不丈量土地,完全听凭土司自愿,这必然派生出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府、州两级的开支从何而来?有关安顺地区各土司认纳粮赋、劳役的情况,《明史》并无确载,明代各地方志所记载的土司税赋数额也极为有限。《明史》仅载:“永乐元年,故普安安抚者昌之子慈长言:‘建文时父任是职,宜袭,吏部罢之。本境地阔民稠,输粮三千余石,乞仍前职报效。’命仍予安抚”。[4]8187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普安安抚司慈长要求承袭安抚司一职时,提及该安抚司认纳的粮赋总数是3 000余石,至于其他各土司的税赋额度,《明史》中很少提及。但对于赋税交纳而引起的纠纷却又极少发生,《明史》仅载西堡长官司两次因向下属征交粮税而激变为事端,该长官司温恺还因此害怕明廷治罪而上吊自杀。与贵州省内其他各府相比,也是一件奇特的现象。府、州两级庞大的行政开支,显然得另有出处。问题的答案是横贯全境的驿道,这条驿道主干线,地处通滇的咽喉之地,全长300余公里。云南方面的庞大军需和人员流动,云南方面的土特产东运都只能凭这一条孤悬“一线路”沟通。明廷为了确保军事、政治沟通的需要,不得不做出巨额的资助。这笔维护驿站的军费在安顺当地由于没有里甲编制和稳定的税赋来源,因而根本承担不起起码的开支。整个明代维护驿路的军费都来自于“协济”,即邻近各省在正常税收中按比率划拨一定的份额作为驿路的维持费。这样一来,就使得驿路的存在不仅不是当地群众和行政机构的负担,反倒成了当地群众一笔稳定的收入。府州两级行政机构的主要职能也因此而发生了转换,不再是统辖民户,征收赋税,审理刑役,而是专管驿路伕马的配置和调拨。这倒是一方几便的管理模式,只要确保驿路畅通,沿线的群众不愁找不到生活来源,府、州两级行政机构也可以很容易从中抽取行政费用,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刑事诉讼也就一了百了。从而可以做到,税赋收入极度低下,基层建置长期空缺,而刑事诉讼极其鲜少的特有行政局面,这也是所辖各州长期可以遥领的经济原因。
三、结论与讨论
明代对安顺地区经营的上述种种特点,若与贵州其余各府相比,显得突出而鲜明。但若以整个明朝对贵州经略决策为背景,这些特点又会变得事出必然,并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维持驿路主干线的畅通,在安顺地区表现为三州共一城。在贵阳地区则表现为驿道常由密集的卫所军管,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用意却一脉相承。这应当视为明代对安顺地区经营特异性的主观成因。除了主观成因外,还与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过程相关联,与当地民族结构,特别是各民族生计方式的差异有联系,更与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密切相关。
从自然地理结构看,明代安顺、镇宁、永宁三州的辖境都处于乌江水系与盘江水系分水岭的南坡。在明代驿路贯穿的地段,地表相对平缓,驿路沿线绝少高山巨川的阻隔,修筑驿路主干道,投工少,维护成本低,安全防卫容易,几乎是最佳驿路走向。但驿路的西段则不同,镇宁州和永宁州的辖境间横亘着打邦河河谷,以及平行排列的若干条地裂,为此驿路主干线不得不绕道从北面的打邦河上游山区穿过。再向西,驿路又得穿越北盘江河谷,驿路主干线同样得向北绕道,从茅口河渡江进入普安境内。驿路在普安境内还要穿越麻布河河谷,翻越云南坡,从武胜关进入云南。东西两段一平一险,直接导致了安顺、镇宁、永宁三州的沟通协调困难,这就使得三州共一城,反而有利于驿路伕马的配置和调拨。三州共一城与其说是一种行政建置上的过渡格局,倒不如说是三州维护驿道的共同职能在地理环境的限制下,在同一城池内办公更简捷、方便。
除驿路主干线穿越的地段外,其余地区高山深谷相间,一山之隔,一水之分,其气候、植被、土壤、地层结构各不相同。整个安顺大地完全可以比喻为“多种自然地理结构和多种生态结构的大拼盘”。位于北盘江河谷的大小盘江、六马属于干热河谷地带,终年无霜,甚至可以种植热带农作物。然而,相距不到十里的安笼箐山却属于高寒地带,冬季冰封期超过一个月,普安境内的高山更是如此。镇宁所辖的康佐长官司,其核心领地在火烘,这儿也是温暖湿润的水稻耕作带。但在明代时,此地疟疾盛行,以至于康佐长官司家族整个夏季都在普定卫城办公,为的是躲避疟疾,到了冬天才去视察自己的领地。至于西堡、十二营、顶营等长官司的领地,由于处在高原台面上,又在江河的上源,因而气候寒冷,水源补给不足,只能种植旱地作物,或者靠畜牧为生。这样的地理背景,对于习惯于吃稻米的卫所屯军而言,当然十分不利,但对维持驿道畅通而言却大有好处,相对价廉的马匹和畜力,以及丰富的饲草资源,有利于降低驿路运输成本,各民族群众也能从朝廷下拨的驿道维持费中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贵州西线驿路在明代相对安定,战乱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得力于地理环境的恩赐。明代驿路的长期稳定延续,导致了安顺地区畜牧业的兴旺,也支撑了牛马集市的繁荣。这样的大牲畜集市,在明亡以后还延续了数百年,直到现代公路开通后,才淡出了历史舞台。明代安顺地区的行政建置,县级机构一直空缺,里甲编制到明末时还没有启动,除了驿道主干线穿过境内使当地群众、行政部门受益外,地理环境的特异性使当地居民可以通过驿路获得稳定收入,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碎分布,必然导致民族构成具有如下三大特征:其一是各民族交错杂居。安顺地区各少数民族在空间分布上的杂居现象极为突出,不管是苗族、彝族、布依族还是仡佬族,都很少由单一民族形成连片聚居区,而是与其他民族交错毗邻杂居。其二是除彝族外,其他民族的社会组织规模都十分有限,跨地区、跨流域的大型社会组织在这一地区历史上很少出现。这里仅以布依族的社会聚合为例,康佐长官司的直辖领地火烘,主体居民是布依族,但这个布依族的社会聚合,其分布范围仅20余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之外,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要与苗族和仡佬族的分布区接壤。再如安顺州的旧址,即明初普定军民府的旧址也是一片布依族聚居区,但整个布依族的分布带也没有超过60平方公里。布依族的村寨附近,还杂居着苗族村寨。至于苗族和仡佬族,其社会组织规模更小。一个寨长所辖之地,一般不超过100户人家,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其三是跨民族的社会联合体的规模很小,而且数量不多。明廷从元朝手中接管的6个长官司,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长官司在明代,都没有发展到足以与明廷抗衡的地步。与明廷的纠纷仅止于赋税的争端,或者是长官司之间的领地纠纷而已。在这样的民族结构中,唯一例外的是彝族的社会集合。
上文已提到,明廷接管的普安和普定地方势力都来源于早年的“于矢部”“特磨道”和“罗甸国”,这一系统正出自彝族,而且是作为南诏和大理政权的延伸部分而存在。也正因为这些彝族地方势力与云南的关系密切,因而明廷接管他们后,一项醒目的行政建置决策就是将他们统统拨归四川行省统管,目的在于割断他们与云南地方势力的联系,等待贵州行省设置,行政机构逐步健全后,才陆续将他们拨归贵州行省统管。而且最先拨归贵州统管的地段正好是离云南最近的普安州,而处在贵州腹地的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则直到正统三年(1438)才拨归贵州行省直辖。这样的划拨秩序不仅揭示了明廷截断普安、普定与云南地方势力联系的行政建置意图,而且充分展示了明廷灵活处置行政设置的政治艺术。
各民族的生计方式同样直接影响着安顺地区行政建置特点的形成。布依族长期从事定居稻田耕作,主产品稻米对支持卫所的存在至关重要,因而布依族在其正常的生计方式中,与屯所卫军的存在很容易兼容,而且容易从中获利,这乃是整个明朝安顺地区的布依族与明廷从未发生过重大冲突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地理结构的特点,安顺地区的布依族聚居点大多偏离驿道主干线,与卫所也保持较远的距离,屯田用地的划拨对布依族土地资源的占用冲击很小,这乃是布依族与朝廷冲突较少的第二个原因。布依族的聚居点高度分散互不连片,其间又隔着苗族和仡佬族的分布地,布依族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政治集合,这乃是冲突较少的第三个原因。
苗族和仡佬族在整个明代,主要靠刀耕火种式的游耕为生,居住地规模小、流动大,对土地资源的占有不稳定,社会集合规模更小,致使明廷各卫所征拨屯田用地时,不容易与苗族和仡佬族发生正面冲突。苗族和仡佬族反而能从驿道的维持费用中获利,因而苗族、仡佬族在明代爆发的事端,矛头都不是指向明廷,而是指向代管他们的长官司,最后还得由朝廷充当仲裁人平息纠纷。再加上苗族和仡佬族的分布虽然很广,但却大部分偏离驿道,特别是安顺地区南部的苗族“生界”,距离驿道主干线最近处都要超过80余公里 ,以至于仅仅6个长官司存在,就足以隔断生界的苗族、仡佬族对驿道安全的骚扰,这乃是明代安顺地区的生界面积并不小,包括麻山和花山两大片区,但在整个《明史·贵州地理志》和《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中几乎没有留下“生界”长期存在的痕迹。这些“生界”一直到清雍正年间才被中央王朝注意到。
在明代典籍中,将安顺地区的众多民族皆统称为“龙家”,仅个别情况下才使用“苗”和“革僚”两个族称,以至于《明史·贵州地理志》和《明史·贵州土司列传》绝少正面提及安顺地区的民族构成,官方文书通常是称为“龙家”,这一地区在明代时的民族关系实况,长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甚至造成了安顺地区的少数民族是从外地迁入的误解。只有揭示“龙家”这一族称内部结构的复杂性,相应的误解才能获得澄清。
从清代典籍看,安顺地区“龙家”的服装都尚白,这显然是曾隶属过彝族土司的后余影响。不同“龙家”的头饰则成了识别“龙家”族属的重要标志,“大头龙家”和“狗耳龙家”大致是指苗族,“小头龙家”是指布依族,“曾竹龙家”和“马镦龙家”大致属于早期汉族移民,而“白龙家”则是彝族下层居民。由于这些龙家均分别归属宁谷、十二营、顶营、慕役、康佐等长官司,这些长官司就成了沟通他们与朝廷关系的唯一通道,虽然这些长官司都位卑权轻,但对明廷而言,这些长官司必不可少,否则就统辖不住各族居民。同时,这些长官司又能从明廷的驿道和卫所获利,因而才达成土司与朝廷相安无事的稳定格局。也正因为这种格局太稳定,以至于《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居然连与明廷相始终的顶营、十二营、慕役、康佐四个长官司竟然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各民族生计方式和传统文化对明代安顺地区的行政建置沿革确实发挥着不容低估的持续影响。明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的稳定,行政建置的稳定,绝不能归因于安顺地区的居民乐于汉化,更不能归因于安顺地区的地方官能力强,其实这种局面的获得是众多社会、人文及自然背景综合作用的产物。
[1] 郭声波,王旭.滇、桂、越三角地——特磨道历史地理考[J].文史,2005(1):23-72.
[2] (清)张廷玉.志第二十二·地理七[M]//明史:卷46.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3] 翟玉前,孙俊.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4] (清)张廷玉.列传第二百四·贵州土司[M]//明史:卷316.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责任编辑 杨永福)
On the Management of Anshunfu in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LUO Kang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Anshunfu in the Ming dynasty hadn’t be set until Wanli 30th (1602), but its organizations directly come from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post road to Yunnan in the Ming dynasty, its position is very important. The Ming dynasty focuses on its administration and military control. Its management shows specialties which can be seen from its setting, power structures and subsequent problems.
Anshunfu; management; basic setting
K248.73
A
1674 - 9200(2017)01 - 0017 - 07
2016 - 09 - 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土司制度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16BMZ021)阶段性成果。
罗康智,男,苗族,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黔东南州州管专家,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保护2011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生态民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