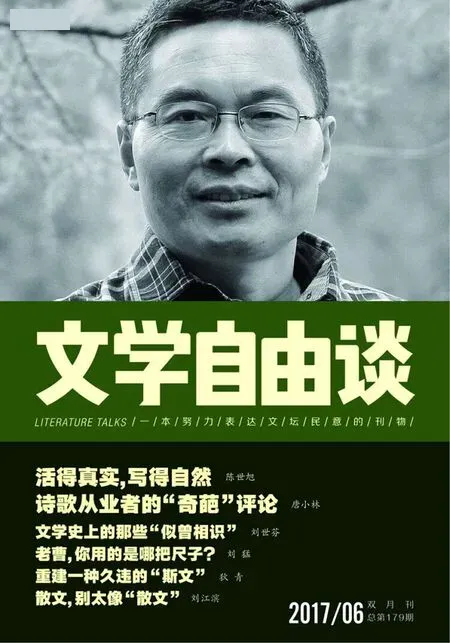朝霞初晕的“早晨”
2017-03-11周婴戈
周婴戈
朝霞初晕的“早晨”
周婴戈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1977年,国家意识到恢复高考、培养人才的紧迫感,遂在当年12月打开了进入高等院校的考场之门,冬日的阳光,在那个月温暖了大江南北。几十年过去了,对1978年2月入校、但仍属于“七七级”的“文革”后首批大学生们来说,那曾经的校园生活,恍如昨日。于是,各种记写当年校园青春的纪念文集接踵而出,如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青春回响》等。这其中,我想提一下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这本书,不必说70万字、上百幅老照片的厚重,不必说北京大学文学七七级四十余位学子的深情文字,也不必说十余位学者教授、文学宿将的厚爱,仅书中收录的四期班刊《早晨》油印杂志,已经让我们回味起曙光初现的那份红晕和诱惑了。
文学,变革前的曙光。就像《新青年》杂志和小说《狂人日记》,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北大学生走向街头时怀揣的星火,文学在1978年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的“前言”说,那个春天坐进北大文学课堂的青年,“多是煤矿、油田、田野、毛皮厂的底层青年”,他们唯一共同的精神特质就是“杀不灭的文学细胞”。“历史的转折使‘文学’再次承担起‘新的国民之精神’的使命”,“遂有油印刊物《早晨》的问世,遂有卷入当年文学论争的种种活动,遂有推动文学新潮的众多作品发表”。文学,对北大文学七七级的48同学来说,“不再是一种专业,而成了他们终身的志业”。
还是从厚达574页的书中去领受那《早晨》的光芒吧。全书分同学、老师、记录三大部分,归入“记录”部分的四期的《早晨》,呈现出最初的原始面貌,此书“后记”自称是“为了留住我们过往的记忆”。这记忆,就是全身心地“弄文学”!虽然有“中文系是培养学者的地方”“进阶要看英语和文学史的考分”等告诫,但是,文学七七级与学弟学妹们显著的不同在于,他们“充分呈现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一代有些特殊的学子的历史特征:道义感、承担勇气、对社会的关怀、创造历史的豪迈以及刻苦的思索与执著的探索”。这是对他们极准确的评价,也是他们自身无法挣脱的品格。他们就是要把文学“弄”起来,在课堂笔记之外,用他们曾经所处的“底层社会”的浸染,来把文学“弄”活。他们太熟悉社会生活那个课堂了,他们在那里浸润了十年,而以后的大学生,已无法有那种群体经历。历史使然,《早晨》不可阻挡地在东方露出霞光,文学创作的势头无可遏制地在七七级中涌现,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梁左、查建英……就这样进入甚至影响着文坛。
北大1980级文学专业的吴晓东是一位学者,他准确地评价了《早晨》的历史位置:“《早晨》不仅是纯粹的校园文学杂志,它既留有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烙印,也深深介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与行进中的历史。”今天,我们通过《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来读《早晨》的作品,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对过往历史的“介入”,仅从那些作品的名称——《流水弯弯》《夏天最后的玫瑰》《夕阳下的江水》《小罪犯》等,你就体味到作者们心绪的苍茫和“底层浸染”的苍劲;诗歌《钢的音乐》《沙枣》《夯歌》,弥漫着粉尘与泥浆,毫无半点儿未名湖的月影垂柳;已逝去的吴北玲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构想,打算写尽“陕北苦人们的那个苦”,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恐怕就是这部长篇最好的诠释,最终她为《早晨》递上了一篇短篇小说……
1956年,北大文学专业出过《红楼》学生刊物,从它的成员——激情的谢冕、单纯的温小钰、直率的林昭、坎坷的江枫……你就知道《红楼》在一年后的风暴中会有什么遭遇。《早晨》依然续写着《红楼》的单纯与直率。谢冕把激情又融进了《早晨》,成为《早晨》唯一的教师成员。后来,当谢冕从助教晋升为硕士生导师时,《早晨》的主编黄子平成了谢冕的硕士生。
《早晨》是《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一书中最鲜亮的部分,换句话说,《早晨》显现出了北大文学七七级的性格本相和历史坐标。后来,黄子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时,惊奇地发现,该馆竟然收藏有一套完整的《早晨》!他“当场傻在那里没动”。
《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为我们保存的那份苍劲的文学,正可以窥见到当年热血的流动和有血色朝霞的早晨。每个新的一天,都是从早晨开始……
《我带着辽阔的悲喜》
林馥娜著 阳光出版社
林馥娜的诗歌囊括着多姿的面孔、多元的触角和丰沛的情感,在物我转换之间寻找到优雅得体的姿态和精神的微光。在展示生活的热情和渴望之际,她的有所思内化为感性又细密的语言观照,在不紧不慢之处获得生命的喜悦和自我的觉醒。她的诗歌因为对生活范畴的把握、人物命运的深悟,从而在苍茫人世里获得了生命的律动和精神层面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