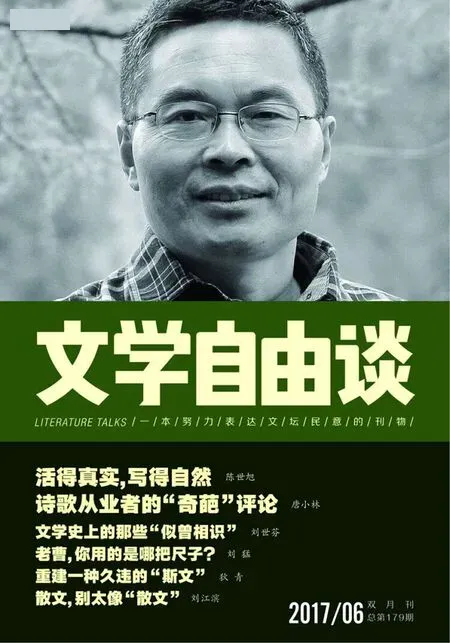写作是一种专业吗?
2017-03-11曾念长
曾念长
写作是一种专业吗?
曾念长
写作是一种专业吗?这个问题或许不算新鲜,但近些年时常被拿来讨论。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专业化倾向已是大势所趋,一切事物均以专业化为标准被重新组织起来,每个人身处复杂交织的专业体系之中,以至于社会学家吉登斯大胆断言:一旦专业失灵,将引发飓风式的社会风险。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写作是一种专业;即便原来不是一种专业,如今也必须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否则,在一个连走路和微笑都有专业可言的时代,写作又要如何立足呢?
今人所理解的专业,是一种现代产物,是知识分类不断进化的结果。倘若写作是一种专业,它就必须形成一种专门的知识体系,可以在同行内部进行标准化评估,可以向未来同行传授。按照这种要求,这个时代出现了一门“写作学”,并且建立了一整套面向写作同行的知识传播体系。这其中最具参考价值的,或许当属美国高等院校的创意写作硕士和创意写作工坊。如今,这一整套技术标准和教学系统也被引介到中国,在国内形成了写作研修热潮。不少名校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许多年轻作家鱼贯而入,脱颖而出,似乎未来文坛的中坚力量正诞生在这条知识生产的流水线上。我们讨论写作是否构成一种专业,其实和当下一拨接一拨的写作研修热有关,也是一个颇为应景的话题。
以上只是略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始终有人怀疑是否存在写作这样一种专业。怀疑者通常会列出一长串名单,用来说明许多杰出作家未曾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鲁迅弃医从文,似乎从一个医生转变为一个作家,如平常人切换电视频道这般简单。还有余华,从一名牙医华丽转身为一名作家,在外人看来似乎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可惜这些尽人皆知的案例虽然颇有看点,有时也让那些欲步其后尘者热血沸腾,但在逻辑上却是破绽百出:我们何以证明,他们不是通过自学成才步入写作这个专业的呢?
有力量的怀疑,不是来自那种模棱两可的外部猜测,而是来自众多杰出作家的自我否定和现身说法。他们声明,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标准化操作且可普及推广的写作知识。当福克纳被问及是否存在写作的秘诀时,他果断回答说没有,倘若有,那就是不停地写。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比如普鲁斯特,公然否认智力在个人写作中的有益作用,甚至全然推翻前辈作家对后世天才作家的必然影响。在他看来,一切天才从零开始。这个零,意味着一切累积性知识的消失,即便一个作家在写作上贡献出了独特智慧,也不可能被复制到其他作家身上。仅凭这一点,写作是一种专业的假设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可复制性和可累积性正是人类经验被塑造成一种专业的重要前提。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可复制的,不因接受个体的差异而发生传播变形;一切科学知识也是可累积的,呈现出线性增长的趋势。但写作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种可能会涉及一点点科学知识的手艺活儿。写作的发生因人而异,且如西绪弗斯的寓言所揭示的,时时显示出从头再来的悲剧意识。
一些作家否认写作是一种专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知识和手艺这两种写作要素的不同。知识依赖于人的智力,而手艺却存乎于人的心灵。一个人有很好的智力,掌握了大量有关写作的知识,但他能否将这些知识转化为手艺,一直是存疑的。《庄子》讲到了一则“轮扁斫轮”的典故:制造车轮的手工艺人轮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傲,连齐桓公捧读的圣人之书,也被他视为糟粕了。这是对知识的不信任,后人自然可以嘲笑轮扁的眼界之小,却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手艺人,他有看待事物的独特视角。在轮扁看来,斫轮这种手艺活儿“得之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倘若诉诸有形之法,精华早已不存了。“轮扁斫轮”的典故被陆机、黄庭坚等诗词文章大家反复引用,以此延续了一种古老的态度:在写作这个行当里,知识与手艺是不能对等转换的。
杜甫晚年作《偶题》,以诗代论总结自己一生的创作,开头两句着实惊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按照杜甫的说法,写作实乃寸心之术,精微奥妙,充满了不确定性,得失无法为外人道也,自然也就无法转化为某种通用的知识,以之指导别人的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是一种怎么都可以的活儿。在同一首诗里,杜甫又说道:“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从中可以看出,杜甫早年学诗,其实是有法可依的,自弱岁之年就已熟练于心了。这个法,就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写作,它可以讲授,又未尝不是一种专业要素呢。
从“有法”到“无法”,正是多数有成就的作家必须走过的写作进阶路线。但也不是每个作家都入得“无法”之堂奥,因此难免被“有法”所困,终其一生也走不出一个有形的天地。这是两种写作类型,也是两种写作境界。
清代吴修龄有一观点:“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吴氏所说的文与诗,并非实指文体,而是泛指实用性写作与精神性写作的区别。这可从他的后续论述中见出其真实含义:“啖饭则饱,饮酒则醉。”对于生产者来说,做饭是可以后天教练的,而酿酒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我的父亲,不善处理生活实务,这方面往往是一塌糊涂,但每逢家中酿酒,就得依赖他的自然天成的手艺。而我的母亲,懂得生活的世故,理得俗世的规矩,却是怎么也酿不出一坛好酒来的。
写作大抵如此。实用性写作可以依赖于某种有形之法,而精神性写作,光有智力和体力,未必就能奏效。关于后者,古人早有不同程度的领悟。曹丕在《论文》中说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个“气”,其实正是古典时期的精神性存在。曹丕论述了精神性写作的特殊意义,开辟了一个时代,远非孔子时代的诗教观能够涵盖得了的。孔子的诗教意在化俗,因而是可传授的,所以诞生了《诗三百》这样发行量巨大的选本性教材。但是曹丕从写作的角度看问题,发现了个体精神的差异性,不仅“不可力强而致”,而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写作是不是一种专业?我们依然无法简单做出一个判断。倘若较真,我们就得深究,哪一种写作可以授业传道,哪一种写作只能寸心感知。我们都知道,应用文写作有具体规范,尽管乏味,却可以在课堂上讲授,现学现用。各种知识性写作和思想性写作,比如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更多依赖逻辑、术语和观点,也是可以做到训练有素的。而文学写作呢,涉及人类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认知,则要复杂得多。在这个时代,文学虽然不再像古时的文章一样无所不包,但依然还是一种宽泛的存在。它的一个极限是潜入人类的精神深渊,如暗夜里的潜行,一切来自白昼的理性法则都有可能是失效的;另外一个极限则与我们的俗世生活相联,与人民同呼吸,与市场共命运,自然也就能在人类智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概念、理论和套路,与各种现实法则相勾嵌。若是前者,作家需要走出技术窄门,完成对狭隘的专业主义的超越;若是后者,作家需要重视各种已经获得世俗成功的写作之法,深耕各种技术套路。
不过,对于多数作家来说,精神性和现实性并无清晰的界限,而是相互纠缠在一起。因此,讨论写作是不是一种专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倘若真有意义,就在于我们借助这种讨论,明晰了对写作本身的某种看法,同时也增加了辨识真假写作的一点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不管在知识和手艺上是否构成一种专业,至少在职业上已经是一个庞大的行业圈子,一个利益可观的社会空间。于是,有些人混迹在这个行当里,识得些字,懂得些遣词造句的方法,就以作家自居了。他们深谙两边倒的辩证法:当有人说写作是一种专业时,他们就削尖了脑袋去上几堂写作课,加入几个协会,获得几本证书,以此加持自己的专业身份;当有人说写作不是一种专业时,他们更是增加了无知者无畏的勇气,以“功夫在诗外”为借口,充当起行业权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