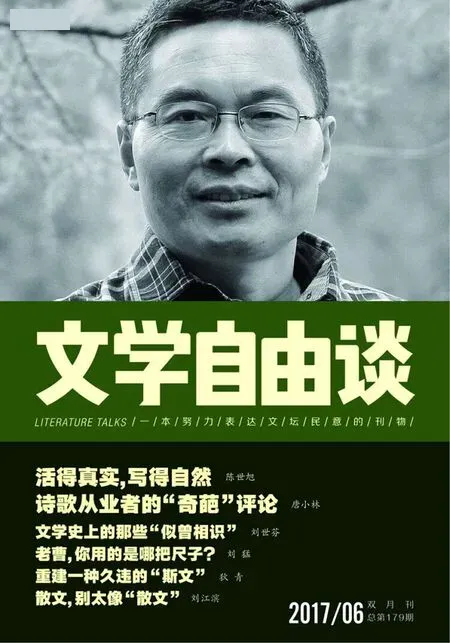周汝昌与《红楼梦》有关系吗?
2017-03-11吴营洲
吴营洲
周汝昌与《红楼梦》有关系吗?
吴营洲
“周汝昌”这个名字,已经和“当代红学”粘连在一起了,任何一位关注“红学”的人,似乎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名字。
当然,这个名字和《红楼梦》本身,或许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说或许欠妥,但也大致不差。窃以为,一个普通的《红楼梦》读者,倘若从未听说过“周汝昌”这仨字,或从未读过周汝昌的任何“红学”著述,读起《红楼梦》来,或许会更为通畅、顺遂、惬意、享受。
《一瓢谭红》(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是裴世安先生的“红学”新著,是他多年来的读红、研红心得,其中的部分文字,涉及到周汝昌。当我翻阅这部分文字时,感到很有意思,起码加深了我对周汝昌与《红楼梦》的关系的了解。
周汝昌的“与时俱进”
周汝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红学”著作,莫过于《红楼梦新证》。裴世安存有此书的三种不同版本,分别是:1953年9月棠棣出版社的“初版本”,1976年4月人民出版社的“增订本”,1985年5月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裴世安在对这三种版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稽核”“考辨”后,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三易书名‘题签’”和“两次更换‘代序’”。
“初版本”的题签,出自书法家沈尹默之手,“增订本”的“题签”则是周汝昌从其老师顾随先生的信札中摘出的,而“重印本”却又换了……
“增订本”为什么要弃掉沈尹默的题签而集顾随的字呢?裴世安分析说,“初版本”的题签,是该书责编约来的,周汝昌可能是“被动接受”;而“增订本”的“题签”者,是周汝昌的先师,“这从感情上来讲,是合情合理的,说明作者是个重感情的人”。然而,裴世安又说:“但也不排除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沈尹默1971年辞世……当年的‘身价’,与往昔和时下,皆不可同日而语。”他说:“三个时期,特定背景下,产生了三个不同的题签,从一本书的‘面相’上看,也够得上是‘与时俱进’了。”
该书还两次更换“代序”,其情形与更换“题签”相类。“初版本”的“代序”,是王耳(文怀沙)将周汝昌的一段文字抽出来,置于书前,并署上了王耳自己的名字。“重印本”则换上李希凡、蓝翎的旧文《评〈红楼梦新证〉》,也算是“代序”。
在“初版本”上,周汝昌如此写道:“没有王耳先生的无私的重视与爱护,这本书是不容易和读者见面的……首先要在此感谢王耳先生。”待到“重印本”时,周汝昌则“热诚相求”了李希凡等的文章作了“代序”。裴世安慨叹道:“个中原由,稍加梳理,直有‘说到辛酸处,双泪落君前’的感觉。”
周汝昌的“四个凡是”
周汝昌出了套《红楼梦——八十回〈石头记〉》汇校本。该书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过,译林出版社2011年8月出过,漓江出版社2009年5月、2010年1月分别出过繁体版、简体版,海燕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时名为《石头记会真》、2006年9月出版时名为《周汝昌精校八十回石头记》。
有论者称,该汇校本是周汝昌“结合自己对曹雪芹创作心灵和文化境界的理解,对抄本流传过程中复杂情况的推详考察,而作出判断”,“每一句,每一字,都是一种文化修养和心灵感悟总体水平的体现,是他六十余年研究红学而‘综互合参’的产物”;“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更‘原生态’的《红楼梦》读本”(梁归智:《红楼梦的“原生态”读本——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光明日报》2010年10月9日)。
然而,裴世安读后,颇感“沮丧”,因为他并没有读出其中的诸多“妙处”。于是,他又买来了“漓江版”的简体字本,以其为主,与周汝昌选定参与校订的十种抄本相比勘,想从中寻找“活色生香”的“原生态”,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裴世安通过对 “叚”“段”、“到”“倒”、“粧”“装”、“采”“睬”、“脏”“賍”、“弹词”“谈词”、“博”“赙”、“二”“爱”、“旷”“矌”、“汎”“讯”、“射覆”“覆射”等字词的比勘,发出慨叹:“明知‘到’‘倒’用法有别,为什么周氏偏要‘教’人混用,竟是雪芹笔下的‘原生态’么?”“把胥手们稀奇古怪的错别字,网罗起来,当作‘雪芹原笔’,这不是在发扬雪芹铸字炼句的精华,而是在给雪芹脸上抹黑。”他诘问:“请问校者,这究竟是在校《红》?甚或是在找‘原生态’?是在做学问?还是在戏弄读者,包括戏弄自己?”
裴世安是“不贤者识其小者”吗?绝对不是。裴世安挑的这些字词,都是周汝昌的“软肋”或“硬伤”;而周汝昌的“软肋”“硬伤”太多,挑不胜挑,以致都懒得再挑了。
经过半年多的比勘,裴世安摸到了一点小“窍门”,就是:周汝昌在汇校过程中,恪守的是“四个凡是”:
一曰:凡是抄本中独有的异文,必取之;二曰:凡是抄本中被点去的文字,必取之;三曰:凡是稀见的文字,必取之;四曰:凡是显眼或别致的字句,必取之。
如此断语,是有众多实例做支撑的,在此不再罗列。最后裴世安说:“至于周式‘原生态’,那只是《红》书版本校订史上的一个故事。”
其实,裴世安过于厚道了。倘若把“故事”一词易作“笑话”,或许更为贴切。
周汝昌的“真本”情结
周汝昌对《红楼梦》的情有独钟,自是众所周知的。印象里,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时,这位耄耋老人的脸上,时不时地就会泛起少女般的红晕……或许他心里清楚,没有《红楼梦》,就没有他周汝昌。
周汝昌也自称,他是“一生辛苦为芹忙”的。他平生的夙愿之一,就是汇校一本“最合乎曹雪芹原意”的《红楼梦》。在他看来,他做到了,《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便是。
众所周知,周汝昌对于《红楼梦》,是只认前八十回的,是绝对否定、厌恶后四十回的。裴世安说,“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不足议”,但,周汝昌“把自己的偏见,强加给读者,因此,不得不议上一议”。
裴世安本来“无心细察”该书,因为他相信曹雪芹写完了百廿回《红楼梦》,只是由于少量散佚,才经程、高之手补全的。因为赶上特价,他才购得周汝昌的汇校本,并“硬着头皮,稍作浏览”。不料,一翻之下,竟然生出两个“感觉”:一个是“汇校者自信心特强”——“既称‘汇校’,却不对异文、误文、漏文出‘注’出‘校’,而是以‘评点’代替‘校注’。意谓:汇校者之取舍,绝对符合雪芹原意……这种气势,让人感到自形猥獕,顿刻矮人一等”;另一个是,《红楼梦》真正的“真本”,“恐怕还在程、高那里”。
关于第二个“感觉”,裴世安举了两个例证。其中一个是,甲戌本“凡例”中,有几处“点睛”二字,皆抄成了“点晴”,这显然是常识性误抄,但周校本却咬住“晴”为“原本”,硬塞入正文。裴世安不由得质疑:“如此汇校,读者怎堪接受。”
现今人们所见到的《红楼梦》抄本,都是胥手们抄写的过录本,即或是抄手依样画葫芦,又奚知是它是一稿、二稿、三稿的文字?因此裴世安说:“所谓‘原笔’云云,也只是猜测之辞。即或果被猜中是最初的原稿,也未必能论定它是最后的定稿。否则何苦要‘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呢?古今文章,都是修改出来的。一笔挥就是罕见的。”
裴世安所言极是。咳珠唾玉、落地成钉的情况肯定有,但那恐非常态。周汝昌探寻曹雪芹“原笔”“原意”的心意固然好,但他的立足点或着眼点,疑似错了。
周汝昌的“新证”价值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究竟“证”了些什么?裴世安是这样评说的:
胡适考证《红楼梦》,至少还抓住了一个“补”字,考出“高续说”;根据曹雪芹的家世,考出“自传说”,不管怎样,还算考出点“名堂”来。可“新证”“证”了些什么呢?其重头篇幅“史事稽年”,从曹雪芹的祖宗三代,一直“稽”到雪芹出世、归天,以至“八声甘州”,五百余页,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似可视作“曹寅年谱”,剩下部分,才硬与“挂钩”,旨在“稽”明雪芹卒年。但它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的:一是卒于癸未,二是存年四十……这两个前提,失去了一个,岂不连整个“史事稽年”,都将成为“多余的话”?再看“新证”想坐实的“高续说”,除了敲打胡适等人早已敲打过的几块“断烂朝报”以外,充其量,再加上一句“高鹗这家伙”,别的什么“证”都没有端出来,更谈不上什么“新”了。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的确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它的“畅行不衰”,一是人们受到了书名的误导,二是曾被某大人物提及,三是赶上了全民“评红运动”的大潮,四是《红楼梦》爱好者的爱屋及乌……
有人称,《红楼梦新证》是“材料考证书”,而在裴世安看来,其“考证”也未必可靠。如上所引。
平心而论,《红楼梦新证》究竟与《红楼梦》、与曹雪芹有多少关系,委实难说得很。这或许跟周汝昌写的曹雪芹“传记”情形相近。我几乎读过周汝昌所有的曹雪芹“传记”,包括各种“小传”“新传”“画传”,以及“大传”(即《文采风流曹雪芹》),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这些“传记”,通篇下来,凡是写到与曹雪芹“无关”(诸如背景资料之类)的东西,总是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而写到与曹雪芹“有关”的内容时,则又语焉不详,含糊不清。
周汝昌的“荣玉”谜案
如果不是读了《一瓢谭红》,我还真没注意过周汝昌会有个“荣玉”谜案。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都会知道第五回关于秦可卿的曲文中有一句“箕裘颓堕皆从敬”,而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汝昌《八十回石头记汇校》,却明明白白地印着“箕裘颓堕皆荣玉”。
那么,这个“荣玉”是从哪里来的?是周汝昌发现了“新材料,新版本”,但他在书中并没有注明出处。
众所周知,这两个字的易换,可是非同寻常的。“箕裘颓堕皆从敬”的意思,是说“先辈的事业没有人继承”,贾府的败落是从宁国府贾敬开始的,而一易换,贾府败落的开端,则成了荣国府的贾宝玉。
易字事小,易义事大。身为《红楼梦》的研读者的裴世安,自然不能不查。可是查来查去,总是查不出究竟。周汝昌对此始终是讳莫如深,就连他数次摆印的“校订批点本”,也一直王顾左右。
然而,被周汝昌极力贬斥为“假货”的“靖本”上,偏偏就是“箕裘颓堕皆荣玉”。而据“靖本”脂批的抄录者毛国瑶称,他曾于1964年将“荣玉”这一异文函告过俞平伯、周汝昌。后来毛国瑶又撰文重提此事,周汝昌“亦未公开指谬”。据裴世安说,时至今日,周汝昌的“荣玉”二字,“依然妾身未明”。
裴世安说:“窃以为,对版本的校勘要求,该怎样,不该怎样,该信守什么,犯忌什么,比如擅增乱改,就是一大犯忌等等,作为老资格的校家,自然熟知其详。”“总之,对抄本的异文,在校勘取舍时,必得交代明白,这是我辈读者对校注者们的最低要求。”
周汝昌的“改与不改”
周汝昌对自己的著作,总是改来改去。
裴世安曾以《红楼梦新证》为例,做过一番“勘查”:该书1953年的“初版本”,是 39万字;1976年的“增订本”,是80万字;1985年的“重印本”,是77.8万字。裴世安说:“一般的增订本,较初版本有所增删,此乃常事,不足为怪。但增减篇幅若‘新证’之‘猛’、之‘骤’,委实罕见。”裴世安发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史事稽年’”,“其次,还增加了‘文物杂考’一章”。“至于重印本,抽去李、蓝的‘代序’,改写‘伤筋动骨’的‘后记’,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是‘历史的产物’。但也可视作‘与时俱进’的‘典范’。 ”
客观地说,仅就《红楼梦新证》而言,周汝昌所改的远远不止这些。他的“增删”“剪裁”“挖改”处,几可说比比皆是。当然,周汝昌所不断改写的,也远远不是这一本书。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倘若谁有兴趣,不妨把周汝昌前后出版的五六本“曹雪芹传”依次摆开,细细对照,便会发现他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错误。如此看来,周汝昌给人一个感觉,当是“生命不息,‘改稿’不止”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曹雪芹当是迥然有别的。因为种种迹象昭示,曹雪芹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没有再写再改过他的啼血之作《红楼梦》的。
当然,改有改的道理,不改有不改的道理,说不上谁好谁不好。可是,倘若因此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周汝昌是个“追求完善”“不断修正自己”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据我所知,有些东西,周汝昌则是绝对不肯更改的。诸如他的“脂砚即湘云”说,他不但不改,反而一再申明:“我平生最得意、最精彩的考证,就是考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的脂砚斋即史湘云。”(周汝昌:《谁知脂砚是湘云》,江苏人民出版社)
这真真令人无语了。
周汝昌当初称“脂砚即湘云”时,“红学”尚处于“初级阶段”,人们掌握的资料也有限,有此一“悟”,倒也难能可贵,或可说是一个“独见”。然而,随着红学史料的不断被发现,随着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人们对《红楼梦》的认识不断提高,连普通读者都知道,现实是现实,小说是小说,“脂砚”与“湘云”压根儿就是不能互换的。在这种情形下,以周汝昌的学识,难道真就不知道自己错了吗?我觉得,他是知道的,甚至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但他“最初的时候”——即他刚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没有改,不但没有改,反而还为了自圆其说,去用一个假说来掩盖另一个假说,或者说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其结果呢,到后来恐怕他是想改都没了回头的可能!——那个“谎”扯得太大了,没法改了!一改,自己毕生所建的所谓“红学大厦”,或他的“红学泰斗”这一封号等等就都坍塌了!
周汝昌的“戏补”曹诗
周汝昌“戏补”曹诗一事,本是当代红学界乃至当代学界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公案”,无须旧话重提,但是我认为裴世安对此事的点评委实切中肯綮,故而简述于此。
1971年底,社会上突然传出消息,说发现了曹雪芹的两句“佚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此事一经传开,顿时轰动了整个“红”坛。有说真的,有说假的。双方唇枪舌剑,势若水火。最最主真者,当属吴世昌。
该“佚诗”是从吴恩裕手里传出来的,吴恩裕又是从周汝昌那里得到的。于是吴恩裕便致函周汝昌想问个究竟,周汝昌于1972年1月14日回复道:该诗“系人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
为此事,胡文彬、周雷还特意造访过周汝昌。周汝昌言称,“佚诗”是一个陌生人送来的,他当即就记在了自己当天的日记上。
有日记为证,且又言之凿凿,胡文彬、周雷信了这话,认为周汝昌当时没有必要编故事。
正当笔头官司如火如荼地打了八年之后的1979年,周汝昌突然撰文称:“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并以“虚玄口吻”,公开站出来把这个“时人拟补”的“弃儿”领了回去,称这首“佚诗”只是他的戏笔。
一时间,论辩双方不免有点尴尬。
没想到,“主真”的吴世昌不干了。这也太丢面子了。于是动了肝火,说周汝昌是在“冒领”,并说以你周汝昌的才学,断断作不出这样的诗。而周汝昌说,他不但作得出来,而且当时还一口气作了三首呢。更更气人的是,周汝昌还说,“流传”出去的那首“唾壶崩剥慨当慷”,则是三首中最次的……
有人说,吴世昌的“一世英名”,就生生地毁在了周汝昌手里。也有人说,吴世昌是被活活气死的。
在这场有关“佚诗”真伪大论战中,梅节是“打假”主将,并以完胜收官。
然而,一如裴世安在书中所写:“应该说,事情已可了结。谁知周(汝昌)也不是好侍候的,特别让他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梅节那句‘不是疑案,是骗案’的话。于是,来了个反面文章正面做……把曾经信以为真的一概人等 (包括二吴以至一般读者如上当者我),着实‘奚落’了一通:有人看错了。脸上似乎下不来,种种胡缠,不过是徒贻口实,我是不想‘奚落’人的,忠厚之道可以使之停止‘闹左性’。”可是周汝昌还是“奚落”了那位“不仅自己受骗,还叫别人上当的厚道学人”吴恩裕:“心太切,意太痴,天真,识别力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的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硬伤。每念及此,不胜嗟惜。”
裴世安为此慨叹道:“始作俑者不过是给低智商者们开了个‘玩笑’,上当者却偏要‘胡缠’,难怪周公子要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裴世安的《一瓢谭红》,谈的主要是《红楼梦》,或是《红楼梦》的“版本”,而谈及周汝昌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然而“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能稍微“读懂”的,也仅仅是这一小部分,所以才有了如上的文字。
然而我清楚,我的这点文字,仅就“裴世安笔下的周汝昌”这一话题而言,恐也不过十之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