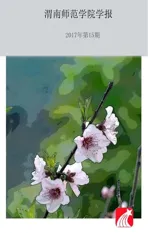我的鲁迅研究
2017-03-11段国超
段 国 超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99)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我的鲁迅研究
段 国 超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99)
我出生在大别山南麓一个特别贫困的农民家庭,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上学。我阅读鲁迅作品,知道鲁迅这个人名是1953年上初中、所有课程都有统一教材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初中语文课本有鲁迅小说《一件小事》《社戏》《孔乙己》,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杂文《“友邦惊诧”论》等。从初中到高中,大约在语文课本上接触鲁迅作品不到15篇,那个时候的语文老师对鲁迅和鲁迅作品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1959年上大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单讲鲁迅就有上下两章,是把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来讲的,是重点中的重点。我的第一个现代文学老师陈楚桥先生上北大时是鲁迅的学生。他讲鲁迅作品,常讲这作品是怎么来的,鲁迅为何写它,介绍鲁迅写这作品时的生活经历和写这作品时的心态与佚闻,把作品的形成和作者当时的为人结合起来讲,讲得入情入理,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不仅让鲁迅的作品印进了我的脑海,也把鲁迅这个人留在我的心里。我当时的古代文学老师曹冷泉教授,在上海时曾拜访过鲁迅,并请鲁迅向当时上海的报纸《申报》推介发表自己的作品。他在课堂上也常讲到鲁迅的为人和为文,同样加深了我对鲁迅为人与为文的崇敬。这使我较大量地阅读鲁迅作品,诸如《呐喊》《彷徨》和多本杂文集。
有意思的是,由于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读点鲁迅”,此时我开始启动了想“写点鲁迅”的内心秘密。1962年底,我把鲁迅关于读书的一些言论摘录整理了15条,标题就叫《鲁迅语录》,投寄《西安日报》,《西安日报》在1963年1月15日居然全部发表了,并且还通知我去报社财务科领了3元钱的稿费。我把这3元钱的稿费从南四府街的报社取出后,在钟楼的一家小餐馆吃了一碗擀面条,余下的钱就在钟楼书店买了几本鲁迅的杂文集,尔后就一路唱着、跳着,步行回到了我在南郊吴家坟的陕西师大学生宿舍。虽然有十几里路,竟没有一点倦意。
《鲁迅语录》发表后,还居然起到了作用。196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渭南师范学校工作。在渭南新华书店,我见这15条鲁迅语录被完整地用隶字装裱成15幅书法作品,张挂在购书大厅的四面墙壁上,显得十分庄严、美观而有意义。但这“鲁迅语录”毕竟是鲁迅语录,它不是我写的文章。我“写点鲁迅”是从“文革”开始的。“文革”是个“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毛主席的提倡鲁迅已被神化,常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在这个时期,我由“读点鲁迅”步入“写点鲁迅”。我写了不少诸如《“将军”下台,还要批判其“主义”——读鲁迅杂文〈“有名无实”的反驳〉》《“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读鲁迅杂文〈并非闲话〉》《“总之是信不得”——读鲁迅杂文〈赌咒〉》《要记取从前驱者变为复古派的教训——读鲁迅几篇杂文的札记》和《“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读鲁迅杂文〈关于妇女解放〉的体会》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大约有20多篇吧,基本上都发表在《陕西日报》《西安日报》《陕西师大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和《陕西教育》《群众艺术》等报纸杂志上。这类文章我写得很顺手,报纸杂志也很欢迎,我以为这是党的事业需要,当时内心感到高兴。现在想起来,写这种“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章,甚觉无聊,亦感愧疚。写这类文章,即使写得再多,对鲁迅和鲁迅作品,也并非真正地理解,只说明是一种曲解,甚而是一种歧途。
那么,我真正“写点鲁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1979年,“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年我写了《“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鲁迅论小说的社会作用》,这篇文章虽说是针对《上海文学》这年所发《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写的,但我至今认为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此文在《宝鸡师范学院学报》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鲁迅研究》复印,其观点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学术界较有影响。另外,在《四川文学》同年第6期上还发表了《浅谈人物的肖像描写——读鲁迅小说札记》一文,这篇文章亦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鲁迅研究》复印。老学者西北大学的单演义教授见此复印文章后专门给我来信,说一年内鲁研文章能被中国人大报刊资料复印两篇,其起点成绩突出,特向我表示祝贺。再加上这一年刚复刊不久的《延河》第1期又发表了我《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一文,三篇文章一起,让我多少引起了陕西鲁研界特别是文艺界一些人的注意。这一年陕西作协在“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不久,即吸收我为第一批会员。自此省作协、省文联、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有什么文艺活动特别是文艺理论研讨活动,都通知我参加,让我在别人眼里显得非常活跃。这在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人以后的言论中可以看到。西北大学单演义教授,陕西师大刁汝钧教授,还邀约我同他们一起筹建了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陕西省鲁迅研究学会。1979年,我在报刊发表各类大小文章18篇,其中关于鲁迅的有5篇;1980年,我在报刊发表各类大小文章19篇,其中写及鲁迅的有4篇。省鲁研会老会长单演义教授在省鲁研会和北京的全国鲁研会的《会员通讯》中写文章予以表扬。此时我认为,所谓学术研究,就是探索人应知而未知的东西,就是追求有价值的新与异,写别人不知道的事,说别人未说过的话。
“文革”结束后,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敢于说真话了。这让我想起了两件事:一是我湖北黄冈乡党胡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在上海的那段师徒与战友的关系,现在可以讲了;二是鲁迅原配朱安与鲁迅的那段婚姻关系,时间久了,已被世人遗忘,现在可以公之于世了。这应是当时鲁迅研究的任务,也是关于鲁迅研究的两大块文章。这两大块文章,在我心中郁积已久,我想写了。于是我开始着手准备:一是查找有关文字资料;二是调查采访。文字资料很少,调查采访主要靠书信。关于胡风,左联老作家吴奚如、胡风夫人梅志及女儿张晓风等,给我提供的资料最多,仅书信就有20多封,另外还给我提供了不少调查研究的线索。关于朱安,绍兴的谢德铣、裘士雄、张能耿、陈文焕,长春的蒋锡金,北京的周丰一、周海婴、吕福堂、荣太之,天津的李霁野,杭州的黄源、俞芳、孙席珍,广州的廖子东,西安的单演义等,我给他们去信不下几十封,他们给我的复信也不下几十封。在与他们联系过程中,关于文章怎么写,一些老专家、老学者帮我出主意,我自己也不断琢磨着。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我的写作提纲也基本构思好了。
《鲁迅与胡风》,1979年1月就写出来了,此文写出了鲁迅与胡风在上海时那段战友与师徒关系,但这所写是禁区,无处发表。寄了多处,都被退回来了,都附信说“此稿目前不宜发表”。1980年9月底中发80年76号文件正式在党内传达,宣布在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但因留有尾巴,认为胡风文艺思想还是有问题,对于这篇稿,大小刊物还是心有余悸,不愿发表。1981年黑龙江《绥化师专学报》第1期将此文刊出,但因刊物级别较低,又是内刊,未产生影响。1981年6月,西安召开“西安地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携带这篇论文和已发表过的《“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鲁迅论小说的社会作用》参加了大会。一天下午饭后,来西安止园饭店参加大会的李何林先生叫我去他的住室,怀里抱着一根拐杖,手里拿着我的这篇《鲁迅与胡风》打印稿对我说:“你这篇稿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说:“李老,没有刊物能发表呀!”他说:“那是因为他们害怕,中央已经为胡风平反了,但是还不彻底!这样吧,我拿回去先发在我们的刊物上。”于是,这年的第6期《鲁迅研究动态》的头一篇就是这篇长达万余字的论文了。这件事王富仁先生知道,他2009年在接受一个专题片编采人员采访时说:“在中国,段国超教授是最先研究鲁迅与胡风关系的学者。”他的印象大概是从这儿来的吧!因为他和阎庆生、李鲁歌、余宗琪三位当时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李何林、曹庆华、戈宝权、孙席珍、蒋锡金和周海婴等先生的生活就是由他们四位专门负责。他们四位整天都在这些老先生身边。至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同,那是胡风个性化的思想认识,属学术问题,不能归结为反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个问题后来政界、思想界、学术界的认识也渐趋统一,胡风问题可以说已全部解决。《鲁迅与胡风》一文,后来在湖南《求索》杂志改题重新发表,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鲁迅研究》全文转载,北京《文摘报》亦摘编。在1981年4月被评为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鲁迅与朱安》一文,近两万字,于1982年7月底写出,写出后也因为涉及禁区,不好发表。我将打印稿寄云南、贵州几家师专学报,以为接近西南边陲,学报稿源不足,容易发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一家师专学报回复说:“你所写事实很新鲜,我们已寄北京有关专家审读。但我们认为,不论专家审读意见如何,此类稿件内容于鲁迅形象有损,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当宜共同为读者负责,以都不犯错误为好!请你谅解。”此稿“于鲁迅形象有损”吗?我以为没有。如是我广为散发,凡我知道的有关学术刊物我都寄上,凡我参加的有关学术会议我都带上。我当时这样想:不论刊物大小,只要有一家愿发,我就满意了,只要有一人赞赏,我就高兴了。想不到我这样做,收效果然很好。1982年10月我携带此文参加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鲁迅学术研讨会,此文获得了一片赞扬声,青海民院一教授在闭幕式上讲话,说这次学术会议有两篇学术论文他最欣赏,其中一篇即《鲁迅与朱安》。回校后不久,虽说连续收到几家大学学报退稿,声明不用,或虽未退稿,而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保存”,但却收到北京出版社一个叫李志强的编辑先生的来信,说《鲁迅与朱安》一稿,他们出版社出版的由王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即将刊用,嘱“勿要另寄他刊”。随之又收到时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的田本相教授来信,正式通知《鲁迅与朱安》一稿将正式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说这期刊物由他组编。《鲁迅与朱安》的结局使我大为兴奋,觉得总算遇到“识马”之人了。这篇文章资料比较充分,第一次比较全面深入地叙述了朱安一生作为悲剧人物与鲁迅的不幸婚姻。我在文中为朱安鸣不平,点名批评了北京鲁博不顾事实,把鲁迅故居内当年朱安居住的卧室挂牌为“鲁迅藏书室”,企图把朱安这个历史人物从鲁迅故居彻底抹掉的错误做法。此文引起了北京鲁博领导和专家教授的重视,不久即纠正了以上的错误做法,重新在朱安卧室门上挂上了“朱安卧室”的门牌,使之回归到当年历史的原貌。西北大学中文系周健教授来信说,此文发表后,北京有人给她来信,打听段国超是何许人,可见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还小有影响的。此文不仅将鲁迅与朱安这早已被人遗忘的婚姻又重新公之于世,而且也在写法上提供了一个实例。北京现代文学馆《丛刊》编辑部为纪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30周年特编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精编·现代资料卷》,把《鲁迅与朱安》一文也作为精品编选进去了(1985年,这篇文章亦曾获得陕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从现在的情况看,《鲁迅与朱安》一文是我这一生所写颇有些影响的论文之一。
以《鲁迅与朱安》作为领头,此后我以鲁迅家世作为一个大题目,花了近10年时间,有计划地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组论文,共计12篇,诸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鲁迅的母亲鲁瑞》等。这些文章作为人物专论,写得比较早,都曾在《人文杂志》《鲁迅研究资料》《谱牒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其中有6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而且还有多篇被《文摘报》《报刊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各类文摘报刊摘发。反响似乎不错,以至笔者被著名学者马蹄疾在他的书中戏称为“家世学者”。到1991年,我接受朋友建议,请著名老学者彭定安、廖子东作序,将这12篇文章按统一体例及其内在联系,编成一本书,共计18万余字,取名为《鲁迅家世》,交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在学术界特别是鲁研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信州大学教授松冈俊裕,在自己的著作《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考》中,对其作了全面评介,而且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其引用多达20余处。通过北京鲁博的介绍,自此还与作者建立了长期联系。为了学术交流,就鲁迅研究深入交换意见,2006年9月5日,其还专门偕夫人来访。国内学者对《鲁迅家世》的评价也很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西北大学教授张华先生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评论说:“《鲁迅家世》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在鲁迅研究史上有它显著的地位,筚路蓝缕,开拓者的功绩是不可没的。”著名老学者、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彭定安先生其万余字的序言,对《鲁迅家世》的内容、特点和出版意图作了较详细的评介。此序后来《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鲁迅研究》都作了全文转载或复印。其他学者如纪维周、张学义、吴志坚等亦在报刊发表评论,予以充分肯定。香港著名学者楼子春、台湾著名学者尹雪曼托朋友在北京书店购买(缺售,最后找到我处,我均签名相送)。应读者要求,教育科学出版社在1998年提出再版,我又借机作了修订。增补了《兄弟“怡怡”,“参商”者何?——鲁迅、周作人关系考述》《“大哥的话,我永远铭记”——周建人与鲁迅》《“真爱”的执著追求者——许广平与鲁迅》3篇文章。共计15篇,30余万字,较初版多了10万余字。著名学者、鲁迅研究大家彭定安来信说:“祝贺您的成功。这修订本内容较前丰富多了,装帧印刷亦佳。”著名作家李若冰来信说:“这本书是我目前看到研究鲁迅家世唯一比较完整的一本书。我对您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贺!”也许这修订本比初版本质量真的有所提高吧,著名学者李继凯、韩梅村、马为华、贺智利、方忠铭、徐明华等连续在《鲁迅研究月刊》《绍兴鲁迅研究》《汉中师院学报》《文化艺术周报》发表评论,予以褒奖。李继凯说:“这是心血所化的‘鲁学’生命。”徐明华说:“这是鲁迅家世研究的新的开拓。”贺智利说:“这是鲁迅家世研究的第一本著作,填补了鲁迅研究的一个空白。”辽宁师范大学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吉鹏在其主编的《鲁迅生平研究史》一书中,用9千余字对《鲁迅家世》修订版开专节评介,说:“鲁迅作为‘社会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周围人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家人,对他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研究需要使学界开始试图改变鲁迅家世研究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在这方面,做出最大成绩的,本时期无疑是段国超。”
《鲁迅家世》出版以后,鲁研界一些朋友如马蹄疾、谢德铣等都曾来信问我,你把关于鲁迅家世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很好!你其他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怎么办?是否也要编成一本书或两本书?于是,2002年我又将其他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编选了一本《鲁迅论稿》(未选入的列出目录索引附在书后),交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名《鲁迅论稿》是王富仁先生写序时定的。这本书都是我在学习鲁迅著作或研究鲁迅生平往事时的一些想法。全书内容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鲁迅与某些现代作家、诗人的交往记载或某些当代作家、诗人与鲁迅的师承关系。第二部分是我学习鲁迅著作的一些零星体会。这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特别是第一部分是这本书的中心内容。第三部分是有关鲁迅的一些散文、读书札记。这部分文章较杂,但内容较新,多是别人没写过的,我以为还有它的某些特别之处,有其出版价值。第四部分,只是一篇文章,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迅研究脉络的一个清理,一个总结,一个述评。著名学者阎庆生教授在他的评论中说它“既切中要害,又建以嘉言”。这篇文章被《文摘报》摘转,亦被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鲁迅研究》转载,还收到了一些读者和专家表示认同的来信,为社会所注重,也可以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书30多篇文章,内有7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鲁迅研究》复印,还有多篇被文摘类报刊摘转。书出版后,书内有些文章曾被其他专书选编,如《鲁迅、周作人“失和”原因探析》即被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周氏兄弟》编入,《鲁迅和胡风》即被陈漱渝、姜异新主编的《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一书编入。这本书的文章是我从90多篇文章中选出的,其质量我本人自感还过得去。当然,我在鲁研界是个小兵,水平有限,这些“选文”的错讹和疏漏也定然不会少。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序言是为鲁迅研究举旗、挂帅、领路的鲁迅研究大家王富仁先生写的,其序长二万七千多字,第一次专论了“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为《学术月刊》《新华文摘》等多家大刊登载,影响很大,让《鲁迅论稿》这本小书借光添彩。再,这本小书的附录收有青年学者张学义先生《段国超先生的鲁迅研究》一文,也为这本小书《鲁迅论稿》加重了分量,这也是我应该表示感谢的。
我在学校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还为学生开设了选修课《鲁迅研究》。为满足教学需要,2004年我将《鲁迅家世》作了第二次修订,算是第三版,交出版社出版。附录里增加了阎庆生、宋琦二先生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的为《鲁迅论稿》写的评论,又将附录中《鲁迅家世研究资料索引》从1989年延续到2003年。全书字数从第二版的28万字增至34万余字,书名改为《鲁迅家世研究》,印数两千。出版后,亦很快销售一空。
我从2002年元月起退休。这之前,关于鲁迅,我写大小文章100余篇,其中有15篇被其他图书、专集所收录,有13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另出书4种,只是其中《鲁迅论稿》的整理出版和《鲁迅家世》二次修订改名《鲁迅家世研究》出版,是我退休以后的事情。这两种书出版以后,我想集中力量写《杜鹏程评传》,不再写鲁迅了。但还是写了几篇,如《关于鲁迅研究的几点想法》《党家斌与鲁迅》《智者的眼光——评介李何林先生对“普及鲁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等,发表以后在学术界的反应比较好。这几篇文章,以后《鲁迅论稿》如有修订再版的可能,我将把它收进去。
以上是我几十年来研究鲁迅的大致情况。有人说我是鲁迅研究专家,按这成绩,我是算不得的。“鲁迅学”是显学,在我国学术界,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较之于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人员,其阵势十分庞大。而我在这庞大队伍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名小兵。再说,我也不曾专门研究鲁迅,我的兴趣爱好较多,古代的司马迁、苏轼,现当代的吴奚如、杜鹏程以及文学理论、文艺批评,甚至姓氏文化,我都下了不少功夫,出版有《文艺论稿》《序跋集》和《南窗灯下集》《姓氏文化研究》以及《常用写作词语类编辞典》(主编)、《史记人物大辞典》(主编之一)等学术著作和工具书。虽然我也想在鲁迅研究上多做一些事情,如曾计划写《〈故事新编〉研究》《鲁迅与帮工》《鲁迅与教育》三本小书,资料日积月累,收集不少,但《〈故事新编〉研究》,仅只写了一篇《〈铸剑〉论析》(被人大复印报书资料《鲁迅研究》1992年第一期全文转载)就放下来了;其他两本竟未着一字。都是因为忙,不是“命题作文”,没有被人催要就被拖下来了。
当然,不论成绩大小,我毕竟搞过鲁迅研究,而且还搞了几十年。那么,我为什么要搞鲁迅研究呢?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是想以文学改造当时的国民劣根性,诸如保守、封闭、愚昧、落后以及妄自尊大而又妥协媚外,乃至像阿Q那样满足于“精神胜利”等等,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心理的体现。当然,其中也混合有千百年来农民小生产者的弱点——狭隘、自私、冷漠、忍辱等等。鲁迅曾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颇有点“以文学救国”的意思。可惜,鲁迅英年早逝,加上文学自身的力量有限,他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联想到现在,其国民劣根性远甚于鲁迅当年,如“吃、喝、玩、乐、抽,坑、蒙、拐、骗、偷”等社会弊病,以及上上下下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触目惊心。如何能改变消除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呢?鲁迅“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其实现在的文艺也没有失去这样的作用。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精神就是鲁迅精神,我们现在要继承、发扬鲁迅精神,传承鲁迅精神,用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提高我们全民族素质,如果不研究鲁迅和鲁迅著作怎么行?我是一名人民教师,我想借鲁迅精神,或者说通过学习鲁迅和鲁迅作品来宣讲鲁迅精神,为国家培养人才,教育广大青年,用以改变当代的国民劣根性,这即是我学习鲁迅和研究鲁迅的根本动机和目的。当然,我对鲁迅的热爱和崇敬以及出于工作的需要,我必须也应该讲好以鲁迅为开山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这也同样是我长期搞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我研究鲁迅是出于一种革命的功利目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遗憾的是,由于我生性愚笨,杂事缠绕,教学工作繁忙,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未能在鲁迅研究上做出大的成绩。我今年近八旬,身虽多病,但如天假我以时日、健康,我对鲁迅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是决不会止步的。
【责任编辑 贺 晴】
段国超(1940—),男,湖北罗田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批评和鲁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