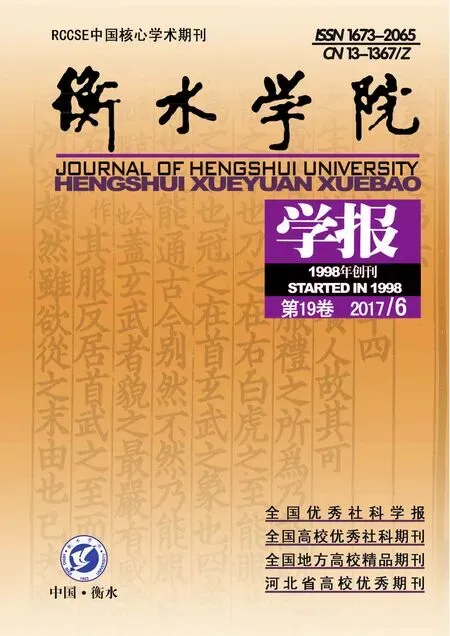杨雄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法言》为中心
2017-03-11宋冬梅
宋冬梅
杨雄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法言》为中心
宋冬梅
(中国孔子研究院 学术研究部,山东 曲阜 273100)
杨雄以孟子的后继者自居,仿效孟子辟杨拒墨,对西汉后期兴起的诸子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诸子学说和儒家学说是不相容的,如果任由诸子学说发展而不加以制止,必定会使人不明是非,偏离正道。杨雄论人性,试图调和孟、荀之说,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认为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方面因素,这一观点能很好地解决为什么社会上有善人和恶人以及一个人有时具有善念和善行,有时又具有恶念和恶行,这无疑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发展。杨雄的中和思想与孔孟的“中和”“中道”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认为“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他所推崇的“中和之道”,就是以仁政为核心的中和政治,赋予中和思想的实践色彩,即君主要想贯彻中和之道,就必须付诸实践。
杨雄;《法言》;孟子思想;人性论;中和思想
杨雄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一生著作颇丰。他少而好赋,前期作了大量辞赋讥讽时政,然其结果不尽人意,顾辍而不复,并将其归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一类;由此,杨雄的著述开始转向以哲学为主,效法《易》作《太玄》,效法《论语》而作《法言》,通过这两本著作,建立起了以维护圣人之道为出发点,以儒家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仿效孟子,力辟异端,维护正统,继承与发展了孟子思想,对我国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孟子生活的时代,天下纷乱,战争频起,各诸侯国为了扩张势力,保存发展自己,重用纵横家策士和法家人物,儒家学说因讲仁义,施仁政,反对战争,不被各诸侯采用。面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的局面,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杨墨之道进行了批判,他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含人,人将相食。吾为惧此,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
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孟子是为维护孔子之道而辟杨拒墨的重要人物。他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的,他希望自己也成为孔子那样的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杨墨之说是邪说,误国误民,如果不加以制止,孔子思想就无法发扬光大。他认为“春秋无义战”,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认为用武力统一中国根本行不通,统治者要想有效地统治臣民就应该施仁政,重视道德教化作用,而那个时代的特征则决定了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不能实现,统治者对法、墨等家的推崇,使孟子理想中的先王之治无法实现,这也决定了其王道思想较之孔子更加激进,他从儒家纲常伦理入手对杨墨之说进行了严厉抨击,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至西汉,杨雄以孟子的后继者自居,仿效孟子辟杨拒墨,对西汉后期兴起的诸子学进行了批判。他和孟子一样,认为诸子学说和儒家学说是不相容的,如果任由诸子学说发展而不加以制止,必定会使人不明是非,偏离正道。在诸子百家中,杨雄最推崇孔子,他把孔子之道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说: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将复驾其所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法言·学行》)
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曰:子户乎?曰:户哉!户哉!吾独有不户者矣?(《法言·吾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
杨雄把孟子、荀子也置于诸子之上,在他看来,只有孟子才能算是与孔子之道完全一致的圣人:
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法言·君子》)
杨雄虽然受道家影响,但对其评价褒贬参半,对老子并不是完全肯定: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
对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的学说,杨雄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说:
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法言·五百》)
在诸子百家中,他对法家的批评更是不吝笔墨:
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则狐狸、蝼蚓不膢腊也与?或曰:“刀不利,笔不铦,而独加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则秦尚矣! ”(《法言·问道》)
或曰:“申、韩之法非法与?”曰:“法者,谓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韩!如申、韩!”
申、韩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法言·问道》)
或问:“人有倚孔子之墙,弦郑、卫之声,诵韩、庄之书,则引诸门乎?”曰:“在夷貊则引之,倚门墙则麾之。”(《法言·修身》)
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法言·问明》)
杨雄认为,申、韩之术专任法,忽视德化,最不仁义,如果任其畅行,儒家的礼义廉耻、纲常伦理就会受其影响,所以崇儒尊孟,维护儒家道德,就必须“倚门墙则麾之”(《法言·修身》)。
孟子批判诸子围绕着儒家的纲常伦理来进行,杨雄对诸子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但他又认为:“吾见诸子之小礼乐也,不见圣人之小礼乐也。”(《法言·问道》)可见,杨雄认为圣人和诸子的根本区别是否“小礼乐”,这又是对孟子批判诸子的发展,也对后世儒家“排佛老”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揭开了后世探讨“人性”的序幕。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造成以后不同的是后期的“习”,然而他的“人性”说是没有善恶之分的。继孔子之后,关于“人性”的讨论成为一个焦点,主要代表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在人性论上,孟子主张“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其本性都是善的,这些成分被称为“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人们加强自我修养,则可将“四端”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凡是圣人都能把“四德”发展到最完美;其更令人惊奇的主张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对于人性善的特点,孟子认为人的天资是善良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是不言而喻的,即“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人的本性向善,就像自然的水向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但就自然的水来说,如果条件改变,将它拍打,水就能飞溅起来高过额头;如果再加压,迫使它倒行,则能使它流上山岗。像这样,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于水来说,只是形势迫使它如此。同样的,一定条件下,人也可以迫使他做不善之事,其本性的改变,也像自然的水一样受到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为了避免人的“为不善”,孟子主张人们要不断地学习,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即主张通过后天学习找回迷失的善性。
至杨雄论人性,试图调和孟、荀之说,他既不主张“性善论”,也不主张“性恶论”,而是主张“人之性,善恶混”。他说: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欤?(《法言·修身》)
在这里,杨雄论人性,讲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之性善恶相混,二是“适善恶之马”的气。关于“混”,李轨注:“混,杂也。荀子以为人性恶,孟子以为人性善,而杨子以为人性杂。”(李轨《扬子法言注》)也就是说,杨雄的“善恶混”,是指人性绝不是单一的善或恶,而是善恶相混,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方面因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善的人,也没有绝对恶的人。有关杨雄人性论的思想来源,学术界更多地认为是对孟子和荀子人性论思想的调和,其中以司马光的评述最具代表性:
孟子以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诱之也。荀子以为人性恶,其善者,圣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遗其本实。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犹阴之与阳也……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者也,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于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于田也。荀子以为争夺残贼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师法、礼义正之,则悖乱而不治,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爱、羞恶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于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于田也。故杨子以为人之性善恶混。混者,善恶杂处于心之谓也,顾人所择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斯理也,岂不晓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谓长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谓去恶者也。杨子则兼之矣。[1]
关于杨雄所讲的“气”,以上没有说明,学术界对其探讨甚多,蔡元培曾感叹:“杨雄之学说,以性论为最善,而于性中潜力所由以发动之气,未尝说明其性质,是其性论之缺点也”[2]。
笔者认为,杨雄的所谓“气”是引导善恶的一匹马,受孟子思想的影响。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赵岐解释“志”和“气”,说:“志,心所念虑也。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赵岐《孟子正义》)也就是说,外在的喜怒哀乐的“气”是受内在意识的“志”支配的,即“言志所向,气随之”(《孟子正义》)。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主体内在的意向性在人的道德修养中的引导作用,杨雄接续孟子,也讲“意志”对“气”的引导作用,说:
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法言·修身》)
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法言·修身》)
鸟兽,触其情者也,众人则异乎!贤人则异众人矣,圣人则异贤人矣。礼义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法言·学行》)
关于养气和实践,根据其人性论,杨雄强调学习和修性的重要性:
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况习是之胜非乎?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法言·学行》)
杨雄认为,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修性的目的,学习善的东西,可以抑制恶的因素;但是学习坏的东西,则可能使性中本有的善因素减少,应当警惕。在具体的修性方法上,杨雄有“取四重,去四轻”之说:
或问:“何如斯谓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轻,则可谓之人。”曰:“何谓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敢问四轻。”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法言·修身》)
杨雄所谓的“四重”与“四轻”是指言语、行为、外貌和嗜好等,与德行相关的外在方面。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杨雄虽然强调“志”这个内因的作用,但在修性方法上,他却是偏重“言,行,貌,好”等外在的因素是否符合道德礼法。在这点上,杨雄与孟子的主内修养的观点不同。
综上所述,杨雄的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有一致之处,即都承认人生来就具有的某一种特质,同时又强调后天的作用对人性实现的影响,而且孟、杨二者的人性论是一种平等论。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杨雄认为:“申韩庄周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法言·问道》)意思说,不管性善,还是善恶相混,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或者君子。但是孟子的性善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现实社会中的性恶又是从何而生?而杨雄的人性善恶相混论,则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方面因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善的人,也没有绝对恶的人,这无疑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发展。
三
儒家的中和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已经存在。中和思想在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哲学,更为注重中和思想。中和,在《礼记·中庸》中释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孔子创立儒家,在继承前人“尚中”“尚和”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为儒家的中和哲学,把神秘化政治性的“执中”改造成主体性理性化的“用中”。孟子的“中和”论吸取了孔子的中和思想。但他论“中和”和孔子论“中和”明显不同,孟子论“中和”并未直言“中庸”,而是提倡“中道”,其中和思想贯穿于思想体系中,《孟子》一书中三次谈到“中道”:首先,孟子言“中道”,出现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他认为君子教导别人正如教人射术,张满弓而不发箭,只做出跃跃欲试的状态来加以引导,能在恰到好处的中道上站立指导别人,这样,学习的人就能紧紧追随。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孟子的“中道”不仅要求有思想上的意识,更要有实践上的体验,其“中道”思想是内在和外在的统一,通过外在的不断努力来提升内在的道德境界。其次,孟子言“中道”,有两处出现在他对孔子相关言论的阐发:“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在《论语》中,孔子原话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在这里,孟子用“中道”替换了“中行”,显然,在他看来,“中道”与“中行”意义一样,两者都彰显了儒家的中和思想,但是孟子在这里做替换,更是为了突出“中道”。他认为“中道”精神体现着圣人的理想品质,所以说他关于中的思想更注重“道”。
孟子的“中道”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这些意思,其精神充斥整个思想体系,他还对偏离中道的学说给予批评。他认为杨、墨二者之所以是异端邪说,就是其偏离了儒家的核心思想,背离了儒家的中和之道。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杨朱主张为我,即使拔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他都不肯干;墨翟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有利,即使摩秃头顶,擦破脚跟,都要去做。子莫持中间态度,持中间态度就接近正确了。但是持中间态度而没有变通,也还是执着在一点上。执着于一点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损害了道,抓住了一点而丢弃了其他一切的缘故。杨墨之道相较于儒家传统的“中”表现出了“过”与“不及”,杨氏的“不及”已经达到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的地步;而墨子兼爱,无差别,无亲疏,已是“过”了,杨墨之道“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样的禽兽之道,显然不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从孟子对杨、墨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所引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这句话的含义,所以,孟子中道思想的道德价值标准是不容降低的,它不是杨、墨的“兼爱”与“为我”思想的简单折中,其中和思想体现着儒家“仁”的境界。另外,这段话也体现了孟子的“权宜中和论”思想。孟子认为,子莫的“执中”接近于“中道”,但“执中”如果没有权的维度限制,也易偏执一端,一味“执中”,就会以“中”为一切,“中”也会在这种形式下变成一种僵死的内容,这就有悖于儒家真正“中”的精神。朱熹曾说:“执中者害于时中。……道之所贯者中,中之所贯者权。”[3]357“执中无权”实质上是“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3]357。“只是一个总的理论与原则,而环境和条件总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应当对这些理论和原则作适当的变通调整,这就是‘权’”[4]。孟子反对“执一”,就是反对在“执中”过程中的形式化、僵死化,如果“执中无权”,就是没有对儒家传统“中”精神进行辩证地理解。
杨雄的中和思想和儒家的传统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其中和思想是《法言》中的基本原则,他明确阐发:
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法言·先知》)
意思是说,建立好的政治,鼓舞号令群众,动员教化天下的民众,没有比坚持刚柔适当、无过无不及的中和方针更好的办法。坚持中和,关键在于了解民众的情况,从民众的需求出发。从中可以看出,杨雄所推崇的“中和之道”,就是以仁政为核心的中和政治。他主张的中和,是天地之道,是圣人之道,其中和政治的标准即在其中,他说: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刚则甈,柔则坏。龙之潜亢,不获其中矣。是以过中则惕,不及中则跃,其近于中乎!圣人之道,譬犹日之中矣,不及则未,过则昃。(《法言·先知》)
在这里,杨雄把治理天下的关键概括为“宽严适中”。他的主张,其宗旨在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他既反对黄老无为之说,又反对申韩的法家之术,黄老无为是“不及”,申韩的主张却又是“过”。他追求的是既无过又无不及的“中和”,与孟子主张的“中道”是一样的,都体现着儒家“仁”的境界。但他主张的在施政中的“中和之道”,绝不是对前人理论的简单重复,其理论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提出的“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中“哲”字的含义,在《法言》中解释为:
或问:哲。曰:旁明厥思。问:行。曰:旁通厥德。(《法言·问明》)
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全面地明确自己的思想就是哲,能够全面地贯彻自己的道德就是行。一个“哲”字赋予其中和思想的哲理色彩,即君主要把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发展到广博的程度,才能做到真正的“哲”;同时,一个“哲”字又赋予其中和思想的实践色彩,即君主要想在政治中贯彻中和之道,就必须付出实践和努力,去了解人民的意愿,了解人民的需要。杨雄所谓的“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与当时盛行的非理性哲学明显地区分开来,他更重视理性思维在施政中的作用,其“哲”的思想与董仲舒建立在阴阳五行上的中和思想以及黄老自然阴阳的中和思想明显不同。他主张:
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地之际,使之无间也。(《法言·问神》)
这是提倡在理性的认知过程中去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从此层面上可以看出杨雄欲消除董仲舒神学论色彩所做的努力。当然,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摒弃董仲舒的影响,其在坚持先秦儒家政治理论原则和立场的同时,也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着儒家的政治思想,使儒学不断适应发展着的时代需求。
总之,如唐代韩愈评价杨雄所说:“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5]终西汉一代,杨雄可以说是最推崇孟子的人,他以孟子自比,仿效孟子批判杨墨,捍卫孔孟之道,建立起了以维护圣人之道为出发点,以儒家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1] 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85-86.
[2]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6.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2.
[5] 韩愈.韩愈全集[M].钱仲联,马茂元,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8.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Yang Xiong’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encius’Thoughts in
SONG Dongmei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Confucius Research Institute, Qufu, Shandong 273100, China)
Considering himself as the successor of Mencius, Yang Xiong,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Mencius’ criticizing Yang Zhu and Mo Di, criticizes the thoughts of various schools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He thinks that their thoughts are incompatible with Confucian thoughts and that, if their thoughts are left developing without being stopped, they will certainly make people unable to se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and deviate from the right path. As for human nature, Yang Xiong attempts to reconcile Mencius’ thoughts with Xuncius’ thoughts. He holds the idea of “human nature includes both good and evil", which is undoubtedly the development of Mencius’ theory that people are born good. His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and Confucius’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as well as Mencius’ “doctrine of the mean” are of the same lineage. He thinks, “If they want to establish good politics, rulers should encourage and give orders to the masses, mobilize and educate the world;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han carrying out the neutralization thought and to do this, the key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situation and their needs. The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he advocates are, in essence, the neutralized politics that takes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and gives the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at is, rulers must put it into practice if they plan to carry out the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Yang Xiong;; Mencius’ though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neutralization thoughts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6.007
宋冬梅(1968-),女,山东曲阜人,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X067)
B234.99
A
1673-2065(2017)06-0042-06
2016-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