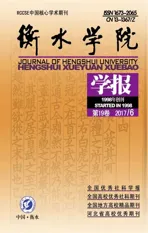阴阳五行与汉代美学——以董仲舒的思想为视角
2017-03-11聂春华
聂春华
阴阳五行与汉代美学——以董仲舒的思想为视角
聂春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303)
从董仲舒的思想出发,可知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汉代美学思想的骨干。受阴阳五行关联性思维的影响,汉代思想形成了宗教、伦理和哲学相结合的混融境界,汉代美学思想须从这种混融境界去理解和体悟;作为阴阳五行系统基本质料的气,为汉代人开辟了一种仰观俯察、吞吐宇宙的流动、有序和系统的大美境界;阴阳五行系统的五行之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成为理解汉代人丰富而有序的审美意象的隐喻原型;阴阳五行系统的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点也塑造了汉代人既新奇炽烈又浅尝辄止、既循环无穷又保守自足、既讲究视角流动又追求秩序规范的奇特的审美心理。
董仲舒;阴阳五行;美学;汉代;审美心理
汉代思想文化的骨干是阴阳五行学说,这一学说经邹衍、《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董仲舒的发皇推导,一时风靡于汉世,汉代的宗教、政治和学术,没有不受其影响的①。但就美学而言,学界对阴阳五行与汉代美学的关系,所论仍相当简略。其实,阴阳五行对于汉代美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不仅奠定了汉代美学的思维方式,塑造了汉代美学基本的审美特征,而且浸透到了汉代艺术的方方面面中。全面探讨阴阳五行与汉代美学的关系,所需笔墨非这里所能承担,故本文仅以董仲舒的思想为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约略加以探究:一是阴阳五行的关联性思维所体现的美学智慧;二是论述作为阴阳五行基本质料的阴阳之气对汉代美学的重要性;三是论述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象对汉代美学的影响;四是阴阳五行的系统论思维给汉代人审美心理带来的影响。
一、阴阳五行关联性思维的美学意蕴
在阴阳五行系统中,事物按照一种特殊的方式活动,但既非按照因果律,亦非原始思维的互渗律,而是根据该事物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来决定。换言之,该体系中的事物就像处于网状的结构或力场之中,事物之活动与整个体系中的其他事物相互影响。李约瑟说:“一旦像五元系统的类别方式被建立起来,事物就不能随便作为其他事物的原因了。或许我这样说会比较正确:从原始的参与式思想发展出来的(至少)有两条路,一条(希腊人走的)是将因果概念加以精练,这种态度引出如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那种自然对现象的解说;另外一条路,是将宇宙万物万事都有系统地纳入于一个结构形式,这个结构决定各部分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有一个质点占据了时空中的某一点,依前者的看法,这是因为另外有一个质点把它推到那里,而依后者的看法,则是因为他与别的一些质点构成一个‘力场’,由于相互影响的结果,才把它送到那一点。”[1]这“另外一条路”,西方学者名之为“关联式的思维”,它与西方的因果律大异其趣,阴阳五行中的各个要素皆通过网络状的系统确定自身的位置,也根据自身的位置而产生关联性的行为,因此系统着眼于整个“宇宙有机体”的循环不已,而此机体中的各要素根据整体的网络结构而运动,它们俱无独立存在的依据。
阴阳五行的关联系统是整个宇宙的全息图,故在阴阳五行学说看来,宇宙万物之权舆徂落,俱非自身独化的结果,而是整个系统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作为汉代思想的骨干,此种关联性的思维方式,塑造了汉代人体系性的综合审美观,而与西方美学之重因果分析迥然有异。在西方语境中,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态的产生,本身即是分析性思维作用的结果。“美学之父”鲍姆嘉通有感于人类知、情、意心理活动的划分,只有对应于知的逻辑学和对应于意的伦理学,才建议设立一门专属于情的美学学科。可见,西方语境中美学的成立,是对人类心理活动做分析性理解而得到的结果。此种分析性的思维,虽不排除学科间的共通之处,但以区别学科领域为要务,以各自独立的对象、方法和范畴作为学科成立的前提条件。但在汉代思想中,要找到这样一种分析性思维的美学,或者以西方分析性思维理解汉代美学,都难免有些隔靴搔痒。
董仲舒的天的哲学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董仲舒所说的“天”有多重意涵,有时“天”是有道德属性的人格神,如“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作为人格神的天与人类紧密依存,所以董仲舒视天为人类的先祖,人的形体、血气、德行俱由天的变化而造就。这种人格神之天虽是“百神之大君”“人之曾祖父”,但它基本上是抽象的存在,人的形体、血气和德行由天的天数、天志、天理变化而成,而所谓的天数、天志和天理均是抽象的。这样的天和古代氏族部落的氏族神和祖先神不一样,后者往往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部落之图腾来崇拜;它和古代的神话传说也不一样,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往往有其具体的形象,如人首蛇身的女娲。董仲舒的人格神之天有其突破原始宗教神话的地方,他虽把天视为百神之大君,但这个天具有一定的抽象意义。此抽象的意义就是“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春秋繁露·俞序》),仁为天心,所以天具有道德属性。董仲舒所说的“天”同时也是阴阳五行化的自然之天,董仲舒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这里出现两个天,“天为一端”的天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元素,就像地、阴、阳、火、金、木、水、土和人是自然界中的元素那样;而“天有十端”则可视为“自然”的代名词,指的是包括天、地、阴、阳等诸元素在内的自然的总称。董仲舒的自然之天的思想深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比如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又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以阴阳五行言天,是董仲舒和先秦诸子在自然之天上的重要区别。先秦时讲的自然之天基本上指的就是自然界或自然界中的事物,而董仲舒的自然之天包括由天地之气分化为四时、五行以至囊括万事万物的一套宇宙生成法则和宇宙运行图式。因此,董仲舒所讲的自然之天并非简单的自然之物,而是自然生成的一套宇宙创化的基本动力学,这里面的丰富意味,是先秦时期的自然之天所无法比拟的。
董仲舒的美学思想便与他这种天人感应体系息息相关,此天人感应的体系通过阴阳五行的关联性思维,将人格神之天、自然之天和人三个单元联结在一起,此三元中的任何一元均无自身独立的依据,必须在其他二元中显现自身,同时作为映像显现其他二元,由此构成一个网状的系统。就美而言,在此系统中,神性美须通过自然美和社会美才得以显现,自然美也受神性美和社会美的影响,而社会美亦受到神性美和自然美的监督警戒。董仲舒说: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其德而皆俫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人君修德爱民,于政治上有所贡献,上天便会降下祥瑞,故天地间被泽而大丰美,这段话最集中地体现了董仲舒在关联性思维中阐释美的思想,先由政治社会上的效应推及自然界美的现象,再由自然界美的现象推及人格神之天的意志,故美的现象在形而下层面联系着自然与社会,而其最终的目的则是形而上的神意的体现。神性美的形式,除落实于自然现象之上,还集中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是在人的形体外貌上。依董仲舒的看法,万物之中唯人能副天,故人最贵,“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为天地间之最贵者,故人的身体形相便也是神性美最集中之体现,因为在万物中只有人才能偶天地。因人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是个有位阶的概念,所以人就一般意义而言是万物中最贵最美者,但若具体到政治社会中各种不同位阶的人,则这种美又是分阶级和层次的。在政治社会的人伦等级中,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故天子在董仲舒思想中实际上应是神性美在人世间的最完美体现者。由此,董仲舒发明了一种“大显己”的身体美观念,使身体形相的美不仅不能忽视,而且此种美的显现应成为必然。《春秋繁露·楚庄王》说:“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不“显己”则上天的意志不明,不“显己”则事君者无法仪志,就天子而言,“显己”包括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当然也包括在身体形相上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异相。
在西方分析性思维中,神性美、自然美和社会美虽共属美的领域,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断不会如此纠缠难解;而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体系中,此三者之所以纠结若此,皆归因于内在的关联性思维方式的作用。故理解董仲舒及汉代美学,须从整个天人感应的体系着眼,要将体系内的各要素联系起来解释,而不能做单独的元素分析。这即是说,我们虽能按照现代学科的分类研究汉代美学,但鉴于此种关联性思维方式的存在,实无一个专属汉代美学的独立领域,必须从宗教、伦理和审美的相互关联中加以系统性的理解,才能体悟汉代人审美观的混融境界。
二、以阴阳之气作为基本质料的汉代美学
气在先秦之时就有多种不同的意涵,如云气、血气、心气、精气、浩然之气等。在汉代,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气作为媒介物被纳入到这套体系之中,成为沟通阴阳五行诸要素的基本质料。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是把阴阳五行的系统作为宇宙的全息图,由此基本的五种元素而包囊整个宇宙万物,因此作为阴阳五行系统基本质料的气,便是以自然界消长变化的物质之气为主,而通过类推的方式统摄其他意涵,如血质之气、道德之气、精神之气等。比如,在董仲舒的学说中,气几乎可指涉万物:作为基本质料的,是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的“天地之气”;作为人格神的天,也是气的构成,“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春秋繁露·阴阳义》);作为自然的天,当然也归结为气,“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春秋繁露·阴阳义》);至于人,既与天相副,当然也是气的践形,“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故自先秦以来所产生的各种气的意涵,通过阴阳五行系统的全息图,全部整合在一起了。
阴阳五行系统是借助气类感动的原理而使宇宙诸事物相互关联而成为有机的整体,并被赋予了机体性的生命意味。作为阴阳五行系统之质料的气,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感性气质,较之于西方古典思想对确定性真理的追求,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说明汉代人不是以静止、绝对和超验的观点来解释世界。按照汉代人的观念:历史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受五行循环所控制,它总要根据一种既定的但又是不断轮转的力量发展;宇宙中的事物也不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阴阳之气和五行运转的规律而不断变化;宇宙诸事物间也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而这些事物的关系最终又可还原为一些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汉代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流动、循环和变化的世界。
此种阴阳五行之气,已适足为汉代美学开出一种仰观俯察、吞吐宇宙万物的大美境界,一种气化流行、消息变动的天地之境。此在董仲舒中和美的思想中最为显见,《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
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是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其动于下者,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
上文的“两和”与“二中”,俞樾云:“两和谓春分、秋分,二中谓冬至、夏至。”[2]董仲舒认为每一年都由这“两和”与“二中”循环而完成。冬至之时,即北方之中,阴气极盛,而此时阳气在下初生,所以万物在地下萌动;夏至之时,即南方之中,阳气极盛,阴气在下初生,所以万物在地上生长养育得很好。在地下萌动的万物若得不到东方之和就不能生长,东方之和就是春分;在地上生长很好的万物若得不到西方之和就不能成熟,西方之和就是秋分。万物不经过春分和秋分就不能成长成熟,故董仲舒认为天地的美妙之处就在两和之处,这两和之处正是二中所要走向的地方,即文中所谓“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按照这种阴阳五行的中和观,整个天地的运行都可归于中与和的状态,如果整个天地按这种中和的秩序运行,则“天地之行美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按照笔者的看法,无论是先秦孟子所说“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的浩然之气,还是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都没有呈现出如此流动、有序和系统的大美之境。
三、以五行之象作为外在表现的汉代美学
在阴阳五行系统中,阴阳之气的运行,需要通过五行之象来表现。气在一年之中所经历的春、夏、季夏、秋、冬的时间序列和东、南、中、西、北的空间位列,都可表述为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要素的运动变化。此五种既抽象又具体的要素,其实是宇宙基本质料的气和纷繁芜杂的宇宙万物之间的中介。它们一方面可最终归结为阴阳之气的流行,另一方面又是宇宙万物的高度浓缩。
在阴阳五行系统中,一要素的行为取向,须照顾两方面的关系:首先,一要素的位置要根据它与中心的关系确定。阴阳五行的网状系统,尽管可以纳入各种不同的事物,但这个系统并不是散乱的,它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如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阴阳五行的系统由“一”散开分化而来,因此系统中的各要素无不围绕着一个隐然的中心而活动。这一隐然存在的中心,在战国末和汉初阴阳五行学说兴起的阶段,未能够很清楚地被揭示出来,而把这个中心解说得最好的则是董仲舒。《吕氏春秋》只是把土附于冬季之后,土并没有明确的地位;到《黄帝内经》和《淮南子》,则已把土作为五行的中心来看待,《黄帝内经》把土和方位的“中”以及季节的“长夏”相配,《淮南子》亦如此。在董仲舒这里,土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他说:“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在董仲舒的阴阳五行系统中,各要素须围绕“土”这个隐然的中心而活动。
其次,一要素的位置要根据它和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此原则在董仲舒总结的“比相生,间相胜”规律中尤为显著。在此系统中,因各种要素按照一种轮转、循环的关系而活动,故诸要素之间不存在线性的因果进化关系,一要素之所“生”或“胜”,取决于它在这一系统中所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位置。比如,木能生火,但这并不意味着木被淘汰,而只是说在某一时空条件下木和火之间出现了轮转。五种要素循环轮转,并无所谓的开始与终结,只有某个具体时空中的网节点。故此系统中的五种要素,相互隶属又相互反映,每一个节点都是宇宙诸事物关系的浓缩,由此每一个节点构成的小宇宙重重映现以至于无穷。
此五种要素的本质即象。五行作为五种基本的象,既可以是物象和气象这样的具象,也可是概括某类事物的抽象符号。因此,五行作为象,与传统美学中的意象类似,是古人观察和理解外在世界的产物。但五行之象的特点,在于使先秦以来的各种意象统摄于阴阳五行的系统中而具有了体系性。因之,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五行之象,遂成为汉代思想中五种基本的隐喻原型,此五种隐喻原型的美学意味很值得深入探究。例如水的隐喻,在先秦美学中,既可看到庄子“秋水”的隐喻②,也有孔子“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的隐喻,但这些隐喻还不是系统思维下的敷衍。而在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水的隐喻却有了自己特定的风格和特点,在五行的序列中,“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而在事义上水又和执法司寇的隐喻相连,“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君臣有位,长幼有序,朝廷有爵,乡党以齿”(《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故此时水的美学风格一般和冷峻、肃穆、守礼等有关。如《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云:“水者冬,藏至阴也。宗庙祭祀之始,敬四时之祭,禘袷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闭门闾,大搜索,断刑罚,执当罪,饬关梁,禁外徙。恩及于水,则醴泉出;恩及介虫,则鼋鼍大为,灵龟出。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则民病流肿,水张,痿痹,孔窍不通。咎及于水,雾气冥冥,必有大水,水为民害;咎及介虫,则龟深藏,鼋鼍呴。”
在五行之象中,土这种隐喻原型最值得关注,因其在阴阳五行系统中的位置,土一跃而成为最贵最美的要素。董仲舒说:“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春秋繁露·五行对》)可见,因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先秦以来散乱的喻象群在此统摄为一个体系,而五行之象也就成为五种基本的隐喻原型,各自具有特定的美学风格而不相淆乱。因之,汉代美学中的各种审美意象,无论是自然界的、社会人事的还是其他各种意象,在看似纷扰的表象下其实都有其体系性的关联。即便是一草一木之美,在先秦之时还只是孤立之现象,但在汉代美学思想中,却要归属于不同的隐喻原型才能得以理解。
四、阴阳五行的思维特点与汉代审美心理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审美心理特点,就汉民族的审美心理而言,若追寻其源头,自然可以溯至先秦甚至更古远的时代,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汉代这个历史时期。原因在于,汉代是先秦各种思想在官僚政体下开始沟通汇合的阶段,直接开启了嗣后两千年中华帝国在政制和思想上的大趋势。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各种思想的沟通上,诚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阴阳五行系统之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通过关联性的思维,以五种最基本的要素,再加上阴阳之气的循环运动,形成一个全息的图式,可以把宇宙间所有事物按照类别一一纳入其中。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面对这套灵活的全息图式,自然容易求同存异,而逐渐趋向于一种统贯综合的思想。由此,阴阳五行的思维特点,不仅对理解汉代人的审美心理,而且对理解整个汉民族的审美心理,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关于阴阳五行思维,李泽厚先生指出其具有“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征”[3],这些特征给我国国民的整个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带来深刻的影响。下面本文便按照这三个特征,就阴阳五行的思维特点对汉代审美心理的影响,作一简要的描述。
1 阴阳五行系统的封闭性
阴阳五行系统虽以五种基本要素的运动为主要表现,但此系统实可以包括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在内,所以阴阳五行系统并非绝对地排斥外物,但此系统却很容易给人营造故步自封的心理。原因便在于阴阳五行系统以某些日常经验为准的,为宇宙诸事物安排了一个想象中的秩序,此种实用主义的考量随即也就阻碍了人们对事物的进一步考察。李约瑟将邹衍视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真正创始者”[4],原因在于阴阳五行学说并非完全的痴人说梦,而是有其经验上的根据。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即以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证明为本,故其学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上的规律。董仲舒秉承此方法,其天人感应体系虽闳大不经,但他通过琴瑟共鸣此类自然现象作为证验,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日常经验的根据,然此套学说本非为了科学上的考察,而是为了伦理政治上的某种目的,故其作为证明的日常经验一旦发挥其效用,就不再对未知事物做进一步的考察,而是把这些未知事物全都按照既有的模式进行解释。所以,像邹衍和董仲舒那样,在验证“小物”上具有科学的精神,然而一旦突破日常经验上的“小物”而推之于“无垠”,则按照“小物”的解释模式来切割涵盖“无垠”,这便反而有失科学的精神了。
阴阳五行学说以五种要素构成宇宙的全息图,这套系统在面对宇宙诸事物之时善于以简驭繁,故这套系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将几乎大部分事物都消化于其内。阴阳五行学说出现以后,汉代人在解释外在世界时便具有一种囊括天地六和的宇宙意识。因之,汉代人的审美心理,似乎一下子进入了上天入地、纵横捭阖的境界,“从幻想的神话中仙人们的世界,到现实人间的贵族们的享乐观赏的世界,到社会下层的劳动者艰苦耕作的世界,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被汉代艺术所注意,所描绘,所欣赏……这不正是一个马驰牛走、鸟飞鱼跃、狮奔虎啸、风舞龙潜、人神杂陈、百物交错,一个极为丰富、饱满、充满着非凡活力和旺盛生命而异常热闹的世界么?”[5]阴阳五行在解释世界上的灵活便给,赋予了汉代人炽烈的审美想象和旺盛的审美情感,形成了汉代人颇为显著的审美心理特点。
但如前所述,阴阳五行系统有其固有的封闭性,超越日常经验层次的宇宙秩序,一般都出于此学说持有者一己的想象,他们这些想象既满足于伦理政治的实用目的,便无心再去深究此种想象到底是否合于事实。就汉代人的审美心理而言,亦有这样的特点,汉代人将审美的视野拓展至浩渺深邃的宇宙,但他们会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想象来理解宇宙诸事物。最明显的便是宇宙诸事物间的关系,董仲舒说的“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就是一个显例,此种感应关系可以解释琴瑟共鸣的现象,董仲舒便以之作为美丑产生的原因,只要此种解释能够圆通便给,他就不再对之深究了。由此也可理解,汉代人对审美现象有着敏锐的认识,对外在世界有着整体性的审美眼光,但往往又是浅尝辄止,甚至是扭曲的。因此可以说,阴阳五行学说的封闭性和灵活性,塑造了汉代人既宏大深邃而又片面固执,既新奇炽烈而又浅尝辄止的奇特的审美心理。
2 阴阳五行系统的循环性
邹衍学说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五行依气运相转用事,由此来推定朝代的更迭情况。《吕氏春秋·应同》篇也认为帝王者之将兴,自然界必有五行代胜的各种祥瑞表现。这些强调的都是历史的循环性,历史是按照五种气运相转用事的规律而循环运行的,故朝代的更迭看似随着时间历程而向前发展,实则按照五种气运做循环往复的运动。
阴阳五行讲究循环圆转如意,为了维系整个系统的均衡,就要强调要素之间的平等共处,它们之间的“生”与“胜”,皆因气的运行位置所决定,各要素并无永久的“胜”,亦无永久的“生”,故气的运转始终控制在一个阈限之内,这便是阴阳五行循环性的基本原则——中和。中和的审美观当然并非在阴阳五行学说产生后始自出现,但先秦的中和审美观偏重从生理阈限和伦理道德上出发,而阴阳五行学说则使汉代人更注意审美感受上的整体和谐观。阴阳五行系统的诸要素通过相互依存和转换的方式存在,而且此种观念通过五行相转用事的图式直观地表现出来。故而,此种图式对于汉代人的审美心理来说,很重要的便是塑造了那种视外在世界为动态整体的感觉。上述董仲舒的中和美思想便很能说明问题,他所讲的并非先秦儒家那种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中和观,而是阴阳之气的组合情况,以及此种组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
由此中和感而来的艺术创造和鉴赏活动,必然在时空的心理感受上与西方迥异。西方艺术的空间再现具有比较严格的科学精神,特别是在建筑、雕塑和绘画中讲究科学的点、线、面焦点透视关系;而阴阳五行视野中的历史则是非线性的,其诸要素间的关系亦非因果律。在阴阳五行学说中,时间和空间总是相转用事,无所谓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只有循环往复的历史重现;其间某一要素出现或消失,并不是因为另一要素导致的缘故,而是整个系统诸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之,中国传统的艺术创造和欣赏活动,不是采用更科学的焦点透视,而是用散点透视和多重视角,以流动的视线、循环的路径、整体的格局,将物象的各种空间关系融会贯通在一起。
3 阴阳五行系统的秩序性
此处所谓秩序性,系指阴阳之气流行的节奏感和五行生灭的规律性。在阴阳五行系统中,气的流行总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时序。例如,阴阳之气是相反之物,两者不会同时出现,此所谓“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阴右则阳左,阴左则阳右”(《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阴阳二气分别于冬至和夏至交汇于北方和南方,嗣后各自向相反方向运行,由此二气力量的互相损益,而形成一年四季和二十四节气之岁功。五行的生灭则更见其秩序性,一要素的出现与寂灭,与其相邻或相间要素有着直接的联系,五种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此起彼伏、循环不断的秩序感。
阴阳五行学说的此种秩序性,对于塑造汉代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也是影响深远。汉代人在其审美和艺术中,总流露出一种深藏在内的秩序感,而此种秩序感是与阴阳五行学说的时空节律息息相关的。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描写的是一位居住在中州的“大人”游历四方的故事。先是“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汉书·司马相如传》),描写“大人”由太阴横渡飞泉驰往东方,嗣后在东方部署众神,并以句芒(东方青帝之佐)为先导,向南方行进;接着“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輵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相纷挐兮,滂濞泱轧丽以林离。钻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坛以陆离”(《汉书·司马相如传》),描写的是“大人”在南方游历之情况;然后是“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一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汉书·司马相如传》),写的是“大人”游历西方的情形;及后“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叽琼华”(《汉书·司马相如传》),“幽都”即北方,此处描写“大人”游历北方的情形。司马相如之《大人赋》,通篇描写居住中州之“大人”游历东南西北之情形,与阴阳五行之方位相合,其受阴阳五行学说之影响比较明显。《大人赋》与战国末的楚辞作品《远游》关系密切,然而《大人赋》改变了《远游》主人公那种游历方向无序的情况,按照东西南北的顺序描写“大人”的巡游[6]。如前所述,从邹衍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子》,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五行方位渐次得到规整,最终在董仲舒那里确定了以中央(土)为最尊、以东南西北四方为次的观念。在《大人赋》中,“大人”居住中州,与阴阳五行学说以中央(土)为尊的观念正相吻合;而“大人”东西南北的游历顺序,亦与五行相生的原则暗中一致。由此可知,从《远游》到《大人赋》游历顺序的改变,正可表明随着阴阳五行学说在汉初的成熟,汉代人审美心理中秩序感的逐步建立。
五、结语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汉代思想文化的骨干,阴阳五行学说的思维特点、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构成了我们理解汉代审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除了上述观念和文献上的探讨之外,汉代留存至今的诗词歌赋、建筑、画像石、器皿等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汉代画像石是我们现今能见到的珍贵的汉代石刻艺术,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和发掘的汉画像石墓已超过200座,汉画像石阙20余对,包括已复原的石祠堂在内的汉画像石祠10余座,用汉画像石雕刻技法雕造的摩崖造像群1处,汉画像石总数已超过1万块[7]。汉画像石在思维方式、表现内容、空间结构、原型母题、符号图案等各方面都带有浓厚的阴阳五行色彩。例如,祥瑞征兆图案是汉画像石的重要表现内容,而这种观念其实正是汉代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观念盛行下的产物。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便是阴阳五行观念的集中体现。此墓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其南北主室墓顶皆有天象图。南主室顶部中心有月亮和星宿画像石,系女主人墓室,主阴;北主室顶部绘有太阳、三足乌、白虎等图像,系男主人墓室,主阳。北主室墓顶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灵图,很明显是阴阳五行观念的体现③。刻四灵于墓顶,因此就有镇守中央、驱除四方邪恶之意。由南北主室的月亮河太阳石刻,到代表四方的四灵图,都显见出浓厚的阴阳五行色彩。画像石是证实汉代审美观念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的一个显例,但若要全面探究阴阳五行观念对于汉代审美现象的影响,仍需要对汉代文献和遗存做更多的工作。
[1]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356-357.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444.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2.
[4]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266.
[5]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71.
[6] 孙晶.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M].齐鲁学刊,2004(3):110-114.
[7] 徐永斌.南阳汉画像石艺术[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2.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①顾颉刚先生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见氏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庄子·秋水》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③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墓北主室顶部的四灵图,据发掘简报(见《文物》1973年第6期)称,四灵的方位是苍龙居西,白虎居东,朱雀居南,玄武居北。1972年后,河南省博物馆与南阳市博物馆、南阳汉画馆组织对此墓进行复原时,对这块画像石西苍龙、东白虎的现象不理解,按照传统的东苍龙、西白虎的布局,把画像石的摆放方向颠倒。其结果,虽然东、西方向与传统四灵方位吻合,但朱雀却调到了北方,玄武到了南方,又与传统的四灵格局抵牾了。此墓四灵格局与传统不一致,大概是汉代人阴阳五行观念在某种特殊情境下的变化。相关讨论,参见陈江风《关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8年第12期,88-89页;刘道广《关于汉“四神星象图”的方位问题》,《文物》1990年第3期,70-71页。
Yinyang &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Han Dynas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s
NIE Chun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Guangd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China)
From Dong Zhongshu’s thoughts, we can deduce that the theory of yinyang & the five elements is the core of the aesthetic thoughts of the Han dynasty. Influenced by the correlative thinking of yinyang & the five elements, the thoughts of the Han dynasty become an indivisible whole of religion, ethic and philosophy, therefore, we must understand the aesthetic thoughts of the Han dynasty from the indivisible whole. As the basic material of yinyang & the five elements, the presence of Qi establishes a flowing, orderly and systemic world of beauty; in the system of yinyang & the five elements, the images of the five elements, which are of high generality and abstraction, become the metaphorical prototype of understanding the rich and orderly aesthetic image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close, cyclic and orderly system of yinyang & the five elements shapes the peculiar aesthetic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who are curious, flaming and satisfied, like cycle infinity, conservatism and self-sufficiency, stress flowing perspective and pursue orderly peculiarity.
Dong Zhongshu; yinyang & the five elements; aesthetics; the Han dynasty; aesthetic psychology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6.003
聂春华(1978-),男,广东韶关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美学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X08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72);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专项(2015ARF23)
B234.5
A
1673-2065(2017)06-0015-08
2015-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