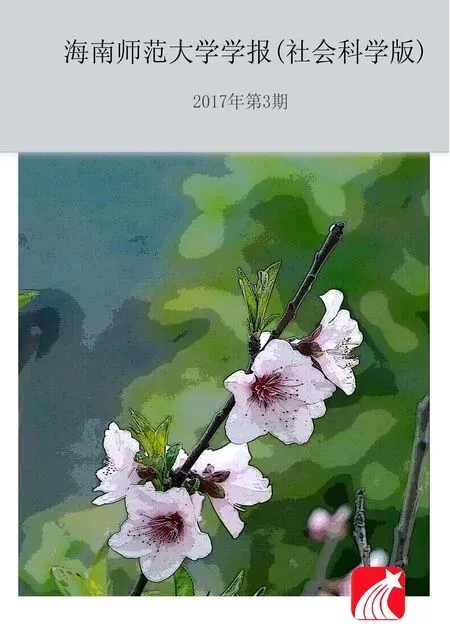文学如何讲述历史
——《红高粱》:虚幻现实主义的源头、方法及立场
2017-03-11王兴文
王兴文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文学如何讲述历史
——《红高粱》:虚幻现实主义的源头、方法及立场
王兴文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红高粱》是莫言虚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轫之作。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小说及魔幻现实主义美学形式的基础上,莫言找到了独特的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方式,也形成了此后小说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人类性立场。莫言以“世界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创作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启示。
《红高粱》;虚幻现实主义;空间形式;编码方式;历史观
《红高粱》无疑是莫言所有作品中聚合了多重价值与意义的一个重要文本。一方面,《红高粱》的诞生以及随后的电影改编与世界性传播,不但是1980年代重要的文化事件,而且也是中国文化世界传播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另一方面,对当代文学而言,《红高粱》所开启的文学讲述历史的模式(以虚幻现实主义铭记家族与民族记忆)成为文学寻根之后影响颇大的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滥觞,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从不同层面挖掘历史记忆的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沾染上了《红高粱》以文学书写历史时不可避免的想象、虚幻以及解构等特征;当然对莫言本人来说,创作《红高粱》的过程是他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因素与西方现代小说技法糅为一体创造出虚幻现实主义美学形式的实验过程,《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以文学人类学式的眼光观照中国式家庭与社会中的“猪圈式”生存、以乡村世界的微观历史隐喻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以虚幻现实主义讲述中国故事的文本特征,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红高粱》。因此,研究《红高粱》如何讲述历史、讲述什么样的历史以及其中所渗透的历史观,不但可以厘清莫言虚幻现实主义的源头、方法及其背后的哲学,而且也能揭示莫言小说世界传播很广的文本因素。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就立足于此:如果把莫言荣获诺奖当作其小说世界传播的成功标志的话,那么除了外部因素(如翻译、介绍的途径、方式等)之外,源出于《红高粱》自身的具有强大交际功能的形式因素(虚幻现实主义)、独特的中国经验(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以及哲学立场(超越阶级的人类性意识形态)——一句话,以“世界语”讲述中国情感经验——是莫言小说世界传播不可或缺的内因。
一、虚幻现实主义:文学讲述历史的形式
毋庸讳言,《红高粱》所叙述的“我爷爷”带领他的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伏击日军的故事,在整个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大历史中是一个很小的片断,充其量只能算作是野史轶闻、家族历史抑或传奇故事;即便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它至多也只能存身于地方志、民间传说故事中。但如果从这一故事所表达的历史意义来看,其中所包含的抗击侵略的精神却是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作为文学文本,《红高粱》在以文学讲述历史时如何兼顾近乎对立的文学与历史,便成为一个问题。显然,以搜集文献为基础辅以反复考证,无论研究如何深入,考证如何精细,其结果都不会是一篇小说。莫言以文学书写历史的独创性在于,将现代小说空间形式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意象营构模式融为一炉,创造出了被称为“虚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美学。
然而莫言在《红高粱》中尚留有斧凿之痕的这种艺术创造,往往被误读为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流响余波。《红高粱》中反复出现的高粱意象、高粱酒意象,以及“我爷爷”、“我奶奶”近乎玄幻的传奇故事,都与《百年孤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特征(诸如离奇怪诞的情节和人物、神话色彩及象征意味等)有一种“家族相似性”,论者往往据此认为莫言的《红高粱》的美学形式源出于《百年孤独》。从时间*在《与王尧长谈》中,莫言说:“《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才在中国出版,或者是我1985年春天才看到,那时根本没空逛书店,更舍不得花钱买书。《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我写《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百年孤独》。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当然,莫言也坦承:“早期的《金发婴儿》(《钟山》1985年第1期)、《球状闪电》(《收获》1985年第5期),就带有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因为我那时已经看过马尔克斯的一个短篇小说集,里边有《巨翅老人》等具备魔幻特征的小说。”见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24-125页。与内容、技巧等方面辨析《红高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作家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并不能遮蔽其独创性;而且,如果要追本溯源,《红高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其实可以追溯到福楼拜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美学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意象营构模式,这两种传统同样能够带给莫言的《红高粱》以类似于魔幻现实主义美学技巧的影响。
从《红高粱》的文本特征看,时间被割裂后重组、主题与章节重复、夸大的反讽等形式似乎都与《百年孤独》中的形式类似,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小说美学其实是现代小说空间形式的表现。早在1940年代,美国学者弗兰克等人就对源出于福楼拜的现代小说空间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弗兰克看来,福楼拜处理时间的方式(即把时间割裂为众多碎片,让读者在阅读时“必须通过各个片断来重新建构”*﹝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页。时间),是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的一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小说的这种空间形式其实是将每一个时间片段当作一个意象,并通过多个意象的并置以表达对现代化、城市化支配下的日常生活复杂景观的共时性、瞬时性经验。当然,这种形式也带来了现代审美经验——类似于电影蒙太奇效果的阅读经验:“通过主题或通过一套相互关联的广泛的意象网络,可以获得一个空间性的程度。像倒叙一样,反复出现的意象阻止了读者的向前发展,并且指点着读者去注意作品中其他较早部分。”*﹝美﹞戴维·米切尔森:《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见﹝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第148页。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既是西方现代作家从文本之内探索的结果,也与西方现代性进程与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眩人耳目的城市景观的刺激分不开。与传统文学叙事方式相比,这种叙事方式虽然在“情节、事件、环境和时间都颠三倒四,支离破碎”,但是对时间的“切割和组合能在不长的篇幅内又提供给读者鲜明而强烈的感受”*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83页。,“而现实生活中的时空关系的完整性,在现代小说艺术创作中,并无多大的意义”*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第86页。。
这种被现代小说奉为圭臬的空间形式技巧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并置的方式处理时间、事件甚至心理经验,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象并置”。作家为了使自己的表达获得一种新奇的效果,把事件、人物的心理经验、记忆等当作一种意象插入文本,并使之与作家本人情绪的流淌相协调,从而造成一种并列形式。这种处理意象的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如“鸡声茅店月”、“枯藤老树昏鸦”等,都是如此。对此,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有清晰的界定:“两个视觉事象的并置与罗列,即是爱森斯坦所提出的‘蒙太奇’。电影中的‘蒙太奇’技巧,在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影响甚巨,而‘蒙太奇’技巧的发明,却是从中国六书中的‘会意’而来。”*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4页。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还提到他奶奶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蒲松龄《聊斋志异》鬼怪故事的讲述方式对他的影响更大。事实上,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因素,毋宁说是莫言讲述中国故事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源头。在融合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意象营构模式、《聊斋志异》中无羁的想象力、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以及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等文学巨匠的艺术技巧之后,莫言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讲故事的方式——虚幻现实主义。由此可见,莫言《红高粱》的美学形式,一方面借鉴自西方文学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他自己的创造。对于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摹仿、借鉴与独创性,莫言如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近乎痴迷地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中国作家也没有今天的冷静和成熟。”*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125页。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仅仅停留在摹仿的阶段,还是不行的,而且他也意识到:“一味地学习西方是不行的,一个作家要想成功,还是要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取营养,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125页。
问题的关键也许并非《红高粱》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而是《红高粱》的讲述方式被如何识别,以及这种讲述历史的方式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如果考虑到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的家族叙事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盛行,特别是当代作家对现代小说空间形式的圆熟使用,那么这篇发表于1986年的小说的价值与意义就更为显豁。由于采用了类似于木偶牵线人(或傀儡师)的控制叙述视点,而且从形式美学的角度看,既糅合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又兼备中国文学意象营构方法以及民间话语的形式,《红高粱》便成为城市化时代共时性瞬间视觉经验的象征性表达。从其文化血缘上说,这种中西结合与古今结合恰好表明其身份是一种文化杂糅的结果,正是这种杂糅性质,使《红高粱》既获得了讲述历史的合法性,又规避了某种制度性规则的限制。这种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既非文学又非历史的特征解构了人们的世界认知方式同时又刷新了人们的文学阅读方式,从而开辟出了一种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张清华认为《红高粱家族》“既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部分”。见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4期。的文学思潮。
二、真实与虚构的辩证法:文学讲述历史的编码方式
莫言以虚幻现实主义讲述历史,其实也是历史自身的空缺与文学对这一空缺填充的结果。一般认为,文学与历史的最大区别在于虚构与真实,但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观念逐渐被解构。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历史不再被视为对既往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被解释为一种“书写”,这种历史书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页。,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组建文本空间、叙述建立起一种契约,组建起社会空间”*﹝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历史书写》,第77页。。如此一来,历史真实的生产过程变成了与文学创作极其相似的编码过程,不同之处也许在于文学通过虚构与想象的方式处理事件;而历史的撰写过程则是将作为共时性存在的编年史材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元素)组织成故事。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按照赋予一组特定事件以动机的方式编码”*﹝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页。。历史编纂过程与文学创造过程编码模式的趋同,便使得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的界限被消弭了。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由于其“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1页。,反而获得了比历史真实更真实的力量。
莫言是否受到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单从《红高粱》的创作来看,莫言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历史文本本身合法性的可疑性。在莫言看来,不管是官方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还是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都不足凭信,因为二者都是特定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莫言:《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换言之,尽管官方历史文本和民间口头历史文本的编码目的不同,但编码方式的一致性导致结果的一致性:都是对于真实历史的某种背离。而所谓的真实的历史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仅留下碎片化的只言片字,要讲述历史,就必须以虚构填充这些真实的历史碎片之间的空隙,莫言的历史书写同样如此。在《红高粱》中,莫言以叙述者的口吻强调:“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虽然莫言通过查阅县志、与92岁的老太太访谈等途径认真搜集资料,但这些资料都是碎片化的。县志中两百余字的记述仅仅说明事件的大致经过和结果,而老太太所讲述的故事则是以破碎凌乱的话语呈现出来的。作为历史基本构成元素的碎片化的历史事件总是无法与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一一对应,因而导致了这些构成历史真实的材料本身的不完整、有缺陷,因此历史真实也需要填充,需要文学虚构的填充与替补,如此,文学讲述历史就获得了合法性。这样一来,莫言在真实的历史碎片的背后,发现了广阔的、可以天马行空般任意挥洒笔墨的空间。这个空间本身是历史碎片之间的空白,由于空白的存在,历史的连续性与真实性都受到威胁,于是莫言用虚构与想象填充了这些空白,完成了历史画图。从编码的角度来看,虚构与想象对真实的碎片之间的罅隙、空白的填充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真实”的历史碎片本身需要填充,就像德里达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某物只有通过让符号和指代者填满自身才能自动填满自身和完成自身”*﹝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另一方面,虚构与想象的内容的填充过程,也是使自身真实化的过程,用以填充空缺的(杜撰的、虚构的)内容由于填充过程本身获得了真实的身份之后,就与碎片化存在的“真实”的历史组建起新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文学讲述的历史就是一种新历史,是在真实的历史碎片与虚构的填充内容之间漫步的编码活动。换言之,《红高粱》对历史的重构渗透着历史与文学的嫁接、真实与虚构并置的互文性,这种互文关系显示了历史编纂学中真实的短板与文学创作中虚构与想象的侵袭。其实除了《红高粱》之外,莫言其他有关历史的小说都有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或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的背景,如《檀香刑》是以孙丙抗德的历史史实为基础创作的,《丰乳肥臀》以恋母情结为出发点反映20世纪中国的乡村史,《蛙》则叙述了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史,其中无不交织着真实与虚构的互文性,这种互文性一旦与虚幻现实主义的美学表达形式相结合,便创设出一种充满张力的文本。
由于虚构与想象是文学的本质特点,因此,在文学讲述历史的过程中,如何使掺入了虚构与想象之后重构的历史更“真实”,就变成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显然,用抽象的概念填充空缺的历史框架是书面化的历史的惯用手段,但是,作为与之相别的“活生生”的历史,显然被遮蔽了。对历史的重构必须借助于当下鲜活的语境。莫言找到了一个妥当的渠道,给虚构的文本镀上一层真实的膜,这层膜构成了莫言小说中真实感知与虚构想象之间的张力关系。《红高粱》中,高粱的气息、高粱酒的味道、血液的味道,都给人以极其细致入微的感官知觉冲击,使人如临其境,这里面包含着莫言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就像莫言自己所说的:“其实,在写作过程中,作家所调动的不仅仅是对于气味的回忆和想象,而且还应该调动起自己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全部的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想象力。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色彩和画面、声音与旋律、苦辣与酸甜、软硬与凉热等等丰富的可感受的描写,当然这一切都是借助于准确而优美的语言来实现的。好的小说,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仿佛进入了一个村庄、一个集市、一个非常具体的家庭的感受,好的小说能使痴心的读者把自己混同于其中的人物,为之爱,为之恨,为之生,为之死。”*莫言:《用耳朵阅读》,第59页。
由此可见,莫言的历史重构,其实是以真实的细节与虚构的情节唤起一种生命体验。它既不是历史的再现,也不是现实的再现;它既不是编年史材料梳理出来的历史,也不是现实生活的具体摹写。它是综合了悖论性质的历史与文学、虚构与现实,它试图打开的是消解了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认知论模式的生活经验世界——高密东北乡:“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就这样,莫言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创造出了与“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可以并肩的熠熠生辉的“高密东北乡”,让读者通过对文本的创造性阅读,达到类似于民族志文本对“日常经验的唤起”*﹝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77页。的最终目的。
三、嵌在文本中的立场:文学与历史背后的哲学
尽管文学与故事及其讲述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衰微,极易使人忽视讲故事的人在口述传统中的神圣地位以及在历史文献建构中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讲故事的人”,莫言在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漫步仍然彰显了虚构的真实与文学化的历史的文化建构功能,这种文化建构表面上指向日常生活经验的唤起;但是从文本接受的角度看,莫言的小说超出了这一功能,而且指向铭写民族记忆、呈现民族国家形象、在作为他者的世界性语境中塑造自我。《红高粱》中的这种潜在的文本功能经由张艺谋的电影改编之后,通过国际化途径走向世界,并将这种潜隐于文本之中的意识形态激活了。如果把《红高粱》看作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文化符号显然可以看作是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形象呈现的寓言。作为文本的《红高粱》本身所蕴含的国际化符码形式(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与可交际性特征(人类性意识形态追求),及其中所包含的生命冲动与力量(我爷爷和我奶奶),恰好使其成为通往世界化的中国文化的最早代表。
如果说“每一种有关实在的历史记述中,确实都显示出一种不可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30页。,那么在《红高粱》中,人类性的意识形态追求便是其关键的符码。首先,从《红高粱》以及后来的《酒国》《丰乳肥臀》以及《生死疲劳》《蛙》等小说中不难看出,莫言的文化建构欲望是建立在强烈的解构与颠覆既定文化模式的基础上的。从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来看,经历了“文革”历史创伤之后的当代文学的叙事逻辑首先是对创伤的描述,其次是对创伤之由的反思,并在反思之中走进文化寻根。莫言的早期创作无疑受到这种集体创作情结的影响,但莫言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执著于对历史、文化的劣根性的描述与探讨,而在于对二元思维方式的超越。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政治,莫言都表现出一种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人类性思维模式。如对于历史,他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历史的这种随意性与虚构性,是莫言以一种夸张的反讽与虚幻现实主义重构历史情境的基础。当然,在这个层面上说,莫言追求的并非是循规蹈矩的历史讲述,而是追求独创性的历史书写。换句话说,莫言的态度是以一种解构的观念看待历史编纂以及历史传播。同样,对于阶级对立的问题,莫言也表现出一种超越性观点。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经典论述,“一切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但是,莫言的小说淡化了阶级意识,站在一种人类性的立场上写作。“从《红高粱》开始我就在做这样的反叛,就想在小说里面淡化这种阶级的意识,把人作为自己描写的最终极的目的,不是站在这个阶级或是那个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莫言:《用耳朵阅读》,第255页。正因为站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立场上,莫言因而看到了不同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表现出人类的残酷性。因此,《红高粱家族》虽然写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土匪,但是莫言没有按照既定的思维模式对这些有着不同政治欲求的团体进行是非评判,而是按照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所能表现出的性格逻辑,塑造人物,推动情节,里面夹杂的作家的政治观点极少。因为在莫言看来,《红高粱》所展示的高密东北乡的乡村社会,虽然可以从阶级、集团的角度做出种种划分,但所有斗争说到底其实都是农民子弟和农民子弟打仗。当然,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是为了更深切地考察战争中所呈现出来(在平时被遮蔽)的人性恶,莫言摒弃了阶级、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而是把它“抽象化为一场试验,表现人的善恶”*莫言:《碎语文学》,第333页。。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小说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具备人类性因素的故事,而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奔放的生存方式,是敢爱敢恨的生命体验。这种奔放而自由的生命体验是建立在如何建构自我,以便在他者面前呈现出自我形象的层面上表现的。因此,莫言在《红高粱》中不止一次说到“种的退化”,而且在《奇死》的结尾反复强调自己对“杂种高粱”的痛恨,以及对“血海一样的红高粱”的赞美。这种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爷爷”、“我奶奶”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悍的生命力的礼赞,但是吊诡的是,莫言这里的“杂种理论”不管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还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说,都与莫言自身的表达相违背。即,生物学意义上的杂种生物,抑或文化学意义上的杂种文化,恰恰是最具强大生命力的;而所谓的纯种的生物或者文化,恰恰会由于亲缘关系而走向没落——这一点不但为生物遗传学所证明,同样为文化理论所证明。况且,莫言的小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杂糅的结果。那么,莫言为什么这样表述呢?我们认为,在莫言的知识性错误的表象之下,是作家深层心理中的“自我”(本土文化)呈现的欲望使然,即在他者面前以一种强悍的方式呈现自我,从而获取他者文化的认同。因为说到底,文学讲述历史的目的最终还是指向现实。无论作家以何种方式讲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呈现为平面镜还是哈哈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最终也要表达文化认同、身份确证。如果从事件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红高粱》的电影改编及其走向世界所带来的接受美学效应,那么我们未尝不能把《红高粱》看作是莫言站在一种人类性的立场上,模糊了现实与历史、阶级与情感的一种讲述,这种讲述并没有实际的功利的对象,其旨归在于定位城市化、现代化及全球化袭来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自我形象如何表征。
总之,《红高粱》所开启的文学讲述历史的模式,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莫言以“世界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经验,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如何表述“自我”,如何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发声,如何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与整个人类的生存经验汇聚起来,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曾庆江)
TheRedSorghum: the Source, Method and Standpoint of Virtual Realism
WANG Xing-wen
(School of Humanities,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Guyuan 756000,China)
TheRedSorghumis Mo Yan’s initial work written in the manner of virtual realism.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aesthetic form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western fiction and magic realism, Mo Yan has found a unique approach to historical reality and literary fiction, thus having constituted his consistent human position in his novels. Mo Yan’s creation method of narrating “Chinese stories” through the “world language” is highly enlightening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TheRedSorghum; virtual realism;space forms; the encoded mode; the view of history
宁夏高校项目“当代小说中的历史书写研究”(项目编号:NGY2015104)
2016-10-22
王兴文(1972-),男,甘肃靖远人,文学博士,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
A
1674-5310(2017)03-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