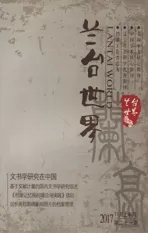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天师道的流变
2017-03-11张紫云
张紫云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15000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天师道的流变
张紫云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150000)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天师道分化革新的大发展时代。它从一个不被主流思想认同并与皇权发生激烈冲突试图政教合一的民间信仰,转变为封建皇权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一部分。是其在与皇权长期斗争处于劣势条件下,在存亡之间选择的一种屈服化的折中表现,也是一种奉道阶级不断上层化,使其向圣洁化、官方化的自觉靠拢。
天师道皇权魏晋南北朝
K291/29
A
2017-06-19
天师道“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1],是道教的前身,其内在的政治思想丰富、严整而且影响深远。天师道源于殷商时期的鬼神崇拜,战国时期的方仙信仰,两汉时期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并一定程度上受到巴蜀地区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诞生之时起,天师道就是一把双刃剑,既为统治者所利用以维护皇权,又被下层民众作为推翻旧政权的精神旗帜。这一时期的天师道,无论在统治阶层还是民间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皇权相互影响深远。前人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天师道教徒活动的个案的细致研究,天师道派别分化和教义调整及经典的解读。如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中对西晋末四大天师教徒叛乱的阐述[2];小林正美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出发,在《六朝道教史研究》中对天师道不同教派在不同时期的分化情况,及教典进行详细解读研究等[3]。本文尝试从曹魏时期溯源天师教的发展传播,运用福柯的“权利、知识、话语”思想,从绝对皇权视角出发来对天师道与皇权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对天师道与皇权相互接纳认同的意图进行比较研究,以求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探寻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与皇权的内在关系。
一、早期天师道的创立与皇权的冲突
天师道的早期源起代表主要是东汉末年形成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东汉末年,张角依靠黄老道创“太平道”,利用“妖术教授”、“符水咒说以疗病”[4]迅速扩大影响力和民间信众团体,以“三十六方”组织信仰者,用“各立渠帅”的方式将教团转化为军团,短短十余年,募集教众数十万,发动黄巾起义,“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5]。起义最终遭到东汉政权镇压而失败,“太平道”并未形成有体系的宗教系统。
张陵于汉顺帝时期创五斗米道(天师正一道),经其子张衡、孙张鲁的承前启后,有了科教金典并教区组织也遍布巴蜀,使早期天师道教义、组织逐渐趋于体系化。张鲁时期的五斗米道,发展兴旺,他“以鬼道渐信于益州牧刘焉”,“巴、汉夷民多信之”[6],使五斗米教遍行于汉中、巴、蜀。与张鲁同时期在汉中还活动着由张修领导的五斗米教团,修创“请祷法”用“三官手书”为信众疗疾,进一步丰富了早期天师道的教义内涵。张鲁被刘焉拜为督义司马,统兵据汉中,杀张修夺其信众,融合两支,在汉中以教代政,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教团王国。同时,张鲁在汉中普行宽惠之政,奉老子为教主,以黄老治国。设长吏,以天师道祭酒为治。对于犯法者,原谅三次不改者,才施以刑罚。这使以张鲁为首的天师道政权,在动乱割据民不聊生的汉末,俨然成为了一个民夷所向往的理想国度。
由此可见,早期天师道利用宗教教团,通过建立严格的教团组织、秩序,构建信仰体系。与民以利,巩固信众信仰,扩大信众数量,使教众只听命于教主,逐渐使教团走向政、教、军合一,以对抗世俗政治权利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道路。当惯于与民争利的统治阶级发现自己的现实利益及政权遭到极大威胁时便会对威胁源头采取严厉的防范和打击措施。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被当权者视为“妖道”,教团领袖及信众被视为“乱臣贼子”,暴风骤雨般的太平道黄巾军起义遭到残酷的武力征讨,被彻底消灭。五斗米道看似被曹魏政权招安,以礼相待,其实不过是善于权谋的曹操假借“养性”之名,不费一兵一卒,将对政权有潜在威胁的方士圈养在身边,严加管控,同时采取笼络上层(曹氏与张氏结为姻亲)、移民北迁等怀柔手段,逐渐将其瓦解。到了魏明帝时期,曹魏更是抛开以往的含蓄,明令取缔一切民间宗教活动。
无论是早期五斗米道的“领户化民”,还是太平道的以“黄天”取“苍天”,它们都打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这无疑是对专治封建集权王朝的一种绝对挑衅。在其羽翼未丰时选择与主流意识对立,被当时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精英士大夫所不齿,使其难以进入上层精英的思想世界,不得不渐渐边缘化、秘密化或民间化。这注定了早期天师道教权不可能与世俗皇权争势的结局。
二、皇权因素对天师道北迁南移分化革新的影响
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拔汉中民数万以实长安及三辅”[7],天师道开始北迁。除大量教众外,不少中上教职人员也北徙邺城。张鲁及其五子虽皆封侯,但都迁居邺城。
由于北迁,天师道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教团内的中上层人物,由于曹魏的怀柔厚待封官晋爵,开始有了一定政治地位,有了接触统治贵族当权阶层机会,并迎合其需求,向他们输送以养生、丹药、房中术等为主的道教内容,从而得到一批统治特权阶级奉道者的支持。另一部分普通教众,则随着北迁将五斗米教带到徙居之地,将五斗米教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总的来说,曹魏时期北迁的天师道,脱离了原巴、蜀易滋生原始鬼神崇拜的特殊封闭的地域环境,受中原文化和正统绝对皇权意识的影响,道义发展大部分与主流意识相融合,变原始义理,日趋正统。
两晋时期,天师道向统治阶级上层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天师道从北方传入江南,最初始于西晋灭吴,“晋武帝平吴后,道陵经法流至江左”[8]。两晋相交,北方人祸战乱不断,天师道随“永嘉南渡”进入江左地区,随之大批江左大族开始成为天师道信仰者。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提到:“东晋南北朝的许多门阀士族,都是信奉天师道世家,据我们初步统计,当时的北方大士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冯翊寇氏、京兆韦氏、天水尹氏,南方侨姓大士族琅琊王氏、谯国桓氏,吴姓士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吴兴沈氏、晋陵华氏、会稽孔氏、钱唐杜氏、吴郡陆氏、孙氏(孙吴后裔)等等,这些家族中都有信教的。”[9]这些原本崇儒的高门大姓转而奉道,无疑会在不自觉中,将名教义理带入,使天师道进一步从蒙昧民间宗教中脱离,更加适应奉道的统治阶级需要。
天师道南迁,并不代表其在北方的断绝。南北朝时期,天师道在南、北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使天师道得到当权者的认可,从民间进入殿堂,就必须进一步自我革新,“清整道教”应运而生。在北魏寇谦之和南朝陆修静的清整革新下,天师道逐渐跳出“三张旧制”形成了北方重仪轨,南方重义理的新天师道。
天师道随政权的迁徙,和不断为迎合统治上层需要所进行的内部教理调整、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宗教与世俗皇权由对立斗争到屈服迎合的发展过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天师道摆脱了单纯原始鬼神信仰和威胁皇权的教团组织形式的桎梏。其内部分化出的不同派别(上清、灵宝),通过各自的充实、发展,再走向融合,也使天师道逐渐走出了“淆乱”和“混浊”。对其由民间信仰提升到官方宗教信仰产生了重要的刺激作用。
三、新天师道与皇权契合度的不断加强
在中国古代,皇权不仅把持着现实政治,而且也要控制虚幻的世界。绝对君主权利,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天师道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想要得到发展和弘扬就必须得到皇权的青睐,为了博得青睐,就必须进行自我清整。
魏晋以来,天师道的奉道群体中,不断涌入豪门大姓,这些来自统治阶层的奉道者,不仅把天师道带入社会上层,也加速了天师道内部清整。可以看到,在这一整顿过程中,天师道抛弃了主张干预世俗事物的“三张旧法”,放弃了仿现实政权的教团组织方式,避免宗教权威与世俗政权重叠,威胁皇权,给统治阶层带来不安。大量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教徒,也参与清整,甚至多数人成为内部清整的中坚力量和主要领导者,他们借仙人之口提醒教徒说过去的道教中,“不知道之根本,真伪所出,但竞贪高世,更相贵贱,违道叛德,欲随人意,人意乐乱,使张角黄巾作乱,汝曹知角何人?自是以来,死者为几千万人耶”[10]。这样一来,使清整后的新天师道越来越靠近上层士大夫伦理取向,越来越与皇权相契合。其与皇权契合度加强,最具有代表性的直接反映有以下几点。
1.“援儒入道”维护纲常,助人主驭民。天师道在其清整的过程中,多由士族奉道者领导革新,士族在奉道前多崇儒,坚守经学传统,所以在清整过程中多将名教思想融入天师道。魏晋时期的儒学虽已从汉代的神坛上跌落,但其对统治阶层的影响仍不可小觑。东晋句容士族葛洪,系统总结了神仙方术理论,“援儒入道”,极大地丰富了天师道的思想内容。他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伦理结合起来,宣扬道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恕信义和顺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将天师道由传统的“度身”转化为“度人”。北魏,冯翊士族出生的嵩山道士寇谦之,在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支持下,主动放弃了旧天师道中“租米钱税”与“男女合气”之说,前者消除了与皇权的经济对立,后者消除了名教对其的伦理口实。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顺民”思想,使天师道理论更为统治阶级接受。南朝道士陆修静,在对天师道的改革中提出“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思想,他还反对“淫祀”以巩固世俗皇权的权威性来确保天师道的合法性。南朝的天师道与朝廷皇权的关系愈发紧密,成为南朝政权驾驭臣民的重器。
2.“君权神授”强化皇权,助人主立威。寇谦之在对天师道的改革中,明确将“尊王”纳入教理之中,他把“符箓授命”作为世俗皇权神授的依据。他还进一步神化北魏太武帝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授符书,以彰圣德”[11]。魏太武帝欣然接受,遂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寇谦之把太武帝神化为“真君”不仅体现了天师道“肉身成道”仙凡一体的信仰,更使天师道“符箓授命”成为皇权神授的重要理论基础,帮助封建君主确立统治威信,得到封建帝王的赏识与推崇,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从此确立了天师道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宗教地位。
3.“佐国扶命”天师入世,助人主理政。“佐国扶命”[12]的政道思想,是天师道在南北朝时期为适应封建皇权需要而提出的。它强调“圣神即世俗,世俗即圣神”的“道俗合一”理论,主张用“尊王”、“尊礼”实现皇权在宗教与世俗俩个领域中的至上性。寇谦之假借太上老君之口“谦之汝就系天师正位,并教生民佐国扶命,勤理道法,断发黄赤,以诸官祭酒之官,校人治箓符契,取人金银财帛,众杂跪愿,尽皆断禁”[13]。他推行新法,使天师道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支持,在北魏极盛。其本人也贵为当朝国师,辅助国政,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协助魏太武帝屡破敌军,成为魏太武帝重要的幕僚。南朝陶弘景,承陆修静,进一步发展了天师道,时人称其“山中宰相”。他隐居奉道,却“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梁武帝萧衍与陶弘景交情颇深,深知其才能,几次“征仕”都被他拒绝了。梁武帝只好常将国家大事写成信件,派人送到曲山请教陶弘景,陶弘景看重多年好友的情谊,就以书信为梁武帝指点政策。陶弘景虽身在方外,却为帝王辅政,甚至萧梁国号“梁”都为其所定,可见他对朝政决策影响绝非一般。
可见自我革新清整后的天师道,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及天师们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使天师道变得更加符合当时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为统治阶级自我正名和维护传统道德规范秩序的新力量。天师道与皇权的契合度进一步加强。
四、天师道与皇权相互认同的动因
天师道的内部清整和其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奉道阶层不断上层化,都反映着天师道与皇权相互之间的不断认同。对天师道的发展而言,在绝对皇权意识主导的社会条件下,“如何使它的知识与技术合理化,如何使它的组织和形式合法化,如何使它的道德与律令神圣化”[14],这都需要通过得到皇权的认同而实现。对皇权来说,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争乱之世,虽有着英雄不论出处,称王不论正统的现实,可在儒家文化浸润百年之久的中原大地,君主为自己正名,强调自身皇权的合法性,始终都是为统治者所热衷的。天师道通过不断革新,主动迎合式地向皇权靠拢,使改革后的天师道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更有利于皇权,这样便得到了皇权的回应,使二者相互认同感日益增强。
1.儒学衰落奉道阶级的变化。西晋以后,天下进入大争之世。长期处在封建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学,显得是治世有余,而乱世不足。处于统治阶层的门阀士族,纷纷转而奉道,士族的加入使得天师道的奉道者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其由普通教徒信奉的教义粗陋的民间信仰逐渐圣洁化,向以上层贵族为主的官方信仰发展。加速了天师道内部清整运动,而引领这场“清整运动”的主要代表——南“陆”北“寇”,均出自士族阶层,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天师道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改革的方向,使其与皇权更为贴合,成为继儒学衰败后,统治阶层维护统治权利的又一思想利器。
2.法术丹药对统治阶级的吸引。法术,是信徒信仰的主要来源,大部分信徒奉道都是起源于道法的施行。道士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打着方术道法的旗号,帮助统治阶级祈福禳祸。通过天师道传统的服食之法演变为外丹之术来满足统治阶级长生续命的愿望,使“秦皇汉武,甘心不息”[15]。寇谦之屡次运用“道术”帮助魏太武帝破敌,使得太武帝对天师道笃信至深。魏晋“服散”之风大盛,更是士族潮流。《抱朴子·金丹篇》曰:“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练人身体,故能令不老不死。”自西汉方士创制金丹后,帝王、士族均以炼丹为事,东晋哀帝司马丕,“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16]。
3.终末论与罪业意识维护社会规范。天师道的“终末论”吸收了佛教的劫运观念,认为在“末世垂及”的时代,地上生民只有立坛宇朝夕礼拜神灵,功德及于上世,并能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才可能成为“真君种民”。这种理论自东晋末开始被教徒广为信奉,为了得到“种民”、“种臣”的资格,社会各阶层的奉道者们都在日常生活中注重道德的善行,以期逃脱末世灾劫。同时,寇谦之在对教义的改革中也加入了“祸福观念”,宣扬人生罪福皆由前世宿业所致。谓今世富贵乃由前世行业,积善愿念所致;而今生魂神苦痛,则皆由前世作恶所致。若今世再作恶,则又将报在下世。这无疑对统治阶层来说是“顺民”思想的变相推行。
4.“佛道之争”到“灭佛崇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并存,其中佛道之争尤为激烈。统治者在“崇佛”还是“崇道”的问题上虽各有选择,但其选择的出发点几乎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维护统治,只有极少数单纯为信仰。南朝齐顾欢提出的“三破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佛教在其教团组织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一面,而清整后的天师道摒弃了之前五斗米“天师化民”与世俗皇权相对立的教团组织形式,显然比佛教更适应统治者要求。特别是释道安提出的“沙门不敬王者”更是与绝对皇权意识相背离,这一点上天师道与佛教不同,天师道戒律的改革受儒家影响,将忠孝礼仪等宗法伦理道德作为道士必须遵守的教规,这样的“忠君”思想在天师道的戒律中也有体现。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毁灭性的“佛难”,却鲜有程度如灭佛般的“道难”。这无疑体现了统治者的认同和选择。
通过以上对天师道与皇权,由冲突对立到相互认同扶持内在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封建皇权至上的社会条件下,皇权掌握着一切“权力、知识、话语”。宗教要想取得合法性,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必然先要取得皇权的认同。竭尽全力与皇权相适应,是其谋求进一步发展,在主流社会站稳脚跟的唯一选择。这一时期的天师道,通过先对皇权认同并配合教义、仪轨、义理、教团组织形式的不断改革,继而也得到了皇权的认同,从而获得了优于先代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 刘勰.灭惑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M].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52.
[2]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实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3]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4] 陈寿.三国志.魏书.一.张鲁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264.
[5] 范晔.后汉书.第四册.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299.
[6] 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
[7] 陈寿.三国志(上).魏书卷十五.张既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2:323.
[8] 玄嶷·甄正论·卷上.
[9]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M]//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64-183.
[10]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经:引·道藏·第十八册:236.
[11] 魏书.第五册.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3053.
[12] 陆先生道门科略·道藏要籍选刊第八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77.
[13] 魏书·第五册·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52.
[14]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3:27.
[15] 魏书.第五册.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48
[16]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哀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8-209.
The Change and Relationship of Imperial Power and Tianshi Daoism in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Zhang Ziyun
(History and Culture Tourism Colleg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0,China)
The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s the great development era of the division and innovation of Tianshi Daoism.It turned from a folk religion that was not recognized by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severely conflicted with imperial power,trying to achieve integ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into a part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ethical notion that has been recognized by feudal imperial power.It was a compromise when facing the choice between survival and death under the unfavorable conditions of long-term struggle with the imperial power,also a kind of conscious approach to holiness and officialization by Daoists.
Tianshi Daoist;imperial power;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