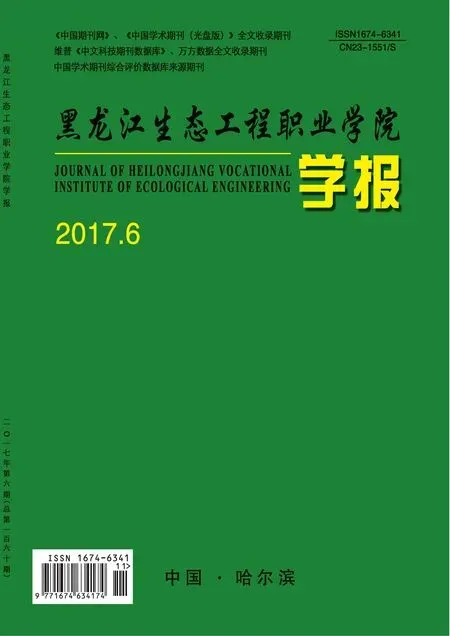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文献学中的应用
2017-03-10杨茜茜
杨茜茜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文献学中的应用
杨茜茜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从事文献研究不仅需要我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还需要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文献的有效方法之一,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使研究内容更清晰,结论更准确。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文献学
我国对于古典文献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从孔子整理六经,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再到后来校雠学产生,用的都是我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法。现代不少关于文献学的著作基本上是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延伸和总结①,都“仍以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为主要内容,继续围绕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文献整理、鉴别或翻译的基本知识,文献的源流、积聚、散佚及典籍体式、介绍诸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或专题性研究”。[1]
随着科技进步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停留在传统模式,我们也需要把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文献学中。新世纪以来,也有一些文献学著作促进了文献学研究的多元化②。
本文主要从哲学层面探讨两种研究方法在文献学中的应用。这两种研究方法分别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1 概念及意义
1.1 概念
根据《教育经济学原理》,“定性研究,就是对于事物质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质是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特有的规定性。此物之所以为此物,此物之所以区别于他物,就是由于它具有质的规定性。”[2]用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定性研究针对的是“质”方面的分析。定性分析经常被运用于对事物下定义的研究中,它主要是解决“有没有”或“是不是”的问题。
郝大海的《调查研究方法》说:“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事物的量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构成事物的共同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等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定量研究是对事物的这些量的规定性的分析与把握。”[3]用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从量的关系上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出更为精确的科学的说明。”[4]定量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量”方面的剖析,主要解决“有多少”或者“占多少”的问题。
1.2 意义
定性研究通过传统的经验总结和反复的哲学思考,为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和应有的方向。通俗来讲,即是深入文献本体,利用传统方法,进一步探究文献之所以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定量研究打破定性研究的固有的哲学思考模式和通常的思维格局,促进了文献研究的科学化与技术化。通过统计与对比,将相关文献技术化、数字化,提高了研究的精准度。
然而,无论是只看重定性研究,还是只运用定量研究,其视野都是比较狭窄的,唯有打破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有效地解决文献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2 二者关系及其在文献学中的应用
2.1 二者关系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正如哲学中“质”与“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量变和质变是辩证统一的。第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第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第三,质变体现和巩固量变的成果,并为新的量变开拓道路。[4]
由此类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也应如此。整个过程大抵可能描述为:定性—定量—定性,即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也是定量研究的结论,也就是朱佩娴认为的“一般而言,H定性研究收集到的 ‘属性’ 信息,能回答 ‘有无’或 ‘是否’ 的问题; 而定量研究收集到的‘数量’信息,能回答 ‘多少’ 或 ‘大小’ 的问题”。[5]另一方面,质和量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所以应该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使内容更清晰,结论更准确。
2.2 二者关系在文献学中的应用方法
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因此,在做文献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密切结合文献学的发展状况,科学地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文献学方法论的研究推入理性的、科学的研究轨道”。[6]而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时,也需要具体的方法,“往往要采用多种比较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比较,从而在整体上全面认识研究对象”。[7]下面举两个例子来介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如何在文献学中应用。
2.2.1 《桧风·匪风》“匪”字的理解
关于《诗经·桧风·匪风》中“匪”字,诗旨不同,对“匪”的理解也不同。我们可以列举并加以比较,最后引用权威说法来确定“匪”字的含义。在《四库全书》相关书籍所涉及的内容中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寄情于景,一种是触景生情,还有一种是情景交融③。三种诗旨对“匪”字的解释有三种:一是通“非”,二是“不是”,三是“彼”。
第一种情况,“匪”当“非”讲。“非”字,在诗经正文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无非无仪”(《小雅·斯干》),这里“非”是动词“违背”。第二次是“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这里“非”是否定副词“不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用法。而在以上论述中的“非古(有道、平常、不可谓)之风,非古(有道、平常、不可谓)之车”,显然是把“非”当作了形容词。“非”当形容词在《左传》中出现过一例,但《诗经》到《左传》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所以《诗经》中不可能有“非”的形容词用法。
第二种情况,“匪”当“不是”讲。如《毛诗李黄集解》中“风则发,今非风也而发。车则偈,今非车也而偈。盖言其政之乱,而人之不安也”,根据吕叔湘《文言虚字》:“不是,同‘非’”[8],“匪”和“非”当“不是”讲的时候用法一样。但此种用法在《诗经》中只有“匪+动词谓语”或“匪+主谓短语”两种用法[9],如“匪报也”(《卫风·木瓜》),“匪女之为美”(《邶风·静女》)。而“风发兮”是个句子,所以“非”和“匪”当“不是”讲,在这里都不成立。
所以,经过统计和比较,“匪”应当“彼”讲。“匪”当“彼”讲,在《经传释词》中就有“‘匪风发兮,匪车偈兮’言彼风动发发然,彼车之驱偈偈然也”[10],与主旨二吻合。
2.2.2 《桧风·匪风》中“发”和“偈”的理解
《诗经·桧风·匪风》中“发”和“偈”表示声音还是状态,毛传将“发发飘风,非有道之风”[11]解释成“飘风”,在《小雅·蓼莪》“南山烈烈,飘风发发”一句,毛传谓“发发,疾貌”。可知毛传中“发”字表示状态。毛传中关于“偈”字的解释是“偈偈疾驱,非有道之车”,可知“偈”字也表示状态。在毛传中此二字算是在一个频道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字的理解产生了变化。《诗说》中把“发”说成是“震动之声”,《诗经注析》和《诗经今注》都认为“发”字是风声;杨树达把“偈”字理解成车声,还用音韵学作了分析。由于毛传距《诗经》年代较近,所以猜想毛传解释当正确。我们可以通过列举并加以比较来证明两字含义:
桧风·匪风
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风飘兮。匪车嘌兮。顾瞻周道。中心吊兮。
谁能亨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句式为 A1 B1 C D1
A2 B2 C D2
其他
可以在毛诗中找到类似句式的诗进行类比分析。如:
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郑风·子衿》前两章句式和《桧风·匪风》前两章句式类似。
“矜”,毛传:“青衿,青领也。”就是“衣领”;《诗经注析》:“衿,「礻金」的假借字,亦作襟,衣领”;《诗经今注》:“衿,古代衣服的交领”,都是名词“衣领”的意思。
“佩”,毛传:“佩,佩玉也。”《诗经注析》:“佩,佩玉。”《诗经今注》:“佩,佩玉。”都是名词“佩玉”的意思。“衿”和“佩”都是名词,且都是与衣服配饰相关。 “心”与“思”都是名词,“心”就是“思”,“思”就是“心”。
“嗣”,毛传:“嗣,习也。” “来”,毛传:“不来者,言不一来也” “嗣”都是动词,有“寄”的意思。一“寄”一“来”,都是动词,属于同类。
据上可知:“衿”和“佩”,“心”和“思”,“嗣”和“来”都属于同类。
还有一例:
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至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此诗前两章句式与《桧风·匪风》前两章句式类似。在此,若没有异议就不再赘述各个注解出处。“楚”与“棘”都是树;“野”与“域”都是地点;关于“处”,《诗经注析》:“有人将这句译为:谁伴他孤独地长眠于地下呢。”这样“处”与“息”都是动词,都有寝息的意思。
由以上种种可以推知:A1与A2句是同一个意思,B1与B2是同一个意思,D1与D2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发”与“飘”同义,“偈”与“嘌”同义。“飘”,毛传:“回风为飘。”表示状态;《说文解字》:“嘌,疾也。”[12]也表状态,所以,“发”和“偈”亦表状态。
3 结语
从上述二例不难看出,文献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在具体应用时,将研究对象列举加以比较后,往往需要一定的文献功底方能下结论,这又需要与我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法(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相呼应。从事文献学研究既要遵循传统的文献研究法,又要尽可能地应用多门相关学科可借鉴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和网络技术条件,加强文献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文献学的应用研究,以适应时代需求。
注释:
①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年齐鲁书社版)、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1994年杭州大学出版社版)、程千帆和徐有富合著的《校雠广义》(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等等。
②邱均平的《文献计量学》(1988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王崇德的《文献计量学教程》(1990年南开大学出版社)等。
③《四库全书》中关于《匪风·桧风》诗旨的说法,有十九处是作者心中先有情,然后将这天下不尊周之政令的忧思寄托到了并非亲眼所见的事物上,即寄情于景;八处提到《桧风·匪风》诗旨的说法,都是作者在适周之路上亲眼所见风发、车偈,风飘、车嘌,生发出的怀古和伤今之情,即触景生情;有八处很明显是主旨一和主旨二的合体,即情景交融。
[1]王丁.我国文献学研究的特点与前景展望[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4):61.
[2]张蓉.教育经济学原理[M].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5(10):18.
[3]郝大海.调查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9.
[4]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6.
[5]朱佩娴.“定量研究”需三思[N].人民日报,2011-09-15:7.
[6]王瑞珍.我国文献学研究方法之探析[J].新世纪图书馆,2007(5):64.
[7]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0):232.
[8]吕叔湘.文言虚字[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215.
[9]张华.先前汉语的“非”和“匪”研究[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4).
[10]王引之.经传释词[M].北京:中华书局,1958(5):228.
[11]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45.
[1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2):32.
责任编辑:李增华
TheApplicationofQualitativeResearchandQuantitativeResearchinLiteratureScience
YANG XI-x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China)
I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not only need our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but also need multi angl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re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study literature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The two will be closely integrated in order to make the content more clear, more accurate conclusions.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Literature science
10.3969/j.issn.1674-6341.2017.06.053
G250
A
1674-6341(2017)06-0146-03
2017-09-07
杨茜茜(1991—),女,山西榆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学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