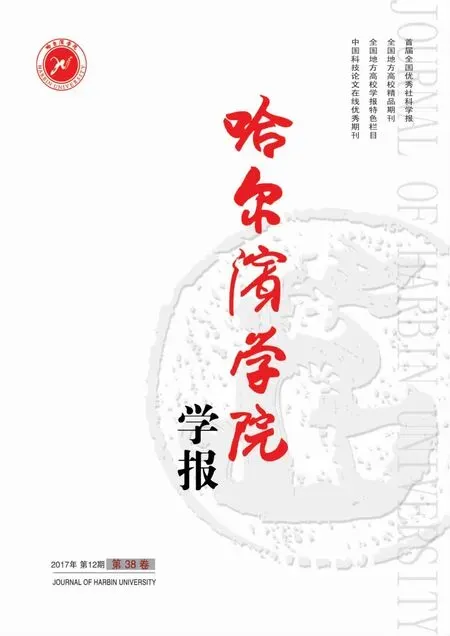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迟暮”意识
2017-03-10郭大章
郭大章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迟暮”意识
郭大章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晚年的鲁迅,由于病痛缠身、处境艰难等原因,对自己一生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产生了质疑。鲁迅在无奈和悲凉中,产生了一种无法避免的“迟暮”意识,这种意识也呈现在他晚年的作品《故事新编》中,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莫大的悲哀。
《故事新编》;迟暮意识;病痛;晚年心态
鲁迅小说《奔月》中,后羿在嫦娥丢下他独自飞升以后,说了一句话:“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此话虽说是后羿对自身的疑问,但也未尝不可看作是一种隐喻,是鲁迅在借后羿之口自况。而类似于这样的隐喻,在其作品《故事新编》中,还有不少:“作为神的女娲,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疲乏”;“伯夷和叔齐在华山中,用野果和树叶来送自己的残年”;“老子也是一个没有牙齿,老花眼睛细得好像一条线,扶着拄杖的老头子了”,等等。鲁迅会在一部小说中屡屡出现这些带着疑问的隐喻,从某种程度上隐射出了鲁迅在《故事新编》中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迟暮”意识。
鲁迅的《故事新编》基本完成于1926-1935这个时间段,这正是鲁迅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鲁迅人生中最为失意的时期:兄弟失和,疾病折磨,早年的理想遭遇到了最为严重的阻抑,各种流言和政敌的包围打击等。1925年,鲁迅肺病复发,遭人排挤从而颠沛流离,正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鲁迅将这种困境和苦闷,投射到创作中,便化作了《奔月》中的“迟暮”意识。后羿是一个英勇而伟大的神,但鲁迅却“偏偏选择了后弈辉煌人生之后的负面。读者眼前的后弈已经沦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为生活的奔波者,整日碌碌无为,不但夫妻失和,暗地里还遭到弟子逢蒙的射杀与诅咒,满身豪气脱尽,及至于嫦娥盗药升天,家破人散,英雄迟暮,岌岌可危,走向了人生末路。”[1]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探索和拯救中华民族精神上的“恶疾”,但各种恶疾却似魔咒一般笼罩和纠缠着鲁迅的晚年。“1936年,病发,自十八日至六月一日日记均有发热记载,六月六日至三十日卧床不起,日记中断。1936年七月一日恢复日记,至逝世前一日绝笔。除少数几日外,每日日记均有病情或治疗情况。”[2]“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2]这是鲁迅在1936年6月30日中断日记后,于高热中补记的内容,而此时,距鲁迅写完《故事新编》中的《采薇》《出关》《起死》等篇章也就刚刚过去半年而已,而距鲁迅离我们而去,也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鲁迅的学生增田涉也这样描述当年所见的鲁迅:“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3]
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病痛对鲁迅的打击是多么的沉重,而鲁迅自己又是多么的无奈和痛苦甚至悲凉,病痛直接影响到了鲁迅的心境,使他产生一种浓厚的生命迟暮意识,这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2]鲁迅暮年的大病,已在疯狂地吞噬着他的生命力……忧郁阴暗和颓唐的精神特征,都表明鲁迅已切实地在面对死亡了。此刻,生对于鲁迅来说仅只是处于“无欲望状态”,他的心境忽明忽暗。生的欲望和死的绝望,生的艰辛与死的超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任何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其思想都应是内省和沉重的,而忧郁阴暗和颓唐,其实正是生命迟暮意识的外在表现,而且也是生命迟暮意识的延伸。作为一个内心世界敏感而丰富的作家,鲁迅的这种迟暮意识,则不可避免的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和死亡梦魇。
任何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都无可避免地会在无意识之中把自身的影子投射进去,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符合作家当时心境的内在风格和气质,鲁迅自然也不会例外。《故事新编》成书于其去世的前一年,而其中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完成于他的晚年,于病痛折磨下写就的故事,大多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迟暮意识。
在《奔月》中,作为射日英雄的后羿,却天天为讨好老婆和食物而发愁,经常唉声叹气,回想往日的英勇:“只有羿呆呆地留在堂屋里,靠壁坐下,听着厨房里柴草爆炸的声音……弩机,长剑,短剑,便都在昏暗的灯光中出现。”[2]在这里,鲁迅把后羿昔日的英勇形象,设置于“堆满柴草的厨房”这么一个琐碎的环境里,把后羿以往所用的弓和剑等武器,用“昏暗的灯光”来映衬,这样,就造成一种强烈的荒诞感,而在这种荒诞中,我们所体会到的却正是后羿(鲁迅)那无可奈何的迟暮意识。“羿看了一眼,就低了头,叹一口气……他于是回想当年的食物……‘唉’,他不觉叹息。”在《奔月》里,后羿经常处于“回想”状态,总有意无意地提到自己的当年之勇,并且还总是在这种“回想”中发出屡屡的叹息声,这意味着人已经“老”了,失却了当年的盛气,而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迟暮”意识。
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飕的一声,——只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本来对面是虽然受了三枝箭,应该都聚在一处的,因为箭箭相衔,不差丝发。但他为必中起见,这时却将手微微一动,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使女们发一声喊,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他们都默着,各人看各人的脸。羿懒懒地将射日弓靠在堂门上,走进屋里去。使女们也一齐跟着他。[2]
这里,后羿的这种生命“迟暮”,已经完全赤裸裸的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昔日的射日英雄,现在竟然连月亮都射不下来,而且月亮似乎还有意示威,使得后羿在使女们面前威风全无,全都静默着,而后羿也无可奈何的收起了射日弓,坐下叹了一口气。在后羿的这声叹息中,那英雄暮年的“迟暮”意识也表露无遗。结合鲁迅晚年时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后羿的这种英雄“迟暮”,又何尝不是鲁迅自身的一种“迟暮”呢!
当然,不只是后羿,鲁迅的这种“迟暮”意识,在《故事新编》的其他篇章里也或多或少有所体现:疲乏的女娲;风烛残年的伯夷和叔齐;没有牙齿,扶着拄杖的老子;像一个老牌乞丐的墨子;黑瘦面皮,长着花白络腮胡子的庄子,等等。一部短短的《故事新编》,鲁迅将众多的真假“英雄”都刻画成了这么一些带着“迟暮”形象的老者,看似无意而为,实则正有意无意地透露出鲁迅暮年那无可奈何的“迟暮”意识。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迟暮”意识,当然并不仅仅和晚年的身体状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鲁迅晚年特殊的精神状态。1926年8月29日,鲁迅抵达上海,作短暂停留后,于9月1日前往厦门。由于厌弃厦门的乌烟瘴气和死气沉沉,于1927年1月又到了广州,但由于当时的时局之变,于9月底又前往上海,并在此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岁月而长眠于此。
“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2]这是1934年1月11日鲁迅致山本初枝的信,在这封信里,鲁迅再次提到一个词——老了,而且是“姑且活下去”。当然,鲁迅这里的“姑且活下去”不能等同于消极的逃避,而应该是积极的但又无奈的面对,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把鲁迅的这种状态称之为“姑活”。这种“姑活”心态在鲁迅蛰居上海期间,是很强烈的,可以说是鲁迅在上海期间的一种恒常心态。之所有这种心态,是源于鲁迅的两段经历:一是离寓避难;二是好友被杀。[5](P19-20)这种“姑活”心理,几乎伴随鲁迅的整个晚年生活,对其写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其作品中才会透露出“迟暮”意识。
同时,晚年的各种经历,使得鲁迅左右为难,让他一度思考自己一生所进行的“启蒙”事业究竟有无成效,甚至有时还对自己的“启蒙”行为产生了深深的质疑。鲁迅的这种质疑,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启蒙者”自身的质疑,二是对“启蒙”对象的质疑。
鲁迅曾对自己的“启蒙”行为有过这样的反思:“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细微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2]
而且,鲁迅的这种质疑,并非只是空穴来风,在这之后,鲁迅曾经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的来信,信中这样说:“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不知不识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2]
我们可以想象,当鲁迅收到这封信时,会有怎样的震撼,又会有怎样的沉重?自己一生所经营的“启蒙”事业,非但没有拯救青年,却无形中使得有知识有担当的青年如此痛苦,更在来信中称自己为“你老”,叫鲁迅“现在可以歇歇了”,从而保全几个“他”,这于鲁迅而言,无疑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痛楚,使得鲁迅一度产生“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的状态。此时的鲁迅,无疑是矛盾的,是痛苦的,他的矛盾和痛苦,来源于他对自身的质疑,对“启蒙者”身份的质疑,而这种质疑,则无可避免地给晚年的鲁迅及其作品带来了一份难以摆脱的“迟暮”意识。
如果说鲁迅对“启蒙者”自身的质疑还只是觉得沉重的话,那其对“启蒙”对象的质疑则堪称痛苦了。1927年9月4日,鲁迅曾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的。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2]
1928年4月6日的《申报》有一段《长沙通信》,记的是湖南省处决共产党人一事。在被处决中,有三名年轻女性,于是,“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之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2]针对这则消息,鲁迅写了《铲共大观》,发挥了一点想象:“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这样的联想,说明鲁迅的心被这则消息刺激得非常痛楚。1906年夏季,在日本的仙台医专,鲁迅正是被一群中国人旁观一个中国人的被杀而决意以思想启蒙为毕生事业的。二十二年后,当鲁迅步入生命的晚年时,这样的场景仍给鲁迅以深深的刺激。……当然,如今面对这样的场景,鲁迅的心中会比二十二年前更多一份沉重,一种悲哀。怎么二十二年过去了,民众精神上的麻木之“厚重”依旧?怎么许多人参与的启蒙事业进行了那么多年,仍不见明显的成效?[5](P71)
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旨在反对对日妥协的“一二·九运动”,遭到军警的镇压。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学生而跪在国民党市政府前请愿。12月21日《申报》的“本市新闻”栏内,刊出了学生跪着的照片。对学生的此种做法,鲁迅颇不以为然。在看到照片的当夜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写道:“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2]学生长跪请愿,目的本在救亡;然而,在鲁迅心目中,这种长跪的行为,为中国带来的羞辱,甚至甚于国土的沦亡。[5](P79)
中国(青年)民众以上的这些行为,显然让鲁迅感到曾经付出的“启蒙”的无效,这深深地伤透了鲁迅的心,让鲁迅感觉到异常的悲凉,甚至于绝望,鲁迅本来是一直寄希望于青年的,然而,现实却是,青年也不足为信,中国的青年还远没有觉醒,远没有被“启蒙”,思想依然很落后,既然如此,那么,该到哪里去寻找希望呢?显然,这样一种“理想”的破灭,对鲁迅晚年的精神世界打击是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在很大程度上,让鲁迅的心境有着相当灰暗和阴郁的部分,同时,也透露出极大的悲观和绝望。虽然鲁迅没有在这种绝望中消沉,而是一直在反抗绝望,但这种绝望始终是存在于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中的,并使得其晚年的创作带上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迟暮”意识,而《故事新编》正是鲁迅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因而,其或多或少呈现出的“迟暮”意识。
《故事新编》是鲁迅晚年病痛缠身,对生命无奈,以及因其一生所从事的“启蒙”受挫而带来的痛苦和悲凉,甚至于偶尔绝望的一种体现。这种“迟暮”意识是生命的无奈和悲凉,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是鲁迅作为“启蒙者”的莫大的悲哀。鲁迅把这种悲哀隐射到作品中,便使得《故事新编》里出现了一群“迟暮”的末路英雄。
[1]增田涉.鲁迅印象·鲁迅在病中的状貌和心情[A].鲁迅回忆录(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袁文杰.试论《故事新编》成集中的悲剧层流[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4]肖同庆.走向死亡:迟暮与辉煌——鲁迅晚年生死观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4,(2).
[5]王彬彬.鲁迅的晚年情怀[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TheImplicationof“Aging”inLuXun’s“NewStories”
GUO Da-zhang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Lu Xun,at his old age,suffered from illness and hard life. He started to doubt his career of “enlightening people”. With the sentiment of helplessness and sadness,he was aware of “aging”. This is reflected in his later works:“New Stories”. To some extent,this is a tragedy for him as a “enlightener”.
“New Stories”;being aware of old age;illness;the mentality of old age
2017-03-02
郭大章(1982-),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004—5856(2017)12—0075—04
I210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12.018
张 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