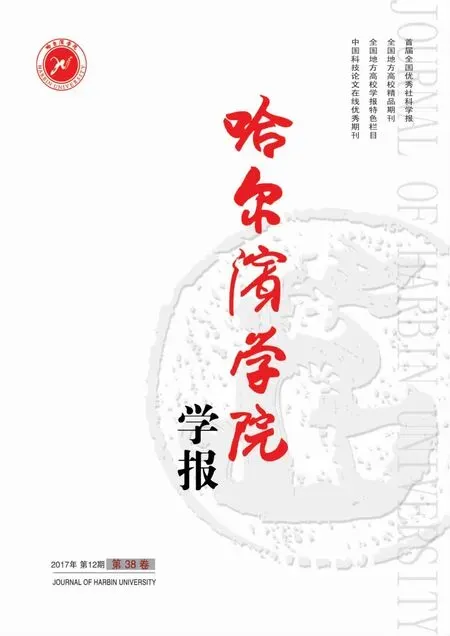黑龙江流域黑河地区古代民族筑城初步研究
2017-12-27王禹浪谢春河王俊铮
王禹浪,谢春河,王俊铮
(1.黑河学院 远东研究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2.阿穆尔国立大学,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 999081)
黑龙江流域黑河地区古代民族筑城初步研究
王禹浪1,谢春河1,王俊铮2
(1.黑河学院 远东研究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2.阿穆尔国立大学,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 999081)
黑河地区位于黑龙江上游和中游分界的结点,自然地理环境复杂,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史上古代民族交错、融合的重要区域,亦是其迁徙移动及水陆通衢的大十字路口,在历史上拥有不曾间断的城市文明。据不完全统计,黑河地区现有古代城址18处,其中以爱辉区西沟古城(老羌城)、逊克县河西古城、西石砬子古城、北安市南山湾古城、嫩江县伊拉哈古城等最为重要。上述古城占据水陆要冲,在历史时期均设置有级别较高的行政建制,亦是室韦诸部、黑水靺鞨、乌古迪烈、女真等古代民族活动的中心城邑。
黑河地区;古代筑城;古代民族
一、黑河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地理空间
黑河地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北麓,距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594公里,其西北接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北部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西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西南部与齐齐哈尔市毗邻,南接绥化市,东南部与伊春市接界。
黑河是我国在中俄两国4 300公里边境线上最大的城市,也是唯一的地市级城市。黑河市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是唯一一座与俄联邦主体首府相对距离最近、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开放最早的边境城市。两市是中俄黑龙江界江文化带上唯一的一对“双子城”,黑河也因此被誉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
黑河市辖境广阔,下辖一区两市三县:爱辉区、北安市、五大连池市、嫩江县、孙吴县、逊克县。黑河地处黑龙江干流上游和中游的分界节点,隔江对岸即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最大支流结雅河与黑龙江交汇口。黑河西部为大兴安岭余脉伊勒呼里山向东南延伸的低山丘陵,中部和东部为黑龙江右岸沿江平原,南部则为小兴安岭余脉。自北向南有托牛河、法别拉河、额泥河、石金河、公别拉河、逊比拉河、库尔滨河等多条较大河流汇入黑龙江。其中石金河又称什建河、什锦河、锦河。石金河蜿蜒穿行在小兴安岭山区中,将山体切割出深达100米的壮丽峡谷,即锦河大峡谷,现已开发为旅游景区。石金河即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室建河”,这一地名相当古老,当与室韦族关系密切。石金河注入黑龙江口南部不远处即是卡伦山古墓。卡伦为1858年清俄《瑷珲条约》签订后,清代沿黑龙江右岸设立的边境哨所。1985年,黑龙江省文物部门曾对卡伦山古墓群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获得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资料。但在关于卡伦山古墓的族属问题上尚存争议。我们认为很可能是辽代室韦某部遗存。公别拉河系黑河爱辉区南部最大的河流,又称坤河,“公”系“坤”的同音异写,“别拉”即“毕拉”,满语河流之意。《黑龙江志稿·地理志·山川》记载:“县南二十二里。源出坤安岭北麓。东北流二十五里,右受盘当沟。又东北流,折东南流三十里,右受一水。折东流五里,阿林河自额勒克尔山,挟布尔噶里河东南流四十里,经六座窑山南来注之。又东流三里,右受一小水。又九里,经萨哈连乌拉站,即坤河南,托尔河挟莫色河来注之。又东流十三里,经曹家屯北,达鲁木河东北流来会。折东北流二十里,经县南,注于黑龙江。”注云:“《盛京志》、《纪略》、《嘉庆大清一统志》均作昆河,蒙古语,昆,人也。《提纲》作尼河。”[1]公别拉河全长141公里,发源于小兴安岭北段大黑山,河流由西向东流经锦河农场、西岗子镇等,在坤河达斡尔族满族乡注入黑龙江。公别拉河河道蜿蜒曲折,上游穿行在小兴安岭北段山区中,植被茂密,遍布森林和湿地,位于黑河市爱辉区罕达汽镇境内的公别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和原生性沼泽植被。下游靠近黑龙江丘陵低地和平原,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公别拉河流域左岸的老羌城在民国九年(1920)出版的《瑷珲县志》中即有记载,上世纪80年代至今,历经多次考古调查活动,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今黑河爱辉区东南部沿黑龙江沿岸为孙吴县和逊克县,即逊比拉河流域和库尔滨河流域。《黑龙江志稿·地理志·山川》载:“逊河,县南二百八十里,源出东兴安岭,合数支渠东北流,折而东南流三百二十里,与占河合。折东流三十里,有乌都里河北流八十里来注之。折东北流三十里,有小岔河二源东南流来注之。小岔河左岸产金。又东北流二十里,经毕拉尔协领署南。又东北三十里,经奇克特镇东。又北分为二道,北流二十里注于黑龙江。自源至占河口,河东北属县,西南属龙镇。自占河至入黑龙江口,河北属县,河南属乌云。逊河南北岸,皆鄂伦春行帐。”注云:“逊,奶浆也。即逊必拉。《纪略》作孙河,古肃慎氏所居之水。语讹为双顺,俗亦称泡子河。因其流经库穆尔窝集,亦曰库穆尔河。”[1]逊比拉河简称逊河,今逊克县即因合并逊河县和奇克县而得名。逊比拉河和库尔滨河均发源于小兴安岭北部,蜿蜒穿行于山区复杂的地形和茂密的植被中。扼守逊比拉河与黑龙江汇合口的逊克干岔子乡河西古城是迄今为止黑河地区唯一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古代民族筑城。该城占据水路要冲的制高点,并通过四道城垣加以拱卫,足见其战略价值之高。
嫩江县、五大连池市、北安市所在的黑河地区南部和西南部为嫩江流域和乌裕尔河流域。嫩江县毗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加格达奇,位于发源于伊勒呼里山的科洛河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甘河与嫩江干流交汇的三岔河口。该地区处于松嫩大平原向大兴安岭地区过渡的平原丘陵区的中心部位,水陆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能有效管控黑龙江上游、大兴安岭地区及蒙古高原东部,因此古代民族筑城也较为密集,其中不乏如“回”字形的高等级大型城址——伊拉哈古城。该古城不仅是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治所,很可能也是唐代室韦都督府、辽代室韦国王府治所之所在。北安市地处我国第二大内流河——乌裕尔河流域上游,地理特征以海拔300-500米的山地为主,均为小兴安岭向西延伸的余脉。随着乌裕尔河自东向西流淌,地势也随之降低。讷谟尔河、通肯河也是北安市境内重要的河流。“乌裕尔”即“凫臾”“夫余”“扶余”“蒲裕”的同音异写。这一地区正是夫余族先世北夷索离国地理分布的中心区域以及金代蒲裕路治所辖区,是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文明相对繁荣的地区之一。五大连池市是嫩江支流讷谟尔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之一,讷谟尔河横贯市辖区中部。五大连池市北部系小兴安岭西侧山前火山熔岩台地,第四纪以来断裂带多次火山喷发形成五大连池火山群,是我国著名火山风景区和矿泉疗养地。五大连池地区受火山群地质地貌的影响,人口稠密区自古以来都分布在市辖境西南部的讷谟尔河两岸。
二、黑河地区古代民族筑城形制、遗存与研究综述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黑河地区现存古代民族筑城共计18座,其中黑河市爱辉区(原爱辉县)3座、北安市2座、五大连池市3座、嫩江县6座、孙吴县1座、逊克县3座。学术界对黑河地区古城的研究尚处在对古城进行著录的阶段,对古城形制、内涵及相关古代民族及其历史地理问题等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综合性著录主要见于如下成果:
郝思德等的《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发现的古城址》[2]著录了北安南山湾古城、庙台子古城,孙吴四方城古城,逊克何地营子古城(即河西古城)、新兴山城、石砬子山城,嫩江繁荣古城、门鲁河古城、小石砬子古城、伊拉哈古城,共计10座古城,并绘制有古城平面简图和地理分布简图,遗憾的是该文缺少对爱辉区西沟古城的记载。该文是目前所见较为详实的黑河地区古代筑城资料。孙文政的《嫩江流域辽金古城简要介绍》(未刊稿)、王禹浪等的《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3]及《嫩江流域辽金古城的分布与初步研究》[4]等亦对黑河地区古城有所著录,但偏重于嫩江流域。截至目前,关于黑河地区古代民族筑城的研究成果均未收录爱辉老羌城。由于关于逊克河西古城的考古学材料较丰富,故对其著录尤详。近年来,王禹浪教授对嫩江县伊拉哈古城、逊克县河西古城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将伊拉哈古城考订为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治所;而对河西古城,在王禹浪教授的带领下,黑河地方史志学者吴边疆、刘忠堂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航拍与多次调查,得出许多新的结论。[5]
笔者综合《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志稿》、民国九年(1920)《瑷珲县志》、1986年《爱辉县志》、1994年《北安县志》、1992年《嫩江县志》、1991年《逊克县志》等方志文献,[6-10]以及近数十年来学术界的研究与著录成果、调研记录等,对黑河地区古代民族筑城的形制、遗存及研究情况予以梳理和综述。
(一)黑河市古代民族筑城
1.老羌城:位于黑龙江省爱辉区西岗镇西沟达斡尔民族村南16公里,又称西沟古城,民间称老羌城或老枪城,有大、小之分。老羌城的北、东、南(偏西)坡30余公里被公别拉河环抱。西沟古城距黑龙江直线距离为24.702公里,海拔高度有三个高点,东北角海拔为251米,北部中间高点海拔为3 535.2米,西北角海拔为368.8米。古城分南、北二城,南城较大,周长2.7千米。南城南墙开一城门,门道外是一条弧形城墙,形成瓮门,门高0.4-0.5米,宽约1米之内。城门内南侧是1条300-400米长的土城墙,城高在1.5-2.5米之间,城墙基宽2-2.5米,顶部宽1.5米左右。城墙每隔40-50米之间有一马面。城墙为堆筑,墙外有护城壕。城墙内距城墙5米左右或10米处有一排不规则的土包或探险坑,推断为住所、垒灶(灰坛)遗址。1976年5-7月,黑龙江省考古队、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师范大学三个单位联合组成“黑河地区文物普查队”对老羌城进行了文物普查,初步定为金代古城。
关于老羌城的地方志文献记载,民国九年(1920)《瑷珲县志》(见图1):“西沟迤西有古围一处,四门、周墙土迹确在,四面,均在十余里,地方人民俗称老羌城。想系康熙以前俄人占据之地。”笔者按,考古调查只发现南门一处,其余墙段未见城门。是文载当地俗称“老羌城”之“羌”恐与清前期俄罗斯人有关,即哥萨克入侵黑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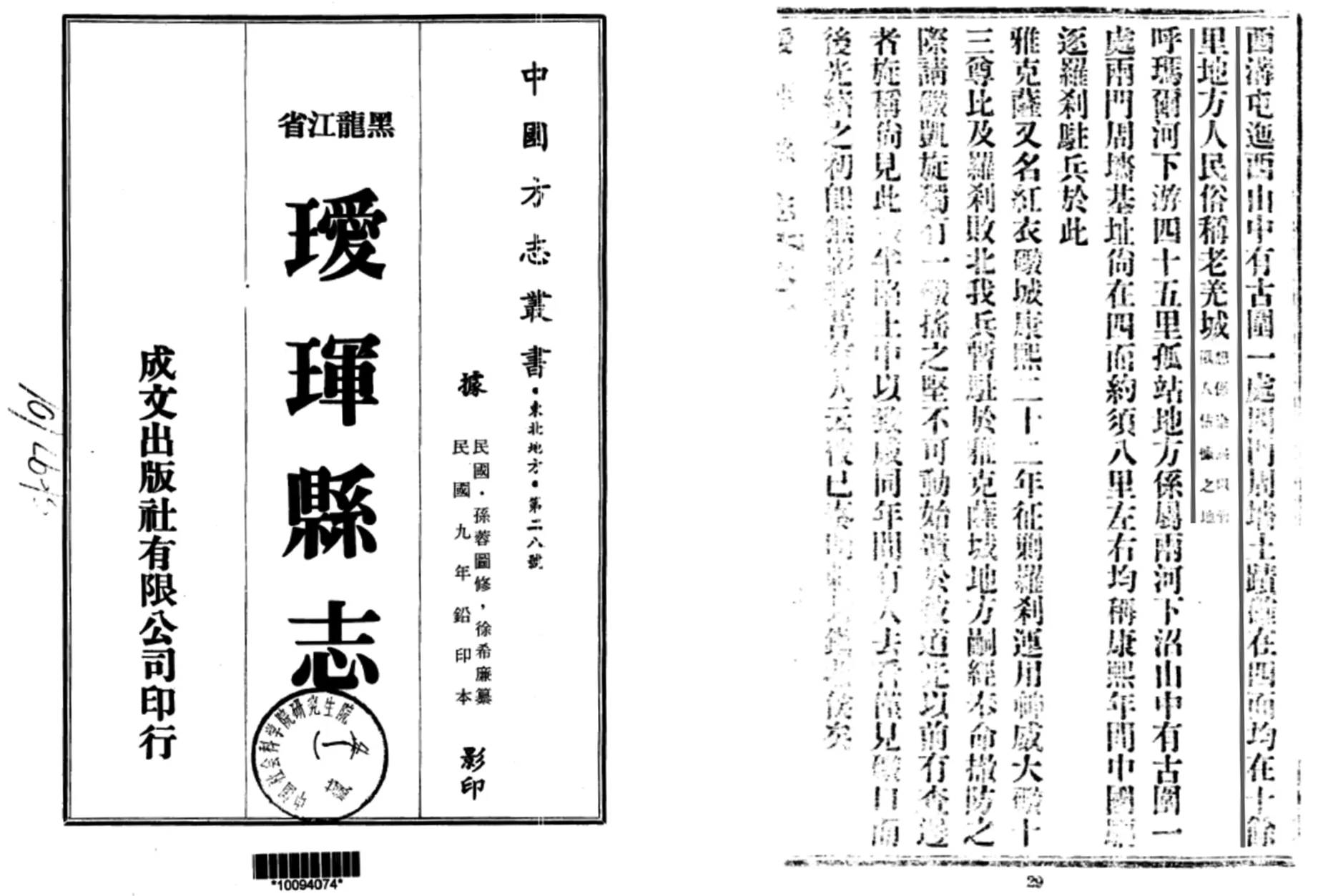
图1 《瑷珲县志》
1986年的《爱辉县志·文物古迹篇》记载:“1981年文物普查,大西沟古城,西沟大队西南20里,待考。小西沟古城,西大队西南16里,待考。”[7]笔者按,“大西沟古城”与“小西沟古城”即老羌城、小羌城。
黑河市图书馆馆员吴边疆提供了1976年、1981年文物工作者两次踏查老羌城的调查记录:
第一次:197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原爱辉县文化馆馆长白长祥与方伦荣(上海知青)对西沟古城进行了踏查,他们一行二人,由林业站检查员勾成海(当年58岁)做向导,于6月13日对老羌城进行了初步调查。
白长祥调查笔录:大羌城位于西沟大队西南的三十余华里的老羌城山上,东端是老羌城山陡峭的山崖,崖下是公别拉河,西端是小窟窿沟,二面有河水所环绕,城墙东西长约550米,城墙底宽6米,顶端2-3米,高2-2.5米,有大小城门四个,城楼三个都已经塌陷,在东端城墙头上向南眺望,可隐约看到陡沟子村,在距城墙内侧2米处有每30-40米,有一个土包,共计4个,直径5.5米,其中第三个为炮台遗址。在离城墙内侧3米处有一条约200米长的壕沟,城内有9个土坑。我们在老羌城遗址拍了五张照片,在大城门和城堡已塌陷的土坑中,我们试掘了几处红烧土,尚未发现其他遗物。随后我们又步行15里到小羌城遗址进行调查。
小羌城位于西沟大队西南,东南山下是公别拉河,此处,地势险要,居高临下,难攻易守,在小羌城里有一道壕沟,约200余米,还发现两山头各有壕沟一条,大小土坑20余个,似是炮台遗址,在这里拍了照片。
在西沟大队,我们走访了几位老人询问这一遗址有关问题,看法不一,众说纷纭。一说,光绪26年跑反(海兰泡惨案),老毛子(俄国人)从齐齐哈尔回来建的。又说,清康熙以前,大岭这一带都是老毛子的地方,康熙皇帝派兵把老毛子赶走了。
从我们实地调查来看,两处城堡虽位于山顶,但是,从老羌城至小羌城之间有约15里长的小岗,地势平坦,适于农耕,山林茂密,野兽踪迹很多,又适合狩猎,其次山下是公别拉河,至今尚有人在这里捕鱼,适于人类居住,难怪现在有人曾计划在此开辟村落。
由于时间仓促,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发掘,没有发现文物,因此,这一遗址是何人、何时所建,目前尚难以断定。建议对这古城遗址作进一步的踏查和细致发掘。(爱辉分队1976年6月19日)
第二次:1981年秋,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黑河地区文管所张鹏,黑河地区文工团杨军、朱东利,爱辉县图书馆副馆长王春复、馆员吴边疆,西岗子文化站站长刘复成等五人对西沟古城进行考古踏查,当时上山只有荒草丛生的山道。村里派了一姓勾的老人,耳朵背,当地人戏称其为“勾聋子”,即白长祥说的勾成海。他带着猎枪和一条狼狗上了山,带领我们,走了大约两、三个小时,穿越了荆棘遍地的野地和耕地羊肠小道,才来到古城,当时古城外表与现在的情形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现在修了上山的防火路。开越野车能直接开到古城边。古城东北是悬崖峭壁,东北方向是夹皮墙。公别拉河水从东边环绕古城北部。
2016年9月18日,正值黑河学院中俄边疆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黑龙江流域文明暨俄罗斯远东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论坛”刚刚闭幕,由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禹浪教授、黑河学院中俄边疆研究中心主任谢春河教授带队的考察团对老羌城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实地调查,对古城城墙形态、马面、穴居坑等进行了系统调查。2017年4月,黑河市文物爱好者吴边疆、刘中堂对老羌城、小羌城进行了寻访和航拍,确定了城墙轮廓,对该城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我们初步认定,该城至少为辽金时期修筑。
2016年9月开始,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筑城课题组针对黑河市近郊的西沟古城进行了多次考察,并对西沟古城进行了首次航拍,摸清了西沟古城是由南、北二城组成。2017年5月,黑河学院与黑河市政府联合成立的“黑河地区自然与文明千里行”项目科考组在参观瑷珲历史陈列馆时发现了展馆中展出的采自于西沟古城的金代“经略使司之印”。这一重大发现使多年来西沟古城一直成谜的历史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一消息在黑河地区千里行活动仪式发布会上公布后,随即引起国内各大媒体的关注,在黑河地方史研究者队伍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在靠近中俄黑龙江流域中游边境地区所发现的最高等级的金代官印,它将会对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意义极其深远。[11]这方官印于1979年采集于爱辉西岗子镇西沟村,边长约7厘米,印文为九叠篆,长把印纽上刻有一字“上”。该官印为金代官印,是金朝末年边镇军事机构的印鉴。边镇军事机构最初设置于唐朝,宋依唐制,设有经略使或经略安抚司,机构官职由节度使担任,属于准省级机构。目前,全国出土的金代经略使司之印总共有四方,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西沟古城出土的金代经略使司之印是第四方经略使司之印。王禹浪教授考证认为,黑河市爱辉区西沟古城作为金代末期的经略使司所在地,可以证明黑河市的准省级建置在历史上并不是自清朝开始的,而是在金代就设置了省级的行政机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出土“经略使司之印”的黑河西沟古城,不仅使黑河市的城史纪元被提前了近五百年,而且具有了确定城史纪元的直接证据,又为黑龙江流域的金代建置填补了空白。
2017年9月25-26日,在黑河学院主办的“首届黑河地区古代文明与城史纪元”学术研讨论证会上,来自国内众多高校的专家学者对王禹浪教授及“黑河地区自然与文明千里行”项目科考组所提出的西沟古城的定位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将西沟古城的年代下限确定在辽金时期是正确的,由此对黑河市城史纪元提前数百年的观点也是可信的。这对于延伸瑷珲古城的历史文明,提升黑河市文化定位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12]截至目前,对于老羌城的研究尚处于起步期,其背后隐藏的历史还远远没有被揭开。我们应该从古代族群活动的地理分布以及古代行政建置沿革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地区历史谱系,并从宏观视野中对老羌城进行比较研究和断代分析,进而为其定性提供重要参照。
2.小羌城:位于老羌城以西约7公里处山顶,东南山下为公别拉河,地势险要。城内有壕沟,约200余米,大小土坑20余个。古城现为耕地,遗迹已难寻。该城可能为拱卫老羌城的卫城或卫星城。
3.黑河卡伦山古城: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郊区卡伦山上,周长1.4千米,呈正方形。1985年,文物部门曾对卡伦山古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发掘墓葬19座。考古报告将其定为辽代女真人墓葬。[13]该说法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可能是室韦人墓葬。卡伦山古城与卡伦山古墓之间显然存在一定关联。
(二)北安市古代民族筑城
1.庙台子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黑龙江省北安市东南约58千米,石华乡立业村西1 000米处的通肯河支流六道沟台地上。古城平面呈长方形,长约600米,宽200米,周长1.6千米。城垣残高0.4米,墙基宽5米。古城外西北方向200米处有一土石混筑方形高台,面积约25平方米。当地百姓称其为庙台子。古城破坏严重,在城内采集和征集的文物有泥质轮制灰陶片、布纹瓦、青灰砖、残磨石、铜镜、铜佛、铜人佩饰、铜钱、铜饰件、铁锅、铁刀、铁鱼叉、铁甲片、陶器人塑像等。
2.南山湾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黑龙江省北安市胜利乡民生四屯西侧的漫土岗上,地近乌裕尔河与闹龙河交汇处。古城为南北向,平面呈方形,周长300米,城墙高1米。南城垣设一城门,城垣四角尚存角楼遗迹,城垣外有近2米宽的护城壕。在城内曾发现陶片、残瓦片、铜镜、铜佛、铜钱、铁镞、石臼等。古城东南700米处发现居住址一处,地表散布铜钱、铁镞、青砖、布纹瓦等遗物。古城附近曾出土金代“曷苏昆山谋克之印”,官印两侧的边款刻有“系蒲与猛安下”及“曷苏昆山谋克之印”等文字,背面右侧还嵌刻“大定十年七月”(1170年)、左侧刻有“少府监造”等字样。[8]可知该城应系蒲裕路下辖曷苏昆山谋克城之所在。该印系黑河地区目前所见唯一一方明确表明行政建置名称的古代官印。

图2 “曷苏昆山谋克”官印与印模
(三)五大连池市古代民族筑城
1.和安村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安村东北约500米处。古城东西长700米,南北宽100米,周长1 600米,城内有明显的建筑遗迹,1973年该遗址出土了一面铜镜。
2.永远村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五大连池市团结乡永远村附近,讷谟尔河支流石龙河右岸台地上。古城内出土有铁器、北宋“元丰通宝”“政和通宝”等字样的铜钱。
3.凤凰山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五大连池市兴隆镇凤凰山村旁的耕地中,古城内出土有铜钺、铁箭镞等遗物,在城址附近的五一水库(即今凤凰山水库)附近发现有金代墓葬。
(四)嫩江县古代民族筑城
1.门鲁河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嫩江县长江乡长江村南2公里处,南距长江村居民住宅100米,距门鲁河口300米,西距嫩江2.5公里。古城呈正方形,边长100米,周长400米。城墙残高约1米,四角设有角楼,南城墙中部有一豁口,应为城门遗迹,城门宽约7米。古城附近为沟塘,四周杂草丛生,现已遗址难辨。
2.小石砬子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嫩江县临江乡小石砬子村农机站院内,东北1 000米处为嫩江。城墙址为农机站石头墙基础,略高于地面,系夯筑而成,但夯土层不明显。城墙残高1米,基宽8米,无角楼和马面,南、北、西墙各有一个豁口,可能为城门。古城为方形,边长近100米,周长400米。小石砬子古城坐北朝南,背靠一座海拔60余米的小山,城前有干涸的河道。
3.繁荣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嫩江县前进镇繁荣村附近,北距嫩江近1千米。古城东侧50米处为居民住宅,东北距嫩江县20里。古城平面呈方形,每边墙140米,周长560米。东、北两面城墙已遭到一定破坏,西城墙残高2米,底宽约10米,南城墙残高1.7米。城址西北和东南角上各有一个凸出部分,可能是角楼遗存。据当地村民反映,原在东城墙中部有个豁口,是否为城门遗迹,现已难辨。古城内采集到铁箭镞、铁锅、铁碗等遗物。
4.伊拉哈古城:位于嫩江县伊拉哈镇红嫩村东北隅,古城与红嫩村毗邻。南距老莱河右岸约1 000米,齐黑铁路横贯古城东西穿过。古城分内、外二城,均呈方形,外城边长765.5米,内城边长665.5米,内城位于外城之东南,内城东南墙与外城东南墙重合。伊拉哈古城外城周长近3 000米,内城周长2 662米。城墙现残高1-2米,内城有角楼,每边墙各有马面三个。北墙保存相对完整,南墙原有瓮门遗迹,现被辟为乡村土路,已无存。古城内出土有大量的金代铜钱、布纹瓦、灰陶罐、定白瓷、仿定白瓷片等。1976年“一普”确认,1999年再次确认,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禹浪将其考订为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治所。[5]
5.海江村古城:辽金时期古城,位于嫩江县海江镇西孟村,北距科洛河6公里。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近千米,南北宽约100米,周长近2 200米。出土有布纹瓦、青砖、北宋铜钱、铁锅、定白瓷器等遗物。
6.兴安城:古城位于嫩江县塔溪乡光明村六屯西北近1公里处,西南距县城约75公里。古城位于山岗坡地,西、北、南三面均为山丘所围。城墙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约115米,宽约110米。城墙现多已不存。城内散见青砖、石块、白灰等居住址遗迹。
(五)孙吴县古代民族筑城
四方城古城:位于孙吴县东北约35公里的沿江乡西屯村西北近2千米处的方形山丘上。古城西北距黑龙江近约3公里。古城方位基本为南北向,城址近方形,周长约420米。城墙挖土堆筑而成,底宽约8米,残高1.5米。城角系漫圆状,未见瓮城、马面、角楼等附属建筑。仅在古城东南角有一道向外延伸的小土岗,长约30米。城内分布众多穴居坑,直径4-5米,深约0.5米。据群众反映,这里曾发现过铁锨镞、陶网坠、残瓦等遗物。
(六)逊克县古代民族筑城
1.河西古城:位于逊克县干岔子乡河西村南约5千米,黑河与孙吴交界处的一架山至逊比拉河河口的弯月形山脉中部,马鞍山西北海拔293米的第二高峰上。城址以北8千米为黑龙江,南10千米为逊比拉河,西北90千米为结雅河与黑龙江汇合口,东105千米为布列亚河与黑龙江汇合处。当地人俗称“老前城”。
古城依山势而建,平面呈不规则的倒三角形,东西最长处约480米,东北至西南最宽处约250米。城东南北均有30°左右的陡坡。西部马鞍形缓坡处筑有四道城墙,东南部有一天然形成的台阶,在上、下台阶边缘各筑一道城墙,东北部有一条狭窄的山脊直通山下。
由西向东排列,第一道城墙建在主峰与西侧峰相接处,长167米,由外侧挖土向内堆筑,城壕最宽处5米,深0.5米,墙基宽5米,高于地面0.7米。城墙两端为陡崖,城门宽5米,城门外有壕,距城北端62米。第二道城墙建在主峰脚下,走向为北偏东30°,长123米,两侧挖土堆筑,外壕宽7米,深0.2米;内壕宽5米,深0.5米,墙基宽6米,高出地表0.8-2米,南北两端与陡崖相接,南端有一座角楼或马面。城门在城墙中部,宽8米。第一、第二道城墙北端间距110米,南端间距28米,城门间距130米。第三道城墙在主峰山腰下,长261米,两侧挖土堆筑,外壕宽8米,深1米;内壕宽8米,深1.5米;墙基宽7米,高出地表1.5-2米;墙体北端有半圆形构筑。第三道墙与第二道墙垂直高差约3米;两墙在南部缓坡处间隔55米,在北部陡坡处间隔2米。城门距墙北端97米,宽4米,壕沟无隔断,西南距二道城门25米。第四道墙建在山腰上部,由外侧挖土堆筑,壕宽6-11米,深1.5米;墙基宽8米,高出地表3米,全长283米;有两个城门,南门距墙南端29米,宽6米;北门距墙北端35米,宽8米,两门壕沟均无隔断。三墙与四墙间距南端80米,北端2米,垂直高差3-5米。在城东南自然两层台阶垂直高差15米,边缘均筑城墙。山腰一道墙长247米,城门宽9米,第二层台阶城墙与山腰墙平行,长103米,两道墙都是基宽8米,高1.5米。城北部山缘向北城拇指状突出的山脊内折角处,有人工修建的马面状建筑。
城内分布209个方形坑,1976年曾出土三件凿形铁镞及少量灰陶片。1990年城内圆形灶坑出土陶罐和铁镞。城内遗物有铁渣、素面泥质灰陶罐、夹砂黄褐陶素面单耳罐。
河西古城发现于1976年,1990年因受黑龙江水电站淹没区影响再度被文物普查队复查。1992年5月,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河分所、黑河博物馆、逊克文管所、孙吴文管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第三次对该古城进行了调查和测绘,发表了《黑龙江省逊克县河西古城第三次调查简报》,[14]并被收录进王禹浪等主编《东北辽代古城研究汇编》[15]中。今人对河西古城的认识几乎完全来自于该简报。简报认为,该城尚未掌握瓮城、马面技术,年代应晚于同仁文化,早于金界壕边堡,并认为该城的修建与剖阿里国叛辽事件有关。
据笔者初步研究,认为逊比拉河之“逊”即是黑水靺鞨思慕部之“思慕”的快读,二者实为同音异写。因此,构造复杂、拥有四道城垣的河西古城可能为黑水靺鞨思慕部筑城。《新唐书·靺鞨传》云:“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河西古城及其所处之逊比拉河流域正位于唐黑水都督府故址萝北江岸古城(我们将唐黑水都督府故址暂定为萝北县江岸古城[16-17])之西北方位。因此,河西古城很可能为思慕部中心城址,逊比拉河即思慕河。河西古城四道城垣的筑城形制及城内发现的铁箭镞显然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关。
2.新兴山城:山城位于逊克县新兴乡新兴村西南约15公里的乌松干河和库尔滨河交汇河口,古城西、北临库尔滨河,南临之乌松干河从古城所在山脚下流过,东流汇入库尔滨河。古城西北距逊克县45公里,四周均为丘陵和沼泽。古城修筑在海拔100米的山岗之上,西、南、北三面均为陡崖,唯有南部地势较为平缓。城墙修筑于城东部,有城墙一道,残长约150米,残高近2米,中设一门。山城周长近700米。城内发现200余个穴居坑。
3.石砬子山城:《逊克县志·文物志》将其定名为“古居住地(古土城)”。山城位于逊克县城西南4公里的大石砬子山岗上,东南距边疆乡石砬子村200米,北距黑龙江2公里,南临黑龙江一条小支流,隔小河对岸为一片开阔河滩地,西靠陡峭的石砬子,成为古城的天然屏障,东面为一处平缓山岗,并向东北延伸直至奇克镇。山城依山势而建,呈椭圆形,周长约800米。城墙垒土而成,残高1-2米,城外设有3道护城壕,壕宽约12米,间距近1米。城墙东北、西南各有一豁口,应为城门所在,可知古城为东北—西南走向。城内地表发现30多个鱼鳞坑,呈扇形分布,前后两排,前排17个,后排16个。穴居坑长约5米,宽约3米,深1-2米。山城内散见夹砂陶片、石器和红烧土、木炭、骨骼等遗物。《逊克县志·文物志》记载,黑河地区文物考察队将其认定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址。[10]石砬子山城内可能存在新石器时期遗物,但城墙与鱼鳞坑显然晚于新石器时期,并应同属于一个时代。
民国五年(1916),奇克特县佐陶炳然辑撰《黑龙江奇克特志略》,其文“胜迹城址”条云:“奇克特迤西五里许,有西山焉,与三峰山相近,山有土城一座,广约二里许,城中土井一,深可数丈,询诸土人,皆无知者。相传为前清中叶时代所筑,用以防御俄人者。其城垣半多倾颓,最高处仅及人肩,前面临江,下视绝壁千寻,后倚山势设险,推其形势,以抽象的推测之,似一兵垒,昔人屯兵之所也。其所谓井者,以具体的观察之,或为军需储藏所亦未可知。或谓此城昔时为鄂伦春人所筑,聚处以避野兽者,而近时鄂伦春人尚未甚开化,当时能富于理想,有此建筑殆亦有人焉。”
三、黑河地区的古代行政建制沿革与交通
战国至汉代,今黑河地区南部的乌裕尔河流域和嫩江流域为夫余族先世北夷索离国的地理分布范围。“乌裕尔”即“凫臾”“夫余”“扶余”的同音异写。索离王子南下建立夫余国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了其疆域范围:“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可知夫余位于玄菟郡以北一千里的地方,疆域东、南、西三面分别与挹娄、高句丽、鲜卑接壤,北部则有弱水。对“弱水”的探索是学界一个热点话题,学界有多种说法,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张博泉等认为弱水即黑龙江;[18-20]李健才认为夫余“北有弱水”是指今东流松花江的西段,而挹娄“北极弱水”则是指通河以东的第一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21-22]林沄先生认为弱水在古代文献中均指西流之河,这里的弱水应是指第二松花江西流。[23]李东在综合诸家之说后对林沄先生的“第二松花江西流说”较为认可,同时他还提出,“弱水”还可能指嫩江上游一带,因为这一地区是夫余源头之一的索离国文化分布地区。[24]朱国忱等则考据“弱水”应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系指今三江平原以挠力河为主的湿地沼泽区。[25]冯恩学则认为唯有作为内流河的乌裕尔河符合“弱水”河水逐渐减弱、河道逐渐消失的特征,故“弱水”应为乌裕尔河。[26]目前,“弱水”为今第一松花江的观点已基本为学术界所接受。因此可以断定,今黑河地区南部是夫余国北部疆界的范围。夫余国灭亡后,一部分夫余族众北迁回索离故地,建立豆末娄王国,其中心区域在今黑河地区南部。魏晋南北朝时期,黑河地区还是鲜卑、乌洛侯、失韦(即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区域。由此可知,该地区长期以来为古代族群和王国分布区,始终未有成熟的行政建制。
黑河地区成熟的行政建制应始于唐代室韦都督府的建置。孙进己和冯永谦认为室韦都督府的地理位置应在嫩江流域。[27]孙玉良依据《唐会要》记载,唐德宗贞元八年“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十一人来朝贡”。唐文宗太和九年“室韦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来朝贺”;开成四年“上御麟德殿,对入朝贺正室韦阿朱等十五人。其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轶虫等三十人来朝贡”,证实了室韦都督府的存在。而关于史籍中称“阿朱”和“轶虫”为大都督,孙玉良认为是都督府升为了大都督府。另外,他根据上述史料,分析一年中有两位室韦大都督入朝,推测室韦中不止一个都督府,而关于室韦都督府的具体情况仍旧是个谜。[28]关于室韦都督府的诸多方面无从考究,王德厚称虽然室韦都督府的具体建立时间地点无法确定,但唐朝设置室韦都督府毋庸置疑。史籍中提到的室韦都督和室韦大都督,特别是室韦大都督不知根据为何,两者之间应有区别,不同之处仍待考据。[29]但张国庆则依据《唐会要》的记载,认为唐朝应是设置了室韦都督府和室韦大都督府两个都督府。[30]程妮娜认为,唐朝在落后的地区不会设置规格很高的羁縻大都督府,因此,室韦大都督只是室韦都督府长官的称号而已。[31]
《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朝设有“靺鞨国王府”“铁骊国王府”“高丽国王府”“日本国王府”“吐谷浑国王府”“室韦国王府”“濊貊国王府”等,将其均视为辽朝属国。辽朝对黑龙江中上游及嫩江流域的室韦设立室韦国王府予以管辖。但“室韦国王府”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室韦此时建立了“室韦国”。所谓“室韦国王府”即室韦部族活动的中心城邑。
蒲裕路与乌古迪烈统军司的设置是金代黑河地区重要的行政建制。蒲裕路又做“蒲与路”“蒲屿路”。金代上京地区设上京路,蒲裕路为其下辖五路中最大的一路。《金史·地理志》载:“(蒲峪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可知今黑河大部分地区归属于蒲裕路管辖。学术界现已达成共识,今克东县金城乡古城村古城系金代蒲裕路古城无疑。距蒲裕路古城不远的黑河北安市南山湾古城附近曾出土金代“曷苏昆山谋克之印”,官印两侧的边款刻有“系蒲与猛安下”及“曷苏昆山谋克之印”等文字。可知该城系金代蒲裕路下辖曷苏昆山谋克城。该城是目前黑河地区唯一一座建制称谓明确的古代民族筑城。蒲裕路辖境西至嫩江流域与乌古迪烈统军司毗邻。在《辽史》《金史》等历史文献中,“乌古迪烈”又写作“乌骨迪烈”“乌古敌烈”“乌虎里”“乌古里”“石垒”“敌烈底”等。乌古迪烈实为乌古部和迪烈部两个部族。辽金乌古部即原室韦乌素固部,迪烈部族源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可能与蒙古草原丁零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乌古迪烈统军司治所范围内应有相当数量的已融入契丹族和女真族中的室韦后裔。史籍有时将乌古部和迪烈部分别记述,有时又合二为一。乌古、迪烈二部一直活动在辽金王朝的北方,时叛时服,其剽悍、骁勇善战的特长,时常造成辽金北部边患不断。因此,辽金两朝专设乌古迪烈统军司或乌古迪烈招讨司,通过招抚和征讨并举的办法加以管控。长期以来,关于乌古迪烈统军司的地望始终莫衷一是,清季王国维撰《金界壕考》[32]一文,将乌古迪烈统军司地望锁定在“兴安岭之东、蒲裕路之西、泰州之北”的范围内。自此国内学者多因循此说。2012年8月,王禹浪教授在嫩江县委宣传部、文化局同志的陪同下实地调查了黑河市嫩江县伊拉哈古城。古城北墙保存基本完好,马面、角楼、城垣均依稀可辨。古城东方的老莱河蜿蜒曲折由东北向西南流淌。笔者通过综合考察乌古迪烈统军司与蒲裕路故城、金界壕、金代庞葛城、金初开国名将婆卢火死亡和埋葬地等的关系,认为唯有伊拉哈古城最符合上述条件,当为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治所之所在。而金代乌古迪烈部的游牧地,就是金界壕外侧,伊拉哈古城以北、以西,今嫩江上游左、右岸之地。我们还初步认定,今黑河嫩江县伊拉哈古城可能为唐室韦都督府、辽室韦国王府治所,后为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所沿用。黑河市瑷珲历史陈列馆馆藏金代“经略使司之印”,则表明黑河市爱辉区西沟古城应为金代末期经略使司治所,是当时的准省级建置。有关该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在辽上京临潢府和辽中京大定府与室韦国王府之间,有一条漫长的交通线,即沿着大兴安岭东麓、松嫩大平原西部的平原,经宁州、泰州、长春州等地到达嫩江流域。金代的金界壕其实也是沿着这条交通要道修筑的。
从金上京会宁府出发至今黑河,也有一条交通大动脉。《金史·地理志》载:“(蒲峪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即由今克东县金城乡古城村蒲裕路故城向北三千里,直至火鲁火疃谋克(大致在外兴安岭南麓的结雅河上游)在内的区域皆属大金国北部疆域。蒲裕路地处金上京会宁府与火鲁火疃谋克之间,其三者大致呈南北一线。金上京所在的阿什河与松花江左岸支流通肯河注入松花江河口相距甚近,两大支流与松花江主河道几乎形成了天然的大十字路口。这条交通大动脉自金上京出发,沿阿什河流域,越过松花江进入通肯河流域,继而到达乌裕尔河流域上游的蒲裕路。黑河公别拉河流域处在以克东县、黑河北安市为中心的乌裕尔河流域及嫩江流域上游至俄罗斯结雅—布列亚平原的过渡交界区域和交通要道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老羌城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阿穆尔州还分布着一座年代大致在公元7-12世纪的帽子山古城。古城建有系统的防御体系,城墙的建筑方法为黏土掺杂腐殖土和草皮堆砌。建筑物内有典型的火炕,出土了宋代钱币等遗物。[33]该古城与老羌城堆筑城墙的建造方法十分相似,其年代也有重合,其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联系。这也说明了黑河爱辉地区,特别是公别拉河流域在黑龙江流域古代历史上是民族交错、融合与交往的“地理枢纽”,沟通了黑龙江流域与嫩江流域以及黑龙江左右两岸的族群往来。
元代曾在东北北部边疆水达达女真聚居区设置了若干军民万户府,《元史·地理志》记载:“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谭其骧曾做过辨析,认为该处“合兰府水达达路”应为“女真水达达路”之误。[34]事实上,水达达路除了统辖上述桃温等五大军民万户府,见诸于《元文类》《元史》《析津志》等文献的军民万户府名称还有吾者野人乞列迷万户府、失宝赤万户府、塔海万户府等。程尼娜综合前人研究,将元代东北北部诸军民万户府地望制表。[35]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将失宝赤军民万户府考订在今黑河爱辉县南霍尔莫津屯。失宝赤军民万户府未见《元史》,而见诸于《析津志》《元文类》。元人熊梦祥出任崇文监期间,考究古籍,遍访元大都(即辽南京析津府)周边山川形势,撰《析津志》一书。后是书亡佚。今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将相关内容辑佚成《析津志辑佚》一书。是书《天下站名》记载了自元大都向四方辐射的交通驿站及路线、区间里程。该文献记载,洋州“至北分三路:一路正北肇州转东北至吉答。一路北行转东至唆吉。”依谭图“辽阳行省图”,吉答位于齐齐哈尔市以西、龙江县以东的嫩江右岸一带。[36]至吉答后,“至此分二路:一路东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吉答至失宝赤一线,依次经过牙刺站、捻站、苦怜站、奴迷站、失怜站、和伦站、海里站、果母鲁站、阿余站。其路线即沿着嫩江上溯至今嫩江县,转而向东北进入公别拉河流域,最终到达黑河地区。《元文类》卷四一引《经世大典》“鹰房捕猎”条云:“国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昔宝赤”即“失宝赤”,为管鹰人的万户府。《〈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证:“按自辽、金以来,黑龙江下游是出产‘海东青’的地区。失宝赤万户府在吉答以东十站处。从这些情况看,这条驿站线应在松花江以北,约自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东北行而东,与另一条沿松花江至奴儿干的驿路相平行,一北一南。清代黑龙江驿站中有一路经齐齐哈尔东北行达瑷珲城,其‘活鲁儿驿’即元代‘和伦站’,其‘枯母黑驿’即元代‘果母鲁站’,‘厄育勒驿’当即元代的‘阿余站’。失宝赤万户(府)在阿余站下,应位于现在黑龙江右侧逊河上流之东,约当现在的霍尔莫津地方,霍尔莫津可能是失(昔)宝赤的音讹。”[37]这一观点失之偏颇,如果元代的失宝赤万户府在阿余站下,那么当是瑷珲区西沟古城无疑。[38]
明代东北为辽东都司和奴尔干都司管辖,其中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大部、黑龙江省、外蒙古东部及俄罗斯远东南部尽为奴尔干都司辖境。该地区明代卫所设置最集中的地区位于第一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沿岸,与之相比,黑龙江中游和上游卫所寥寥无几,今黑河地区成为一个行政管辖相对缺失的区域。唯有墨尔根即今嫩江县设木里吉卫,“墨尔根”与“木里吉”系同音异写。事实上木里吉并非源于明代,而是早在金代即已经出现。[39]谭图中还标注了1449年,在今黑河、孙吴、逊克三市县相邻的沿黑龙江地带曾设巴忽鲁卫。随着明中期以后奴尔干都司建置的名存实亡,黑河地区卫所行政体系也不复存在。
清代黑河归黑龙江将军衙门及其下辖的瑷珲副都统衙门管辖。瑷珲即“黑龙江城”,又称“艾浑”。康熙十三年(1674)建瑷珲旧城于黑龙江左岸江东六十四屯地,为吉林水师营驻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龙江将军衙门进驻瑷珲旧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因居江左,来往公文一切诸多不便”,[40]遂将黑龙江将军衙门迁往黑龙江右岸瑷珲城。中俄雅克萨之战后,雅克萨城废,瑷珲逐渐成为黑龙江流域中上游第一重镇。清代在黑河设置了萨哈连乌拉站、坤站等驿站机构,用以沟通黑河与外界的联系。
四、与黑河地区古城相关的古代民族地理分布研究概述
(一)黑河与室韦地理分布研究概述
室韦是北魏至辽金时期分布于黑龙江流域上游及嫩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其地理分布与黑河关系相当密切,笔者即对与黑河相关之室韦地理分布的研究成果予以概述如下。
自上个世纪初至今,我国学者关于室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民国时期有:[41-53]丁谦的《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吴廷燮的《室韦考略》、王国维的《鞑靼考》和《黑车子室韦考》,王静如的《论阻卜与鞑靼》、方壮猷的《室韦考》和《鞑靼起源考》、冯家昇的《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和《述东胡系之民族》、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等。方壮猷翻译的日本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的《失韦考》,王国维翻译的津田左右吉的《室韦考》和箭内亘的《鞑靼考》。这些著述无疑奠定了室韦研究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54]一文掀起了室韦史研究的热潮,相关成果主要出现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重要论文有:[55-58]干志耿、孙进己合撰《室韦地理考述》、郑英德的《室韦地理新探》、王德厚的《室韦地理考补》、张久和的《室韦地理再考辨》等。而张博泉等撰著的《东北历代疆域史》、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是书第二章“南北朝隋唐时期”之“失韦(室韦)与失韦诸部”由郭毅生撰写)、孙进己和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37;59-60]均对不同时期室韦地理分布有所考述。室韦专著类主要有:[61-62]孙秀仁等合著的《室韦史研究》和张久和的《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的观点和理论对后世学者影响颇大,如孙秀仁、干志耿、孙进己等合著《室韦史研究》受到白鸟和津田观点的重要影响。张久和的《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从探索蒙古族族源的角度综合梳理了前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代表了目前国内室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室韦最初以“失韦”一词出现在《魏书》中。学术界一般认为,室韦在北魏时期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流域。隋朝时期范围不断扩大向外拓展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上游,形成南室韦、北室韦、大室韦、钵室韦和深末怛室韦。《隋书·室韦传》云南室韦“分二十五部”,北室韦“分为九部落”,钵室韦“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大室韦和深末怛室韦的部落分布情况未见记载。唐朝时,五部室韦进一步分化和扩张,变为二十余部。唐朝为管辖室韦专设了羁縻府机构——室韦都督府。晚唐以后,见诸于史籍的室韦部落名称大量减少,文献中多以“室韦”泛称黑龙江上游一带室韦故地的室韦部族,并接受了突厥语族部落对室韦的泛称——达怛。契丹人则称这一时期西迁入蒙古高原的室韦部落为“阻卜”。黑车子室韦、大黄室韦、小黄室韦、臭泊室韦、兽室韦等为文献中新见之室韦部落名称。辽代为管理室韦各部,还在黑龙江流域专设了室韦大王府予以统辖。这一时期的室韦分化较为严重,处于族群解体阶段,并与周边其他族群融合,形成新的族群。从东北地区的嫩江、黑龙江流域直至蒙古高原,均有室韦及后裔的分布。
室韦在北魏时期称“失韦”。关于北魏失韦的地理分布,《魏书·失韦国传》记载:“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有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水。”该文献中出现了啜水、盖水、犊了山、屈利水、刃水、水等众多古地名,其中水的地望无疑对判断失韦的地理分布最为关键。白鸟库吉认为,水为黑龙江,他在俱伦泊为今呼伦湖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由此湖水流出之室建河(《新唐书》作望建河)即今Argun河也。又此河注入之那河,即今黑龙江;而《魏书》之水,与《唐书》之那河为同名,亦黑龙江之古称也。《朔方备乘》、《黑龙江舆地图》等之著者考订此那河为嫩江者,盖徒拘泥于声音上之类似,而未尝深考《唐书》之本文,故有此误也。”且认为水、那河、难河均为蒙古语“碧河之义”。故将北魏失韦地望锁定在瑷珲、海兰泡一带。“位于瑷珲东南八日程之屈利大水,必为近嫩江无疑也。”[63]津田左右吉依行进里程将失韦考订在今齐齐哈尔附近,并认为:“如是,则其国中自北来之水即今之嫩江。嫩江,魏时谓之难河,唐称那河。水之名,与之相合也。”[52]后世学者多从此说,认为水即今嫩江,“”系“嫩”的同音异写。但失韦分布在嫩江流域的具体河段却尚存争议。谭其骧在其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认为在嫩江上游,干志耿、孙进己则认为在今齐齐哈尔附近,[55]孙秀仁、干志耿认为在齐齐哈尔以北。[61]王德厚则认为,“北魏时的失韦当以嫩江中游齐齐哈尔以北的嘎仙洞一带为中心,向其东、南、西、北诸方广为分布较为合适。”[57]张久和认为北朝失韦在嘎仙洞这一地理坐标的南部地区,即东邻豆莫娄,西毗地豆于,东南与勿吉邻近,北与乌洛侯相连,沿嫩江中下游及以西各支流居住,中心地域在雅鲁河和阿伦河之间。活动于甘河流域的乌洛侯也应包括在室韦之中。[58]可知今黑河地区嫩江县、五大连池市、北安市等均应是北魏失韦的分布范围。
隋朝时室韦地理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并向外拓展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上游,形成了南室韦、北室韦、大室韦、钵室韦和深末怛室韦。《隋书·室韦传》云南室韦“分二十五部”,北室韦“分为九部落”,钵室韦“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大室韦和深末怛室韦的部落分布情况未见记载。干志耿、孙进己考证北室韦在齐齐哈尔附近,钵室韦在嫩江上游甘河一带,其范围大致在今黑河西南嫩江县及其以西、以南地区。[55]张久和考证南室韦在嫩江中下游及以西各支流,北室韦在今呼玛、黑河一带。[58]
唐朝时,五部室韦进一步分化和扩张,据张久和先生对《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的比定和梳理,室韦部落凡二十部——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讷北室韦、婆莴室韦、达末室韦、骆驼室韦、乌素固、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那礼、大室韦、西室韦、蒙兀室韦、落俎室韦、东室韦。[62]郑英德则认为,历史上的乌洛侯、乌丸、达姤、鞠、地豆于—霫、俞折等不同时期的族群部落均应属于室韦。[63]另外,达姤部、落坦部等也应属于室韦族。有学者考证,那礼部在今黑河市嫩江县,岭西室韦在黑龙江省嫩江县以东、小兴安岭以西一带,讷北支室韦在今小兴安岭北段山区一带,蒙兀室韦今黑河爱辉。[56]唐朝为管辖室韦专设了羁縻府机构——室韦都督府。晚唐以后,见诸于史籍的室韦部落名称大量减少,文献中多以“室韦”泛称黑龙江上游一带室韦故地的室韦部族,并接受了突厥语族部落对室韦的泛称——达怛。契丹人则称这一时期西迁入蒙古高原的室韦部落为“阻卜”。辽代为管理室韦各部,还在黑龙江流域专设了室韦国王府予以统辖。笔者初步认定,唐室韦都督府与辽室韦国王府均在黑河市嫩江县伊拉哈古城。
尽管学术界对室韦族及各部的历史脉络与地理分布已经形成初步认识,但对其各部的地理分布还相当模糊不清。而可以肯定的是,黑河地区自北魏至辽金始终是室韦的重要分布区域,但为室韦何部之活动地域尚不甚明了,其南部和东南部则为与黑水靺鞨的交界地带。
(二)黑河与黑水靺鞨地理分布
俄罗斯作为我国的邻国,与我国地域相连,该国学者在近二百年的时间中,利用地缘优势,一直致力于对黑龙江流域黑水靺鞨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发掘,其在黑水靺鞨考古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俄罗斯学者在进行黑水靺鞨考古学探索的同时,也对其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如沙弗库诺夫考证黑水靺鞨之“黑水”并非今天的黑龙江,而是乌苏里江以及穆棱河,黑水靺鞨的活动范围也主要位于此。进而指出黑水靺鞨和女真人从未活动于今黑龙江沿岸地区,在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嫩江河谷、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居民是室韦人。[64]沙氏观点遭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科学分院学者涅斯捷罗夫的反对。他在《中世纪时代早期阿穆尔河沿岸的民族》(新西伯利亚,1998)一书中认为穆棱河与乌苏里江自南向北流淌,不可能形成南北靺鞨诸部,黑水即松花江河口以下的黑龙江河段,黑水靺鞨应主要活动于此。Д·Л·鲍罗金、B·C·萨布诺夫的《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认为中世纪早、中期的阿穆尔河沿岸大部分地区属于女真文化分布区,黑水靺鞨人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以东地区。[65]
清末至民国时,我国曹廷杰、景方昶、李桂林、金毓黻、冯家昇等学者都在其论著以及地方志中对黑水靺鞨的地理分布也有所考究。
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对相关史实阐释较为详尽,其中:“窝稽说”考证了靺鞨七部的具体方位;“黑水部考”考证了黑水部的地理分布范围;“挹娄国越喜国考”还考证出铁岭县南为黑水靺鞨越喜部所在地。景方昶亦在其著作《东北舆地释略》中对黑水靺鞨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给予阐述,认为“黑水”即黑龙江,黑水靺鞨跨黑龙江南北而居。晚清由长顺修、李桂林纂的《吉林通志》卷十:“黑水部:今三姓东北及富克锦左右地。”即今依兰东北至富锦一带。又云:“黑水部应为今黑龙江,然安车骨西北,仅就其西境而言之,其实黑水分部以南北为栅,则三姓以东、混同江南北之地,皆其部之所在,即皆吉林地也。”
通过引述前人文献可知,曹廷杰、景方昶、李桂林等均认定黑水部或黑水靺鞨位于安车骨北或西北,活动地域跨黑龙江南北,特别是《吉林通志》明确指出黑水部位于安车骨西北是“仅就其西境而言之”,并未说明黑水部只分布在安车骨西北。曹廷杰虽然考订出的黑水靺鞨分布地域广大,已延伸至庙尔地方,但将黑水靺鞨之东界定位于海兰泡,还认为该地即是黑水都督府所在地,从而也基本肯定了《隋书·靺鞨传》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的记载。笔者以为,曹廷杰、利桂林的结论是合理的。从《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记载的黑水靺鞨活动区域中可以看出,黑水靺鞨东起于大海,南与渤海相接,西与室韦为邻,而海兰泡至大兴安岭一线正是黑水靺鞨与室韦活动区域的交界地带。这也证实了至少有一部分黑水靺鞨正是分布于安车骨的西北方向。
金毓黻先是在《东北通史》中认为“近人曹廷杰考释较确”,[66]而后在《渤海国志长编·地理考》中认为黑水靺鞨在今黑龙江下游与松花江交汇处,进而论述道:“余意黑水以在今黑龙江东境及俄领沿海州北部之地而偏北者为近似,故云东北为黑水靺鞨也。惟其西北境尚无明文,若谓与契丹接,则不应远至是地,若谓与室韦接,亦无显证。然考之唐书室韦传,谓其四境,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则其东南与渤海接壤,明矣。”[67]也就是说,金毓黻在《渤海国志长编》中以证据不足为由,认为黑水靺鞨西北境尚不可知。然而,后文所引述唐书室韦传又明确记载室韦东临黑水靺鞨,不知金毓黻先生所指“明文”“显证”究竟为何。冯家昇的《述肃慎系之民族》(《禹贡》第3卷第7期)则以伯力以下的黑龙江流域为黑水故地。由此可知,金毓黻、冯家昇等学者已将黑水靺鞨地理分布范围缩小至黑龙江中下游一带。
我国建国后对黑水靺鞨地理分布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名汇编(东北卷)》、孙进己等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张博泉和魏存成主编的《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等著作对黑水靺鞨都督府及黑水诸部的分布都有较详细的地理考证,[37;27;68-69]均认为《隋书·靺鞨传》记载的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有误,早期黑水靺鞨应分布于今阿什河流域的安车骨之东北方位,即黑龙江下游地区。孙进己的《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一书也论述了黑水靺鞨的疆域问题。[70]沈一民认为黑水靺鞨分布于牡丹江以下的松花江东流段及黑龙江下游的南北两侧,文献中记载的黑水靺鞨“东至于海”(《旧唐书·靺鞨传》)、“东濒海”(《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所言之“海”,即鄂霍次克海。[71]李秀莲细致分析了《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记载的黑水靺鞨活动区域,考证出黑水靺鞨的活动范围是东到大海,即日本海;南与渤海临界,在今黑龙江省泰来附近;西到大兴安岭以西,与室韦相接;北到贝加尔湖。[72]
王禹浪在《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中对黑水靺鞨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全新的探析,认为黑水靺鞨应分布于安车骨西北方向的今三肇(肇源、肇东、肇州)地区,从而肯定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性。[73]马一虹的《靺鞨部族分布地域考述》考证了唐代各个时期靺鞨各部族的地域分布,认为王禹浪先生所考订的三肇地区即使的确是黑水靺鞨的最初居住区,黑龙江中游大量的靺鞨遗存证明这里也是靺鞨的最初住地。[74]何光岳在《女真源流史》中介绍了靺鞨诸部与唐代黑水靺鞨诸部的地理分布。[75]范忠泽的《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及对鹤岗地区的影响》认为黑水部活动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今鹤岗也包括在黑水部活动的区域内。[76]王彤以考古学材料为支撑,认同黑水部应该在黑龙江流域及其与松花江汇合处的广大区域内。[77]邓树平的《黑水靺鞨地域范围与黑水府治所初探》推定西迄今俄罗斯境内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到我国境内的黑河、逊克、嘉荫的黑龙江沿江一带以及小兴安岭东麓的鹤岗市至汤旺河流域之间、东到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今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下游流域地带,是黑水靺鞨的传统分布区域。[78]
在对黑水靺鞨诸部的研究上,冯恩学的《黑水靺鞨思慕部探索》一文认为结雅河下游发现的特洛伊茨基墓地当属黑水靺鞨思慕部。[79]他进一步论证,由于特罗伊茨基墓地位于与室韦的交界地带,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贝加尔湖草原的影响较大,所以特罗伊茨基墓地的人骨所反映的人种只能代表思慕部居民的种族类型。它是否能代表黑水靺鞨乃至全体靺鞨的种族类型,还需要新的人类学资料对比研究才能确定。如若此说正确,位于结雅河口南岸的今黑河地区显然与黑水靺鞨思慕部存在密切关联。
通过对学术界关于黑水靺鞨地理分布研究成果的综述可知,今黑河地区正处在黑水靺鞨与室韦的交界与杂居地带,这充分体现在室韦“造酒食啖”、养猪、以猪皮(即韦)为衣、与靺鞨同语言等习俗、文化与满族先民十分相似,表现了室韦与黑水靺鞨的接触与融合。
五、结语
黑河地区南通嫩江流域可直达龙城,即今朝阳,由朝阳而南便是中原腹地。西抵蒙古草原,西北与大兴安岭接壤,北连黑龙江上游左岸及外兴安岭山区,并与结雅—布列亚平原隔江相望,东及东北延伸为小兴安岭,并于黑龙江中、下游两岸相接,可直达黑龙江入海口之地。东南则与小兴安岭山地、三江平原、兴凯湖平原,以及绥芬河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相通,并直达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因此,黑河地区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史上民族交错、融合的重要区域,亦是各民族迁徙移动及水陆通衢的历史地理的枢纽。黑河地区古代民族筑城正是黑河古代文明最重要的历史注脚。据不完全统计,黑河地区有古代城址18处,其中以爱辉区西沟古城(老羌城)、逊克县河西古城、北安市南山湾古城、嫩江县伊拉哈古城等最为重要。上述古城占据水陆要冲,在历史时期均设置有级别较高的行政建制,亦是室韦诸部、黑水靺鞨、乌古迪烈、女真等古代民族活动的中心城邑。学术界对该地区古城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其背后所隐藏的城市文明的发展与古代族群的分布还未被揭开。2017年5月,由黑河地区政府与黑河学院联合举行的“黑河地区自然与文明千里行”是揭示该地区古代文明,以及黑龙江流域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会对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文明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1]万福麟.张伯英.黑龙江志稿(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郝思德,张鹏.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发现的古城址[J].北方文物,1991,(1).
[3]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
[4]王禹浪,郝冰,刘加明.嫩江流域辽金古城的分布与初步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7).
[5]王禹浪.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地望新考[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6).
[6]孙蓉图.徐希廉.瑷珲县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20.
[7]爱辉县修志办公室.爱辉县志[Z].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86.
[8]北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北安县志(内部出版)[Z].1994.
[9]嫩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嫩江县志[Z].海口:中国三环出版社,1992.
[10]逊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逊克县志[Z].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1]王禹浪,谢春河.黑河市西沟古城发现金代经略使司之印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10).
[12]翟少芳.首届“黑河地区古代文明与城史纪元学术研讨会论证会——以西沟古城研究为中心”会议综述(待刊稿)[Z].
[13]郝思德,李陈奇.黑河卡伦山古墓葬发掘的主要收获[J].黑河学刊(地方历史版),1986,(1).
[14]张鹏,于生.黑龙江省逊克县河西古城第三次调查简报[J].北方文物,1995,(3).
[15]王禹浪,薛志强,王宏北,王文轶.东北辽代古城研究汇编[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16]邓树平.黑水靺鞨地域范围与黑水府治所初探[J].满族研究,2011,(1).
[17]王禹浪,王俊铮.唐黑水都督府研究概述[J].东北史地,2015,(4).
[18]白鸟库吉.弱水考[J].史学杂志,1890(第七编第11号).
[19]张博泉.夫余史地丛说[J].社会科学集刊,1981,(6);
[20]张博泉.夫余的地理环境与疆域[J].北方文物,1998,(2)
[21]李健才.夫余的疆域与王城[J].社会科学战线,1982,(4);
[22]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3]林沄.夫余史地再研究[J].北方文物,1999,(4).
[24]李东.夫余国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25]朱国忱,赵哲夫,曹伟.关于弱水与大鲜卑山[J].东北史研究,2014,(1).
[26]冯恩学.夫余北疆的“弱水”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4).
[27]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8]孙玉良.唐朝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的府州[J].社会科学战线,1986,(3).
[29]王德厚.东魏至唐时期室韦与中原皇朝及毗邻民族的关系[J].民族研究,1994,(3).
[30]张国庆.略论唐初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府州的设置[J].黑河学刊,1988,(2).
[31]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制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2]王国维.金界壕考[A].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3](苏)С.П.涅斯捷罗夫,等.俄罗斯黑龙江中游左岸的帽子山古城[J].黑河学院学报,2016,(1).
[34]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J].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
[35]程尼娜.元朝对黑龙江下游女真水达达地区统辖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2).
[3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37]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38]王禹浪,谢春河,吴边疆.元代失宝赤万户府新考(未刊稿)[J].
[39]王禹浪.墨尔根为金代木里吉猛安考(未刊稿)[J].
[40]瑷珲县志·历史[Z].民国九年.
[41]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A].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C].
[42]吴廷燮.室韦考略[J].四存月刊,1922,(14).
[43]王国维.鞑靼考[J].国学论丛,1928,1卷3号.
[44]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J].国学论丛,1928,1卷3号.
[45]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1,2(3).
[46]方壮猷.室韦考[J].辅仁学志,1931,2(2).
[47]方壮猷.鞑靼起源考[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3(2).
[48]冯家昇.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J].禹贡,1934,2(7).
[49]冯家昇.述东胡系之民族[J].禹贡,1935,3(8).
[50]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J].辅仁学志,1939,8(1).
[51]〔日〕白鸟库吉.室韦考[J].史学杂志,1919,第30编第8号;东胡民族考(下)·失韦考[A].郑培凯.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中外交通与边疆史)[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52]〔日〕津田左右吉.室韦考[A].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一册,1915;王国维.观堂译稿(下)[A].王国维遗书:第14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53]〔日〕箭内亘.鞑靼考[A].蒙古史研究[C].刁江书院,1930.
[54]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J].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3-4).
[55]干志耿,孙进己.室韦地理考述[J].社会科学战线,1983,(3).
[56]郑英德.室韦地理新探[J].社会科学辑刊,1983,(4).
[57]王德厚.室韦地理考补[J].北方文物,1989,(1).
[58]张久和.室韦地理再考辨[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1).
[59]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60]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1]孙秀仁,孙进己,等.室韦史研究[M].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
[62]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3]〔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下)·失韦考[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64]〔苏〕沙弗库诺夫.徐昌翰.“黑水”地理位置及“黑龙江女真”族属考[J].黑河学刊,1992,(1).
[65]〔苏〕Д·Л·鲍罗金,B·C·萨布诺夫,郝庆云.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J].北方文物,1995,(4).
[66]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M].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
[67]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J].社会科学战线,1981.
[68]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69]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
[70]孙进己.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71]沈一民.论9世纪前中国对鄂霍次克海的认识[A].黑龙江省第二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下册)[C].2010.
[72]李秀莲.女真人与黑龙江流域文明[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2).
[73]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J].北方文物,1997,(1).
[74]马一虹.靺鞨部族分布地域考述[J].中国文化研究,2004,(2).
[75]何光岳.女真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76]范忠泽.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及对鹤岗地区的影响[J].黑龙江史志,2009,(3).
[77]王彤,李茅利.略谈靺鞨七部[J].中国地名,2010,(11).
[78]邓树平.黑水靺鞨地域范围与黑水府治初探[J].满族研究,2011,(1).
[79]冯恩学.黑水靺鞨思慕部探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2).
PrimaryResearchontheFortressofAncientNationalityinHeiheRegionofHeilongjiangRiverBasin
WANG Yu-lang1,XIE Chun-he1,WANG Jun-zheng2
(1.The Far East Institute of Heihe University,Heihe 164300,China;2.Amur State University,Blagoveshchensk 999081,Russia)
The region of Heihe is located in the junction of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Heilongjiang River,which possess a complex physic-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gion of national fusion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Sustained city civilization existed in history due to its geographic location of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there are 18 ruins of ancient city in the region of Heihe,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ities among them are Xigou ancient city in Aihui district (Lao Qiang city),Hexi ancient city in Xunke county,Xishilazi ancient city,Nanshanwan ancient city in Bei’an city and Yilaha ancient city in Nenjiang County.The ancient cities mentioned above occupy communication centre in which set up higher leve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They were also regarded as the center cities of n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Shiwei tribes,Heishui Mohe,Wugudilie and Jurchens.
the region of Heihe;ancient fortress;ancient nationality
2017-10-15
王禹浪(1956-),男,黑龙江方正人,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名誉院长、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荣誉博士、博士生导师、特聘教授,大连大学二级教授,主要从事东北流域史研究;谢春河(1966-),男,黑龙江黑河人,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院长、教授;王俊铮(1990-),男,陕西宝鸡人,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博士预科,主要从事东北史地和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
1004—5856(2017)12—0001—12
K877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12.001
李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