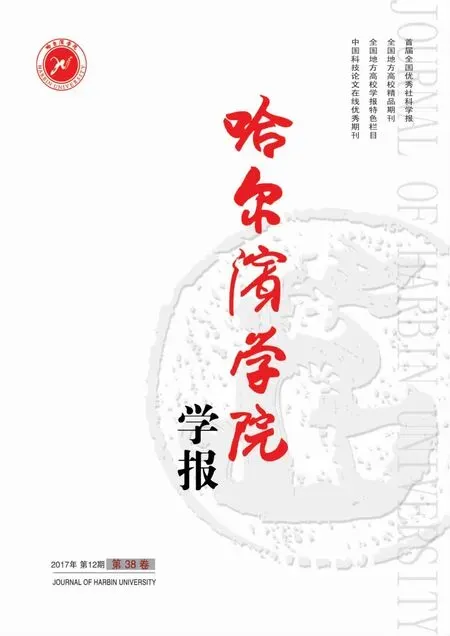论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2017-03-10耿宇佳
耿宇佳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论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耿宇佳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以赛亚·伯林在以往自由观念的基础上,针对政治自由、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个体不受到干涉和阻碍,它关注的重点在于是否有外在的个人和组织对其进行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自由的限度;积极自由阐释了自我的自主性和主动活动的自由,它的核心在于恰当的运用积极自由,避免造成滥用。
伯林;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一、两种自由的划分
自由是西方哲学中不断阐释却又说不清楚的一个重要概念。以往的哲学家都试图对自由进行言说,却引起了更大的争论。以赛亚·伯林对自由进行了两种划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伯林区分的自由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所谓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伯林所指的是,“我把自由说成是不存在阻碍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障碍。这是这个词通常的、可能是最通常的意义,但它并不代表我自己的立场。”[1](P31)伯林认为,如果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是自由做自己欲望内的事,那另一种自由就是消除欲望。伯林以斯多葛派为例,“斯多葛意义上的自由,不管多么崇高,必须与被压迫者或压迫性的制度实践所截削或毁坏了的那种自由分别开来。”[1](P32)斯多葛派所倡导的精神的自由、道德的胜利、心灵的无羁绊并不能代表他的自由。伯林所讲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这种区分会澄清自由的概念,避免产生歧义。不仅如此,伯林是在吸收了古典自由观的基础上论述自由。
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对自由做出了区分,伯林继承了贡斯当关于自由的区分,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诠释。据考证,伯林并非两种自由划分的首创者,但由于他融合了古典自由观,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两种自由,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且此后也不能避伯林而谈自由。
二、消极自由
何谓消极自由?伯林认为,“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的行动的领域。”[1](P170)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个人或团体组织干涉我的自由,这时候我是自由的。这里不被干涉的自由就与强制联系在一起了。哈耶克说,“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取决于强制概念的定义,而且只有在对强制亦做出同样严格的定义以后,我们才能对自由做出精确界定。”[2](P89)而伯林则认为,“强制并不是一个涵盖所有形式的‘不能(inability)’的词。”[1](P170)也就是说,自由意味着不被他人干涉。强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概念,除强制之外,还有外界的束缚、自然的障碍需要进行区分。由于生理限制,盲人不能看见书籍,耳鸣的人听不见汽车的笛声,都不能算是缺乏自由;而穷人买不起面包,这种并非人刻意干涉所造成的贫穷不能算是没有自由。伯林认为,“判断受压迫的标准是:我认为别人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阻碍了我的愿望。在这种意义下,自由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地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1](171)
与之对应的是,这个领域到底应该多大,也存在分歧。首先,“这个领域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1](P172)因为一旦这个领域没有限度,就会有一种所谓“自然的”自由,强者践踏弱者的自由,弱者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证,社会上人人都处于自由的混乱中。所以,应追寻一种不受干涉的自由,与此同时,也要保证个人的最低的自由,这就涉及了自由的限度。也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涉及的是“多少个门向我敞开”。[3](P37)伯林也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进行了论述:(1)自由与平等等终极价值的概念是不能混淆的。“任何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既不是平等、公平、正义、文化,也不是人的幸福和良心的安稳。”[1](P174)牺牲自我的自由并不能增加或补偿什么。(2)自由是需要有限度的。“绝对的自由是可怕的,绝对的平等也是可怕的。”[3](P134)(3)“消极自由的作用还在于,没有了它,其他价值也都会化为乌有,因为没有了去实践它们的机会,没有了各种机会,没有了各种相互歧异的价值,到头来就没有了生活。”[3](P138)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的提出,是有权威的存在,权威时刻威胁人的自由。如果有了消极自由,那么权威也会受到制约。因为一旦没有了自由,那各种压迫与强权就会随之而来,同时,消极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失去了消极自由的限度成为绝对自由,就会对人类其他价值目标造成威胁。然而,自由的界限到底在哪?或者说,无论是对于强制还是平等,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的界限?
伯林关于自由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三个问题:(1)自由界限在哪里。“一个消极自由的范围,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有什么门、有多少门向他敞开,他们敞开的前景是什么,他们开放的前景如何等等的函数。”“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依然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是多么小,只要入侵它,都将是专制。”[1](P174)(2)自由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存在着附和恶的自由,是否是真正的自由。“在终极价值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发现快捷的解决办法的。在这些情形中理性的做决定就是根据普遍的理想,即根据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所追求的整个生活模式来做决定。”[1](P47)(3)强制的另一种形态,为了增加消极自由而造成自由的缺失。“只有当你被人为地阻止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你才能说缺乏政治权利或自由。纯粹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缺乏自由。”[1](P42)
以上问题,都与消极自由的界限有关。伯林没有明确地给消极自由划界,是因为消极自由的界限产生问题,会对消极自由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伯林只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指出限定因素。那么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假设有一国的国王,本来拥有国土、人民、妻儿,因为战败,失去了国土、人民,妻儿也不在身边,每天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一个小屋子,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按照伯林的消极自由而言,别人不能干涉或强制我的自由,我就失去了消极自由;同时,国王并非完全没有自由,还有一个屋子是他可以支配的范围,从这个角度讲,国王又没有失去消极自由。问题在于消极自由的界限是在于国界还是那个屋子的界限。更进一步,如果这种自由的不断后退仍然不算是失去自由,国王仍保留自由,这种自由更等同于斯多葛意义上心灵、精神的自由了,这与前面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就会产生混淆。在伯林两种自由区分的基础上,斯金纳提出了第三种自由。在斯金纳看来,国家的自由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只有在实现国家的自由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倘若就此而看,物理上的界限关涉到个人自由的实质,而这个界限却始终是一个说不清的症结。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伯林不赞成绝对的自由,更不赞成平等、正义等价值目标的绝对化,而是试图使它们有一个相对的平衡,而第二个问题正在于,当消极自由附和恶之时,此时消极自由是否算真的自由。在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有些本土德国人是可以帮助犹太人的,或反对这种恶的行径,但很多德国人选择沉默,犹太人被困集中营,但一些德国人自身行动等方面都属于自由的,这种保有自身的消极自由能否称得上是真实的自由是值得质疑的。而在诺齐克看来,“个人自由这个领域是被正义的规则所规定的。道德上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是约束自由。”[4](P693)这也引起了道德正义与自由之争。就第三个问题而言,伯林认为消极自由是干涉或阻碍了人的自由。反过来,如果他人或团体给予个人自由行为的方式反而阻碍了个人自由,是否能称得上干涉个人消极自由。如果现代福利国家给予了个人很多福利,使拥有工作的个人丢弃工作回家等着福利与补贴,这种消极自由是否还是自由。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对自由主义者是存有敌意的,认为“个人应感激国家所给予的”。[4](P361)关于这方面,也引起了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长时间的争论。以上说明,都是对自由限度的质疑,可以说是由自由限度引起,联系到后来学者对伯林消极自由的争论,在此意义上,对消极自由的不当使用都会造成消极自由的违背。
三、积极自由
伯林提出,“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的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1](P170)积极自由是指“个体成为他自己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1](P179)在伯林看来,自我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积极的去行动,是自我决定的。积极自由是一种积极自主的向外的自由观。但是,个体因为受到外界意想不到的因素的制约,现实中可能并不能完成自己的自主。这种自主关涉到的只是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可见自主只是积极自由含义的第一个特性。同时,积极自由又是由两个自我所导向的:一个自我是高级的自我,是理想的自我。康德提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5](P4)黑格尔也类似地表达人类自我应顺应国家的观念。康德、黑格尔的自我是一个积极的、自主的、自律的自我,这种自律的自我受到人自身的理性与知识的控制。另一个自我是低级的自我,是经验的自我,现代功利主义者认为,倘若人无法掌控欲望,人就是欲望与激情的奴隶。功利主义者恰恰是根据人有趋乐避苦的本性,用欲望引导人遵守法律,守法就可以免于被惩罚的痛苦。“如果人生的善与恶可以用一种数学方式来表达的话,那么良好的立法就是引导人们获得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方法。”[6]在哲学史上,有高级的我战胜低级的我的时候,也有低级的我战胜高级的我的时候,使两种自我免于斗争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大我控制小我,或反过来行之;第二,大我消灭小我,或反过来行之;第三,大我与小我二者合一。自由主义者最为理想的状态就在于用非强制的方式使二者合一。这是理性、非理性统治下的情况。而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危险正在于此,在政治统治下,“真实的自我可以被理解成某种比个体(就这个词的一般含义而言)更广的东西,如被理解成个体只是其一个要素或方面的社会‘整体’:部族、种族、教会、国家、生者、死者与未出生者的大社会。”[1](P180)具体言之,其中的高级自我会壮大成为一个整体,以整体的名义,使非理性的人被强迫、被教育,以此来获取更高的个人自由,而这正是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出现的根源。这个整体需求什么,就是自由所给定的含义。“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在独裁主义、极权主义等面前成为一个谎言。”[5](P686)
伯林曾谈及,“有人怀疑我捍卫消极自由而反对积极自由,以为消极自由更文明,那只是因为我觉得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虽然更重要,但与消极自由相比更频繁的被歪曲和滥用。”相对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更容易受到外在的强制,造成积极自由的滥用。积极自由要做自己的主人,一旦自己在外界碰壁,就会修复自己,回到传统的禁欲主义,这是为了内心的安宁,按康德的说法,就是服从自己的理性。
[1]〔英〕以赛亚·伯林.胡传胜.自由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刘明贤.以赛亚·伯林自由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杨祯钦.伯林谈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Goodin,Robert E.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M]. Chichester:Wiley-Blackwell,2012.
[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英〕边沁.沈叔平,等.政府片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Berlin’sConceptofNegativeandPositiveLiberty
GENG Yu-jia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Isaiah Berlin,based on the previous concept of liberty,distinguishes negative liberty from positive liberty concerning political,individual,and social liberty. The negative liberty refers to the idea that the individual would not be interfered or obstacle. In other words,the focus is whether there is outside force,people or organizations,to stop liberty and the limit of liberty based on this. The positive liberty interprets self autonomy and the freedom of active movement. The core is that the positive liberty should be used appropriately while abuse should be avoided.
Berlin;the negative liberty;the positive liberty
2017-03-02
耿宇佳(1993-),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1004—5856(2017)12—0020—03
B82;D08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12.004
谷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