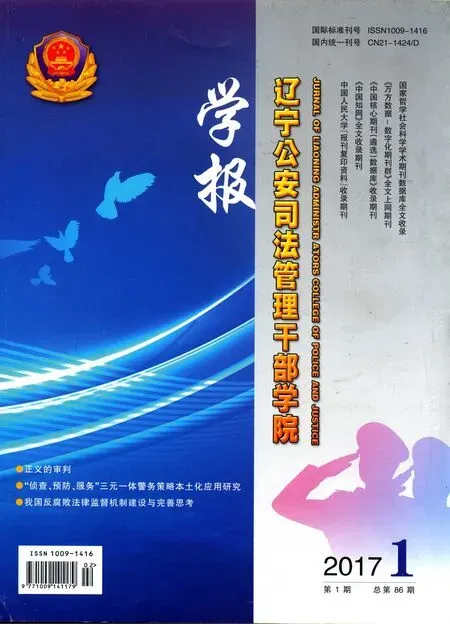卷宗移送制度之省思
——“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
2017-03-10段明学
段明学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重庆401147)
【司法理论与实务研究】
卷宗移送制度之省思
——“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
段明学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重庆401147)
卷宗移送制度构成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区别。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实行卷宗移送制度便于法官在庭前对案件作实体性审查,从而发现事实真相。但是,卷宗移送制度会导致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或偏见,妨碍公平审判原则的实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需要改革卷宗移送制度,淡化书面卷宗对庭审的影响。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不切实际,双重卷宗制度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以审判为中心;卷宗移送主义;起诉书一本主义;双重卷宗制度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行“卷宗移送主义”,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主要复印件移送主义”。2012年再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在实质上恢复了“卷宗移送主义”。对于此次修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时至今日仍未达成共识。2016年8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卷宗移送方式采取回避的态度,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目的在于落实直接言辞、证据裁判、控辩平等原则,实现庭审实质化,通过程序的公正实现实体的公正。不改革卷宗移送制度,法官庭前预断就无法排除,庭审实质化就难以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愿景就可能落空。
一、卷宗移送制度的渊源及法理分析
在欧陆纠问制时期,刑事诉讼实行书面的、秘密的审理程序,法官主要根据卷宗作出判决。无论世俗法院还是都会法庭均是如此。“诉讼的每一个过程的细节都要制作相应的文书,无论是已经进行的勘验、查证,还是听取的证人证言以及各当事人的陈述、声明等等,直至作出判决,付诸执行,无不采用书面形式。”[1]“在此程序下,审问者进行‘秘密’的调查,诉讼程序的每一步,以及审理过的每一个证据,都要被记录在案。因此,正式的‘调查案卷’内容繁多,含有对举证结果进描述的各种细节。在所有严重的刑事案件中,侦查终结时,卷宗被送到合议庭的法官手上,他们仅凭或主要凭卷宗中记录的证据判决。”[2]当时流传着一句著名的法谚:“卷宗无记录,便是不存在”。从这一法则可以看出,卷宗既是法官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依据,也是对法官作出裁判的限制。也就是说,法官必须按照卷宗以及记录上正当展示出来的证据进行裁判,而不能根据自己的私人知悉作出判决。这乃是欧陆中世纪道德神学的要求。“对于审判法官来讲,卷宗记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区分个人知悉与公共知悉,私人良心与公共(司法)良心。为了区分‘个人知悉与司法公共知悉’,‘卷宗记录’成为纠问制法官探寻‘司法事实’的唯一渠道,没有记录在案的即没有发生。”[3]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各国相继废除了纠问式诉讼和刑讯制度。在案卷移送问题上,英美国家普遍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同时实行比较严格的传闻证据法则,以防止法官产生预断,使裁判结论真正建立在控辩双方平等辩论的法庭审判过程中。大陆法系国家则保留了卷宗移送制度的传统。“记录先前官方活动的书面卷宗是程序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较低层级审判中发生的事情,必须保留下来以备较高层级的审核。因此,先前活动的记录成为最重要的证据信息来源。法律程序以间断的方式时开时合,案件的卷宗则为这些断断续续的程序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联系和生命线。”[4]
在法国,无论是违警罪案件、轻罪案件还是重罪案件,也无论是否经过预审,均须向预审法庭或者审判法庭移送卷宗。卷宗的主要内容包括:警察制作的确认犯罪事实的笔录;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被告人向警察所做的说明、辩解;证人证言;以及有关被告人人格的简单介绍。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轻罪、违警罪案件,审判长往往以卷宗为基础进行审判,审判时间可能只持续几分钟。被告人会进行简短的答辩,通常是进行有罪供述。如果有必要,法官还会宣读卷宗中的证人证言。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发表简短的意见之后,宣布判决和量刑。对于重罪案件,审判长在审判之前应当“深入了解案卷”,如认为有必要,有权进行补充证据调查。法庭审理遵循直接言辞原则,审判长所进行的讯问,各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的陈述,审判长与律师向证人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方相互提出的问题,都采用言辞方式。“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法庭审理(法庭辩论)要重提已经归入诉讼案卷的各项材料,并且用言词性产生的‘活的说明’来加以补充,必要时,还要补充可以收集到的、对查明事实真相有帮助的其他材料。”[5]在控辩双方总结证据之后,法庭退庭评议。在重罪法庭评议过程中,如果审判长认为确有必要对某些诉讼文书进行审查,可以要求将案卷送至评议室,并在检察机关派员到场时打开案卷。
在德国,当有犯罪发生时,警察进行侦查并编纂包含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陈述以及其他证据的卷宗。侦查终结后,将卷宗移送至检察官处,由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2款规定:“公诉书应当包含启动审判程序的申请。公诉书连同案卷一并提交法院”。法院审查起诉书和卷宗,并正式决定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开始审判程序。“虽然法庭依靠检察官提交的卷宗进行庭前准备,但卷宗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所有的证据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口头提出。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宣读庭外的书面证言。”[6]
卷宗移送制度孕育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同时构成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区别。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书面卷宗是整个诉讼程序运行的支柱,也是从警察侦查程序直到上诉审的各个诉讼阶段所主要使用的案件管理工具之一。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口头的与公开的听审在案件管理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即使在进行辩诉交易的案件中也是如此。由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实中的积极作用,因而要求实行卷宗移送制度,便于法官在庭前对案件作实体性审查,并积极、主动地去收集、调查证据,从而发现事实真相。如果法官庭前不研究、熟悉卷宗,就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无法有效地进行法庭讯问询问,因而削弱法官查明事实真相的职能作用,影响审判的质量与效率。
二、卷宗移送制度对公平审判的影响
公平审判原则是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程序的重要基石。尽管人们对公平审判原则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法官的无偏颇性或中立性属于公平审判原则的核心内涵。[7]当然,法官也是人,可能会受制于自身偏好或者偏见的约束,从而妨碍其公正地作出判决。“既然法官和其他决策者都是人而非机器,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是自身教育、经验和背景的产物。他们判断案情的思维,不会是一张白纸。但是,他们应努力警示自己,抵消任何可能干扰他们判断的外部因素,如果他们意识到了偏见,或者意识到了可能引发偏见的事项,他们就必须拒绝作出有争议的决定。”[8]从卷宗移送制度的运行情况看,其症结在于可能妨碍公平审判原则的实现。
(一)卷宗移送制度会导致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或偏见
在审判之前,法官先行熟悉卷宗,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预断或偏见。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其危险主要表现为“抽样误差”,即法官往往在庭上更愿意接受符合他预断的信息,而不愿意接受偏离他预断的信息,难以保持中立性。达马斯卡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预先获取信息的行为存在重大缺陷。由于对案情多少有些了解,法官不可避免地会对需要重构的事实形成一定的预断。……更重要的是,这带来了一个‘高发’危险:法官可能更容易接受那些符合他预断的信息,排斥那些相冲突的信息。法官一般也会意识到这种心理歪曲机制,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歪曲机制损害判决准确性的危险性,可尽管如此,这一制度的缺陷并不能完全被矫正。”[9]因此,否认卷宗会在法官头脑中留下印象,甚至形成预断或偏见,显然不切实际。
(二)卷宗移送制度不利于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庭审通常就是法庭对被告人有罪与否的积极调查。法官利用审前细致准备的卷宗,询问证人和被告人,而不依靠当事人构建案件事实。法官的积极主动作为虽然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但是却可能导致审判职能的异化,损害了法官的中立性、公正性。因为法官承担了本应由检察官承担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很容易变成“一方当事人的不速之客”——当事人辩论活动的莽撞入侵者。由此导致控辩双方的作用被严重矮化,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激烈的对抗。
(三)卷宗移送制度会导致庭审流于形式
由于卷宗移送制度的存在,法官极大地依赖卷宗,并沉迷于卷宗是真正“司法”审查结果的神话。在庭审中,法官经常不传唤证人出庭,而是直接宣读卷宗中的书面证言。布朗·麦基洛普通过对法国违警罪案件、轻罪案件和重罪案件庭审情况的观察,发现证人极少出庭作证,往往由审判长宣读证人庭前陈述取而代之;即使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也主要以卷宗中的证人陈述为基础询问证人,以确保证人法庭上的陈述与书面陈述相互“印证”。由此,他认为法国的审判程序并非是口头式的,而主要是书面性或文件性的。审判程序只不过是对侦查卷宗中得出的有罪结论进行公开确认的程序[10]。美国学者戈尔茨坦等认为,“如果法官没有明显的理由仔细询问证人,而且如果没有律师或者当事人的鼓励使法官这么做,其后果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具有探索性而且也不可能偏离卷宗太远的庭审。这种庭审与其说是纠问制理论所允诺的全面且独立的司法调查,不如说更像对卷宗有选择的验证。”[11]
正因如此,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尝试引入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的口头案件处理方式以弱化书面卷宗的作用。类似的改革已经在意大利(1989年)、阿根廷的联邦系统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州(1992年)、坦桑尼亚(1999年)、智利(2000-2003年)展开了。法国2000年6月15日颁布法律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重大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突出庭审的公正性、对抗性,以淡化卷宗对审判程序的影响。德国则对阅卷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合议庭组成人员中,只有一名成员可以阅卷,其他成员都无权阅卷,必须依靠庭审才能完整地了解案情。此外,各国还通过立法限制侦查笔录的证据能力,以突出刑事审判的直接言辞原则。
三、我国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设想
一直以来,卷宗移送制度导致法官未审先定、庭审流于形式的问题十分突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就要求重新审视卷宗移送制度,淡化书面卷宗对庭审的影响。对此,理论界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
(一)起诉书一本主义是否可行
目前,废除卷宗移送制度,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呼声甚高。在笔者看来,起诉书一本主义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卷宗对法官的影响,防止法官庭前形成预断,但起诉书一本主义不仅对法官的素质、能力、经验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且要求诉讼结构、诉讼文化与之契合,否则,就可能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
在这方面,日本引入起诉书一本主义就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尽管日本激进地推行起诉书一本主义以防止法官预断,但事实证明只是一厢情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法官获取案件信息的渠道十分便捷和多样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控方证据信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起诉书一本主义基本上宣告“失灵”,不可能发挥消除法官预断的作用。同时,由于证人出庭率较低,庭审中难以形成有效的控辩对抗,经常使用侦查过程中制作的陈述笔录作为证据,“口头辩论”经常被用来宣读证据文书,刑事案件审理的案卷化倾向日趋严重,“案卷决定审判”的特征日趋明显。因此,起诉书一本主义在确保庭审实质化,实现审判中心主义方面作用微乎其微。与法国的庭审相比,日本的法庭审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对侦查中的有罪结论进行公开确认而已。
此外,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法官对卷宗不够熟悉,在“空白状态”下进行审判,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极易被控辩双方的诉讼技巧牵着走,难以形成有效的心证,不利于发现事实真相;还会造成庭审的中断、拖延,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
总之,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制度基础以及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必将面临重重困难。
(二)双重卷宗制度的建构
有学者提出建立双重案卷制度,即起诉时不直接将侦查卷宗移送人民法院,而应制作单独的起诉卷(主要为证明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移送,对其他非证据材料不再随案移送[12]。笔者认为,双重案卷移送制度,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庭前预断,确保法官的内心确信主要形成于法庭审理,又可以保证法官在审前了解案件事实,更好驾驭庭审,提高庭审效率,因而不失为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
为了确保审判法官进行审判时不会先入为主,意大利于198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作了严格的划分。司法警察在初查中的工作和检察官的工作被分别记录在两个不同的卷宗里。其中一个卷宗仅仅反映了诉讼中一些不可重复进行的程序,如检查、查封或者窃听。这个卷宗将交给审判法官,审判法官可以在审判前获知相应的信息并允许在审判中宣读这些信息。另外一个卷宗包括了所有的侦查材料,如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当事人可以自由查阅这份卷宗,并可以用于质疑证人或者被告人在法庭上与卷宗内容不同的证言或者供述[13]。由于法庭不再将卷宗作为组织证据审查之有保障的信息生命线,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事实认定习惯已经开始改变。意大利的双重卷宗制度无疑值得借鉴。
实行双重卷宗制度,首先需要明确卷宗移送的范围,即哪些卷宗不应当移送到法院,哪些卷宗应当移送到法院。根据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将“主要证据的复印件、照片”移送法院,对于其他“次要”的证据材料,则由检察官当庭出示、宣读。“由于法官在开庭前只能接触‘主要证据的复印件’,而不了解全案证据情况,这确实解决了法官庭前对案件事实形成预断的问题。”[14]然而,法官通过“主要证据的复印件”,特别是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仍然可能先入为主,形成预断。笔者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法官庭前预断,促使法官重视庭审,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制作两份卷宗:一是言词证据卷宗。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这份卷宗不移送到法院,而由法院在庭上直接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二是其它证据卷宗。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所有证据、文书等。这份卷宗在提起公诉时一并移送到法院,以便法院对案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实行双重卷宗制度,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措施,以保障庭审得以顺利实施。
1.切实发挥庭前会议的功能
庭前会议除了研究讨论回避、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外,还应当梳理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以便法官把握庭审的方向及重点,为实质性的法庭审判作准备。
2.充分保障辩护方的阅卷权
无论是已经移送法院的诉讼卷宗,还是未移送法院的诉讼卷宗,辩护律师都应当有权自由查阅,以便尽早发现案件疑点,进而提出有力的辩护意见。
3.强化证人出庭作证
目前,证人出庭率仍然过低,法庭审理仍然带有较强的书面审特点。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卷宗中心主义”诉讼模式限制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功能发挥[15];另一方面在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款规定的证人出庭范围、条件弹性过大。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出庭证人的范围和标准。在简易、速决程序案件中,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在普通程序案件中,证人原则上都应当出庭作证。对于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存在重大分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必须确保对分歧部分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证。
4.严格规范卷宗的运用
一是要确立传闻证据排除法则。只有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方具有证据效力。对于证人的庭前陈述,原则上不应认定其具有证据效力。只有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以宣读证人庭外陈述代替当庭证言。二是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弹劾证据使用。即可以用于质疑被告人或者证人在法庭上与卷宗内容不同的供述或者证言。三是严格规范法官庭后的阅卷。对于极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法官不能当庭宣判,认为确有必要阅卷时,可以要求将案卷送至评议室。但是,只有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到场时,才能打开案卷查阅。
[1]贝尔纳·布洛克[法].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1版).罗结珍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39.
[2]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美].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00.
[3]佀化强编.形式与神韵基督教良心与宪政、刑事诉讼[M].北京:三联书店,2012:282.
[4]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美].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4-15.
[5]贝尔纳·布洛克[法].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1版).罗结珍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489.
[6][美]虞平,郭志媛编译.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选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95.
[7]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1.
[8]汤姆·宾汉姆[英].法治.毛国权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32.
[9]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美].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96-197.
[10]唐治祥.刑事卷证移送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49.
[11][美]虞平,郭志媛编译.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选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43.
[12]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J].中国法学,2015(03).
[13]陈光中等主编.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路径[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80.
[14]陈瑞华.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J].政法论坛,2012(05).
[15]侯建军,刘振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研究[J].法律适用,2015(12).
【责任编辑:张戈】
Reflections on the file transfer system——From the perspective of“trial-centered”
Duan Mingxue
(The First Branch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Procuratorate,Chongqing 401147,China)
The file transfer system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tigation model of the power and the litigation model of the party.Under the litigation mode of the power,the file transfer system is convenient for the judge to examine the case before the court,so as to discover the truth.However,the file transfer system will lead the judge to form predetermination or prejudice before the court to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fair trial.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file transfer system to dilute the impact of written files on the trial.In view of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it is impractical to implement the sole-filing system of indictment,but the double-filing system is a more reasonable choice.
trial-centered;file transfer system;sole-filing system of indictment;double-filing system
段明学(1973—),男(汉族),四川安岳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研究室主任,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与检察制度研究。
2016-11-22
D915.18
A
1009-1416(2017)01-0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