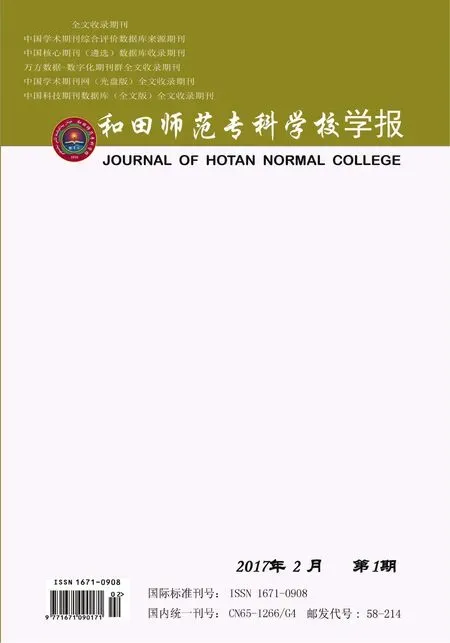清代新疆关帝庙碑探析
2017-03-10马学兵
马学兵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清代新疆关帝庙碑探析
马学兵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碑铭作为重要的资料,从中可以发掘新的史料价值。本文辑选清代新疆部分的关帝庙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方志从新的视角在对庙碑按序整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碑文内容,整体比较其异同,分析新疆信仰关羽背后的原因与特点。
新疆;关帝庙碑;探析
古碑依其特点划分为御碑、三绝碑、无字碑等,按其用途则划分为功德碑与纪事碑等,被史学界称为“会说话的石头与储存历史记忆的容器”。时人立其碑记记其事迹,为后世“立此存照”。为直观分析碑文所载关于建关帝庙的经过与兴废情况及发起人、集资者的状况,本文对于庙碑之内容进行摘录,部分内容从简。立碑时间以已考证时间所载为准。目前对于新疆关帝信仰的研究,学者集中于社会制度体系与民俗文化关系的探讨,王鹏辉先生集中于新疆佛寺道观庙宇的研究,涉及吐鲁番、奇台等地,兼及考证,成果丰硕。齐清顺先生对于新疆关帝崇拜的原因与特点及地域分布,从整体上进行了阐释,本文借此管窥之见,以庙碑为中心,按立碑时间顺序,对于碑文内容进行探讨分析,不足之处,恳请各同仁批评。
一、历代关羽信仰之概况
关羽,汉末倾頽之际将军。(三国志·蜀志)中记载:“其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今山西省运城县人,协助刘备建立蜀汉王朝。名著《三国演义》中通过桃园结义、斩庞德、单刀赴会等将关羽塑造成了英豪。史家陈寿谓:“关羽时称为世虎臣,为之死用,有国士之风”。[1]罗贯中曰:关羽忠义刚烈,爵禄不能移其志,集礼智廉耻信等传统美德于一身的英雄人物,而为后世奉为神明加以崇拜。诸葛亮称其为:“兼资文武,一世之杰”东晋学者葛洪称其为:上将之器,三九之才。[2]唐时有记关羽为三郎神,三郎所指关三郎,尚属人鬼之民徒。孙光宪记载:关三郎鬼兵入城,户户恐惊。公元782年,关羽被朝廷列为武成王庙(主祀姜太公)的配享者,及至宋朝,大兴朱熹义理之学,“忠义”道德的关羽被提出来,上升到“武圣”位置。宣和五年,封“义勇武安王”并恢复了从祀武成王庙的资格。至元朝时张宪记“张侯生冀北,关帝出河东”其由令人敬畏的凶神演化为大众接受的人物,地位也有所上升。迨至明洪武时期,朝廷恢复关羽汉寿亭侯之号,万历中期(1590年),关羽进爵为帝,尊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3]清朝在入主中原时期,就开始崇拜关羽,追封其父祖二人为公爵的同时,命全国各地“春秋二祭,牲用太牢”[4]及乾隆时,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在全国大建祀庙,以示瞻首。清代学者赵翼云:北极寒垣,南至岭表,凡儿童妇女,皆震其威灵,香火之盛,亦有数耶?[5]顺治十二年, 又御制碑纪,嗣机推崇关羽精神。康熙、雍正朝等也都不断提升赏赐的头衔,光绪朝最为明显,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在清朝政府的官方文书中,如四大方略与回疆志等史籍中也不断出现关羽显灵助官军的记载。
二、清代新疆关帝庙碑概况
(一)新疆关帝庙碑的简介
查阅戴良佐著《西域碑铭录》一书和近期考古资料,新疆关帝庙著名的有10座。大致情况如下:
雍正哈密关帝庙碑
该碑立于雍正七年(即1729年),现碑无存,为新疆关帝庙中建立较早的一块现据<回疆通志>录文如下:
“粤自古迄今,天地之所覆我,日月之所照临,以垂之永久而不朽哉,帝君(即关帝)生于汉末倾頽之际,当奸雄蠡起之时,独与桓候兄事昭裂皇帝。誓以共死,同辅汉室……格于丁末(即乾隆五年)冬奉檄来兹。抚理彝情。以来见夫,百彝效顺。烽烟用靖,士马咸宁。仰见圣天子之文德武功,覃敷异域,然冥冥之中犹赖帝君默佑耳。己酉二年春祀之辰,同事、僚属及兵民等佥议,因旧建庙宇措赀萁,更塑圣像,以大清雍正七年岁次已酋仲秋格同立。”
乾隆哈密关帝庙碑
该碑立于1750年,全文如下:“余于己巳奉命防守斯土,敬谒关帝君庙。盖昔年筑城之始,即建有此庙。迨之戌辰岁,有回首张三多、周玉龙等,夙昔虔募,已蓄有多金,但工程浩大,凡在官兵商民,靡不捐资恐后。此昔制度,规模数倍,其大功哉。在我朝尤为赫濯。今兹换其观,固圣能感激也。神庇边檄奠安,永垂不朽云耳,是为记。”
通古斯鲁克碑
乾隆1759年立于新疆南部通古斯鲁克之墟,回疆通志中称之为通古斯鲁克碑,由驻防官兵商民捐资建盖,兆惠等将军联名请于叶尔羌七十里洗泊地方而建立之庙碑。是为庆祝清军与霍集占叛军先后在通古斯鲁克与呼尔满的战争最后取得大捷而建,故又称叶尔羌关帝庙碑。[6]碑文内容遗失。
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关帝庙碑
碑文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碑文所载:“准我关圣帝君,神同六合,道炳九绝越殊方,备沾佑谷。恭逢圣天子武功大定,式瞻帝君,神应无方。……昔日民之冰天雪窖,今之凉燠应时;昔日之毡幕穹庐,今已闾阎匝地……明禋祝嘏,永庙貌于金城。凡诸同志各附姓名。”
补建迪化城关帝庙碑
“忠义为人,心共秉之。彝上下数百年,何尝不鼓努竞强;慨然以名教自任,乃未能彪彪柄柄。盖浩气之未易充而小善之,不足尚也……兹地于乾隆辛已岁建有庙,以安神灵,第堂宇促狭,不足蔽风尘……即其地势而增修膳厅三大间,非敢谓足以报功德也.惧其亵也,且以见忠义之在人心,有同悦焉。乾隆三十五年补修。该碑与迪化关帝庙碑互为补充,在原基础上扩建而成。”
惠宁关帝庙碑
该碑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五月建于惠宁城,清庭认为平定不尽人力,是因神威布获,为八旗官兵休养生息之际,虑久远计。正如碑文所载“建城郭、立制度,同文共轨,则庶乎神之降鉴有赫而垂佑无疆……撰文者为佐领伊勒图,监修者为世袭骑都尉伍岱。该碑立于城之北门内,大门三间,正殿五间,门内厅碑二座,同治以前尚存,今已无存。”
巩宁城关帝庙东亭碑
该碑于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望日落成,自乾隆二十年(177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原为游牧地区的乌鲁木齐由满族官兵三千余名驻于巩宁城(俗称满城),进行屯兵与民屯,农业恢复,嗣功于神灵保佑碑文中所载:“自汉唐以来,未尝列为郡县,如今日之盛者也。凡新疆疆土,咸归功于神.以迄灵佑而保安宁,乃于巩宁城敕建关帝庙.索诺木策凌督率文武官弁,实司其事。”[7]
伊犁关帝庙碑
该碑建于惠远城西,时间上存在争议,清实录记为最迟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开始筹划,“参赞阿桂等奏,于伊犁建关帝庙,每年春秋祭祀,并请求将前在伊犁政绩显者班第、鄂容安二人在庙后房屋祭祀,帝从之,令遵行。”[8]在前惠宁城庙碑中有如下记载:“惠宁城西七十里为惠远城,今年春,移陕西省八旗兵众驻于此,乃于城北面南之地,建立关帝庙,未逾年,而庙城。”[9]由此推断,该碑与惠宁城之立碑时间吻合,即为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建,但从成书时间来看,伊江汇览乾隆四十年(1775年)明显晚于清实录,因而其立碑下限应为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之间。该碑记载殿中设画像,于丁亥仲夏,塑圣像,即指关羽,是年,赐匾联:“春秋志在威名远,戍巳屯开庙貌崇”。碑文记载了其供在位之官致祭祀而建。
巩宁城关帝庙西亭碑
乾隆四十二年建立此碑,“自版章归附,钦命大臣统屯防兵于置粮务官司,始有户民,作城邑。厥后开营制,复筑城于北为迪化新城。今统称二城为汉城。以巩宁城为满城云。西域既平,南定回疆,北通哈萨克,一带贯通……”乾隆四十二年索诺策凌所撰文。碑现已无存,此二碑所载不仅可以得知建立新城之颠末,从城内建宫房,关帝庙如其制的记述中可以考察巩宁迪化二城的庙碑是为申译厥旨,抚兹城者。
长流水关神武庙碑
此碑立于距离哈密地区70公里处的长流水,于嘉庆五年(1800年)修建,洪亮吉为其撰碑记,在其文集中有载。原碑已不存。碑记不仅记载关羽之迹,而且也兼及其偏将周仓与关平,扩大其声威。
(二)陕甘关于新疆关帝之碑
原在西固沙柳古城,现由西固文化馆保存,该碑题为《重修关帝庙大殿补修二殿碑记》,刻写了资助修庙人的清单:粤自万历二年,山西副使胡维新等创建此庙。嘉庆七年动工,工将告峻,将施化人等记於后,以垂不朽。甘肃兰州道、隆银拾两。庄浪协副将保银伍两。甘州府正堂、喻银叁两。安肃兵备道、罅银伍两。钦差哈密总办大臣佛银贰两。镇西府奇台古城巡检李泰银肆拾叁两。前任陕西抚院泰银拾玖两 ,嘉庆九年岁次申子梅月建立此碑。庙于公元1957年拆除,碑闲置。碑文楷书,正文六行,行14字。碑原嵌在墙壁上,碑石纵55厘米,横78厘米,厚8厘米。[10]
根据碑文中各人员在嘉庆年间捐助庙宇的状况及抚银的数量,特为之记名勒碑,考述此碑记述,陕西巡抚、甘肃兰州道员、凉州副将恩施钱财在关帝庙呢?此事是具有偶然性还是出于某种已存的动机呢?大抵因地理位置的变迁,从事远途商旅之众或为官于新人士,在陕甘总督文绶(?-1784,清朝大臣)提出“屯田五事”后,大多内地汉族民众迁入新疆致中原人口饱和,遂“内地之民多趋之,村落连属,烽火相望”[11]其“亲不亲一家人的”心理作用逐渐变为一种寄生的精神信仰,尤其是陕甘民众把自己家乡佛教化的关帝信仰带进新疆,一则资助乡村兴建了大量的关帝庙,二则可能为乡土情结下庇佑的寄托,同事、僚属及兵民等佥议为之。该碑表明新疆的关帝庙与陕甘的关帝信仰传入西陲存在联系,并且逐渐被回疆地区所认同,哈密镇西台官员也参与其中,回首张三多、周玉龙等,夙昔虔募,无排斥修碑之意。嘉庆三年完工的迪化城隍庙碑,[12]乃乾属永、武二邑,有乐善不倦之念,同心筑其庙址碑文反映了陕西乾州移民乌鲁木齐人数之多的状况,我乾人于东者,亦可庇我东人于西者,以志不朽云。
三、碑文背后之探讨
综上所述,通过笔者对于碑文的内容全面的分析,整体比较得出新疆关帝信仰的主要原因:
(一)从民众视角解读
从碑铭中“塑圣像,以隆瞻仰,群丐为文以志之”、“督率文武官弁,实司其事”“民之冰天雪窖,今之凉燠应时”“我圣朝屡降典礼,更报尊崇”分析,清代,随着中原文化的东传,关帝孝悌信义的独特品质已深入人心,一则对于其义,是民众崇尚崇尚正义的寄托。《新疆志略》中载“回族之道德重信、敬老、亲仁、简直”[13]是义的一种精神追求,也是缠回与寄居于新疆的汉族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父母之心,以示无外”从碑文回首张三多、周玉龙、乔殷元等,夙昔虔募,已蓄有多金可窥。从其封号伏魔大帝来看,魔者说文解字曰“鬼也,从鬼麻声”,从谐音可以释为“磨”百姓期待磨难尽失,盛平太世之寓意。一方面是其内涵和精神符合普通大众的心理需求, 将关羽当驱邪神、守护神、武财神。
(二)从碑文的撰者与修建者视角解读
乾隆关帝庙碑为官绅合建,甘肃关于新疆之碑刻属于民间的商民或绅民修建外,关帝庙的修建者多为拥有都统、伊犁将军、知州、都尉等上层官吏的推动,如叶尔羌关帝庙碑。驻扎各城的军府官员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掌管祭祀,以彰忠节,碑铭中官碑数量多于私碑的数量。各种关庙碑记,无论是处于北疆地区之迪化、伊犁,南疆之喀什,东疆的哈密都体现着清朝上层提倡封建礼法,宣扬武功、抚恤民众、尚其风俗、约束人心的治边策略与政治意图,清政府在治理新疆时,在“烈焰弗戟,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其势日张,其志日移,则疆圉一日不靖”[14]的治边方针之下,采取宽松的信仰政策,实行汉回一视同仁。但是,汉回相雠,仇隙愈深频酿祸端之问题积小成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各种宗教力量的相互制衡,便利清政府实现自己统治的媒介,切于身心家国,安内防患。碑记中“覃敷异域,然冥冥之中犹赖帝君默佑耳。谨拜手稽首,扶服向化,而为之记”凡新疆疆土,咸归功于神、以迄灵佑而保安宁之记述,适指关帝庙碑的修建得到政策的引导。乾隆皇帝给关帝庙的题匾大多有“神佑新疆”“声灵绥佑”“灵镇岸疆”的记叙,皆有借关羽的神灵保佐新疆安宁之意。[15]另外,清官方修书中,关羽显灵也有所记载,凡是清军边疆的军事行动,关羽就会大显神威,助清军战胜敌军,在统治阶级的宣传鼓吹下,新疆许多军民对关羽神灵的武功也深信不疑,因此巩宁城军民在与敌作战之前,才会到关帝庙“祷永默佑”求关羽助战。“吾朝录其人才,准其仕进,而癖居关外者,又复为之立教,虽非我族类,但能传我声教,服我田畴,输将赋税,安得以其教之不同而歧视哉”?[16]在者从上述碑铭的内容梳理来看,大多都源于战事而立,或为记功而立,政治上推行以夷制夷,恩威并用,军事上宣示赫功,令各族报国以忠,作战以勇,这与关羽在治理新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关,兹关帝崇拜得以在新传播壮大。
(三)从各地的立碑时间视角解读
碑文所列只是部分有资料记载的碑铭,南北疆还有类似很多此性质的庙碑,具体参见学者门建军、郭院林之文章《清代关帝信仰研究》新疆关庙地区分布图的图表统计,以窥全貌,非本文重点,不在赘述。上列关帝庙碑碑铭,从时间来说具有一定的承序性,从康、乾、雍三朝直至嘉庆、光绪年,都有庙碑记载的记录,相关文集也零星记载。洪亮吉因事遣戍伊犁时,在其文集《天山客话》中曰:“过镇堡城邑,人口众者多仅百家,少则十家,然村必有一庙,庙中祀关神”。清代碑铭学的兴起,从碑铭总体来看康乾两位皇帝时最多,北疆地区总体多于南疆,且北疆多集中于迪化、哈密一带。据(三州辑略)卷二载:巩宁城(满城)不但在城市中心的鼓楼旁建有一座关帝庙供全城军民祭祀,而且在城内满、蒙古各族军民生活的地方还建有规模不等的关帝庙,抚兹城者,以治行为垣墉。《回疆通志》载:关帝庙碑在地区范围上,南北疆都有分布,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山川三分九里的农村也建,规制不一。吐鲁番的庙宇布局几同城置状,城中间为万寿宫,城东面有关帝庙一座,西面兼有风神祠龙神庙等,关帝庙与龙神庙从时间上皆为春秋致祭。[17]
(四)从移民迁居,佛教影响的角度解读
关羽在佛教文献中被视为护法伽蓝神,道教奉关羽为护法者,尊为“伏魔大帝”以示教义。道教为迎合封建儒家观念,被佛教吸收改观至祁福赐灵,求符建醮蔚然成风。季羡林指出新疆作为四大独立文化体系的交汇之地,商贾骈臻,文化交流繁盛。在乾隆年间(1736~1795),兵屯人口为陕甘地区占多数;参加屯田的人数众多,人口来源多样。[18]赵朴初在《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一文中指出:从事文史哲研究,不理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得不出准确之结论。[19]碑铭的建立背后多少与佛教紧密联系,市井之地,冠带之伦,于是改观。清朝统一新疆后,形成满人、汉人、蒙古族与回族、维吾尔人杂居的大集体,继而融合影响信仰的的变迁。在今奇台县, 仍有一座始建于乾隆时期的民间募建的关帝庙,虽然原来作为大清战神的关帝威武塑像已毁, 但此建筑却依然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20]
四、结语
据上分析我们得出新疆关帝庙碑的筹建,实非偶然。从碑时间的连续性与现存空间分布来看,当时新疆尤其康乾两朝的中原的文化统治下,民间社会的一种侧面反映。其碑撰文都显现忠义在人心、神庇边檄、宣敕武功的含义,因此本文认为清朝上层的政策与新疆各族民间的认同的结合是信仰得以传播的内因,也是庙碑建立的出发点,经济屯田所致的内迁,按就近原则,陕甘地区关帝信仰是新疆关帝得以延续的主要外因,构成新疆地区关庙碑的外部因素,是本土文化与西北社会文化的互融的一部分。但就碑文背后,可否窥之庙碑与佛教具体是怎样的联系?对同时期新疆与其他地区关公庙碑的建立又是如何施加作用力的,佛道信仰又是如何在碑中体现的,限于碑铭的残缺与资料的匮乏,只姑且认为是存在影响来做以结论。
[1]陈寿.三国志(36卷)[M].中华书局,1959: 563.
[2][3]李祖基.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的形成[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43-46.
[4]孙光宪.关三郎入关[M].北梦琐言(11卷).丛书集成初编本,93.
[5]门建军、郭院林.清代新疆关帝信仰研究[J].丝绸之路·宗教文化,2011(12).
[6][7]戴良佐.西域碑铭录[M].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342.376.
[8]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编.周轩、高健整理.《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M].(乾隆朝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1272.
[9]格琫额撰.伊江汇览[M].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新疆卷之《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10]薛仰敬主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11)[A].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309.
[11][18]袁大化修、王树楠撰.新疆图志·民政四·户口(43卷)[M].民国十二年刊本.
[12]和瑛.三州辑略·艺文[M]. 西北文献丛书整理影印.成文出版社,1985:256.
[13]许崇灏编.新疆志略[M].正中书局印行,1944: 74.
[14]傅恒等撰.亲征平定准噶尔方略(卷首)[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1.
[15]皇甫中行.文化关羽[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167.
[1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编.马大正、黄国政整理.曾炳熿.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宗教[M].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241 [17]王鹏辉.清代至民国前期吐鲁番的佛寺道观庙宇考实[M].2014(6):35.
[19]薛克翘.佛教与中国文化[M].昆仑出版社,2006: 13.
[20]薛宗正.奇台现存多神教庙宇小议[M].新疆文物,1987(3):44.
2016-12-20
马雪兵(1993-),男,汉族,甘肃省张家川县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硕士生。研究方向: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