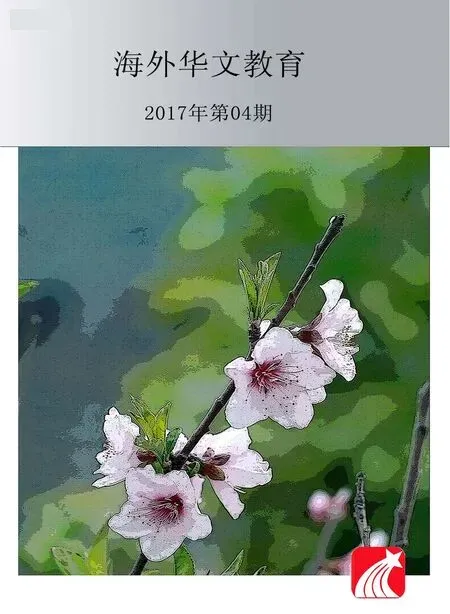高本汉论汉语汉字特征的启发
2017-03-09李如龙
李如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厦门361005;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厦门361102)
高本汉论汉语汉字特征的启发
李如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厦门361005;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厦门361102)
高本汉提出,汉语的“单音节、孤立”是从早期具有复杂的形式变化演变过来的,比英语更先进。汉语的特征是词义繁复、句法灵活、缺乏形态,单音词可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修辞上多省略和隐喻。他把“六书”归纳为单体象形、复体会意、借音和半表声半表意,如果理解造字法,认得少数象形字,学会一两千字并不难。汉语和汉字“辗转循环”,互动发展。由单音词到复合字,为别同音加偏旁,无语缀则造语助词。文言书面语超越方言并可与古人交谈,使人热爱古代文化。对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他热情肯定,但指出汉字拼音化办不到,因为汉语和汉字“非常适合”,废弃汉字,文言就难以保存。由于熟知印欧语和汉语,又无偏见和成见,所以能把“他者”看得透彻。
高本汉;汉语;汉字;特征
一、引 言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发表100年了。这部巨著对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基础上,高本汉后来还有许多关于汉语汉字特征的精辟论述,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了他的许多见解都是正确的、富于启发意义的。本文试就以往大家关注比较少的他的三本普及性小册子所涉猎的内容,谈谈学习这些有关论述的体会。这三本书是:
《中国语与中国文》,1923年作,张世禄译,1931年出版于商务;
《中国语言学研究》,1926年作,贺昌群译,1933年出版于商务;
《中国语之性质及其历史》,1945年作,杜其容译,由中华丛书委员会于1963年在台北出版。
下文引用时分别按照他的写作时间简称1923、1926和1945。
二、关于汉语的“单音节孤立语”及其评价
用惯了多音节的、富于形态变化的语言的西方人一接触到汉语,很快就觉察到汉语的“单音节的孤立语”的特征。关于汉语的单音节孤立语,很早就有西方的学者提出来了,正如高本汉所说,直到十九世纪,“许多人都相信,中国语缺少语词的形式变化,便表示中国语言是一种相当原始的语言,它还保持在一个幼稚的阶段,还没有产生出高雅的表达法……可是,这种说法不久就动摇了。”(1945:67)他提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的德国的汉学家Wilhelm Grube和Leipzig的论著已经对此提出质疑,而第一次全面论证来纠正这个错误结论的正是高本汉。他说:“散布于全世界,如非洲、澳洲以及美洲各区域的原始野蛮部落民族,他们的语言里,大部分都拥有非常复杂的形式变化系统。没有形式变化与转成语并不是原始的表示,而且甚至于恰恰相反……印欧语言的发展,也是向正好相反的方向走的,它们的形式变化,一个一个在逐渐消失。大家都逐渐在变向中国语的型式。”(同上)他强调了:中国语的“复合语词(composita)是很丰富的”,只是“单纯语词”(simplicia)“总是包含着——有几个例外,可是不很重要——单个的音缀”(1923:22-23);“没有一种单纯语词是由转成上的附添语所构成的”;“没有应用附添语来表示文法上的各种范畴……中国语正和印度欧洲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者)纯粹的论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1923:26-27)可以说,高本汉是为汉语的单音节孤立语摘去“原始落后”帽子的第一人。
为了说明汉语的孤立语是从更早期的复杂的形态变化中走过来的,高本汉就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他说:“孤立性是现在通行的中国语的最重要的特性;而它所指的是:语词没有形式变化,没有转成作用,不同的词类在文法形式上没有区别;可是凡是这些并不是中国语本来的和原始的特性……上古中国语在人称代名词上还有典型的格的变化……上古中国语中有很多的词族;每一个词族里面的语词都是从一个共同的语干孳乳而来的,它们形式上的不同有时可以很清楚地表示出文法上的范畴,如名词与形容词的对立,名词与动词的对立……这些个有趣的迹象都显示出原始中国语的特性……具有相当丰富的形态变化。中国语言具有孤立性的特点是经过转变而来的。”(1946:100-101)
在做出这个结论之前,他已经论证过,“中国语在原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主格与所有格的‘吾’,同时也有一个间接受格与目的格的‘我’;不过,在孔子时代,这个体系便已经开始演变”(1946:70),他还列举了许多“词干是如何的由音的转变,孳乳出不同的词来”(1946:75),如:官—宦,窟—掘,帚—扫,参—三,弗—勿,迎—逆,能—耐。他并说“西藏语是与中国语有亲属关系的,虽然关系离得很远。西藏语中元音的转换在动词的形式变化中是一直很规则的现象。”(1946:82)后来他还编了《汉语词族》的专书,用更多的语料来论证上古汉语的这种构词法。
也是在1946年,周祖谟在《四声别义释例》一文中提出了:“籍四声变换以区分字义者,亦即中国语词孳乳方式之一端矣。其中固以变字调为主,然亦有兼变其声韵者……汉语古代书音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之形态变化。”(周祖谟,1966:112-113)。后来周法高(1962)也用形态学眼光来解释上古汉语的变读现象。王力晚年研究古汉语这类变换字音以区分字义的“滋生词”时说:“欧洲语言的滋生词,一般是原始词加后缀,往往是增加一个音节。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因此,汉语滋生词不可能是原始词加后缀,只能在音节本身发生变化,或者仅仅在声调上发生变化,甚至只有字形不同。这是汉语滋生词的特点。”(王力,1982:46)他在这部《同源字典》中收了上古汉语音义相近、相关的同源字3000多个,可见当时的这种滋生手段是很能产的。把上古汉语的滋生词认为具有汉语特色的构词形态是顺理成章的。
从那时到现在,快70年过去了,上古汉语的研究和汉藏语的比较又发掘了大量的事实,做出了有力的论证。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外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出了许多新结论,例如:上古汉语有不少复合辅音,有多种词头或词尾的辅音,后来这些辅音的脱落就成了区分声调的依据(带紧喉音的成了上声、带-s尾的成了去声)。有的学者还提出,除了连绵词,上古汉语还有一些纯语音的词头,“谐声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有些异读反映古代的形态现象”(潘悟云,2000:122-124)。看来,从远古汉语到上古汉语经历过一番类型的演变,有越来越多的语料可做论证,因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一类型的演变。高本汉的这种说法是很有启发性的。
三、关于汉语的语法、修辞的特征
在本文介绍的三本书里,高本汉都用了整章的篇幅来讨论汉语的语法。他曾经用自己所理解的“广义语法”把汉语的语法特性概括为三句话:“语词意义的繁复错综,语句组织的空漠无定,书写上种种辅助记号的缺乏。”(1923:134)。这主要是针对文言文说的。所谓“语词意义的繁复错综”,主要是指常用的单音词分裂出许多不同的意义,在复合词和句子之中有复杂的组合,例如“上”可说“上边、上马、上有天”,如今还有“基本上、组织上”;“生”可以组成“学生、生肉、生子”。这类情况包含着词义的展延、词性的变换和词句中语素的多种组合关系,既有词的语法意义问题,也有构词法的问题,对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来说,这是一种综合性的难点。所谓书写记号的缺乏,指的是没有标点符号、不分大小写,其实还应该包括没有按词分连写。标点符号后来的白话文是有了,专有名词的大小写至今也没有被汉语接受,似乎并不是大问题,倒是词与词之间没有分写,使得汉语的词语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造成了外国人阅读中文的严重困难。这个问题不但还没有解决,可以说至今人们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大问题来研究。彭泽润教授曾经作文出书、奔走呼号过,也没有引起注意。这些广义的语法问题,正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现在研究汉语语法的很少把它作为研究内容了,但事实上是高本汉自己学习汉语的经验之谈,也确实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所存在的困难。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应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做好必要的研究。
至于“语句组织的空漠无定”则是对于汉语语法的全部特征的巧妙概括。包括他在三本书里经常提起的“没有形式变化和附添语”(指形态变化和语缀),“没有各种相当的词品”(即词类,有时也称“没有正式的词品”),“独立的语词演化成的助语词”,“应用一种井然不紊的语词序次”,只有最后的这两条,才是他认定的“语法特征”。他说:“中国文法,事实上最简单:主要的只有几条语词在句中的位置的若干法则,此外也就是若干文法上的助词的功用的主要规则。”(1945:66)
有几分奇怪的是,不仅是高本汉,好多用惯了富于形态变化的印欧语的语言学家,都说汉语是没有形态的孤立语,并且还认为这并非“原始落后”的标志,可是有些中国的语言学家却总是不放心,老在发掘“广义的”或是“中国式”的“形态”,一旦有人说,汉语没有词类,就要受围攻。连只能用在几条语词前后的词汇意义十分显著的成分也要认定为“词尾”或“语缀”,好像这是个光彩的帽子。
在再三说明汉语语法的简单之后,高本汉更多强调了,外国人学习汉语最困难的是语用修辞(“藻饰,文辞的修饰”)。在这个方面,他罗列了以下几项。第一,自由。“大多数中国语的语词意义的应用极端自由。”这对于学习的人“实在是个最严重的困阻”(1923:119)。“中国语的语句里,语词彼此的关系,没有形式上的表明,只有他一种主要的措辞方法,语词的序次,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畧资补救。”(1923:120)后来又说:“同一个不变的单音节的词可以分别当作名词、形容词或动词去用”(1945:60)。第二,简略。“中国语的语句比较欧洲语言实在是一种‘简略的辩论法’(brachylogical)……主辞和述辞,假使其中的一个可以从上下文里看懂的,就无需把它们表示出来。”(1923:121)第三,隐喻。“中国人的修辞法,经常特别有趣……要了解它,需要费许多心思”。(1945:62)他举的例子是“蒙泽”:受恩惠,“雪耻”:洗刷耻辱。第四,引证(quotation),他举的例子是:“以德报怨、坐井观天、唇亡而齿寒、塞翁失马”,伐柯:当媒人,“东床”、“而立之年”,“贵姓、令爱”等。这就包括了成语、典故和谦称。他说:“能用一个有历史依据的隐喻语,中国人最受欢迎。……依这种方法,渐渐集合成为专门名词的宝藏。”(1923:137-141)可见,他对于汉语的语法修辞的理解是很到位的。中国关于语言表达的古典传统不就是集中于研究修辞吗?“语法”只是百年来的“舶来品”罢了。
四、关于汉字的性质、流变及学习汉字的难与易
在向西方人介绍汉字的时候,高本汉一开始就强调了两点:“从它的字形上只能够看出它的字义,而不能看出它的字音”(1945:12);“中国文字的构造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发音的变化,完全不能从字形上反映出来”(1945:17)。前者说的是汉字的共时的表意而不表音的性质;后者则是说明汉字字形的历时不变的特征。可谓简明扼要。
关于汉字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演变,高本汉并没有拘泥于历来的“六书”的说法,而是重新归纳为“四个发展的阶段”:“最初有单体象形字,其次有复体会意字,再次有借音字,最后有改进了的借音字,也就是半表声、半表意的复体字。”(1945:16)这种概括是很科学的。象形、会意是完全不表音的,“借音字”就是“假借字”,表述更明确;“半表声、半表意”也比“形声字”的说法更准确。从字形上说,会意和形声都是两个部件合成的“合体字”。拿原来的“六书”来说,“指事、会意”其实并无大的区别,“转注”历来就说不清楚。概括为四个阶段,既准确明白,又符合一切文字演进的由形到意、由意到音、由单体到合体的一般规律。
关于汉字的“六书”,中国学者到了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才有人提出修正。唐兰(1935)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陈梦家(1956)的“三书”改为“象形、假借、形声”,前者缺了借字表音的假借,后者所缺的“表意”也并不是其他造字法可以代替的,都没有“四书”的说法准确。
更难得的是高本汉还分析了汉字的自源性和它的文化个性。他说:“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比西洋文字那样质实无趣,所以对于中国文字的敬爱,更是增进。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文字常常因为艺术上的目的而写作。书法学是绘画术之母……因为书和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常为书法家而兼绘画家……文学和书法又发生了密切的关系。”(1923:84-85)一个外国人能够理解汉字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意味,实在是不容易。
一般的西洋人对方块汉字总是一味惧怕三分,却不知道学习的难处究竟在哪里。高本汉由于摸透了汉字,很善于开导汉字学习的难与易。他说:“如果只求能读一点现代的教科书和报章杂志的话,则记熟两三千字也就足够应付了……只要能明了造字的方法,学习起来并不会感到太大的困难。因为你一旦认识了几百个简单的象形字之后,剩下主要的问题就只在辨认它的合体字……依照这种简单的、合理的方法去学,一年内记熟两千个字,也没有什么问题。”(1945:16)真正的困难是字音跟着时代逐渐改变,“中国文字的构造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发音的变化完全不能从字形上反映出来。”(1945:17)如“侈”从多得声,“的”从勺得声,后来语音变了,声旁就不能表音了。“只有完全机械地去记住某字即是口语里的某词,字体是由某两个成分构成”(1945:20)。
在《中国语之性质及其历史》的末尾,高本汉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要充分“估计学习中国语的困难”,他接着说:“困难完全看我们对于‘学习中国语’如何解释而定。如果一个人的目的只在能以官话或其他的现代方言会话,那么学起来自然非常简单容易;如果有更大的野心,希望能把文字也学好,那必须做到的工作当然就有很多,不过,也仍然没有什么出奇的难处;如果再进一步,有更高的抱负,希望能精通文言,同时能了解三千年来中国文学的各方面,那么,工作可就惊人了。我们已知的那些可能,大部分都只有靠长久的经验与广泛的阅读才能解决。”(1945:127)
汉字的总量多达数万,常用的不过二三千,在汉字汉语的教学中应该注重频度,常用先学、多学,这在汉语教学界早已引起关注,但是许多教材(尤其是对外汉语教材),还是经不起检验。至于如何在教学中为学习者尽量提供各种认知汉字的造字理据,掌握便捷地认记汉字的方法,依然没有引起注意,至少应该把声旁还可以类推的字、会意还可以分析的字罗列出来,编进初级课本和读物。至于最后高本汉所说的学习汉语的三种不同困难的境界,对于我们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就还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按照不同的需求去编写不同的教材,采取不同的教法。如果不加区别地“一锅煮”,初学者不是一下子被汉字的拦路虎顶回去,也会陷入说不清楚的“语法点”不能自拔,到了接触许多带着古汉语的成语典故,就彻底丧失信心了。
五、关于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其互动的结果
为什么汉语会采用表意的方块汉字,而这种不便表音的文字又能存活数千年?高本汉用他的睿智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个简单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1926:15)接着又说:“在纪元前的年代,中国语的形式与声音已经达到极单纯的局势,遂使其文字的结构具有一种特别的性质,辗转循环,又影响后来语言的发展,至深且钜。”(1926:17)关于“极单纯的局势”,他指的是“单音制,无形式变化,缺少仆音群(按即‘复合辅音’),语尾运用仆音很有限制:这些现象都是使中国文字成为方块头,发生许多形体类似,笔画紧密的原因,所有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文字,不特能够同行,而且极其自然,没有什么障碍。”(1926:32)
至于汉语和汉字怎样“辗转循环”,后来他还有许多论述,例如单音词不够用,便造出“复合字”(compound words多音词),为区别同音字,就加上表意的偏旁,没有语缀,便造出语助词等等。
关于汉字的长盛不衰,后来有中国学者周有光很精练、又很准确的说法:“汉字适合汉语,所以3000年只有书体的外形变化没有结构的性质变化。”(周有光,1992:120)
至于汉字的“影响后来语言的发展”,高本汉着重分析了汉语的文言和口语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文字是一种习惯上的表意字,只能适用于眼看,一究起古代的音读,则人皆茫然不知,泰然不问,不管是非,大家都只用着自己的方言去读就是了……许多世纪以来,文言和口语各自独立,分道扬镳。”(1926:44-45)但是文言和口语又会相互影响,正如他所描写的:“新增的语词,是不绝的凭空发生而融入于语言之中,旧有的语词多被废弃而摒逐于语言之外”(1926:46);“在中国学问的旧领域中,文言还可以施展很大的势力于一般受教育者的口语中,成千累万的单字和成语,从文言直接应用于口语,在高等社会或教育界极其流行,应用愈多,则愈有文质彬彬的风度。”(1926:58)
关于汉语的文言和白话的对立和融合,在中国早就成了热门的话题,上世纪初叶甚至还掀起了一场大风浪,白话取代了文言的统治地位,但文言和白话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停止,而是用新的方式在继续较量、继续调和、融合。
对于文言和俗语的分离,高本汉还分析了它的另一个效用。他说:“中国地方有许多种各异的方言俗语,可是全部人民有了一种书本上的语言,以旧式的文体当作书写上的世界语。熟悉了这种文体,就于实用方面有很大的价值。中国人要感谢这种很精巧的交通工具,不但可以不顾方言上一切的分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而且可以和以往的古人亲密的交接,这种情形在西洋人士是很难办到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古代的文化,具有极端的敬爱和认识,大都就是由于中国文言的特异性质所致。”(1926:45-46)
这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汉字使汉语的书面语具备了超越时空的功能,让不同方言区的人能得到沟通,现代人能读懂古人的作品。事实证明,只要是个智者,就必能“旁观者清”。高本汉的这些说法,直至今天还留给我们宝贵的启发。
六、关于汉字的拼音化改革
在1923年写的《中国语与中国文》,高本汉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为何不废除中国奇形老朽的文字,而采用西洋简单实用的字母呢?”他肯定,采用拼音文字,学童们“可以减省了一二年的苦工”,但是要付出两个代价:第一,“中国人因为要采用字母的文字,就不得不废弃了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学,又因此而废弃了中国全部文化的骨干……中国的文书一经译成了音标文字,就变为绝对的不可了解了……中国的文书,卷帙繁多,为世界最……这种翻译工作是完全不能实现的。”(1923:49)第二,“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标文字,那这种维系的努力就要摧破了……历代以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需要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在的基础降服于他人了。”(1923:49-50)后来他又说:“文字的改革,是一种打破传统势力的勾当……在中国改革上两条途径是很需要的……其一,便是废除旧式刻意雕琢的文言文,而采用直接根据口语的白话文,其二,便是根本推翻旧式的表意字,而采取音标文字……文言文如果用音标文字转录出来,势必不易领会,有了一大批同音异义的字,只有用中国字写出了才能区别得出。但是,前者的改革不必定要包括后者,因为现时口语上流行的中国语仍是用中国字口语写出来的……所以中国人如要废弃表意字而用罗马字母,必须弃绝文言文才行,虽然即使把文言文废弃了,仍不足以阻止中国文字的保存。”(1926:171-172)
二十世纪上半叶,不但中国掀起了文字改革运动,在日本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对此,高本汉说:“日本语与没有形式变化的中国语,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日语动词的形式变化有很丰富繁复的系统,因此中国文字不能适用于日本语,故当第九世纪时,日本已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即所谓假名……把日本文统改为拼音文字,势必过激,引起反感,终或无从实现,何况又非必要的呢?”(1926:161-163)他还说:“日本人在最近五十年中,已经茫然走入歧途,到了‘此路不通’的境地。他们想把那种不易听懂的日译汉字的羁绊摆脱,自1868年以来,尽是努力挣扎着。而最近几十年来,一般文化上、学术上,现代新名词仍用日译的汉字构成,输入于日本书中,却把这种羁绊反而增剧。”(1926:169)他曾经用一段优美的散文描写他对汉字的崇敬:“好像苍凉荒旷的古境中,巍然耸峙着一座庄严的华表,那倒影普映着东亚全部的文化,虽然是一片残败的墟址,而那华表却依旧完全保持着它的尊严,这便是中国文字与书籍上所表现着的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与书籍为亿万的生灵深深地敬爱着,占得这么一个强固的地位,除非是绝大的能力,休想把它动摇。”(1926:157)
虽然,高本汉只是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住了两年,作为一个汉学家,他是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的。他也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清除旧礼教、建设平民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声浪,高响入云。他们高呼着:用简单明白、不加藻饰的口语文来代替那刻意雕琢的古文,一切文学的、科学的论文杂志以至于诗歌,都需应用通俗的文体。”(1926:178)对于思想文化的改革,他是赞成的,看了一些白话文,他也觉得“确是很有生气”,“有些读来是很可以听懂的,但一涉及抽象的或科学的术语,或普通文化的名词,便完全失败了。因为这些术语和名词的构成,都极其简赅,听起来自然不会明了……关于高深的学理及科学上的事情,我们也必须拒绝这种表意字所铸成的术语,因为它们是在说话的时候不能听懂的。”(1926:180-181)他还说:“至于现时以中国字译外国的人名地名,便实在无法翻译了……这种笨拙的联合中国字以代外国的专名,如verdun之译为‘凡尔登’……谁也没有把握猜着所指是什么,至于报章杂志,一涉及到外国字的音译,便疑难丛生,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如果采用音标文字,这种困难,便立即可以消磨,所有外来的专名,都可以译得很周全了。”(1926:183)在当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还很热情地思考共同语的建设,提倡“创造一种完美的标准口语,不应带了地方色彩过于浓厚……须得与口语十分密切……沟通各种密近的方言……能尽量的采用最通行最普遍的语词”(1926:185-186)。在展望“中国文学的将来”时,就在日本人气势汹汹地侵占东北的时候,他就表示深信:“中国无论何处何时何事是常有伟大的艺术家的;当此风潮激荡,国难在前的时代,中国文学将如在荒漠中竖立起一座金字塔,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含着新生的力与美。如果已经理解及赞许过去与现在的中国的人,这是谁也不能怀疑的。”(1926:190)
可见,这位难得的欧洲汉学家对于中国的文学革命、汉字的改革不但是满腔热情地支持,而且做过深入的思考。他提到的问题,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语文运动中提出的关于推行国语、改革汉字、实行拼音化所讨论的课题。现在看来,他的许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单就汉字拼音化改革这一项来说,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开始,一百年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风起云涌、高潮迭起;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政府到民间,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或是在和平年代文化建设的原野中,从学术界、教育界到文化界,不论是主张“北方话拉丁化”或“国语罗马字”、抑或是反对拼音化的,都曾经做过认真的研究,贡献过自己的意见。到如今,“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在十亿人民中普及,并成为国际公认的拼写汉语的法定标准。站在今天的大门口,我们必须为一百年的汉语拼音运动做一个历史的总结,哪些是有益的经验,哪些是失误和教训?对于传承数千年的汉字,我们是否应该对它做一番历史的定性和定位?未来的时代,汉字要不要继续走拼音化的道路,究竟汉字能不能拼音化,要不要拼音化?如果不实行拼音化,还需要做哪些必要的改革,如何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眼前的现实无法回避的,也是炎黄子孙必须回答的。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高本汉以及许多探讨过有关问题的先人发表过的意见都值得我们参考。例如上文提到,高本汉认为,汉字改为拼音,文言就废弃了,所有的古籍是无法翻译成现代口语保存下来的。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许多文言文只能留给专门研究的少数人去读了,许多古文献也未必都需要翻译成白话保存;然而还有大量的已经进入现代汉语的文言词、书面语词,在改用拼音后能否保存下来?这也值得研究。试以带“然”字的词为例,必然、不然、固然、果然、忽然、虽然、偶然、自然,这些已经是现代口语的常用词,改用拼音照样能听懂;既然、寂然,焕然、涣然,豁然、霍然、或然,默然、漠然,未然、蔚然这些完全同音的和同声韵、不同调的“安然、黯然、岸然,盎然、昂然,当然、荡然,恍然、惶然,释然、使然、实然,依然、已然、怡然、毅然、易燃”就有点麻烦了,即使加了调号也不那么容易辨别;还有那些口语很少用的就基本上都要淘汰了:铿然、栗然、歉然、卓然、酣然、迥然、诧然、蔼然、森然、恬然……如果改用拼音之后,把数以万计的书面语词(包括口语里少用的成语)都抛弃了,是不是成本太高的“以文害语”了?
七、余 论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语言和文字,其中必定有共同的规律,也必定有不同的类型,还一定有各自的特征。共同的规律、不同类型的特征都是值得研究的,然而不论是理论上或是应用方面,语言文字的特征研究都应该是最重要的。汉语和汉字在世界上都显然是“特立独行”的,研究它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显得尤其重要。
为了了解特征,就要和不同的语言做比较,这是常理。如果有熟悉别种语言的大学者来研究我们的汉语,分析其特征,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旁观者清”是很难得的。自从西方人来到东方,中国成为奇异的“他者”,几百年来他们不断考察着这奇异他者的方方面面,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讨论。应该说,高本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高本汉所以能够在汉语的特征问题上贡献出好意见,是因为他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印欧语和汉语都做过深入研究,有真切的理解,而不是一般的感想或印象;二是不存在政治上的偏见或文化上的成见,真正能凭语言文字的事实说话,按语言学的一般原理分析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有关汉语汉字的特征的种种论述,都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当然,这些著作已经发表七八十年了,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当年的历史背景,还应该参考半个多世纪的后续研究,并用相关的社会实践来检验。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李如龙:《汉语特征研究论纲》,《语言科学》,2013年第9期。
李如龙:《汉字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走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彭泽润:《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唐 兰:《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王 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年。
周祖谟:《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Edifications from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W orks By K 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LIRul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 China;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102 China)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as a monosyllabic isolating language,had involved from completed form in early stage and was superior to English.Chinese is complex in semantic,flexible in grammar,and lack inmorphology.Amonosyllabic word can be a noun,verb and adjective all in one.Ellipsis and metaphor are common in rhetoric.He thought that if one can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know some pictographs,it would be easy to learn 1000 to 2000 Chinese characters.Chinese and its character interact and develop and thewritten languagemakes it possi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ancients.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thought that vernacular writing was good but alphabetization as impossible because Chinese and its character suit very much.As a foreigner to Chinesewithout bias or prejudice,hemade an incisive analysis on Chinesewith good knowledge to Indo-Europe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Chinese;Chinese character;feature
H021
A
2221-9056(2017)04-0437-08
10.14095/j.cnki.oce.2017.04.001
2016-01-02
李如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Email:lirulongchina@126.com本文是“汉语史观暨汉语史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念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始发表100周年”(复旦大学2015年11月)会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