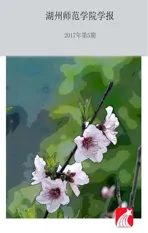空间、知识和权力*
——基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文本解读
2017-03-09孙米莉
孙米莉
(1.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空间、知识和权力*
——基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文本解读
孙米莉1,2
(1.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福柯借用“规训”这一关键词,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权力作出了独特的分析,他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权力观,而且建立了一种微观权力理论,对空间在其中的基础地位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作了深度分析。更为深刻的是,福柯指出19世纪是与以往不同的社会,这是一个借助空间把规训日常化、普遍化、内在化的社会。福柯激进的微观权力思想,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诊断,在理论和现实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规训;空间;知识;微观权力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当代西方最具有批判性和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被尊为知识界的“思想怪杰”和核心人物,他的思想新奇怪异,但又精辟入里。福柯并没有提出一个一般性的空间理论或权力理论,但福柯终其一生在思想和行为层面反抗着现代社会权力体系。反抗建立在深度认识基础之上,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等著作及《权力的眼睛》《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性的历史》等访谈中对现代社会的权力体系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而这种分析离不开对空间及知识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肯定。福柯指出,传统权力观在本质上把权力看成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定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了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和掩藏等等。在写作《规训与惩罚》时接触监狱,并与监狱具体打交道过程中,福柯认为传统权力观是不充分的,他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而应关心它的技术、战术和战略[1](P172)。于是,通过对19世纪一个“规训社会”的大量的相关职业和相关活动的考察,在福柯那里涌现出的观点,为研究他所使用的知识和权力的概念,为研究他对社会关系中空间维度的重要作用的认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些“规训话语”具体说明了内在于并且运作在空间的形式表征中的各种各样的权力实践,这种权力实践的运作空间正是福柯社会理论的一部分。福柯借用“规训”这一关键词,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权力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并对空间在其中的基础地位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作了深度分析,他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权力观,而且建立了一种微观权力理论, 对现代性进行了一种精准的诊断、犀利的批判。
一、惩罚权力的演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之需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沿用一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考察了惩罚权力的历史,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二是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再现”式惩罚;三是19世纪开始的,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从中世纪对罪犯的肉体酷刑到19世纪规范化监狱的演变,并非简单的由野蛮、残酷到理性、人道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复杂的影响因素。首先是生产与社会制度的发展使然。在18世纪之前,劳动力乃至人的肉体远没有工业经济中来得重要,没有相当的效用和商业价值。又由于生产条件、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因饥荒、瘟疫、疾病而死亡的现象极其普遍,同时,基督教轻视肉体存在,这一切导致人们对死亡司空见惯,也就能够较为包容肉体酷刑、公开处决一类的刑罚。后来,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社会状况不同,一切就不同了。其次,民众开始拒斥公开酷刑和公开处决。公开酷刑不再能够获得期待的效果。“在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了怜悯或赞颂的对象”[2](P9)。最后,司法权力的混乱和低效。司法机构大量存在,比如教会法院、贵族法院、王室法院等等,他们各行其是,相互冲突。司法改良者首先希望的不是更人道,而是更高效、更合理,能够更好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需要)的制度。
19世纪是“规训社会”,确切地说是从18世纪末发展而来。工业革命的影响与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得非法活动结构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被改造——“由于出现了新的资本积累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合法财产状况,所有非法行使权力的民间活动,不论是静悄悄的受到容忍的日常活动,还是暴力活动,都被强行归结为对财产的非法占有”[2](P96),从而“刑法改革产生于反对君主的至上权力和反对司空见惯的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力的斗争的汇合处”[2](P97)。最后改革的目的就是“用一种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机制取代临时应付和毫无节制的机制”[2](P97)。同时,因为自由被视为他者的权利和财产,惩罚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不是肉体的酷刑和消亡,而是把罪犯身体控制在一个强制的、剥夺的、限制的空间与体系中,监禁它或迫使它劳动,于是,运用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社会就产生了。
福柯指出,18世纪刑罚改革与其说是出于“人道”和“仁慈”,不如说是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或权力技术学。惩罚权力不再针对肉体,而是运用于灵魂。“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2](P24)总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解读出不同于传统权力的微观权力,一种使规训内在化、日常化、普遍化的技术、战术和战略。
二、权力微观化:规训的内在化与日常化
在福柯的著作中,“权力—知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围绕这个核心概念,具体说明了作为一个过程的权力和知识之间不可剥离的动态关系:通过在特殊的和地域化的场景中使用和建造知识,权力得以分布和实施,借助于知识,权力得以建立、保持和预设。比如,福柯讲到刑事司法,“……它的命运需要不断地由知识来重新确定”[2](P113),“在这种刑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人们可以发现惩罚作用点的置换,……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2](P24)。福柯指出,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福柯对权力的分析主要是对权力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和范围运作的理解,于是这种分析就与权力在空间中如何运作的认识发生了关联。对于福柯而言,与其说他在质询什么是权力、谁掌握权力及什么是权力的资源,不如说他专注于权力运作中的各种力量关系。对于福柯来说,权力分布于整个社会。因此,权力不是任何特定的群体、阶级或者机构的所有物(具有合法性的契约、法律和法规的司法体系)。因为权力呈现为许多不同的形式,所以权力不会单纯地从流通和生产领域派生出来,它也不能局限于类似于国家这样的机构。福柯关注的焦点是“微观权力”如何侵犯到我们日常生活和相互关系,如何构成了权力运作的条件和手段。他说:“在社会身体的每一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身;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它们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1](P176)很显然,福柯所谈论的、关注的不同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中权力的占有和压迫,而是泛指社会关系中各种具体关系与力量的相互作用。这就意味着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权力,每一个集团,每一个人都受制于权力,也行使着权力,这就是福柯所讲的“微观权力”。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非被占有的权力,这些权力运作的条件和手段,不仅仅服务于国家以及与国家对应的各种设施,而且服务于那些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二元理论中没有得到更好的理解的多种形式和路径。权力是多种多样而且普遍存在的,走向微观,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18世纪的经济变化却要求权力在更具有连续性的微观的渠道也能得到流通,能够直接贯彻到个人、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和日常行为”[1](P154),所以与权力斗争的方式也必须是具体的、局部的。这些微观权力在大量的地方性领域或者区域中如何生效、如何得到建构,是理解巨大的、集中化或者全球化的权力中心和体制化安排的基础性要素。
正因为如此,福柯还强调权力非重压,非全为负面。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2](P218)这里,也再次说明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的相互连带、相互构造的关系。通过创建、组织和监管空间的特定形式,规训技术在创造、塑造或者铸造主体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主体通过教育和培训扩散开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知识、价值和规范内化,创造出更有用、更有序和更文明的富有效率的个体和人群。借由建筑和设计,自律意识被灌输,并实现“价值的标准化”的内化在普通的人群中、特别是在劳工阶级中进行,通过相互联系的规训网路,社会规训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成为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控制的技术,这种规训及规训话语侵入并且殖民化了私人和公共领域,实施各种努力去控制、管理和提升最有效的、也是“最有益”的对娱乐和休闲时间和空间以及对劳动、监狱、学校等的时间和空间的使用,借助于这样的手段,空间的知识得到分析、得以设计,并且服务于最大功效的目的,最终确保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蒸蒸日上的城市和工业经济中财富的积累和社会运动的调节。
三、空间权力化:空间的关键地位
对于福柯来说,权力的运作在不同的时间经由大量的个体、机构和组织、以大量不同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发生。不过,尽管在传统的社会分析中时间相比空间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空间在社会的、经济的、政治运作中和社会组织中依旧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福柯在1976年与一群法国地理学者的面谈中,承认长久以来一直专注着空间,“……但是,我认为通过它们,我确实达到了我追寻的根本目标:权力和知识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3](P29)福柯明确提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3](P13-14)。对于福柯来说,空间就是关于权力和知识的话语成为实际的权力关系而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和抽象的概念寄居的地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和划分就变成了一种基本的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知识和权力日益增强,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以运作。《规训与惩罚》中,规训权力成功的关键在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包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而这些首先建立在对人的空间进行分配、对时间进行控制、对动作进行规定的基础上。
无论是具体的规训技术还是全景式监狱的产生,都离不开对空间进行分配和控制。“纪律又是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穿纪律的保护区”[2](P160),规训把身体分配在不同的适当的空间,使其发挥最大效能,一个基本的方法是把身体禁闭在某个地方,医院、军队等机构的权力,也是通过限制身体的离开才能运行。为了更仔细和有效的控制,权力的运作需要把空间进一步划分,寻求更灵活更细致的方案来利用空间,如对空间进行分类,形成空间的等级序列。同时,在规训中,“各种因素是可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他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他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2](P165)。这种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规训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
福柯在研究18世纪的医院与监狱建筑改革的同时,研究了边沁1787年的设计,并把它当成是强调纪律的社会中空间、权力和知识交织的典范性例证。这种全景敞视建筑四周是一种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安置一个需要被监督被禁闭的对象。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2](P224-228)
边沁为监狱建筑设计的全景监视监狱被认作是规训空间实施最有效管理的理想设施。福柯进一步阐明,“全景敞视监狱”表征的是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规训技术的一种一般性图解。边沁提出的适用于监狱的全景图式,应该也能够适用并且吸纳进入其他的领域和空间。全景监视监狱这样的建筑,使得规训注视、“监视系统”以及“权力的眼睛”成为典范,继而成为变成机械化生产的一种必要的、基础性的部分,变成在发展工业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分工中权力运作的基本机制。
除了对空间的控制,规训技术还要求对个体在时间上的控制,例如,由宗教机构(如寺院和修道院,还有军队)的活动引发的时间表可以被学校、监狱、车间和工厂吸收、采纳和转换。需要强调的是对时间的监控和精确使用在受到管制的空间中进行。由此,福柯开发出了“驯服的身体”这个概念,这种“驯服的身体”作为权力、权威以及各种规训活动的实施主体,构造一种“身体的解剖政治”作为认识和控制空间中身体的手段。规训权力并不是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来征服个体,也不是运用主流意识形态来控制整个社会,而是通过空间安排、活动编码、时间控制和力量组合等微观技术,以及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手段来规范身体、训练身体。身体就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中通过规训权力的应用被锻炼、被驯服、被操纵。经由空间控制,创造出现代社会需要的“驯服而有用”的身体,每个人成为机器中的一环,“这里,权力并不完全属于某个单独可以对他人实施控制的人。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我认为这就是19世纪确立的社会的特点”[1](P59),规训的内在化、日常化、普遍化得以实现。
福柯指出,空间已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重要因素,“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3](P18)
福柯对现代社会空间的分析强调了特定的空间如何被规训话语和权力、知识技术生产、构造、控制和规制,强化着列斐伏尔的断言,即需要把鲜活的、创造性的使用空间视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作用中的一种基础性要素。
四、评 析
福柯研究规训权力过程中对空间的重视,为社会研究、哲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同时,在空间基础上构建的“权力—身体—知识”的三维关系成为权力分析的基础,这也是福柯对现代性的一种诊断,意在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探求人的自由、解放之路,并为之后的空间社会学、身体政治学等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首先,福柯对空间关键性作用的强调为后人深入开展空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作用,为社会研究、哲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提供了重要启示。苏贾曾这样评价福柯,“他走的路径是一种整合性的路径,而不是一种解构性的路径,在紧紧地抱住他的历史不放的同时,给历史增添了关键的连结,这种连结将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空间、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4](P32)
福柯对现代社会空间的分析强调了特定的空间如何被规训话语和权力、知识技术生产、设计、构造、控制和规制。它们具有特定的功能性目的,其一般性的目标是制造和操纵驯服的身体,或者是单个的个人身体,或者是个人的聚集体的身体。于是,福柯对一种现代规训社会的分析,就是对在物理景观的发展中的空间、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交织的规训社会的分析,在这种物理景观中,建筑是构造各种关系的突出手段。19世纪是规训的社会,并不是说之前不存在规训,而是19世纪的规训是内在的、普遍的和日常的。这与把鲜活的、创造性地使用的空间视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作用中的一种基础性地位不无关系。
其次,激进的微观权力思想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诊断,一种揭露,一种批判,产生了巨大影响。《规训与惩罚》完稿时间是1975年,距离福柯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1970已有五年,《规训与惩罚》被视为福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文本。张一兵教授在《回到福柯》一文中指出:“它直接映现了福柯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向:从认知话语结构的批判到资产阶级政治现实中权力的批判。”[5](P24)这一文本中,福柯细致考察并试图呈现,借助于知识和空间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资产阶级新型政治权力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即在认知(工具理性)开展中对政治肉体的隐性规训支配”[5](P24)。启蒙运动以来,具有自由自觉的主体性(大写的人)战胜大写的神,张扬的理性战胜蒙昧的信仰而成为现代性的两大根基,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等都致力于宣扬和捍卫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而尼采、伯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对理性和现代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韦伯对现代性的“理性化”(合理性)保持乐观的态度,但同时也有一定警惕。他认为资本主义理性化必将导致两难的困境,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分裂。而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并未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欢乐、幸福,相反,却是永无休止的劳作、身体的疲惫、心灵的倦怠、价值的迷失。所以他们反对理性、消解现代性,反对普遍性和“宏大叙事”,主张多元性、差异性,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主张把人从现代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探求人的自由、解放之路。
探求解放之路,先要进行揭露与批判。福柯的社会权力理论,没有依从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路径,不是抽象的讨论诸如民主、公平和法权等宏观概念、宏观权力,而是将权力场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角落,揭露权力关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根毛细血管。福柯认为,近代以来权力运作机制中那种残酷的、暴力的、血腥的、直接的成分正在逐渐减弱,看似是“人性”的胜利,是更加“人道”的表现,但实际上这种新机制——规训——对人的控制并没有减弱,而是大大增强了。它借助于空间、知识,借助于一系列新的运作条件,不仅控制人的肉体,还控制了人的精神;不仅控制了时间,还控制了空间;不仅控制了人的现在,还控制了人的未来。权力借助于这种规训技术和战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受监视和约束,形成了一个规训社会,而这种规训是日常的、内在的。这种日常的、内在的规训,在西方民主社会所标榜的一般社会运行模式背后,透视出一种并不直接存在于传统政治领域的新型奴役。更为人所不易察觉的是,这种新型奴役恰恰是作为传统专制暴政的替代物即“民主”与“科学”的形象而出场的。 “福柯断言:正是在以认知为控制和支配的隐性权力线之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构了有史以来最精巧的微观权力物理学,也建成了人类文明中第一座现代灵魂的全景规训式的牢狱”。[5](P24)
从表面上看,福柯的著作所关注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主题,诸如精神病、麻风病、医院、监狱、性等一般学者都不太愿意涉及或者很少涉及的领域,但这些纷繁芜杂的表象背后潜藏着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其是“一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6](P78)。这不仅与福柯受到人本主义和尼采思想的影响有关,也和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总之,福柯激进的微观权力理论,在理论和现实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
[3]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周宪,许钧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张一兵.回到福柯[J].学术月刊,2015(6).
[6]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杨 敏]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iplineandpunish”
SUN Mili1,2
(1.School of Marxism,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2.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0, China)
Foucault uses the “discipline” of the word in the bookDisciplineandpunish,tomakeauniqueanalysisofthepower,henotonlysubvertsthetraditionalconceptofpower,butalsoestablishesofamicropowertheoryofspaceandmakeadeepanalysisthebasicstatu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knowledgeandpower.Moreimportantly,Foucaultpointsout,nineteenthcenturyisdifferentfrombefore,anditisasocietywhichemploysspacetomakedisciplinedailygeneralizedandinternalized.Foucault’smicropowerthoughtisakindofdiagnosisofmodernity,andtherehasbeenanextensiveanddeepinfluenceintheoryandpractice.
Michel Foucault; space; knowledge;micro power

2017-01-04
孙米莉,讲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B565.59
A
1009-1734(2017)05-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