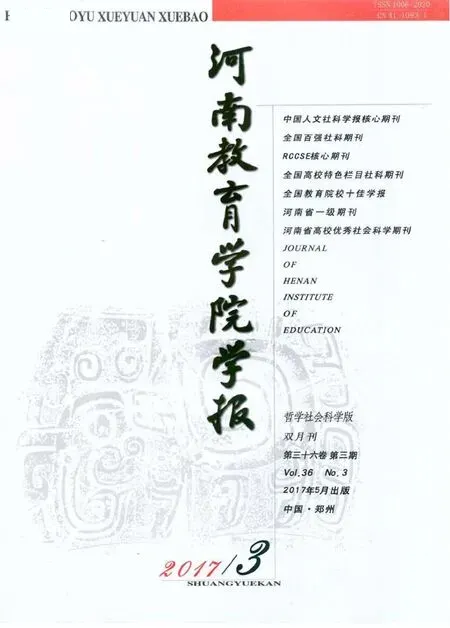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特性浅考
2017-03-09陈翔宇
陈翔宇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特性浅考
陈翔宇
与西方美术教育以及近现代美术教育相比,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和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官民统合的教育机制,培养人文素质的教育目的,“两实两虚”的学习对象等方面。这些特性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文化条件、教育环境等众多因素决定的,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当下美术教育仍有很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教育机制;教育目的;学习对象
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1867年左宗棠在船政学堂设“绘事院”和1905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课为标志。先秦至19世纪末的中国美术教育则被称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阶段。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美术教育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形成了独特的品质。
一、官民统合的教育机制
“恒稳性”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发达的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学校教育始于先秦,美术学科(包括书法在内)是古代学校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明德”为目的、关注“文化教养”的美术教育主要在庠、序、学等学校教育机构完成。这些学校以“六艺”为教学内容, “六艺”中的“乐”“书”和美术教育有诸多的共性。作为中国古代美术的根基学科——书法,一直贯穿于古代学校教育的始终。西晋“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1]3211,出现了独立的国家级书法教育机构。隋唐时期,学校教育进一步完备,除了归国子寺(监)管辖的“书学”,朝中的高官贵族子弟还在弘文馆、崇文馆习书。明代国子监以及地方府州县学都有书法课业制度。自秦汉书画分立之后,绘画的“存形状物”功能得以强化,虽然东汉昙花一现地出现了鸿都门学,北周设立了麟趾学,但绘画教育总体上没有以独立的形态进入学校教育。直至宋代,徽宗赵佶于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置书、画、算学”[2]361,以美术学科作为独立教学内容的教育机构由此出现。可惜“画学”只存在了两年时间,徽宗赵佶在崇宁五年(1106年)春正月丁巳“罢书、画、算、医四学”[2]501。
相较于学校教育,独立的图画教育更多的是由翰林图画院这样的创作机构来完成。汉代宫廷开始设置“黄门画工”“尚方画工”,这些画工在创作之余交流绘画技艺、传授绘画技法,这种形制成为古代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在集贤院、秘书省等画作收藏、鉴定、修复、创作机构中设立了“直官”制度,画手在“图画直”的指导下接受美术教育。翰林图画院制度在五代两宋时期延续了二百多年,画院设有待诏、艺学、祗候、学生等职。画院的“学生”虽与专门从事学习的学生有所区别,但画院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建立的具有部分教学性质的机构。宋亡以后,翰林图画院制度随之中断。但元代的“梵像提举司”,明代的“仁智殿”“英武殿”“文华殿”,清代的“画院处”等都兼具美术创作和教育的功能。
璀璨夺目的工艺美术伴随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个进程。以工艺传承为目的的“百工”美术教育在先秦时期已经独立,主要隶属于王家官府。“百工”由“工师”统领,教育在制作过程中完成。秦汉时期,政府机构内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百工”,“工师”既是行政长官,也承担对百工进行技艺指导和传授的任务。这一时期,以家庭作坊为依托的民间百工创作与教育机构开始形成规模。唐代的工艺创作和教育机制更加完备,少府监和将作监可视为具有“教诸杂作”的专业技艺教育机构,工匠“在资深匠师和直官的指导下,有四年、三年、两年、一年不等的教习学制,还有为期四十天的短训班”[3]67。宋代的工艺美术教育非常兴盛。宏观统领机构包括少府、将作、军器,具体创作和教育机构包括宫廷内部设立的文思院、东西作坊、后院造作所,以及各地方庞大的官府作院、作场等。元代则设有匠作院,工部又下设“诸色人匠总管府”等来掌管百工技艺。明清两代的官方工艺美术教育,是在“内廷作坊”“造办处”“织造衙门”等机构中,通过熏染、制作过程来完成的。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得到了高度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佛教美术的兴盛。和其他美术活动相比,佛教美术创作具有很多特点。比如,经历时间长,创作队伍规模大,宗教文化要求严格,涉及统筹、管理、利益分配等诸多管理方面的内容。这就推动了以开凿石窟寺、雕塑、壁画为工作导向的“行会”制度的出现和发展。画行虽以保护同行业的利益为主要目的,但同时在画行内也形成了依师徒、行尊卑而成的教学关系。据记载:“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遂潜写吴生真相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生观之。”[4]208就此处提到的“讲席”来看,在画行内存在“聚众授课”性质的教学活动。行会还通过对本行业祖师神进行纪念、祈福的活动强化师徒关系,对行内技艺传授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以后,行会转为帮会、会馆等形制,其教育功能得到延续和发展。
随着城市文明的萌芽和繁荣,独立的民间性质的行会、画会、家庭作坊等开始出现,并成为一个个“半封闭的”教学系统。这一点在手工艺和晚清绘画领域表现得比较突出。从元代开始,在丝棉纺织、制瓷、家具木作、造园、版刻刊印等行业,开始形成独立的民间机构,这些机构手工艺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师徒传授”与“父子传授”等。这种私密性较高的教育方式,一方面促使特定技艺向深度发展,形成了许多“绝活”和“特产”。但这也为许多工艺技术的失传布下了阴霾。晚清时期,商业文化的兴盛导致了“扬州画派”“海派”等艺术流派的诞生,这些画派促使文人画家雅集越来越频繁,并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画会活动。文人画家通过画会活动互相观摩作品,相互交流切磋创作心得,形成了一种有组织、较灵活的美术教育机制。
二、培育人文素质的教育目的
自先秦以来,中国艺术就是特定文化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以工艺样式传承为目的的“百工”美术教育还是六艺教育,都在于“明德”而非“执技”,正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5]96。这一教育目的源于孔子的“绘事后素”文艺理论。绘事后素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指出必须在懂得了色彩的伦理标准之后才能从事绘画[6]28,后世逐渐发展出了“鉴戒贤愚”的艺术功能观和艺术教育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充的“劝善惩恶”论[7]98,张彦远提出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8]261等。这些理论都认为,画家需注重个人的品行修养,并在美术作品中表达于世有益的观念。
另外,古人将画作品格的高低和作者的文化修养、精神气度、生活阅历等联系起来考察,深化了艺术品和创作主体的“气韵”关联,并进而提出了“怡悦性情”的艺术功能和艺术学习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顾恺之的“传神”论,宗炳的“畅神”论,谢赫的“气韵生动”论等。他们都认为“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9]161,因此要求画家“胸中有万卷书,目饱前代奇迹,又车辙马迹半边天,方可下笔”[10]201。这种美术教育观的实质即为美术教育不应局限于技法传授,而要注重在哲学、文学、书法、生活体验等多方面进行修习。
三、“两实两虚”的学习对象
学习对象,也就是“师”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程中,“今人”和“造化”构成了“师”这一概念“实”的方面,“古人”和“心源”构成了“师”这一概念“虚”的方面。
首先,每一时期美术创作的繁荣必然和“今人(当时直接指导创作者的师资)”力量的繁荣密切相关。比如,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第一个繁荣期的南北朝时期,重要画家都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荀勖师于卫协,史道硕、王微师于荀勖……各有师资,递相仿效,或自开户牖,或未及门墙,或青出于蓝,或冰寒于水……”[8]168李永林认为:“魏晋南北朝绘画教育的兴起,首先表现在这种密切而连绵的师资传授关系上。”[3]44又如,作为中国古代美术创作第二个高峰期的唐代,也得益于师徒制美术教育的成熟,吴道子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这类“老师”在生活中和徒弟“实实在在”生活在一起,在美术教育过程中“真实”地演示每一步作画过程;弟子通过“直观的”观看、领悟、描摹、创作来完成美术学习。
其次,美术是一门视觉艺术,美术家面对的现实世界既是他们的表现对象,也是他们的学习对象。美术史上,每当艺术教育思潮重新回归到以“造化”为师的主线时,艺术创作也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比如,“外师造化”[8]200理论的提出,不仅促使唐代人物画发展为中国古代绘画的高峰,也使得鞍马、禽鸟、花木、台榭、舟车等美术学科获得独立。两宋绘画教育,尤其是官方的画院教育机构,将“师造化”作为美术教育的核心导向,使宋代绘画,尤其是花鸟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术教育涉及的技法、美感、风格等问题,都是在画家在对现实世界的观察、研究、体认过程当中完成的。
再次,“师古”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其实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师,是借“师古”之名而达到传承文化之实。这一理论不仅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特征,还高标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气质。“师古”源于孔子的哲学理论“(对待典籍应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1]69。美术教育理论将其演化为:“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12]105毫无疑问,画家所师的这个“古”,更多的是一种“意境”“感受”“氛围”“审美导向”方面的问题,这种东西是艺术中“虚”的部分。在美术学习和教育方法上,“体悟”就被当成了主要的方式,“临摹”则成为“师古”的必经途径。
最后,作为创作主体的“我”也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将“我”对象化,尊重自我内心的体悟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又一重要特征。张藻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8]200的美术教育理论。既然“我的内心世界”可以作为艺术家的老师,那么这个“老师”的什么品质是最重要或者说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是“气韵”。正如董其昌所言:“气韵……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9]249可见,开阔自我的眼界和心性,进而将其表达出来,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终极目标。当然,“师心源”也是最难以企及的。范宽对“师古”“师今”“师造化”“师心源”的关系做了简短而深入的阐释:“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14]379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从发端伊始,就兼具了培养人文素质与传承技艺的功能。在这一教育功能观的指引下,形成了独特而庞大的美术教育体系、美术教育理论和美术教学实践。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独特性恰恰是这一教育体系培育出来的,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和中国古代文化特性是相适应、相匹配的。反观当下美术教育,在西方美学观和教育观的主导下,出现了一些和中国文化不相适应的美术教学体系。这不仅有碍于中国艺术的繁荣,更妨害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本文的梳理希望给当下艺术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实践方向。
[1] 薛居正.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宋史 [M].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
[4]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
[5] 礼记[M].陈澔,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李一.中西美术批评比较[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
[7]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8]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9]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10] 赵希鹄.洞天清录[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11] 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12] 张丑. 赵子昂·自跋画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4] 岳仁.宣和画谱[M].岳仁,译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On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AncientArtEducation
CHEN Xiangyu
(SchoolofArt,HainanUniversity,Haikou570228,China)
Compares with the western art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art education, the art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has a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which mainly respects in the integration education mechanism of the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the humanities, the “two real and two imaginary” learning objects, etc.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determin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specific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Although it has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ts teach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achievements still have a strong reference and guidance on the current art education.
Chinese ancient art education; educational mechanism; educational purpose; learning object
1006-2920(2017)03-0105-04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7.03.015
陈翔宇,海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海口 570228)。
(责任编辑毕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