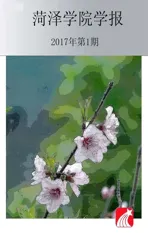略谈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的新可能
——以中国人物画工作室写生实践为例*
2017-03-09任海丁
任海丁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辽宁沈阳110000)
略谈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的新可能
——以中国人物画工作室写生实践为例*
任海丁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辽宁沈阳110000)
通过对今日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模式的一般性描述,分析了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实践所遭遇的“搬运”困局,映现出今日中国画“语言-内核”逻辑的两难。以中国人物画工作室的写生实践为例,探讨中国人物画写生的一种新的可能路线:它来自实践的客观直观与反省检验的综合。最后,试图展望并分析这种新可能写生路线或将带来的、中国人物画再发生的实际意义。
中国人物画;写生;实践;个体
一、目前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实践的“困局”
一般在学院中国人物画的写生训练中,除去基本的造型能力培养以外,其目的指向更多地在于如何使画种的文化根性在绘画形式上应用于具体对象的描绘。也就是说,在实践上,一方面要将西方写实性造型观构建并衡量写生造型的正当性;一方面是要把古代绘画的形式语言抽离出来,以一种“形式配置”的方式进行处理,将之组合到写生人物画的表现中去。我们经常见到的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实践,就是这种“组配型”中国人物画。
这种“组配型”中国人物画的发生,其来有自。20世纪初呼应着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美术革命”,使中国画丧失了自身传统的合法性。在一种强力意志推动下,代之以“新人文艺”的功能上的诉求,中国画做超越自身的“上升”运动已成亟须之务。当其时,中国画实践新资源的获取,最便捷的方式当然就是“拿来”,尤其在人物画上有西方绘画的直接参照——徐悲鸿早年提倡的“改良论”,就建基在对西方写实人物绘画观念与技巧直接“拿来”的基础上。诚然,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流汇与嬗变是艺术发展正常现象,但是过于自觉并将之快速地做拼接与组装,就成了问题。如果说明代波臣派的容像画实践,对外来艺术形式的吸收是适度的话,那是因为波臣派画家们相当自然节制地撷取他异的表现方法来充实自身,比如波臣派的容像画对早期古典油画明暗法的少量引用、对体积视幻感描绘的微妙线性转化、摒弃强光照下的衣料质感描绘而保留了本土书法性的衣纹表达法等等。“拼接与组装”的不恰当的例子,可见于清代康乾时期的宫廷叙事画。在权力意志主导下,清宫叙事画几乎成为了他异风格恣意拼接的范本。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马箭图横幅》(佚名):人物与宫殿的描绘,是处在平行透视法下的明暗造型表现,完全同于欧洲尼德兰绘画的表现方式;而树石水岸则又是明代浙派传统风格的画法——此两种不兼容的语汇在气息与表现上的隳突窘窒,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事实上,最初的学院中国人物画的写生“拿来”,就是在波臣派的适度与清宫叙事画的鲁莽恣意的夹缝间前行。欧洲写实绘画的精义如何与传统笔墨语言相调适,确是严峻而困难的挑战。如说早期学院中国人物画的“徐蒋”写生体系,颇为艰难地开辟出不同于波臣画派和清宫叙事画的一条路线出来,而后来的学院中国人物画的写生实践,就未必能有这样的突出表现了。其原因,一则最早的学院中国人物画家,或得欧洲写实绘画名家亲炙,或承有传统艺术余荫,第一手经验新鲜而深厚,后来的画家无有这种特殊的经历;二则西方艺术在20世纪急速转向,泛化的媒介表达成为艺术主流,而作为“拿来”资源的西方绘画,于1960年代后不再形成具宣言性质主张的流派,或说已经来到了它的衰落期,很难继续输出有力的观念与技巧。也就是说,今日学院中国人物画“拿来”之路已不大再有可能;同时,既然学院中国人物画有着一个“拿来”的前身“传统”,后来者的实践重心也难免习惯性地停留在资源“组配”的角度上,虽然后来的组配,较少来自西方而更多地出于中国传统其它画科的资源。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今日人物画写生常见的方式:作为一种表征画种内核的“中国画”语言形式应用。比如,对人物形象的表现语汇,并不出自直接的观察提炼,或出自山水画的线群与皴擦关系模式,或出自大写意花鸟画的点厾用墨语法,甚而是不顾彼此“上下文”的直接“搬运”……乃至为了搬运来的形式语言自身的完整,不得已破坏掉人物的直观形象感,也是总有的事。这个过程中被给予高度关注的,很难说是人物的表现,却是组配的合法性及其巧妙与否的问题。
可以说,学院中国人物画前驱的实践,可以不顾及或较少顾及表现上的中国画合法性问题,因为亟须打破的正是合法性的“束缚”。但“85新潮”以后,90年代兴起的传统文化回归热,在学院中国人物画的实践取向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一种扭转:今日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路线恰恰不再是前驱们“摸着石头过河”的藉外而内的改良实践,而是惮其矫枉过正的中国画内核的形式持守。似乎只要将传统中国画语言拆装再组配过来,只要重新组合起来的配件行使了代表传统审美内核的符号权即可,而这几乎已成为今日学院中国人物画的写生观了。不过,这也正是它的一个表现“困局”:画中无人,只有传统语汇的拥挤的自我表现。
画家朱新建曾对中国画的表现问题打过一个“瓶鹅”不共在的比方。这个比方来自一个瓶中鹅的禅宗公案,大意是:把一只鹅自小养在瓶子里面,瓶中鹅长大以后,问:不破瓶不碎鹅,怎样把鹅取出来?禅宗公案提示的问题,就是最初的行为因——先把鹅养到瓶中,造成了后来结果的两难处境。这个公案用来比喻上述中国人物画问题,也似乎很恰当。一旦确定了何谓中国画,那它就只能做该概念允许的事,如果它做了该概念不允许的事,那它将不再属于这个概念:中国画。那么,既不“破瓶碎鹅”,又想赢得一种超过限定的表现,这在逻辑上是困难的。符合逻辑的干净做法,便只有非此即彼的两个:概念的中国画的保守或者取消。这个逻辑的困难,出自90年代后有关中国画的考察的角度。它同样基于简单的中西之辩争,是行改良的前驱们的救亡与图存的文化考量问题“余绪”:只是此时紧迫的“要着”,是已然成功“救亡与图存”后的先进与落后、独立提领的民族文化问题。换言之,即是绘画中本土文化根脉于形式中的保证问题。这是一个不同于“救亡”的后起的文化利害问题。
如将这样的文化利害问题,拿到绘画自身中去解决,那么所谓“中西之辩”的出发点,就有着绘画中“圈地运动”的味道——片面地在中西绘画的差异中寻找“中国画”特殊性的东西作为它的“文化根脉”。无论上述的保守还是取消之论,所依据的前提仍都是一个——作为“中国画”,都已经被设置了一种前限定,划好了圈子。可这种被动辩白式的考察会废弃一些它认为是无关这个整体线索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过度紧张于中国画工具技术层面(语言)与艺术意味之间的关联。因为二者的动机都是出于对中国画“文化内核”的“鸡肋”态度,事实上都认定了中国画的文化内核必须要固锁并对立于传统形式才可以得到认知与保障。无论在中国画保守或取消的左或右,弃与留,都反过来强化了作为“中国画”实体的静态特征。最为关键的,它从文化“利害”目的出发,刻意寻找与之适配的绘画语言形式,并多少把这个“组配”过程等同于艺术表达本身的问题。这样一来,绘画形式与文化层面的艺术理解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处理得过于简单,同时“圈地运动”把一种动态的艺术发展可能性取消了。也就是说,这样的考察视角,即文化“利害”的角度,把人物画表现与中国画传统语言的形式联接性本身,看作了本质性的终极的内核,却忽略了它与社会整体范畴之间的、实际上的功能性交渡——相对于社会整体范畴,在画种内部的形而上的价值体系不是终极性质的,它也是一种历史的功能性的历时结构。
《庄子》有寓言“濠梁之辩”:在知鱼还是非知的论辩就要无止尽的进行下去的时候,庄周打断惠施那一句很关键——“请循其本”——这样就把问题交还给了更加基本的层面。正是由于同在“濠梁之上”,才产生了鱼乐的知非知的问题。同样,中国画问题大约也并非是在“中西之辩”中确立本体的问题,而在于绘画本身的“濠梁之上”。这大约才是所循之“本”的“本”。所谓“中国画”在明清时代之前,在西画的进入与发展还产生较大影响以前,也无非就是绘画。其中各个流派有异,但更多的只是审美趋向差异问题,无关文化内核的自我确认。当其时这原本是自明并且无待的。西学东渐,“中国画”自否与自保,则均要从其中提一根线索串联成一整体——清代以降,中国画界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不能不说是某种退守性的主张,这种理论眼光或不是比较积极的。应该说,在画种概念内部进行方式更新,可以视作是旧有的中国画理论视界自身的逻辑困境,它带来一种中国画的外部环境的某种事实,也的确促成了今日紧张的文化焦虑和消极意义的更新意识。按此,不止人物画,中国画的更新也许会始终陷在一种内核形式化的、相互“搬运”的组配指证循环里。
二、中国人物画工作室的写生实践的启示
中国人物画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是由鲁迅美术学院赵奇教授主导的创作教学单位,其方向是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研究与实践,负责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及其学业的独立发展。从1997年到2016年,经历了二十个年头的人物画教学实践的工作室,曾到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兄弟院校做过公开展览交流并得到认可赞同,很多毕业生均已取得个人学术与事业上的成功,此不赘述,作为学院中国人物画的现当代实践,工作室一直强调着并贯穿在教学中的写生路线,才是于今时更有汲取意义的中国人物画路向实训。
如前所述,中国画问题实质上隐含着民族自尊及其文化战略等社会问题,因此今天中国画问题比以往要复杂的多,但这通常都发生在艺术与绘画事件本身以外。对于中国画,无论保守还是取消,都体现为社会学意义上文化利害论,而文化利害问题是不可能在艺术以及绘画内部进行解决的。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它需要各个专门学科之间的通融与协作,综合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识及心理领域的认识与研究,才能够有效的讨论和判断。单单就绘画理论本身来处理它是很困难的事情。实际上作为画者(手工性的),从事艺术实践,最终不免侧重于它与具体个人相结合的全部,即绘画行为承载者的身心与绘画行为的契合,尤其在中国绘画发展理论已经走到两难境地的时候。也正是在这里,工作室写生实践的路线性就显得颇可思考:写生作为一种画者和对象之间的“晤对”过程,于其中重新体会并认识绘画行为这件事本身,中国画合法性的“组配”考量倒要退居其次。这一点也正是工作室写生观的基点:从个体的实践情境出发,绘画先要交给绘画主体的观察与思考。
工作室的中国人物画教学并不复杂,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修习,都是直接写生。其写生路线的特殊之处,就是通过个体的写生实践,辩证的看待中国画传统与绘画本身之间的关联。这与前面说过的“内核”形式化的“中国画”语言应用的那类写生不同,它多少是试探性的。一方面它要求直面所看到的客观事物,做到某种直观;一方面它又要求调动已知的传统绘画的语言资源,作为检验与反省的材料。只要做过长期写生的画家,就会知道画者和对象之间的“晤对”,是一种关于打“照面”的至深孤独与无助的遭遇、一种观察与思考的“无穷动”——怎样把觉之不尽的对象感受定型、捕捉、并呈现出来,永远是件神秘而困难的事情。20世纪伟大的写生画家的实践,都包含这种直观与反省的无穷动要素:例如塞尚、贾科梅蒂、弗洛伊德、奥尔巴赫……这个名单可以很长,此处不提。回到工作室的中国人物画教学路线,从动机上进行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不是用中国画既有的形式语言现实作为材料去处理;有时还要反过来,以诚恳的直观去考察中国画语言。其中重要的是,如何在写生的过程中展开对传统和绘画本身的体会与认识。这有点像绘画行为的自我审视,有一些穷本溯源的意思;同时还有一种绘画清理的意思,因为这种写生要接受两种检验:一个来自写生对象本身具有的“超”绘画的东西,一个来自绘画(或者来自于传统)本身特殊的“超”具体对象的东西。它们的结合不能简单的用既有理论框架来判别,也就很难做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性表述。在追求上,这种方式的写生的任务艰巨而可敬,它也许要求改变既有的中国画理论阐释模式。
对于中国人物画,毋庸讳言,它面对的是一个消逝中的传统和一个待建的未来。就是说它可能长久的处于期待之中,而且它身处的也许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环境。这样,以什么样的内在和姿态继续这条路,就成了检验其价值的几乎是唯一的角度。在这一点上,工作室表现出了难能的坚定与果决。那么极端的说,在这里,“中国画”的所循之“本”,对于画者个体,将不再是“中”姓的问题,而是“画”的问题——不再局困于印象中的传统概念和它派生出来各种审慎的语言匹配。温和的说,就是要认真对待中国画的前限定,不要简单地先把鹅养到瓶子里去。
或可说,工作室写生实践较为特殊的启示就是:在对中国画形式语言的限定体验与自由体验中错综,体现了观察与思考的某种厚度。在实际层面,它意味着偏离相关范式和风格的预设,与之做试探性的对话;并于其中触碰绘画行为的动因及其与中国画形式的交互影响。其中,画者主体也作为检验与反省的材料,通过绘画行为与自我的双重审视,通过反射与应激,激起的是困难中求克服的主体能量,而这种能量可以视为绘画更加本然的原动力与推进力。在当下中国画本体的实体化及虚无化的对立中——即保守与取消的对立中,其方法论的转化具有很大的困难。而这里提及的工作室写生实践中相关主体性的“观察”,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谨慎态度,“思考”体现了对转化的积极反思。对于中国画方法论的转化,它提请悬停话语建制正反两面的前限定,走向绘画行为的存在性理解。进而,关于绘画形式处理的能动性交给画者,交给进行局部认识的历时性行为主体。尽管这些在绘画行为中的局部认识具有模糊的碎片的特征,但同时缓解了对中国画整体概念判断的焦虑;最重要的是,使认识与方法的局部建设成为可能。
就绘画表达的角度,新时期中国画积极发展的方向体现为一种增广运动,画种的内部纪律的变化则是增广的条件之一。所谓中国画本体在这个运动中也要受到考量,假若它想同时获得(历史的)自身合法性以及一种(当下的)文化上的能产性——其外延就不得不通过认识与方法的局部建设零敲碎打的进行。也就是说,是“个体性”的审美趣味而并非是公约性语言趣味,作为学院中国人物画写生新可能的出发点,于是就在这一点上,便与旧有的写生模式拉开了距离。
结语
因此,以中国人物画工作室写生实践为例,或许能够大胆展望,中国人物画乃至中国画更新的关注点,可以从以往的语言匹配的公约性(被动的笔墨适配性)过渡到个体的抉择性为本位(主动的语言择取)——在公约性语言趣味落入时代性的怀疑主义时刻,个体的抉择作为中国画再发生的基本条件,从而寄之以厚望。附带提一句,一直以来取消中医的争论,和关于中国画的争论如出一辙。中医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也无非就是“医”本身,中西之辨的根结在于,当医术用以解释世界的最小元素层面发生了基础性变化,那么医学体用的开展也就有了冲突。这其实更是一个关于它在社会诸结构中的位格,或者说文化价值判断的问题——然而对于人本身来说,重要的只是获得健康。医学的本体价值和它的应用问题在这里倒是次要的。有关中国画的问题似乎也正是如此。
On New Possibilities of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Sketches——A Case Study of Sketching Practice in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Studios
REN Hai-ding
(Fine College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00,China)
The paper describes current Chinese figure paintingmodes and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in sketching practice,which reflects the dilemma between painting language and kernel logic.Taking the sketching practice in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studios as an example,it probes into a new possible sketching route,which com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objective intuition and self-examination.Finally,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ese figure painting,which will be brought aboutby this new possibility.
Chinese figure painting;sketch;practice;individual
J214
:A
1673-2103(2017)01-00139-04
(责任编辑:陈光磊)
2016-05-15
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黑龙江现实主义美术研究”(2014D016)
任海丁(1973-),男,辽宁沈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画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