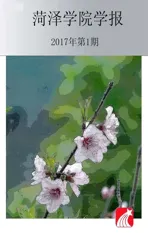多重隐秘符码的文化容器
——从次要人物解构《喊山》*
2017-03-09王宏
王 宏
(太原学院中文系,山西太原030051)
多重隐秘符码的文化容器
——从次要人物解构《喊山》*
王 宏
(太原学院中文系,山西太原030051)
《喊山》作为葛水平的经典之作,有很多解读方式。重读《喊山》,从次要人物入手,深入挖掘作品内涵,会发现文本是一部隐藏着诸多符码的文化容器。腊宏恣肆的“暴力”、琴花尴尬的“妖女性”、红霞无言的“失语”、腊宏前妻潜在的“被蚕食”以及村长王胖孩浑然天成的“自足”,化外世界不仅笼罩着深刻的先民文化,而且有着难以言说的男权文化的渗透。
《喊山》;文化小说;小农;女性;先民
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喊山》,给葛水平带来无限荣誉,以致文学界甚至有人把2007年称作“葛水平年”。对于《喊山》的解读,学者们大多围绕着鲁迅文学奖的评语——“《喊山》以‘声音’为主题,在民间生活的丰厚质地上展现人心中艰巨的大义和宽阔的悲悯”——展开,或鉴赏其人物红霞,或论述其人性光辉,或分析其生命悲歌,或揭示其女性隐喻,或欣赏其乡土意味,真可谓是一部说不尽的《喊山》。重读《喊山》,细细思索腊宏、琴花、王胖孩和韩冲这几个次要人物,总觉得有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是流氓,我怕谁”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自古以来是小农与流民并存。和平时期是大家安于耕作,安于小农生活。一旦战乱发生,很多小农甚至整个家族背井离乡,流落各地就变成为流民。据王学泰学者所说,“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或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都可视为游民。游民重要的特点在于‘游’。他处在社会最底层,只有在动荡的时代才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他们不理会秩序,反而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1]16也就是说,流民如果脱离了“家族群”,没有被安置好就极可能变成游民。
《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流氓”的解释:“①原指无业游民。后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②指放刁、撒泼、使用下流手段的恶劣行径。”[2]735可知,游民与流氓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游民发展到极致就成了“流氓”。
那么,当“小农”与“流氓”对垒时,会发生什么?
以韩冲为代表的山野村民,一辈子在土地上耕作,经济收入微薄。再加上或识几个字或根本不识字,囿于物质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双重逼仄,愚昧落后和保守排外构成他们这些小农的基本心理特征。腊宏呢,作为流氓,是专制和暴力的象征。于是,以腊宏为代表的流氓文化与以韩冲为代表的小农文化在文章中很自然地形成对峙。
腊宏“瓦刀脸,干巴精瘦,痘痘眼,干黄锈色的脸皮儿上有害水痘留下来的痘窝窝,远看近看就一个字‘贼’”,“长得一副鸡头白脸相不说,人很懒,腿脚也不轻快”。“常常顾不住嘴,要出去讨饭”。可以看出,腊宏不仅长得尖嘴猴腮,而且懒惰猥琐。一出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流民”形象。腊宏是外来户,是从“四川到岸山坪来落住的”,这又是典型的“游民”特征。之所以到了岸山坪,是因为在家乡不但打杀了前妻,还经常殴打买来的后妻红霞。事情败露后,他带着已经在他吓唬威胁之下变成“假哑巴”的红霞逃亡至此。他的“流氓”习性可见一斑。到了岸山坪后,他并没有改邪归正。以前的“杀妻”暴行不允许他与村里人发生直接关联,腊宏一进村就把自己放逐于村人之外——选择了韩冲养驴的屋子。“岸山坪的人不去腊宏家串门,腊宏也不去岸山坪的人家里串门。”日子一长,人们发现腊宏懒也就罢了,甚至经常打老婆,“打得很狠,边打还边叫着:‘你敢从嘴里蹦一个字出来,老子就要你的命!’”于是,一个典型的“游民+流氓”形象就活脱脱地跳了出来:不事生产、不治产业,崇尚暴力、懒散怠惰。等到腊宏死后,哑巴红霞追忆自己失语的原因时,我们在为主人公哑巴红霞的命运唏嘘不已的同时,也再次领会了腊宏的流氓本质。
韩冲呢,老实巴交的一个小农。因为身处大山,没人愿意嫁到山里,他只得与老爹相依为命;又因为男人的性本能需求,他与隔梁的琴花不清不楚。但他心地善良,不仅收留了腊宏一家人,而且还时不时地给腊宏女儿东西吃。
第一次听到腊宏打老婆时,他也曾冲了进去,想要干涉。可是,面对腊宏的怒喊“谁敢管我们家的事情,我们家的事情谁敢来管”,以及腊宏“一双痘痘眼聚焦在鼻中央怪阴气的。韩冲扭头就走,边走边大气不敢出地回头看,怕走不利索身上沾了什么霉事。”在暴力面前,在流氓面前,善良的小农第一反应很自然地是想要干涉,但看到可能会祸及自己,马上“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自扫门前雪”等思维就占据了绝对位置。所以,这也就决定了后来村民们“不大愿意管他们家的事了。”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老实本分的小农文化在与暴力血腥的流氓文化对峙时,很自然地败北,很自然地逃避。而处于小农文化与流氓文化对垒中间的哑巴红霞,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接着忍受她的不幸命运。因为她本就是小农中的一员,因为不敢反抗本就是小农的一个基本特征。
很多年前,鲁迅曾说过,中国的国民性是“羊与兽”的交替,遇到羊时就是兽,遇到兽时就是羊。善良的山民,朴实的小农,面对强暴的腊宏,只能一个个畏缩如小羊,或躲避如韩冲,或忍受如红霞,或干脆被其吃掉如腊宏的前妻。作者葛水平在一篇不太长的中篇里,言简意赅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羊兽共存图”,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在山野之村也自然流传,流氓文化在这里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喊山》整个小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篇秉承五四传统,透视国民劣根性的“批流”小说。
“喊出你的痛”
“喊山”作为一种山区的习俗文化,是人与山的对话,是人们站在山头或山腰,自由地放开喉咙大喊。喊山最初的意图,一来吓唬山中野兽,二来给静夜里出门的人壮胆,后来慢慢演化成一种劳动习俗,或缓解劳动的疲惫,或舒缓置身大山的孤独。
小说一共写了三次“喊山”,第一次不属于哑巴红霞,而是韩冲与琴花之间的。在文章的一开头,韩冲就很隐晦地向琴花发出性的呼求,琴花也顺其自然给他以暗示,接受了他的诉求。
韩冲一大早起来,端了碗吸溜了一口汤,咬了一嘴右手举着的黄米窝头冲着对面口齿不清地喊:“琴花,对面甲寨上的琴花,问问发兴割了麦,是不是要混插豆?”
对面发兴家里的琴花坐在崖边边上端了碗喝汤,听到是岸山坪的韩冲喊,知道韩冲断顿了想绕着山脊来自己的身上欢快欢快。斜下碗给鸡们泼过去碗底的米渣子,站起来冲着这边上棚了额头喊:“发兴不在家,出山去矿上了,恐怕是要混插豆。”
这样的开始,使众人对琴花充满了鄙夷,再加上后面腊宏死后需要有人披麻戴孝来“哭丧”,琴花乘机敲了韩冲一只猪的竹杠才答应下来。更有甚者,是琴花在气势汹汹地拒绝了韩冲的借钱之后,还能提上口袋再来韩冲家要玉茭面。一个小肚鸡肠、斤斤计较、贪图小利的女人马上呈现出来。但在鄙视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她之所以这样做的背后原因:儿子马上就要娶媳妇了。“自己两个儿,比不得一儿一女的,两个儿子说媳妇,不是个小数目,现在就得一分一厘省。”如果她不竭尽全力,那儿子就可能成为韩冲第二。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处境。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母亲。她不得不为儿子倾尽全力,即便是别人再鄙夷她,她也得充分利用她自认为是资源的资源。到这儿,如果说这个女人没有作为人的心,那她至少有作为母亲的心。实际上,此类妇女,在农村并不少见。在具体分析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她所处的现实境遇。如果说哑巴红霞所反映的女性问题是显在的,那琴花的生存困境则是潜在,是人们尤其是女性常常以“我自清白”的骄傲而忽略掉的。这样看来,这个人物作为次要人物,并不“扁平”,她集中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妖女”形象,有着深刻的女性困境内涵。
第二次是得知腊宏死后,哑巴红霞来到他的坟前所进行的声嘶力竭的“喊山”:
哑巴绕着坟堆堆走了好几圈,用脚踢着坟上的土,嘴里喃喃地说着一串儿话,是谁也听不见的话。然后坐到地垄上哭。岸山坪的人都以为哑巴在哭腊宏,只有哑巴自己知道她到底是在哭啥。哑巴哭够了对着坟堆堆喊,一开始是细腔儿,像唱戏的练声,从喉管里挤出一声“啊”,慢慢就放开了,唢呐的冲天调,把坟堆堆都能撕烂,撕得四下里走动的小生灵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往草丛里钻。哑巴边喊边大把抓了土和石块砸坟头,坟头下的人让她悚然而栗,她要砸出他来问问他,是谁给他权力要让她这么无声无息地活着。
哑巴红霞的“第一次出门”,作为外在动作,不仅象征着她走出腊宏营造的男权家庭,而且象征着她勇敢地走向人,走向自我。这是一声声动天地、泣鬼神的哭喊。一个可以说话却被迫多年不能说话的女人,终于发出了声音,发出了她自己的心灵最深处的呼喊。鲁迅说过,“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的主人公就在被压迫得奄奄一息之时得以喘息,所以,她不由自主竭尽全力发出她生命的第一声呼喊。她是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她的悲愤惊天动地,无数的生灵为之震颤。
第三次是秋天的夜晚对面甲寨为吓唬獾而“喊山”,这喊山声刺激了哑巴,
她先是“拿了一双筷子敲着锅沿儿,迎着对面的锣声敲,像唱戏的依着架子敲鼓板,有板有眼的,却敲得心情慢慢就真的骚动起来了,有些不大过瘾。”于是,从家里找出一个新洋瓷脸盆,“提了火台边上的铁疙瘩火柱出了门”,“她的喊叫撕裂了浓黑的夜空,月亮失措地走着、颠着,跌落到云团里,她的喊叫爬上太行大峡谷的山骨把山上的植被毛骨悚然起来。直到脸盆被敲出了一个洞,敲出洞的脸盆儿喑哑下来,一切才喑哑下来。”
如果在腊宏坟前的“喊山”是一次演练,那么这次则是哑巴整个的心灵舞蹈,它喊出了哑巴记忆深处最原始的人的萌芽。从此,哑巴开始真正成为人,真正开始为女人而活,为自己而活。接下来,她去探望狱中的韩冲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韩冲是她生命中碰到的第一个把她当对待的人,是他的无介蒂唤醒了她成其为人的意识,也使她朦胧地感觉到做女人的美好。
小说是关于人的故事,更是关于众多女人的故事。在新社会的今天,看似“男女平等”,但自古以来很多男权社会所留存的“集体无意识”已经深深地沉在人们的心底,尤其关于女性话语权的问题。红霞的“失语”开始于她不幸听到了丈夫腊宏竟然是危害前妻的凶手,从此在腊宏的“夫权”淫威之下,她开始慢慢失去了说话功能。外在言语的丧失,隐喻了内在话语权的丧失。就在我们为红霞哀惋的时候,大家都普遍忽略了一个人,即腊宏的前妻,这个若有若无的女子的死亡,不仅充当了哑巴红霞失语的直接动因,而且包含了一个女性被无形杀害而社会长时间未能给其伸冤的隐含命题。正如曹禺《雷雨》里周母为周朴园娶的第一个结发妻子那个不知名姓的女子,从繁漪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想到她所经受的惨痛压迫。同样,从哑巴红霞的被迫失语,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女子经历的苦难,以至于生命都被这个流氓丈夫蚕食掉,社会却多年来仍在放纵他迫害着另外一个女子。这里可以说,嵌套着另一个活生生的家庭暴力事件。葛水平在叩问中国法制问题的同时,更是一点一滴地挖掘女人所经受的苦难——在大家都以为两性平等的社会,女人正悄悄经受着不为人知的苦难。
所以,一个外形丑陋的女人琴花,一个被迫失语的女人红霞,一个不知名姓的女人腊宏前妻,就足以形成女性对世界的叩问。在《喊山》这篇女性小说里,弥满着众多有姓无姓有名无名女性们无法言说的沉痛、沉沦与抗争。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借助于灵动的笔墨,作者在小说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化外世界,这里有潺潺流水,有荫荫树丛。在作者的笔下,太行山有最质朴原始的自然,也有不被尘世现代文明浸染的“纯净”——先民文化在这里占着绝对地位。
一个杀人犯腊宏逃之夭夭,就在这深山峻岭之中,继续着他的恶行。另一个无意过失杀人犯韩冲,同样是在这深山峻岭之间,被村长包庇,以金钱换取生命的保全。人们的恶就这样一层一层被崇山峻岭包裹起来掩藏起来。
身处闭塞的大山,从远古以来的先民文化,很自然地慢慢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和外在行为。且看“炸人”事件发生之后,众人对此事七嘴八舌的议论:
一个说:“事情既出由不得人,也是大事,人命关天,红嘴白牙说出来的就得有个理道!”
一个说:“哑巴虽然哑巴,但哑巴也是人。韩冲炸了人家的男人了,毕竟不是韩冲想炸人家男人,既然炸了,要咱来当这个家,咱就不能理偏了哑巴,但也不能亏了韩冲。”
一个说:“毕竟和韩老五打架的事情不是一个年头了,怕不怕老公家怪罪下来?”
一个说:“现在的大事小事不就是俩钱吗,从清光绪年到现在哪一件不是私了!有直道儿不走偏走弯道儿。老公家也是人来主持吗?要说活人的经验不一定比咱懂多少!舌头没脊梁来回打波浪,他们主持得了这个公道么!”
王胖孩说:“话不能这么说,咱还是老公家管辖下的良民嘛!”
这些话语至少透露出:1.死了人是大事;2.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3.私了是历史由来已久的,曾有过韩老五的先例;4.人们对“老公家”办事不太信任。
敬生畏死的观念,使他们认为“活着大于一切”。死了人,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情,一定要秉公行事,不能因为对方是哑巴就有所偏袒。而且,不能诉诸于官方,因为就经验而言官方不一定能主持了公道。所以,受“要活的人更好地活着,死的人还要体面的埋掉”“人死如灯灭,活看的大小人儿日子长着呢”“人死了就想着埋,埋了人就想着活人”的原始生命哲学支配,村长王胖孩在得知韩冲炸獾炸死了人后,第一做法不是报告公安机关,而是带着人来到韩冲家和腊宏家,劝说施害人韩冲与受害人家属红霞双方“私了”。因为如果私了,那么死了一个,就死了一个,反正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活。可要是报告公安机关,那就不是死一个的问题,而是死一双,有一个必须要为另一个偿命,而这对于山野先民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反而白白搭上一条命。而且活着的人,也未必活的好。俗话说,“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这才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最原始的生存哲学。
作品对于这种先民文化的处理方式非常耐人寻味,代表先民文化意识的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作为行政最高长官的村长,而且,外在包裹先民文化意识的也是冠冕堂皇的官方形式——合同,“一式两份,韩冲一份,哑巴一份。”无形之中,文本在蕴含上形成不可避免的悖论,一种内在的精神焦灼,既无情地被撕裂又无奈地紧密纠缠扭合在一起,成为一篇流淌着很深的先民意识的生存小说。
葛水平中学时期非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那美丽淳朴的乡情描写,引起了她强烈的共鸣,对她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早期她的散文,写得温婉怡人,颇有沈从文之风。即便是在《喊山》里,作者的笔墨也灵动四溢,既有乡野之风,又不无女子的温婉之气。如匆匆走在山间小路的哑巴,昼伏夜出的地老鼠恓惶中的疲惫与挣扎,让哑巴惬意、微笑。“天上的星星眨巴了一下眼睛,天上的一勾弯月穿过了一片儿云彩,天上的风落下来撩了她的头发一下,这么着哑巴就站在了山圪梁上了。”这时候,长久压抑着的心灵在夜的掩护下慢慢舒展,对人的诉求也如崩堤之水汹涌而出。于是,她终于发出使山中植被也毛骨悚然的“呼喊”。
上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在书写乡土文学时,有意识地与城市文明相对照,试图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着“质朴、自然、不悖乎人性的人性”。所以,他笔下的自然是温婉的,是自适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是自足的。而葛水平作为太行山脉孕育出来的作家,她更多的经受的是太行山区人民的雄性,那种对生命的野性的呼求在她的血液里很自然地流淌着。当提起同乡赵树理时,她说:“小时候常听人说:半河腰出了个赵树理。半河腰子上出的事情太多,但是,知道赵树理是一个编故事的,我知道了就很激动。因为,我们同喝一条沁河水!”[3]所以,在审美观照时,葛水平似乎有意识地放弃了对“唯美世界”的刻意营造,而选择了赵树理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其作品自然而然地渗透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她在不可避免地睁大眼睛看世界时,看到的既有太行山的峻美,也有太行人的愚昧。因此,她的作品既有沈从文的写意美也有赵树理的现实美——抱着问题意识审视社会现实,用唯美的笔墨倾诉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担忧。傅书华先生曾经感慨,葛水平的小说“得赵树理小说创作‘真实’的精髓”。[4]
多年前在李锐、成一、郑义等作家笔下呈现出来的“吕梁苦难”“山西苦难”,如今在葛水平笔下,变成了“晋东南苦难”。再加上葛水平是女性作家,很自然地,她就看到了很多男性作家所看不到的女性悲伤。这个化外世界不仅笼罩着深刻的先民文化,而且有着难以言说的男权文化的渗透。
[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2]沈米成,宋福聚.现代汉语大词典[Z].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8.
[3]翟少颖,葛水平.赵树理家乡走出的女作家[N].三晋都市报.2005.5.12
[4]傅书华.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5):21-25.
Cultural Container M ultip le for Secret Symbols——Deconstructing Out in the Silence Based on Minor Characters
WANG Ho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Taiyuan University,Taiyuan Shanxi030051,China)
There aremany ways of interpretation of Ge Shuiping’s Out in the Silence.Starting with theminor characters to reread the works and deepen its connotation,the paper thinks it a cultural container with many symbols.From La Hong’s unrestrained violence,Qin Hua’s embarrassing female animality,Hong Xia’s silentaphasia and potentially being eroded of La Hong’s formerwife’s toWang Panghai’s natural self-contentment,all these show the externalworld has notonly descended the ancestor culture,butalso had an unspeakable penetration of patriarchal culture.
Out in the Silence;cultural novels;rogue peasant;female;ancestors
I207.427
:A
1673-2103(2017)01-0054-05
(责任编辑:谭淑娟)
2016-10-10
王宏(1974-),女,山西翼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