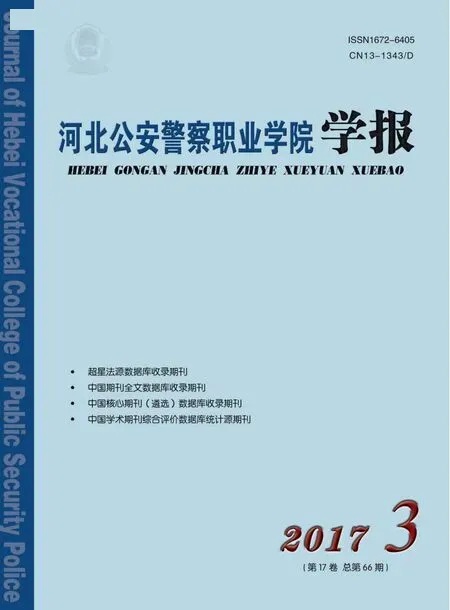浅析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2017-03-09孙凤君任延涛
孙凤君 任延涛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 沈阳 110083)
浅析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孙凤君 任延涛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 沈阳 110083)
目击证人对嫌疑人的辨认是法庭定案的重要依据,也是心理学以及司法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些年的研究数据显示,目击辨认错误是错误定罪的主要原因。记忆缺陷、目击证词评估人员缺乏相关知识以及现有司法程序存在弊端是目击辨认错误的主要原因。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对刑事司法人员的培训,建立正规的目击者访谈和辨认程序,进一步完善证词评估的相关司法程序以及促进心理学家与法律专业人士的合作。同时,我国在关于目击辨认的程序与政策的建立与完善方面也可以此为借鉴。
目击辨认;目击辨认错误;目击证人;解决办法
目击辨认对审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目击辨认准确与否至关重要。有研究数据显示,美国312个免罪案例中,目击辨认错误占75%;Gross和Shaffer对“国家免罪登记”中的873个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目击辨认错误占76%;Smith和Cutler也对1198个错误定罪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大约有50%的无罪人因为目击辨认错误而被判为有罪;美国心理协会指出平均每三个目击者中就会有一个作出错误辨认,[1]这些数据表明目击辨认错误是错误定罪的主要原因。同时由错误定罪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会削弱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心,法律的公正性受到威胁。因此,为何出现目击辨认错误以及如何减少甚至避免目击辨认错误是刑事司法系统首要考虑的问题。西方国家对目击辨认的相关研究颇为深入,其中尤以美国为甚,因此本文以美国为例,从记忆、目击证词的评估人员以及现有的司法程序三个方面对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目击辨认错误的解决办法。
一、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
(一)记忆存在缺陷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人类的记忆在编码、保持、检索和提取的过程中存在缺陷。目击者的记忆也有同样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记忆的编码和保持阶段。
1.记忆编码阶段
在此阶段中,影响目击者记忆的因素分为常识性因素和非常识性因素。常识性因素包括犯罪持续时间、照明条件、距离、犯罪者是否伪装以及注意力的集中程度等。
非常识性因素包括目击者的应激反应、武器聚焦效应、跨种族面孔识别等,一般认为这些会加深目击者记忆的因素反而会降低记忆准确性。[2]研究表明,目击者面对犯罪事件的恐惧反应会削弱记忆,武器会分散目击者的注意力,从而降低记忆的质量。此外,大多数人对自己种族成员的面部编码要好于对其他种族成员的面部编码,这也会对记忆的准确性产生影响。虽然罪犯的种族、面部细节以及是否携带武器等关键因素会影响目击者记忆的准确性,但是这些因素并不在司法系统或者执法人员的控制范围内。
2.记忆保持阶段
在记忆的保持阶段,事后信息的干扰以及记忆的重组会对目击者的记忆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记忆不能清楚而完整地进行回放,经编码而存储的信息易于改变。由警察、检察官、媒体、其他目击者、家人和朋友提供的事后信息可以改变目击者对犯罪相关信息的记忆。执法人员在审讯过程中有关罪犯容貌、衣着等带有诱导性的提问或者不同的列队辨认嫌疑人的方式可能会降低目击者记忆的准确性,而目击者通常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记忆已经被事后信息所干扰。此外,一旦记忆被改变,恢复目击者对于犯罪信息原始记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认知心理学认为记忆是一个重组的过程。目击者在面对犯罪过程、犯罪嫌疑人等问题时,通常会受到来自自我、侦查人员、家庭甚至媒体等方面的压力。目击者会根据其他证人、侦查人员等所提供的相关信息来猜测或重构原始记忆。例如,在1995年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中,三名目击者受卡车租用店店员的影响而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存在同谋的虚假信息。由此可见,记忆重组是一把双刃剑,更新或重构知识库的认知功能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和推理,但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取证来说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二)目击证词评估人员缺乏相关知识
除了影响目击辨认错误的记忆因素外,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还包括目击评估人员不能对目击证词的准确性的进行评估。在美国,目击证词评估人员主要包括:陪审员、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执法人员和专家证人。Magnussen等人对目击证词评估人员在目击证词相关知识的了解方面进行过大量的调查。[3]无论是本土研究还是跨文化研究都表明:目击证词评估人员不能完全掌握目击者的相关知识,在目击证词准确性评估方面,通常依赖较为狭隘的预测因素,例如审判时的目击者自信心、细节的回忆以及目击证词的一致性等,而忽略了其他的准确性预测因素,如罪犯是否进行了伪装、是否使用了武器等。[4]同时不了解目击者自信心与审判准确性的相关程度和目击错误在错误定罪中的作用,以及缺乏对目击证词的怀疑都会影响对目击证词准确性的评估。而Alonzo和Lane的研究表明:目击证词评估人员难以将目击的相关知识应用到实际的刑事案件中,[5]因此,即便他们了解目击的相关知识,在评估目击证词的准确性方面仍然会遇到问题。正如Cutler和Penrod所述,即使是专家也难以将他们的知识完全整合到实际的案件中,[6]这种易导致目击辨认错误的现象应引起法律系统的高度重视。
(三)现有司法程序在避免目击辨认错误方面的弊端
为避免目击辨认错误,美国建立了预先审查、交叉询问、陪审团指令和专家证人等司法程序,但这些程序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弊端,并不能完美地发挥作用。
1.预先审查
在美国,预先审查是通过有效的测评工具对预备陪审员的态度倾向、资格等进行审查,从而筛选陪审员的过程。调查显示,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美国的许多法院不仅缺乏测评工具,而且也没有对预备陪审员进行审查的意识。[7]陪审团成员良莠不齐,这会影响其对目击证人的相关评估。因此,预先审查因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困难而不能有效地避免目击辨认错误。
2.交叉询问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交叉询问的解释是:在审判或听证中由与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一方相对立的一方对该证人进行的讯问。在交叉询问的过程中,律师必须了解目击证人的相关知识,以便进行科学合理的询问。此外,陪审员必须也必须了解相关知识以便理解交叉询问实施的必要性,同时也需要结合交叉询问的结果做出合理的决策。[8]但在实际的司法程序中,律师和陪审员对目击证人的相关知识了解有限,很难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刑事案件中。因此,交叉询问也不能有效地避免目击辨认错误。
3.陪审团指令
由于预先审查和交叉询问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许多学者建议法院使用陪审团指令以避免目击辨认错误的发生。但研究者对美国使用最为广泛的特尔法尔陪审团指令[9]的测试表明,该指令的外部效度没有达到研究者的预期。即便经过众多学者的修改与完善,[10]也依然无法有效避免目击辨认错误的发生。
4.专家证人
英美法系创设了专家证人制度,所谓专家证人是指具有专家资格,并被允许帮助陪审团或法庭理解某些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的专业性问题的证人。Cutler等人的研究表明,使用专家证人将会出现三种结果:第一,法官不理解专家证词或不被说服;第二,法官对所有的目击者都持有怀疑态度;第三,法官会将目击者相关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刑事案件中。[11]但不论是Leippe和Eisenstadt,还是Martire和Kemp的研究都表明,专家证人也无法有效地避免目击辨认错误。[12]
二、目击辨认错误的解决办法
(一)加强对目击证词评估人员的培训
由于目击证词评估人员对于目击者相关知识的了解有限,因此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例如,刑法和刑事诉讼等法律课程应该包括不同类型目击辨认错误的知识、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以及使目击辨认错误最小化的司法程序等;执法机构对法官和律师的培训内容应包括如何对目击者进行指导和收集目击者的详细信息;对于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等专家证人,专业组织也应该为他们提供相关培训。此外,对研究目击者证词的心理学家也应该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刑事调查和审判的相关知识,从而提出与实际相符的目击者改革建议。
(二)建立正规的目击者访谈和辨认程序
进行正规的目击者访谈和辨认程序对于减少目击辨认错误至关重要,因此,司法系统应该在科学的程序中对收集目击证据的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和认证,以顺利的实施目击者访谈和辨认程序。建立正规的目击者访谈和辨认程序,需要对司法系统施加更大的压力,其中潜在的压力源包括:法律、法院裁决、专家证人以及媒体对目击辨认错误的关注等。[13]近年来,为避免目击辨认错误,科学家建议的列队辨认程序包括:无辜者与嫌疑犯比例适当的列队辨认结构、适时地给予列队辨认指令以及采用双盲列队辨认法和顺序列队辨认法等。
近期,Wise创建了访谈—辨认—目击因素(I-I-E)的方法来完善司法程序。[14]该方法包含了四个步骤:第一,需要确定执法人员是否从正规的目击者访谈中获取了大量准确的信息;第二,评估是否实施了正规的辨认程序;第三,评估犯罪过程中的因素如何影响目击者的准确性;第四,就案件中目击证词的准确性作出结论。对该方法的三项测试表明,它能够提高陪审员评估目击证词的准确性。[15]但是在得出I-I-E方法能够避免目击辨认错误的结论之前,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三)促进心理学家与法律专业人士的合作
心理学家应与法律专业人士密切合作以进行更多的目击者实证研究,共同推进目击者改革。法律专业人士具有心理学家缺乏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而这些对于目击者改革至关重要,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缺陷,需要心理学家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以确保目击者改革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有关目击者研究的亨内平县的随机试点项目[16]和格林斯博罗协议[17]证明了心理学家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能够有效减少目击辨认错误。
三、研究展望
由目击辨认错误而导致的错误定罪是对法律公正性的一种威胁,而放任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更是对法律威严清明的一种挑战。错误定罪削弱了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法律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也在无形中减弱。对美国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分析可以为我国目击辨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目击辨认错误的防范方面提供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实证研究和司法程序两个方面。
(一)加强对目击辨认的实证研究
在以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为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对目击辨认错误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分析归纳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美国在目击辨认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对目击辨认错误的防范方面,大多是通过实验室研究分析同时结合实践中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相比之下,我国在关于目击辨认的实证研究方面重视不足,经验不够,资金投入少,缺乏系统性,还存在很多有待填补的空白。因此,我国应加强对目击辨认以及目击证人证词准确性的实证研究,构建系统而完善的研究体系,从而为建立、完善目击辨认制度和防范目击辨认错误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完善目击辨认的司法程序
美国法律对目击辨认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也对其有相关的规定和保护。[18]而我国目前只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涉及目击辨认,但因两机关的规定存在矛盾,模糊不清,不能形成上下联动的运行机制,以致于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此外,在目击辨认过程中,辨认方式的分类不明晰,导致实施辨认的侦查人员也是一知半解,甚至在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不能保持中立,这些都会为目击辨认错误提供可乘之机。鉴于此,应首先建立目击辨认的基本规则,明确相关规定,以为实践提供一般指导。其次,需建立和完善目击辨认的程序和内容,可借鉴美国的经验,采用双盲列队辨认法从程序方法上避免目击辨认错误的发生,同时也为侦查人员在辨认实施的过程中提供具体的指导措施。最后,从辨认的权利保护入手,通过律师在场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对被辨认人的权利保护,从而进一步防止目击辨认错误的发生。[19]
[1]Curiae B F A.Steve Fuller(sociologist)[J].2015.
[2]Pickel K L,French TA,Betts J M.A crossmodal weapon focus effect:The influence of a weapon's presence on memory for auditory information.[J].Memory,2003,11(3):277-92.
[3]Magnussen S,Safer M A,Sartori G,et al.What Italian Defense Attorneys Know about Factors Affecting Eyewitness Accuracy:A Comparison with U.S.and Norwegian Samples[J].Front Psychiatry,2013,(4).
[4]Desmarais S L,Read J D.After 30Years,What Do We Know about What Jurors Know?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ay Knowledge Regarding Eyewitness Factors[J].Law and Human Behavior,2011,35(3):200-210.
[5]Alonzo J D,Lane S M.Saying Versus,judging:Assessing knowledge of eyewitness memory[J].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2010,24(9):1245–1264.
[6]Melinder A,Magnussen S.Psychologists and psychiatrists serving as expert witnesses in court:what do they know about eyewitness memory?[J].Psychology,Crime&Law,2015,21(1):53-61.
[7][8]Devenport J L,Kimbrough C D,Cutler B L.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safeguards against erroneous conviction arising from mistaken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M].Expert Testimony on the Psychology of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2009:51-68.
[9]Rosenzweig P.United States v.Telfaire.469 F.2d 552(D.C.Cir.1972)[J].
[10]Bornstein B H,Hamm J A.Jury Instructions on Witness Identification[J].Court Review,2012.
[11]Cutler B L,Penrod S D,Dexter H R.The eyewitness,the expert psychologist,and the jury[J].Law and Human Behavior,1989,13(3):311-332.
[12]Martire K A,Kemp R I.The impact of eyewitness expert evidence and judicial instruction on juror ability to evaluate eyewitness testimony[J].Law and Human Behavior,2009,33(3):225-236.
[13]Cutler B L.Reform of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J].2013.
[14]Wise R A,Safer M A.A Method for Analyzing the Accuracy of Eyewitness Testimony in Criminal Cases[J].Court Review,2012.
[15]Educating Jurors about Eyewitness Evidence[J].
[16]Klobuchar A,Steblay N K M,Caligiuri H L.Improving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s:Hennepin County's Blind Sequential Lineup Pilot Project[J].Cardozo Pub.l.poly&Ethics J,2006.
[17]Steblay N K,Dysart J E,Wells G L.Seventytwo tests of the sequential lineup superiority effect:A meta-analysis and policy discussion.[J].Psychology Public Policy&Law,2011,17(1):99-139.
[18][19]刘静.目击证人辨认错误之原因及其防范[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
[编辑:张钦]
D918
A
1672-6405(2017)03-0033-04
孙凤君(1993-),女,辽宁抚顺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2016级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犯罪心理学、警察心理学。任延涛(1976-),男,辽宁丹东人,心理学硕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基础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犯罪心理学、警察心理学研究。
2017-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