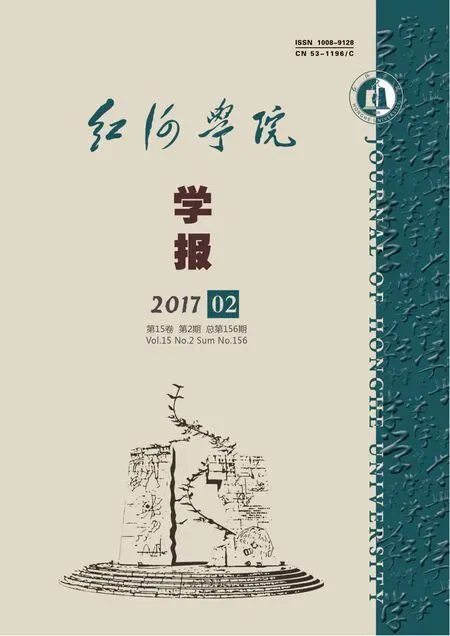传播媒介中的少数民族话语的构建
——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视角
2017-03-09施红梅
施红梅
(大理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传播媒介中的少数民族话语的构建
——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视角
施红梅
(大理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中国少数民族和谐话语的建构是我国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也已成为传媒舆论引导的一个重要方向。鉴于此,少数民族的话语能否得以真实传达,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文章以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视点,剖析我国少数民族话语的实现状况,探讨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福柯;话语理论;少数民族话语
一 引言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被视为“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 福柯的学说在西方思想界拥有广泛影响,其中,“话语”(discourse)问题是贯穿其全部思想的主题,而话语功能则是其全部思想的基石。[1]福柯认为,所谓“话语”,就是对展示出某种外在功能的符号系统的称呼。在《知识考古学》中话语的功能是在“话语实践”中对话语网络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从《规训与惩罚》以后,话语的功能性跃出话语层面,进入“话语一权力”层面,此时话语与权力缠绕在一起。[2]
中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如何通过恰当的方式来传达少数民族的话语,以及如何让少数民族同胞自己来表达话语,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栗原小荻(2001)评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权;梁代生(2006)则以青海地区为例,探索了建构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途径[3];兰杰、辛金钦、殷兆武(2009)提出了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和谐话语及其面临的新问题等[4];刘艳萍则(2015)探讨了大众传媒在建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作用[5]。如上所述,学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谐话语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鲜有学者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探讨少数民族话语权的建构问题。本文拟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关照下,剖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话语的实际状况,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 话语理论关照下少数民族话语表达的现状
徐军义(2010)认为,福柯的权力是指“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不是指某个阶级、集团或个人所享有的权力,而是指这种权力是如何行使从而拥有了权力。[6]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根据宪法的这一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了一系列规定来保障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的一员,享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不仅如此,针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的具体情况,国家还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权利的享受方面给予了特别的照顾。例如,在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等方面,都有专门的相关规定,并采取法律、行政等方面的措施,促使这些特定权利得以实现。
然而,尽管国家对少数民族制定和实行大量的优惠政策,但时至今日,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依然比较片面,少数民族的真实话语尚未得到完全地传达,少数民族同胞仍有被边缘化的心理,甚至会有下意识地想要隐藏自己民族的自卑心理。白族诗人栗原小荻(2001)在评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权时,真实地记录了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当面对汉民族文学人士时,总是先把自己的母语民族身份掩藏起来,直到获得对方的认同之时,才会把自己的文化血缘道白出来。[7]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话语传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何甚至连一些才华横溢的少数民族作家,在面对汉族同行时,还想要隐藏自己的民族身份?无需说普通的少数民族民众普遍存有的不自信心理了。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话语的建构仍然存有问题。
三 话语理论关照下少数民族话语表达存在的问题
刘慧苹(2010)认为,个人话语权是个人权力的表达,话语权决定了社会导向和个人意志。[8]传播媒介是话语权的重要实现途径。在当今少数民族地区,借助于媒介来传达少数民族的话语,依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少数民族地区媒介形态结构的失衡,造成少数民族的真实话语难以被完全传达,造成了被边缘化的现象。
由于自然、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同胞大多地处偏僻,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贫困问题时至今日依然严峻。作为主要宣传媒介的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兴网络,甚至到了当今的自媒体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以少数民族语言发行的报刊种类稀少;新兴的网络媒体只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心城市,尚未真正进入和覆盖广大的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能读到的主流报刊杂志、接收的主流广播电视节目都是以汉语为载体,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宣传难以被民族地区受众完全看懂、听懂。结果一方面造成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宣传没有得到有效传递;另一方面也造成少数民族感觉被边缘化,不被重视。
(2)传播媒介对少数民族的报道大都是以汉族为视角,少数民族的真实话语难以得到全面体现。
对于话语形成的原则,福柯在谈及陈述方式的形成时提到,要追问三个问题:谁在说话?话语发生的地点在哪儿?主体占有什么位置?[9]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话语是由谁在发话,主体占有什么地位呢?邱爽(2013)剖析了报纸对少数民族的报道文本的特点,认为文章均从汉族的视角来看待少数民族,其通过对文章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媒介“局外人”报道视角——即少数民族群众总是处于“被报道”“被塑造形象”的状态。[10]
可见,在真实的传播媒体中,少数民族群众并不是少数民族话语的陈述主体,少数民族的真实话语难以得到完全真实的体现。
(3)媒介话语霸权的存在,使少数民族难以真正拥有表达话语的权利。
福柯认为,权力对话语的约束是多方面的,来自结构的权力话语总是循着人们总结的一套逻辑规则,对不符合这套规则的话语“过滤”,从而起到“净化风气”的作用。[11]杨培德(2010)发现“扶贫”已经成了报道少数民族地区最常见的话语,然而“扶贫”就意味着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少数民族地区则“把少数民族异化成国家救济和防范的对象”的贫困他者。[12]如今,在地区很常见的现象是,在官方与投资商合作开发的少数民族旅游项目中,作为权利主体的少数民族民众,几乎很少有话语权与参与权。再者,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为了迎合普通大众对少数民族的好奇心理,往往不顾当地的真实状况而推出所谓的少数民族特色旅游项目以吸引游客。造成过分渲染少数民族同汉族的“不同”而隐藏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真实状态。造成了少数民族真实话语的传达受到抑制的现象。
四 传播媒介中少数民族话语的建构方法
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3]要使少数民族的真实话语得到传达,建构真实的少数民族话语,应努力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1)传播媒介应该通过大力优化民族地区的媒介生态以强化国内舆论引导,切实扩大少数民族传达话语的途径。优化民族地区的传媒结构,扩大少数民族语言的报纸发行范围;增加对民族地区广播电视硬件和软件的投入,并力求突出地方特色,以民族文化带动主流文化的传播;扩大网络的覆盖范围,注重网站的日常管理和新闻策划,注重与受众及时互动。[14]大力发掘自媒体在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巨大潜力,提高传播的开放性,互动性和高实效性等特点,尽量让少数民族民众成为民族地区的发言主体,消除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的现象。
(2)改变完全从汉族的视角来报道和宣传少数民族的传播模式,消除媒介话语霸权。改变过分渲染少数民族的民俗化、娱乐化、风情化的报道风格。在报道少数民族地区状况时,应该结合当地真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注重现实性和现代性。在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困难时,也要报道反映进步和发展的面貌。在报道宣传党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时,也要报道各少数群众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安宁以及促进中华文化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从而提高少数民族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让少数民族的话语得到真实表达。
(3)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自己的传媒产业,引导好自媒体的运用。只有这样,才能依靠“政府引导、市场操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自己的传媒产业”的方式来建构少数民族的话语,不仅有利于塑造真实的少数民族形象,传播民族文化精髓,同时也有利切实增强少数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
(4)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力度,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因为权力与人的话语密切相关,权力的建构离不开话语,只有通过话语,权力才能得以建立。[15]只有保护好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才能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与国家建设中的话语权。
五 结论
在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意识,大力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应当要尊重少数民族民众表达话语的权利。一个理想的、和谐的社会应该让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表达话语的权利。通过改变对少数民族宣传报道的传统视角,发展少数民族自己的传媒产业,让少数民族的话语得到全面真实的传达,加强民族认同感和参与意识,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1]庄琴芳.福柯后现代话语观与中国话语建构[J].外语学刊, 2007(5):94
[2]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D].上海:复旦大学,2004:3
[3]梁代生.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以青海为例对建构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6):10-15.
[4]兰杰,辛金钦,殷兆武.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话语[J].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4):54-56
[5]刘艳萍.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J].人民论坛2015(32):172-174.
[6]徐军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J].文教资料,2010(35):119.
[7]栗原小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权评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87.
[8]刘慧苹.话语权之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J].科学发展研究(理论月刊), 2010(8):42.
[9]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6.
[10]邱爽.我国当代报纸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刻板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新京报》为例[J].民族艺林,2013(2):34-38.
[11]陈长利.论福柯的三维话语理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128
[12]杨培德.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视角反思发展话语: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为例[C]//宋敏,等.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0文集:发展理念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13]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14]李谢莉.当前我国民族团结舆论环境的理性分析[J].民族学刊,2010(2):143
[15]周倩.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女勇士》[J].海外英语,2014(18):237.
[责任编辑张永杰]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inority Nationa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SHI Hong-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0,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ority peopl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National unity, as the demands for the current 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ic,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Therefore, that the discourse of the minority people can be conveyed is of grea significance for our country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guided by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Foucault, the French philosoph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
Foucault; Discourse theory; Minority nationality’s discourse
G206
A
1008-9128(2017)02-0069-03
10.13963/j.cnki.hhuxb.2017.02.017
2016-07-04
201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接触视点下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与政策研究(YB2015075)
施红梅(1972-),女,云南大理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汉对比,民族语言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