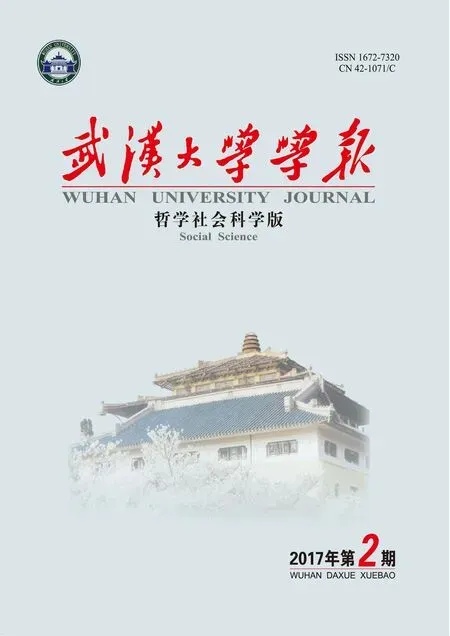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变革与走向
2017-03-09喻少如
喻少如
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变革与走向
喻少如
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是一种新的行政程序形态。协商民主、反思性法以及公私法融合为其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此种行政程序可以在提升行政权力的民主正当性、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性中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行政程序将朝着以下的方向变革:程序价值的兼容并包、主体结构的伙伴化、程序风格的交往理性化以及程序表达的论辩规则化。基于此,未来在制定统一的中国行政程序法时,在制度选择上需要强化对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程序规范,重视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式治理,注重合作式行政程序的设计与推广以及程序参与主体在协商程序中的积极义务。
行政程序; 合作行政; 反思性法; 变革; 走向
一、合作行政的兴起及对传统行政程序法的冲击
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是广义行政法规范的对象,因此,只要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变迁,行政法体系也就必须做出相应变革(陈爱娥,2005:5)。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行政任务的变化,行政职能的扩张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反而产生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以及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等一系列“政府失灵”现象。为此,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力图通过公私合作治理来共同实现行政任务,国家不再以权威代表的身份现身,而是希望和私主体之间建构一种实质性的伙伴关系。基于此,一种作为传统行政模式修补方案的合作行政模式应运而生。反观我国,由于国家任务的不断扩大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诸多经济社会难题也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加强合作的途径才能予以克服解决。面对合作行政这种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技术予以应对,行政程序显然是应对这一新面貌的重要技术之一。
在公私合作治理过程中,行政与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分化,传统上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高权行政”法律关系,日益让位于以服务与合作为内容的“平权型”行政法律关系:“在隶属关系中,个人是被统治者。除此之外,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个人作为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提供服务;有人则与行政机关结成了合作关系。”(让·里韦罗,让·瓦利纳,2008:23)由于公私合作治理使行政与私人地位相对平等,传统行政程序法的强制与对抗色彩开始变得弱化,意思自治的成分有所增加。对于传统行政程序来说,无论是在秩序行政时期还是在给付行政时期,均明显具有浓厚的对抗性色彩。因为在行政任务的两端,也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行政机关仍然把持着行政任务的主导权,为了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不受行政机关的侵害,透过行政程序对行政权力的运行施加控制就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而随着合作行政的来临,行政程序法更多吸纳了私法的平等、自治和协商精神,“现在比过去要求更多的是说服和合作,行政机构所发布的许多‘命令’如仍以单方面决定的形式出现,则应是通过一个称为‘协商’的程序同有关的个人或企业谈判的实际结果。”(勒内·达维,2002:108)
合作行政下公私合作关系本质的变化,导致行政程序法调控范围的扩大,行政程序法的覆盖范围扩张到参与承担行政职能、合作完成行政任务的私人部门,由此,“行政程序法的规范主体呈现出私人化的倾向”(陈军,2013:125)。在传统行政程序观念看来,程序是针对政府行政提前预设的行动轨道,行政过程的推进全然凭借行政机关的需要和意志,相对人只能被动接受程序的结果。在合作行政背景下的公私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不再是只顾追求私人利益的被管制客体,同样可以成为分享行政职权和分担行政任务的主体。公共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狭隘观念,也被不可逆转的公私合作治理洪流所摒弃。私人不仅可以充当公共服务的承担者,而且可以参与规则、标准的制定,更重要的是,私人还可以承担自我管制者的角色,通过自我监控、定期审计、信息披露等方式,与政府“合作管制”,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发现、披露、预防和矫正违法行为,身份的变化必然要求私人部门遵守相应的行政程序。
合作行政下公私之间关系本质的改变,逐渐改变了行政程序固有的封闭性结构。在传统程序结构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是行政程序得以向前推进的动力来源,伴随着利益诉求的不断多样化,这种传统的单方主导的行政程序只会加剧利益主体冲突对抗的风险,行政机关的程序负担随之也会不断加重。正因为看到了传统行政程序的不足,基于平权型法律关系的协商型行政程序建制大量涌现,如美国的行政立法协商程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管理式谈判”),成为一种替代以通告——评论为特征的传统行政立法程序的备选机制。在这一机制设定的框架内,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来参与设计一个双方同意的行政立法或者政策,较之于机关强加于人的政策,这种程序无疑因为鼓励合作而非对抗使得程序的参加人对程序结果有了更强的可接受性(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1996:210)。类似的协商型行政程序建制在我国也正在蓬勃兴起并且颇具本土特色,如重大行政决策逐步探索了一种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的开放性决策方式,在这一多元决策结构中,决策机关、利害关系人以及公众等主体可以充分交流互动,从而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的质量和可接受性。
合作行政下公私之间合作形式的多样化,涌现出大量的各种不同于传统单方行政行为的合作行政行为,由此出现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行政程序。在实践中,公私部门常常通过特许经营、行政委托、合同外包、专家参与、行政助手和补助等形式实现行政任务,这些类型的公私合作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错综复杂,但在理论上大致可分为契约形式的正式合作行政行为和以指导、单方允诺、“君子协议”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合作行政行为。行政冲突的复杂化以及社会变迁导致行政契约被大量使用,行政机关为了应对挑战和解决冲突,必须在传统的高权行为之外另辟蹊径,寻找一些更富有弹性的手段,“尤其是人民之‘参与’与‘协商’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方式时,行政契约即符合了这些种种的要求,而且,依据实际操作经验,行政契约也能善尽其‘解决冲突’的功能。”(陈新民,2001:13)与行政契约相比,非正式合作行政行为更加灵活、更富有弹性,双方合作关系能否形成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或私人部门的单方面允诺或者“君子协议”。这昭示着一种不同于正式行政程序的非正式行政程序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国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中,行政合同程序和行政指导程序被广泛纳入立法文本,可以说印证了行政程序发展的这一趋势。
二、合作理念下行政程序的基础及其意义
(一) 合作理念下行政程序的基础
1.从代议民主到协商民主
从依法行政的正当性来讲,民主无疑是其中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在代议民主框架下,行政权的正当性源自于代议机关的授权,法院的司法审查无非就是保障行政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界限。此种行政正当性的观念,自二十世纪以来日益受到挑战,随着全球化、信息革命以及民主化的发展,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变得方便、快捷,人民的意见可以通过更直接的方式传达到政府决策链条之中,民意的表达渠道更加多样化。因此,协商民主成为一种证成行政正当性的新途径。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的合法性的最大特点既不是某种抽象的价值,也不是预定的个人意志,而是通过反思性的对话、辩论与商谈的话语过程来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承认的合法性,也可以称为“程序主义的合法性”。“通过赋予公众以特定的协商地位,行政部门和公众之间就会发展出一种解决问题的合作关系,信任也就建立起来了。因而行政机构在应用它们的规定和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具反思性。”(詹姆斯·特曼,2006:161)
2.从理性到反思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需要法律根据社会的不断变迁而相应的改变自己,法律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自我参照、自我指涉和自我管理才能逐渐完善和成熟。因此,法律的变革,也只有通过法律体系中的自我反思,才有可能达成。图依布纳正是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反思的法”这个模型,反思理性既依赖于“看不见的手”机制,却又不归属于“自然的社会秩序”,它追求一种“有管理的自治”,其本质是一种新程序主义,倾向于利用程序规范来调整过程、组织关系、分配权利。基于这一理论,我们便必须放弃一种行政法上的传统观点,那就是认为行政法的规范会直接带来社会的变迁,因为依理性主义建构的行政法忽略了行政法系统与其所规范的其它社会次级系统之自我再生性,而必须由一种内在的循环因果之理念来替代,也就是说“就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而言,法律规范系统便不会直接造成其他社会系统的变迁;社会次级系统会选择性地利用法律来处理自身的问题,并且是恣意地选择,来建构它自己的秩序。”(廖义铭,2004:168)进一步来说,这种反思性行政法主张“一种有别于传统‘行政控权式’及‘市场主导型’的行政法制度而设计的第三条道路选择。”(杨振宏,2010:158)其基本目标就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寻求一种中间型制度,来完成行政任务和实现善治理想,其基本策略就是通过行政法内部的反思机制和对话程序,来实现直接沟通、谈判协商和组织合作。
3.从公私对立到公私混合
在合作行政下,行政法理念转换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从公私分立到公私混合。传统上强调公法与私法泾渭分明,然而公私的界限并非当然,事实上,合作行政下的许多机构都兼有公私部门的性质,很难去截然分开。以私法的方式完成行政任务也并不鲜见,契约也不仅仅是私法园地的一株奇葩。在高权行政下,行政程序被定位为公法程序,对抗性极强,相对人的参与不可避免地沦为“艺术上的陪衬”;而在合作行政下,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私人主体由管制客体一跃而成为与行政机关一样的管制主体,适用于私人行为的“私法化程序”亦被导入行政流程之中,“私法程序的纳入促进了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充分沟通和协商,行政程序也因此呈现出合作式、沟通式、讨论性、透明度高的现代化特点。”(赵宏,2015:29)
(二) 合作理念下行政程序的意义
1.通过参与协商式的直接民主来提升行政权力的民主正当性
行政任务的扩张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给代议制民主带来了难题,如何才能既解决现实问题又保持行政权的民主正当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种“将行政过程视为一种政治过程,通过向这一过程注入更多的民主化要素而使行政过程及其结果获得合法性的思路”得以提出(王锡锌,2009:46)。这种新的民主性供给的形式就是协商民主在行政过程之中的实验,合作理念下的行政程序承接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在程序中的协商、交涉与谈判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赋予了行政权以民主正当性,这是一种民主正当性生成的自主模式。当然,该种民主正当性的补足作为政务民主的典型样本,也存在着私主体利益或意志得到过度尊重而损害公共利益,以及私主体转换为公共机关的担忧。此种担忧既需要一般程序的规制,也要结合公共化工具的选择,包括信息披露、责任机制以及常见的契约设计,而不是单纯依靠传统较高成本的政府监管。
2.通过交往协商式的沟通过程来提升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包括从行政决定评价为正确到还可以被承认这样的范围,就可接受性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关系来说,有学者认为:“法标准具有优先性,亦即欠缺可接受性并不会夺走适法决定的拘束性。反过来说,违法决定也不会因为它被接受而免于法反映的评价。”(施密特·阿斯曼,2012:98)因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可接受性的前提,但是可接受性又是超越合法性而追求行政正确性的因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有在开放性的裁量空间内,可接受性才具有独立的地位。在传统行政法看来,行政裁量权是法治的敌人,彼此势如水火,因而将正当行政程序的使命聚焦于对裁量权滥用的严密防控。而在合作行政下,行政权威不再是单一的政府一方,而是在公私各方主体的互动与交往行为中生成的。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实质上是行政机关与私人进行“反思性”对话、交往的过程,一个通过契约、协商与和解进行实质性利益沟通的过程。内生于交往理性下的行政程序,与其说是控制裁量权,倒不如说是创建了一个沟通交往的平台,这一平台致力于追求在裁量范围内寻找“横轴上那个最佳结合点”,行政行为不再是行政机关的单方意志决定,而是在多方利益主体沟通妥协下的产物。显然,这种在裁量范围内共同作出选择的方式更能够保证最终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
3.通过合作程序机制的“控制器”和“安全阀”功能来提升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是行政程序最终追求的目标,传统行政程序力图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其根本的思想在于“堵”而不在于“疏”,程序的推进仍然是行政主导型的,官民双方之间的对立并未在程序中得到消解,只是将这种冲突暂时掩盖起来,一旦遭遇敏感议题,这种矛盾就会冲破程序的控制,实在地置于统治者面前,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一再验证这一判断。相比于传统行政程序,合作理念下的行政程序则将自身定位为一种达成妥协的中立机制,合法权益受到影响的公民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正常宣泄对行政决定的不满情绪,借助于行政机关的说理,这种不满情绪能够在程序中得到安抚,避免演化为赤裸裸的社会冲突;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具体来说,是指人们一旦参与到程序中去,除非程序的进行明显不公正,就很难抗拒程序所带来的后果(季卫东,1993:89)。这种对程序运行结果的服从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合作理念下的行政程序因为保障了利益相关方的实质性参与,显著扩张了程序带来的结果服从效应,巩固了社会稳定。
三、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变革方向
(一) 行政程序多元价值的兼容性
传统行政程序以“权利保护”和“权力管控”为其使命,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充满浓厚的程序工具主义意味。虽然它也重视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但终究因为是以行政权为思考主轴,因此,它并不太关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就传统行政程序的目的而言,其旨在保障最终做出的行政决定的形式合法性,只要严格按照既有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做出且没有其他违法事由,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就应该在后续的救济程序中得到确认。这种封闭的、一元化的价值立场常常会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困境,譬如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提高行政效率和控制行政权力彼此不能兼容,控制权力必须牺牲行政效率。
行政程序的确具有控权功能,但若将程序控权作为唯一价值,则无法应对现代行政复杂流变的新需求,正如学者所言:“社会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呈现的越来越大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终结了权威单一、主体单一、方式单一、透露着工具主义陷阱的程序控权的神话。”(王学辉,2009:33)在合作行政背景下,程序理论从传统控权工具的辅助角色跃升为制度性表达平台和交涉过程整合网络,程序脱离了工具主义的藩篱而兼具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不再依附于实体而真正具有独立价值。由于这种反思整合型程序是在一种新的、非等级制的、去集权化的环境中生长和运行的,因而无论是从程序主体还是行为方式上来说,都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相比于传统行政程序,行政相对人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在行政程序中得到了极大地张扬,行政程序再也不是依靠行政机关一言堂式的专断进行推进。在合作行政下,行政正当性不再仅仅取决于行政机关遵照既定流程合法作出一个决定,而是更强调通过沟通、互动和协商来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因此,这种交往理性之下的行政程序能够兼容多重价值,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排序。如公正和效率,常列为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予以讨论。其实,两者虽有冲突,但并非不能统一在“行政效能”这一新的观念之下。行政效能不同于效率范畴,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实现其管理目标,从事公务活动,发挥功能的程度及其产生效益、效果的综合体现。”(马春庆,2003:29)当然,合作行政下行政程序价值的多元化也是其程序开放性的体现,在这一开放性程序框架内,多方主体可以通过不断地交涉、沟通与对话寻找价值兼容或者价值有序的可能性。
(二) 行政程序主体结构的伙伴化
传统行政程序的主体结构是“线型模式”,即行政程序调整的是处于对峙态势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作用的场域,这种线型主体模式以命令—服从为特征,以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传输意志。而由于私人主体的加入,合作行政下行政程序由线型模式演进为网状结构,在这一伙伴型程序结构之中,各主体间意志的传递以交互式进行,公部门与私人主体分享权威,共同完成治理使命。具体而言,首先,程序主体的伙伴结构性变革本质上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于行政程序中转换的具体体现,具有传承性与延续性;再者,伙伴化也伴随着私人主体将竞争要素融入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具有兼容性与现实性;同时,伙伴化结构不是简单的强调行政主体与私人主体如何分配任务,而是利用合作式架构的优势致力于如何发挥行政程序在提升合作行政中的品质,因而具有共识性与互补性。
主体结构的伙伴化变革使得行政程序进一步优化:第一,程序的高度中立性。由于私人主体分享权威,承担行政任务,提供公共服务,新行政程序的设计就必须做到对于公部门和私人主体均能理性规制,尤其是要把利益衡量原则与公益原则贯穿于具体程序设计之中,包括如何规制天然追求利益的私人主体、如何防范行政主体规避公法规范的适用而肆意采用不相称的私法方式来达成行政任务;第二,程序的回应性建制。在伙伴式的程序主体结构模式中“行政机关和私人行动者通过行政程序本身来制定规则和标准、收集信息、分配资源、研究计划,指导目标、策略性执行,公与私的合作等。”(戚建刚,2013:161)因此,合作行政下行政程序的设计需触及传统行政所不重视的指南、手册、清单等各种行政新实践形式以及公众参与机制、协商机制等合作机制,同时也需要回应私人主体的程序角色与履责情形。
(三) 行政程序过程的交往理性化
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程序蕴含着交往理性的内核。在程序发展史上,程序工具论逐渐让位于程序独立价值论后,对于程序独立价值的考验促使程序的主体性地位获得认可,藉由程序主体性地位的认可,为交往理性提供了一个开放、无压制的生长环境,充分调动程序参与者的“表达欲望”。
现代程序理性的四标准之一就是:“程序创造了一种根据证据资料进行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这样可以使各种观点和方案得到充分考虑,实现优化选择。”(季卫东,2014:18)如果说合作行政的经济学基础包括受热捧的公共选择理论,那么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变革方向则是对这种选择的延续,一个高效的沟通平台需要合理分配一个行政决定的作出需要的信息、事实、资料等要素的举证责任并保障其真实性,因此如何让程序参与主体互负真诚义务,也是程序维持稳定有序的关键。
季卫东先生提出理性程序的另一个标准是,“通过结果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拘束力这两种因素的作用调动程序参加者角色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强烈的参与动机也会促进选择的合理化。”(季卫东,2014:18)其实,这仅仅是基于程序参与主体的角度进行程序优化的方向,实际上整个程序系统除了前述沟通平台以及激励机制,也需要从程序过程统一性角度来思考,包括如何在程序框架下为多元价值寻求共识。交往过程中的暂时性共识是通过程序进行整合的,即反思整合型的行政程序需要做到通过吸收各节点信息完成对交涉每一阶段的整合。反思整合性的启动及运行机制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的行政程序来说难度较大但有必要,不仅可以及时反馈决策失误的可能,降低政治风险,也能使得交涉阶段暂时性的共识通过不断整合固化成为确定性制度。
(四) 行政程序表达的论辩规则化
行政程序风格及内容的交往理性化常常以交涉论辩的形式表现。论辩规则化则为程序各方主体在交往平台空间中提供了行为准则。我国在地方行政立法中就引入了辩论规则化的理念,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第33条第1款:“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辩论机制的设置明显优于“全票通过会”。辩论规则化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只不过目前对于论辩的规范性依据尚缺乏,对于论辩的规则各地也鲜有涉及。
论辩是现代程序的活力所在,对于争议焦点的解决具有先天优势,尤其是观点在碰撞后更易直抵问题核心。但是论辩也并不是各方自说自话,而是在充分围绕信息、证据与资料的前提下,严格合理论证、逻辑推导,发现焦点,达致对话协商与法律适用。论辩过程中行政主体不可恣意任性,无故中断程序,需善于倾听与捕捉有效信息;相对方也不可以论辩之名,发泄私愤,阻断程序,需有的放矢针对问题焦点竭力辩驳。因此,有规则的论辩是辩驳程序的魅力所在,论辩的规则化是约束论辩使之可控的必然要求。关于规则化需要把握两个维度:一是各类型行政程序具体论辩规则的差异性,行政立法程序中的论辩机制与一般行政执法中的论辩程序机制需分别设计,前者偏重论辩中的质量与严格性,后者偏重论辩中的直接互动与信息收集;二是论辩程度的掌控,即论辩的节制性,对于论辩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终止的各节点均明确行政权威的隐性存在,在论辩程序失范时,强制权威或登台代替论辩或严控论辩规则。
四、对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发展的建议
(一) 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程序规范
我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受制于传统行政法理念影响,仍以行政行为为规范对象,并未对私人主体行为予以有效关注,导致私人主体行政程序法上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在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要有效规范私人行为,主要需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第一,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时是否取得行政主体的地位?第二,行政主体通过何种程序监督私人主体履行行政任务?第三,正当法律程序是否严格适用于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行为?
在德国,给付行政和引导行政领域“只要没有法律规定或者事实理由反对,行政机关就可以选择公法方式或者私法方式活动。”(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422)其中,对于私人主体以公法方式承担行政任务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此时私人主体具有高权主体地位(周敏,2015:110);对于私人主体以私法方式承担行政任务,则不完全受制于公法制约。不过,“在以私法方式执行直接行政任务时,行政机关仍然受特定公法原则和规则的约束(受管辖权规则,行政活动的一般原则、基本权利约束等)。”(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422)而在美国,长期以来,民营化中的私人主体无须遵守《行政程序法》与任何程序性的要求,包括无须遵守《信息自由法》(美国法典,第5编,第552条),《行政程序法》则明确将补贴与契约排除在通常适用于联邦行政机关的通告与评论规则制定程序之外,且行政程序法通常只要求行政机关接受司法审查(朱迪·弗里曼,2010:606)。但是该做法受到一定质疑,主要是基于公众参与、责任性与正当程序的法律价值遭受牺牲的可能性。
比较法只能提供视角,且域外对于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公法规则尤其是程序法的态度正处于不断改进中。因此,在借鉴的同时仍需要立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发展的现状以及我国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实践的需求。在我国,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参与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领域中去,财政部等部门制定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第四章规定了购买方式及程序的具体内容,其中第21条规定:“承接主体应当按合同履行提供服务的义务,认真组织实施服务项目,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任务,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主动接受有关部门、服务对象及社会监督,严禁转包行为。”但仍可在监督市场评估机制、政府信息决定告知、政府责任与私人责任衔接等方面优化*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存的问题与制度完善可进一步参见周佑勇:《公私合作语境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存问题与制度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2期,第90~99页。。鉴于我国行政主导色彩偏重的权力架构,建议完善履行行政任务的公法方式,同时发展行政指导、柔性行政等方式,适时通过行政主体资格赋予的方式来激励和规范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
(二) 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参与式治理
新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行政法的关注重心由传统的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向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及行政立法转移,而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该如何设计才能应对该种转移?主要在于保障重大行政决策模块的公众参与机制。美国学者托马斯(2010:27)曾提出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与共同决定五种阶梯式公众参与类型。本文所探讨的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所追求的参与该采取哪一种类型呢?实际上此处探讨的“参与”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它更接近于协商参与式治理模式,无论是在决策还是规范性文件制定均需要把公众视为过程伙伴,而非仅止步于信息的提供者,且应当赋予公众更多的实质参与权利,实质分享决策权,否则协商参与式治理极易落入形式主义。
即便抛开具体公众模式之争,也需将核心集中于实质参与权的获得上,关注参与的质量与效果,将协商参与式治理模式贯穿于行政决策与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建议在启动程序方面,赋予除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程序参与主体一定的行政立法的动议权、公民建议权等;在程序设计方面,赋予公众分享议程设置的权利;在程序参与主体方面,在行政立法起草组中积极吸纳社会力量,设置利益代表均衡与比例制度;在法律后果方面,设置不采纳意见的理由说明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条第2款规定:“编制机关应当认真考虑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并应当在报送审查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附具对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案卷排他性制度等。
(三) 合作式行政程序的设计与推广
合作式行政程序的推广得益于合作行政的兴起,它吸收并平衡了意思自治的私法契约因素与公法规制的力量,相对于传统行政程序来说,它丰富了行政程序的内涵,为大量新兴行政活动提供了支撑。合作式行政程序的完善有利于规制公私合作中公权力的滥用,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另外,鉴于合作行政中行政权力与市场机制相互依赖的现实,合作式行政程序也是解决传统行政程序与市场机制功能冲突的难得途径。
合作式行政程序的样态较多,其运行结果通常表现为行政合同*其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尤其是在税法、反垄断法、环保法、证券法等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内,本质上为执法和解程序并在结果形式上体现为行政合同的订立。。如税法领域的税务和解制度,《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八十六条:“对下列行政复议事项,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前可以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也可以调解”。税务和解尽管因其源于税务事实的复杂性而与其它的合作式行政程序相比具有特殊性。然而,本质上其仍然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因为“协商民主理念的引入,改变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模式,树立了协商式行政的新机制。”(颜运秋,2012:43)一般来说,不论和解程序在具体程序设计上有何差异,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程序两造彼此合作的良好互动关系。
在我国,行政合同被排除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加之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迟迟未能出台,所以我国关于行政合同的规定主要散见于相关单行法之中。近年来,各地地方行政程序规定相继以特别行政程序或专章对行政合同予以规定,虽然立法体例有所不同,但内容颇为雷同,主要就行政合同的内涵、适用范围、订立原则、方式以及合同监管等作出规定,缺乏对行政合同缔结程序的细致设计。为了保证合作式行政程序的推进,未来有必要对行政合同作出统一规定,其中需重点明确行政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中止与解除的程序细则,方能使行政程序立法中的行政合同程序与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协议”部分相衔接。
(四) 程序参与主体在协商程序中的积极义务
传统行政程序本身是为防御行政权滥用设置的,因而相对于行政程序主导者行政机关来说,其他程序参与主体多是被动接收程序的来临,而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各方主体处于共生状态,在追求公益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因此更强调各程序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相对人的积极义务。有学者认为“合作式行政行为的程序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行政机关将行政决定上的各种先前调查工作交给私人来做。”(陈军,2013:126-127)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此,国外行政程序发展近来出现对信息尤其是“地方性知识”重视的趋势,以公众参与的程序建制为例,假如在行政行为的某个阶段作出决策需要大量的地方性知识,此时如何保障决策获得更多的信息应当被优先考虑,因而在选择与该目标相匹配的参与时机、参与形式、参与范围和参与密度等公众参与程序机制时就需要更多地考量决策信息获取的便利性、成本与合法性。在合作行政背景下,新行政程序观念尤其强调:一是参与主体程序意识的培养,行政程序中其他程序参与主体能否积极协助程序的开展,需要具备主体性认同的意识、互负真诚义务的意识、辩驳的意识和选择的意识等等,这将会为行政程序大大减负,也利于拓展交涉的深度与广度;二是强调配合行政决定协助性工作的开展,包括检验、鉴定或计划的情形、约定送达方式的选择、信息及资料的主动提供等。离开了这些配合与协助,既定的行政活动可能被阻断无法继续开展,此类行为不仅仅具有辅助性,甚至直接决定行政行为的走向。如在我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反垄断和解制度中*《反垄断法》第四十五条:“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的涉嫌垄断行为,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可的期限内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该行为后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调查。中止调查的决定应当载明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的具体内容。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中止调查的,应当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经营者履行承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最终反垄断和解程序能否顺利进行乃至最后达成反垄断和解协议,都必须依赖于被调查的经营者在调查程序中的消除垄断行为后果的积极行为;三是对于非正式行政行为约束力的遵守与支持,由于合作行政采取了大量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匹配的程序更具灵活性,对抗性要素稀少,同时也欠缺透明性与安定性,因此法律约束力较低甚至仅具有事实效力,但是其对于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而被广泛适用,所以相对人在成为非正式行政程序的主体时,应自我设限,服从其一定的约束力,这既是合作双方相互信任的表现,也是合作行政中参与主体“绅士品质”的体现。
五、结 语
协商与合作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而行政与私人间的协商与合作需要行政程序的护航,所以整体而言,探讨合作行政下行政程序的变革趋势和规律,正可谓是当下时代精神的捕捉与反映。既有的行政程序法研究经验表明,行政程序法治的发展离不开部门行政领域程序需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如同我们无法用本文倡导的行政程序观完全架空或替代传统行政程序的统摄力一样,我们也无法代替部门行政领域程序类型的多样化、组合化与知识的地方化。比如对于环境行政、风险行政等具有专业性的行政领域,其程序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多回合构造的协商型程序、集中型的计划裁决程序等部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这些值得我们去挖掘、探索与提炼。不过,这并不否认本文论题的价值,无论是传统行政程序还是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无论是总论性、一般性的行政程序还是地方化、部门化的行政程序,它们之间仍是共生共存、相互交融的关系,尚不存在替代与排斥的可能。可以明确的是,在合作行政疆域上生长而成的新型行政程序,因其契合现代行政程序的发展规律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必将反哺新行政法的变革与合作行政的发展。
[1] [德]施密特·阿斯曼(2012).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陈爱娥(2005).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德国行政法总论改革的轨迹.月旦法学杂志,5.
[3] 陈 军(2013).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程序变化与革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4.
[4] 陈新民(2001).公法学札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 [法]勒内·达维(2002).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6] [美]朱迪·弗里曼(2010).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 [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1996).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 季卫东(1993).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
[9] 季卫东(2014).法治秩序的建构.北京:商务印书馆.
[10] [法]让·里韦罗、让·瓦利纳(2008).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1] 廖义铭(2004).从理性到反思——行政学与行政法基本理论于后现代时期之整合与转型.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4.
[12] 马春庆(2003).为何用“行政效能”取代“行政效率”.中国行政管理,4.
[13]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4] 戚建刚(2013).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环球法律评论,5.
[15] [美]詹姆斯·特曼(2006).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6] [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2010).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 王锡锌(2009).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法商研究,1.
[18] 王学辉(2009).超越程序控权论:交往理性下的行政裁量程序.法商研究,6.
[19] 颜运秋(2012).税务和解的正当性分析.法学杂志,8.
[20] 杨振宏(2010).后现代国家转型背景下的反思型行政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
[21] 赵 宏(2015).合作行政与行政法的体系变革.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2] 周 敏(2015).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行政程序变革与走向.法律科学,6.
■责任编辑:李 媛
Reform and Trend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YuShaoru(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and citizen is regulated by generalized administration law. So, along with the chang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and citizen, administrative law system has to acclimate with that changing. Deriving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formation in the 1970s, Cooperative Governs gradually becomes the well performed key to the government failure of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reafter. By now, the new type of administrative state requires a set of administrative law technology, of which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s a part. According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the change and trend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urns into a significant academic issue which needs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things: What is the impact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has on the traditional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i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justifie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s the direction of its transform? And how to establish a specific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has the following impacts on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 and government going to be polarization and equal-oriented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hip with service-cooperation which has take the place of high-powered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order-obey. And the coercive component in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s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autonomy is ascending. Secondly, because of the preceding polarization, the scope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must be expanded. It manifests as more private subject should be regulated b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While traditional procedure law could not cover the private sectors who take part in the administrative duties with government as the new one. Thirdly, inherent closed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procedure could not deal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s coming with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should transfer to negotiat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based on equal-oriented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hip. Last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citizen and government could work together in a variety of forms including kinds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ve act belongs to unilater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 great deal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ooperative procedure have been brought into being, but traditional procedure could not cover a great deal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neither in formal nor informal.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not only could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coming with the cooperative governs,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foundation itself. Specifically,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laid the most fundamental justification foundation for it. While reflection mechanism and interactive program in reflective law laid the foundation of directly communication,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Meanwhi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the rising focus on private and legal procedure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cords with the trend of converge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Meanwhil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at is to say, firstly, the new one views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as political processes. Final agreement was made in negotiation, interference and compromise between various interests subject through the given processes, which laid the justification foundation for administrative power. This is exactly an independent model of the formation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n accepta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s different from legitimacy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The former one values soundness of the act more than the later one. In the open discretionary rang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creates a platform to communic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dministrative action born in this way is more acceptability. Finall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has a restriction effect on all participators. Except of the obvious unjust processes, no other reasons could overturn the result coming with the processes. The very acceptability could confirm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The major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e descrip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ransforming dir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To be specific, there are four parts: The first is the compatibility of procedure valu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is open. It means various parties could discover the possibility of value compatibility and value order by interferenc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The second comes to the partnership of subject’s relationship.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transformed from linear structure into network, in which the will of each subject transmitted in an interactive way, so that public sectors share 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duties with private subjects. Interactive rationalization in procedure is the third par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provides an open and unrestricted environment for interactive rationalization. That could meet program participants’ need of expression. The last emphasizes the expression under discuss rule-driven procedure. It provides a code of action to the intercourse platform, which has advantages over solving disputes. Based on that, when we draf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more on regulations over privates participating in administrative duties, negotiated-rule in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designing and promoting of the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s well as participators’ positive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This article is innovative due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discovering the troubles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fac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insightfully, and manages to offer a brand new view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Second, describing the transforming dir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which could guides the legislation of national-leve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in the futur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reflective law; reform; trend
D912.1;D6
: A
: 1672-7320(2017)02-0111-10
10.14086/j.cnki.wujss.2017.02.010
2016-1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FX091);西南政法大学科研项目(2013-XZRCXM008)
■作者地址:喻少如,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E-mail:yushaoru200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