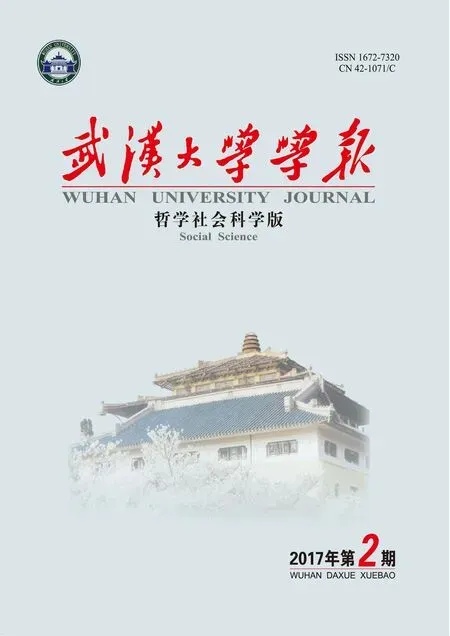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的逻辑关系与实证比较
2017-03-18赵素萍
葛 明 赵素萍
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的逻辑关系与实证比较
葛 明 赵素萍
文章依据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等核算口径的内涵,经逻辑演绎提出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构建核算模型,经数理分析验证了上述假说:一国总值进、出额按价值来源均可区分为国内、外增加值两部分,出口国外增加值与进口国内增加值之和构成重复核算部分,而总值进、出口额分别剔除掉重复核算部分之后就得到单边增加值进、出口额;由此进一步推论得到:总值贸易差额等于增加值贸易差额。在此基础上,应用三种口径分别核算和比较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及贸易差额。
总值贸易; 贸易增加值; 增加值贸易
一、引 言
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物流贸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全球生产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和工序间分工等更为细化的方式迅速演变,中间产品频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由此引致了要素价值的“国家间转移”、“产业间转移”和“重复核算”(葛明、林玲,2016:20-33)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继续应用总值贸易额来表示一国进、出口规模,既不利于反映出口总额的多边价值贡献和最终消费价值的国别来源,也影响到国际贸易结构的识别以及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因而存在严重不足(王直等,2015:108-127)。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卡尔·拉米(Pascal Lamy)*“Lamy Suggests ‘Trade in Value-Added’ as a Better Measurement of World Trade,”June 6,2011,See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1_e/miwi_06jun11_e.htm.在2011年就曾呼吁,采用“增加值”作为国际贸易核算新的口径;随后,WT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开发了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欧盟(EU)资助开发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为国际贸易核算方式演进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目前,国际贸易核算调整的主流方式是采用“贸易增加值”(Value-Added in Trade,简称VAiT)和“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简称TiVA)两种口径。贸易增加值是基于生产链的特征,分解出口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要素投入的价值增值过程,重点关心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及其所占份额。而增加值贸易则是分析最终消费品的价值来源问题,其国内价值被国外消费的部分构成了增加值出口额。虽然两种方式的研究视角不同,但均基于“增加值”口径,笔者认为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与总值贸易这三种口径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依据不同口径的内涵,笔者首先提出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继而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验证了上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核算和比较了不同口径下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总值贸易口径是当前海关统计采取的方式,其最大特点在于一个产品跨越各个关境时都以总流量计入进、出口贸易额(沈梓鑫、贾根良,2014:165-179)。如果在产业间贸易分工条件下,商品的生产流程基本在国内完成,而进、出口的商品均为最终消费品,这种口径核算的结果能够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交换额。但是,在国际分工日趋细化、中间产品贸易占据主流的背景下,进出口关境的产品就不再由一国的要素价值构成,总值贸易口径自然会产生中间要素价值的重复核算问题,从而虚增各个国家的实质进出口规模;此时也难以识别贸易产品价值的“原产地”和“消费地”结构,以及全球价值链上各个国家的贸易利得。后来,学者们依据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提出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两个口径对国际贸易核算方式进行修正。
贸易增加值体现了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在生产过程中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过程,一般应用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来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收益(刘遵义等,2007:91-103)。依据获取的数据库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沿着以下思路演进:(1)基于企业会计报表分解个别产品的国别价值,以芭比娃娃、大飞机、iPhone手机等为代表,研究对象比较微观,但结论却具有启发性。(2)应用企业层面数据测度贸易增加值,数据来自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库(唐东波,2012:13-32)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Upward等,2013:527-543;Kee & Tang,2012:1402-1436;张杰等,2013:124-137)。此类方法较为直接,也可对异质性企业和产品的特征进行解释分析,但无法反映要素价值“产业间转移”问题,由于未包含服务贸易数据,也无法反映一国的出口规模。(3)基于单区域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核算出口国内增加值,Hummels等(2001)开创性地提出了垂直专业化的测算方法(简称HIY方法),即一国总出口中进口中间品价值所占的比重,但该模型无法识别要素价值的国别来源和最终消费去向;一般假定进口中间品价值全部由国外创造,因而也无法探讨中间要素价值折返的数量和比重;由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是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并未区分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消费品和出口品生产中的比例,因而在应用HIY方法时一般假定两者相同(CCER课题组,2006:3-11;黄先海、韦畅,2007:158-159),导致测度偏差有可能进一步增大。(4)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分解出口额的国内、外价值构成,UNCTAD(2013)利用UNCTAD-EORA数据库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s)分别建立了一国出口额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模型。Stehrer等(2010)将“价值转移”和“价值折返”纳入到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构建了统一的模型考察了进、出口的国内、外价值贡献。
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仍非一国的价值出口额,原因在于“产业价值转移效应”和“国别价值转移效应”的存在,比如某些海关出口额为零的服务业,其价值可能隐含在制造业中实现了价值出口;也有某些海关统计为零的两国间贸易,其可能通过第三国的间接贸易而实现了两国间的价值交换。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增加值贸易口径来反映一国的实质进出口规模。所谓增加值进口是指一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吸收的另一国创造的增加值成份;而增加值出口则是指由本国初始创造但由它国最终消费的价值量。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Daudin(2011)首次提出了增加值贸易的概念,明晰了“谁为谁生产”的问题;Johnson和Noguera(2012)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值出口的概念和度量方法,基于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 7.1)数据库实证分析了各国的增加值贸易额;Robert Stehrer(2012)基于一国最终消费品价值来源的视角,构建了一国单、双边增加值贸易的测度模型。Timmer等(2012)基于WIOTs测度了各国要素收入和制造业的需求状况,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李昕、徐滇庆,2013:29-55;陈雯、李强,2014:107-115;樊茂清、黄薇,2014:50-70;罗长远、张军,2014:4-17)。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分别从生产侧和消费侧两个不同的视角考察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进、出口贸易利得,但两者之间也并非截然孤立的。Koopman等(2014)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将一国总出口的增加值来源分解为被外国吸收的增加值、返回本国的国内增加值、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由于中间品频繁进出关导致的纯重复计算等四部分,并进一步根据出口品价值的最终去向细分为9个部分;王直等(2015)扩展了上述方法,建立了总贸易流分解框架,将双边贸易额、双边部门贸易额、贸易总额和部门贸易总额等依据价值来源和最终吸收地分解为16个部分,从而形成了自官方总值统计到贸易增加值统计(以增加值为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体系)的一整套核算法则。虽然上述模型提到了出口总值、出口国内增加值、增加值出口额等三个不同的口径,但并未明晰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且研究出发点是基于出口总值的完全分解,因而出口中被国外吸收的价值并不一定等于增加值出口额;上述模型也未对不同核算口径下的进口额和贸易差额进行探讨,因而探讨国际贸易不同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本文贡献在于经过逻辑演绎提出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假说;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构建三种核算口径下的进口、出口以及贸易差额统计模型,并应用投入产出技术,经数理推导验证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的数据做经验分析。
二、逻辑分析、假说提出与模型演绎
(一) 逻辑假设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P和Q,均为开放型国家。贸易流程如下:第一步,P国向Q国出口价值A的产品;第二步,Q国消化吸收*消化吸收是指进口产品的价值留在进口国内,而不管产品的形态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进口部分(1-α)A的价值,而αA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置于总价值αA+B的商品中又出口至P国;第三步,P国自Q国进口的这部分商品价值,其中的(1-β)(αA+B)部分由P国消化吸收,而β(αA+B)部分作为中间投入要素随总价值β(αA+B)+C的出口品转移至Q国,并被Q国全部吸收。至此,两个国家间分别展开了一个回合包含价值折返和价值转移行为的贸易往来,并以价值全部被吸收而终结*现实贸易中,尽管每一个回合中P出口至Q的贸易不可能全部是最终品,但那不过是对第一个回合的重复,而中间产品都将以成为最终品被消费而结束,因而做出上述抽象假设。,如图1所示。

图1 两国模型下的全球生产网络简图
(二) 逻辑分析
依据图1的贸易流程,按照总值贸易核算口径,进、出口额将忠实于两国间商品的进出关记录。对于P国而言,出口额由贸易流程的第一步和第三步组成,出口额合计为A+β(αA+B)+C;进口额由贸易流程的第二步构成,金额为αA+B;由此核算出P国的贸易差额A+(β-1)(αA+B)+C。
依据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出口将剔除进口中间要素的价值,以国内增加值来表示。对于P国来说,第一步出口国内增加值仍为A,但第三步出口国内增加值是C,来自进口的中间投入要素价值需要从出口中剔除,因而在此核算方式下,P国出口额为A+C。进口额的核算限定在第二步,核算对象是进口国外增加值,对于Q国来讲就是它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价值量为B,也即是贸易增加值核算方式下P国的进口额。由此计算出P国贸易差额是A+C-B。
在增加值贸易核算口径下,出口额的核算将以本国要素价值是否为他国所消化吸收为标准。以P国为例,第一次出口额中被Q国吸收的价值为(1-α)A,第二次出口额中被Q国吸收的价值为β(αA+B)+C,但是其中βB的价值是由Q国初始创造的,需要予以剔除,那么P国对Q国的增加值出口额就核定为A+C-(1-β)αA。P国自Q国进口的商品价值中,只有(1-β)(αA+B)部分被消化吸收,但是其中的(1-β)αA部分由P国初始投入要素创造,其价值并不属于Q国,也需要予以剔除,因而,P国自Q国的增加值进口额就核定为A+C-(1-β)(αA+B)。于是,P国的增加值贸易差额是A+C-(1-β)(αA+B)。

表1 三种统计口径下P国外贸指标及其比较
(三) 逻辑假说
依据表1比较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核算口径下的P国进、出口额以及贸易差额,可以发现:
1.就出口额而言,(Ⅰ)>(Ⅱ)>(Ⅲ)。其中,(Ⅰ)-(Ⅱ)=β(αA+B),即出口贸易总额(Ⅰ)等于出口国内增加值(Ⅱ)与出口国外增加值β(αA+B)之和。(Ⅱ)-(Ⅲ)=(1-β)αA,即增加值出口(Ⅲ)等于出口国内增加值(Ⅱ)剔除进口并消费的国内增加值(1-β)αA部分。(Ⅰ)-(Ⅲ)=αA+βB,意味着增加值出口(Ⅲ)等于出口总额(Ⅰ)与整个贸易流程重复核算的部分αA+βB之差。
2.进口额也有相似的发现,(Ⅰ)>(Ⅱ)>(Ⅲ)。其中,(Ⅰ)-(Ⅱ)=αA,意味着总值进口额(Ⅰ)可以分解为进口国外增加值(Ⅱ)与进口国内增加值αA两部分。(Ⅰ)-(Ⅲ)=βB,说明增加值进口额(Ⅲ)等于总值进口额(Ⅰ)剔除P国自Q国进口又再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出口至P国的增加值βB。(Ⅰ)-(Ⅲ)=αA+βB,表明总值进口(Ⅰ)与增加值进口(Ⅲ)的差额也为αA+βB,即相对于增加值贸易核算口径,总值贸易进、出口额会以相同的绝对额αA+βB夸大P国的价值交换规模。
3.结合表1,比较不同核算口径下贸易差额的大小,可以确定(Ⅰ)-(Ⅲ)=0,即增加值贸易差额(Ⅲ)并不改变总值贸易(Ⅰ)口径下的贸易失衡状况。(Ⅰ)-(Ⅱ)=β(αA+B)-αA,总值贸易差额(Ⅰ)与贸易增加值差额(Ⅱ)的大小并不确定,这取决于出口国内要素增加值β(αA+B)与进口国内要素增加值αA的大小。(Ⅱ)-(Ⅲ)=(1-β)αA-βB,贸易增加值差额(Ⅱ)与增加值贸易差额(Ⅲ)的大小也不确定,而是取决于进口并消费的国内增加值(1-β)αA是否大于出口并在国外消费的国外增加值βB。
(四) 模型演绎
本部分将在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构建三种口径的进出口规模核算模型,在此过程中,比较分析各种口径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验证上文的假说。
1.投入产出分析框架

表2 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两国模型)

(1)
其中I为单位矩阵。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和世界投入产出框架,可以得到下列恒等式:
(2)
用分块矩阵形式表示为:
X=AX+f=(I-A)-1f=Bf
(3)
令f1=(F11F21)′、f2=(F12F22)′分别表示1国和2国最终消费列向量,记f=(f1f2)为世界最终消费矩阵。
2.总值贸易核算模型
根据投入产出框架,在总值贸易口径下,1国对2国的进口额等于1国生产中投入的2国中间品价值X21与1国消费中包含的2国最终品价值F21之和;同理可得到1国对2国的出口额;进一步推导出1国对2国的贸易净额,分别用以下三个公式表示:
(4)
(5)
(6)
3.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
依据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和投入产出技术,1国出口至2国的总额,依据增加值国别来源不同,可应用下列模型分解:

(7)


(8)

(9)
4.增加值贸易核算模型
在增加值贸易口径下,1国对2国的出口额表示2国总消费中来自1国的价值贡献,用下式核算:
(10)

(11)

(12)
上式中的替换关系主要依据投入产出表横向和纵向恒等式:
X11+X21+V1=X1=X11+X12+F11+F12
(13)
式(12)意味着在在增加值贸易和总值贸易两种口径下,1国对世界的贸易净额是一致的,即增加值贸易核算口径并不改变一国的单边贸易净额。由于
(14)
上述等式的计算主要利用了B12=B11A12(I-A22)-1以及投入产出表横向恒等式,该式表明1国对2国的增加值出口额等于1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减去进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同理可以核算得出:
(15)
上式表明1国增加值进口额等于1国进口贸易国外增加值减去出口贸易国外增加值。
三、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比较分析1995-2011年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进、出口贸易及贸易差额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不同口径下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世界投入产出库*数据来源:http://www.wiod.org/。WIOD汇报了35个产业部门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在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投入产出状况以及所有国家各产业部门的直接价值增值和最终消费状况。(WorldInput-OutputData,WIOD),该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5-2011年,包含27个欧盟成员国和13个其它主要经济体以及1个世界其它国家集合体*2009年,除世界其它地区以外的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全球GDP的86.14%,因而,可以较好的反映世界生产格局和贸易模式。,涵盖16个生产部门和19个服务部门。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中间投入矩阵(维度1435×1435)、中间投入总和行向量(维度1×1435)和总产出行向量(维度1×1435)可以直接获取,利用简单的投入产出技术可以得到中间投入消耗系数矩阵A(维度1435×1435)和增加值率行向量v(维度1×1435),而各国最终产品消费矩阵(维度1435×41)经简单加总*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最终消费包含有家庭消费、政府消费、非盈利组织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五部分,在模型中不再区分,统一合并为一国的最终消费。也可以得到。在此基础上,应用上述模型核算各国各产业在三种口径下的贸易规模和差额,主要运算过程在软件Matlab2014a中实现。
(二) 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对外贸易额及其比较
1995-2011年,在总值贸易口径下,中国出口额持续增长,仅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稍微波动,整个样本期间年均增长17.1%。进口额也有相似趋势,2009年较2008年降低了近1400亿美元,但2011年又达到最高值,相对于1995年增长了12.6倍,略高于出口额。贸易差额一直为正值,区间特征明显,1995-1998年贸易顺差额迅速增加,四年间增长1.2倍;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贸易顺差额波幅平稳,始终维持在450亿美元以下;只是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顺差额极速增加,至2008年已经达到4163.7亿美元,5年间平均增速48.9%;但是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后,贸易顺差额大幅度下降,2009年相对于2008年减少了1320亿美元,之后由于各国经济刺激措施的发力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贸易顺差额开始缓慢复苏。
在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由于剔除了总值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影响,中国出口额相对下降,但整体增长的趋势与总值出口额相仿。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2002年之前保持在80%以上,平均值为84.6%;加入WTO之后,由于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进口中间投入要素增多,出口品中的国内增加值率相对下降,至2011年基本保持在80%以下,平均值为76.9%,仅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这一数据回升至80.7%。中国进口国外增加值相对于总值进口额的降幅非常小,1995-1999年小于1%,2000-2003年小于2%,2004-2009年小于3%,2010和2011年为3.2%,17年间平均值为2%。这表明中国进口产品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国外要素直接创造的,与出口的情况对比鲜明。正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进口国外增加值率的显著差异,导致此口径下的中国贸易差额相对于总值口径核算额降幅明显,且有鲜明的区间特征,1995-1999年呈现顺差状态,1998年达到最大值302.3亿美元;2000-2005年呈现逆差状态,且绝对额快速扩大,至2004年达到最高值684.8亿美元;2006-2009年又转变为顺差状态,均值为574.4亿美元,2008年处于峰值915.8亿美元;2010和2011年又极速转变为逆差状态,其中2011年时为1019.3亿美元。
在贸易增加值的基础上,剔除国内价值折返的部分,就得到了增加值贸易额。如表3所示,增加值进、出口额进一步下降,下降幅度源自价值折返部分所占比重,1995-2011年,增加值出口额占总值出口额的比例由83.6%下降至75.5%,尤其是加入WTO以来,这一比例维持在80%以下,充分反映了中国嵌入全球化程度的增加,中间产品频繁进出关导致的重复核算部分持续增长;但增加值出口与出口增加值的差距并不明显,减少幅度约为2%,主要是由进口中的价值折返部分造成的。增加值进口额相对于总值统计结果降幅更高,自2000年以来的平均值为29.2%,其中2004-2008年高于30%,2011年为28.6%,降幅主要源于中国出口额中大量的国外增加值,而这一部分在增加值出口核算中必须剔除;由增加值进口额与进口增加值的巨大差异也可以反映这一点,2002年以来两者差异大概是总值出口额的28%。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完全一样,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以及模型论证。

表3 1995-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单位:10亿美元)
(三) 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对外贸易地位及其比较
在总值贸易口径下,2011年,中国出口额20861.9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1.3%,高出美国2451.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以出口国内增加值来衡量为16319.7亿美元,占比11.8%,略高于美国仍居世界第一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78.2%,高于全球平均值75.2%,低于俄罗斯、巴西、印尼、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印度,居第9位。增加值出口额15744.2亿美元,占总值出口额的75.5%,虽然低于美国的79%,但绝对额仍位居世界第一位。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出口额虽然迥异,但规模世界第一的位置并没有变化。
中国总值进口额17914.5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9.7%,比美国低了6075.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两个口径均未改变这一地位,只是绝对值变动明显。由于中国进口国外增加值率高达96.8%,而美国为94.5%,因而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美进口额的差距有所收窄。中国增加值进口额仅相当于总值进口额的71.4%,而美国这一比值为83.9%,因而在增加值贸易口径下,双方进口额的差距扩大至7334.2亿美元。

表4 2011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额(单位:10亿美元)
2011年,中国总值贸易顺差额2947.4亿美元,略低于德国的2985.5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与前文模型论证的结果相一致,各国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完全一致,从而说明总值贸易差额仍然可以反映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但若是依据贸易增加值口径,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1019.3亿美元,然而此时世界总的贸易差额显示为逆差40608亿美元,其原因在于各国的出口国外增加值率显著大于进口国内增加值率,由于该巨额逆差与贸易差额平衡理论明显相悖,因而贸易增加值并不适于作为国际贸易规模的核算口径,但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指标仍能反映一国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创造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该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
(四) 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各产业对外贸易额及其比较
依据核算结果2,首先可以确定本文的理论假说和模型结论仅适用于一国单边贸易总量层面,而不适用于产业层面。因为针对某一产业部门,增加值贸易额并不必然小于总值贸易额和贸易增加值额,而增加值贸易差额也与总值贸易差额并不必然相等。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间要素价值在产业之间存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效应,从而出现间接的增加值贸易,一方面本产业出口中包含有其它产业的价值a,另一方面其它产业出口中又包含本产业的价值b,当b>a时,增加值贸易额大于总值贸易额;增加值进口与出口的不对称变动将导致两种核算口径下贸易差额的差异。
在总值贸易口径下,中国出口额主要来自制造业部门,以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为代表,出口额7214亿美元,占比34.6%;但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不高,仅为71.1%;再考虑到出口价值折返回本国的部分,该产业增加值出口额大幅下降,仅为1938亿美元,相当于总值出口额的26.9%,在增加值出口总额的占比降为12.3%。这一典型事实凸显了总值贸易结果容易高估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夸大出口收益规模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国外先进要素投入的产业,而出口增加值率有助于认识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增加值出口则从总量上厘清产业的贸易收益规模。其它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增加值率相对要高一些,比如食品饮料烟草、皮革及其制品、木材及其制品、造纸印刷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纺织业为例,其总值出口额2418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1.6%,国内增加值率为85.7%,增加值出口额1058亿美元,与总值出口额的比值为43.8%。农业、矿产采掘业以及大部分服务业等18个部门的增加值出口额大于总值出口额,其中农业、矿产采掘业、金融业的增加值出口额分别是总值出口额的6.5倍、8.2倍和35.6倍,凸显了这些产业对其他产业出口的支撑能力,也反映了总值出口额可能掩盖国内各产业部门的真实竞争力来源。
三种核算方式下的中国各产业进口额也有显著差异,比如总值进口最多的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增加值进口额为1346亿美元,不足矿产采掘业的47.8%,约为总值进口额的32%,在总进口额中的比重也由23.4%下降为10.5%,但进口国外增加值率93.2%,说明中国多是进口该产业部门的上游产品,国内价值含量比较低。其它产业部门的国外增加值率也维持在高位,平均水平96.8%。基础产业、矿产资源以及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增加值进口额小于总值进口额,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各国各产业的上游产品特别是优质农产品、矿产资源以及先进零部件等中间要素的需求量巨大,而这些中间要素的价值一般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大部分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进口额高于总值进口额,这是因为相当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价值被包含在其它产业中间接进口,比如金融行业,总值进口额41亿美元,而增加值进口额439亿美元,间接进口额是直接进口额的近10倍。
就贸易差额而言,由于贸易增加值差额没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和现实意义,且与总值贸易差额差别不大,因而,本部分重点关注各产业总值贸易差额与增加值贸易差额的区别。首先,总值逆差的9个产业部门表现为增加值顺差,比如农业部门由逆差543亿美元转变为顺差620亿美元。其次,总值顺差的5个产业部门表现出增加值逆差,以租赁和其它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由顺差28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84亿美元,主要是由于增加值进口额变动幅度较大,这反映了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对其它产业较强的支撑作用。再者,持续保持逆差的5个部门,增加值逆差普遍小于总值逆差,比如矿产采掘业大幅度下降了1476亿美元,原因在于增加值出口核算了矿产资源价值的间接贡献,而进口多是直接资源,其价值变动不大。最后,一直保持顺差的14个产业,增加值顺差额普遍小于总值顺差额,比如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由总值顺差3011亿美元降低为增加值顺差592亿美元,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显著下降,这也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模式产业的典型特征。两种核算口径下贸易差额的差异取决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向的变动比例,具体依产业的特征来分析。这说明厘清价值的来龙去脉、关注产业价值的国内外转移、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对于重新认识产业部门的价值贡献十分必要。
四、结论与启示
当前探讨全球价值链的文献多是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的视角,重点关注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占比;也有文献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分析了一国的增加值贸易额,并与总值统计结果比较分析,但是少有文献把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三种相互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方式放在一起比较分析。笔者在逻辑演绎的基础上,依据世界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三类国际贸易核算模型,明晰了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总值进、出口额依据价值国别来源均可区分为国、内外增加值两部分;而出口国外增加值和进口国内增加值虽然并没有跨国界被消费,但其数额在总值贸易中均被计入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官方统计,因而依据增加值贸易的视角来看,同属于重复核算的部分;所以总值进出口额分别剔除这两部分重复核算值就得到了增加值进出口额,即实质发生价值转移的部分;对于一国单边贸易来讲,总值进出口中重复核算的数额相等,因而总值贸易差额与增加值贸易差额完全一样,这说明增加值贸易核算并不改变一国的对外贸易失衡规模。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推论得到,针对一国单边贸易统计结果,总值贸易额必然大于贸易增加值,而贸易增加值必然大于增加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贸易核算口径,因为其并未考虑国内出口价值折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清晰理解三种核算口径的内涵及其数量关系。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笔者比较分析了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1995-2011年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及其贸易差额,结果发现:进、出口贸易额在样本期内均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只是在内部或外部市场出现系统性变化时,有较大幅度波动;横向对比来看,数量从大到小依次是总值贸易额、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由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明显低于进口国外增加值率,因而贸易增加值统计下的贸易差额变动幅度较大,部分年份显示为巨额逆差,也因此,有些文献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严重高估,这实质是对贸易核算方式不完全处理的结果,因为在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世界进、出口总额并不相等;而在出口和进口两端分别剔除掉进口国内增加值和出口国外增加值之后,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完全一致,这表明官方统计差额是能够反映外贸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其政策启示在于:从稳增长、促就业这个层面上来讲,追求一定幅度的外贸顺差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总值贸易额与增加值贸易额的差值为重复计算部分,其中出口国外增加值贡献较大,这符合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占主导的对外贸易结构,因此,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总值进、出口规模明显回落,但由于重复计算的数据“水分”挤出效应明显,因而对中国增加值进、出口的影响却极为有限,其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外贸发展不能过分依赖“饱含水分”的加工贸易模式和总值进、出口规模,而应转变为谋求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分工地位的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额。在开放的世界里,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因此,剔除掉“重复核算”的水分之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绝对优势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结论仅适用于三种核算口径下一国进、出口总额的比较,而不适用于产业部门层面,因为模型并未充分考虑单个产业中间要素价值的国内外转移问题。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与中美贸易.世界经济,5.
[2] 陈 雯、李 强(2014).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规模的透视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财贸经济,7.
[3] 樊茂清、黄 薇(2014).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世界经济,2.
[4] 葛 明、林 玲(2016).基于附加值贸易统计的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
[5] 黄先海、韦 畅(2007).中国制造业出口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4.
[6] 李 昕、徐滇庆(2013).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全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中国社会科学,1.
[7] 刘遵义、陈锡康、杨翠红等(2007).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5.
[8] 罗长远、张 军(2014).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6.
[9] 沈梓鑫、贾根良(2014).增加值贸易与中国面临的国际分工陷阱.政治经济学评论,4.
[10] 唐东波(2012).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分析.管理世界,12.
[11] 王 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9.
[12] 张 杰、陈志远、刘元春(2013).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经济研究,10.
[13] Daudin,G.,Rifflart,C.&Schweisguth,D.(2011).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revueCanadienneD`economique,44(18).
[14] Hummels,D.,Ishii,J.&Yi,K.M.(2001).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54(1).
[15] Johnson,R.C&Noguera,G.(2012).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6(2).
[16] Kee,H.L.&Tang,H.(2016).Domestic Value Added in Chinese Exports: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6).
[17] Stehrer,R.(2012).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the Value Added in Trade.WIODWorkingPaper,8.
[18] Stehrer,R.,Foster,N.&deVries,G.(2010).Value Added and Factors in Trade:A Comprehensive Approach.Dynamics,67.
[19] Timmer,M.,Stehrer,R.&deVries,G.(2012).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WIODWorkingPaper,12.
[20] UNCTAD(2013).WorldInvestmentReport2013:GlobalValueChainsInvestmentandTradeforDevelopment.New York:United Nations.
[21] Upward,R.,Wang,Z.&Zheng,J.(2013).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of Chinese Export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41(2).
■责任编辑:刘金波
Logical Relation and Empirical Comparison between Trade of Gross Value, Value-Added in Trade &Trade in Value-Added
GeMing(Southwest University)
ZhaoSuping(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import and export scale revealed through gross statistics is difficult not only to trace the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of value in exports, but also to identify international trade structure and develop macro-trade policy. Therefore, this method have its shortcomings. Current literature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scope of value-added in trade, focusing on the share of domestic value-added in export. Some studies promote trade in value-added; meanwhile, little does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three calculating cabers (i.e., trade of gross value, value-added in trade and trade in value-added), which are mutuallu related but entirely differen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logical deduction and the world input-output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above three calculating models. Then, it clarifies quantitativ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calculating calibers:(1)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 of value, both import and export value in gross trad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domestic and foreign value-added);(2)Although foreign value-added in export and domestic value-added in import are not consumed by other country, they are counted in gross trade of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countries. Thus, according to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in value-added, foreign value-added in export and domestic value-added in import constitute double counting in unilateral trade statistics;(3)removing double counting from import and export value in gross trade can get the value-added of one country’s import and export. Therefore, the balance of gross trade and trade in value-added should be equal, and the caliber of trade in value-added doesn’t change one country’s foreign trade imbalance.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for a country’s unilateral trade statistics, gross trade volume is inevitably greater than the value-added in trade, while value-added in trade is greater than trade in value-added. The last requires a bit of explanation that value-added in trade is not an exactly calculating caliber, because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rade reentry of the domestic export value.Using 1995-2011 data from world input-output tables, this paper finds that:(1)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trade volume of import and export both presented a rising trend, which varied greatly depending on systemic changes in inside and outside markets;(2)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rade volumes from largest to smallest were gross value, value-added in trade and trade in value-added.(3) Since domestic value-added in expor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foreign value-added in import, therefore balance of value-added in trade changed in large scale, even running large trade deficits in some years. And so some literature insists that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foreign trade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e seriously overvalued.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don’t consider correct calculating calibers, it is difficult to hold its essence and subsequently it showed that the results were not accord with the facts. (4) Removing double counting from import and export value in gross trade can get the value-added of one country’s import and export. Therefore, the balance of gross trade and trade in value-added should be equal. This shows that the balance of the gross statistics was able to reflect the export and had direc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olicy enlightenment is that it is actively significance to pursue a certain amount of trade surplus with keeping steadily growth and promoting employment status. (5) Double counting is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ss trade and trade in value-added, and foreign value-added in export is a bigger contributor. All of these are in line with China’s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whose leading position is the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rade. Therefore, China’s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rade was influenced to a large ext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export and import of gross trade had dropped significantly. As a result of insignificant crowding-out effects in double counting, there was a smaller influence on China’s trade in value-added.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China cannot depend excessively on water-logged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rade and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value of gross trade. Instead, for its own further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pursue trade in value-added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which have high added value, technical content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6) In an open world, the major economies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to various degrees. Therefore, eliminating the repeated accounting section, the position of China in world trade doesn’t change, but absolute superiority is lower than befor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above conclusions only apply to unilateral trade in above three calculating calibers other than industrial level, because these calibers don’t take into full account inside and outside trade diversion effects from intermediate factors of an industry.
trade of gross value; value-added in trade; trade in value-added
F74
: A
: 1672-7320(2017)02-0061-12
10.14086/j.cnki.wujss.2017.02.006
2016-08-23
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S07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6YJC79014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4CJY08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303192)
■作者地址:葛 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Email:geming85@whu.edu.cn。 赵素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重庆 400031。Email:whuems@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