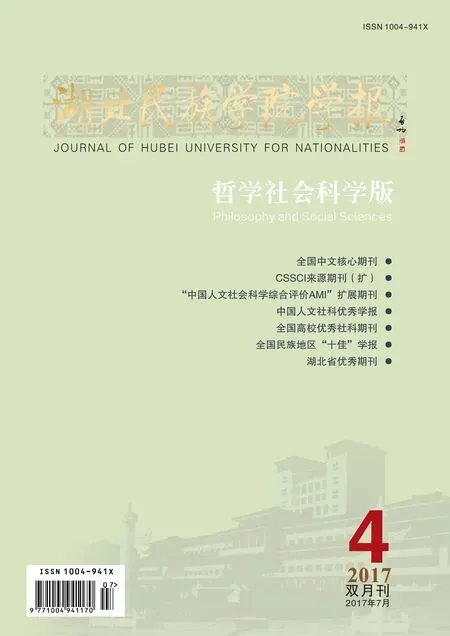《窦娥冤》之窦天章形象辨证
2017-03-08田兴国
田兴国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文本,于元代流行情况之真相,莫得而闻。元人钟嗣成撰《录鬼簿》,版本繁复所载不一。孟称舜本、曹楝亭本、王国维藏本等皆无载,唯天一阁本录及。现在可以认定元人所编杂剧选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无载录,朱权《太和正音谱》有载,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见其身影,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定本六种无载,王骥德《古杂剧》无录,臧晋叔《元曲选》录之,陈与郊《古名家杂剧》选录,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之《酹江集》见之,涵芬楼《孤本元明杂剧》不录等等元明戏曲文献,大概可觇知元明清三代对《窦娥冤》的基本认知及接受情况。此种态势恰好与一部分文人不接受乃至不理解《窦娥冤》所呈现的社会情状大体吻合。正如朱权所谓:“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1]这种理解几乎成为某种标准认识,一直相沿至上世纪中期。由于社会境域及时代精神状况(意识形态)的迁转,对关汉卿及《窦娥冤》的理性认识发生颠覆性变化,关汉卿成为“人民戏剧家”,《窦娥冤》亦上升为“首屈一指的代表作之一”[2]。当然,此种颠覆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直接渊源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剧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在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3]王氏博采欧洲学术哲思观照元杂剧,其结论自然与传统学术迥异其趣,劈出中国现代学术之前行方向。对《窦娥冤》之学术灼见直接被现代学者所承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王季思召集全国高校戏曲学者、组成学术团队编纂《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集》,《窦娥冤》名列十大悲剧之首。关汉卿于元明清三代剧家群中很难被文人拔为头筹,几乎处于马致远或王实甫之下,尽管有《录鬼簿》之“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将其列为第一[4],但此种情况较为罕见。当下既然将其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我国戏剧史上最早也最伟大的戏剧作家”[5],全社会普遍公认,则必有迥异于其他杂剧家的内涵优长所在——社会底层人物的反抗性即是。但是,一种“文学理论之所以长期与审美经验为敌,就是因为一味以理论的普遍性遮蔽文学文本解读的惟一性。这种舍本逐末之所以成为千年的痼疾,原因还在于,文学解读的惟一性本身蕴含着悖论。文本个案的所谓惟一性,就是不可重复、独一无二。但理论上却不能不是普遍的,因为它是对于无数惟一性的概括。理论上所说的惟一性,所指的是每个文本的惟一性。这种惟一性,恰恰是每个文本的共同性、普遍性。这种普遍的惟一性,本身就是对特殊文本惟一性的否定……从根本上说,理论的惟一性是与个案的惟一性不相容的。这样,个案的惟一性与理论的惟一性就成了永恒的悖论”[6]。但有一点非常明确:无论何种理论,必然以具体的、特殊的个案为基础,方能展开理性提升。离开具体的个案,也就无所谓理论的普遍性。即理论不能涵括所有个案。循沿此思维向度,《窦娥冤》赫然呈现出一个问题亟待澄清,即窦天章形象问题的恰切理解。
一、经济生态学视域之窦天章
明人选本凡载及《窦娥冤》的曲本,其窦天章形象无较大变化,基本保持一致。故以臧晋叔《元曲选》之《感天动地窦娥冤》为读解对象展开探讨。臧氏将《窦娥冤》杂剧按次序列于第四册、一百本杂剧之第八十六位,当可悬想关汉卿杂剧作品于其编选视域的当下地位。
窦天章首次出场于楔子,由蔡婆引领而出。楔子设置并蕴涵全剧所有事件发生的基础。卜儿扮蔡婆叙述窦天章向其借贷二十两银子,根据元代本利相侔之偿还原理,窦天章应该归还四十两银子。经过数次催索,“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她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他说今日好日辰,亲送女儿到我家来。老身且不索钱去,专在家中等候”[7]1499。冲末扮窦天章上场“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煞马相如。汉庭一日承恩诏,不说当罏说子虚”。画其形态,露其神质。自我道白曰:“小生姓窦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浑家亡化已过,撇下这个女孩儿,小字端云。从三岁上亡了她母亲,如今孩儿七岁了也。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她家广有钱物。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她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她四十两。她数次问小生索取,叫我把什么还她?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要小生女孩儿做她儿媳妇。况如今春榜动,选场开。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小生出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做叹科云] 嗨!这个哪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她一般,就准了她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分外但得些少东西,够小生应举之费,便也过望了”,“[做相见科,窦天章云] 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送来与婆婆,怎敢说做媳妇,只与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儿在此,只望婆婆看觑则个![卜儿云]这等,你是我亲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兀的是借钱的文书还了你,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亲家,你休嫌轻少![窦天章做谢科云] 多谢了婆婆,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缠,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婆婆,女孩儿早晚呆痴,看小生薄面,看觑女孩儿咱!”“[窦天章云] 婆婆,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则骂几句,当骂呵则处分几句!孩儿,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爷,将就的你。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儿呵,我也是出于无奈!”[7]1500
上引几乎全部是人物上场诗句及对白细节呈现。楚州蔡婆出场叙述窦天章借其“羊羔儿息”,于今本利必须归还。因窦天章家境贫甚无力偿还,蔡婆却看上其女孩儿,与之早经协商,用窦端云抵偿四十两银子债务。此蔡婆眼中之书生窦天章形象。高利贷者的贪婪本性遮蔽于似乎是温情的等价交换之上,实乃蔡婆为自己八岁儿子未来婚姻考虑,因窦天章借其二十两银子,且无力还贷,遂逼迫其以女儿相抵,销除两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从蔡婆而论,仿佛高利贷编织的经济关系建构起全剧事件始发的源点。
“羊羔儿息”即史料所谓“斡脱钱”。蒙古族个体、族群本没什么积蓄,于蒙古帝国征战史上逐渐由自发过渡到法令形式稳定下来。“是岁,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8]《史集》亦载有窝阔台与斡脱钱相关的逸闻轶事七八则,“一个很老的人来见合罕,恳求给他二百金巴里失去经营斡脱”[9]90,及“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10]等文献可知,“斡脱钱”即“羊羔息”或“羊羔儿利”。蒙古语ortoq或突厥语ortaq音译为“斡脱”,意谓合伙做生意之人,明显指向官商一体建构特质。上述文献表明,窝阔台时期,“斡脱钱”使用在汉地颇为流行且相当混乱,百姓、官府深受其害,但窝阔台、耶律楚材等提出最高上限“子本相侔”、“本利相侔”加以约束。即“著为令”或“永为定制”。时代递嬗,“斡脱钱”逐渐纳入帝国规范化管理体制。诸如颁布“债负只还一本一利,虽有倒换文契,并不准使,并不得将欠债人等,强行扯拽头皮,折准财产,如违治罪”[11],至元十九年四月,“随路权豪势要之家,举放钱债,逐急用度,添搭利息,每两至于五分或壹倍之上。若无钱归还呵,除以纳利钱外,再行倒换文契,累算利钱,准折人口、头皮、事产,实是与民不便。今后若取借钱债,每两出利不过三分”[11],《元史·刑法志》“诸临监官輒举贷于民者,取与俱罪之。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輒取赢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偿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诸典质,不设正库,不立信帖,违例取息者,禁之”[12],《元典章》亦多次以令旨形式颁发整个帝国,“依在先大体例里,一两钞一月三分家利钱,已上休要者。今后多要呵,本利没官”,且多次强调“每月一两钞,一钱、两钱利钱要有”等类[13]。结合《黑鞑事略》:“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铤之本,辗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铤”,“自鞑主以下,只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回回或自转贷与人,或自多方贾贩,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佐证等实际情况[14]。“斡脱钱”实质已经获得蒙元帝国以法律形式承认,只不过以法令形式限定利息的最高额度,即每从一两获利不超过本息数递减为不超过三分。如若超规越矩则会被严惩。而窦天章的私债情况,对照以上所述,他不仅默认蔡婆的“羊羔息”要求,而且也无起中介作用的担保人。“有一个人一再请求从国库里给他五百八里失的现金,用它们去做买卖。[合罕]分付给与。近臣们[向他]报告说,这个人没有可靠的担保,一个钱也没有,并且还欠多少多少的债。”[9]91应该说,民间借债都会有一个中人角色出现,他与蔡婆纯粹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任何保证。但是剧作家却将“借钱的文书”(契约)这个关键物证纳入文本,说明剧作家并不是只粗疏交代一件事,可以遗漏居间担保人,但决不能省掉一纸契约。
根据《感天动地窦娥冤》所呈现之事实,比较符合元代前期北方汉地实际生存状况。尤其符合元太宗窝阔台至成宗大德六年。有研究者将蒙元帝国刑法“划分为1260年以前、1260至1271年、1271至1302这样三个发展阶段”[15],其基本特点则蒙古法、汉法、回回法等并行天下,此种情形恰好与学界所推定关汉卿的生卒年限基本吻合(学术界一般认定关汉卿生活于13世纪左右)。有相关论者甚至推定“《窦娥冤》可能也写成于至元末年(1294年)”[16]。从关汉卿创作实际来看,“羊羔息”于剧中只是锻造窦娥冤狱形成之基本条件之一,完型其冤狱还需要其它因素的配合。由于它与窦天章直接相关,极其容易以“羊羔息”取代或遮蔽他的功名欲望这一源始质素。“羊羔息”非常残酷,百姓即生活于如此社会生态之中,它笼罩着所有人的生活,具有普遍性。并且,蒙元帝国以法律形式肯定其合法性,变无序为有序,只不过较前期的混乱较为规整些罢了,但一直没有取消此项政策,它广泛、直接地渗入百姓日常生存生活。对民间之影响可见一斑,关汉卿撷取书生窦天章形象刻写“羊羔息”,其涵括之深、之广当为大元剧家第一人。对照朝鲜汉语教材《老乞大》《朴通事》(1392-1910年)所述来理解,当更直白透显。窦天章与蔡婆之借贷关系平和解决,以端云作抵押,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正是各种各样的私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组织了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也支撑了整个社会秩序的有效运作。总而言之,正是形形色色的难以计算的契约文书建构了,也维持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及其有效运作”[17]。藉此,诸如窦天章与蔡婆之间发生借贷之事,民间何其多也。且民间一直奉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信条,被视为天经地义。自然发生,自然解决。即使抵押房产、卖儿鬻女等,在民间均视为正常。窦天章如此,其他百姓如此。常人习焉而不察,关汉卿流泻于片楮,呈演于舞台。它呈现为窦天章的悲剧,也是全社会的悲剧。但不是窦天章悲剧发生的源始抑或根源。
二、政治生态学视域之窦天章
一旦我们将观照之眼投放于窦天章,则又非常明显地否定了经济关系建构《窦娥冤》悲剧的初始理路。窦天章上场辞自我定格为饱读诗书之儒士,但经济上一无所有;一旦听闻朝廷选场开,立马以攀附司马相如史事而自我证显。传统文化中的达济天下,穷善其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胸怀,于此类文人身上很难觅其影踪。凸显的却是异常强烈的功利价值取向,诗书仅仅是谋取手段而已。其下,具体介绍其祖籍长安京兆,自幼以儒为业,不习生理,因而其妻在端云三岁之时西归。端云七岁时,一家流落至楚州。既然窦天章清楚明确地表述自己“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他于当世所获得社会承认的身份必然是儒户无疑。元王朝的儒户与僧、道等户享有某种优免权,即免除某些赋役、苛捐杂税等项。那么,“最初设立儒户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援引僧、道免差的先例,救济流离失所的儒士,另一方面,也有为国储存人才之意。及至忽必烈即位以后,已以继承中国历代正统的王者自居,优待儒士在政治上乃属必然”[18]。读解元王朝基本历史文献,诸如宋濂等编纂的《元史》、魏源《元史新编》、律法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等,以及域外文献诸如波斯拉施特撰《史集》、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及《马可波罗行纪》等。当然,《蒙古秘史》更是基础性文献。大致可以说明儒士、儒户于元王朝享有某种优待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只是科举停废更是显赫事实。因此,窦天章之自述呈现一个较大漏洞:作为儒士、儒户的他,生计、生理基本不成问题,而其妻缘何而死,就成为一明显模糊之处。由于外在之天灾人祸,抑或直接缘于窦天章(病殁、寒饿死等类),于本杂剧来说,或明或暗均指向于他,对所有观赏者而言,基本不会产生怀疑。这与蔡婆述其夫主已逝迥不相侔,故而不会受到异议。此一节点便聚焦为窦天章形象缺憾、甚而让人产生怀疑的问题之一。
窦天章一贫如洗,却视科举功名为惟一要务,因而不屑于或无能打理生业。从人物形象上可直观命名为“范进型”。其欲望显表层则无一例外地趋向于救贫之策,深层涵蕴着主体精神文化心理建构的终极完型,即自我实现。不仅可以光宗耀祖、显亲扬名,而且可以伸展自己燮理阴阳、经纶天下大手,从而无限趋近儒家所谓“三不朽”神圣境域。所以,窦天章向蔡婆告借二十两银子作盘缠参加科举考试,不幸铩羽而归;连本带息需归还四十两银子,生计无门的窦天章在蔡婆三番五次派人游说情形之下,被迫答允将女儿端云与四十两银子相抵,卖给蔡婆当童养媳。时值朝廷选场开,窦天章盘算着也许还可以从蔡婆那儿得到某些赠予。蔡婆果然多送她十两银子,正好可作为此次上京应考的所需花费。当可想见,窦天章的真实心理状态——惊喜。端云与功名,于窦天章救贫之策和自我实现现实、心理相较中处于劣势,功名之念压倒养育女儿之伦理亲情。尽管窦天章表现出悲叹神情,毕竟是血缘亲情,亦难割舍。质言之,于儒家(不管是原儒还是新儒家)视域而论,它也不强调为实现功名而弃绝所有,经纶天下,实际是将仁爱亲人,推及泛爱天下,如张载所谓:“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9]儒家之仁建基于血缘家庭,向外扩展于无血缘关系之所有人。窦天章以功名制扼血缘亲情,悖逆于儒家理论框架;弃女儿生死于不顾事相,揆诸常情常理,普通人亦难理解并有效接受,遑论其认同此父此情。
合而论之,窦天章因为上朝取应,先行向蔡婆借贷二十两银子,导致无法偿还窘境,最终驱使其将端云抵押给蔡婆做童养媳。经济关系仿佛先行展开,实乃前有窦天章上京赴考之举形成的借贷关系,其底蕴只有政治关系方能担当《窦娥冤》全剧展演的核心构建重任;当然,并不是说没有研究者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政治问题是造成窦娥的悲苦身世的根本原因。她父亲窦天章,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惜把七岁的女儿以四十两银子卖给蔡婆当童养媳。且不说这个贫秀才自身的动机是‘汉庭一日承恩诏,不说当罏说子虚’,想借科举改变自身的困顿境遇;在他一意赴考、灭绝亲情的背后,又反映着历代封建王朝收揽人才、笼络人心的政策”等等论述[20]。明确指出政治因素乃窦娥身世的根本原因,但就谢柏梁核心论旨来说,一方面,窦天章人物形象不是论者阐述的重点,一方面,论者较少或没有针对此问题展开详细阐述。至此真相大白。殊非“关氏在《窦娥冤》一剧中,便是以高利贷作为致祸之由,加以当时官吏的贪污,因而造成窦娥的无辜被斩”[21]。此节塑型为窦天章形象缺憾之二。此种设定既缺乏现实基础,又不能体现编剧的艺术深心,难以企及有效传输艺术真实的目的。
第四折,窦天章由楔子的小生转换成老夫形象。“老夫窦天章是也。自从离了我那端云孩儿,可早十六年光景。老夫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谢皇恩可怜,加老夫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随处刷卷审囚,体察滥官污吏,容老夫先斩后奏。老夫一喜一悲:喜呵,老夫身居台省,职掌刑名,势剑金牌,威重万里;悲呵,有端云孩儿,七岁上与了蔡婆婆为儿媳妇。老夫自得官之后,使人往楚州问蔡婆婆家,她邻里街坊道,自当年蔡婆婆不知搬在哪里去了,至今音信皆无。老夫为端云孩儿啼哭的眼目昏花,忧愁的须发斑白。今日来到这淮南地面,不知这楚州为何三年不雨。”[7]1500窦天章之类人物在元杂剧中,一般表现为特别侥幸,大都穷困潦倒却矢志诗书,最终如愿博取功名。只不过证明此类书生真的浸淫诗书有年,腹蕴才华,发抒剧作家一腔郁愤而已。窦天章之喜,涵括天下所有怀才不遇者的精神心理上的自我慰籍。虽然超离于元王朝社会现实远甚,但具有其艺术真实性。离家十六载,而功名已经到手,此时念及被己抛弃的孩儿端云之悲,完全笼罩于科举之喜氛围中。窦天章前后并置对观,编剧使其处于同一悲情状态之下,其无意中所造成的讽刺别有一番风致。
官拜参知政事、加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窦天章,廉访两淮各地。赴至楚州驿馆,审阅各类卷宗。冤死的窦娥鬼魂日思夜望官府为其昭雪,窦天章于灯下看读文书,见其姓与己相同,罪名却是“药死公公”,属于“十恶不赦”之罪,其心早已认定前官断案合情合理。窦娥鬼魂两次吹灭灯火,一以梦境哭诉其苦,一以鬼魂直接向父道其详情。由于窦端云到蔡婆家之后易名为窦娥,窦天章不知,及至造成如许误会。窦天章楔子中出场,主要是确立全剧生发的原始起点——政治而来。结尾再次上场之时,已官拜参知政事、加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为女儿窦娥伸张冤屈,同样是为政治而来。因为只有政治手段方能解决政治所酿下的苦酒。应该说,审阅卷宗的窦天章也够不上清正廉明,只因整个传统社会所认定的十恶不赦罪名,即不能秉持公心冷静看卷,其颟顸可知。
[正旦做悲科云] “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7]1513作为所有事件的承受者——窦端云,眼见亲爷离己而去,也无能改变此一事实。对亲爷的埋怨、愤怒却没有以极端言行加以展露,编剧似乎尽力于维护父权这一本相(所谓的女子“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将它与“哎,你个窦天章直恁的威风大,受了我窦娥这一拜”续成整体[7]1511-1512,七岁之窦端云和十六年后已化为鬼魂的窦娥比较,端云在父亲抛弃自己既成事实面前,满腹幽怨不敢发泄,化为鬼魂竟然直呼窦天章之名,愤怒之情于魂旦脚色显露无遗。那么,窦天章形象最大的败笔当在于深陷政治与血缘伦理亲情两难困境时,他选中政治科举,弃亲情于不顾,违背了儒家仁爱本义;且与元代社会现世儒士生存事实有较大出入。进入朝堂,本应该忠于君王,勤于王事,廉访地方,应该对人命关天之事认真审阅,分辨黑白,而不应该有先入为主之见,敷衍了事。窦娥悲剧酿成,原点在其父窦天章的科举功名与生存生活等量齐观,甚至科举功名凌驾于生存生活之上。即窦天章的考中科举是以牺牲其女端云的性命换来,窦端云成就了窦天章,成为其父换取银两的工具。窦天章成功了,窦端云却冤屈而死,儒士燮理阴阳之志伸展,将子女亲情伦理埋葬。既是政治的悲剧,也是伦理的悲剧。无论注意与否,窦天章作为始作俑者难辞其咎。他的戏剧形象殊少历史真实性,却涵蕴着异常丰富的社会真实,特别是人性的丰厚与复杂。因此,窦天章形象本身就是一大悖论——真中蕴含非真,非真之中孕育着深刻的真实。于剧作家而言,真与非真的窦天章本不是主要脚色,他的使命在于建构全剧生发之源与结穴目的,以大写意手法达到终极目的,收缩全剧。以此视域观之,窦天章形象问题当可迎刃而解了。也许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不分折、基本不存在独白、对白内容等因素作为衡量标准,《窦娥冤》的楔子应该不会存在,可能依靠演员上场临时添加而来,明代的改窜本大抵如臧本:对白、独白较为丰富。关汉卿原本究竟如何,如今无以获知。过错只能归咎于陈玉阳、臧晋叔等一干明代文人。
结语
关汉卿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以最为普通的一个下层妇女——窦娥一生遭际,向人们呈现出一种社会、一种时代的生存本相。普通人、小人物的悲剧发生,本质上由蒙元帝国政治所统摄,它向外伸展出多重因素,经复合酝酿、锻造而成。却不能由经济——高利贷“羊羔息”这一被伸展出的因素来顶代它的生发源——科举政治。
揆诸情理,窦端云父亲——窦天章,贫困潦倒半生,科举功名是其一生念想,视其为生存生活的全部、生命价值意义的惟一。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事先借下蔡婆“羊羔儿息”二十两,落第归来,无力归还债务,被蔡婆所逼,只能将女儿窦端云抵押做童养媳,顺带还赚得十两银子作为此次参加科举考试的盘缠。综观窦天章整个人生,其生存能力极低,甚或根本就不具有生存能力;女儿窦端云成为手中一大物品似乎可以随时出售;尽管他也表露出某种血缘伦理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显得极为虚伪矫饰。功名与女儿的选择更凸显其人性基本特点,以及现世生存价值取向,功名需求明显高过女儿性命。其妻之死虽然一语带过,但给人留下较大遐想空间,极有可能将责任归诸窦天章无生存生活能力所致。因而,窦端云社会生存悲剧的终始原因只能由窦天章领代了。即由窦天章的科举功名欲望推促而成。那么,关汉卿究竟是热望科举功名抑或抨击之,于全剧所创情境中可以发现:关汉卿对窦天章因为科举功名抛弃女儿,执持一种良心愧悔向度;既热望功名,又难离弃女儿,终究弃绝女儿,窦天章是痛苦的,关汉卿自然处于痛苦状态。窦天章失去女儿换取功名取得成功,关汉卿采用科举成功冲淡窦天章丧女之痛,仔细揣摩当可觇知。关汉卿精神心理层强烈认为儒生的惟一出路即在科举,诸如剧本《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之书生韩辅臣出场辞“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幼习经史,颇看诗书,学成满腹文章,未曾进取功名”[22],《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之书生柳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幼习儒业,颇读诗书”[23],《望江亭中秋切鱠旦》之白士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自登科甲,金榜姓名标”等等观念性表达即是[24]。一旦面临生存生活之际,其价值取向则变得较为复杂——苦痛、欣羡交织,但始终聚焦于科举成功,以其“贫”遮蔽窦端云政治性悲剧动力始发点。因而极易误导观赏者将窦端云社会悲剧建构始基滑向蔡婆为代表的高利贷者,即经济原因(蔡婆本身也成为帝国政治的受害者)。窦端云悲剧实在发端于儒士科举功名热望、政治因素残酷挤压而成型。踵武而来的经济上的“羊羔息”盘剥、流氓恶棍陷害、官员贪赃枉法斩杀窦娥等情实均于政治这一基础生发。
中国传统社会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精英们就不断从理论上讨论社会理想治理模式,圣人治理天下体制被广为接纳,他集政治、伦理道德、学术等于一身,沟通天人;中原族群所建构的各帝国体制将全天下人群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置于末尾,且帝国体制特别标榜“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商被置于道德论之“奸”范畴,此可明瞭,中国传统社会帝国政治决定经济之实质。尽管蒙元帝国按照征服之先后顺序,将人群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类,且明显提高商人地位,甚至鼓励官员经商,建构起经济上的“斡脱所”制度,但蒙元帝国经济运转依然由帝国政治所生发,也因蒙古族群生存生活之游牧方式导致而成。中国传统社会之圣人治理天下本身即意味着政治与伦理的同构,因而,商人、商业必然被排除在外,又因为人之生存生活自身离不开商人、商业,那么,政治、伦理就会对商人、商业展开体制监管与道德约束成为必然之理。同理,窦娥悲剧性最终形成之源始基点,只能是其父窦天章科举功名之政治实现欲望。“羊羔息”顺承政治体制而来,却无能成型为基点,它只能成为强有力推手之一。
当然,《感天动地窦娥冤》创作主体关汉卿内心不死的情结,聚焦点始终指向蒙元帝国对科举80年左右的停废的极端不满。
[1] 朱权.太和正音谱笺评[M].姚品文,等,评.北京:中华书局,2011:24.
[2] 冯沅君.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C]∥名家解读《元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212.
[3]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99.
[4] 钟嗣成.录鬼簿[M]∥王国维,校注.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449.
[5] 游国恩,王起.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86.
[6] 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3.
[7] 臧晋叔.元曲选·感天动地窦娥冤·第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6:1499.
[8] 宋濂.元史·太宗本纪·卷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8:18.
[9]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M].余大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0] 宋濂.元史·耶律楚材传·卷一百四十六[M].长沙:岳麓书社,1998:1942.
[11]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杂令·违例取息·卷第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1:678.
[12] 宋濂.元史·刑法志·禁令·卷一百五[M].长沙:岳麓书社,1998:1540.
[13]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户部·卷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1:996-997.
[14] 彭大雅,等.黑鞑事略·其贾贩[M].许全胜,校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83-84.
[15] 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80.
[16]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2.
[17] 徐忠明.《老乞大》与《朴通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96.
[18]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0:387.
[19] 张载.张子正蒙[M]∥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353-354.
[20] 谢柏梁.世界悲剧文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206-207.
[21]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87.
[22] 关汉卿.关汉卿集·杜蕊娘智赏金线池[M].马欣来,辑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48.
[23] 关汉卿.关汉卿集·钱大尹智宠谢天香[M].马欣来,辑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67.
[24] 关汉卿.关汉卿集·望江亭中秋切鱠旦[M].马欣来,辑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