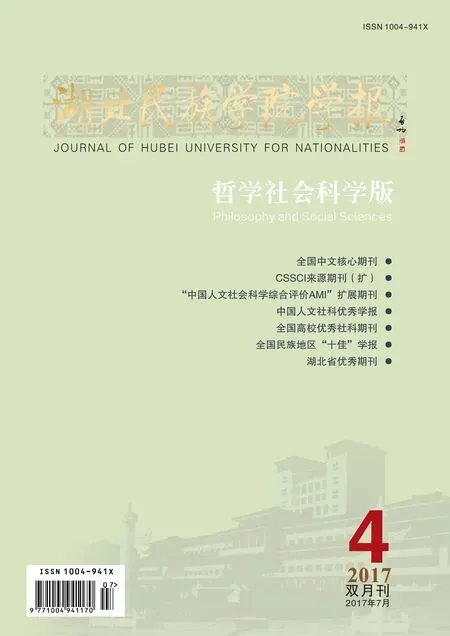从祭祀仪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撒叶儿嗬”的当代嬗变
2017-03-08陈心林徐红艳
陈心林,徐红艳
(1.湖北民族学院 研究生处,湖北 恩施 445000;2.湖北民族学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引言
“撒叶儿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在亲人过世后吊祭逝者的一种祭祀仪式,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丧葬文化中“丧事喜办”的一个典型,目前主要流行区域为鄂西清江流域的巴东、建始、长阳、五峰等县市。“撒叶儿嗬”实际上是一个衬词,因其每一段唱词后面都需要一句“撒叶儿嗬”来应和,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这种祭祀歌舞的名称,因为不同的汉字记音,也有“撒尔嗬”、“撒忧祸”等几种说法。“撒叶儿嗬”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地理志》:“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扣弓箭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之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也。”[1]清《巴东县志》记:“旧俗,殁之日,其家置酒食,邀亲友,鸣金伐鼓,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2]土家族“撒叶儿嗬”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唱丧词、打丧鼓、跳丧舞等。“撒叶儿嗬”文化承古而来,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原生态的文化意蕴。作为清江流域土家族一项标志性的民族文化事象,“撒叶儿嗬”很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潘光旦先生在巴东调查时,就注意到“野三关的‘丧儿贺’跳得很好,有名。”[3]
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关注度的提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与“撒叶儿嗬”有关的议题也迅速成为土家族研究的热点,相关成果相当丰富,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仪式本身的研究,如《土家族“撒叶儿嗬”源流、内涵及功能探讨》[4];二是对其舞台化、艺术化的研讨,如《鄂西“撒叶儿嗬”舞台化问题探讨》[5];三是对其传承与变迁的分析,如《土家族“跳丧”文化传承与转型若干问题的探讨》[6]、《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7]。综观已有研究成果,比较而言,学界忽视了对“撒叶儿嗬”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嬗变的研究,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一、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撒叶儿嗬”
“撒叶儿嗬”是清江流域土家人孝亲、爱亲、思亲的一种仪式表达。土家族老人过世之后,停灵于堂屋正中,亲友邻人前往吊祭。天黑之后,宾客踏歌打鼓,通宵达旦唱跳“撒叶儿嗬”,营造热烈气氛送亡人,慰生者。“撒叶儿嗬”一方面是吊祭亡人、抚慰生者的歌舞表演,同时还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其歌调声腔是一种古老的三声腔,这种歌腔在其它地区已经消失,仅在“撒叶儿嗬”中得到了保存。
土家族老人过世,往往会停灵三至五日。在停灵期间,夜夜跳丧。土家人将死亡分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两类。非正常死亡的如英年早逝、死于非命,都不能唱跳“撒叶儿嗬”。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已经步入老年,且后代昌盛,但是若父母健在,也“不应该走”;在土家人看来,这属于没有完成尽孝的义务,因此依旧归为非正常死亡,也不跳“撒叶儿嗬”。只有当亡者已经步入花甲之年,有儿有女,父母离世,才算是正常死亡,称之为走“顺头路”。凡这种“顺头路”,都应该跳“撒叶儿嗬”。在跳“撒叶儿嗬”的过程中,乡邻会以热闹的程度来评判后人是否孝顺。如果丧礼办得冷冷清清,会受到当地舆论的谴责。在“撒叶儿嗬”举行过程中,孝子及女性不能参加。因为孝子需要迎接宾客,为宾客装烟倒茶,女性跳“撒叶儿嗬”则有“女人跳丧,家破人亡”的说法。除此之外,不论年龄大小、辈分高低均可参加。
“撒叶儿嗬”所展现的内容主要为土民图腾信仰、渔猎活动、农事稼穑、爱情生活、历史事件等,反映了土家族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记忆以及品德观念、是非观念。因土家族人世代居住在沟壑纵横的武陵山区,日常生活以及农事活动中需要跨山越水、负重攀岩,由此形成了“撒叶儿嗬”唱跳中的粗犷风格。
“撒叶儿嗬”通常由歌师击鼓,舞者依据鼓点起舞,两人或者四人对舞于灵前。舞者头包白毛巾,身着白色对襟上衣,黑色粗裤布鞋。人多时可设多个舞场,掌鼓者既是舞蹈的指挥者,又是歌唱的领唱。开台歌结束之后,掌鼓者边击鼓边领唱,舞蹈者闻声起舞,边跳边唱,围观群众随节拍而击掌。届时以鼓、堂锣、马锣伴舞,所舞内容包含“五句子歌”“哑谜子”“双狮抢球”“凤凰展翅”“滚身子”“虎抱头”“犀牛望月”“燕儿衔泥”“叶儿合”“四大步”等24种套路。
舞蹈主要包含三种基本动作:第一种是二人对立,游手上步,行至右侧交换位置;其二为二人对立,互为绕手,上步于对方右侧,左旋及原位;第三种,分四步,同起右脚,一步贴面,二步擦背,三步亦贴面,四步同擦背,随后转半圈至面对面。以上三种方式构成了“撒叶儿嗬”的基本动作。舞蹈过程中,舞者双脚与肩同宽,脚掌紧紧贴地,稳重有力。“燕儿衔泥”是整场仪式中最精彩的部分,舞者模仿燕子衔泥的动作,双手展开,弯腰用嘴去叼地上的“五巾”(五巾是由五种颜色的布条组成)。“撒叶儿嗬”动作的核心特点是顺拐、屈膝、颤晃。双腿上下晃动,胯部左右摇摆,上肢随之晃动。
“撒叶儿嗬”音乐唱腔分为高腔和平腔,节奏鲜明。所谓“高音扯上云霄,任他乌云作幔;低音扎入九泉,管他恶鬼成群。”最常用的曲调有《十绣香袋》《哑谜子合》《十梦》《十绣天子城》《荷包歌》等。旋律节奏主要有2/4、4/4、6/8拍,以6/8拍子带切分音的节奏为主。“撒叶儿嗬”的乐器主要是一面大鼓。开场后,一人持木槌击鼓而歌(大鼓放置于棺材左侧),二人或四人开始交叉跳舞。同时,“撒叶儿嗬”的音乐也延续了部分楚国音乐的旋律,带有鲜明的荆楚遗风。[8]
“撒叶儿嗬”的演唱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掌鼓歌师击鼓领唱,众人和唱。演唱者多以假声喊歌,在巴东县以清江为界,野三关、白沙、长岭等地区均是清江北岸的风格;清江南岸的水布垭、杨柳池等地的表演则是另外一种形式:掌鼓歌师击鼓领唱,以唢呐伴奏,众人不帮和。“撒叶儿嗬”唱词繁复,最开始是为亡者歌功颂德,到了后半夜就开始唱“五句子歌”或者打“哑谜子”,内容十分丰富。
“撒叶儿嗬”作为丧礼上的祭祀歌舞,也展现了土家人豁达的生死观。如《开台歌》中所唱:
人生好比一台戏。
离合悲欢在哪里,
来者来兮去者去。
他们认为人的生死是顺应自然规律,是人生的出世之礼,自然值得庆贺,因此也就有了“白喜事”之说。
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撒叶儿嗬”
土家族“撒叶儿嗬”申遗之路于2002年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正式开启。2002年5月,长阳先后建成了县文化馆资源库,成立了抢救、保护优秀民间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建立了“长阳县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出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切实推进了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也为“撒叶儿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4年7月,长阳县政府成立申遗工作专班,县长任组长,出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申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工作方案》,把“撒叶儿嗬”申报名称初定为“跳丧舞”,7月8日在长阳文化局召开了“申报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跳丧舞’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动员大会”。在2004年7月至2005年10月间,长阳县政府先后开展了三次业务培训、两次田野调查、三次专家论证,获得了大量关于“撒叶儿嗬”的系统资料。
2005年8月11日,经省文化厅批示后,长阳县将“撒叶儿嗬”以“湖北长阳土家跳丧舞”为名称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1月5日,国务院正式公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候选项目,共501项,长阳土家族“撒叶儿嗬”名列其中。2006年6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共计518项,长阳土家族“撒叶儿嗬”列为第121项,属第三类民间舞蹈类(编号Ⅲ—18),传承人为张言科、覃自友。
巴东县本为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叶儿嗬”丧葬仪式传承的核心区域,长阳土家族“撒叶儿嗬”的成功申遗极大地刺激了巴东县。紧随其后,巴东县迅速启动了该县“撒叶儿嗬”的申遗工作。巴东县委、县政府自2005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文化部门组织专班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研究及申遗工作,对“撒叶儿嗬”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形成了大量的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巴东县野三关镇更是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2006年11月,土家族“撒叶儿嗬”入选巴东县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11月入选恩施州第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入选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终于2014年成功当选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发[2014]59号)。
三、从祭祀仪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撒叶儿嗬”的当代嬗变
(一)文化功能的变迁
1.传统功能
(1)教化与凝聚。文化系统对于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运行具有制约性的作用。“撒叶儿嗬”作为一种丧葬仪式,集中地蕴含和体现了清江流域土家族关于人生与社会的观念,在其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的位置,对于该社会的意义系统与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规约功能。
第一,规范行为,道德教化。“灵堂就是学校,歌场就是课堂”[9],土家族人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祖先崇拜的主旨在于增强族内的向心力、凝聚力,规范族内人员行为。
第二,增强社会凝聚力。涂尔干曾深刻地分析了仪式对于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性:“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感;与此同时,个体的社会本性也得到了增强。那些荣耀的纪念不仅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也可以使人们体会到彼此的亲属关系,使人们感到自己可以变得更加强壮,更有信心。”[10]“撒叶儿嗬”也具有这种功能。在土家族聚居区,往往谁家有丧事,亲朋好友都会自发前来吊唁,相聚一堂,共诉哀思,分享同样的情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人死众人哀,不请自然来”。哪怕与死者生前有矛盾,也会自动化解。
(2)精神慰藉。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的功能在于满足个人的需求[11]。马氏将葬礼上生者对死者的悲痛视为一种习俗和手段,目的是为了减轻因死亡对个人带来的压力。“尽管这些神佛并不能满足世俗的一切愿望,但他能够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安慰和幻想的幸福。”[12]“撒叶儿嗬”仪式虽不能使人们完全忘却亲人过世的悲伤,但是仪式形式的“撒叶儿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生者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减轻压力,宣泄了内心的悲痛与苦闷。
(3)传承民族文化。“撒叶儿嗬”的唱词内容,充分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例如《开场歌》中唱到:“向王开疆辟土,土民守土耕稼。”这是土家人对其祖先向王的赞颂。《待师》中唱到:“走进门来抬头望,桑木弯弓挂墙上。”是对土家人原始狩猎生活的记载。它也展示了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融合。如《盘古出世歌》《姜子牙》《桃园结义》等都吸收了汉文化的重要内容。
(4)娱乐功能。“撒叶儿嗬”的唱词是土家人民智慧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娱乐的功能。“撒叶儿嗬”唱词灵活多变,曲调活泼,可即兴编唱,从生产生活到自然科学,从现实故事到历史传统,爱情的,时政的,伦理的,无所不包。在缺少文化活动的年代,“撒叶儿嗬”成为土家男女老少的重要娱乐方式。
2.当代功能的变迁
传统“撒叶儿嗬”作为一种祭祀仪式,在土家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成功“申遗”之后,“撒叶儿嗬”的祭祀功能开始弱化,表演功能、经济功能开始突显出来。
上文述及,传统意义上的“撒叶儿嗬”只能在特定的场合举行。2006年“撒叶儿嗬”成功申遗之后,我们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观看到“撒叶儿嗬”的表演。
2006年之前,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土特色文化,也曾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出台了相关政策,并利用旅游业来推广和传播。在1997年“五个一工程”推行的时候,恩施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州却没有自己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为了打造文化品牌,政府于第二年起开始在全州征集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词和音乐。受2001年来凤举行的万人摆手舞启发,张汉卿先生(时任恩施市文化局副局长、州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利用恩施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创造出了清江舞(分为五个部分:摆手舞、喜花鼓、苗舞、肉莲响、撒叶儿嗬)。2002年建始县将根据“五个一工程”所编写的校本教材带入课堂,要求每周必须有两节民族文化课,使得清江舞真正地走入了中小学的课堂。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在2006年8月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健身操比赛并获奖,这是清江舞首次在全国性大赛中获奖。2006年,巴东县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在全县中小学开展普及推广清江舞活动的通知》,并组织各中小学的体育教师和舞蹈教师在县里举行培训,使得清江舞在校园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当时,教育局为落实“两课两操两活动(每周2节体育课,每天做好广播操及眼保健操,每周上好2节课外活动),要求学生会做团体操,会跳清江舞。同年,清江舞被正式列入体育中考内容。
2010年,巴东县野三关农民黄在秀代表湖北省参加文化部在苏州举办的“首届中国农民艺术节”,他领衔表演的《撒叶儿嗬》获得金奖。2013年,在第十三届CCTV“隆力奇杯”青歌赛中,黄在秀的弟子谭学聪获得原生态唱法金奖。同年,谭学聪获湖北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屈原文艺奖”人才奖。当前,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些旅游景点,也有关于“撒叶儿嗬”的舞台表演。如利川腾龙洞的大型舞台实景剧《夷水丽川》中的白虎雄风部分就包含了土家“撒叶儿嗬”。《夷水丽川》自2005年开演以来,已演出6000余场次,直接经济收入过亿元[13],并于2015年荣获第九届湖北“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该节目不仅为景区带来丰厚的收入,同时对土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年,湖北省民族歌舞团打造了民族歌舞旅游演艺剧目《武陵绝响·毕兹卡音画》,其中包括八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三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撒叶儿嗬”名列其中,于2015年4月在恩施州文化大剧院成功上演。
(二)文化空间的变迁
“文化空间”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它是指:“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举行场所,也可定义为其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由此可见,文化空间并非地理学范畴,而是兼具时间性、空间性和文化性的概念。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空间指的是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性地进行的地方。例如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集市等,都是典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
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在巴东野三关地区“撒叶儿嗬”表演已基本形成产业化。在过去,一旦有人过世,周边的亲朋好友都会前来“闹夜”,自发地跳。而到了现在,“只要死老人,就是请的班子,已经形成格局,都要给钱”*笔者在调研时,当地文化部门工作人员提供了相关材料。。如今,表演“班子”一接到订单,就迅速通知班子内部的骨干人员,前往孝家。表演“班子”在正式进入孝家的大门时,孝家要向班内成员包红包,分发毛巾、香烟。等吃完饭,客人基本到齐就开始表演。表演者根据之前与孝家的约定,有的是唱整晚,有的只有半夜,酬金也依此增减。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可依据自身情况中途休息。在表演“燕儿衔泥”的时候,地上的物品由之前的五巾变成由孝家放置的红包和烟。如今,这也成为检验孝家是否“大方”的一个标准。
按照传统,女性是不允许跳“撒叶儿嗬”的*针对为何不准女性参与跳“撒叶儿嗬”这一问题,民众普遍解释为不吉利,即所谓“女人跳丧,家破人亡”。笔者认为,形成这一文化传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普遍存在的对女性性别歧视观念的影响;其二,“撒叶儿嗬”作为一种丧葬仪式,祖先崇拜是其重要的信仰内涵,必然会形成偏好男性而排斥女性的文化偏见;其三,“撒叶儿嗬”作为一种丧葬仪式,尽管它体现出显著的“丧事喜办”的特质,但神圣性仍然是其核心的文化意蕴,而诸多民族志案例表明,女性在很多文化体系里面被贴上“污染”“不洁”“异常”“危险”等负面标签,所以也被选择性地排斥于“撒叶儿嗬”仪式之外。。在2006年以前,当地不少女性对跳“撒叶儿嗬”十分向往,但受到传统的约束,无法参与其中。2006年,巴东县举办首届民间文化艺术节,要求所有乡镇必须有自己的民间文化节目。当时,野三关镇政府和文化部门依据当地特色,选择了“撒叶儿嗬”作为自己的特色文化进行打造,文化部门迅速在当地征选男同志参加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文化站站长邓清国无意间得知相邻的清太坪镇也选择了表演“撒叶儿嗬”,且从县文工团请了专业人员前来指导。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邓清国站长迅速想办法,认为此次参加比赛是舞台表演性质,于是创造性地征选女性前来参加训练。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九男八女参加比赛,经过比拼,喜获一等奖。由此,开启了女性参与“撒叶儿嗬”表演的先河。之后,巴东县受邀参加在长阳举办的湖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文艺演出,野三关当时参加比赛的“撒叶儿嗬”表演队也随同前往,获得文艺演出第三名。如今,在丧葬仪式上,当地的绝大多数人也接受了女性参加,只有极少数的保守人士不接受这种情况,或者是要求女性只能在院坝、不能进入堂屋表演。
(三)传承模式的变迁
“撒叶儿嗬”成功申报为非遗之后,其传承方式也由过去的一元形态向多元形态转变。同时,“由于丧葬活动群众参与性强,致使‘撒叶儿嗬’仪式的传承方式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14]”过去单一的传承方式给“撒叶儿嗬”的发展带来一些局限。按照传统的传承方式,“撒叶儿嗬”的唱词与动作就只能由表演者口耳相传,学习者想要学习,征得师父的同意之后,只有在举行丧礼的时候,才会有短暂的学习机会。
如今,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撒叶儿嗬”表演被录制成视频,可供学习者随时学习;教育部门的引导,使得“撒叶儿嗬”在学生群体中迅速传播;申遗成功之后,政府部门也开始大力推广。2008年,在巴东县野三关镇举办了全县首届“撒叶儿嗬”免费培训班,共有47名人员报名参加。参加培训的学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18岁,其中有女学员5名。培训班由野三关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办,州民间艺术大师黄在秀和参加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巴东“撒叶儿嗬”伴舞演员黄本红负责讲课和示范表演。巴东县政府为此拨出专款,培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虽然没有明确的拜师仪式,但根据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培训班的老师就是学习的师父,形成了明确的师承关系。据当地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如今“撒叶儿嗬”在当地传承效果很好,产业化趋势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使得当地年轻人踊跃参加,已不再需要政府部门组织培训。
结语
“撒叶儿嗬”作为一种祭祀仪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内涵,是土家族和中华民族一项重要的文化财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撒叶儿嗬”的传承空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已关注到了这种状况,着手对其进行保护。随着“撒叶儿嗬”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逐渐由原来仅仅用作祭祀的一元形态向表演、健身的多元形态转变,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其发展空间。
“撒叶儿嗬”的当代变迁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产业化、舞台化为核心的转型有利于“撒叶儿嗬”走出去。人们将“撒叶儿嗬”中的一些独特元素抽离出来,进行加工和改编,促进了“撒叶儿嗬”的推广和传承,加深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了解,使得“撒叶儿嗬”成为土家族的一种标志性文化符号。另一方面,以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标志,市场化、产业化成为“撒叶儿嗬”发展的主导力量。原本在乡土社会特定文化空间生成与传承的“撒叶儿嗬”丧葬仪式,逐渐被移植进新的展演场所,比如庆典、景区、殡仪馆乃至中央电视台,使得“撒叶儿嗬”与其得以生发的社会文化土壤日渐区隔,形成了突出的如吉登斯所指出的“脱域”特征[15]。舞台化的“撒叶儿嗬”迎合了社会的某种需要,但这一进程也导致“撒叶儿嗬”逐渐远离本来面目,丧失其精髓。
[1]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98.
[2] (清)廖恩树修,萧佩声纂.巴东县志(下卷)[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582.
[3] 张祖道.随潘光旦师川鄂“土家”行日记[M]∥彭振坤.历史的记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256-257.
[4] 朱祥贵.土家族“撒尔嗬”源流内涵及功能探讨[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4):52-56.
[5] 张玉玲.鄂西土家族“撒叶儿嗬”舞台化问题探讨[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6):114-116.
[6] 谢雪峰,刘俊梅,李芳,付晓芬,艾蕾蕾.土家族“跳丧”文化传承与转型若干问题的探讨[J].体育科学,2011(07):17-22.
[7] 谭志国.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124-131.
[8] 周耘.荆楚遗风——跳丧[J].文艺研究,1990(04):121-134.
[9] 田万振.土家族生死观绝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社,1999:67.
[10]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96.
[11]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6.
[12] 蔡少卿.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J].江苏大学学报,2004(04):32-35.
[13] 湖北人民政府网.打造实景剧奇葩繁荣群众文化新闻发布会[EB/OL].2014年8月26日.
[14] 谭志满.从祭祀到生活——对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变迁的宗教人类学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76-79.
[15] 刘谦.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