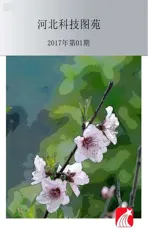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
2017-03-08潘艳蕊张晓霞
潘艳蕊 张晓霞
(河北大学图书馆 河北 保定 071002)
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
潘艳蕊 张晓霞
(河北大学图书馆 河北 保定 071002)
唐代是官修史书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官修史书主要包括官修前代“六史”及本朝国史两类。官修史书机构并无固定的属员配置,修史者多是临时措置而来的“兼职”官员。修史兼职人员多,工作耗时长、难度大是补偿性奖励官修史书编纂人员的重要原因。官修史书具体的奖励形式包括赐物、玺书褒美、封赐爵位、加散官、追赠、职秩变迁六大类。这些奖励具有前后期时代差异,既重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等特点。
唐代;官修史书;奖励
东汉以来的中国封建王朝大多重视前朝及本朝史的编纂工作。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繁盛阶段的唐朝,创立了宰相监修、官方修史的模式,由官方修纂了“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六史”;修撰的本朝国史至少有21部之多[1]342,五代、北宋时期仍有大量的唐朝国史存留[2]1092-1098,成为编修两《唐书》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唐代笔记与史传文学的重要来源[3],具有极高的文献资料价值。但唐代官修史书机构并无固定的属员配置,修史者多是临时措置而来的“兼职”官员,修史工作耗时长、难度大。在完成修史工作之后,朝廷对参修人员常常给予特定的奖励。唐代是如何奖励官修史书的参修人员的,这是未见学界专门探讨的唐代图书编纂问题。
1 唐代官方修史工作的机构与人员
唐代常设性的史书编纂机构是专修国史的史馆。史馆原隶于以收藏、整理图书为主要职能秘书省著作局,贞观3年(629)从著作局分离立于皇宫[4]281,后移置到门下省之北,并以宰相监察修史工作;开元年间(713-741)成为中书省所辖的修史机构,是事涉国家机密的修史单位[2]1285。史馆“专掌国史”,无常置属员, “以他官兼领;或卑品有才,亦以直馆焉。”史馆的主要职掌是根据起居舍人所作的皇帝起居注,载录天地日月等祥瑞现象,山川封域的划分,皇帝昭穆次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大政,“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4]281,所成之作就是“国史”即唐代某一帝王的实录及数个帝王期间的历史。
唐武德5年(622)始修前代封建王朝史。但当时并无专门的编修机构与监修制度,而是临时措集各部门史学之才分工修撰,主修人员涉及7个部门16人:中书省官员4人,门下省官员3人,秘书省官员5人,大理寺、太子府、吏部、秦王府各1人[2]1287。主修者多而无统一管理之制,武德年间修前代史无果而终。贞观3年(629)太宗重修前朝史,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强化了对修史工作的统一管理。秘书内省主要的修史人员多从三省六部职员中措集,与史馆修史人员一样具有兼职修史的特点。贞观20年修撰《晋书》所设“修史所”,人员也是临时措集,分功撰录的[2]1287-1288。
国史是据一个或数个皇帝期间的史事纂集而成,它同修前代史一样也不属于日常性的修纂任务,所以史馆无常置属员而以他官兼领,卑品有史才者也可以于史馆中处理日常工作。这种兼领性质的人员设置,一是能够节省朝廷官俸,二是足以应对修史之需。但以他官兼领史馆工作则是他官的“兼职”任务,对兼职工作给予必要的“补偿”是一个基本的劳务原则。较史馆的工作而言,编修前代史更是一个非经常性的工作,那些临时措集的修史的人员,同样具有“兼职”的特点,在修史工作完成之后对修前代史人员给予“补偿”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2 唐代官修史书的两类基本活动
唐代官修史书一是官修前代史。官修前代史的活动始于武德5年(622)唐高祖命大臣撰修“五代史”,以求“拯救”前代文籍史事,并达到“惩恶劝善”的政治目的。但其管理缺陷导致修史工作“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太宗贞观3年(629)重新启动编修工作,改变修史人员无法统一管理之弊,“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至贞观10年初步撰成了南朝梁、陈,北朝魏、周及隋“五代史”。贞观20年“五代史”再次进行改进性修撰,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最终成书[2]1287-1288。“五代史”前后修撰历时35年之久。贞观20年又修《晋书》,22年成书,历时不到3年。这是唐朝官修的“六代史”。
唐代官修史书之二是修国史。唐代共二次修撰数帝期间的“国史”,情况相对简单,但修撰各帝实录的情况较为复杂。唐前期(618-755)官修实录有三个特点:一是及时修撰先皇实录,如太宗修高祖实录、高宗修太宗实录、中宗修则天实录、玄宗修睿宗及中宗实录等;二是皇帝在位时期修自身的实录,如唐太宗修贞观14年前实录;三是续修、重修先皇、先后实录,如高宗朝两次续修贞观实录,开元4年(716)重修高祖、太宗实录,两次重修则天实录、睿宗实录[2]1289-1292。续修、重修高宗朝实录至少3次[5]1471。随着唐朝国力的变化,唐后期(756-906)实录修撰一则重修工作相对较少,仅见武宗会昌元年(841)重修宪宗实录一例,二则宣、懿、僖三朝实录终唐也未完成[2]1295-1296,修撰实录的工作已经大不如前。
官修前代史历年弥久,本朝国史也有重修之例,其工作难度之大,付出之多不难想见,对“兼职”人员给予“补偿”更是合情、合理之举。各种“奖励”是唐代对两类修史工作的一种“补偿”形式。但唐代所修前代史与本朝国史难度有别,参编人员的“出身”并不相同,唐代前后期的社会风尚、国家财力也存在较大的不同,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修史工作中的奖励对象、奖励形式、奖励特点有着不少的差异。
3 唐代官修史书工作的主要奖励对象
唐代官修史书人员的临时措集性特点,决定了官修史书奖励对象的混杂性。编纂“六史”所受奖励人员一是六史监修官、中书宰相、《周书》编修者房玄龄,共1人[6]2462;二是秘书省参修官员,如秘书监魏徵[2]2548、著作郎姚思廉[2]2550、秘书郎岑文本[6]2593共3人;三是非中书宰相、秘书省官员,如与魏徵同撰《隋书》的太子右庶子兼国子司业孔颖达[6]2536,《齐书》撰者、中书舍人李百药[6]2602,共2人;四是有史才的无官职人员,如以公事被免雅州刺史之职,裁定《晋书》“体制”的令狐德棻[6]2577,共1人。除房玄龄为宰相、魏徵为秘书监高官外,其他参编人员多是当时的鸿师硕儒,政治地位同样不低。
国史编修工作中的奖励对象一是监修官,如高宗朝监修高祖、太宗《实录》的房玄龄[6]2596;二是史馆修纂官,如武宗朝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6]2462;三是非史馆人员,如高宗朝(650-684)编修贞观13年(639)以后实录的国子祭酒令狐徳棻[6]598,宣宗朝(847-859)修成《文宗实录》的门下省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沨、右补阙卢告、膳部员外郎牛丛等[6]2599。这些非史官参修国史的人员,都是号称“当代名手”的史学人才,所编史书的质量较高。《旧唐书》前半部分全以国史、实录旧本写就,反映的就是史馆所修国史、实录的高质量性[1]342-345。但史馆修撰人员的地位较修前六史者为低。
上述人员皆为主笔或监修人员。但修史工作是个系统的工程,从唐代秘书省的职官设置情况看,除去这些人员之外还有正字(字体规范人员)、楷书(抄书人员)、校书(校对正误人员)、熟纸匠(管理纸张人员)、装璜匠(书籍装璜人员)、笔匠(制笔人员)以及其他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具体如何奖励、有无奖励的情况皆未见于文献记载,他们在修史工作完成之后即使有所奖励,也不是奖励的重要方面。
4 官修史书奖励的主要类型
根据《唐史》、《唐会要》两大基本文献的记载,唐代对官修史书参编人员的奖励大体包括如下几种形式:
4.1 赐物奖励
官修史书赐物奖励在唐代并不少见,但某些赐物记载相对模糊,如唐前期髙宗朝房玄龄以撰高祖、太宗《实录》赐物一千五百段[6]4570,孙处约以预修《太宗实录》赐物七百段[6]2462,中宗朝韦思谦以修《则天实录》赐物五百段[6]2756。
唐前期修前代史所赐之物皆为绢。如太宗朝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6]2865。姚思廉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赐彩绢五百段[6]2593。史馆馆臣修实录的赐物奖励包括赐帛、赐马两种。高宗朝敬播撰《太宗实录》二十卷,赐帛三百段[6]2599。睿宗朝岑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赐良马一疋[6]2540。
唐后期有具体记载的所赐之物包括锦及银器。如宪宗朝宰相裴垍进所撰《徳宗实录》五十卷,赐裴垍锦彩三百疋及银器等物[6]432。宣宗朝魏謩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沨、右补阙卢告、膳部员外郎牛丛皆颁赐锦彩银器[6]4570。文宗朝路随进所撰《宪宗实录》四十卷,赐史官等五人锦绣银器有差[6]536。
4.2 玺书制书褒美
这种奖励形式主要发生在唐代前期,且用于对修实录之臣的奖励。如房玄龄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高宗降玺书褒美;崔融以预修《则天实录》,中宗降玺书褒美;岑羲修《中宗实录》,睿宗下制书褒美[6]2462;崔融以预修《则天实录》,中宗降玺书褒美[6]3000;岑羲修《中宗实录》,睿宗下制书褒美[6]2540。这是对修实录之臣的奖励。
4.3 封赐爵位
对编修史书者封赐爵位,是给予修史者的荣誉。太宗朝岑文本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封江陵县子[6]2536,魏徵因监修“五代史”之功进封郑国公[6]2550。高宗朝许圉师以修前朝实录封平恩县男[6]3330,许敬宗以修武徳、贞观实录封髙阳县男[6]2761。顾胤以撰武徳、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封余杭县男[6]2600。中宗朝徐彦伯以预修则天实录封髙平县子[6]3006,韦思谦以修《则天实录》之功赐爵扶阳县子[6]2865。令狐徳棻撰《髙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6]2559。中宗朝刘知几《修则天实录》,封居巢县子[6]3171。
此外,亦有赐予修史人员后裔爵位的情况,如贞观年间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成,开元年间追封房玄龄一子为县男,许敬宗一子为高阳男;神龙年间监修国史中书令魏元忠、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国子司业崔融等修《则天实录》三十卷成,追封元忠一子为县男,徐彦伯等各赐爵二等[2]1291-1292。但这些奖励形式也仅发生在唐代开元(721-741)以前,开元之后并未有见。
4.4 加散官
散官是与官员本品等级相配的称号。对史书编修人员加散官,同样是给予编修者的荣誉奖励。为修史者加散官的事例主要包括:太宗朝孔颖达与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6]2602。魏徵兼修诸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6]2550。姚思廉撰成《梁书》、《陈书》,加通直散骑常侍[6]2593。顾胤撰成《太宗实录》,加朝散大夫[6]2600。这些都是唐代前期的案例,唐后期未见这种奖励形式的存在。
4.5 追赠官
编纂者死后被追赠加官,如宪宗年间太仆寺丞令狐丕进其亡父令狐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赠令狐峘工部尚书[6]432。这也是一种荣誉性的奖励措施。但这种奖励在唐代仅见此一例,唐后期对修史的管理工作并不及时。
4.6 除官、拜官、迁官、转官、加级
除官、拜官、转官、迁官、加级是给予史书编修者的职官变动奖励。对身处官场中的官员而言,这种职秩变迁奖励可能比其他形式的奖励更有实际价值。
除官。除官指被授予新官。唐前期一例:令狐德棻撰《晋书》,书成,除秘书少监[6]2596。
拜官。拜官指被授予官职,其义与“除官”相似。唐后期一例:蒋乂以修《徳宗实录》,拜右谏议大夫[6]4028。
迁官。迁官指升任高品秩之官。前后期各一例:敬播以撰《太宗》实录,迁太子司议郎[6]4594;宇文籍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6]4209。
转官。指出任同品官,一般是转任更加重要的部门。前后期皆有:吴兢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6]3182。韦处厚修《徳宗实录》五十卷,转左补阙[6]4183。陈夷行预修《宪宗实录》,转司封员外郎[6]4495。蒋系受诏撰《宪宗实录》,转尚书工部员外[6]4028。魏謩修成《文宗实录》,转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6]4570。
加级。唐代官员有九品十八级,加级是提升原品等级。仅见于唐前期,如房玄龄等人修《晋书》凡一百三十卷,“颁赐加级各有差”[6]2463。神龙二年修成《则天实录》,除封魏元忠子、徐彦伯爵外,“自余卑官加两阶”[2]1292。
上述职秩变迁以转官这一奖励形式为主,其他奖励形式应是这一奖励形式的补充,职秩变迁对多数史书编修人员的影响并不大。
5 唐代官修史书奖励的特点
从以上文献所载的官修史书的奖励内容、奖励形式看,唐代官修史书的奖励有如下几个特点:
5.1 唐代官修史书奖励形式具有多样性
从总体上看,唐代官修史书具体的奖励形式有10来种之多,涉及赐物、褒美、赐爵、加散官及职官变动等手段。其中既有赐物等物质奖励,又有褒美、赐爵、加散官等荣誉称号,还有切实影响仕途变迁的职官奖励。这种奖励对修史人员无疑具有较大的荣誉性与实效性。如下文所示,多样性的奖励又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多样性与综合性相结合,使唐代官修史书的奖励大体涵盖了能够给出的奖励手段的方方面面。对那些能够参与修史的文官而言,这些奖励是其获取官方荣誉、职事变迁的重要手段,具有切实激励修史人员积极修史的作用。这是唐代官修史书的首要特点之一。
5.2 唐代官修史书奖励种类有主次之分
仍就唐代官修史书的整体奖励来说,赐物以绢、帛、锦等丝织物品为主。唐代丝帛等物具有货币的作用,赐物奖励其实就是变相的以货币为主的奖励。封爵是相对次要的奖励形式,其他如散官、职事变动则是奖励中并不多见的个案,官修史书中的职事升迁奖励对正常的官员升迁途径的影响不大,它表达的更多的是对官员的一种荣宠之意。唐代官修史书奖励种类有主次之分,奖励具有以物质奖励为主,兼顾多样性、灵活性又不失原则的特点。
5.3 官修史书的奖励类型有前后期差异
从唐代前后期时期的分化来看,唐前期封赐爵位是仅次于赐物的奖励形式,唐后期修史人员的奖赏则以赐物形式为主,未见封赐爵位、加散官、诏书褒美等现象。唐代前期仕途管理相对规范,荣誉奖励难以惠及普通官员。但在后期藩镇割据的形势下,荣誉奖励较前期滥而常见,这是唐代前后期荣誉奖励变化的重要原因。在赐物奖励中,唐前期以帛绢类奖励为主,唐后期期以锦及银器类为主。锦较帛绢珍贵,银器更属高档奢侈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唐代前期帝王提倡节俭,后期渐尚奢华的世风流变。唐代官修史书的奖励具有突出的阶段性特点。
5.4 官修史书奖励具有综合性及等级性
前述奖励大多是综合授予的,如房玄龄等人修《晋书》一百三十卷,“颁赐加级各有差[6]2463。李百药撰《齐史》,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6]2577。房玄龄以撰高祖太宗《实录》,降玺书褒羙,赐物一千五百段[6]2462。岑羲监修中《宗实录》,睿宗赐物三百段,良马一疋,仍下制书褒美[6]2540。在同一修史工作中,所受奖励也是有区别的,如裴垍进所撰《徳宗实录》,赐裴垍锦彩三百疋及银器等,史官蒋武、韦处厚等则“颁赐有差”[6]432。路随进所撰《宪宗实录》,赐史官五人“锦绣银器有差”[6]536。根据官员品阶高低决定赏赐程度,这是唐代官修史书奖励的又一特点。
6 结语
唐代官方修史制度开了后世历朝官修史书的先河,其对编纂人员的奖励更为后世官修史书提供了先期性的历史经验。唐代官修史书重在给予编纂人员物质奖励,兼顾赐爵、褒美、加散官、追赠等荣誉形式。这些奖励虽然以重要的编修人员为重,各类人员的奖励具有等级差异的特点,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编纂业绩集体化的奖励原则。在不破坏整个官员任免制度的基础上,对部分编纂人员职官的迁转又使奖励活动具有较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唐代官修史书活动的机构设置、人员措集、奖励缘由、奖励对象、奖励特点,对当代图书编纂工作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1](清)趙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
[3]严杰.唐代笔记对国史的利用[J].文献,2004,(3):117-131.
[4](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5](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五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Rewards ofOfficial History Compilation in Tang Dynasty
Pan Yan-rui Zhang Xiao-xia
the Tang Dynasty is the period of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official history compilation, the six previous generation histories and its own histories are the two main kinds of official history compilation. Much of temporary concurrent posts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compilation staffs, long time of work, and a lot difficulty are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compensatory reward to official history compilation staff. Rewarding goods, praising by Yuxi book, awarding the title of nobility, rendering reputation official, posthumously awarded official, and promoting officer are the six specific reward forms. Pre and post time difference, both attention principle and with flexibility are the characters of the Rewards.
Tang Dynasty; Official History Compilation; Rewards;
G253
A
10.13897/j.cnki.hbkjty.2017.0019
潘艳蕊(1973-),女,汉语言文学学士,河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张晓霞(1980-),女,硕士,河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2016-12-01 责任编辑:张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