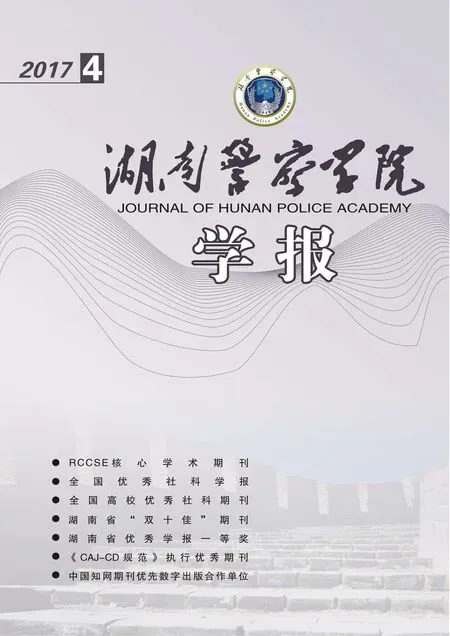习惯作为法源的条件与方法
——基于《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范分析
2017-03-08唐雅蓉
唐雅蓉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习惯作为法源的条件与方法
——基于《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范分析
唐雅蓉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民法总则》第十条将习惯正式纳为民法法源,这为习惯入法并以此指导民事司法判决开辟了法定性道路。对习惯的定义有事实属性和规范属性两类,民法总则第十条中的“习惯”应当是指具备规范属性的习惯规则。习惯规则成为法源应具备各项具体性约束条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习惯与制定法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应当超越二元对立的观念,以实现对等正义为目标在司法领域内适用习惯规则。
习惯规则;法源条件;二元对立;司法适用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表决通过。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规定便是将习惯正式作为民法法源。在我国基层司法实践中,民间习惯规则一直发挥着诸如补充制定法、解释制定法和认定案件事实等重要作用。此次习惯作为法源被法定化体现了我国当前社会自治的时代法治精神。本文从民法法源条款的立法演变出发,对比了新旧条款之不同及其立法背景。然后结合多种对习惯及习惯法的定义分析阐释《民法总则》第十条中“习惯”一词应有之含义。接着通过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习惯司法检验之标准总结归纳习惯规则成为法源应具备的条件。最后基于案例对习惯规则的适用进行规范性分析。
一、民法法源条款的立法演变
《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当法律出现漏洞没有对民事活动有所规定时,《民法通则》规定的是适用国家政策,而最新《民法总则》则是规定可以适用习惯。民事领域中,由于法律无法避免的滞后性缺陷,导致民事活动的许多方面都存在“法律漏洞”。国家政策是指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规束。《民法通则》通过于1986年,那时我国的法制体系尚不完善,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适用国家政策无可厚非,因为国家政策能有效弥补裁判依据的不足,也能使党引领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通过国家政策在司法中的运用渗透到社会中来。然而,虽然国家政策代表了理想的制度建设,但缺乏法律强制性和稳定性的特质,国家政策的优越性在于其在应对形势变化时具备较为迅速的反应和调整,但是其优点也导致了其程序性约束不及法律那样严格和专门化。因此,如果国家政策作为民法法源适用后又频繁变更,这不仅会影响判决的合法性,影响司法在民众心中的权威,也会使民众对正在进行的民事活动的合法性预测处在不确定当中,并且国家政策作为行动准则,规范民事活动的方方面面,这也有违民法作为私法和任意法的基本属性。
《民法总则》诞生于我国法制较为完善之时,法官已具备较好的法学素养,形成了较为正确的适用法律的思维,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权力意识也有了较大提高。将“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替换为“可以适用习惯”是法治社会的时代要求。习惯指的是在一定的地域或特定的人群范围内自发形成并为人们普遍认可和反复践行,具有一定社会强制力的行为准则。习惯的存在不可回避,在中国这个人际交往密切的社会中,民俗习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积累和文化沉淀,融合了民间的情理法,成为民众进行民事活动时最普遍遵循的行动指南,也是民众共同意志的体现,将民间习惯作为民法的另一法源,使其充分发挥对制定法的有益补充,对基层司法定纷止争和社会效果改善大有裨益。习惯规则是人们合意的外在体现,此处更改体现了对民法基本属性即私法和任意法的正确认识。即使法律的明文规定不足,也能依据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对民事纠纷进行定纷止争,这正是现代法治精神——社会自治的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近现代兴起的大规模法典编纂运动在一定程度削弱了习惯的法源地位,但其仍在法源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例如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第一条规定:法律无规定之事项,法院应依习惯法。许多商法上甚至明确规定习惯适用优先于法律。我国法律现代化基本遵循大陆法系国家的道路,此次《民法总则》将习惯明文规定为法源,赋予了它“合法”的身份,象征着我国在法律现代化道路上的前进。
二、对《民法总则》第十条“习惯”定义的理解
在赋予习惯以法律渊源地位后,我们需要要对习惯这一概念有清晰的认知,由于习惯与习惯法的界定不清,许多学者都对习惯和习惯法给出了定义,但却莫衷一是。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学者们定义这两个概念的大致进路。
对于“习惯”,学界存在两种定义,第一类以《辞海》中对习惯的释义为源泉,认为习惯即是社会事实:习惯是“由于重复或多次联系而巩固下来的并且变成需要的行为方式,如良好习惯、坏习惯。”[1]在日常语境中,习惯可以分为个人生活习惯和特定群体共同的习惯,从《辞海》的这个定义来看,我们无法识别习惯的主体是群体还是个人,而显然二者是有区别的,法律的普适性特征意味着法学意义上的习惯应当且只能指的是某一群体共同遵守的习惯规则。再者《辞海》界定习惯为“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属于社会事实,不具有规范性。因此,《辞海》实际上是将习惯定义为一种社会事实。以此定义为基础界定习惯的学者主张“习惯指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反复的运用而逐渐认可的一种行为模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经常进行的活动。”[2]以及“从法社会学、法文化学视角观之,所谓习惯,是指对一定范围内之社会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模式或心理模式的客观描述。”[3]两位学者都将习惯定义为行为模式,即某一群体社会成员反复行为的定式,是一种从事实视角对习惯的定义。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被当做社会事实予以认识的习惯更像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法官依据此推断还原案件事实,这类习惯的出场能够帮助法官迅速并尽可能正确地厘清案件事实,节约司法成本并避免产生不合理的判决。第二类则是认为习惯是一种被社会认同的群体成员行为准则,即社会规范。这类定义来源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一法学卷》,其中这样定义习惯:“习惯是社会生活中,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为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4]45将习惯定义为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以内心确信和社区舆论为约束力的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系统。李可认为习惯与习惯法并无区别,都是指民间社会自发生成、得到人们奉守的行为规范[5]。眭鸿明在研究民初习惯调查时将习惯界定为:“国家法律之外的、民间的行为规则的类名称或者总称,它包含风俗礼仪、民问习俗、交易惯例等。”[6]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习惯定义的落脚点都是规范或规则,因此,这类从规范视角对习惯作出的定义可以归纳为某一群体成员由于对某一行为作反复实践而形成的具有以内心确信和社区舆论为拘束力的行为规范。在具体个案中,除了制定法规,习惯规则也是法官用以判定行为合理与否的依据。例如在《乡土司法》中所举的一个相邻权纠纷案件中,法官在判决书中认定,按照当地习俗,民间私人厕所应当建在自己院内,所以被告把厕所建在院外的做法不合理,应予以拆除[7]。
对习惯法的定义,主要存在“国家认可说”与“社会公认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一法学卷》将习惯法定义为“国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是法的渊源之一。”[4]87是“国家认可说”的典型表述。国家主义认为,“国家认可说”是以国家权力介入与否来区分习惯与习惯法的,国家权力的介入有两种方式,即立法与司法。立法途径是通过立法规定在解决某类纠纷时从习惯,例如日本曾在其《涉外民事适用法》中规定:“不违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之习惯,经法令认可者及相关法令未规定之事项者,均具有与法律相同之效力”。[8]6在日本的语境中,这两者都具有习惯法的效力,无需当事人主张和证明,法官原则上就要引用。其中的经法令认可者(如:相邻关系从习惯)即是“国家认可说”的体现。另一种是在司法审判中对习惯规则进行识别适用,在特定案件中,习惯规则作为当事人共同行为的准则,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具备一般法的特征,通过法官识别使之作为案件判决的大前提予以适用,判决生效后,习惯规则便以判例之形式转换为习惯法,如此,习惯规则便迈进习惯法的领域。正如哈特所说:“在法院将习惯规则适用于特定案件之前,它们只是习惯,绝不是法律;当法院适用它们,并依它们下达了生效的命令时,这些规则才得到承认,才成为习惯法。”[9]国家立法的认可和国家司法对民间习惯的适用是习惯规则成为习惯法的路径,因此依据该定义,习惯法是习惯经由国家权力整合后的产物,习惯法是一种得到官方认证的法律规范。而习惯法的“社会规范说”定义很明显是一种法社会学的立场,一种多元主义法律观,认为法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活动并注重它的社会实际效果。高其才认为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外,依据各种社区舆论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0]梁治平也主张习惯法即“人们一旦有逾越的行为,就会受到来自族长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和来自本村社会共同体的谴责、蔑视和惩戒。”[11]两位学者都认为习惯法之约束力来源于社区舆论、宗族势力亦或共同体的谴责蔑视等等,其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国家法必定有国家权力的介入和保障,因此此习惯法的“法”并非国家法意义上的“法”。
由此,在习惯,习惯法的概念区分上,我们较为认同以下观点:经由立法认可和司法适用后的习惯规则称之为习惯法,即习惯法的“国家认可说”,是习惯规则中被国家认可的一部分习惯;“社会公认说”之习惯法与“社会规范”之习惯一道称为习惯,是具备规范含义的习惯;而被定义为“社会事实”的习惯,是具备事实属性的习惯,可以称之为惯行。《民法总则》第十条中的习惯作为制定法的补充法源存在,它必然也要具备制定法的功能和作用。法律的作用可以分为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法的规范作用是指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进一步细分为五种作用: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而只有具备规范含义的习惯规则才有调整规范人们行为这一效用。因此,我们认为第十条中的“习惯”应当指的是具备规范含义的习惯。同时,从习惯和习惯法的内含外延相比较,第十条使用习惯一词较之习惯法更为妥当。习惯法源于习惯,习惯之内含的外延范围显然包含且广于习惯法之内含的外延。习惯法只是习惯中被国家识别出来并被确定认可的一小部分,并且一旦经确认就成为现行法的一部分。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非常强,民间习惯也是瀚如烟海,其中仍有许多未被采撷却具备法的特质且有利于解决民间纠纷的习惯规则,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有了习惯的广泛内含,才能给基层法官更多适用习惯的空间和选择并以此更好地定纷止争。
三、习惯规则成为法源需具备的条件
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如前文所述,习惯具有社会事实和社会规范的双重定义,以事实为定义的习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被认识而缺乏规范行为的能力,只有当习惯具备规范定义时才有作为法源的可能性,因而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习惯作为法源运用到司法中应具备的条件。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明晰习惯成为法源需具备的具体条件,即习惯的司法检验标准。对习惯的司法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这方面已有的一些法律规定中得到一些启发。例如英格兰对习惯的司法检验合格与否取决于习惯是否符合既定的五个条件:1.久远性,1275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规定,只有从1189年即已存在的习惯才能在法庭上引用;2.合理性,即习惯需具备合法理由,如若与普通法冲突则不能得到认可;3.确定性,一项习惯必须在总体性质、作用群体及作用地区三方面同时清晰和确定;4.强制力,强制力是法律规则的基本特征,该习惯必须具有强制力才能被引用;5.未间断,该习惯必须自1189年以来从未间断过[12]。英格兰这五项对习惯的司法检验标准可谓是非常严苛,法官必须在有证据证明某一习惯完全符合上述标准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它。可见英格兰对习惯司法适用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事实上能通过检验的习惯规则也是凤毛菱角,如若将该标准放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权的变更和法律体系的翻新,能被适用的习惯几乎不存在。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定义习惯为“多年惯行,地方之人均认其有拘束行为之效力”。其多年惯行的表述即表示该习惯的长久持续,是该习惯得以引用时间要件。地方之人均认即表明该习惯必须被某一确定地区的大众集体认可,要达到共识的地步。拘束行为之效力即表明该习惯是有约束力的,若有人违反就会受到社区舆论的谴责,这种约束力也是社区共识的外在表现。尽管上述地区对习惯司法检验的标准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但它们仍反映出习惯能作为法源应具备的基本特质。
(一)主体认同性
习惯的主体认同性是指在一定地域内的公众普遍确信规制他们行为的习惯股则。事实上公众对这种“法”的确信就是对公平、正当的确信。该习惯作为社区成员的基本共识即所有人都应该受其约束的信念,一旦有成员违背该习惯就会受到社区集体的舆论谴责。社会主体的认同是习惯正当性的来源。无论是英格兰还是台湾对习惯司法检验的标准都有时间长久持续的要求,这也是侧面强调了作为法源的习惯应具备主体认同性,因为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习惯的存在则不可能持续长久。
(二)确定公开性
秩序是社会健康运行发展的基础,也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要想维系秩序价值,习惯就必须具备规范确定性和社会公开性,因为只有习惯规范指明了确定的行为模式,只有该习惯为广大社会成员所知晓,人们才能以此作为自身行为的指南,才能预测并合理安排自己的行为,如此社会才能拥有秩序。同时,习惯还应当具有能被抽象出具体权利义务范式的内含,这是由习惯进入司法的实用主义目的决定的,如果一个习惯规则权利义务配置模糊不清,无法作为裁判依据解决纠纷,则它也就失去了进入司法领域的意义。
(三)普遍约束性
对习惯的普遍约束性要求来源于法律的普适性和强制力。法律的制定适用都是为调整不特定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而非单个特定群体的纠纷而存在,因此能司法适用的习惯规则应当要是不特定的社会成员中内化的共同信念。约束性则是指习惯应具备自身的“强制力”,即社区成员都对该习惯规则一致遵守,当然,习惯的这种强制力无法比肩法律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制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作用的实际效果,这种强制力更多来源于社区舆论,在中国的语境下,还有中国人特有的人情、面子等机制制约。
(四)合理正义性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法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良法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主张法治的根本和内在基础就是良法。良法是指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本身必须具有正义性。“恶法非法”早已成为大众共识,公序良俗原则也是我国民法明文确定的法律原则,因此符合合理、正义应是习惯规则成为法官裁判依据的前提。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合理性乃是某一惯例的有效要件之一,所以法院不能确立一种不合理的或荒谬的习惯去影响当事人的法律权利。”[13]
(五)不得与制定法强制规范冲突
《民法总则》第十条给了习惯在民法领域正式法源的地位,该条文明确表示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可以适用习惯。而民法规范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民法以私法自治作为最高原则,在其任意规范范围内,当事人的契约规范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和不危害国家公共与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优于任意规范,而当事人的契约通常来源于习惯规则,因此,具体而言,习惯规则得以适用而不能与之冲突的应当是制定法的强制性规定,而非一言以蔽之的法律,这是具体优于抽象的适用。因此,习惯不与制定法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是其司法适用的基础条件。
四、对习惯规则适用的规范分析
民事制定法存在漏洞或是与习惯相遇于同一案件并存在结果矛盾时,“不得拒绝裁判”使得法官陷入困境。存在立法空白尚可以通过吸收习惯规则作为裁判依据,但当制定法与习惯产生矛盾,法官便会陷入两难,一方面,基层法官是国家法治的践行者,其裁判应当谨遵制定法的规定,而另一方面,习惯规则作为裁判依据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此时,就应当回归到民法的社会功能即预防和解决私人间利益冲突去考量,民法是以实现对等正义为其终极目标,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应当以追求对等正义最大化为己任[8]10,无论是制定法还是习惯都应效力于追求对等正义。但是,法官对习惯规则的适用仍应当止步于宪法的基本分权原则,即使是在民事领域,民事规范原则上仍应由具备民意基础的立法者决定。[8]11因此在此前提之下分析对习惯规则的适用。
(一)超越二元对立的意识理念之习惯与制定法的矛盾与融合
【案例】山东“顶盆继承案”[14]
青岛市李沧区石家村村民石君昌拥有平房一套,在其妻子儿子相继病死后,石君昌也患病身亡,该房屋被村民认为是“凶宅”。该村仍有“顶盆发丧”的习俗,一般由长子为死者发丧,如为绝户,则可以顶盆者为嗣子,由顶盆者为其发丧并继承其遗产。石君昌为绝户,只有一兄石坊昌,村民证实,当时石坊昌因嫌弃该房屋为凶宅,拒绝为石君昌发丧。石君昌有一远房侄子石忠雪见其叔叔无人发丧,自愿为其顶盆并继承石君昌的住宅,获得该房房产证和土地证。八年之后,因城区扩建该村拆迁,石君昌留下的住宅因在拆迁范围,石忠雪可以获得新居一套,但此时,石坊昌向法院起诉主张该房产的所有权。石坊昌诉称其是该房产的法定继承人,拥有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石忠雪系非法侵占。(石坊昌主张其所有权的另一依据是赠与合同,因该合同与习惯与制定法冲突的论述并无关联,因此省略)石忠雪辩称,其以按照民间风俗为死者顶盆,已过继为石君昌的嗣子,获得该房的继承权。法院经审理认为,石忠雪因农村习俗,为死者石君昌顶盆发丧因而继承其房产,并非非法侵占,因此对石坊昌的诉求不予支持。石坊昌不服判决后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遗产的继承顺序:“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继承法中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通过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先从制定法的视角分析本案,石君昌死亡后,因其生前没有订立遗嘱,其遗产应当依照法定继承的顺序被继承。石君昌的妻儿先于他死亡,依照继承法对“子女”含义的规定,石忠雪是石君昌的远房侄子,并不符合石君昌子女的身份,因此石君昌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因此其兄石坊昌作为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依据继承法的规定享有该房产的继承权。但是依照民间习惯,因石忠雪在石君昌死后为其“顶盆发丧”,石忠雪就成为石君昌过继的“嗣子”,享有石君昌遗产的继承权,该房产应当归石忠雪所有。至此,案件中继承权的归属能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实际上是因为案件中掺杂了两套规范系统,即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本案所涉的民间习惯——“顶盆过继”,来源于中国传统宗祧继承里的立嗣制度。所谓立嗣,指的是当不存在符合条件的亲生子孙时,当事人另择继承人以延续自家香火。立嗣实际上是防止户绝的一种补救办法。在传统中国社会,一旦立嗣关系成立,嗣子就与被继承人的亲生子孙无异,取得相应的继承权及财产权,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义务。由于中国社会受儒家礼教影响至深,非常重视家族的后代延续,这一习俗依旧沿习至今。然而国家法作为精英理性的建构,认为宗祧继承作为一种落后的、迷信的封建宗法制度,以宗法伦理外衣来掩饰其争夺财产的野心应当予以剔除,因而我国制定法并未保护“嗣子”的财产权益。但是事实上,宗祧制度体现的并非全是封建落后的思想,其中不乏美好的传统美德,而国家法对宗祧制度的彻底否决,导致的也并非全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具体到本案中,石忠雪在石坊昌对石君昌死后置之不理导致石君昌面临无人料理丧事的窘迫困境下毅然决定顶盆过继为石君昌的嗣子为其料理后事,当时石君昌的房产不过是农村的一间平房还被认为是“凶宅”,并不值钱,可见石忠雪并没有争夺财产意图,他只是因为善良不忍心看着石君昌死后无人为其发丧才决定过继为他的嗣子,这是中华美德的体现。而反观石坊昌,在其弟石君昌去世时不管不问,任由其“户绝”,还因嫌弃石君昌的房产为“凶宅”不愿为其发丧,当房屋面临拆迁,房屋价值倍增时,石坊昌就主张依据继承法享有其弟房产的继承权,真是惟利所在,真小人也。如果依照继承法肯定他的继承权,则很显然与社会之公平正义观相去甚远。其实,本案中习惯所体现的正义观与民法中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是相符的,石忠雪获得石君昌遗产的权利是基于其履行了为石君昌发丧祭祀的义务。而石坊昌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却想拥有石君昌留下的财产权利,显然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这从村民们对石忠雪的正面评价和对石坊昌的负面评价中也可窥得一二。本案法官结合具体案情,充分吸收了民法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和民间“顶盆继承”习惯规则,肯定石忠雪的财产权益,是一种对制定法和习惯规则的融合适用。
我们应当看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流动的增加,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一个仅靠地方性共识就可维系秩序的熟人社会,由于乡土社会“信息对称”程度即农民之间互相熟识度的降低与“地方性共识”约束力的弱化甚至丧失,导致“乡土逻辑”变成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都无法解释的社会形态,它突破了“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在现代社会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形下,村民之间的传统社会关系却在逐渐解体[15]。在这种社会转型期,许多纠纷都不是纯粹的法律或是习惯纠纷,制定法与民间习惯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在乡土社会广泛存在。如同本案中,当事人不仅有立嗣制度的传统认识也有现代继承法的认识。若将“法律—习惯”、“现代—传统”对立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会使法官在面对“经验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的冲突中变的手足无措。一方面,尽管依据民间习惯已经符合“经验合法性”,但是由于害怕依据民俗习惯判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法官在制定法上找不到直接的条文规则就不敢轻易作出判决;而另一方面,如果依照“规范合法性”严格适用制定法,有时会产生明显的社会不公,不仅判决结果难以有效执行,还可能引起民众和舆论的哗然和围攻,从近年来法官被攻击、威胁事件频发便可见一斑。中国目前所处转型社会中基层法官的现实处境,显然不能同西方法治社会理想状态中的基层法官之处境比肩,依照苏力教授的观点,允许习惯规则进入司法,对基层法官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能让他们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和制度环境中生活得更好和更安全一点。因此,《民法总则》赋予习惯规则法源地位不仅有利于基层法官获得更好更安全的司法职业生涯,更重要的是当基层法官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对习惯规则的适用更有底气时,对等正义的实现将更有保障,这才真正有利于基层司法的发展。
(二)习惯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在以民法实现对等正义的最高追求之下,习惯规则与制定法适用有迹可循。首先,如果国家制定法的法理与传统习惯的情理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两者是高度契合且处理结果近似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习惯有所取舍地柔和到国家制定法的判决中去。其次,在国家制定法没有规定之时,即按照我国的民法总则之规定,将可适用习惯引入民事领域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中,从而将民事纠纷予以成功结案化解社会矛盾并保障了我国司法运行的高效稳定。“任何纠纷的解决,都不能以服从严格的规则主义为主的,而是以解决纠纷、解决问题为主...在一个具体纠纷的处理中,在法律规定的弹性空间内,需要我们合理和灵活地考虑和运用民俗习惯的资源和做法。”[16]将习惯引入民事司法领域可以很有效地将纠纷解决,这样在当今民事纠纷纷繁复杂的局面,习惯适用的入法实际上也使国家立法机构认识到适用习惯旺盛的生命力和张力,从而在张力充足的空间内将民事纠纷最终成功化解,这样也维护了我国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最后,在相关的习惯规则不符合前文所述可司法适用的习惯且与制定法的强制规范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我们就应当严格依照国家制定法的内容来对其进行解决,通过一个个的判决将法治思维和法律规定内化为当地或该民族的内心,从而直接培养和促使民众心中的法治思维的构建。这样国家制定法就必须以强硬的姿态进行介入,尽管纠纷解决不可能让当事双方都满意,但这就是法治的通行,社会民众之后就会形成依照“法治”规则进行民事活动而非去寻求“人治”路径来解决纠纷,这样国家制定法的权威性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在民间都得到渗透贯彻。
基层司法还要善于运用调解制度化解民间纠纷,由于我国“无讼”和“和为贵”的传统思想依旧在民间社会占据重要地位,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基层司法也是偏爱调解制度。由于调解内容以当事人意思优先,制定法的约束力较弱,习惯规则作为当事人的行为依据在调解中展现了其优越性。范愉教授认为,调解适宜调动当事人的参与和认同,避免僵化适用法律规则、软化程序的对抗性,求的情理法的融通和良好的解纷效果。甚至更认为,民间社会规范最适当的作用方式主要是调解[17]。在许多民间纠纷中,当事人行为依据的多是社会习惯,当矛盾无法调和诉诸法院时,他们心中的裁判标准依然是他们所熟识的习惯规则。因此,基层法官依据习惯规则主持调解往往能达到较好的解纷结果。
结语
民法是私法的基本法,被誉为法制健全完善的标示。《民法总则》将习惯法源地位的法定化保持了民法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开放性,使民法可以从社会优良的习惯中汲取养分补充完善民法规则,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将民法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对现有诸多定义的辨析,我们认为对第十条中“习惯”一词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其规范含义上,它只有具备约束、指引公众行为的作用才能作为补充制定法的法源。其次,本文仅从英国和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中归纳出习惯司法检验的若干一般条件,但是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客观存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检验标准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最后,基层司法应当基于我国半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突破制定法与习惯的二元对立,使二者都服务于对等正义的实现,这样才能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108.
[2]田成有.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22.
[3]周赟.论习惯与习惯法[A].民间法[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84.
[4]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5]周铁涛.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J].湖湘论坛,2016(3):125.
[6]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
[7]高其才.乡土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37.
[8]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0]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3.
[11]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固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66.
[12]何勤华.外国法制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02.
[1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495.
[14]王彬.民间法如何走进司法判决——兼论“顶盆继承案”中的法律方法[A].民间法(第七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51-52.
[1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10.
[16]田成有.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和运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23-27.
[17]孟军.司法改革背景下中国司法责任制度转向——法官司法责任追究的正当化[J].湖湘论坛,2016(1):76.
The Conditions and Methods of Customary as the Source of law
TANG Ya-rong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
Article 10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defines the custom as a source of civil law, which opens up a legal path for the customary becoming guidance of civil judicial judgment.The definition of custom has two kinds of fact attribute and normative attribute. The “custom” in article 10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should refer to the customary rules with normative attributes.Customary rules become legal sources should have the specific constraints.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stomary and the law should go beyond the concept of binary opposition,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ciprocity justice in the field of justice.
customary rules;source of law conditions;binary opposition;judicial application
D902
A
2095-1140(2017)04-0014-08
2017-05-18
唐雅蓉(1993- )女,湖南郴州人,南开大学法学院 2015 级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天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