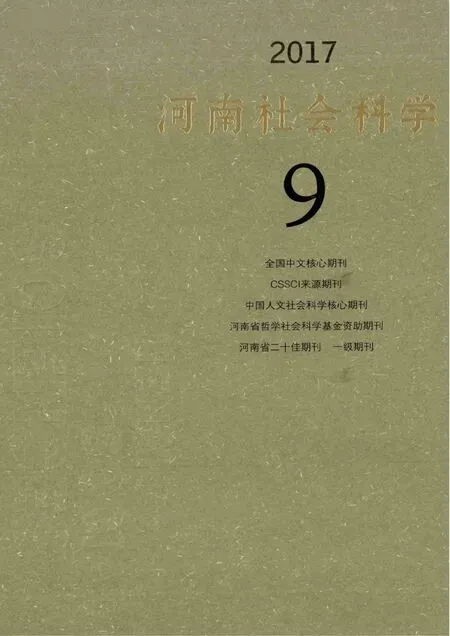伦理视域下的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研究
2017-03-07杨澜
杨 澜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02)
伦理视域下的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研究
杨 澜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02)
伊恩·麦克尤恩通常以日常生活中的创伤事件为切入点,以独特的方式刻画不同背景的人物在遭遇创伤事件后的心理历程,并挖掘其深藏的情感契机与伦理困境。以麦克尤恩的代表性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创伤与伦理的理论为研究基础,分析麦克尤恩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特征,探索创伤事件、创伤性人格在麦克尤恩作品叙事主题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背后的伦理缘由。
伊恩·麦克尤恩;创伤;叙事;伦理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的重要作家,他擅长以日常生活中的创伤事件为切入点,以独特的方式刻画人物在遭遇创伤事件后的心理历程——他们的悲痛、反抗、无奈及自我拯救。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看似其乐融融,但背叛、分离、死亡及各种形式的缺失都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从《水泥花园》的乱伦到《只爱陌生人》中被虐待的极端事件,到《时间中的孩子》中的意外丧女、《追日》中科学家一一失去妻子情人与名誉。麦克尤恩将创伤经历与家庭伦理结合得天衣无缝,将人性的脆弱、无奈与不堪展现得淋漓尽致。综观麦克尤恩的作品,从伦敦郊区到德国柏林,从被水泥覆盖的花园到冰天雪地的北极,从童年、少年直至成年后,创伤以及它的受害者以各种年龄、职业在不同的场景中一一呈现。然而,将创伤呈现甚至放大绝不是麦克尤恩写作的唯一意图。相反,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麦克尤恩笔下的创伤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作为善良、正义与救赎的前提与铺垫,这份独具匠心的伦理思考正随着他作品的成熟也越发明显。
一、伊恩作品的创伤叙事特点综述
创伤事件与创伤性人格在麦克尤恩作品的叙事主题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形成了一幅复杂的现代伦理图景。乔恩·艾伦在1995年指出,创伤性经历有两个构成要素:一是客观性的,二是主观性的。“正是对客观事件的主观体验,构成了创伤。”[1]116以破坏性的方式发生的客观经历引领当事人对事件真相进行探索,并衍生出一系列审视自我、接纳自我与建构自我的尝试。为了理解创伤事件的意义与原因,创伤经历的受害人必须通过回忆、做梦、书写及叙述等方式将创伤经历转化为某种语言形式。在麦克尤恩的作品中,诸多遭受创伤经历的人物正是通过书信、日记、梦境、书写及叙述等形式进行创伤的宣泄;这些内聚焦允许读者进入人物内心的创伤世界,聆听他们内心的声音并追溯其创伤的根源。
麦克尤恩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既有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如《蝴蝶》中因外表畸形而备受歧视的男人,以及《水泥花园》中相依为命的四个孤儿;也有表面上看起来生活安逸的成功人士,如《阿姆斯特丹》中的音乐家、《追日》中的科学家、《甜牙》中的当红作家等。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普通人,像《只爱陌生人》中的情侣、《时间中的孩子》里的父亲,以及《赎罪》中的若干主角。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却又企图相互制约,一次次地将自己封闭在人性的炼狱中。在这座人性炼狱里,温情处处缺失,扭曲的伦理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实;人物之间充斥着支配、误导、欺骗,而创伤性事件的介入则将他们的生活进一步抛于强烈的窒息感之中。
关于创伤的特点,美国当代学者如凯如斯、李斯等人提出了创伤具有“潜伏”“重复”“延迟”等特征。师彦灵教授则将创伤经历的主要方面区分为“再现、记忆及复原”[2]。通常情况下,创伤性事件虽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压抑,但仍会以更强烈的形式回归。创伤性事件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分裂性,让当事人仿佛身处时间、空间的裂缝中,在事件过后仍有被定格在事件发生的彼时情景这样的错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独立于外界空间的“小世界”,一遍遍地反复回忆、品味、思考当时事件发生的每一个细节、结局与意义。对于被突发的灾难性事件挫伤的人物而言,这个由自我选择的细节组成的、自己阐释其意义的小世界是另一个现实世界,一个与真实的现实情况并列存在的真相。关于创伤经历的真相被疑惑、痛苦与曲解笼罩,误导受害者进入一条幽暗的隧道;在抵达光明之前,两个世界中并存的真相相互抵触、相互否定却又相互指涉。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物都无法理解创伤性经历的原因和蕴含,只得深深将其植入无意识之中。事实上,受害人只有把创伤性经历从无意识转入意识,理解其成因和蕴含,才有治愈的希望[3]。
二、《水泥花园》中“拜物式叙事”背后的伦理寄托
《水泥花园》是麦克尤恩早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看似诡秘、实则被创伤摧毁的成长故事。杰克以第一人称讲述了父母先后去世,自己与家中其他三个孩子将母亲的尸体藏于家中,背负着沉重的秘密继续生活的故事。在这座与世隔绝的伊甸园中,被迫面对死亡的孩子们如同失去上帝庇护的亚当与夏娃;他们用谎言编织了一篇可怖的黑色童话,用肉体对抗着被揭穿、被抛弃、被惩罚的命运。正如杰克亲口承认的那样,自己与父亲的死脱离不了干系;而尽管杰克对父亲的种种行径感到反感,父亲对母亲的粗暴行为竟然被杰克自己复制(对象变为其他孩子)。如果说不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母间的裂痕使敏感的杰克最早体味到创伤的伤痛,那么通过复制父亲的行为,杰克在幻想自己取代父亲成为一家之主的同时也再次选择重复体验了创伤——只不过这一次杰克是主角而非旁观者。
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自己过往的经历是人的本能,是人们试图了解真相、梳理问题、排除疑问的行为。然而,在叙述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当事人则有意无意地对过往的经历进行了筛选、修正与粉饰。这样的叙述是不完全可靠的,是当事人对创伤性事件的主观加工与创造。以杰克为例,杰克口中的自己与其他家庭成员如朱莉、苏口中的形象明显不符;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杰克的叙述是不可靠的。考虑到发生的一系列创伤性事件对正处在青春期的杰克的影响,其叙述的不可靠性无疑说明了创伤性事件的巨大影响及杰克掩饰真实感受的初衷。这种有意为之的认知谬误实则出于对创伤性事件的有意规避,所以希望用遗忘与再创造来代替早已深深根植于记忆中的创伤性经历。从无意识地回避创伤回忆,到有意地通过叙述构建新的创伤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拜物式叙事”(fetishistic narrative)。例如,母亲死后,几个孩子还一度整理房间、准备饭菜、扔掉垃圾。成为孤儿的孩子们显然不习惯这样新的、可怕的事实,故而试图用一种旧的模式来掩盖残酷的现实。
在杰克关于自己的叙述中,他回避了自身的若干缺点,他在美化自身的同时也尝试美化创伤的回忆,即重构创伤历史——虚构出一段经历和另一个自我形象,用以替代不堪回首的经历和不甚完美的自己。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规避与创伤经历相关的一切真相,故而用模拟的事实进行自我欺骗,避免真实场景再现时对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创伤记忆与正常记忆从本质上讲无法融合,受害者在试图还原创伤经历时常以异于自我的身份出现,“以脱离逻辑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2]。例如,在他人的追问下,最小的汤姆谎称散发出腐臭的是一只狗。这一辱没母亲的言辞非但没有招致其他孩子的不满,反而令他们捧腹不已。这一不合逻辑的讲述方式正是从上一次的创伤经历中幸存下来的几个孩子需要的;而这也为真实的创伤记忆的还原提供了必需的前提。对15岁的杰克及家中的其他3个孩子而言,他们经历的并非普通的成长阵痛,而是由双亲死亡这样的创伤事件造成的巨大的认知障碍——对自己、对他人、对生存与死亡的根本性质疑。在这种类似哈姆雷特式的痛苦中,孩子们尤其是杰克,并没有像莎翁笔下的丹麦王子那样奔赴死亡,而是以“拜物式叙事”的方式不断回顾创伤,以求穿越创伤,到达成长的彼岸。
三、《阿姆斯特丹》中的集体创伤与道德沦丧
《阿姆斯特丹》是一部充斥着黑色幽默的作品,描写了一座现代“疯人院”及其中的集体创伤——这里的个体全都被剥夺了选择权,被抹杀了个性。在这座群魔乱舞的监狱中,个体的迷失与集体的道德沦丧互为帮凶,个体的空虚感被来自外界空间的威胁放大,交织成为对死亡的无限恐惧和对彼此的深恶痛绝。借用其主人公克里夫的语言,每一个人“小小的脑袋底下是眯缝起来的小眼睛,发育不良的累赘胳膊,屎眼都翘得老高,还黑糊糊的——像这样的生物是永远都不会在乎彼此的”[4]193。克里夫本人虽然没有遭受具体的、无法忍受的创伤,却不得不承受着灵魂与肉体撕裂,既自我厌弃又自恋不已的痛苦。其分裂的内心极具代表性,代表了肉体尚存、灵魂已死的现代集体创伤。现代人在对物质的盲目追求中失去了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感,被功利心蒙蔽的灵魂既不能救赎无谓的躯体,又不能督促个体无畏地赴死。在幸福感与价值感缺失的当下,音乐家克里夫幻想自己“像是个英雄般让人敬爱”[4]171,却不得不依赖酒精的麻醉来逃离“一种病态的麻木,一种虚空,一次死亡”[4]171;其好友弗农被权力的虚无感折磨,却又希望凭借权力摆脱“活死人”般的状态。他们都是现代文明的牺牲品,是个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剥离后行尸走肉般的“空心人”,游走在生之空虚与死之恐惧之间,无所依附。同时,浪漫的自然被工业废物与城市噪声取代,让城市人不得不被封闭在独立的空间内,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却丧失了与自然、与他人建立对话的能力。因此,现代城市人在获得所谓“自由”的同时,将自身变成了被消费主义与实用主义操纵的欲望机器。
小说中的伦敦俨然一座福柯笔下的“疯人院”,伦理的谬误变成了真理。人们在相互利用、相互欺骗的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彼此提防;无论朋友、夫妻、情人还是同事,彼此之间全然没了怜悯、慈悲与感恩,取而代之的是麻木不仁、锱铢必较与妄自尊大。小说中的主人公都以伪善为伴,将人性中的丑陋与邪恶当作求生的必备技能;而这种掩饰在死亡的逼迫下显得微不足道,将本性中的麻木、自私自大还原到最丑陋的本相,压抑许久的人性之恶一并迸发。这一群自以为强者、胜利者的人,兴高采烈地奔走在生活的旋涡中,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欲望的碎片。在伦理与邪恶的夹缝中,死亡的恐惧将他们牢牢束缚住,形成典型的现代集体创伤——精神萎缩、主体分裂。这样的创伤背后是整个社会都应当被追究责任的伦理缺失——工业文明过多地强调理性、强调个体的消费能力,这种新的行为准则却是以消耗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条件的。结果是背叛与欺骗当道、虚荣与自私横行,人们心中向往的美好与风行的伦理道德不知被抛到了哪里。究竟孰是孰非、孰轻孰重,这是每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应当扪心自问的伦理问题。
四、《蝴蝶》中的“代际间幽灵”创伤与家庭伦理的缺失
黄丽娟提道:“家族隐秘的创伤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造成作为创伤的间接而非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5]这就是所谓的代际间幽灵(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在麦克尤恩的作品中,代际间创伤多半与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有关,多见于幼年时成长环境中不甚和谐的父母并在其成年后以某种扭曲的形式寻求释放。比如,《赎罪》中父母关系疏远直接导致布里奥妮敏感内向的性格,为即将发生的悲剧埋下伏笔。在《追日》中,主人公别尔德经历了严重的童年创伤,目睹了父母的隔阂,成年后则完全丧失爱的能力。在传统伦理中,“家庭”在未成年人通往成人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代表着秩序与规范。然而,家庭的扭曲失衡与父母的缺席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自我身份的确立[6]。在麦克尤恩的诸多作品中,《蝴蝶》出色地呈现了家庭内部代际间幽灵造成的精神创伤。
《蝴蝶》讲述了一个成年男性杀害未成年女孩儿的故事。“我”因为长相丑陋而被边缘化,与家庭没有联系、与他人没有沟通,生活在孤独、冷漠的世界里。这个习惯了他人的冷眼与嘲讽的“局外人”,由于长期缺乏家庭与温情的滋养,好似存在于异层空间的外来者,对他人充满戒备、内心冷漠异常。因为“我”没有下巴,异性从不愿亲近“我”,连“母亲也一样”[7]88。与“我”成年后离群索居的状态相似的是,母亲“从未有过朋友,无论去哪儿都是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母亲,“我”无法感受到亲近,甚至连母子之间的正常亲情都感受不到。在“我”看来,母亲“活像一条小灵犬”。连母亲的死都没能给“我”带来伤感,反而让“我”联想到之前见到的死狗。在“我”看来,生与死似乎处于平行的生存空间,毫无差别。这与“我”一直与孤独、冷漠为伴,从未感受到从家庭、他人或群体传递的善意与温暖直接相关。这一切都说明创伤在“我”的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恰恰是童年家庭内部的伦理缺失,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冷淡与疏远。
很明显,小时候的“我”渴望母爱但没有获得,心理上的失落造成了隐形的创伤,扭曲了“我”的伦理准则。成年后的“我”从未对别人讲述过曾有过的隐秘创伤,但在与小女孩儿的接触到杀掉小女孩儿的过程中,“我”显然试图找回寻常伦理中的亲密关系,只可惜最终以失败告终。杀掉小女孩儿后,“我”并没有夸耀自己的杀戮行为,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向一个不存在的听众讲述曾经发生的事件。通过讲述,“我”把自己过往的创伤性经历置换为小女孩儿的死亡事件;在“我”的意志中,杀死小女孩儿等同于释放对自己母亲的极端厌恶与仇恨。当正常的伦理被“我”摒弃后,以往讲述中提到的那个被遗弃、被厌恶的“我”不存在了,随着小女孩儿的离去不再被提及了。此外,通过再一次的亲临死亡场景(上一次是“我”母亲的葬礼),并亲手结束一个女性生命个体,“我”终于得以向记忆中母亲的鬼魅告别。这样一来,小女孩儿与“我”母亲的形象合并,亲历的杀人快感取代长期的压抑与挫败,从而使曾经的创伤性经历通过重复而被消解,“我”内心的创伤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愈合。进而,事件后通过讲述“我”与小女孩儿之间发生的具体细节,“我”以讲述别人故事的讲述者身份焕然新生——“我”既具备参与者的切身体会,又被赋予重组故事情节的权力;并且在重新讲述的同时回味自己作为权力拥有者的兴奋,以便再次强调自我的强大概念。《蝴蝶》中的“我”既是可怖的,又是可怜的——若不是遭到生母的唾弃,什么人才会体会不到丝毫温情呢?麦克尤恩描述出的冷漠与残酷让人发指,但同时也映射出家庭伦理的缺失对人性的摧毁程度。
五、结语
从弗洛伊德等人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开始,“创伤”理论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而创伤这一概念也不再只限于心理学范畴,而是成为历史学、哲学、文学及文化学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背景下,创伤研究已从起初对歇斯底里症的个案分析逐渐演变成为研究诸多创伤群体,发掘其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多元起源的研究体系。事实上,在道德沦陷、金钱至上、疾病蔓延、环境污染的今日社会,人们看似平静的生活表面掩盖了诸多矛盾与冲突,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为创伤事件埋下了伏笔。
研究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中的伦理主题,探讨其中独特的文学叙事和精神宣泄,不仅可以提醒人们在物质生活日益繁荣的同时,精神的完整与伦理的正常都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基石。麦克尤恩作品中的大量创伤性事实可以作为反面事例帮助现代人客观地处理各种精神危机、家庭问题、身份认同危机等现代性“疫病”。通过在作品中塑造不同人物在经历创伤事件后的内心挣扎与自我治疗,麦克尤恩在揭示了创伤之普遍性的同时为读者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伦理问题。麦克尤恩作品中诗意与现实感结合的意象,展示了一幅幅伤痛与力量并列、梦魇与救赎共存的画面。同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这些作品旨在指出,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背景下,人们不应屈从于外在的非正义与诱惑,而应始终坚信自己内心的力量,追求精神上的启示,探索生活的真相。
[1]JoeAllen.Copingwith Trauma:A Guideto Self-Understanding [M].Washington: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1999.
[2]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32—138.
[3]季广茂.精神创伤及其叙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5):60—66.
[4][英]伊恩·麦克尤恩.阿姆斯特丹[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黄丽娟,陶佳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1,(2):100—105.
[6]史默琳.家庭在麦克尤恩早期小说中的缺失与变形 [J].山花,2014,(3):121—122.
[7][英]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A Study of Ian McEvan’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ics
YangLan
While depicting daily problems and traumatizing events,McEvan deals with the inner worlds of various characters after the terrible events in his unique ways.Besides,McEvan also focuses on their emo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making unusual ethical choices.This essay adopts the theory of trauma and ethics,covers several representative works by McEvan,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characterization,traumatizing events,traumatized personality in his narration,and,most of all,the ethical reasons behinds all those.
Ian McEwan;Trauma;Narrative;Ethics
I06
A
1007-905X(2017)09-0095-04
2017-06-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XW058);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15-JKGHYB-0062)
杨澜,女,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编辑 贾 敏 陈 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