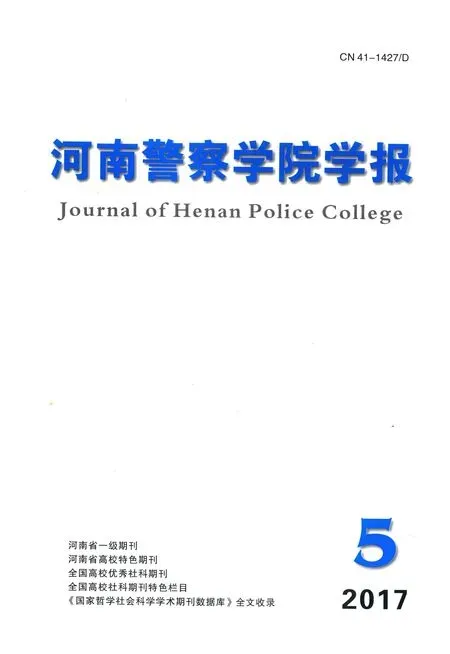中美警察执法程序规制比较及启示
2017-03-07姜峰
姜 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38)
中美警察执法程序规制比较及启示
姜 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38)
中美对警察执法行为的法律规制模式存在差异。美国宪法和司法判例对规制美国警察执法行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官在判例中通过对宪法条文的解释,积累并抽象出规制执法行为的规则,摆脱了法律文本表述对司法的制约,实现了较好的执法规制效果;我国主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发布司法解释对警察执法进行规制,强调立法过程的逻辑严谨和文字表述精湛,但忽视司法过程的能动性,法律适用受制于文本表述的局限,因而有时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现实效。我国法律对警察执法规制应更注重实用主义,从“立法规制”向“司法规制”的思维模式转变。
中美比较;警察执法;执法规制;法律制度
引言
美国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在世界上享有一定声誉,这是因为美国警察在执法中受到诸多法律的约束,“警察就像执法的机器人,程序早就设计好了”[1],几乎所有的执法行为都有标准的程序规定,警察如果不按照规定来进行就可能受到纪律处分。著名的“米兰达警告”规则要求警察在羁押讯问时告知沉默权和聘请律师权,如果警察没有履行,则获取的供述将被排除。米兰达规则于1966年确立,半个世纪以来,它和其他由美国法律确定的规则共同对警察执法进行严格的规制,因此美国警察执法通常有着十分统一规范的表现。
我国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法治建设时间还不长,以刑讯逼供、暴力执法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执法不规范行为如同社会的暗疾,阻挡着法治前进的脚步。这一定程度表明现行法律制度在方式和内容上没有对警察执法进行有效的规制。本文试图对中美警察执法规制体系进行比较,以期为我国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启示。尽管中美两国在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法律体系等各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是在现代法治的语境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警察执法都是对国家意志的实现过程,警察执法权力的运作方式和规制手段都必须在法律及其构建的制度下进行;从具体的警务实践来看,警察执法的目的都是对犯罪的打击和社会秩序维护,并拥有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限制的暴力手段,同时警察执法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规制。因此,无论是从权力运行,还是具体警察执法行为来看,中美警察执法制度的比较都有着充分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一、美国警察执法的法律规制
美国社会有着较长的法治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美国法律积累了大量对警察执法行为的规定,并形成了一套细致的执法规制制度。
(一)美国宪法修正案对警察执法的直接约束
美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基础而构建的,因此警察执法的依据,最终都由宪法来决定。1791年,宪法前十则修正案——《权利法案》通过,对个人权利进行了保护[2]52,这样用于对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与自由便构成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基础[3]180。《权利法案》规制了联邦政府的行为,保护了公民不受联邦政府的侵犯,但是州政府则不在规制当中。这一情况到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后发生改变。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将《权利法案》的大部分规制对象扩展到了州政府。
对宪法的解释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职责。当某些法律或某些行为对宪法一般理解形成挑战时,最高法院将作为一种最终的手段对宪法进行解释。20世纪期间及其后,许多的警察执法行为被认为与《权利法案》有冲突,因而以侵犯宪法权利为诉由被诉至最高法院。其中,主要有第四、第五、第六修正案通过保护公民权利的规定对警察行为进行了规制[4][5]。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免受非法搜查、扣押的权利。“除非基于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证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和人或者要扣押的物品,否则不得签发搜查和扣押状”。第四修正案对警察执法中的相当理由(probable cause)、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逮捕、搜查和扣押、电子监视和列队辨认环节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第五修正案保护个人“不得被强迫作指控自己的证言;……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得自证其罪的要求对警察审讯、诱惑调查等方面进行了规制。同时,也要求警察必须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采取强制措施。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有权……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于己不利的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第六修正案关于约见律师的规定对警察执法程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和监督。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个州根据实际的情况和特点制定自己的法律。但各州的法律也是根据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制定的,法律标准只能比联邦宪法和修正案更高,而不能更低。各个警察局内部也通常会根据宪法、法律以及判例制作警察执法手册,用于对警员的训练以及日常规制。警察手册的原则和要求通常由宪法的规定延伸而来。因此,美国宪法和修正案在多数情况对警察执法都起到了直接的制约作用。
(二)最高法院判例对警察执法规则的塑造
宪法生效后不久,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便在马伯利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参见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137/case.html。中,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违宪审查权,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判断国会的立法是否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并可以宣布国会的立法不符合宪法规定因而无效。这一规则的确立,同时也赋予了法院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审判时,对宪法进行解释并运用到实际判决中的权力。如此一来,现实中的判例更加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更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
美国警察执法虽然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执行,但宪法的条文毕竟只是文字,各人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因此仅宪法条文本身无法使全国警察的行为和标准达到统一。美国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它能不断更新着自身的体系,同时使社会的理解和实践都与此保持一致。这一功能主要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实现的。美国作为普通法的代表之一,判例是其法律的正式渊源。普通法系并不强调立法的完善,而是在不断的司法运作当中对现有的法律进行解释、修正、丰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宪法经历了两百多年,除了增加了27个修正案,并没有改变,但已经可以精细而具体地规制警察执法行为。
例如,在武力使用方面,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多数美国的警察局采用“重罪逃跑规则”(fleeing felon doctrine),即警察可以使用致命武力(deadly force)来逮捕任何在逃跑的重罪嫌疑人。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一规则已渐渐不再合适,而且也与美国司法的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冲突。1985年,著名的田纳西州诉加纳案(Tennessee v. Garner)*参见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71/1/case.html。中,两名警察奉行重罪逃跑规则将一名黑人盗窃嫌疑人击毙,法院判定这一规则违宪。这一判例确立了“生命保护规则”(defense of life standard)这一新的致命武力使用标准。生命保护规则的含义是,只有警察合理的认为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使用致命武力,这一规则对美国警察使用武力作出了很大限制[3]182。
两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条文没有变化,但却始终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规制政府或警察执法行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司法判例和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使得美国宪法可以在不进行修改条文的情况下,具有适应历史发展的柔软性。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美国的司法积累并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判断警察执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可以说,美国宪法是一部动态、持续生长的法,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功不可没。正如我国学者苏力评论,“我并不是在赞美美国宪法本身。我只是在赞美美国的法官和律师们的工作和技巧,赞美他们在其传统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地维护了美国社会制度”[6]。
(三)美国司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规制警察执法的极为重要的原则。这一规则本身没有直接规定在宪法修正案中,而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中对宪法的解释逐步确定的。1914年威克斯诉联邦案(Weeks v. United States)*参见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232/383/case.html。中,最高法院裁决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收集的证据不得用于在法庭上指控被告。但这项规则当时还只适用于联邦法庭,而没有扩展到各州的法庭。于是,这促成了另一种被称为“银盘理论”(silver platter doctrine)的警察不端行为。银盘理论是指只要避免证据由联邦执法人员参与收集或者经手,而由州执法人员收集,那么即使通过非法程序获得也可以使用。1920年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联邦案(Silverthorne Lumber Co., Inc. v. United States)*参见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251/385/case.html。中,法院将这种被污染的证据生动的比作“毒树之果”(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并明确规定不能在法庭使用[3]182。
另一起重要案件是1952年罗莎诉加利福尼亚州案(Rochin v. California)。*参见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42/165/case.html。该案中,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形下进入了罗莎的家中,并看到罗莎将两颗疑似毒品的胶囊吞入了腹中。警察将罗莎带至医院洗胃,发现两颗胶囊,然后将其用作指控罗莎的主要证据。罗莎因此被判罪行成立并判处60天的监禁。然而最高法院撤销了对罗莎的判决,并确定强迫取证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这对警察执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然而这起案例仍没有完全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于所有州,而是对极其严重“使良心震惊”的警察不端行为[3]183。
直到1961年,最高法院才在马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参见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67/643/case.html。中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到各州的执法警察。马普案之后,最高法院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一些补充。如在联邦诉里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参见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468/897/case.html。中,最高法院认定,如果警察出于善意(acting in good faith)认为法官签发的搜查令是有效的(但实际却因为未达合理怀疑标准等原因无效),那么非法获取的证据可以被采用[2]56。
法官对每一起案例的判决都可能对今后的警察执法造成影响,因此美国的执法规则可谓处于时刻变化的状态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警察执法体制受到法官和律师的重大影响和监督,并在不断补充添加新的内容。
二、中国警察执法的法律规制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我国制定了一系列警察执法的法律文件,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构建出约束机制,实现对警察执法行为的规制。
(一)宪法和法律法规对警察执法的整体规制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所有法律的母法。宪法规定了我国法律的根本原则,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我国警察执法也要受到宪法的约束。例如,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宪法》第四十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即使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也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对通信进行检查。这两条分别确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公安机关在对上述权利进行约束或限制时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
但是,我国现实中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刑事执法都不会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因为我国宪法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通过本身的条文直接规定的,而是经过转化为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来实现。如前述的逮捕强制措施,必定有宪法之外的法律条文对公安机关进行约束,也就是《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八十一条等法律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款。可见,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法律的制定提供依据,而其本身在具体执法活动中并不具有适用性。我国法律受大陆法系影响较大,成文法是我国主要的正式法律渊源。司法活动是利用现有法律体系的规则对法律事实进行演绎推理,遵循“三段论”的模式,即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判决或裁判就是结论[7],因而我国的法律运行必须严格强调立法时的逻辑严谨和缜密。而宪法的概括性和纲领性不可能满足具体案例的适用需求。
在宪法的统领之下,我国制定了大量规定警察执法规则的规范性文件,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常用法律法规包括:《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枪支管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戒严法》《禁毒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其中,《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讯问、取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的法定程序;《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时进行行政处罚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和程序;《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规定了警察遇有暴力行为等紧急情形可以使用枪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则进一步将使用枪支的法定情形限定在包括危害公共安全、危及生命安全、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等在内的十五种情形,从而对警察使用枪支进行了法律规制。除此之外,公安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对警察执法有规制作用,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等。前两个程序规定文件直接对警察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标准流程进行了细化规定,《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要求所有现场执法活动必须全程录音录像,以促进警察现场执法的规范化。
这些法律、法规等规范文件构成了规制警察执法的体系,从不同的方面对警察执法行为进行了规制。
(二)法律解释对警察执法规则的解释和补充
在普通法系中,法官可以根据以往判例帮助判断某一案件中警察执法是否违反程序。而判例不是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法官在判案时一般不能直接参照以往案例,而是仅对案件本身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抉择。但是,如果完全把对这个范围和程度的界定交给每个具体案件中的法官来判断则会十分有难度,也会给法官过高的裁判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法律采取的方法之一是发布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某部法律或某些条款的适用发布司法解释,*本文中的司法解释作广义理解,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解释性文件。以对法律表述的矛盾、不足、和漏洞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法律效力低于法律,对于其是否属于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当前还存在着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司法解释在我国具有现实的强制力。因此,司法解释必然限制着警察执法行为。例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对法律适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例如,对刑讯逼供行为作出了界定(下文详述),对警察执法有一定规制作用。
然而,司法解释仍没有摆脱法律本身所受的局限性。司法解释仍然受制于文字表述和逻辑推理的规则,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法律适用中的困惑。和法律并非万能、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一样,司法解释也同样永远无法穷尽警察在执法中的所有不规范行为。单纯的法律文本与其所追求的效果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的不足与欠缺,使法律表述趋于完善。但司法解释与立法过程一样,属于人的认知基础上的法律再造,不能跳出立法本身所面临的窘境。在解决现有法律的漏洞和矛盾的同时,也必然会面临着新的漏洞、新的矛盾[8]。
(三)我国司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与美国类似,我国警察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也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法律文字之间,可以感受到立法者在措辞时的谨慎和小心。立法者似乎希望在表述条文时,就能够预设可能发生的情形,并把所有应当排除的证据都列入其中。因此法律用“刑讯逼供等方式获取”来对非法证据进行了归纳和概括。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注重法律表述逻辑的严密性,将非法证据分为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书证物证几类。
但是,这样的法律表述在实践中仍难以操作,即如何界定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程度可称之为“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九十五条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通过把“刑讯逼供”限定为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遭受剧烈痛苦的办法,把“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标准从程序和后果两方面考虑,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对排除的范围进行了细化。但是实践中 “精神痛苦”包括哪些内容?构成的程度标准如何界定?解释中未给出明确答案。2013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将采用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所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同刑讯逼供一同都列入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但这种表述方式仍然存在着列举不能详尽的弊病,而且,这些方式需要达到何种程度仍然需要法官费尽心思的裁量活动[9]。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再次细化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包括:采取“……暴力方法或变相肉刑”,使执法对象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获取的供述;以暴力或危害权益威胁,使执法对象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获取的供述;采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获取的供述;重复性供述等。显然,对于“变相肉刑”、“难以忍受的痛苦”的界定仍然没有明确清晰的界限,有待于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法律通过文件补充文件、文字解释文字的方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但是在现实的适用过程中,总是会遇到标准和界定的难题。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法官既不能参考现成判例,又无权创制新的判例,这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免给人以“纸上谈兵”的感觉,也因此而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10]。
三、中美警察执法规制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中美警察执法程序的规制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法系之间的区别。美国是英美法系的代表之一,我国则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较深。如储槐植所说,“英美法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经验(经验往往包含理论一时难以说明的真理成分),价值目标是实用(这样的目标容易达成共识,但可能缺乏深入探讨的推动力)”,“英美法系见长于运作能力”,而“大陆法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概念(概念本身即为理性认识的成果),价值目标是完善(此目标难以达成共识,但留有充分讨论的余地)”,“大陆法系见长于想象能力”[11]。两者在思维方式、运行模式上各有特色。在对警察执法的规制方面,美国法律因其灵活性、实用性、可操作性而取得更为明显的效果,可以为我国提供启示。
(一)重视警察执法规制中的“法律实用主义”
在法学研究中,美国大法官霍姆斯首创实用主义法学。他指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人们所感受到的需求、道德、政治理论,甚至是法官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12]。霍姆斯认为,应当根据社会利益和社会目的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用主义法学认为法律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带来效益,而不是在于仅构建出一套看似合理的理念。法律所追求的自由、正义、秩序的价值是在对现实社会关系调整中逐渐实现的。
在警察执法规制上,美国的法律体系实用性更强。法官可以根据现实中的情况作出合适的判断,从而对警察执法进行有效规制。司法活动多从经验和实效的角度考虑,能符合社会利益,对警察行为作出有效规制的法律才会得以保留和延续。我国法律规制更加注重理论的严密和法律条文的完备,在法律构建的体系之下,司法活动则是基于已有法律规则的适用。其运作的假定模式是,如果有一套完美的执法规制制度,那么法官就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引用从而判决警察的执法行为是否有罪。
我国法律对警察执法的规制有着系统的规定,逻辑性强,但是由于制度是抽象构建而成,因此在现实中经常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例如,我国法律赋予警察开枪的十五种情形,虽然看似完备,限制了警察的开枪情形,但是对于具体的警察开枪行为是否能够归于这十五种法定情形之中仍然十分困难,导致庆安枪击案*具体案情参见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5-06/01/content_35705030.htm。等现实执法中警察开枪的行为合法性难以判断,同时也导致了对警察开枪规制效果大大降低。而美国法律通过简单的“生命保护规则”和相关的判例,使得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条件深入人心,并有效的规制了美国警察的开枪行为。由此可见,对警察执法规制的法律不在于其表述的精湛,而应更重视现实的有效性、可操作性。
(二)实现从“立法规制”到“司法规制”的思维转变
在法学的研究中存在着立法中心主义和司法中心主义研究方式的差异。“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围绕着规则的生成研究法律,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 如果没有国家立法机关的制定和认可, 就没有法律规范。这实际上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从完善法律规范的角度研究法律。这种研究忽略了法律向判决的转换过程, 忽略了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司法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则更加关注规则的适用,在司法的过程中充分的论证、实践法律的价值,更有利于以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为了避免对法律形成片面的认识,应当“从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向司法中心主义转移”,“关注成文法向判决转换的过程与方法”[13]。
美国对执法规制的法律体系不强调最初的完备性,而是在适用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和生长。对警察执法的规制,是法官在每一起案例中通过对宪法和法律的解读,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评价进行积累,从而抽象出的规则。这些规则通过州的立法以及每个执法单位的执法手册,约束着警察的每一起实际执法。美国法律在适用时需要法官更多发挥主观能动,因此对法官的要求较高。
在我国的法制体系建设过程中,长期都以制定法为主。当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缺陷暴露出来之后,我们总是习惯于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去填补漏洞。对于社会中出现的新的问题,许多人将其归结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呼吁“加强立法”“完善立法”。诚然,与美国等有着数百年法治历史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法治建设时间较短,法律制度还有不足之处。但法律制度的构建并不只是立法的一种途径。通过制定的法总是滞后于社会,它是静态的。而通过运作的法可以更加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它是生长的法、动态的法。立法和司法的内在存在着一定张力,这来自法律文本对抽象规则表述的局限性。美国法律在司法过程中构建了警察执法行为规制的规则体系,通过法官对具体的案例赋予了法律新的生命力。或许美国这种“法官造法”的举措不一定能够适用于我国,但是足够让我们重新审视立法和司法的关系。将立法和司法的内在紧张转变为一种交融促进,使法律可以发挥更大的调整作用。
[1]孔宪明.中国警官走进美利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8.
[2]Michael J. Palmiotto. Policing: Concepts, Strategies, and Current Issues in American Police Forces[M].3rd edition.CreateSpace Independent,2013:52,56.
[3]John S. Dempsey,Linda S.Forst.Police[M].Student Edition.New York:Delmar, 2011:78,180,182,183.
[4]张小兵.中美警察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224.
[5]张小兵.论美国宪法对联邦警察的规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2):120.
[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3.
[7]姚岚.论演绎推理在大陆法系的应用[J].法制与社会,2015,11(中):7.
[8]吴萍.理性看待司法解释的作用[N].法制日报,2004-04-02(10).
[9]宋远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化与实化[J].证据科学,2017(1):14.
[10]李奋飞.司法解释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虚置” 的成因分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14(1):118.
[11]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
[12][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13]陈金钊.法学的特点与研究的转向[J].求是学刊,2003,30(2):64.
ComparisonandEnlightenmentofChineseandAmericanPoliceLawEnforcementProcedureRegulation
JIANG Fe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legal regulation patterns of police law enforcement.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mendment and judicial precedent jointly regulate the police law enforcement. The judg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judicial precedent accumulates and abstracts the rules of the law enforcement law, gets rid of the constraints of legal text and achieves a better law enforcement effect. China mainly regulate the police law enforcement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 and announcement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which emphasizes rigorous logic and textual expression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ut ignores the initiativ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The law is subject to the text limitations, so the operability is low,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actual effects. By comparison, we can see that China’s law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agmatism in the police lawenforcement, and change from "legislative regulation" to "judicial regul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police law enforcement;regulation of law enforcement;legal system
2017-09-04
姜峰(1990— ),男,湖北大冶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治安学。
D908
A
1008-2433(2017)05-0138-07
(责任编辑:岳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