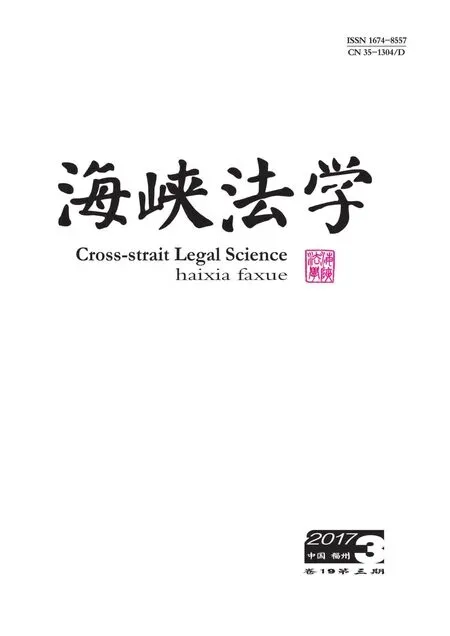“终身监禁”的问题分析
2017-03-07郑朝旭徐久生
郑朝旭 ,徐久生
“终身监禁”的问题分析
郑朝旭 ,徐久生
“终身监禁”的入刑,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并不能有效应对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目的是制定刑事政策的核心依据之一,刑事政策必须体现报应公正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但“终身监禁”具有违背上述刑罚目的的缺陷。“终身监禁”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着违背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与公平正义的问题。
终身监禁;刑事政策;刑罚目的;刑法适用
一、“终身监禁”的刑事政策问题之所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所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人,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条第4款规定,犯第1款罪,有第3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刑法》第386条所规定的受贿罪也适用该条所规定的刑罚。因此,对于因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人,法院原则上对其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同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人,在二年考验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方式。从严厉打击贪腐案件的角度看,《刑法》第383条所规定的刑罚及其执行方式不可谓不重,体现了我国对贪污、贿赂案件重点整治的刑事政策取向。
然而,《刑法修正案(九)》关于“终身监禁”的规定所体现的刑事政策取向,一方面对犯罪人的责任报应过重,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对引起犯罪的其他原因的考察和刑罚目的的定位。刑事政策的制定不是仅仅基于重点整治犯罪这一目的或者出发点,而是对多种因素的考量与价值取向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刑事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犯罪原因、犯罪人、刑罚目的与效果等方面,同时确立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处罚犯罪人或者矫正犯罪人,抑或是二者的结合。缺乏对上述因素的考量与对刑事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选择,一个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政策将是片面的,既无法有效治理犯罪,也无法完善制度架构本身。易言之,如果对导致犯罪的原因以及各种具体的刑罚方法的效果缺乏客观了解,是不可能制定出适当的刑事政策的。①笔者认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分析,“终身监禁”这一刑罚执行方式,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终身监禁”并不能有效应对贪污、贿赂犯罪
刑事政策是关于如何治理犯罪的措施的展开,其核心在于通过各种刑事与非刑事措施来控制犯罪的范围、规模与影响。李斯特认为:“与犯罪作斗争是以了解犯罪的原因和刑罚的效果为前提条件的。同时,离开了对犯罪生物学(人类学)和犯罪社会学(统计学)的研究结果,也不可能制定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刑事政策。对犯罪和刑罚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研究完全不需要追求刑事政策目的;只要我们瞥一眼犯罪统计方面的资料,或者看一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们就会找到充足的理由。但是,如果刑事政策学家缺乏通过对事实的仔细的和全面的了解才能获得的科学基础,那么,他依然只不过是一个半吊子。”②如果在制定刑事政策的过程中缺乏对犯罪原因的了解和对犯罪人的分析,那么一个国家所实施的刑事政策是无法对犯罪做到有效应对的。增加“终身监禁”作为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以往的案件中对罪行特别重大的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无期徒刑又过轻,无法做到罪当其罚,因此,在这其中增加一种严厉性介于上述两种刑罚的刑罚执行方式。然而,这样的理由是从刑罚的严厉性或者说是从责任报应的角度来应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并不是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案发原因上去分析。在缺乏对案件原因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加重刑罚,可能于事无补,也可能本末倒置。
(二)刑罚目的是刑事政策产生的基石③
刑事政策围绕刑罚目的展开,而“终身监禁”却存在着脱离或者违背刑罚目的的问题。既然刑事政策的核心是控制犯罪的发生,那么纯粹的责任报应的刑事政策只不过是对刑罚的强调,因为这样的刑事政策把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当作是刑罚的目的,必然缺乏对犯罪人的矫正教育与对其他人的犯罪预防,也即缺乏了目的刑的内容,是一种僵化的刑罚理念。刑事政策本身是国家为了灵活应对现实生活中变化的犯罪情况所做的调整,以期用最小代价的刑罚去实现最大效益的防治犯罪的目的。当代刑法学虽然有各种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基本是如何在责任刑的限度内追求预防刑,以及当责任刑与预防刑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换言之,当代刑罚已不再是纯粹的责任报应,其中必然要包含着目的刑的色彩。“终身监禁”并不能起到特殊预防的效果,同时一般预防的效果又由于缺乏对犯罪原因与犯罪人的考察,也必然大打折扣。
二、“终身监禁”与刑罚目的的冲突
刑法学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大致有三种,即报应论、预防论与综合论。综合论由于最大程度地兼顾责任报应与预防犯罪这两个刑罚目的,并对报应论与预防论取长补短,从而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青睐。综合论的核心是,在追求刑罚的报应目的与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还应当追求刑罚预防犯罪的功利目的。而在追求功利目的方面,特殊预防处于优先的位置,一般预防次之,但同样是应当加以追求的。如果必须在报应公正与预防功利之间作出两者择其一的选择时,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在刑罚领域,理应公正优先,兼顾功利,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④笔者赞同综合论者的主张,因为综合论可以最大程度地兼顾人权保障与社会利益。报应论者从个人本位出发,认为犯罪是个人意志自由的结果,所以对其适用刑罚是对其意志自由的结果进行否定的评价与非难,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对意志自由的尊重——本质是对人权的尊重,因为刑罚以责任为限。与此相对,预防论者认为,刑罚目的应当从社会本位出发,犯罪行为是犯罪人反社会人格的体现,必须通过刑罚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并教育国民不要犯罪,所以刑罚应以预防再次犯罪所需的时间长短为限,而不是以责任为限。但是,报应论者的主张缺乏灵活性,即缺乏对预防犯罪的重视,而预防论者的主张则可能违背责任主义,导致不定刑与不定期刑。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既要针对个人恣意保护社会法益,也要保障个人自由,这是“刑法的二律背反性”。⑤“刑法的二律背反性”表明,片面地保护社会利益或者保障个人自由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责任报应与预防犯罪的目标。我国刑法从立法到司法,都是坚持综合论的主张的。《刑法》第61条表明,我国立法者认为量刑根据是罪行本身与罪行对社会的影响,这主要是关于责任报应的规定,而《刑法》同时又规定了从轻、减轻、免除、从重处罚等情节,例如自首、坦白以及累犯。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6条也明确指出,刑罚的适用不但要考虑惩处罪行的刑罚目的,同时也要考虑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在《刑法》第383条修改之前,我国对于最为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的最重刑罚(包括刑罚执行方式)是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由于受国内外关于废除死刑主张的影响,我国对死刑是持“少杀、慎杀”的原则,即使是罪行最为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人,也基本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⑥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对于特别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所能适用的最重刑罚便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但由于考验期、减刑、假释制度的存在,这些犯罪人还是可能在经过一定的服刑期后被释放。因此,有人认为,这样的处罚方式对于罪行特别重大的犯罪分子处罚过轻,不足以起到责任报应与震慑犯罪的效果,以致形成了“死刑立即执行过重,死缓或无期徒刑过轻”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终身监禁”应运而生。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点,很可能是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所产生的强烈处罚情感的结果。换言之,在当前死刑立即执行基本不适用罪行特别重大的贪腐犯罪人的背景下,对他们只能适用死缓与无期徒刑可能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以及无法满足公众强烈的处罚情感。此外,如果说死刑立即执行是一种“死刑”,而“终身监禁”是与死缓、无期徒刑同属于“生刑”的话,那么这表明了公众与立法者寄望于加重“生刑”的严厉程度来达到震慑公职人员的效果。然而,笔者以为,“终身监禁”是与我国的刑罚目的相冲突的。具体而言:
(一)“终身监禁”突破了犯罪人的罪责边界
根据综合论,无论预防犯罪的需求多么强烈,对犯罪人的量刑也不能突破罪责的边界。因为责任主义要求,对犯罪人的刑罚只能在罪责的边界内去追求。所以,即使预防犯罪的需要非常大,也不能突破责任刑的限度对罪犯增加刑期的长度或者加重刑罚的程度。虽然我们无法精确确定罪责的大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罪行之间的比较来大致确定罪责的边界,刑法中关于各种具体罪行的法定刑与量刑规定便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终身监禁”入刑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改变“死刑立即执行过重,死缓或无期徒刑过轻”这一局面。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对于特别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人,无论是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或者无期徒刑,都无法做到罪当其罚。而且在他们看来,“终身监禁”对责任报应的严厉程度是低于死刑立即执行的。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死刑的“少杀、慎杀”原则,可以肯定的是,其适用于所有规定有死刑的犯罪。所以在罪行程度大致相当(因为并没有罪行完全一致的犯罪)的情况下,量刑与执刑当是一致的。故意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等罪行的恶劣程度并不比贪污、贿赂犯罪低,甚至在法定刑上是重于贪污、贿赂犯罪的。但是,“终身监禁”却并不适用于这些犯罪。对于这些犯罪,除死刑立即执行外,最重的处罚当属《刑法》第81条第2款之规定。质言之,对于罪行重大的这些犯罪的犯罪人,虽然不得假释,但是在减刑制度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可以在经历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监禁之后得以释放。这就表明,立法者与司法者认为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关押后,犯罪人的责任报应已经实现,无论其罪行所需要的预防时间多么长,也不能予以继续关押。而反观罪行恶劣性质相当的特别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人,其一旦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在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则完全失去了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既然立法者与司法者对与此罪行的恶劣程度相当的上述犯罪的犯罪人可以在责任刑内追求预防刑,那么为什么要对特别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人实施“终身监禁”这一突破了责任限度的处罚方式呢?如果认为杀人、强奸、绑架这类的犯罪侵犯的是个人法益,因此无需以一个人的终身自由来付出代价,而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社会法益或者国家法益,是对社会大众利益的侵害,所以以一个人的终身自由为代价进行惩罚并没有问题。但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范畴,况且杀人这样的犯罪侵犯的是生命这一至高无上的法益,而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上述矛盾的处罚方式表明,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的侵害在性质上要恶劣于侵害生命,这难以令人信服。退一步说,叛国、颠覆国家、煽动叛乱这样的罪行直接侵害国家安全,其危害性更重于贪污、贿赂犯罪,但对这些犯罪却并不适用“终身监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对公职人员廉洁性的侵害在性质的恶劣上要重于对国家安全的侵害呢?恐怕很少有人会持肯定回答。所以,对于罪行特别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人适用“终身监禁”,其虽满足了强烈的处罚情感,但却是以牺牲每个犯罪人的人权为代价的,这样的做法对于法治而言是本末倒置的。
(二)“终身监禁”并不能实现特殊预防
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使其不再实施犯罪行为。作为目的刑的组成部分,特殊预防起源于对犯罪人反社会人格的研究。目的刑论者认为,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是其反社会人格的体现,为了保护社会不会再遭受犯罪人的侵害,应该在适用刑罚时对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进行治疗,使其摒弃犯罪思想或失去犯罪能力,最终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因为刑罚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纯粹的责任报应只是僵硬的处罚,缺乏依据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做灵活处理的张力。在综合论的立场下,因为刑罚必须与罪行相均衡,故可以防止为了追求预防目的而出现畸轻畸重的刑罚;因为刑罚必须与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相适应,“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⑦故又可以防止为了追求报应而科处不必要的刑罚。⑧所以,通过刑罚来矫正犯罪人以使其不再犯罪成为了刑罚目的的重要内容。例如,我国《刑法》中的累犯与再犯制度表明,对于再次犯罪的犯罪人,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大、再犯可能性大,因此需要更长时间的矫正教育才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这便是典型的特殊预防在刑罚中的体现。但是,当我们无法通过刑罚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时,我们又该如何量刑呢?如前所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据犯罪人的责任程度来量刑,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人,司法者只能在责任刑的限度内尽量追求一般预防的效果。因为被判处了刑罚的这些犯罪人,不可能再担任公职,即失去了再犯罪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终身监禁”入刑只能追求责任刑与一般预防的效果。但是,如前所述,这样的刑罚方式是违背了责任主义的,其所追求的并不是基于责任主义所要求的刑罚,而是基于强烈处罚情感而要求的刑罚。此外,“终身监禁”在使犯罪人重回社会这个角度上与死刑立即执行并无二致,对于适用“终身监禁”的犯罪人来说,其无论如何证明自己已改过自新都无法再回归社会。死刑立即执行是对罪行极其严重且无改造可能性的犯罪人适用的,而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人在已经失去了再犯罪能力的情况下,立法者与司法者又是依据什么认为其无改造可能性呢?
(三)“终身监禁”也难以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
一般预防也是目的刑的组成部分,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来震慑、教育国民,从而预防国民犯罪。从这个意义来说,似乎刑法对犯罪规定和适用的刑罚越严厉,对国民所起到的震慑、教育作用越大,因此“终身监禁”由于加重对“生刑”的严厉程度,可能使得其他的公职人员不敢实施职务犯罪。也有学者认为,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直接堵死了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可能,意味着其永远不能重返社会,基本上没有再犯的可能性,特殊预防确实毫无意义。但是刑罚目的的预防论不仅包括针对犯罪分子本人的特殊预防,更包括针对社会公众尤其是其他潜在的犯罪行为人的一般预防,不能否认终身监禁所具有的威慑力和警示功能。⑨然而,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首先,人类关于刑罚的理念从残酷、严苛的观点逐渐演变为宽和、人道的刑罚观,这反映在刑罚制度的变革中。肉刑已基本退出了当代刑罚制度中;死刑在有些国家已经被废除;在仍然存在死刑的国家,死刑的适用数量也在降低;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得到大量的适用。但是,刑罚的宽和并没有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犯罪浪潮,社会治安也没有恶化,所以加重刑罚的严苛程度对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是十分有限的。其次,如何有效地治理贪污、贿赂犯罪,不能仅依靠加重刑罚来实现,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善监督机制、促进法制建设等方面来实现。“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⑩对于职务犯罪而言,如果仅仅只是在刑事司法方面加重刑罚,而没有辅之以其他的社会政策,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只是使案发的犯罪人得到了法律的审判,而犯罪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也就只是立法者的臆想。最后,一般预防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来达到预防国民犯罪的目的,这势必导致将犯罪人当做预防犯罪的工具,使犯罪人为其他人的犯罪负责。因为通过威慑进行一般预防,或者为了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而适用刑罚,意味着不仅因为犯罪本身而受处罚,而且为了他人而受处罚,意味着将犯罪人作为预防其他人犯罪的工具或者手段,这便侵害了人的尊严。国家不能将个人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个人在国家之前便存在,是国家应当保护的人格价值的担当者,在人皆平等的法秩序里,不应将人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11因此,“终身监禁”无论是对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还是从有效治理职务犯罪角度而言,其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终身监禁”也可能将犯罪人当做是预防犯罪的工具,进而侵犯人的尊严,这是违背当代刑法价值的。
三、“终身监禁”的法律适用矛盾
《刑法》第383条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改变了之前以犯罪数额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条件、以犯罪情节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定罪量刑模式,而直接采用了以“犯罪数额或者犯罪情节”作为定罪量刑条件的模式。此外,《刑法》在第383条第3款规定了法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并将之适用于第1款所有的贪污犯罪行为,改变了以往仅将法定减轻、免除处罚情节适用于贪污罪第1款第4项的做法。一方面,在《刑法》第383条被修改以前,司法实务中对待贪污、贿赂案件,偏向于以犯罪数额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忽视了对犯罪情节的考察与运用,这导致了不同犯罪数额的贪污、受贿案件之间判处的刑罚差别不大,难以体现刑法对不同行为的评价差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立法者要引入“终身监禁”的原因。而在采用了“犯罪数额或者犯罪情节”的定罪标准模式之后,相比较而言,更加符合实务中对待不同案件之间的量刑差异,同时也能正确、全面评价贪污、贿赂犯罪,有利于实现量刑的公正与均衡。另一方面,扩大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范围,也有利于促使犯罪人自首、坦白,减少犯罪后果的危害,节约司法资源。虽然新修订的《刑法》第383条有着上述两个方面的进步,但在“终身监禁”这个部分仍然存在着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否存在将犯罪情节既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又作为宣告“终身监禁”的依据,从而导致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第二,对于被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犯,其能否因为在“终身监禁”期间的重大立功而被减为有期徒刑呢?
(一)禁止重复评价
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对犯罪人的一次犯罪行为或情节只能进行一次评价,而不能再将其作为其他定罪量刑的依据。例如,犯罪人窃取了被害人一个价值“数额较大”的财物,那么法院对被害人定罪量刑的依据便是“犯罪人窃取了一个‘数额较大’的财物”,而不能再将这个“数额较大”的财物作为犯罪情节看待,从而增加对犯罪人的刑罚,否则便是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具体到贪污、贿赂犯罪上来,问题便是:当法院根据犯罪人的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对犯罪人决定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能否再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同时宣告对犯罪人适用“终身监禁”呢?笔者认为,当法院已经根据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对犯罪人决定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不能再依据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对犯罪人宣告“终身监禁”。理由在于:第一,既然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已经作为认定犯罪人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根据,再将其作为适用“终身监禁”的依据则是重复评价的做法。第二,《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的是,犯第1款罪,有第3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此,笔者以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该规定认为在依据数额可以认定对犯罪人应予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情况下,犯罪情节可以作为宣告“终身监禁”的依据。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将犯罪数额与犯罪情节作为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依据,则犯罪情节就不再是宣告“终身监禁”的依据,因此条文中所称的“犯罪情节等情况”应解释为,被作为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据的犯罪情节以外的可以表明犯罪人责任或者犯罪性质的情节。上述两种解释既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时也能兼顾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并且也符合《刑法》之规定。而且,即使这样的解释是类推解释,那么也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二)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从法条解释的角度出发
“终身监禁”是依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而存在的,即“终身监禁”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才开始执行,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被宣告“终身监禁”的犯罪人,其刑罚执行经历了两个阶段——死刑缓期执行阶段与“终身监禁”阶段。而前一阶段执行完毕并不必然导致“终身监禁”阶段的开始。因为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阶段,如果犯罪人有“重大立功”的话,可以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并不存在无期徒刑,因此对于犯罪人而言,自然没有适用“终身监禁”的可能。所以,假如犯罪人在死缓期间能够实现“重大立功”的话,其有可能避免被适用“终身监禁”,从而可以依据减刑、假释制度在执行一定期限的监禁后重获自由。由此可见,《刑法》第383条并没有完全使得特别重大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人丧失重返社会的可能性的。但成为问题的是,假如犯罪人是在“终身监禁”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其能否还可以依靠减刑制度得以减为有期徒刑,从而终止“终身监禁”的执行呢?有的学者认为,“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因重大立功而减为有期徒刑的,同样不再具有执行终身监禁的法定依据,《刑法》第383条第4款关于裁量和执行终身监禁的规定,并不是《刑法》第78条规定的例外规定。12换言之,即使在“终身监禁”期间,犯罪人依然可以因为“重大立功”而被减为有期徒刑,从而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服刑后重返社会。但笔者不赞同这样的观点。第一,从“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理由13与定位来看,“终身监禁”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减少死刑适用、加重非死刑刑罚的需要。假如说犯罪人还可以在执行“终身监禁”期间依靠“重大立功”被减为有期徒刑,从而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服刑后重获自由,那么其所谓的加重非死刑刑罚严厉性的效果便不复存在,“终身监禁”也只是虚有其表。更为矛盾的是,这样效果的“终身监禁”是与无期徒刑的效果相同的,因此在刑罚制度中便成为了多余的存在。第二,刑法总则的规定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刑法分则的,除非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的适用作出了特别的规定。例如,《刑法》第383条第3款规定,犯第1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1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有第2项、第3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因此,当犯罪人具有上述情节时,即可直接适用《刑法》第383条第3款,而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坦白的规定。《刑法》383条第4款规定,犯罪人在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不得减刑、假释”是“终身监禁”期间的附加条件,是对“终身监禁”的进一步强化。这便意味着,当犯罪人由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法院所宣告的“终身监禁”开始执行,在此期间内,即使出现任何依据刑法总则可以减刑、假释的情节,对于被执行“终身监禁”的犯罪人也不能减刑、假释。第三,也是最为矛盾的地方,特别重大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人,即使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同时在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适用“终身监禁”,但只要犯罪人在死缓期间可以有“重大立功”,其依然有可能被减为有期徒刑而不适用“终身监禁”,但其在“终身监禁”期间的“重大立功”反而不可能使其减刑。这不得不令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只是因为“重大立功”时间点的不同,便使得同样罪行的犯罪人所遭受的刑罚待遇竟有如此大之差别?由于在上述二点,笔者已经论证过“终身监禁”的最终结果是犯罪人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那么从制度设计、刑罚目的定位来看,似乎上述差别并没有什么问题。也有学者指出,死缓期间重大立功之所以能够减刑从而绕开了终身监禁既是该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也体现了“重大立功”的时间节点不同反映了服刑人员的可宽宥程度的差异,何况所谓的公平是相对而无绝对的公正。14笔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首先,这一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何在?其次,“重大立功”的时间点不同是如何体现出服刑人员可宽宥程度的不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越早立功的话,得以减刑的可能性便越大。但是,立功制度本身并没有如此规定,而且以立功时间点的不同来体现对服刑人员宽宥程度的不同是非人道的。最后,公平的确是相对而无绝对的公正。但是在刑罚领域,我们应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正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生命、自由、资格、财产,如果动辄以“公平是相对的”这一概念来区别对待,则无论对刑法公信力还是对犯罪人都是不幸的。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终身监禁”的入刑,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并不能有效应对贪污、贿赂犯罪,又存在着背离刑罚目的的倾向,难以实现刑事政策的目标。其次,从刑罚目的的角度看,“终身监禁”突破了刑事责任的界限,违背责任主义;犯罪人在仕途终结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实施职务犯罪,特殊预防的效果无从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对于预防犯罪的实际作用微乎其微,纵使有效,又由于缺乏其他社会政策的辅助,其效果也是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存在将犯罪人当作预防犯罪的工具这一问题。最后,从刑法适用的角度看,“终身监禁”的适用需要切实处理好对于犯罪数额与犯罪情节的运用,避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重大立功”在不同时间点的矛盾是“终身监禁”入刑的最大问题之一,其无法体现对犯罪人的公平正义。
(责任编辑:刘 冰)
①徐久生:《刑罚目的及其实现》,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8页。
② [德]冯·李斯特著:《论犯罪、刑罚与刑事政策》,徐久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
③储槐值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页。
④徐久生:《刑罚目的及其实现》,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⑤参见团藤重光等编:《泷川幸辰刑法著作集(第5卷)》,世界思想社1981年版,第74页以下。
⑥笔者了解到,距今最近的因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是2011年的两个案件,分别是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贪污受贿案和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贪污受贿案。
⑦ [英]边沁著:《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孙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⑧张明楷著:《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⑨黄永维、袁登明著:《<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3期,第36页。
⑩对此名言的考证,参见徐久生:《刑罚目的及其实现》,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页。
11张明楷著:《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12黄京平:《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01页。
13关于立法理由,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第八项修改意见。
14黄永维、袁登明:《<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3期,第40页。
D924.12
A
1674-8557(2017)03-0085-08
2016-11-06
郑朝旭(1992-),男,福建福州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徐久生(1961-),男,江苏金坛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