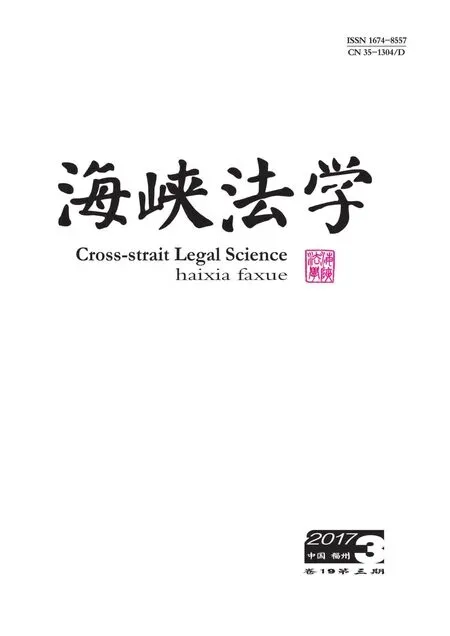日本缓刑假释与保护观察之法制与运作
2017-03-07余振华
余振华
日本缓刑假释与保护观察之法制与运作
余振华
由于保护观察对象接连发生再犯重大犯罪事件,学界与实务界纷纷批判缓刑与假释等保护观察制度已经出现严重缺失。2013年6月13日,日本国会通过《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及《有关违反药物使用罪之部分缓刑法律》,增订“部分缓刑”制度,并于2016年6月1日开始施行。部分缓刑制度允许法官在审判阶段得决定实际执行与缓执行之刑度,有别于日本及台湾地区相关规定,该制度相关内容之介绍,目前在台湾地区及大陆均属首见。通过对日本“部分缓刑”之规范内容及其背景、内容与争议问题等进行介绍,同时比较缓刑与假释所实施保护观察之相异性,期望对台湾地区及大陆之现行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本更生保护制度;部分缓刑;缓刑;假释
一、前言
日本在2004年至2005年间,保护观察对象接连发生再犯重大犯罪事件,各界严格批评实施保护观察之实效性,为了实现国民所期待之更生保护,因而需要从宏观角度检讨更生保护制度之全貌,法务省于2005年7月邀请十位学者专家组成“思考更生保护方针专家会议”,经过17次会议讨论后,向法务大臣提出《更生保护报告书》。①在该报告书中,提出更生保护制度有:(1)国民或地方社会并未充分理解更生保护制度之运作;(2)保护观察实施体制依赖民间之脆弱性;(3)保护观察在指导监督与辅导援助两方面未发挥充分之机能等三大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以下三点改革建议:(1)扩大国民或地方社会之理解;(2)使官署之职能明确化,并整顿更生保护官署之人或物的体制,依此而实现高实效性之官民协力体制;(3)提高保护观察之有效性、使更生保护制度之目的明确化、改革保护观察官之意识等,藉以实现坚强之保护观察。
法务省基于《更生保护报告书》之建议,为了强化保护观察之防止再犯机能,乃提出《更生保护法草案》,于2007年6月经国会通过后公布施行(2007年6月15日法律第88号公布、2008年6月1日开始施行)。综观《更生保护法》之内容,计有八章99条,包含第一章总则(第1条〜第32条)、第二章假释等(第33条〜第47条)、第三章保护观察(第48条〜第81条)、第四章生活环境之调整(第82条〜第84条)、第五章更生紧急保护等(第85条〜第87条)、第六章恩赦之声请(第89条、第90条)、第七章声请之审查(第91条〜第96条之2)、第八章杂则(第97条〜第99条)。
再者,2013年6月13日,日本国会通过《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②及《有关违反药物使用罪之部分缓刑法律》,③增订“部分缓刑”制度,并于公布后三年之2016年6月1日开始施行。此种制度允许法官在审判阶段得决定实际执行与缓执行之刑度,有别于日本及台湾地区以往之假释、缓刑及保护观察(台湾地区称“保护管束”)相关规定,该制度之内容目前在台湾地区及大陆均属首见,确有探讨之必要性。基此,本文除探讨全部缓刑及假释之保护观察法制外,更针对《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更生保护法》以及《有关违反药物使用罪之部分缓刑法律》中“部分缓刑”之规范内容,逐一分析该制度制订之背景、内容与争议问题,同时比较缓刑与假释所实施保护观察之相异性,期望对台湾地区及大陆之现行制度有重要之参考价值。
二、缓刑制度之梗概
日本以往之刑罚制度,大致上与台湾地区或大陆并无不同,针对自由刑之判决,法院只能决定全部自由刑或全部缓刑,亦即针对宣告自由刑,法院只能宣告刑之全部执行或全部缓执行,并无选择性。在2016年6月1日开始施行之部分缓刑制度下,法院可针对所宣告之自由刑决定执行其中一部分,并针对其余部分给予缓刑,此种新制度使法院增加了选择性。日本刑法上有关“部分缓刑”制度之增订,主要系规定在《刑法》第 27条之2至第27条之7。
(一)刑之全部缓执行
有关刑之全部缓执行规定如下:
“Ⅰ 受三年以下惩役、禁锢或五十万元以下罚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情节,自判决确定之日起,在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期间内,暂缓执行其刑之全部:
一 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
二 曾被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自执行完毕或免除其刑之日起,五年以内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
Ⅱ 曾被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而受刑之全部缓执行者,在受判处一年以下惩役或禁锢而依情节有应特别酌量减轻情形者,亦同。但依第二十五条之二第一项之规定交付保护观察,在保护观察期间内更犯罪者,不在此限。”(日本《刑法》第25条)
依据本条之规定,缓刑制度系就有罪判决之宣告,而将其执行于一定期间内加以延后,一旦经过缓执行之期间,则使刑罚权消灭之制度。虽然缓刑制度与缓宣告制度均为延迟刑罚,但后者系法院在为有罪认定时,将有罪判决之宣告或刑之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加以保留之制度。两制度之差异,乃在于有否刑之宣告存在。再者,缓刑在形式上系属刑罚之附随处分,而非刑罚本身。当缓刑处分撤销时,实际仍须服刑。而当缓刑期间经过,则不只刑之执行可以免除,刑之宣告亦失其效力,其系具有利益性质之处分。本条之规定包涵针对初次(第1项)以及再次之缓刑(第2项)。
(二)刑之部分缓执行
有关2016年6月1日开始施行之“部分缓刑制度”,其部分缓刑之规定如下:
“Ⅰ受三年以下惩役、禁锢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考虑犯罪情节轻重及犯人境遇或其他情状,有认为防止再犯之必要且相当时,得在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期间内,暂缓执行其刑之一部:
一 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
二 虽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但暂缓执行其刑之全部者。
三 虽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自执行完毕或免除其刑之日起,五年以内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
Ⅱ 依前项规定暂缓执行刑之一部者,执行其未暂缓执行部分之期间,自该部分期间执行完毕或该部分不再执行之日起,计算其缓执行期间。
Ⅲ 依前项规定未暂缓执行刑之执行完毕或该部分执行失效中,有其他应执行之惩役或禁锢时,第一项规定之缓执行期间,自该他执行之惩役或禁锢执行完毕或不再执行之日起,计算其缓执行期间。”(日本《刑法》第27条之2)
1. 部分缓刑之对象:依据上开条文第1项第1款及第2款之规定,部分缓刑之对象,包括“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但暂缓执行其刑之全部者”,亦即,其对象系没有自由刑前科之初次入监者。此外,依同条项第3款之规定,“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自执行完毕或免除其刑之日起,五年以内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亦可成为部分缓刑之对象。
本条文系针对未曾接受设施内处遇者(初入者)而来规范刑之宣告中一部缓刑一部执行之情况。在条文中虽未曾明文规定初入者,但依第1项第1、2、3款规定,可以得知系针对初入者。由于考虑其违犯较为轻微之罪,且一部宣告实刑,一部则宣告缓刑,在其中承认其有中间刑事责任之情况。一部分缓刑一部分执行系考虑使受刑人负担其刑事责任,此外亦结合设施内处遇与社会内处遇之效果,追求防止再犯以及改善更生之制度。一部分缓刑之要件以受三年以下惩役、禁锢之宣告为基础,另符合第1项第1款(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第2款(虽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但暂缓执行其刑之全部者)、第3款(虽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自执行完毕或免除其刑之日起,五年以内未曾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者)之情形时,得予以一部分缓刑。
2. 部分缓刑之期间起算:依同条第2、3项为判断。第2项为依前第1项规定暂缓执行之刑之一部分者,执行其未暂缓执行部分之期间,自该部分期间执行完毕或该部分执行失效之日起,计算其缓执行期间。第3项规定则在第2项之情况中,讨论其他应执行之惩役或禁锢时之情况时,其缓刑期间之计算,则自该他执行之惩役或禁锢执行完毕或执行失效之日起计算。
(三)部分缓刑中之必要撤销
有关部分缓刑之必要撤销,其规定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销刑之一部缓执行之宣告。但在第三款之情形,受缓刑宣告者有第二十七条之二第一项第三款所揭之情形,不在此限:
一 在缓刑期间内更犯罪,而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时。
二 缓刑宣告前所犯之他罪,有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时。
三 发觉缓刑宣告前所犯他罪有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而未宣告刑之全部缓执行时。”(日本《刑法》第27条之4)
依据本条文之规定,部分缓刑之必要撤销情况,第1款规定在缓刑期间内更犯罪,而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时。由于犯罪非一部缓刑之条件,故该撤销事由系包含在一部缓刑制度中本身内在之内涵。再者,第2款规定缓刑宣告前所犯之他罪,有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时。有关一部缓刑的确定判决前之余罪部分,将受有禁锢刑以上之宣告者作为必要撤销事由。此系由于在一部缓刑一部执行宣告下,就余罪而言,之前的一部缓刑的确定判决所认定适当之设施内处遇与社会内处遇之结合构造便难以维持,因此有必要将之作为必要撤销事由。此外,第3款规定发觉缓刑宣告前所犯他罪有受判处禁锢以上之刑,而未宣告刑之全部缓执行时。只要本条第3款所列之情况系五年以上者,即适用第27条之2第1项第3款之情形,而非适用本条之规定。裁判时实际上并不具备一部缓刑之宣告之要件,亦即之前之一部缓刑宣告为违法,因此事后有必要将之撤销,此亦与第26条第3款同其趣旨。
(四)部分缓刑中之裁量撤销
有关部分缓刑之裁量撤销,其规定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撤销刑之一部缓执行之宣告:一在缓刑期间内更犯罪,而受判处罚金者。二依第二十七条之三第一项规定所交付之保护观察,不遵守应遵守之事项者。”(日本《刑法》第27条之5)
依据前条部分缓刑之必要撤销条件规定,相对于此,本条则规范部分缓刑之裁量性撤销。本条与第26条之2第1、2款相对应。一部缓刑确定后,直到缓刑期间经过之间,再犯科处罚金之刑者,定为裁量性撤销之事由。再者,第2款则是依照第27条之3第1项刑之部分缓执行情况下,在缓刑期间内交付保护观察时,如受缓刑人不遵守交付保护观察所应遵守之事项时所产生之法效果。受一部缓刑宣告之受宣告人若有进一步增强之犯罪倾向时,对其提高社会内处遇之实效性便显重要,故要求其遵守特定事项,以强化其社会内处遇之表现。
(五)部分缓刑中撤销之其他缓刑撤销
有关部分缓刑中撤销之其他缓刑撤销,其规定如下:“依前二条规定撤销禁锢以上刑之一部缓执行之宣告时,缓刑中其他禁锢以上之刑,亦应撤销其缓刑之宣告。”(日本《刑法》第27条之6)
本条之规定系对应于第26条之3之规定。撤销禁锢以上刑之一部缓执行之宣告时,缓刑中其他禁锢以上之刑,亦应撤销其缓刑之宣告。
(六)部分缓刑期间经过之效果
有关部分缓刑之裁量撤销,其规定如下:“刑之一部缓执行期满,刑之一部缓执行之宣告未经撤销者,以其未缓执行之惩役或禁锢部分之刑期,减轻惩役或禁锢之刑期。此种情形,该部分期间执行完毕或不再执行之日,视为执行完毕之日。”(日本《刑法》第27条之7)
依第27条规定,刑之全部缓执行之期间经过后其刑之宣告便失其效力。本条系规定部分缓刑部分执行时,部分缓执行之期间经过后,可将未受到缓执行之惩役或禁锢为刑期判断之期间加以减轻。于此情形中,惩役或禁锢之刑期执行终了或免受执行之日即服刑终了。
(七)药物使用者或单纯持有毒品者之部分缓刑
对于单纯药物滥用者或单纯持有毒品者之“部分缓刑”要件,则在《有关违反药物使用罪之部分缓刑法律》规定,药物滥用者适用“部分缓刑”制度之要件,与其他类型之犯罪人不同,主要是让药物滥用之累犯仍可成为部分缓刑制度之对象,此系因考虑到药物滥用相较于其他犯罪类型,行为人不易戒治而容易成为再累犯之故。④
对于保护观察之规定,亦因应是否为上述毒品相关之犯罪而有所区别。若是一般类型之犯罪,对于初次入监之受刑人,在部分缓刑期间法院得依裁量决定是否命付保护观察,但药物滥用者则一律应付保护观察。
三、假释制度之梗概
(一)假释之条件
有关假释之规定如下:“受判处惩役或禁锢而有悛悔之情状者,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一,无期徒刑逾十年,得依行政机关之处分,暂时假释。”(日本《刑法》第28条)
本条文系规定假释之要件,以往称为“暂时出狱”。2003年《监狱法》修正,将监狱改为刑事设施后,暂时出狱便改称为假释。假释之形式要件如:对象为受科处惩役或禁锢,且监禁于刑事设施之中,接受刑之执行者。其许可条件为刑之执行逾一定期间,有期徒刑三分之一,无期徒刑逾十年之期间条件。实质要件,则须有悛悔情状。
(二)假释之撤销
有关撤销假释之规定如下:
“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撤销假释之处分:
一 假释中更犯罪,受判处罚金以上之刑者。
二 假释前曾犯他罪,而受判处罚金以上之刑者。
三 假释前之他罪受判处罚金以上之刑,并应执行者。
四 未遵守假释中应遵守之事项者。
Ⅱ 受刑之一部暂缓执行之宣告,而该刑受假释处分之情形,在假释中受撤销该缓执行时,该假释处分失其效力。
Ⅲ 撤销假释之决定时,依前项规定而使假释处分丧失效力者,其出狱中之日数不算入刑期内。”(日本《刑法》第29条)
本条规定假释撤销事由及其效果。撤销之形式要件为第1款假释中更犯罪,受判处罚金以上之刑者。第2款假释前曾犯他罪,而受判处罚金以上之刑者。此2款之区别在于实行犯行之时期。所谓受刑之科处,须其判决确定系在假释期间当中,倘若仅止于刑之宣告而尚未确定,假释期间即告终了时,则不得依此两款规定撤销其假释处分。第3款则是在假释前便已犯罪且已告确定应予执行者。由于本款以应予执行为要件,故罹于时效或执行终了等无法执行或无执行之必要者,皆非撤销假释处分之事由。
假释撤销时,须执行其残余之刑期,如假释于残余刑期间未受撤销者,则刑之执行终了。但一部假释时,当该假释受到撤销,则该撤销处分失其效力。而第3项明文规定假释受到撤销而其处分失其效力者,假释中刑期之进行不算入刑之执行中。
(三)假出场之条件
有关假出场之规定如下:
“Ⅰ 受判处拘役者,依情况随时得依行政机关之处分,准许假出场。
Ⅱ 因不能缴纳罚金或科料而受留置者,亦同。”(日本《刑法》第30条)
本条文对于受拘役或因不缴纳罚金、科料而留置于劳役场所者,得依行政机关之决定而暂时出场,亦称为“假出场”。假出场之要件与假释不尽相同,无须以收容于设施中最低期间为要件,随时皆可受假出场之处分;实质要件,亦不以有悛悔之情状为必要,而依情况即可。此处之“情况”,具体化于“社会内处遇规则”中所叙述之“身心的状况、收容或留置之期间、社会之情感或对其他事情之考虑认为相当时”。⑤假出场时,即使未规定有应遵守事项,亦无须交付保护观察,且无撤销事由或再收容之相关规定,因而尽管附有暂时之名称,但实际上则为完全释放。
四、缓刑及假释之基本理论
(一)缓刑之基本原理
缓刑制度主要系避免科刑所产生之弊害,而且在违反条件之情形,依执行刑之心理强制而使犯罪者改善更生。缓刑不仅系科刑而已,亦系刑之附随处分。有关缓刑制度之目的,除维持宣告刑之应报效果外,亦避免无用之行刑,而合理地追求犯罪者自力更生,此即刑罚目的之“特别预防”。
付保护观察之缓刑,系显示教育原理之制度,例如法院裁量给予犯罪者付保护观察之缓刑,基于被告之环境等情状,实施保护观察之辅导援助与指导监督,期待被告改善更生。付保护观察之缓刑,若是单纯缓行刑,则会有再犯之虞,为了防止再犯,必须实施保护观察,如此可更进一步促进犯罪者之改善更生。
(二)假释之理论基础
在符合假释条件中“悛悔情状”之情形,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一、无期徒刑逾十年,得许假释(日本《刑法》第28条)。准许假释之具体基准,依“有关犯罪者及非行少年社会内处遇之规则”(2008年法务省令第28号)第28条“有悔悟之情形及改善更生之意欲,无再犯之虞,且付保护观察被认为改善更生系属相当者。但社会情感无法肯定时,不在此限。”⑥之规定。
关于假释制度之机能及目的,有恩惠、刑的个别化、社会保护、改善更生等四种。⑦所谓恩惠,系指对在刑事施设内有良好行为之受刑者给予褒奖而言。所谓刑的个别化,系指因应受刑者之状况变化,排除不必要的拘禁,实现个别正义而言。所谓社会保护,并非将受刑者之拘禁状态完全地释放,而系一方面依保护观察防止再犯,另一方面亦使受刑者习惯社会生活,当有再犯危险时,立即以再收容来保护社会有犯罪之危险。所谓改善更生,系指将受刑者之拘禁期间止于必要的最小限度,残刑期间将施设内生活移至社会内生活,以保护观察来指导监督而导向自立之目标。
有关假释之法性格,学说上认为与其说是假释后之处遇,其不过是附条件之释放而已,而有以下二种见解,其一、仅仅系解除刑事施设之拘禁,法律上之地位系视为在服刑,因此假释只不过是变更刑之执行形态而已(刑执行之一种形态),其二、假释系暂缓执行残刑期间(刑之一种形态)。前者系属通说之见解。⑧
(三)撤销缓刑与撤销假释之相异性
因违反遵守事项而撤销保护观察之缓刑,系由接受保护观察所所长提出、检察官声请,而由法院来决定。接受撤销缓刑者系在刑事施设内服当初被宣告之刑期。有关保护观察所所长提出撤销缓刑之基准,系依《有关犯罪者及非行少年社会内处遇之规则》第100条“考虑保护观察之实施状况等,认为违反遵守事项之情节系属重大者。”之规定,此与撤销假释之提出(同规则第91条),明显并不相同。
因违反遵守事项而撤销假释,系由保护观察所所长提出,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来决定。接受撤销假释决定者,残刑期间系在刑事施设内服刑。有关提出撤销假释之基准,依上开规则第91条“考虑违反遵守事项之情状、保护观察之实施状况等,为了改善更生而认为无继续保护观察之特别情形时。”之规定,亦即,保护观察所所长针对假释者违反遵守事项之情形,首先应检讨撤销假释,若有特殊之情状,可例外地不提出撤销假释之声请。因此,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依撤销假释许可之基准,认为撤销假释之声请系属相当时,应撤销假释(同规则第96条)。
撤销缓刑与撤销假释之提出或接受声请之撤销,其判断基准之法条规定明显并不相同。付保护观察缓刑之撤销,仅限于违反遵守事项之“情节重大时”(日本《刑法》第26条之2第2款),而假释之撤销并无“情节重大”之要件(日本《刑法》第29条第1项第4款)。
因违反遵守事项而撤销付保护观察缓刑,有二种思考方向:其一、违反遵守事项系违反付保护观察缓刑宣告缓刑时之条件,因为破坏判决之先提条件,故必须严格地追究责任,此种撤销缓刑系基于“应报或惩罚”之思考;其二、违反遵守事项之问题点在于改善更生之契机,撤销缓刑系保护观察之最后手段,此种撤销缓刑系基于“教育或保护”之思考。有学者认为,撤销缓刑应以教育或保护之思考为基本,再加上应报或惩罚之思考。⑨
五、缓刑及假释之保护观察
日本保护观察之处分,主要系以非行少年及犯罪者之改善更生为目的之社会内处遇。有关保护观察制度之规范内涵及处遇措施,主要系以《更生保护法》⑩来加以规范。其立法目的为“本法主要系针对犯罪者及非行少年实施社会内适切处遇,预防其再犯罪或消除该非行,使该等保护观察者以社会善良的一员而自立、扶助其改善更生,同时在期望恩赦的适正运用之外,亦实行促进犯罪预防活动,依此而保护社会、增进个人及公共为目的。”(《更生保护法》第1条)。
(一)全部缓刑之保护观察
有关全部缓刑之保护观察,其规定如下:
“Ⅰ 前条第一项之情形,得在缓刑期间内交付保护观察。前条第二项之情形,在缓刑期间内交付保护观察。
Ⅱ 依前项规定之交付保护观察,得依行政机关之处分暂行解除。
Ⅲ 依前项规定之暂行解除保护观察,针对前条第二项但书及第二十六条之二第二款规定之适用,在撤销该处分前,视为未交付保护观察。”(日本《刑法》第25条之2)
本条系保护观察之基本规定。对于初次之缓刑宣告者,依法院之裁量,交付保护观察;对再次之缓刑宣告者,则须交付保护观察。一般而言,存在有与缓刑相当之情状,加上因保护观察所得之指导监督与辅导援助,能够有助于促进受刑人之改善更生时,便可考虑适用交付保护观察。而交付保护观察之决定,须与判决宣告同时为之(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3条第2项)。有数个刑之宣告时,分别均宣告缓刑,可否只对其中之一个宣告交保护观察,如系初次受缓刑宣告者,系依法院之裁量,故没有否定之理由。至于保护观察之期间,通常与缓刑之期间相同。
(二)部分缓刑之保护观察
有关刑之部分缓执行规定如下:
“Ⅰ 前条第一项之情形,得在缓刑期间内交付保护观察。
Ⅱ 依前项规定之交付保护观察,得依行政机关之处分暂行解除。
Ⅲ 依前项规定之暂行解除保护观察,针对第二十七条之五第二款规定之适用,在撤销该处分前,视为未交付保护观察。”(日本《刑法》第27条之3)
依据本条之规定,以第27条之2一部缓刑时,有关交付保护观察为对象。在可得一部缓刑一部执行之情况,一旦开始起算缓刑期间,依本条第1项规定即可交付保护观察。再者,本条第2项则是依第1项所为之交付保护观察中,行政机关得处分暂时解除该保护观察。此外,本条第3项则就第2项之暂时解除保护观察之情况,于适用下述第27条之5第2款规定,于行政机关之处分受撤销后,视为该条款中所谓之未交付保护观察之状态。
“部分缓刑”制度已经于2016年6月开始施行,在日本有支持者,然亦有批评者,支持此制度者认为适当之运用将有利于犯罪者之社会复归,倘若能增设判决前调查制度,将更能使法官妥适判断社会内处遇之必要性。相对地,亦有认为此制度将会对犯罪人产生不利益,因为实刑部分执行完毕后、缓刑部分开始时,受保护观察之可能期间变长了,甚至可长到五年,而且此制度之实施亦可能破坏现有之假释制度、实质上阻碍了假释制度之改善与运用。11
(三)假释之保护观察
有关许可假释者,应付保护观察之处分(《更生保护法》第40条)。假释之保护观察,系以犯罪者之改善更生及社会复归为目的,在使犯罪者过社会中通常生活之同时,指导及监督其必须遵行遵守事项,以及实施必要之辅导与援助,属于社会处遇之重要手段。实施保护观察之政府机关,系保护观察所,而专任之保护监察官在得到官署、学校、医院、公共卫生福祉机关之必要援助及协力下,对被保护观察者实施无给职民间志愿者之协力,实施指导、监督、辅导与援助(《更生保护法》第29条、第30条)。
有关《更生保护法》所规范之内容,包含保护观察之对象、保护观察之实施方法、一般遵守事项、特别遵守事项、特别遵守事项之特例、特别遵守事项之设定及变更、特别遵守事项之取消、一般遵守事项之通知、特别遵守事项之通知、生活行动指针、指导监督之方法、辅导援助之方法、对保护者之措施、保护观察之管辖、保护观察之实施者、应急之救护、出庭之命令及拘提、保护观察目的之调查、被害者心情之传达(同法第三章保护观察第一节通则第48条)。此外,针对有药物依存之保护观察对象亦以特则规定,其内容包含保护观察之实施方法、指导监督之方法(同法第一节之二第65条之2、第65条之3、第65条之4)。
依《更生保护法》第三章保护观察第48条之规定,保护观察之对象包含以下四种:(1)少年法第24条第1项第1款所规定之付保护处分者(保护观察处分少年);(2)本法第42条所规定从少年院假退院者准用第40条之付保护观察者(少年院假退院者);(3)依本法第40条所规定付保护观察之假释者(假释者);(4)刑法第25条之2第1项、刑法第27条之3第1项或《违反使用药物等罪之部分缓刑法》第4条第1项之付保护观察者(付保护观察之缓刑者)。
针对保护观察之处遇,该对象者有依遵守事项而为一定行动之义务或禁止一定行动,同时实行指导监督及辅导援助之基本构造。有关遵守事项,依法律规定有一般遵守事项(同法第50条)与为了对各保护观察对象者之改善更生而在特别必要之范围内具体规定之特别遵守事项(同法第51条)。若保护观察对象者有违反遵守事项之情形时,则有撤销假释等之不利益处分(不良措置)。有关保护观察之指导监督,有以下三种方法:(1)依面试等方法保持与保护观察对象者之接触,把握其行为情状;(2)对保护观察者应遵守一般及特别遵守之必要指示或采取必要措施;(3)实施为了改善特定犯罪倾向之专门的处遇(同法第57条第1项)。有关辅导援助,主要系以援助适当住居或其他住宿场所及回到该住宿场所居住、扶助接受医疗及疗养、辅导职业及扶助就业、扶助得教养训练之手段、调整及改善生活环境、实行使其适应社会生活所必要的生活指导等七种方法(同法第58条)。具体而言,例如,针对因饮酒犯罪之保护观察对象,依遵守事项而禁止其饮酒,同时亦实施持续性接见维持戒酒之指导监督、介绍戒酒之自助机构、斡旋就业之辅导援助。
以往,针对受保护处分之少年,实施保护观察之处遇,期待能达到“健全之教养”(日本《少年法》)。然而,针对受刑事处罚之成人,其所实施之保护观察,几乎未讨论基于刑罚之原理。因此,必须论述刑罚论后,检讨假释者与付保护观察缓刑者之保护观察处遇的相异,二者之相异应论述以下三点:(1)刑罚之基本原理系由应报的原理与教育的原理所形成。在宣告刑中,应以应报的原理为优先,而在犯罪者处遇中,应将教育的原理列为优先考虑。(2)缓刑系属于刑之付随处分,其虽重视教育的原理,但假释系刑执行之一种形态,其亦重视应报的原理,基于两者之相异性质,必须由保护观察官来执行处遇。(3)保护观察官除应意识保护观察之假释者与付保护观察之缓刑者之不同外,亦应注意保护观察结构之积极机能。
六、结论:撤销缓刑与撤销假释之实务运作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刑罚之本质,系以应报原理为基础(应报刑主义),再加上期待改善更生为目的之教育原理(目的刑主义),而针对宣告刑犯罪者所实施之保护观察处遇,系以教育原理为最主要考虑。12为了呼应教育原理,在刑事施设内对犯罪者实施矫正处遇之改善指导或教科指导等,在社会中实施保护观察之处遇。因此,在法律上,明定保护观察系以防止再犯及改善更生为目的之社会内处遇,保护观察系属于基于教育原理之制度。然而,对犯罪者给予缓刑或假释,所实施之保护观察,其法律性质上仍然有所不同。由于假释系行刑之一种形态,故针对假释者,系以应报原理为基础所必要实施之行刑中措施。相对地,有关付保护观察之缓刑,缓刑系属于刑之附随处分,付保护观察之决定系为了犯罪者之改善更生,若将假释与缓刑相比较,则缓刑主要系重视教育之原理。以下,针对日本缓刑与假释制度在实施保护观察处遇时,有关撤销缓刑与撤销假释二者在判断上之基本思考。
(一)违反遵守事项撤销缓刑之实务见解
违反遵守事项违反而撤销缓刑之“情节重大”之判断,在实务判决中,必须符合以下三项:(1)有违反遵守事项之事实者;(2)违反遵守事项之内容,系从本人之生活态度整体来观察,有自力更生意欲不足或欠缺之原因者;(3)纵然继续实施保护观察之指导援助亦难期待有自立更生之状况者。
《更生保护法》施行后之裁判,有关违反专门处遇计划所规定特别遵守事项之接受讲习义务而撤销缓刑之案例(2010年3月5日东京高等裁判所裁定)。所谓专门处遇计划,系指法务大臣所规定基于专门知识改善特定犯罪倾向之体系化处遇,以特别遵守事项而付予接受讲习之义务。具体而言,有性犯罪者处遇计划、药物犯罪者处遇计划、暴力防止计划及防止饮酒运转计划四种(2008年法务省告示第219号)。若未出席专门处遇计划,则属于违反遵守事项。
在2010年3月5日东京高等裁判所之裁定中,系针对药物犯罪处遇计划中遵守事项之接受讲习者,该犯罪者不仅未参加该讲习,而且未居住在所申报之住居内,亦未接受保护观察官或保护司之面谈,仍然过着案件发生当时之放荡生活,因此被认定系属“情节重大”。在《更生保护法》施行后,被以违反遵守事项而撤销缓刑者,此裁判系属唯一之案例。
(二)撤销缓刑以“情节重大”为要件之理由
付保护观察缓刑之撤销,由于遵守事项之规定过于抽象,故附加“情节重大”之要件,此种见解有以下二个问题,第一、在《更生保护法》施行以前,规定假释者之保护观察者系犯罪者预防更生法,该法亦规定假释者之遵守事项为“保持良好行为”(同法第34条第2项第2款)。因此,无法说明唯有对付保护观察缓刑者规定“情节重大”。第二、《更生保护法》施行后,《犯罪者预防更生法》及《缓刑者保护观察法》同时被废止,“保持良好行为”改以“保持不再犯罪或消除非行之健全生活态度”之具体用语(《更生保护法》第50条第1款),而特别遵守事项,其违反仅限于成为不良措施为前提(《更生保护法》第51条第2项)。目前,针对付保护观察缓刑之撤销,系以“情节重大”为要件,有关遵守事项之抽象性,无法说明撤销假释与撤销缓刑之不同要件。
付保护观察之缓刑,系以教育原理为优先考虑之制度,故缓刑之撤销亦必须以教育之观点来加以判断。如同前述,学说上亦认为针对缓刑之撤销亦应以教育或保护之思考为基础,裁判例针对“情节重大”,亦以保护观察是否自立更生之教育观点来判断。因此,针对“情节重大”为撤销缓刑要件之理由,在撤销缓刑处分之际,从教育观点来慎重判断系属适当之解释。
(三)以违反遵守事项为由撤销假释之解释
针对假释者,法律上并无以“情节重大”为撤销假释之要件,而当假释者违反遵守事项时,原则上系提出假释撤销之声请(《有关犯罪者及非行少年社会内处遇规则》第91条)。再者,以违反遵守事项违反而撤销处分,假释比缓刑更多,因此积极运用撤销假释处分,系因应假释以应报为基础之行刑的一种态样。
然而,遵守事项有各种不同之种类,具有个别相异之机能。例如,诚实接受保护观察官或保护司之指导监督、住居之报告、居住在所提报之居所、变更居所或旅行必须经过许可等遵守事项(《更生保护法》第50条),系实现保护观察之机能。而与素行不良者之交际、禁止浪费或饮酒过度之遵守事项(《更生保护法》第51条第2项第1款),系禁止再犯主要原因之行动。再者,规定就业、通学或接受专门处遇计划讲习之遵守事项(《更生保护法》第51条第2项第2款、第4款),主要系为了改善更生而有益或必要行动之义务。因此,由于在遵守事项中具有相异之机能,故违反遵守事项之措施,其运用亦应基于各种而加以检讨。
(责任编辑:苏 婷)
①《更生保護のあり方を考える有識者会議》报告书《更生保護制度改革の提言―安全・安心の国づくり、地域づくりを目指して―》,同会議の議事録及び報告書の全文は¸法務省HPで閲覧できる。http//www.moj.go.jp/shingil/kanbou_kouseihogo_index.html,下载日期:2017年3月11日 。
②日本《刑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2013年6月19日法律第49号公布、2016年6月1日开始施行)。
③日本《薬物使用等の罪を犯した者に對する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に関する法律》(2013年6月19日法律第50号公布、2016年6月1日开始施行),其内容计有5条,包含第1条立法旨趣、第2条定义、第3条部分缓刑之特则、第4条部分缓刑中保护观察之特则、第5条部分缓刑必要撤销之特则。
④参见日本《薬物使用等の罪を犯した者に對する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に関する法律》(2013年6月19日法律第50号)第2条定义及第3条部分缓刑之特则。
⑤参见日本《犯罪をした者及び非行のある少年に対する社会内における処遇に関する規則》(2008年4月23日法务省令第28号)第29条(仮出場許可の基準)“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仮出場を許す処分は、拘留の刑の執行のため刑事施設に収容されている者又は労役場に留置されている者の心身の状況、収容又は留置の期間、社会の感情その他の事情を考慮し、相当と認めるときにするものとする。”
⑥参见日本《犯罪をした者及び非行のある少年に対する社会内における処遇に関する規則》第28条(仮釈放許可の基準)第三十九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仮釈放を許す処分は、懲役又は禁錮の刑の執行のため刑事施設又は少年院に収容されている者について、悔悟の情及び改善更生の意欲があり、再び犯罪をするおそれがなく、かつ、保護観察に付することが改善更生のために相当で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にするものとする。ただし、社会の感情がこれを是認すると認められないとき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⑦参见勝田聡、羽間京子:《仮釈放者と執行猶予者の保護観察処遇の相違について——刑罰の基本原理を踏まえた考察―》,载《千叶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第61卷),第347页。
⑧参见[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10年版,第540页。
⑨参见勝田聡、羽間京子:《仮釈放者と執行猶予者の保護観察処遇の相違について——刑罰の基本原理を踏まえた考察―》,载《千叶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第61卷),第348页。
⑩《更生保护法》(2007年6月15日公布、2008年6月1日开始施行)系整合《犯罪者预防更生法》(1949年5月31日法律第142号)与《执行犹豫者保护观察法》(1954年4月1日法律第58号)二种法律而制定。
11参见太田達也:《自由刑と保護観察刑の統合:アメリカの新しい二分判決制度を手掛かりとして》,载慶応義塾大学法学部编:《慶応の法律学:刑事法》第27页、30页。
12余振华著:《刑法总论》,三民书局2013年版,第497~498页。
D931.34
A
1674-8557(2017)03-0030-10
2017-03-18
本文系中华司法研究会2016年一般课题“涉台港澳犯罪人管制、缓刑、假释研究”、福州大学2016年科研启动经费项目“涉台犯罪人缓刑假释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190-51039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余振华(1952-),男,福建晋江人,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日本明治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原台湾地区刑事法学会理事长,现任台湾地区比较刑法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