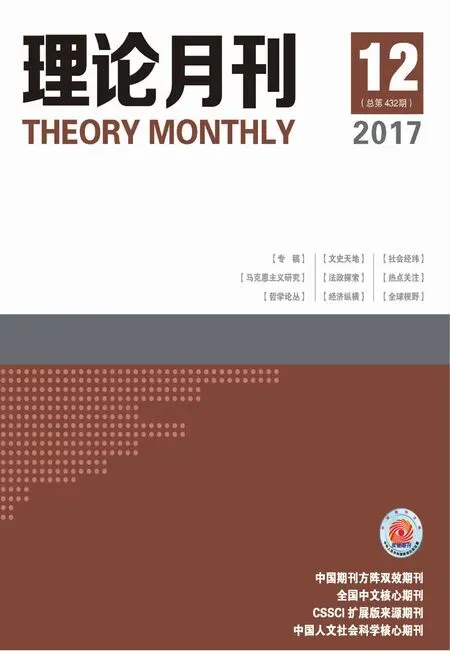栖居于断裂的历史链条处找寻他者
——论福柯对尼采谱系学的理解与运用
2017-03-07马成昌
□马成昌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栖居于断裂的历史链条处找寻他者
——论福柯对尼采谱系学的理解与运用
□马成昌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尼采与福柯对谱系学的理解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都批判传统历史观的起源与目的概念,强调事件发生的独特性、历史性、偶然性与断裂性。福柯由尼采对道德谱系的分析生发出了权力谱系的理论,认为权力构成了现代社会运作的核心力量,形成了独特的知识—权力分析方法;由尼采对教士道德异化现象的批判发展出对整个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以《规训与惩罚》为标志,福柯进一步发挥了尼采的谱系学,并赋予新的意义和研究模式。他将尼采对教士道德的分析运用至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引入了监狱的规训模式,从而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体;同时发展了尼采不同道德谱系造就不同文明演进的观点,认为不同的权力谱系制造不同的社会个体。
福柯;谱系学;尼采
与德里达、德勒兹相比,福柯没有专论尼采的著作,1971年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是他唯一阐述尼采的文章,但其中却包含着对尼采最深刻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尼采的谱系学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最出色的运用,这在他由知识考古学转向权力谱系学的首部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谱系学就是要消除强加给历史事件的各种累赘,强调历史发生的偶然性、断裂性与共时性。
1 福柯与尼采谱系学理解之异同
Généalogie(谱系学)由词根 alogie与 géné构成,前者意指知识,后者意指出生,所以,从词源学来讲,该词是关于出生的知识。所以,有的学者将其翻译为“出生学”或者“出身学”。由于这样翻译可能在整体上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人们普遍采用“谱系学”这一译法。但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所说的谱系学概念与尼采、福柯所指的谱系学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传统谱系学是对祖先之起源、家世与血统之演变的追寻,探索家族世系之连续性,即强调连续性。而尼采与福柯则强调事件发生之偶然与断裂,即强调的不是事件是怎样接续下来的,而是强调事件是怎样突然出生或出现的。“谱系学的出发点是开端和事故的多样性、扩散性、偶然性:它无论如何都不会试图追溯时间以便重建历史的连续性,相反它试图恢复独特性之中的事件。 ”[1]69在尼采那里,Ursprung (起源)等同于Entstehung(出现)、Herkunft(出身)、Abkunft(来源)、Geburt(诞生)。但形而上学历史观却在与后面这些词完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Ursprung(起源)。在尼采与福柯看来,Ursprung(起源)只是一种虚构,是形而上学家将鲜活的历史事件加以形式化、规范化的结果,他们以一种无时间性的先验概念来统摄人们生存中实际发生的事件。《论道德的谱系》只在个别处对Ursprung(起源)与Herkunft(出身)进行了区分,多数情况相互替代使用。谱系学就是要消除强加给历史事件的各种累赘,强调历史发生的偶然性、断裂性与共时性。Herkunft(出身)代表着一种时间性与境遇性的出现,它不具有高贵血统,不代表任何本质,它只是在时间中生成,而起源则代表一种无时间性的观念。所以,福柯说:“我们将谱系学定义为对‘出身’(Herkunft)和‘出现’(Entstehung)进行的研究。 ”[2]292
从整体上说,尼采与福柯在对谱系学的理解上是一致的:二者都否认传统单线条的必然历史观,认为历史不受任何超验的力量所主宰,它仅仅是一个性质迥异的各种偶然原素互相交织的复杂系统,因此应打破传统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霸权地位,在谱系学的视野中理清历史沉渣,修正历史误区,重新给历史事件以应有的位置。但二者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有待澄清。首先,尼采的谱系学主要是对道德偏见起源的分析,而福柯则将这种道德谱系学转化为一种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将其应用到对各种事件及其关系的考察,重新确立事物之间的细致脉络。作为一种方法,它拒绝接受传统哲学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以及作为科学方法的因果律;拒斥历史事件中的统一性、连续性叙事风格,而以微观视角考察历史与社会发展中的局部领域,特别是那些长期被曲解、被拒斥、被贬低、被遗忘、被抛弃的各种话语体系,如犯罪、疯癫、监狱、性。福柯关注的正是这些不合法的、不连续的、不被承认的、不具全局性的知识,从而反对看似严整和谐的理论,消除具有等级秩序的知识体系,强调知识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从而把位于非中心地带、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的不合法知识解放出来,以争取与所谓的合法知识具有平等的地位。其次,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以观念虚构的方式对人的道德作了类型学的划分,即奴隶道德、教士道德与主人道德、高贵道德,从而凸显一种旨在反基督教禁欲主义古典精神类型的至高无上地位,而福柯则消除了尼采的理论预设以及预言家式的立场从而将其转换为一种客观的审美立场。
“谱系学”概念来自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因此,在具体阐述福柯对尼采谱系学的理解与运用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著作中与论题有关的诸关节点加以概述,以阐明二者在思想上的接续关系。《论道德的谱系》以文明与本能的对立为出发点,提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道德观,即教士道德与高贵道德,前者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者以希腊悲剧为代表。教士道德的传统源远流长,由苏格拉底开始,继而是基督教道德,接着是启蒙运动中的卢梭与康德。教士道德压抑人类健康的本能,它用来世统治现世,将体现人之本能的酒神精神视为原罪的根本,继而对其加以惩罚和规训。尼采认为,只有使酒神与日神复活方能摆脱精神与时代的虚无,但在西方历史上,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几经复活,却皆因教士道德的阻止而遭失败:文艺复兴的第一缕曙光被宗教改革所遮蔽;17至18世纪古典人文主义的崛起被卢梭与康德所压制;19世纪的技术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使这种复活更加不可能,陷入虚无主义深渊不能自拔。
在尼采看来,教士道德如何成功做到了对自然本能的清除?为此他做了心理学的分析。教士将本能和负罪心理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能从根本上说是罪恶的,将原罪看作是坏良心的主要特征,并将其精雕细琢,成为统治人的主要武器与隐秘机制。坏良心是一种有序的精神扭曲的运行机制,将人的本能内化为负罪心理,它包括原罪、内疚、惩罚、救赎、良心谴责、忏悔等精神要素。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两种负罪,即主动担当的英雄式负罪,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即是典型,这种主动负罪是一种自然本能的显现,它包括承担、不屈、赠予、友爱、进取等精神因素,通过这些要素卸除掉可能使人产生内疚、怨恨等内化式的负罪心理,在不断地外化中克服,从而使人呈现出自由、愉悦、轻松、豁达、健康、高贵自然的生存状态。在希腊悲剧中负罪表现为释放本能的积极的创造性力量,并不压抑本能,也不产生深度记忆,这便是外化力量、长于遗忘的高贵道德。“唯有作为审美现象,此在与世界才是永远合理的。”[3]48而教士道德却内化痛苦,强化记忆。具体来说,教士道德将“欠债要还”的古老心理作了一种观念转化:出于仁慈,上帝派耶酥拯救人类,被钉于十字架,耶酥为人类抵罪,结果在人的良知中却欠下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它与原罪概念相连,并且通过种种暴力手段让人铭记。“在这样一种记忆的帮助下,人们最终会‘达到理性’!——哈!理性,严肃,对于诸般情绪的驾驭,这整个阴暗的事情,被叫做思索,人类的所有这些特权和瑰宝:它们昂贵的卖价多么合算哪!在所有‘好事物’的根底里有多少血和战栗啊! ”[4]63在尼采看来,理性史就是理性征服本能的残酷历史,它是基督教教士道德的变异。本能即原罪,暴力惩罚、规训本能。尼采认为,惩罚的功效并没是使人性有所改进,而是使人性更加驯服。它使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使人的恐惧不断增长,使人的本能不断受到压制。尼采关于两种道德的对立、理性对本能的残酷压制、利用原罪观念施加暴力的理论在福柯那里都引起了强烈共鸣。福柯认为,整个现代文明史无非是知识与权力联手驯服灵魂的残酷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教士道德的延续。
2 福柯对谱系学的理解
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通过对尼采谱系学的阐释,既批判了以往的形而上学历史观,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历史观,又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理论。这一理论反对传统历史学中有关目标、起源的理论预设,反对历史社会演进中的单向进步性,追踪事件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细节,力图发现被传统的整体历史观所遮蔽的那些历史事件,使它们能够重见天日,使它们不再是人类历史舞台所上演的一幕幕大团圆喜剧(进步性、目的性)的不和谐因素而被随意裁制、删改与抛弃,从而呈现它们之所是的本真样态。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谱系学批判总体历史观中的无时间性的起源与目的概念,强调事件发生的独特性与历史性。福柯认为,谱系学并不是单纯表示物种的结构、演化、分类及其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谱系树,而是尼采所提出的强调事件发生的断裂性与偶然性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作历史的宏大叙事,一切从细节处着眼,“谱系学是灰暗的、 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2]279,强调以独特的视角处理这些原始资料,在对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时拒绝对它作任何目的性解释,而只强调它的独一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它的远大前程,都能成为某一伟大目标的得力助手,但我们必须要呈现它,展示它,而不是为了某种高贵的目的而掩盖它,埋葬它。所以,谱系学“反对各种理想意义和无尽的目的论作元历史式的布展(deployment)。它反对寻求‘起源’。”[2]280整体历史观把所有事件都有序地编入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服务于某一超验的目的,从而彰显它们的历史意义,而不为这一目的服务或有违于这一目的的事件则统统将其抛入黑暗的深渊。所谓深渊就是由于未能服务于一种合理的历史序列而被真理之光所掩盖的那些历史事物所处的隐匿之所。按照福柯的观点,谱系学就是要力图甄别那些历史事件的独一性,如拿破仑就是拿破仑而非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工具。我们通常所见的历史事件未必是真实的,因为它只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服务,而真正真实的东西,即事件本身的独特性,可能我们是看不见的。谱系学所关注的就是这些居于深渊之所、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整体而只为自己存在的历史事件,即作为独特的“他者”而存在的事件。它抛弃了形而上学概念,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一个独特的他者,它们本无本质,所谓本质都是出于一种外在于自己的目的论概念逐渐构建起来的。谱系学揭示被那些整体历史观所遮蔽的每一历史事件所表现的完全不同于以前的面相,重新发现它们的独特性,说明它们不再是某一伟大历史目的中的一个章目、一个环节,它们只是它们本身,没有所谓具有本质性、目的性、起源性特征的另一个“我”。福柯忠告说,“如果谱系学家去倾听历史,而不是信奉形而上学,他就会发现事物背后‘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并非一种无时间的、本质的秘密,而是这样的一个秘密,即这些事物都没有本质,或者说,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点点的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 ”[2]282由上观之,在关于事物产生的独特性与异质性方面福柯明显遵循了尼采的思想理路,因为在尼采看来,甚至理性都是偶然产生的结果,而真理与科学只是学者们的激情与争斗所致,所谓自由则完全是统治者的一种发明而已。
其次,谱系学反对历史研究的高贵起源论,强调历史开端的卑微与事件发生的偶然。这一问题承接上一理论而来。人们通常认为事物的起源是完美无缺的,它们神圣无瑕,光彩照人,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标。而事实上,“历史的开端是低贱的”[2]283。 目的论历史观总认为它所挑选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所谓的 “高贵起源”,如理念、上帝、绝对精神等,起源即是真理之所,它们在开端上完美无缺,具有非肉身性、非时间性与非空间性。世界万物皆由它产生,故不及它高贵,事物产生、变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而历史发展的过程就表现为对这种堕落的拯救,从而走向高贵的开端。而福柯认为,历史是“一部表面上写的是我们称之为真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历史”[2]284。任何时代所普遍承认的真理其实都可能是错误的。尼采的谱系学强调事件的出现(Entstehung)与出身(Herkunft)而非目的意义上的高贵起源(Ursprung)。在这三个词中,传统哲学将前两个词都错误地理解为后一个词,这是大错特错。因为出身(Herkunft)意味着来源,而来源则异于非时间性的起源(Ursprung)。从出身(Herkunft)的角度来看,那些所谓高贵的、纯粹的血统其实并不高贵也并不纯粹,它们都是在整体历史的叙事中虚构出来的。就像人们更愿意相信,人是尽善尽美的上帝创造的而不是丑陋的猿猴演变的。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是一个去除杂多与排除异己的过程。谱系学反对的高贵血统论就是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连续性、一致性与和谐性,它有意遮蔽了太多的具有荒谬与丑陋的历史真实。谱系学反对起源而探究事件之来源,它把曾经被编排到一个序列或抛入黑暗中的历史事件重新拆散开来而保持它的独立状态,确证出它们的偶然性与悖谬性,从而揭示出那些始终对我们的生存方式产生决定影响的各种价值观念的虚幻性与荒谬性,告诉我们真理之所不在起源之处,而在偶然之中。“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既不遵循目的,也不遵循机械性,它只顺应斗争的偶然性。”[5]157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自身的异质性,都有自身的来源,这种来源是一些零散破碎的小事件,彼此之间是断裂的离散式组合,而不是传统历史观所美化与虚构的具有本质必然性特征的伟大开端。福柯认为,尼采的“出现(Entstehung)”概念并不是指事件的连续变化,而是指它的别具一格的突然显现。事件的突然涌现是各种力量相互角力的结果。这恰恰与传统强调事物的在场持存性观念形成鲜明对立。以往的线性历史观往往错误地将一个事件的突然涌现看作是历史的光明前途中理所应当的结果,并赋予其之所以这样出现而不是那样出现的某种必然性。在历史的发生中,那些无序的事件就摆在那里,没有所谓的人类光辉的顶点或历史的终结。传统历史学家或形而上学家们似乎始终带着某种神圣的敬畏感仰望着那些高贵的起源,而谱系学则以冷峻的怀疑感审视“弥散和差异”与“野蛮和无耻的混乱”中历史的真实。它在对历史资料的处理上并不像以往的历史学那样,出于一种对起源、目标、进步等形而上学概念的迷恋而有选择性地抽取那些光鲜亮丽的且只为这种写作目的服务的历史资料。传统历史观在阐述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时总是肯定并试图探究这些事件背后某种永恒的纯洁本质。不同于这种从整体、开端、理性之光处对事件做一种有序和谐的历史编排的总体历史观,谱系学专注于每一个个别事件的出生,这种出生往往是低俗卑贱的;专注于传统历史观视之如敝屣因而被抛弃的诸多偶然事件;专注于每个事件开端的细枝末节与小奸小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者。
最后,谱系学反对研究视角的客观性,强调研究视角的主观性,考察实际历史之发生。传统历史观执着于抽象逻辑构造的视角,寻找非时间性的理论支点,这个支点是理念、上帝、绝对精神等,坚信这些概念的客观性与绝对普遍性,进而相信历史前进的最终目的,而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奔向那个永恒实体的线性发展历程的环节。这种历史除了本质、意义与价值这些抽象的概念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真实的历史事件石沉大海,永无天日。这种客观性观点决定了哪些历史事件是存在的,是以哪种形式存在的,从而过滤掉按照这一尺度所衡量的那些无用的事件。谱系学是对这种客观性的爆破、离散与解构,它是一种“分辨、分离和分散事物的敏锐眼光”[2]293,能够看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异质性、时间性与主观性,福柯称之为效果史。这种“效果史”不追求事件发生的基础、终点、稳定性与连续性,而是颠覆诸如终极目标、永恒理性等形而上学的概念预设,呈现出历史事件发生的本真性与偶然性。它专注于每一个不同的历史事件,呈现其所是的本真性,反对将每一个历史事件强行塞进一种目的论运动中,而是让它们从最独特之处显现出来,这就是真正的效果史。而传统的客观历史观则“千方百计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抹去某些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暴露了他们在观察时的地点、时间和立场,以及他们不可抗拒的激情。 ”[2]296它将自己的有限视角转化为无限视角,将主观视角粉饰为客观视角,而尼采与福柯的历史感则否认存在着某种不偏不倚的观察视角。所以,谱系学反对这种普遍、绝对的目的论视角,它承认观察角度的有限性与主观性,不掩饰自身的视角,不探寻本质性的规律,不把自身的有限视角绝对化为上帝视角。
3 福柯对尼采谱系学的运用
在所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中,福柯无疑是受尼采影响最大的一位。但这种影响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有主次之别,而这个“主”当属《规训与惩罚》所探讨的知识—权力的主题。“福柯主要借鉴了尼采关于如何看待权力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见解。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福柯从尼采关于权力、真理与知识的联系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灵感。”[6]39以《规训与惩罚》为标志,福柯承继与发展了尼采的谱系学,并赋予新的意义和研究模式,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它将尼采对教士道德的分析运用至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引入了现代监狱的规训模式,从而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论道德的谱系》考察了不同道德谱系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即不同道德谱系造就了不同的文明演进,福柯由此引申出《规训与惩罚》的主题,不同的权力谱系制造不同的社会个体。福柯的谱系学告诉我们,整个西方历史只是巧合与偶然的结果,只是知识与权力的合谋,权力如何制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总起来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福柯由尼采对道德谱系的分析生发出了权力谱系的理论,认为权力构成了现代社会运行的核心力量,继而形成了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方法。第二,福柯由尼采对教士道德异化现象的批判生发出对整个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第三,福柯由尼采揭示教士道德束缚下本能状态的畸变生发出对变态人的心理特征分析。
《规训与惩罚》基于权力谱系学考察了知识和权力的内在关系,它与传统上将二者看作是无关涉性的观点相反,认为特定的权力产生特定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权力的运用。规训(Discipline)一词就充分诠释了权力和知识的这种内在关联。它身兼二义,既具有纪律与训练之义(权力),又具有学科之义(知识)。所以,它既是权力干涉身体的技术,又是生产知识的途径。权力谱系学告诉我们,知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所谓客观中立的:知识制造权力,从而驾驭主体;看似更为人道,实则更为隐秘。《规训与惩罚》细致考查了权力的谱系,划分出西方社会权力谱系的三个时期与三种规训形式: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封闭式规训、古典时期的全景式规训、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监狱式规训,最后这种监狱式规训使西方社会成为规训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管理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运作起来的,它使权力运作更便捷、有效,从而以一种巧妙而隐秘的形式达到社会强制的目的。现代监狱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它是对全景敞视主义规训的发展。它是最强的规训机构,目的是隔离犯人,进而改造他们,实质上就是由一系列规训机制构成,从而生产出受到规训的个体。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具有与监狱同样的规训模式,从而塑造了现代人的人格特征。同尼采所批判的教士道德对人的本能压抑一样,福柯认为监狱式的现代社会也实施着同样的异化现象。
正如尼采强调对本能的分析,福柯强调对灵魂—肉体的双重分析。以往对犯人实施公开肉体酷刑,而现代监狱对犯人实施灵魂监禁,作用客体由肉体转向灵魂。在前现代时期,教士对罪犯采取公开的肉体酷刑,剥夺其生命所有权。现代时期,隐蔽的灵魂监禁取代了公开的肉体酷刑,看似人性得多,实则不然。前现代时期,肉身只是原罪的抽象载体,对肉身的惩罚就是对原罪的惩罚,而现代的肉身则因生理学、心理学的产生而变得更加的复杂化、科学化,罪恶的肉身概念已经消失,代之以由生理学、心理学所构建起来的灵魂观念,由此现代社会对个体的规训与惩罚由肉身指向灵魂,进而实现对现代人的肉身与灵魂双重规训。福柯关注了由肉体到灵魂的权力运作机制,并断言在这种转换过程中都是一样的非人性。看似“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实际上,与这些变化伴随的是惩罚运作对象的置换。……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7]17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基本根除了公开而残暴的酷刑场面,表面上似乎更人性了,而实质并非如此,而是对人的认识更加功能化、“科学”化了。现代社会通过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科学由以往残酷而公开的规训机制转向对人的灵魂的隐秘规训,对人的规训并不是变得更人性化,而是规训机制更复杂了。福柯认为,传统社会对人惩罚的残酷手段以更加隐秘、复杂并贯以合理化、科学化的形式规训着现代人,这从根本上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尼采所说的规训本能与肉身的教士道德。
《规训与惩罚》以对弑君者达米安肉身的公开酷刑开篇,而这种对肉身力量的控制就是福柯所谓的“肉体的政治技术学”,它将肉身看作是可以随意征服的对象,这一过程既暴露了犯人的罪行又展示了君主的权威,同时又达到了对民众的震慑。所以,酷刑既作为一种惩罚技术而存在,也作为一种权威仪式而存在。但是,在君主展示其权威的同时,民众也表现出对权力的排斥,对罪犯的同情,对行刑者的蔑视。“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 ”[7]66因此,公开酷刑越来越失去了它固有的效力。随着人们对暴刑的批判以及对惩罚人性化的呼吁,公开的肉体惩罚消失了,由之而来的是以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所构架起来的一套知识体系,即一系列的惩罚技术符号。这一体系使惩罚变得更加经济、隐秘、细致、仁慈、高效。惩罚表现为一系列权力表征符号。在这些技术符号的背后是各种权力的运作。对肉体的公开处决转变为对人们头脑中各种知识符号的强化,进而达到时刻规范其行止的目的,使其对各种知识符号所指涉的权力体系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惩罚的目的不是消除其罪行,而是防止其再犯;不是惩罚其肉体,而是改造其灵魂。而改造灵魂的过程就是一个权力运作与知识参与的过程,即一方面特定的权力符号随时对灵魂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一系列的技术性话语体系作为权力实施之手段得以运行。而这种权力与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合谋最终是在监狱的监禁这种权力惩罚机制中显现。在监禁制度中,罪犯必须遵循铁一样的作息纪律:起床、整理内务、洗漱、就餐、劳作、收工、睡觉等。在这一过程中,罪犯的每一个活动都被施加特定的限制,如上厕所必须遵循时间与次数的严格限制,而这些限制恰恰是在监狱对犯人的监督中实现的。通过强制劳动与监视,监狱既达到了对犯人强健肉体的驯服又实现了对犯人柔软神经的控制。这样,权力的眼睛驱逐了一切黑暗之所,消除了一切小奸小恶的想法,使每个人成为自我监督者与自我规训者。由此产生的是完全不同于公开酷刑的旨在规训个人灵魂的监禁权力机制。福柯称此规训方式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它源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这一设计:一座圆形建筑,中心立一高塔,高塔向外都是无死角的透明玻璃。圆形建筑被分割为无数的小囚室,每个小房间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向内开一个向外开,这样,阳光可以进入使囚室不再黑暗,注视者的目光也可以进入,使监视者对犯人时刻关注。 犯人“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 ”[7]225边沁把它称为一种可以看见的但却不能确证的权力,即被囚禁的个体随时都能够看到监督他的高塔,但他却不能确定里面的监视者是否在注意他。这种全景敞视建筑充分诠释了监视和被监视这种对立的权力运行模式。其结果是,通过对身体的规训与监视,灵魂变得轻柔而顺从。灵魂自动囚禁了肉体:因为每个人都实现了自我规训。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机制渗入到整个社会机体之中,学校、军队、医院、企业等机构都在做着同样的规训身体与灵魂的活动。与传统上公开的权力展示与对身体的暴虐不同,现代规训机制以科学话语的名义使权力运作方式更为持久、稳定、精致。权力以一种被规训者不能确定是否被注视的方式运行着,使人们倍感压抑,这种焦虑感与紧张的情绪每时每刻都在折磨和抑制着个体的思想与言行,长此以往,他们实现了自我监督,实现了灵魂的自我规训。所以,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是一种微观权力,因为它建立在看似合理的知识话语之上,它隐而不显,却疏而不漏,它使受囚禁的个体经历着信息的匮乏与生命的单调。福柯想说明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各个机构中都充斥着这种隐秘而又运转高效的压抑人性的、机械化的、非酷刑式的微观权力运行机制。这无疑是尼采批判衰退的教士道德、张扬高昂的生命意志的回响。
[1]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M].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刘小枫,倪为国.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C].上海:三联书店,2003.
[3]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赵千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6]ALAN D SCHRFT.Nietzsche’s French Legacy[M].New York:Routledge, 1995.
[7]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2.007
B516.5
A
]1004-0544(2017)12-0042-06
马成昌(1978-),男,山东郓城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