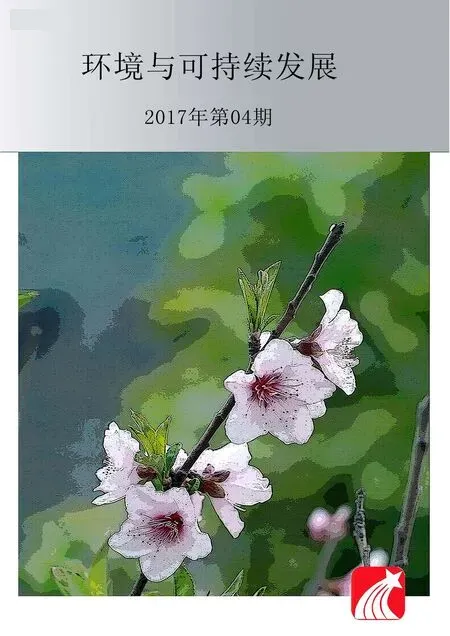环境法中的生态损害:识别、本质及其特性
2017-03-04刘倩
刘 倩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环境法中的生态损害:识别、本质及其特性
刘 倩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摘要 生态损害是围绕生态损害所形成的法律理论体系与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深入分析生态损害论争的焦点及分歧原因就会发现:生态损害是生态功能的损害,其不等于自然资源损害或环境质量或容量损害,也不宜称之为“生态环境损害”或“环境本身损害”;生态损害的本质是人的生态利益的损害,生态利益以生态功能为客体,是对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具有秩序性和本底性的典型属性;生态损害还具有“量”的特性,是达到严重程度的生态功能的损害,对生态损害进行评估仅是认定损害结果的权宜之计。
生态损害;生态功能;生态利益;“量”的特性
概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生态损害概念及其内涵是围绕生态损害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与制度设计的基础。虽然生态损害作为不同于人身、财产损害的新的损害类型已得到环境法学研究的密切关注,但是对于生态损害的内涵存在诸多不同见解,生态损害也未成为环境法学理论观点与制度构架的依归,甚至因生态损害内涵的不同界定而导致理论体系与制度设计上存在本质性的偏差。辨析生态损害的内涵、本质及其特性,是相应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也是构建生态损害预防与救济法律制度面临的紧迫任务。
1 生态损害概念的论争
1.1 关于生态损害概念的观点
生态损害概念的使用及其探讨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不同的学科范畴对生态损害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在法学领域中,国内外学者都是在与传统人身、财产损害相区别的新型损害类型的意义上使用生态损害的概念,但对概念的称谓及其具体内涵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说明。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采用“自然资源损害”的概念,将生态损害定义为对自然资源的物质性损伤,包括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动植物和他们间相互作用的损害[1]。采用这一概念的观点又可根据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是否可通过传统民事侵权法获得救济、是否具有量化可能性等而分为不同的主张,具体有三种。第一种主张认为生态损害应限定为“公共性的无主自然资源的损害”,因私人所有的自然资源适用传统民事法律关于财产损害的救济理论即可;第二种主张将生态损害界定为可量化的超出市场价值的自然资源的损害,因为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双重价值,只有在经济价值之外的生态价值损害才是生态损害,但生态损害需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能够计量[2];第三种主张并不区分自然资源的有主、无主或可否计量,而只是一般化地认为生态损害是对自然资源的损害。
第二,采用“环境权损害”或“环境利益损害”的概念,将生态损害界定为对公民环境权或公共环境利益的侵犯,是指因环境要素被污染或破坏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人们享有健康、舒适的环境的权利或损害公共环境利益[3]。这一观点认为公民环境权或公共环境利益是生态损害的客体,环境权或环境利益是无法为公民人身、财产权所包括的新型权利或利益类型。至于是采用“环境权的损害”,还是采用“公共环境利益的损害”,主要取决于对环境权利的认可及其程度。
第三,采用“生态效益或生态价值的损害”概念,这一观点认为,环境污染除了可以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权利的直接侵害外,大多数场合是对周围的环境与生态所造成的所谓间接侵害,即对生态效益或者生态价值的侵害[4],但该观点对何为生态效益或生态价值未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第四,采用“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将生态损害界定为由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伤。“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较多见于国家政策性文件,法学界的使用也较为常见,因“生态环境”一词源于我国《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规定,学界往往在与“生活环境”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但是,由于“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并非环境科学意义上的术语,学者们对两概念法学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对“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两者关系的界定也多有不同。
第五,采用“环境本身损害”的概念,将生态损害界定为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与人身财产损害相区别的环境本身的损害。但是,这一概念对何为“环境本身”并未进行深入探究。
第六,采用“生态损害”的概念,将生态损害界定为生态系统的任何组成部分或者其任何多个部分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能的任何重大退化。这一概念与“生态环境损害”概念的内涵一致,仅在概念称谓上有所差异,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进一步根据生态损害的量化可能性和生态损害预防、控制和修复的责任将生态损害类型化为预防性措施费用、清除措施费用、修复费用和附带损失等[5]。
1.2 生态损害概念论争的焦点
关于生态损害概念的称谓及其内涵的观点立足于事实层面、规范层面或经济价值层面,从客观损害对象或结果、环境权利或利益被侵害、生态价值或效益的损失等角度揭示了生态损害的内涵。这些观点反映出论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生态损害的不同理解与认识,均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同时也反映出论者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一是,对自然资源、环境质量、生态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理解不同,生态损害是自然资源的物质性损伤,还是环境质量或容量的下降,抑或生态功能的损害?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与生态损害是否相关?二是,对生态损害进行定义的立场不同,生态损害是应立足于人的环境权利或利益的损害还是应立足于资源、环境或生态的损害进行定义,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三是,对生态损害的程度及其量化可能性是否应进行界定存在不同理解,生态损害是否需达到严重程度方可进行法律救济?若通过科学技术无法量化,如何救济生态损害?本文将围绕此三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以期识别生态损害概念的内涵,探究其本质,并发掘其典型特性。
2 生态损害的识别
2.1 资源、环境与生态的关系
从损害事实的客观视角来看,生态损害的对象与结果是物质性的自然资源,还是环境的质量或容量,或是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这是准确把握生态损害内涵的基础,有必要对自然资源、环境与生态系统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廓清各自的边界范围。
虽然“自然资源”较常在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意义上使用,广义的自然资源将自然物资与自然条件都整合进概念之中,认为自然资源包括了环境,但从法律意义上讲,资源与环境并未统一到一个体系,狭义的自然资源概念仍是通说,指自然界中可以被人们所利用的有形或无形的物资和能量[6]。 “环境”一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界定,环境法上一般倾向于认为“环境”指以人类为中心,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既指独立的环境要素,又指由环境要素形成的生态系统,而且,“环境”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概念,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能够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的条件或状况都可能成为“环境”。“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构成的综合体,即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不断进行着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的自然整体。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并非所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条件都能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
从以上定义来看,自然资源侧重说明人类生存、生产所利用的物质要素,表现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静态物质和能量;环境侧重说明围绕人类的外部空间、条件或状况,表现为静态的环境要素与动态的某一特定时空的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7];生态系统侧重说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表现为有形的生物存量和无形的生态功能。因此,资源、环境和生态三者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要素,其强调经济价值但具有环境或生态特性;环境是以自然资源为载体形成的具有一定品质的外部条件,环境质量或容量是超脱于自然资源载体的独立存在;生态系统是资源实体与外部环境形成的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相对平衡的功能体系,其中,自然资源等物质与能量的供给源于生态系统的供给功能,环境容量吸收与净化污染物质的能力源于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
2.2 生态损害的辨析
生态损害是传统法律无法涵盖的损害类型,是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害,“自然资源损害”、“环境本身损害”、“生态环境损害”等概念的表述并不妥当。理由如下:
第一,“自然资源损害”是美国法律中表述生态损害的概念,我国也有学者在同样的意义上借用此概念,但是这种借用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有待商榷。因为自然资源是组成各种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影响环境并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自然资源的损害不仅造成资源的实体性损害,也对所在区域生态系统或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自然资源损害的双重性决定了其可分为经济性的损害和生态性的损害两种类型,其中,经济性的自然资源损害可归入传统的财产损害进行救济,生态性自然资源的损害才属于生态损害。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自然资源”强调自然资源的经济属性,主要在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其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虽然“自然资源”的概念也包含有生态属性的意义,但只是附随性地涉及而非将其作为专门对象。因此,在我国法律语境下使用“自然资源损害”的概念表述生态损害易导致过分关注资源实体的经济性损害而忽略自然资源在生态系统或环境中起到的生态作用。
第二,“环境本身损害”也是较常使用的表述生态损害的概念,这一概念与“环境损害”的概念密切相关但内涵不同。“环境损害”可理解为经由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对环境的损害两种含义,经由环境造成的损害包括了因环境媒介受污染或破坏而造成的人身、财产和环境本身的损害,对环境的损害仅指环境本身遭受的损害。“环境本身损害”的表述虽然可以明确地将生态损害与传统的人身、财产损害区别开来,但是由于“环境”一词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含义,既可以指环境的载体即自然资源,也可以指环境的容量,还可以指区域环境所处的生态系统,即使将“环境本身损害”解读为环境容量或质量的损害也难以涵盖虽未造成环境容量或质量上的改变但影响生态系统平衡的损害类型。因此,“环境本身损害”这一概念仍未揭示出生态损害的直接对象与后果。
第三,“生态环境损害”是目前在国家权威性文件中使用较多的概念。这一概念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态环境”该如何理解,二是“生态环境”的用法是否妥当。对于第一个问题,据学者已有的考察,“生态损害”的理解源于我国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规定,也因此“生态环境”往往在与“生活环境”相对的意义上使用,虽然“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内涵及其关系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大体而言,“生活环境”指正常舒适生活所需的一定质量限度内的环境,仍属环境侵权的范畴,“生态环境”则指生态环境质量及生态服务功能意义上的环境[8]。关于第二个问题,有环境科学领域的学者也指出,“生态环境”的含义因其构词法问题而多义和含混,不具作为术语的资格,而且,如将“生态环境”定义为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而用作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术语,其中的“生态”实质为赘语,并将引起严重的逻辑混乱[9]。
另外需说明的是,有观点将“生态环境”理解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简称,将“生态损害”中的“生态”等同于“生态破坏”中的“生态”,同样存在逻辑上的错乱。虽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都可能造成生态损害的结果,但 “生态损害”中的“生态”是从损害结果的生态性意义上进行定义,而“生态破坏”中的“生态”是从原因行为的意义上进行定义。由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见,“生态环境损害”并不适宜作为生态损害的概念使用。
第四,“生态损害”是目前相关概念中最为准确的表述。如前文所述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关系,资源是环境或生态系统的载体,环境是以资源为条件的容量和品质,生态系统是由环境和资源组成的生态功能体系,资源与环境处于生态系统之中。资源、环境与生态三者之间有一定的重合关系,自然资源生态属性的损害、环境容量与品质的损害、生态系统的功能损害相互之间也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只是在损害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可能有所差异和侧重。但是,从整体性的生态系统的角度看,自然资源生态属性的损害、环境容量与品质的损害、生态功能的损害都可统一归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损害。因此,本文认为,使用生态损害的表述,将生态损害定义为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损害,从揭示概念内涵和概念表述上看都更具合理性。
3 生态损害的本质
从生态损害的对象与结果的角度看,生态损害是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的损害,这是从客观事实的立场所进行的分析。但是,由于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客观上的生态功能的损害需对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才能进入法律调整的视野。虽然环境权利和利益并不相同,但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因此可直接从生态利益的角度对生态损害进行规范意义上的分析,但“生态利益”如何解释是需探讨的问题。
3.1 生态损害与生态利益的关系
“利益”一般被解释为“好处”、“有用性”、“期待”、“收益”等,是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生态利益是生态功能满足人类生态需要的特性。生态利益包含着两方面的要素,从对象的角度看,生态利益表述的是生态功能的属性对人类的意义这种关系,从主体的角度看,生态利益表述的是人类从生态功能上可得或已得的“收益”这种关系,生态利益是生态功能的有用性与人类的收益性两要素的结合。
但是,只具有对象的有用性与主体的收益性并不能完全解释生态利益,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后,生态功能才产生对人类的收益性[10]。因为生态功能区别于生态系统的经济和精神功能,生态功能的损害由人类开发利用环境或资源超过生态系统承载力而引起,生态功能的损害反过来对人类的不利影响不是及于个人或某一小部分人,而是某一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人类。因此,虽然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都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且持续不断地从中获得收益性的满足,但是,人类在生态系统的自然承受能力的限度内从事开发利用活动的历史并未产生生态利益的概念或主张,只有在人类的开发利用程度超过某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最大承受限度从而影响到生态功能,并且对区域人群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该区域的多数人才会因区域生态功能的损害而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主张生态利益的保护。也就是说,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诉求或期待是在区域生态功能损害达到某种对人的利益损害的程度才发生的,只有在人类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超出生态系统的自然承受限度,生态功能对于主体人类的有用性才被提出,人类从生态功能处获得的收益性才成为不得不努力争取的利益,生态利益是生态功能被损害后人类所失去的利益[11]。
3.2 生态利益的本质属性
正如前文所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态功能并未损害到一定程度,生态利益也未成为人类关注的问题,当时人类注重的只是具有稀缺性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只是在生态功能损害到一定程度,生态利益的稀缺性和有用性才得到人类的重视。人类重视生态利益的原因在于生态功能的损害虽然并不一定直接对人身、财产利益造成损害,但使人身、财产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所以,生态利益从本质上看是生态功能对人身、财产利益安全保障需要的满足。
从人身、财产利益安全保障的意义上看,生态利益具有秩序性和本底性两种典型属性。所谓秩序性是指处于正常状态下的生态功能才可以为人身、财产利益提供保障,生态利益是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正常状态的秩序对身处其中的任何人都存在好处或利益,而正常秩序的扰乱对其中的任何人均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威胁到个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生态利益的秩序性决定了只要生态功能可以在客观上维持正常状态,就能对生存其中的任何人产生利益,但生存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将生态利益进行分割而单独享有某一份额的利益。生态利益的本底性是指生态利益是生态功能在未受损害前的基线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利益,因为生态利益是生态功能损害之后才被发现的利益,未经损害的基线状态的生态功能才是利益所在。生态利益的本底是保障人身、财产利益所需的最低限度和最起码的状态,也决定着人类从中获取其他利益的最大可能[12]。
4 生态损害“量”的特性
4.1 生态损害的程度
生态损害具有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双重特征,事实性是从客观上分析是否存在生态损害的事实,规范性是从法律上界定生态损害是否需要通过法律予以保护。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客观存在的生态损害都需要通过法律进行救济,只有对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的生态损害事实才有必要进入法律调整的视野。因此,法律上的生态损害除有对生态功能造成损害的这种“质”的规定性外,还具有达到一定程度的“量”的规定性。
生态损害的法律意义上的“量”至少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第一,需要有客观事实上的生态损害,这是生态损害进入法律调整的前提;第二,客观事实的生态损害需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如果生态损害轻微,通过自然机制无需人工干预即可在短期内恢复到基线状态,则不构成法律上的生态损害,无需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救济;第三,虽然生态功能的损害达到一定严重程度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救济,但法律救济并非万能,应综合运用其他手段进行干预。第四,生态损害是否超过一定程度需要法律设定一定标准,这种标准的设立应以区域生态功能是否受损为前提,环境质量标准是判断生态功能是否受损的重要参考。
4.2 生态损害的认定与量化
生态损害质与量的双重特性决定了生态损害进入法律调整视野需以科学角度对生态损害的认定与量化为基础,认定的目的是判定生态损害是否存在,量化的目的是计算生态损害的程度,也因此生态损害体现出强烈的技术性。但是,由于生态功能损害的高度复杂性,人类并不能完全认识和掌握生态损害的全部不利后果,而只能受限于当下的科技水平和认识能力对能够认识和能够确定的一部分生态损害进行救济,从这个方面说,即使是科学上的生态损害也不是完全的真实的生态损害,能够认识和确定的生态损害永远小于真实的生态损害。而且,由于环境损害评估是目前认定与量化生态损害的基本技术,损害评估的核心是运用经济学上的方法对生态损害进行价值意义上的计算,损害评估所得的价值即被姑且视为生态的价值,但这种经济性的价值并非真实的“生态”价值,因为生态功能本质上是无法通过经济价值进行衡量的[13]。
5 结 语
从损害对象和结果的事实方面看,生态损害是生态功能的损害,不等于自然资源的损害或环境质量的损害,也不宜称之为“生态环境损害”或“环境本身损害”;从生态损害的规范层面看,生态损害本质上是人的生态利益的损害,生态利益是生态功能处于正常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利益,或者说是生态功能被损害后人类所失去的利益,是保障人类人身、财产利益的一种秩序和本底性利益;在“量”的角度上,生态损害是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生态功能的损害,需借助评估技术进行认定和量化,但人类技术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评估所得的生态损害只是一部分生态功能损害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而非全部生态功能的真实损害。
生态损害内涵的识别、本质属性与特性的发掘表明,生态损害是能够对人的生态利益产生不利影响,达到一定程度的生态功能损害。这种概念界定的意义在于,生态损害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需以人的生态利益的保护和救济为核心,生态利益的保护和救济以维护生态功能的正常状态为最低要求。同时,这一界定对后续研究提出了仍待解决的问题:生态功能损害达到何种程度才会对生态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对生态利益的不利影响该依据何种标准进行判断?生态利益的秩序性和本底性对政府、企业、公民的权利(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架构将产生何种影响?等等。
[1]梅宏.生态损害预防的法理[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2007:17-18.
[2]蔡守秋,海燕.也谈对环境的损害———欧盟《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的启示[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97-102.
[3]马骧聪.环境保护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27-128.
[4]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50.
[5]竺效.生态损害事实及其可填补之类型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12.
[6]黄桂琴.论自然资源权的物权属性[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5:4-5.
[7]常纪文.环境权与自然资源权的关系及其合并问题研究[J].环境与开发,2000(4):4-6.
[8]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74.
[9]竺效.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拓展[J].中国法学,2015(2):248-265.
[10]徐祥民,朱雯.环境利益的本质特征[J].法学论坛,2014(6):45-52.
[11]杜健勋.环境利益:一个规范性的法律解释[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2):94-101.
[12]刘卫先.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识别、本质及其意义[J].法学评论,2016(3):153-162.
[13]徐祥民,高振会,杨建强,等.海上溢油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与技术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157-158.
Ecological Damage in Environmental Law:Discrimination,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LIU Qian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Beijing 100012)
Ecological damage is the basis for related theories and systems.Through deep analysis about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and reasons for disagreement on ecological damage,we find that ecological damage is the damage to ecological function.Ecological damage is not the same as natural resources damage 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damage,it should not be call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or “environmental damage itself”.The nature of ecological damage is the damage of human ecological interests.Ecological interest is a kind of security guarantee to personal interes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order and background.Ecological damage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y”,the damage to ecological function should be serious.Carrying out technical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damage is only a matter of expediency to determine damage.
ecological damage;ecological function;ecological interests;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ity”
项目资助: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和流域水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及其示范研究”(批准号:2013ZX07602-002)
刘倩,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保护法基础理论
文献格式:刘 倩.环境法中的生态损害:识别、本质及其特性[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7,42(4):137-141.
X21
A
1673-288X(2017)04-01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