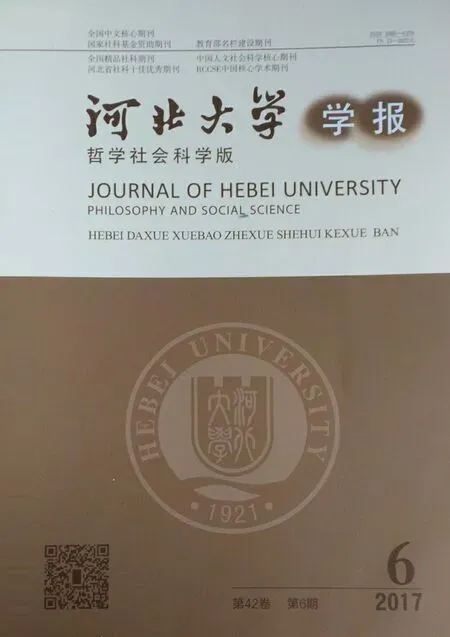作为价值多元论的庄子齐物论
2017-02-28汪韶军
汪韶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齐物论》是整部《庄子》中最难理解的一篇。“齐物”的提法非始于庄子。《庄子·天下》载彭蒙、田骈、慎到学派“齐万物以为首”①为避免烦琐,从《老子》《庄子》《文子》《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墨子》《韩非子》等经典性古籍中引用的文句,本文只注明所出篇目。,但此所谓“齐万物”是树立一个客观标准(法),凡事皆一断于法;庄子说的“齐物”则不然。历史上也有人将篇名读成齐“物论”,北宋张耒可能是首倡者,其言曰:“昔楚人有庄周者,多言而善辩,患夫彼是之无穷而物论之不齐也……”[1]35南宋林希逸、王应麟亦持是说,他们认为《齐物论》非欲齐物,而是为齐“物论”之是非而作。此说为我们理解《齐物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需要注意的是,齐论与齐物实为《齐物论》所兼包,不可执其一而否定它说。今人陈少明先生则析为齐“物论”、齐万物、齐物我三个层次:“齐‘物论’,也即齐是非是问题的出发点,齐万物则是齐是非的思想途径,而齐物我不仅是齐万物的前提,最后竟也是齐是非的归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2]81
庄子讲了很多齐大小、齐是非、齐寿夭、齐生死的道理,但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产生误解。比如,郭象就误用齐物思想抹除了《逍遥游》中的大小之辩(至于这种误读是否精彩,则是另一回事)。今人最容易照字面将其误解成使物变得整齐划一,或以为庄子主张万物在事实层面没有差别,或给庄子哲学贴上相对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标签。其实,“齐”不是使动用法,否则将直接违背道家自然无为的学说宗旨。“齐”是意动用法,它是在价值论上将宇宙万有、各种物论等而视之,拒绝贵贱尊卑、是非善恶美丑等人为判分,其目的是突出多元平等观,从而为万有的差异性开出各自的存在空间。
一、物与物的平等
《庄子·知北游》道在屎溺一说,尽人皆知。这是以极端的说法突出道的遍在性。那么,庄子强调这一点有何用意呢?韦政通先生的分析可以说明问题:“这个观念使形上与形下两界打成一片,使客观与主观融而为一,也是庄子万物平等观的根据。……庄子用最卑下的事物做例子,是要人警觉到道并不是高高在上,更不是人所能独占。”[3]190-191形上形下打成一片,是万物皆秉有道性。就秉有道性而言,万物“一齐”。
庄子又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大块噫气”的结果。《至乐》篇:“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知北游》篇:“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人是如此,物亦如此。万物皆源于一气之运化,故说“通天下一气”,这也是在万物的根源上说其齐同。
《秋水》篇从价值论谈“齐”:“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万物如柤梨橘柚,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万物都有各自特定的“功”,这是其异;然就其皆有“功”而言,万物无有不同。既然如此,我们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同篇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凡此都是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也都有它特定的价值与意义,且不存在贵贱高下之分。
万物殊性,这是不待证明的直接现实。道家认为,独特性正是个体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他们意图保持这样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骈拇》篇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性”是长长短短、参差不齐的,各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不可用一个标准来加以齐同,而应任由这个长那个短。庄子想要证明的是差别各具合理性,而不是否认差别的存在。其“齐物”不是以一则制割万物,取消万物形态上的差异,而是强调万物殊性之平等,即用价值上的齐来保住形态上的不齐。“齐物论”说到底是一种价值多元论,是为了存异。清代胡文英得之:“《齐物论》是言物之不能齐、不可齐、不当齐、不必齐。”[4]17徐复观先生亦指出,齐物“戳穿了说,是对物之不齐,却加以平等观照的齐物”[5]264。陈鼓应先生说:“这哲理落实到社会层面则为重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落实到政治层面则为尊重个体的尊严和殊异才能。”[6]54
二、非人与人的平等
本来“万物”是将人包纳进来而言的,但由于世人总是强调人与物的不同,于是渐渐遗忘了人本是万物之一员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家那里,“物”既指称一般意义上的“东西”(笔者将其称为“非人”),也经常指人。《庄子·达生》:“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既如此,人当然也是一物。《人间世》篇栎社树见梦于匠石说:“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若”(匠石)与“予”(栎社树)都是物。再如《徐无鬼》篇“夫子,物之尤也”,尤物显然指人。以“物”指称人的现象在道家文献中很常见,因为道家一系都认为,人与物在根源上是相同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中与物相并列的一个成员。《文子·九守》:“吾处天下,亦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何以相物!”这种思想的背后,实际上是强调非人与人的平等,需要单独加以论列。
人类最初没有自我意识,无法将自身与周围的世界区分开来,他们与世界是直接合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与非人毕竟不同,乃至产生自己是“万物之灵”的感觉,于是顿觉自己身价倍增,有时便不免颐指气使起来。郭店楚简《语丛一》:“夫(天)生百勿(物),人为贵。”[7]194《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儒家这类言论很多,它们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可以激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我们必须加以警惕,因为它容易蜕变成自我中心,扩而大之便是睥睨天下的人类中心论。
道家则强调人的有限性,反对自视过高。《老子》33章:“自知者明。”《庄子·秋水》篇首说:人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在天地万物中,人只是“一”。人类没有理由自认为是宇宙的中心,没有理由把自己当成衡量万物的尺度。
我们还可以就儒道两家的人禽观做一番比较。帛书本《五行》:“遁(循)草木之生(性)则有生焉,而无[好恶。循]禽兽之生(性)则有好恶焉,而无礼义焉。遁(循)人之生(性)则巍然[知其好]仁义也。”[8]23《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认为,凡人与圣人是同类,与禽兽则异类,因为人性中本有仁义良知,此为“心之所同然”,而这些为禽兽所没有。人应该存心养性,扩充仁义礼智四善端,以期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而不可把自己降格成禽兽。《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礼记·曲礼上》:“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还是说,人的可贵之处在于知礼义。儒家一方面强调将仁爱推及禽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一方面又极力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拔人于鸟兽之中(儒学的本质就在这里)。前者认为禽兽是人类自上而下的施惠对象,后者更明确地认为相对于人,禽兽等而下之。所以孟子坚持夷夏之辨,将许行贬为“南蛮鴃舌之人”,批评杨、墨是禽兽,都是不足为怪的。
对于非人与人,儒家习惯于自其异者视之,道家则强调自其同者视之。道家不关心人与物的分界,而总是放下身心与万物一例看,或者把物提到与人平齐的高度来加以对待。《庄子·大宗师》:“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庄子认为,人类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实在不必因生而为人就洋洋自得。荣启期式的三乐(生而为人、生而为男人、行年九十)*参见《说苑·杂言》或《列子·天瑞》。,是庄子所不屑的。道家倒不介意“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韦政通先生指出,齐物思想“含有一种普遍尊重生命的伟大伦理精神。孟子强调人禽之辨,对提高人类的尊严很有贡献,但也因此重视万物之间的不同等级。……这种等级的观念也助长了人类破坏的本性,妨碍了博大精神的培养”[3]184,此论极为公允。
三、物论的平等
(一)以辩止辩
贵贱尊卑、是非善恶美丑等观念都出于人的判分,在庄子看来,这种人为的判分及继起的爱憎取舍是很成问题的。以下分析庄子以辩止辩。
“辩”有辩论、分辨、分别等义。《墨子·小取》曾这样概括辩的功能:“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我们知道,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正是百家争鸣最热闹的时期,这种学派争鸣虽未至于后世思想领域内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已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而相互攻伐,其目的是在辩论中胜出并让败方销声匿迹。而庄子否定争辩的有效性。他认为,辩不能使是非历然分明,因为:其一,辩者都是自师其心者,其言论都发自一己之成心,所以是不可靠的。《齐物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你说如此,事情就果真如此吗?是非果真由你定夺吗?你所说的果真是终极真理吗?辩者的症结在于拘于一偏之说、一己之见,却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从而走向自美,甚至强人从己。其二,由于人人都自师其心,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评判标准的可靠性。《齐物论》:“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这里是说,某次辩论看似有人胜出了,并不代表此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而“我”、你、第三者之间所以互不相知,都是因为三方各师其成心,东望而不见西墙(“固受其黮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谁来决断呢?还需要第四人、第五人、第N个人吗(“而待彼也邪”)?不需要了,因为他们同样各执己见,谁也没有资格充当裁判者。没有“同是”“公是”,所谓的评判标准(“正”),其实是不存在的。彼之所是乃此之所非,此之所是乃彼之所非,物论皆既是既非。《齐物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庄子不是要止辩吗?可他自己辩了又辩。北宋邵雍有诗云“齐物到头争”,还说:“庄、荀之徒,失之辩”,“庄子‘齐物’,未免乎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9]167、175这种指责代不乏人。今人张松辉先生认为,庄子从实践、理论上都破坏了自己的齐物论,“在他大谈无是非的时候,同样陷入了是非之争而不能自拔,他以无是非为是,以有是非为非,这本身就是十分鲜明的是非界限。”[10]193这类说法乍看似乎有理,其实没有抓住齐物论的真实意图。庄子之辩与其他学派之辩处在不同层次上。辩者之辩否定的是某种观点,庄子之辩否定的是辩论行为本身,对无穷无尽的是非之争来一个釜底抽薪;辩者之辩是让自己胜出并使对方销声匿迹,庄子之辩则是让各种物论拥有各自的存身之地。假如世人本不争执是非,就用不着庄子去大谈无是非。
(二)以道观之
庄子认为,辩无胜者,是非之争永远不会有个了期,因而是无意义的。与其“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针尖对麦芒似地辩个没完,不如干脆跳出来,从分别对待中超越上去(“和之以是非”),转而从“天”的高度来观照万事万物。《齐物论》:“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是非之别是怎么生起的呢?只是为了争一个“是”(“为是”)。但是,辩者并未达到真正的洞见,只是借争辩来夸示己能。怎么办呢?不如不论不议、不分不辩,也就是不要满脑子转着是非美恶等观念,而应以空明澄澈的朝彻之心,像大道一样去兼怀万物。“无适焉,因是已!”该休歇了,不要再分别争辩了,明智的做法是以物为量,因万物之所是而是之。
“以道观之”(《秋水》)是基于虚静的心灵境界而发显的一种观物方式。它有许多可以互换的说法,如“照之于天”“以明”“休乎天钧”“和之以天倪”等等。《齐物论》:“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明”是虚静空明之心,空而明,虚而明;去除成心,才能一如明镜,让万物如其所是地朗现*“以明”之“明”亦即“神明”。在庄子那里,“神明”是“天光”的同义语,是人人本具的光明觉性。《齐物论》“劳神明为一”意为将“神明”误用于立一偏之说,它否定的是“劳”,而不是“神明”。楼宇烈先生将“以明”释为“已(终止)明”(楼宇烈:《“莫若以明”释——读〈齐物论〉杂记一则》,载于《中国哲学》第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74-275页),非是;韩林合先生将“神明”理解为“通常的心智”(韩林合:《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亦非。。
《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是不是,然不然”是要超越是非,结果是:无不是,无不然。“天钧”即“天倪”,《寓言》:“天均者,天倪也。”“天钧”、“天倪”喻指道,“休乎天钧”就是休心于道、游心于物之初,“和之以天倪”就是“道通为一”。物本无是非,是非缘于人的分别。不分别则无是亦无非,无非则无不是矣。
“以道观之”是一种超越通常参照系的参照系,这种参照系的特点在于“两行”“不谴是非”“因之以曼衍”。南宋林希逸注曰:“两行者,随其是非,而使之并行也。”[11]27不谴是非,任是非两行,即与世界相遇时不作是非上的判分。因此,“两行”的实质是强调物我共在,各行其是,互不相扰,两不相伤。《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逍遥游》“旁礴万物以为一”,《齐物论》“道通为一”,庄子似乎像大鹏一样上至“九万里”的高度鸟瞰这纷繁的人间世,发现天地苍茫一片、万物一齐,无小无大、无是无非、无成无毁、无生无死……。人们常说庄子强调无分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读出“无”的动词意味。无分别不是客观实然上无差别,而是说认识主体主观境界上毋分别。庄子试图传递的是一种在世方式和认知态度。
常有人说庄子是相对主义者。我们不应忘记,相对主义有一种自我取消的本性。《墨子·经下》“以言为尽誖,誖”,就指出了相对主义必将反弹到自身,解构自身。有论者认为这话针对的就是庄子学派,非是。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庄子有破也有立,道的境界是他的最高蕲向,他也没有认为诸家之言完全不可取。美国学者爱莲心(Robert E. Allinson)精辟地指出:“《庄子》不可能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演练,因为这样说便意味着它不能提出任何观点,包括相对主义的观点。……如果所有的观点都只具有相对的价值,那么,一个相对主义者在什么基础上来推荐他自己的观点呢?相对主义最后必然是自拆台脚的。”[12]11庄子相对化的言论不是相对主义,而是一种严肃的思考,其重点在于反对绝对主义或独断论。
(三)自嘲与反省
难能可贵的是,庄子虽然批评世人争执是非,并推出道的观物方式,但他并不强求世人顺从他的主张,而是认为,只要互不相扰,那么各种物论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块存在空间。《列御寇》:“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必”是武断而不留讨论的余地,所以争竞(“兵”)不断。众人“必之”,圣人“不必”。庄子对自己破、立的过程有明确的反省:“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齐物论》)庄子常以“妄言之”“尝试论之”作开场白,也经常使用游移不定的口吻。有论者认为这是对知识的怀疑,类似于晚期希腊皮浪式的怀疑主义*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16-517页;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67-174页。。笔者则以为,这是庄子将自己所说的“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贯彻下去,展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一方面,这是庄子为了保持自己理论一贯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包容他者。只要提倡自由平等,逻辑上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特权,强调反省与包容。在道家文献中,我们会经常遇到在其他学派那里难得一见的自我反省。《齐物论》借孔子之口自嘲道:“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丘也与女(汝)皆梦也,予谓女(汝)梦,亦梦也。”自嘲之所以值得推许,就在于有反省,在于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强人从己。叶海烟先生称庄子“用存疑替代独断,用一连串的问号替代自信满满的句号”[13]88,诚为的论。庄子破外在的权威,并不把自身立为新的权威,他不会自信满满地宣称自己所说的就是终极真理*方东美先生对此做了高度评价:“自余观之,斯乃精神民主之形上义涵,举凡其他一切方式之民主,其丰富之意蕴,胥出乎是。”(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历史地看,儒者易有几个通病:第一,虽然强调时中、权变,但更多的是守信师法,把传统当正统,将自己局限在前辈画定的思想框架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允许他人越出一步,因而容易导致教条化。第二,以正统高自标榜,认为自己把握到的是终极真理,故而往往自以为是而不见异量之美,乃至强人从己。《孟子·滕文公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子·解蔽》虽然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但他的根本主张是“天下无二道”,不许世人“蔽于一曲”(抱有自己的见解)。《非十二子》篇提出“务息十二子之说”,因为它们都是“天下之害”。像这样,一元价值既然被视作绝对价值,势必会增长独断性、排他性。儒家不遗余力地讨伐其他学派乃至对内争正统,这种兴一方、灭一方的做法易导致思想文化的专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实乃儒学题中应有之义),恰恰违背了“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美好愿想。
墨子主张“上同而不下比”。《尚同上》认为“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情形是非常糟糕的,思想界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下》:“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天志上》:“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虽然这种尚同思想以尚贤为基础,所谓的“天志”也实则是兼爱兼利原则,但墨子对多元的排斥依然是有隐患的。如果所尚的“同”出了问题,或者被恶意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墨子出身于儒家,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的精神一致。
出于荀子门下的韩非,表面上已与儒家决裂而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思维模式也还是一样。他嫌儒家对社会的管制力度还远远不够,于是把儒学中的排他性一面发挥到极致,结果连儒墨后学也被他斥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行”。韩非又建议人主对异己的思想者“宜去其身而息其端”,最终酿成焚书坑儒之祸。
可见,一家思想但凡被定于一尊,必定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道家则与此截然相反,他们推倒偶像,又不把自己立为新的偶像。韩非在概括先秦学术时,只说儒、墨两家是显学,而没有提及道家。“道家”作为一个学派名称,最早见于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许多学者据此认为,道家在先秦的影响并不大。这种想当然的做法并不可取。道家虽未必如民国时期江瑔《读子巵言》所言为“百家所从出”,但从传世先秦古籍及出土文献看,道家在先秦时就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韩非为什么没有把道家称为显学呢?从其论述来看,他的重要标准是学派性强不强,以及是否有较为明显的师承谱系。与此相比,道家强调自隐无名,抵制自封为真理的做法,不好为人师,其虚而待物的态度也反对学派的封闭性、排他性。这应该是道家在先秦影响虽然广远,但又没有被列入显学甚至没有被视为学派的原因。
回到庄子。并行不害,乃《齐物论》之宗旨。差别各具合理性,物论也各具合理性。《天下》篇说百家“皆有所明……皆有所长”,惠施学说“充一尚可”,又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齐物论主张百花齐放,因此容易造就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和兼容并畜的思想文化格局。庄子反对的是自以为然而走向独断论,并不反对自以为然而各行其是。他虽然也批评一曲之士,但在他那里,一曲之士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在于只知其一又恶人言其二。一曲之说也许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我们不明了自身的有限性而把自己膨胀起来吞没他者(“自贵而相贱”),把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当成终极真理并强迫天下人遵从,就会连本有的那点合理性都化为乌有。强人从己,首先是对自身的误解,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庄子则告诫世人不要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而要走出自我。只有正视自己的有限性,才不会强人从己,才容得下他者。历史上受老庄影响很深的学派(如黄老学派)及知识分子(如苏轼),却遭遇“杂家”之讥,都是因为人们不知他们原是不盲目排他而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综上,齐物思想通过强调万物价值的平等来破除等级之分、爱憎之情、取舍之见和强人从己的做法,就他者而言,是对多元价值的尊重与包容;就个体自身而言,则可达成价值取向上的不羡不嫌,如《庄子·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
[1] 张耒.刘壮舆是是堂歌并序[C]//张耒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M].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
[4] 胡文英.庄子独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陈鼓应.道家的和谐观[C]//道家文化研究:第15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8]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9] 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 张松辉.庄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3] 叶海烟.中国哲学的伦理观[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