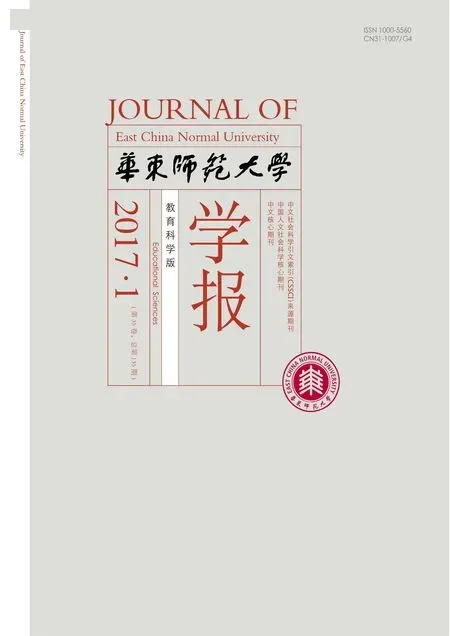课程,悠游于科技的边缘
——威廉·派纳与杨澄宇关于课程和科技关系的对话
2017-02-26威廉派纳杨澄宇
威廉·派纳 杨澄宇
(1.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温哥华; 2.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上海 200062)
课程,悠游于科技的边缘
——威廉·派纳与杨澄宇关于课程和科技关系的对话
威廉·派纳1杨澄宇2
(1.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温哥华; 2.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上海 200062)
杨澄宇(以下简称“杨”):宽泛而言,您是否认为科技的进步会促进教育的发展?
威廉·派纳(以下简称“派纳”):是的,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如果没有技术的帮助,诸如网络资源在内的许多教育经验无法获取。但更重要的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科技会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会重建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使他们之间不再需要互相适应并以此来决定学习的方式与内容。这是一种控制学习的“方便法门”。这样看来,原本应是“复杂对话”的课程变成了项目间的对话,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当本该是交互式形态的课程仅仅提供文本或产品之时,教学也就沦为了其所采用工具。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论断,我基本赞同。
杨:好的。那么从更宽泛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您认为高科技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吗?
派纳:我基本赞同。譬如医疗的发展,可以救治人类疾病;但有些药品也会危害到人的生命。
杨:今天我们的世界或许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后人类”(Post-humanity)的社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正在大行其道,您认为我们的教育或课程需要对此做出改变以适应它吗?
派纳:当然必须去适应。我认为我们需要去研究这样的境况:为何会有这么一个新概念出现?它为何重要?如果我们把世界作为文本来分析,这样的情况会对国际文本、历史文本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对于人类的新概念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所以我认为,课程理论与课程专家们更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并对这个话题做出回应。
杨:是的,让我们考虑国际的、具体的“文本”。中国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越来越关注高科技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政府大力提倡信息技术教育与信息意识的培养,这也是国际的趋势,譬如21世纪新技能的提出等等。
派纳:对于这样政策的制定,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是一种对于课程的控制方法,并且限定了讨论的边界。它暗示我们,教育天然地要为经济服务。但是我认为教育是独立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甚至就是学习和理解自我,而非为新经济和新技术作准备。教育并非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有竞争力,或者使得我们成为雇主希望变成的样子。这个话题在美国也有很大的争议。在政府层面,他们知道雇主的要求,为之所做的准备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对大学的控制方法。当然,在这方面,公立和私立大学在课程管理和商业参与方面不尽相同。另外,在大学层面,让每个学生变得更加专业,让开设的课程更加专业化,这确实是非常“经济”的做法。
杨:您对美国大学教育提倡的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Mathematics)理念有何见解?
派纳: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我觉得目前他们提倡的只是STEM,没有A,没有艺术教育。在他们看来艺术并不重要,这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并不在乎艺术、美术、音乐、诗歌,我们唯一在乎的就是赚取金钱。
杨:如此说来,您似乎对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好感?
派纳:是的,这里没有自由市场,只有非自由市场。少部分人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这是一个垄断的资本市场。
杨:您知道,我本科所学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我还是相信自由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对政府的行为有不信任感,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让我们摆脱政府的控制。
派纳:我并不相信这点。就西方而言,政府和商业机构紧密合作,整个国家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大的“生意”。有一点我非常欣赏中国。就我在中国的课程研究经验来说,尽管我从未和他们分享过我对意识形态的观点,但我确实欣赏政府将国家和经济分开看待的态度。在美国已经无法这样了,在加拿大也只能是勉力为之。另外,就算市场是自由的,有“看不见的手”让我们摆脱政府的控制,但它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依旧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因为“看不见的手”总是将大多数人的东西交到少数人手上。
杨:是的,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深有感触。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国一些地方的学生放学后会在校车上完成作业,因为那里有家里提供不了的网络。
派纳:对。而且我还说过,要让孩子们远离网络。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网络会放大孩子的焦虑和紧张感,会起到示范效应,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自杀率的上升。
杨:您认为这是网络的责任吗,还是说这是学习和生活压力增大所导致的?
派纳:网络让事情更加糟糕,比如它鼓励人们上传暴力等充满负面情绪的图片。
杨:但是,您知道吗,上海家庭的网络覆盖率达到了95%,这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江苏省早就实现了的一个项目,就是让每一所学校都有网络教室。
派纳:哦,太糟糕了。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会比较糟糕。
杨:当然,有这个可能。我们这么做是想让学生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
派纳:是的,这就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在农村地区通过广播接受远程教育的原因。当时纽约的教师通过广播向农村的孩子讲授数学、化学等课程。所以,希望你们能取得好的效果。
杨:让我们从宏观转向微观领域。您知道,在如今的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充满了许多新科技的元素,譬如翻转课堂和慕课的流行。许多学者认为这将使得学习更有效率。
派纳:他们是怎么测定的?你相信吗?
杨:他们相信新技术的运用可以使老师更有效率地匹配学生的需求。
派纳:他们或许只是在做一项“生意”,以此获利。或许,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宿命”:技术成为了他们新的信仰,就像成为了他们原先所信仰的上帝一样。
杨:所以说您不相信科技可以促进学习?
派纳:不,我相信科技。对于特定课程而言,一些网站确实可以提供有用的、有趣的学习资源。但是就每一个微观事件而言,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由政府来力推这些可能是有危险的?
派纳:是的,我赞同这点。经费可以用在其他更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提高教师的薪水、缩小班级的规模、提升教师的经验等;另外,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费为教师创造更好的条件,譬如更舒适的休息室等等,让教师们的生活不要那么紧绷,而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和张华教授曾共同编著过一本书,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状况的,对于其中教师是怎样失去自我、怎样耗尽自我精力的部分,我感到震惊。
杨:让我们回到具体的课程。您觉得不同学科在面对科技进步时遭遇的问题一样吗?譬如数学、物理、化学与艺术等课程是否面临同样的境遇?
派纳: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不同学科是否都需要运用更先进的科技来进行教学?在北美和欧洲学界,有一种称为“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新兴学科,用信息技术的手法来处理人文问题。我曾听过我一位同事的演讲,他统计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他发现罗密欧使用这个词多过朱丽叶。这说明什么?我不太确定。我认为艺术、人文学科乃至人类的交流无法用数字来测算,对人类的某些行为与情感做统计也是没有必要的。总之,将新技术运用于所有学科,这是个很危险的趋势。
杨: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在中国,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也加入了新技术运用这个元素,鼓励乃至要求教师采用信息技术。
派纳:人类正处于日益科技化的世界中,技术占据统治地位。我认为我们很难跳出这样的境遇来感知和行动,这也是我觉得历史学科应当成为一门主要课程的原因。历史上至少有过不同于今天的境况,对于教学而言,过去的经验如影随形,想要摆脱非常困难。我因此提出了“再激活”(Reactivation)这一概念,引导学生“瞥见”其他时刻或可能的道路。
杨:是的,如您所说,“在别处”非常重要。我常常疑惑的一点在于,现在的西方教育界有一种声音,呼吁要学习中国的基础教育以及学生学习的方法。但是目前中国的许多课堂甚至还处于“前现代化”的程度,遑论“后现代化”的课堂了。许多学者认为,我们需要先达到教育的“现代化”阶段,譬如对数据的重视,高科技的采用,乃至民主精神,然后再走向后现代。但是有人则认为我们可以直接从“后现代”启程。
派纳:我并不认为历史是分阶段演进的,也不认为所有地区都要遵循同样的历史进程。就我所理解的中国而言,它是复杂和多样的,一些农村还处于前现代,但大城市已经拥有非常高的科技水平了。就民主来说,有一种非官方、非政府的存在形态,它发生在大街上,形成于人群中。另外,我们正面临后现代境遇,对所有事情都争论不休,外来者和本地人一样聪明和复杂。所以我觉得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杨:但是还有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拒绝接受别人的经验。比如,我们会说,别光盯着西方的课堂,他们也正遭受一堆问题的困扰。
派纳:确实,只用中国方式同样也会有问题。当然,不仅仅只有一种“中国式教育”,而是有许多种。不同地区的环境不同,课堂也不同。在我的研究领域中,我非常欣赏中国同行的一点就是,他们想了解西方,但会做出判断,辨别哪些是自己需要合作的对象,并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杨: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更本源地看待课程与科技的关系。现代课程诞生于管理时代,恰如加拿大籍日裔学者Ted Aoki所言,这是基于规划的课程。如果我们同意课程理论源于此,那么,我们的道路在何方?回到生活世界,还是走向美学和艺术?于我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派纳:确实是两难,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两难。通过理解它,知道它产生的原因,知晓它如何成为历史的,了解隐藏于其后的原因,我们就能找到超越它的经验,并对下一步行为做出建议。我理解你们可能处于的境地。我们的政府曾经对我们说:“走开,你们是麻烦制造者。”他们现在希望通过商业操作来解决问题,虽然也会失败,但人们沉迷于其中。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分理解这种两难。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工作会被这种两难所捆绑,当然,我们的力量也很微小。
杨:是的,在时代面前我们微乎其微。我想起了海德格尔曾经探讨过工具“在手”的状态,我的疑惑是: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现代社会都有工具和技术,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锤子在手的状态和现在拇指党的状态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派纳:我认为“在手”客体的改变会带来主体关系的改变,以及“在手”的变化。你可以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没必要成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事态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只有一点曙光,这就是我们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原因。但你可以有所作为,可以继续教学。我在高校刚入职的时候,有一次校长来听新教师的课并给出评价。但我没有因为校长来听课而做出任何改变,我依旧让学生以非常放松的姿态进行交流。我想,他能看出我在做什么:我正在用自己的声音、方法,让学生互相交流并沉浸在课堂中。
将教育和就业、经济状况联系起来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教育更多地关乎自我发展。当然,我觉得政府会很高兴看到今天的这种改变。按照我的理解,课程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不仅仅包括诸如语言、数学、艺术等在内的学校科目。当然,也要有一些正式的课程,来满足人们的具体需求。讨论课程其实就是讨论不停累加的教育经验,而不是限于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因为这些经验是互相交叉的。
杨:是的,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就像Ted Aoki曾经说过的,课程就像一座桥梁,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快速通过,而是在桥梁上凝视(Contemplation)、徘徊(Lingering)。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游戏与悠游的状态。我们常说要打开课程的“黑箱”,但是我现在愈发觉得打开的方式很重要。采用像医生那样打开病人腹腔的方式恐怕是不妥的,老实说,我倒是觉得“黑箱”是一种保护。
派纳:这个关于“黑箱”的说法,我很欣赏。
杨:说到“上手”,我最近正在思考身体和课程的关系,回到身体或许是件有趣的事情。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身体可能和西方观念不太一样,这或许是个理论的突破口。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体不仅包括自然的身体,也包括社会的身体和某种意义上超越的身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有时候甚至是以通过对一种身体的压制或削弱的方式来获得另一种身体的解放。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中国戏剧《牡丹亭》,在其中主人公因为生病而得以在梦中再续前缘。通过对自然身体的削弱,她暂时摆脱了社会身体的压制并使得超越的身体成为可能。因为,在汤显祖的观念中,至情即道。
派纳: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经验。我记得曾有一位美国作家在旅行至摩洛哥时患病高烧,他认为通过这段病痛的经历,我们得以理解自我,理解自我和身体的关系。对我来说,年轻时病患是我的朋友,而现在它却试图杀了我。
杨:最后向您请教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作为课程理论界的大家,您觉得课程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您曾经领导了课程理论的概念重建主义运动,您觉得下一个10年或20年,在课程理论界可能会发生什么?
派纳:我觉得这取决于不同国家,取决于在哪里提出问题。在美国,我看不出有什么能超越个人中心,这是一种身份政治。几乎所有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受到的伤害多过他人。他们呼吁保护个人权益,譬如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问题,这表明社会生活会受到极端政治的威胁。课程理论应当对此做出回应。我呼吁课程研究从个人政治转向伦理领域,希望人们可以超越对于“革命”的渴求。就我现在所在的加拿大而言,我还看不到具体的前景。如果我接下来几年没有退休,我将从事加拿大的课程理论研究,了解它的过去并描绘它的未来。我曾经编撰过一本关于国际课程研究的手册,张华教授在其中一个章节中曾描述并展望过中国课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对话手记(杨澄宇):我震惊于派纳教授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这样的体验不仅来自于和他的对话,也来自于对他著作的阅读和谛听他的授课。他不仅坦诚率真并善解人意,而且对同行的工作充满尊重。在课堂上,当他介绍Ted Aoki的思想时,我似乎感受到历史正拂过我的肌肤。对于我所请教的问题,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列出详尽的书单。温哥华是座美丽的城市,有着众多的华人和日益高企的房价;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城市的一角,面朝大海和雪山。在对话结束的时候,在回去的路上,我问派纳教授怎么看待去年其所在的教育学院排名上升到了世界前十的问题。他笑道:“因为我在这里啊,噢,不,我不知道原因,我是在开玩笑。”最后,我们谈论了生活。(2016年7月12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
(责任编辑 童想文)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1.011
威廉·派纳(William Pinar),著名课程理论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研究首席教授,概念重建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曾任国际课程研究促进协会主席,亦是其美国分会的创始人。2000年,派纳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04年其著作WhatisCurriculumTheory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颁发的杰出著作奖。杨澄宇,本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领域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现象学等;2016年出版著作《语文生活论》(教育科学出版社),此前亦出版过诗集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