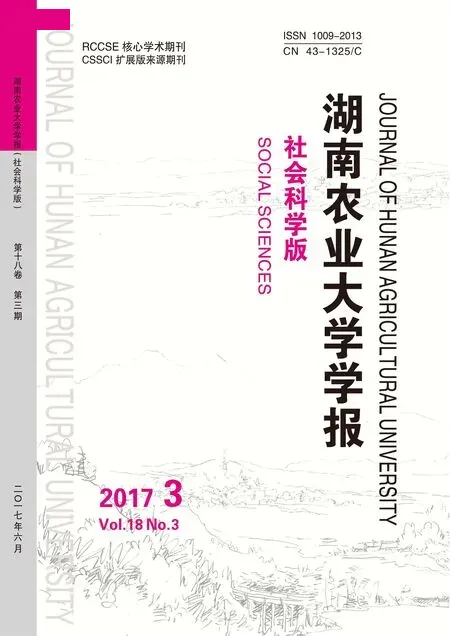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其模糊性研究述评——基于五项权利视角
2017-02-24刘灵辉
刘灵辉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其模糊性研究述评——基于五项权利视角
刘灵辉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1731)
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农村集体土地转为非农用时)和继承权(承包人死亡时)五项权利及其模糊性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在简要评述基础上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及其相关研究予以展望。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继承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土地产权不清晰。有人认为农地产权模糊性表现在所有权模糊和使用权模糊两个方面[1-2],而有学者则认为农地产权模糊体现在产权主体模糊、产权内涵模糊和产权处分模糊三个方面[3]。有学者根据产权理论将农地产权定义为农地控制权,认为模糊的农地产权相应地指农地控制权实际归属上的模糊[4-5]。一些学者通过扩展巴泽尔的(公共领域)概念揭示产权模糊化的本质,认为农地产权模糊性表现为法律歧视制造的“公共领域III”和行为能力受约束所形成的“公共领域V”[6]。
由此可见,学术界在农地产权模糊性的表现形式这一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现行法律政策比较明确的农地产权格局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是农地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显然,“三权分置”下的农地产权格局是以承包地保持农业用途不变为前提的。但在农地非农转用时,还必然涉及到农地发展权问题,即农地由农业用途的土地转化为其他用途,获得最佳回报的权利[7]。同时,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和发展权均属于承包人生前所面对的农地权利体系,在承包人死亡后,还涉及到农地继承权问题。因此,根据农地农用和农地非农转用、承包人生前和承包人死亡后两个维度,中国农地产权包含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和继承权五项权利。为了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模糊性及其表现的探讨,笔者现基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五项权利视角,对相关文献予以全面梳理,包括农地产权模糊性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应对措施,研析相关代表性观点和结论,以对当代中国土地产权结构模糊性进行反思性述评,进而对中国土地产权结构改革进行展望。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模糊性
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方面,韩立达等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有组、村和乡(镇)三级集体经济组织[8],但对于所有权主体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各个层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各自拥有多少土地产权份额、各个层级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围绕土地产权的关系为何等问题,徐宏潇和Peter Ho认为还处于法律政策上含混不清、实践上兼而有之的状态[9-10]。除集体经济组织之外,黄涛认为应以“董事制改造的村民委员会”[11],雷寰认为应以“法人化的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12]。然而,周昌洪认为村民委员会名为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上为准行政组织,它与上一级行政组织乡(镇)政府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土地名为集体所有,实际上成了乡村干部的小团体所有,有的甚至成为个别乡村干部的个人所有[13]。张千帆认为,集体所有不是村委会或任何村级组织所有,而是全体村民所有[14]。
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的成因,陈明认为是由于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同时被两个或三个集体组织享有,而没有明确到底谁是农村土地最终的所有者[15],孙鹏则归因于“集体”这一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和模糊性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载体[16],何·皮特认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上的不确定性是“有意的制度模糊”,政府在制定法规时有意地模糊了“集体”这个概念,模糊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最基本单位[17]。
所有权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法律政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这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造成“人人有权、人人无权”的局面,同时,农地所有权主体的不清晰很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多个主体对农村产权的交叉所有问题,这是造成我国大量出现侵犯农地现实权利享有者利益的根本原因之一。为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陈胜祥建议从具有“总有”性质的集体所有权之中派生出具有成员所有权含义的农户承包权,以此对集体所有权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可在实践中经由个人支配的产权形态[18],杨小凯、文贯中提出应实行彻底市场导向的改革——农地私有化[19-20],胡萧力则认为,要解决农村土地产权的模糊性,私有化并非唯一解决方案,更非现实的方案,进而提出“双层制集体所有制结构”以实现集体所有制清晰化[21],李自成建议实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多元化改革,建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级土地所有制[22],王金红认为未来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形式是“集体所有、农民永佃”[23],然而,李维庆认为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24]。
二、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模糊性
学术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存在较大争议。谭玲认为承包权是一种产生于所有权而又相对独立于所有权的一种权能[25]。肖鹏认为,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的认识,关系到如何规范土地承包权的概念和内容,也关系到如何将土地承包权纳入现有的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因此,土地承包权的权利性质界定不清,会影响到土地承包权的权利内容及权能实现,并直接影响着“三权分置”下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之间的权利格局。
对于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的争议,有“成员权说”“物权说”“综合权利说”与“期待权说”之争。张占斌等研究认为,土地承包权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的权利,并且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有[27]。王景新认为我国农民土地承包权实际上是集体成员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综合体现,承包权即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这项权利是由习俗逐渐成为法律的[28]。刘灵辉等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在行使所有者权利发包土地时,农户依法享有承包土地的资格[29]。朱广新认为承包权实际上是成员权在土地承包上的一种具体化,是土地经营权取得的一种中介[30]。刘守英研究认为承包权是其社区成员权在家庭承包制下的实现方式[31]。持“物权说”的学者却认为承包权是一种物权。张力等指出将承包权界定为单纯的权利能力或者资格的观点混淆了承包权与农民身份,也无法实现承包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承包权理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是一项独立的物权,性质也为用益物权[32],然而,邓大才通过对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本质和特征分析,认为土地承包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性质,但是这一物权性质一直难以得到落实[33]。朱继胜研究认为,土地承包权既非“成员权”亦非“物权”,而是当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立土地经营权,将土地交给他人利用时,其占有、使用权能受到土地经营权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4]。一些学者持“综合权利说”,如潘俊认为土地承包权主要包括“承包地位维持权、分离对价请求权、征收补偿获取权、继承权、退出权等,其中承包地位维持权是最重要的身份性权利,是其他财产性权利的基础”[35]。一些学者持“期待权说”,如丁关良研究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种期待权,在发包前或继承、转让、互换前,只有可能性而不具备现实性[36]。
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模糊的成因,管洪彦等认为是将“农户承包权”的误读导致了对“三权分置”的内涵产生误解,以至于认为“农户承包权”是异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创概念[37]。朱继胜研究认为,对于土地承包权的性质有“成员权说”和“物权说”之争的原因在于,前者之所指为土地承包权Ⅰ,即集体成员承包土地的资格,后者所指为土地承包权Ⅱ,即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土地经营权后的权利状态[33]。陶钟太朗等研究认为,“农户承包权”的二元性使其在不同的三权分置模式下,或者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或者表现为集体成员权(成员权)[38]。
为清晰界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性质,陈朝兵提出从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入手,将土地承包权的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并明确承包权的主要权利内容,主要包括占有权、收益权、继承权和退出权[39],肖鹏研究认为,“三权分离”后无法说明和体现土地承包权的内容,是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难点所在,因此,应当围绕农户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同一地块的权利,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权包括持续承包、继续承包、优先购买和补偿请求等权利内容[26]。张守夫等研究认为,“三权分置”后,禁止承包权流转作为过渡性政策是土地制度改革的近期战略目标;但是,从长远的战略趋向看,承包权不可能让农民永远带进城市不变,当中国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时承包权最终可以流转[40]。
三、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模糊性
土地经营权作为农民可以依法处置的一项用益物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刘灵辉研究认为,经营权是指农民在承包期内对承包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及部分处置的权利[41]。如果处于核心地位的土地经营权都异常模糊不清,那么对于农民流转权利的意愿、农地权利的市场优化配置等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权利主体方面,李伟伟研究认为,在土地未流转的情况下,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是“合二为一”的,权利主体都是农民,在土地发生流转的情况下,经营权的主体则是第三方经营者[42]。然而,赵鲲认为在共享土地经营权形成的规模经营中,承包农户并没有完全让渡土地经营权,而是通过合同约定方式与新型主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分享[43],胡振华等还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也应通过“三权分置”获得一定程度的经营权[44]。在经营期限方面,James Kai-sing Kung et al研究认为,农民所持有的农地使用权缺乏预期的稳定性且具有不确定性[45]。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然而,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下农民享有的经营权期限并不确定。李凤梅认为,农民的经营期限存在着无限年[46],胡昕宇等认为农民的经营期限超过现行30年但不高于70年[47],张红宇等认为农民的经营期限可参照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的规定,将土地承包周期为70年[48]。在经营权指向地块方面,孟祥仲等认为,虽然《物权法》规定承包期届满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但其并未明确规定农民在什么情况下有续包多少土地的权力[49],同时,林旭认为,续包的土地是否是现在承包的土地亦不明确[50]。在经营权的处分方式方面,农民对经营权的处分除法律法规允许的流转权之外,农民是否可以抵押经营权、选择有偿退出方式完全让渡经营权都尚未在法律层面得到体现。同时,鉴于承包权和经营权的紧密相关性,经营权的处分是否会连带地影响承包权也尚不明确,尤其在土地转让时,史卫民、袁震认为转让的法律后果使原承包人完全退出承包经营关系,也即转让会造成农民承包权的丧失[51-52],而丁关良等认为转让是保留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在承包期内将部分或全部权利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即转让不会对农民承包权产生影响[53],朱广新则认为转让可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最终丧失对农村土地的权利,或者至少造成其在剩余承包期限内丧失对农村土地的权利,即承包权丧失和承包权不丧失均有可能[29]。
关于经营权期限的模糊,杨久栋等认为,“长久不变”是具有指引方向功能的政策性语言,要转变为准确表述、便于执行的法言法语,就必须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期限[54]。然而,现行法律政策并未对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与经营权的期限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规定。关于经营权指向地块的模糊,刘灵辉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现行承包关系向下轮承包过渡时政府和集体采取何种方式让农民的承包关系得以延续这一问题做出详细规定,那么集体在实际操作中就存在至少两种可能性:第一,维持上轮承包地位置、面积等不变,单纯地延长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期限。第二,届时集体按各户享有承包资格的人数再进行一次土地发包[55]。关于经营权的处分方式方面,丁关良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抵押权的客体有动产和不动产。关于经营权债权抵押的“创新”违背了大陆法系“债权不得单独抵押只能质押”的国内外立法例[56]。因此,债权不能抵押,只能成为质押标的物。关于经营权的处分是否会连带地影响承包权方面,蔡虹认为,目前农村土地转让大多是农户间自发进行的,采取口头协议进行土地流转的仍然不少,大都没有通过签订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便存在为数不多的书面流转协议,大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确定等问题[57]。
对于明晰集体土地经营权的对策建议,刘振伟指出,三权分置关键是土地经营权定性[58],赖丽华认为“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权利法律制度构建,重心在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逻辑结构与现实国情,将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独立出来,构造物权化和债权化并置的二元农村土地经营权制度[59],李国强认为,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土地经营权应与土地所有权权能意义上的使用权区分开,将其作为法律制度创制的新的私权[60],张毅等指出,经营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和入股方式流转条件下属于债权性质,在转让和互换流转条件下属于物权性质[61]。关于经营权的期限,刘灵辉认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土地承包期的“长久”性可以通过“法定承包期届满+自动无偿续期”来实现[62];关于经营权指向地块,李洪波认为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彻底锁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分配、分割和调整[63],刘灵辉认为,应完善《土地管理法》和《农地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农民享有的承包地不再打乱重新再分配,按照“长久不变”的政策单纯采取延长土地承包期[64]。在经营权处分方式方面,陈朝兵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内容主要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其中,处分权包括入股权和抵押权等[39],陈锡文也强调,在原来“两权分离”模式下,农民对承包地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没有处分权,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抵押、担保的,但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后,“三权分置”模式下则允许入股、抵押和担保[65]。关于经营权转让对承包权的影响,刘灵辉指出,转让并不是转入方获得承包权的法定途径,承包权作为一种身份权事实上也不能转让[41]。
四、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模糊性
发展权涉及到农地非农转用的决定权和巨额增值收益的性质与分配,郭熙保认为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是农地产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权利[66],事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项目法人等多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要实现农地非农化转用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建立起“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必须消除农地发展权的模糊性。
集体土地发展权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权利来源方面,王海鸿等认为土地发展权源于对土地用途的价值选择[67],刘黎黎认为土地的发展权源于各方面因素对于农地进行非农业化所产生的巨大利益的获取[68],田莉等认为土地发展权源于空间管制[69],彭新万等认为土地发展权源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非农用地供应政策和城市化速度等因素[70],杨永磊认为农地发展权源于农地所有权,而非来自国家主权[71]。在权利归属方面,沈守愚、胡兰玲及吴郁玲等认为农地发展权应属于国家[72-74],张安录则认为农地发展权归农地所有者所有[75],王海鸿等认为受村集体这一所有权主体的模糊属性影响,可能导致土地发展权虚置,因此应该将土地发展权归属于集体土地的使用者——农民[67],藏俊梅等指出农地发展权的行使无论是给农民个人还是集体经济组织都不恰当[76]。丁同民提出农地发展权应该由国家、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分享[77]。在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理论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George、王万茂[78-79]主张“涨价归公”,郑振源[80]主张“涨价归私”,周诚、陈莹等[81-82]主张“私公兼顾”,晓叶认为,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分配应兼顾失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等主体的利益,在“市场之手”的调节下,可以在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确定合理比例,让国家、集体、以及具体的土地使用权人公平共有土地发展权[83]。
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模糊的成因,王永莉认为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制度设置[84],田园认为我国法律从未明确提出(土地发展权)这一概念,更没有涉及到土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85]。韩凌芬指出,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下我国并没有明确土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86]。沈子龙则将农村土地的权利主体“农民集体”模糊不清的定义当成引起发展权归属问题争论的源头[87]。
为消除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模糊性,朱一中等提出创设土地发展权是完善中国土地产权体系的重要内容[88],林坚等则认为我国应在法律上明确土地发展权概念,引入必要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使之成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89]。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程雪阳认为在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维护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建设用地指标管制”向“规划管制+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方式转变[90],彭錞建议摒弃土地发展权私有论和国有论之间的无谓争论,接受我国发展权国有的制度现实,并更新对其合法性基础的认识[91]。同时,在理念和制度上将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脱钩,使并不享有土地发展权的集体和农民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能获得增值收益。刘明明认为,我国土地发展权的实现应当采取土地发展权移转和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国情实现土地发展权利益的公平分享[92],柳斌等认为要明确农地发展权的权利归属,使之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权利存在于我国相关制度中。合理分割农地发展权收益,加大初次分配中农民所占有的份额,确定和完善二次分配中农民和农村集体的参与方式[93]。
五、农村集体土地继承权模糊性
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问题,理论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继承开始时点、继承人范围确定、继承方式、遗产份额划分等问题存在着巨大争议。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在法律政策上处于空白地带,但农业部已在全国10个县市区开展了土地经营权继承试点,未来土地经营权继承会在试点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放开。因此,深入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显得紧急而迫切。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的问题上,刘春茂、梁文书等、徐志珍等[94-96]对承包经营权继承持否定观点,而丁关良、张钧、郭明瑞[97-99]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开始时点上,顾昂然、刘保玉等认为,家庭中部分家庭成员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问题[100-101],韩志才则认为应以“农户”中个别成员死亡的时间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时间开始点[102],刘灵辉、周应江认为,只有在“绝户”的情形下才可能会发生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因为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只有该农户中的最后一名成员死亡时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如果农户的家庭成员为多人,其中一人(即使是户主)死亡,作为承包方的农户还存在,还具有经营管理承包地的能力,不发生继承问题[103-104]。李长健等则认为,在家庭发生死亡绝户问题时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继承,除非有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105]。在继承方式方面,刘凯湘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应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允许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也应承认遗赠[106],石胜尧则认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应实行特别制度,承包土地不应实行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107]。在继承人的选择和确定方面,董栓成认为应遵循“单嗣继承制”[108],梁慧星认为“只有与被继承人共同承包的人才能对承包地有继承权”[109],陈华彬认为“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继承人才享有继承权,其他继承人不享有继承权”[110]。在遗产份额划分方面,学界观点各异,张月等认为应采取共同继承[111],余红等认为应采取分别继承[112],而梁慧星认为可采取折价补偿和折价分割[113]。
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继承权模糊的成因,王廷勇等认为是因为现行法明确对承包权、经营权继承认可的内容十分有限,采用了“该承包人的继承人继续承包”这一模糊不清的表述[114],郑若瀚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的继承问题被立法悬置了[115]。即使抛开立法规范对于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模糊规定,单从“家庭承包”本身的性质而言,其继承问题便有着特殊的困难。由于建立在“户”的基础之上,因而它并不属于个人财产,只要不是全部家庭成员死亡,承包经营权主体就没有发生变更,财产分割亦无可能,继承也因此无法进行。
陈会广等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应是下一步权能深化与结构变迁中加以统筹考虑解决的[116]。适时启动法律修改程序,修改《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现行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有关规定,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能范围,调整制定法在继承利益上的适用。李圣军指出,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下,不能继承的承包土地肯定不是长久不变的,但绝对的继承也不是真正的长久不变,因此必须设定继承资格,主要是家庭存续自动顺延、举家迁移禁止继承、跨越社区禁止继承、五保户抚养人继承、经营权依附承包权等[117]。陈甦认为根据当前的改革与发展趋势,应当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作为制度选择方案,但须以土地承包费重估与交纳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与收回请求权制度作为配套措施[118]。
六、研究简要述评及展望
土地产权明晰化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学术界对农地产权的模糊性、模糊性产生的原因及如何明晰农地产权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大量的观点,但并未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的具体表现在整体上从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发展权和继承权五项权利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因此,学界应深入研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的具体表现及其深层次影响,着重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方面。一是加强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以及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产权边界的研究,二是研究如何重塑一个实体的、拥有法律人格的集体经济组织,三是对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及内部成员之间土地权利关系和性质进行研究。
(2)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方面。一是要对集体成员权获得与丧失的事由进行研究,二是开展成员权与承包权的关系研究,三是界定承包权的性质与权利内容。
(3) 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方面的研究。包括承包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下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的承包经营权衔接策略(单纯延长承包期还是打乱重新再分配),经营权的性质与权利内容,经营权处分的方式与法律后果。
(4) 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的研究。可细分为发展权的权源与归属研究,发展权交易与收益分配方面的研究。
(5) 农村集体土地继承权方面。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人范围确定的原则及方法研究,二是当继承人为2个及以上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遗产的划分方法,三是土地流转后的经营权和土地未发生流转的经营权继承实现差异问题,四是在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时,作为遗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处置方法等。
[1] 陈忠卫,王文举.农用土地产权模糊化及其流转思路[J].财贸研究,1994(6):46-48.
[2] 欧名豪.产权制度模糊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及改进[J].当代经济,2011(5):10-12.
[3] 王桢桢.透视农地产权的模糊与“锁定”[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6(1):58-62.
[4] 黄砺,谭荣.中国农地产权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吗?[J].中国农村观察,2014(6):2-13.
[5] 陈春霞,冯巨章.模糊产权的界定、成因及其绩效[J].乡镇经济,2005(1):11-13,32.
[6] 罗必良.农地产权模糊化: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J].学术研究,2011(12):48-56.
[7] Cynthia J.Nickerson,Lori Lynch.The effects of farmland preservation programs on farmland prices[J].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01,83(2):341-351.
[8] 韩立达,王艳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土地权属调整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6,30(4):21-27.
[9] 徐宏潇.转型期中国农地产权模糊性特征及其双重效应——评《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J].社会发展研究,2016(1):233-241.
[10] Ho Peter.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Land Ownership,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1] 黄涛.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之完善——兼评物权法草案第八十八条[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57):5-8.
[12] 雷寰.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权益与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研究[J].经济界,2005(4):92-96.
[13] 周昌洪.贵州省思南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实证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19-21.
[14] 张千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困惑与消解[J].法学研究,2012(4):115-125.
[15] 陈明.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困境与出路[J].现代经济探讨,2014 (11):21-25.
[16] 孙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7.
[17] 何.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林韵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8] 陈胜祥.农地“三权”分置的路径选择[J].中国土地科学,2017,31(2):22-28.
[19] 杨小凯.中国改革面临的深层问题——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杨小凯、江濡山谈话录[J].战略与管理,2002(5):1-5.
[20] 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1] 胡萧力.模糊的清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再建构[J].法学杂志,2015(2):133-140.
[22] 李自成.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J].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2004(5):80-82.
[23] 王金红.告别“有意的制度模糊”——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核心问题与改革目标[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13.
[24] 李维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及变革方向[J].中州学刊,2007(5):42-44.
[25] 谭玲.论土地承包权的性质[J].社会科学研究,1986(4):29-32.
[26] 肖鹏.土地承包权初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1):118-125.
[27] 张占斌,郑洪广.“三权分置”背景下“三权”的权利属性及权能构造问题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1):29-37.
[28] 王景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9] 刘灵辉,陈银蓉,成楠.土地征收对承包权的影响与补偿研究[J].资源科学,2011,33(2):315-321.
[30] 朱广新.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政策意蕴与法制完善[J].法学,2015(11):88-100.
[31] 刘守英.土地制度与农民权利[J].中国土地科学,2000(3):1-9.
[32] 张力,郑志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再分离的法制构造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5(1):80-81.
[33] 邓大才.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变革及制度选择[J].东方论坛,2000(4):67-71.
[34] 朱继胜.论“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J].河北法学,2016,34(3):37-47.
[35] 潘俊.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权利内容与风险防范[J].中州学刊,2014(11):67-73.
[36] 丁关良,田华.论农用地物权制度的选择——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名称的存废[J].中国农村经济,2002(2):25-32.
[37] 管洪彦,孔祥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内涵与表达思路[J].江汉论坛,2017(4):29-35.
[38] 陶钟太朗,杨环.农地“三权分置”实质探讨—寻求政策在法律上的妥适表达[J].中国土地科学,2017,31(1):64-72.
[39] 陈朝兵.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功能作用、权能划分与制度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4):135-141.
[40] 张守夫,张少停.“三权分置”下农村土地承包权制度改革的战略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7(2):9-15.
[41] 刘灵辉.农村土地内部产权关系解构下的征地补偿标准研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2,29(4):101-107.
[42] 李伟伟.“三权分置”中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及权能[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5):54-57.
[43] 赵鲲.共享土地经营权: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J].农业经济问题,2016(8):4-8.
[44] 胡振华,沈杰,胡子悦.农地产权二元主体视角下“三权分置”的确权逻辑[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8(4):120-130.
[45] Kung James Kai-sing ,Cai Yong-Shun.Property rights and fertilizing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Evidence from northern Jiangsu [J].Modern China,2000,26(3):276-308.
[46] 李凤梅.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之立法探讨[J].国土资源情报,2011(9):22-25.
[47] 胡昕宇,韩伟.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若干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101-105.
[48] 张红宇,王乐君,李迎宾,等.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若干问题[J].当代农村财经,2014 (6) :21-24.
[49] 孟祥仲,朱健.目前法律框架下农村土地产权界定的难点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8(3):97-100.
[50] 林旭.农村土地产权界定的困境与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08(6):88-94.
[51] 史卫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完善[J].现代经济探讨,2009(5):62-65.
[52] 袁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之法理分析[J].河北法学,2011(8):83-90.
[53] 丁关良,陈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J].中共长青市委党校学报,2004(12):17.
[54] 杨久栋,苏强.农地产权“长久不变”的法律创新及其实现[J].农业经济问题,2015(4):27-31.
[55] 刘灵辉.农地使用制度不确定性与水库移民安置区利益冲突及整合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5):62-65.
[56] 丁关良.家庭承包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乱象剖析和法律规制研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 (6):28-33.
[57] 蔡虹.转型期中国民事纠纷解决初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8] 刘振伟.三权分置关键是土地经营权定性[N].东方城乡报,2015-11-26.
[59] 赖丽华.基于“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二元法律制度构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112-118.
[60] 李国强.论农地流转中“三权分置”的法律关系[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6):179-188.
[61] 张毅,张红,毕宝德.农地的“三权分置”及改革问题:政策轨迹、文本分析与产权重构[J].中国软科学,2016(3):13-23.
[62] 刘灵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与实现形式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107-116.
[63] 李洪波.关于“长久不变”几个关节点的分析与思考[J].农村经营管理,2010(11):23-25.
[64] 刘灵辉.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长期补偿机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4):141-148.
[65] 冯华,陈仁泽.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不能突破[J].农家参谋(种业大观),2013(12):24-25.
[66] 郭熙保,王万珺.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J].河南社会科学,2006,14(4):18-21.
[67] 王海鸿,杜茎深.论土地发展权及其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创新[J].中州学刊,2007(5):79-82.
[68] 刘黎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发展权研究——以长沙市洞井镇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13.
[69] 田莉,姚之浩,郭旭,等.基于产权重构的土地再开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地方实践与启示[J].城市规划,2015(1):22-29.
[70] 彭新万,崔苗.我国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实现路径的理论与策略分析——农民、农村集体与国家分享视角[J].求实,2015(11):76-81.
[71] 杨永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机制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2.
[72] 沈守愚.论设立农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J].中国土地科学,1998,12(1):17-19.
[73] 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J].河北法学,2002,20(2):143-146.
[74] 吴郁玲,曲福田,冯忠垒.论我国农地发展权定位与农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J].农村经济,2006(7):21-23.
[75] 张安录.城乡生态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的机制与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经济,1999(7):43-49.
[76] 藏俊梅,王蓓,薛诗蓓,等.农地发展权在土地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研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9,26(5):101-104.
[77] 丁同民.将农地发展权引入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思考[J].中州学刊,2014(1):56-60.
[78] 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A New and Condensed Edition [M].London:The Hogarth Press LTD,1979.
[79] 王万茂,臧俊梅.试析农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6,23(3):8-11.
[80] 郑振源.征用农地应秉持“涨价归农”原则[N].中国经济时报,2006-05-08.
[81] 周诚.我国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分配的“私公兼顾”论[J].中国发展观察,2006(9):27-29.
[82] 陈莹,谭术魁,张安录.武汉市征地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测算[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12):16-21.
[83] 晓叶.土地发展权何去何从——从闲置土地说起[J].中国土地,2016(2):1.
[84] 王永莉.国内土地发展权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07,21(3):69-72.
[85] 田园.农村土地资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启示[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4):117-121.
[86] 韩凌芬.基于农地征用制度视角下的土地发展权探析[J].台湾农业探索,2009(5):24-26
[87] 沈子龙.土地发展权中国化的路径选择[D].杭州:浙江大学,2009
[88] 朱一中,杨莹.土地发展权:性质、特征与制度建设[J].经济地理,2016,36(12):147-153.
[89] 林坚,吴宇翔,郭净宇.英美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启示[J].中国土地,2017(2):30-33.
[90] 程雪阳.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J].法学研究,2014(5):76-97.
[91] 彭錞.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国问题与英国经验[J].中外法学,2016,28(6):1536-1553.
[92] 刘明明.论我国土地发展权的归属和实现[J].农村经济,2008(10):94-97.
[93] 柳斌,张海莹.我国农地发展权研究综述[J].农业考古,2016(6):115-120.
[94] 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95] 梁文书,黄赤东.继承法及其配套新解新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96] 徐志珍,张立.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可继承性[J].广西社会科学,2009(4):69-71.
[97] 丁关良.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主要分析依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30.
[98] 张钧.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法律问题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2):74.
[99] 郭明瑞.也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J].北方法学,2014(2):17.
[100]顾昂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R].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5):359.
[101]刘保玉,李运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探析[J].北方法学,2014,8(2):5-14.
[102]韩志才.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若干探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7(3):118-121.
[103]刘灵辉,胡小芳.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研究[C].湖北省土地年会论文集,2005:335-339.
[104]周应江.家庭承包经营权:现状、困境与出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05]李长健,陈志科,蒋诗媛.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继承问题探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1):60-63.
[106]刘凯湘.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J].北方法学,2014,8(2):20-28.
[107]石胜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流转的依据与对策[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1):27-30.
[108]董栓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优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09]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10]陈华彬.物权法原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111]张月,曲佳敏.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的探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5):15-16.
[112]余红,刘玉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探析[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4(4):26-30.
[113]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第二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14]王廷勇,杨遂全.承包经营权再分离的继承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17(1):35-42.
[115]郑若瀚.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逻辑、原则与制度选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3):11-16.
[116]陈会广,陈真.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基于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1):68-74.
[117]李圣军.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J].江汉学术,2017,36(1):67-73.
[118]陈甦.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机制及其阐释辨证[J].清华法学,2016,10(3):57-71.
责任编辑:黄燕妮
A literature review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ambigu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rights
LIU Linghu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five land rights and their ambiguity. The five land rights include ownership, contracting right, management right, development rights (when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s use is changed from agriculture to non-agriculture) and right of inheritance (when the contractor died). On the basis of brief comment on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author forecasts related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rural collective land; ambiguity of property rights; ownership; contracting right; management right; development right; right of inheritance
10.13331/j.cnki.jhau(ss).2017.03.013
F321.1;D922.3
A
1009–2013(2017)03–0071–06
2017-03-24
2014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14SFB30029);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资助项目(ZYGX2014J 108);四川省软科学资助项目(2017ZR0176)
刘灵辉(1982—),男,河南伊川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为土地制度与政策。